蘇聯解體27年祭——一位蘇聯公共知識分子晚年的自我反思_風聞
逗你玩-2018-12-25 1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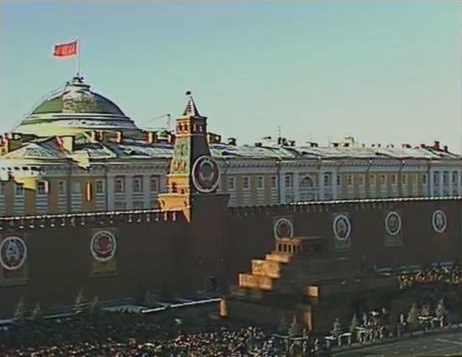
蘇聯解體27年祭——一位蘇聯公共知識分子晚年的自我反思
前言:
亞·季諾維耶夫(1922—2006),二戰蘇聯飛行員,戰鬥英雄。是蘇聯異議作家和持不同政見者。
在蘇維埃體制如日中天之時,他勇敢地對斯大林模式提出批評;
在漂泊和僑居西方之時,他對西方民主體制同樣持“詳加審查”態度;
當蘇聯解體、他再次挺身而出,批評激進社會和政治改革,抨擊西方化之弊,大聲疾呼珍視蘇維埃優秀價值觀念,重建共產主義思想體系。
這篇文章就是他在1994年的對蘇聯的再認識。
蘇聯時期是俄國曆史上的頂峯時期
——亞·季諾維耶夫訪談錄
維克多·科熱米雅科
“蘇聯時期是俄國曆史上的頂峯時期”
編者(指我國當時刊登這篇譯文的雜誌——引者注)的話:1994年7月1、2日兩天,《真理報》連續刊登了俄羅斯著名哲學家亞歷山大·季諾維耶夫接受記者維克多·科熱米雅科採訪的長篇記實。兩天的標題分別為:《我認為蘇聯時期是俄國曆史上的頂峯時期》、《俄羅斯正在被變成殖民民主主義的國家》。現摘譯如下:
記者:莫斯科一家新的出版社出版了您的兩本書:《共產主義是現實的》、《共產主義的危機》。第一本寫於1980年,第二本寫於1990年。在西方廣為人知,而在俄羅斯是第一次發表。這件事對您來説意味着什麼?
季諾維耶夫(以下簡稱季):説實話,我沒有期望過我的關於共產主義的書會在俄羅斯發表。現在出現了一種十分奇怪的形勢。前些年我的這些著作被認為是反蘇聯的、反共產主義的。現在共產主義似乎是被摧毀了,同樣是這些書,卻被認為是親蘇聯、親共產主義的。
記者:真是怪事,最大的怪事!
季:如果仔細研究一下,沒有什麼奇怪的。只不過對我的書的態度納入了意識形態和政治的軌道。而我既不是思想家,也不是政治家。還在1939年,我就確定了自己的生活方針:我有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記者:這就是説,當時在1939年,您已經有了這一公式?當時是十七歲嗎?
季:差不多。當時可能説法不同,但實質就是如此。我就是這樣確定自己作為一個科學的社會學家的立場。理想的社會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有。我接受生我的社會的現實性,並給自己提出了認識這個社會的任務。我想過,我曾經打算渡過一生的社會制度永遠逝去了,而這影響到我考慮和研究問題的性質。
記者:您是如何反斯大林的?
季:一個問題並不妨礙另一個問題。在心理上我是一個反斯大林主義者。後來,成年以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很自然重新作出評價。當然,現在我對當時許多問題的態度已經不同了,和十七歲的孩子時期的看法不相同了……然而我一生都十分關切共產主義,並且要繼續關切下去。
記者:為什麼您十分珍視您的書在祖國出版?
季:我是為西方讀者寫的。我到國外後,就確信那裏的人們對蘇聯社會的看法是十分荒謬的。於是我力求在科學理解的水平上向他們解釋,如何理解這個社會。
當然,我的書在這裏出版,我很高興。至少在這裏有人知道,有一個俄羅斯人還在70年代就分析了這個社會。現在罵共產主義輕而易舉。但是今天説我是共產主義辯護士的那些當時的智者和勇敢分子到哪裏去了呢?
書畢竟出來了。但是,很遺憾,是在一種很惡劣的形勢下出來的。如果現在要我作出選擇:在俄羅斯不發表我寫的任何一個字,而能因此保存我國原來的社會制度;或是與此相反。我寧可選擇前者。寧可我的書不出版,讓社會制度保存下來吧!
記者:這和您的思想相呼應:如果您知道“把蘇聯這隻船搖向何方”(其中您的書也幫了忙),你大概不會寫這些書吧。
季:不會寫。但是,既然已經發生了,那現在就給自己提出一些任務。告知俄羅斯人民和全世界,第一,改革前俄國的社會制度是什麼樣的,也就是由於改革我們失掉了什麼。第二,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第三,我們國家今天的狀況以及它對未來期望什麼。我是這樣理解今天自己對俄羅斯應盡的主要公民職責。
記者:我們能按順序來分析這些問題嗎?
季:好。先説蘇維埃制度是什麼樣的一種制度。所有的西方的蘇聯學、政治學、社會學,所有的西方的意識形態和宣傳,和我們這裏今天反蘇聯、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宣傳一樣。在俄羅斯,所有的意識形態和宣傳把我們的蘇聯時期評價為歷史上的一次黑色失敗,他們把蘇聯社會看成似乎是馬克思主義者臆想出來的一種什麼東西,而布爾什維克則用武力和欺騙強加於人們。
我堅決反對這種説法,我認為蘇聯時期是俄國曆史上的頂峯時期。我不是共產主義的辯護士,但我認為這個時期是真正令人驚歎不已的時期。**隨着世紀的消逝,後人將十分驚奇、十分讚歎地研究這個時期,將驚訝於在處於十分困難條件下的國家如何在很短的時期內做了那麼多的事。**是的,也做了許多不太好的事,也有過犯罪、失誤和令人失望的東西。但是,不管怎麼説,這是俄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時代,是人類歷史上最最壯觀的現象之一。
我認為我們的革命是偉大的革命。只要舉出我們粉碎了世界上最有實力的軍隊——德國軍隊這個事實,就足以令人信服地證明這是多麼了不起的表現。儘管在西方現在極力證明,似乎是美國人和英國人取得了勝利(而我們似乎不相干),甚至説似乎是斯大林而不是希特勒發動了戰爭……
西方的和親西方的宣傳有一個任務:盡一切力量詆譭我們的這個時代,貶低它,不惜一切手段破壞它的美好形象。然而它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成果。
記者:但是它是俄羅斯歷史的繼續嗎?
季:當然是,我認為俄國曆史的斷裂不是發生在1917年,而是發生在現在。正是現在,時代聯繫斷裂了!而在1917年之後,俄國曆史是正常地繼續發展。要知道**俄國社會從一開始就屬於依靠國家、政權和管理的力量從上而下地把廣大人民羣眾組織成一個統一的整體這種類型的社會。**這是由我國的一些特點決定的。如它幅員廣闊、自然條件、居民分散、民族眾多、人的物質條件、歷史傳統等。共產主義社會發展了在蘇聯具體條件下什麼東西最合適的這種觀點。當然,在把人們組織起來的同時,整個政權限制了個人的東西。
記者:您認為蘇聯社會哪些長處最為寶貴?
季:我不提出估價。只是指出某些特點。仍然是國家的具體條件決定了這些特點的價值。
例如,**所有的居民聯合成一個集體。**形成蘇聯的俄羅斯民族和其他民族熱愛集體生活,甘願把“我們”置於大寫的“自我”之上。這種集體生活就是這樣得以發展。
沒有失業者。有保障的勞動,有保障的教育,醫療服務……難道這還少嗎?我們的革命向人們揭示了富有幻想的前景。其中最宏偉的前景,就是文化為我們敞開了。從社會的最下層開始,我們完成了向世界文化高峯的巨大沖刺!消滅文盲是令人難以置信的躍進。如此慷慨地把文化和教育給予我們好幾代人,這是從未有過的。
舉一個例子,就説生活水平吧。我的家庭是科斯特羅馬省一個偏僻地區的多子女家庭。一個哥哥是工程師、工廠廠長,另一個兄弟是上校,我是教授,其他成員也都是自己事業的行家能手。
再過許多年,俄國人會感到他們失掉了什麼。一個人不只是靠麪包活着。牛仔褲和口香糖也將不是幸福。我們所失掉的寶貴東西比我們得到的東西要高得無比。最主要是我們的制度保證了生活目的的明確性和對未來的信心。制度的這些特點,對世界各國來説,成了令人神往的榜樣。
記者:在我國革命的影響下,各國勞動人民也有許多收穫。
季:我認為,這在當時是盡人皆知的。而今天卻成了小心謹慎隱瞞着的事實。正是在十月革命之後,西方才第一次真正談論關於社會權利……
總之,如果説到蘇聯領土上的廣大居民階層的利益,那為他們所做的事多得令人難以置信。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社會、沒有一種社會制度能為廣大人民羣眾做到這種程度。
記者:並且這是在很短的時期內完成的,還考慮到一場大的戰爭……
季:所以我們並沒有陷入黑色的失敗,沒有用武力強加人們“什麼”,而完全是自然產生的社會制度,它有深刻的歷史和人的根源。它的優越性值得我們認識再認識。
記者:現在談第二個問題: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
季:有一種大家都知道的看法:共產主義制度的垮台是由於內在的弱點、矛盾和無能。西方宣傳的基本立場(今天俄羅斯也採取了這種立場)就是如此。我認為這是一種很粗野的意識形態的謊言。
不是這麼回事!事實是怎樣呢?一般説來,對任何社會來説,危機是一種常有的現象。西方經歷了多次週期性的危機。馬克思寫了這個問題。我不是完全接受他的危機理論,但是總的思想是完全正確的。辯證的思想:危機是由一些原因產生的,而正是由於危機社會得以鞏固和富足起來。
因此,我認為:這種危機是可以克服的。蘇聯社會有克服的辦法——一定要改革!一定要有激烈的運動!我們有政治常識,有領導廣大人民羣眾的常識。如果一支隊伍倉惶逃竄,那任何一位聰明的統帥都無法把它改組好。這位統帥應首先制止驚慌失措。
我的思想就是如此。經受住危機,要有忍耐性。改革是必要的。然後,您要有信心,相信生活會多多少少穩定下來。另外,危機是可以緩和、減弱、消除的。
但是,當然沒有人會聽我的。我現在還認為:共產主義制度的生命過程被人為的中斷了。我還要強調一下:共產主義制度的生命的結束並不是通過自然的途徑,而是被人為地中斷了!
記者:是哪些因素起了促進作用?
季:第一個因素:在“冷戰”中西方佔上風——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第二,我們已經談到:蘇聯領導人沒有適時地開始改革方針,從而表現出罕見的有歷史性的愚蠢、真正的國務呆痴症。最後是變節因素。1985年,當戈爾巴喬夫剛剛出現在歷史舞台上時,我在一次講話中説過:大叛變的時代開始了。
記者:是在1985年嗎?
季:是的,是在1985年。的確,我還認為,人們會清醒過來。然而枉然。變節行為流行開來。西方沒有人期望過從蘇聯領導方面得到如此的贈禮。
記者:可能有人期望過。
季:想是想,但並不相信!……變節行為逐步成熟。當全部改革明顯失敗時,當權者在救自己的命和力求不惜代價抓權時,開始走上了變節的道路。一切都跟着來了,這已經成了自覺的叛變。
最主要是他們導至毀壞了我們的國家制度及其基礎——蘇聯。**要知道我們的國家體制不是通常的議會黨。**1954年我加入黨的行列,在聲明中大概是這樣寫的:**我過去認為,現在也認為蘇聯共產黨是整個蘇聯社會制度的基礎,是國家制度的基礎和國家的決定力量,它能保證國家的生存和進步。**當時有些人嘲笑我:嘲笑寫了一份誓言。實質上是説黨的主要使命。這是在革命成功之後的時期布爾什維克的一件很了不起的發明。很了不起的啊!於是有些人把這個黨破壞了。
記者:您所説的來自我國領導層的變節行為是指與西方的利益相吻合嗎?
季:歸根結底是這樣。沒有西方的幫助,他們控制不住政權。他們成了附敵分子,成了第五縱隊。別忘了,“冷戰”是真正新型的戰爭。它的思想家們早就懂得:在普通的戰爭中要想戰勝蘇聯是不可能的。因此開始了一場非同尋常的新型戰爭,這場戰爭的計劃制訂得極為周密。結果蘇聯所受的物質損失甚至大大超過它在偉大的衞國戰爭中的損失,就更不用説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損失了。
看來,蘇聯人民可能希望黨和領導人起來捍衞黨。而結果怎樣呢?他們拋棄了黨。國家的高層領導、知識精英、搞藝術的知識分子——它們統統都跑到敵人的營壘去。背叛了自己先輩的遺訓,背叛了那些為保衞祖國而獻出生命的人。
記者:西方是反對共產主義還是反對俄國?
季:兩者交織在一起。有一點很清楚:今天是單獨和西方鬥,就像在偉大的衞國戰爭時期一樣,俄國當時之所以能夠取得勝利,就因為它是共產主義強國。我敢擔保,就是這樣。如果沒有共產黨,俄國人早就是隻受三年教育並且去放豬。或者情況更壞——擦拭臉上的泥土。
記者:今天許多人都忘記了這一點。有人説,如果德國人勝利了,就可以喝巴伐利亞啤酒。猶太人也忘記了,過去他們的遭遇是怎樣的。
季:猶太人一個都不剩。而俄羅斯人在最好的情況下被消滅了三分之二……
總之,在我國出現的共產主義社會是自然產生的,是整個俄羅斯歷史的有機繼續和發展,但卻人為地、被許多因素和勢力有目的地糾合在一起而毀掉了。
“俄羅斯正在被變成殖民民主主義的國家”
記者:下一個問題,也很重要。現在的情況怎樣?你如何看待我國目前的狀況?
季:俄羅斯被置於死地了。從歷史的意義上説,是被置於死地了。有人對我大喊大叫:你怎麼把俄羅斯看得那麼不好,難道像你所説的那樣!我全身心地為俄羅斯擔憂、難過。但是事實更有説服力。我不想參加騙子們的大合唱,他們大聲歌頌似乎我們國家正在復甦的假象這個主題。是什麼樣的一種復甦呢?今天的俄羅斯是什麼樣子,——是歷史性的半僵死狀態。並且將使它達到僵死狀態。
記者:看來,你是第一次在談到關於蘇聯處於失敗狀況下可能出現的前景時,引用了“殖民民主主義”這個術語,今天這個術語用得很廣泛。
季:是的,是在三四年前,還是在8月事件(指819事件——引者注)之前。
記者:在1990年,你在西方出版的《共產主義的危機》一書中,有一章用了這個標題。
季:以前我在一些演説中就用了這個術語。我們今天所發生的事,可能不是明天,而是要經過兩、三代人才能充分顯現出來。這是置俄羅斯民族於死地的過程。曾經加入蘇聯的其他一些民族將各不相同,當然,命運也不佳。西方將在原始的水平上——封建的、民族的水平上給他們一點支持。某些民族現在已經落到什麼地步:那你就看看格魯吉亞或車臣吧。
而俄羅斯……關於它今天的狀況我是這樣説的:統治上層人物和知識精英們背叛了它,它被擊潰了,正在被變成一個殖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十分沉重地承受着有些人施加於我的祖國的東西。它成了全世界取笑的對象!住在西方,這你就看得更清楚。在那裏,我們的領導人、將軍們、知識精英們是如何卑躬逢迎、低三下四、巴結討好,這些簡直難以入目。這就是曾經是世界第二大強國,曾經戰勝了法西斯的偉大軍隊的代表人物嗎!
驅使俄羅斯所走的這條道路,並不是向前進。這條道路意味着倒退和瓦解,意味着想把國家倒退到矇昧時期。一位曾經是共產黨員的人遞過一張名片,在這張名片上我看到了雙頭鷹,這張名片對我來説是不祥之兆。我感到:一切都到頭了!
記者:而另一些人則認為這恰恰是大有希望的開端。
季:一切都十分奇怪地改變了!真正的愛國者被描繪成國家的敵人,騙子和偽善者成了真理的捍衞者。有人不願給像我這樣的人提供講壇,因為許多人從我的講話中感受到令人不安的、無情的真理。
記者:您認為我們的今天不光明,那明天呢?
季:您知道:還要黑暗。這就是將把俄羅斯引到悲慘境地的殖民民主主義的發展、深化和加重。當然,在歷史上可能出現各種偏斜和意外情況。我們住着,也説不定明天掉下某一顆彗星……
各種情況都可能發生。但是作為一個研究工作者,在考慮所形成的形勢、有影響的傾向和我所知道的一些社會發展規律性時,我應先着重研究以下情況:
將來,不應使俄國脱離整個國際關係。有人説:曾經有過韃靼——蒙古的枷鎖,我們挺住了!然而世界卻是另一回事。一定要關注當今世界的情況。世界是向着總體社會方面發展。可以説,這種社會正在形成,我們已經生活在總體社會之中。在世界上沒有一次重大事件是孤立發生的:在地球一角發生的重大事件必定在另一角產生反響。你看,存在多少國際組織、國際經濟帝國。一切都糾纏交織在一起。西方一體化。對俄羅斯的命運應從這種觀點來研究:俄羅斯在這種一體化社會中佔有什麼地位?
俄羅斯已經失去了獨立地發展歷史的可能性。只有共產主義使它具有這種可能條件。獨一無二的可能條件!現在這種條件已經喪失了——並且可能永遠喪失了。可能在人類歷史上這種可能性再也不會出現。
有人説:那中國呢?要知道,中國也被控制着。記住我的話:同樣西方要對中國做手腳。鎮壓了南斯拉夫,正置俄羅斯於死地,將來也會收拾中國。
有人説:但是還存在前蘇聯共和國的聯合傾向。是的。但是今後的聯合也在納入殖民化和西方化的綱領之中。開始是分離、分解——為了制伏,然後局部聯合,為了便於管理這塊殖民地。將來又聯合起來。在南斯拉夫將成立某種仿聯盟的東西,或是在那裏成立聯邦,在俄羅斯也是如此。但是,在俄羅斯卻事先粉碎了共產主義的潛在能力。即使在我國不能徹底清除共產主義(俄羅斯人一直仍然嚮往這種生活方式),那無論如何也會使共產主義傾向具有雜牌的形式。
記者:您看,在世界社會中為俄羅斯準備好了什麼位置?
季:可以肯定地説:**俄羅斯任何時候都不會成為像德國或英國、法國或美國這種類型的國家。**這是根據多方面的原因。而第一位和主要的原因是西方根本不允許俄羅斯站在和它們這些國家同一水平的位置上。一些主導的西方國家不允許這樣!在總體社會中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位置。要知道,在西方沒有權利平等的對手。在那裏,存在官位等級。
總之,只要您注意許多事實,你就會明白,在這個世界上,俄羅斯處於第二等、第三等的地位,即西方文明後院的地位。我們的未來,是一個殖民地國家,最好的情況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要知道俄羅斯民族已被置於絕種的道路上。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鼓勵酗酒。俄羅斯越來越分成單個的民族,這些民族是被人為地分離開,它們之間的糾紛愈演愈烈。怎麼就不想想,在蘇聯一開始就形成了人們的新型的具有歷史性的集體——統一的蘇聯民族。
記者:您不認為這是一種宣傳上的説法嗎?
季:當然,不認為。我自己生活在這個國家。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説不分什麼民族。例如,我們不可能掀起反猶太人運動。這一切都是人為地煽動起來的。這納入了“冷戰”的策略之中。
現在俄羅斯最偉大的民族精神被窒息了。也就是説,事實上已經使俄羅斯失去了民族基礎。老實説,今天我國努力喚起的民族主義現象,並不令我高興,我也無法接受。
記者:這表明您不同意那種認為正是在蘇聯國際主義精神窒息了俄羅斯精神的人們的觀點?
季:不同意。當時俄羅斯人第一次有可能在知識和精神發展方面被提到如此高的水平上。國家的其他民族也是如此。
記者:俄國今天所形成的條件不是有利於目前的某種改革嗎?
季:俄羅斯所陷入的狀況,我稱之為泥潭。政治泥潭,文化、精神和各種別的泥潭。沼澤地,在沼澤地裏沒有暴風雨。
記者:但是去年9—10月事件(指1993年10月葉利欽炮打白宮事件——引者注)叫作什麼呢?難道這不是風暴嗎?
季:不是,這是一次大的發作。有很大的歷史規模。
記者:您如何評價今天俄羅斯的反對派?
季:至於説反對派的特點……我認為:相同的反對派是沒有的。有許多各種各樣的政黨、集團、流派,至於説把它們合為一體,很遺憾,現在沒有可能,我沒有看見真正強有力的領袖人物。出現少數英雄人物,他們受到折磨,但是暫時他們還沒有形成氣候,不起決定作用。那些為了崇高而神聖的目的作出犧牲的人引起我不只是同情,我熱情讚頌他們。在西方,我常常想到他們。而今天仍然夜不能寐。他們的動機無比高尚。
我常常把今天我們的時代與衞國戰爭的第一階段作類比。我記得,在戰爭初期,我們被包圍,當時許多人説:“抵抗也無用,投降吧!”他們走到德國人那裏去,而德國人把他們全都打死了,另一些人則不同,他們説:“我們面臨滅亡,因此我們要突圍衝出去。”一部人衝出去了,得以繼續生存下來。
記者:我想清楚地瞭解您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我不止一次談到您的聲明:説您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然而您的第一篇學位論文似乎是根據馬克思的理論。後來您又寫到關於馬克思的天才。
季: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文化中最偉大的現象。我認為馬克思是人類歷史上最有天才的人物之一。我從來都是高度評價馬克思的。但是,我的確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原載《中流》199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