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圖爾特·班納:互聯網時代財產權的終結
反主流文化的領軍人物斯圖爾特·布蘭德(Stuart Brand)在個人電腦出現的早期階段就宣稱:“信息想要免費/自由。”(原文為“Information wants to be free.”“free”同時有“免費”和“自由”兩層意思。作者在文中隨即解釋了這裏的“free”既指免費,也指自由。——譯者注)免費,意指不須任何成本;自由,意指不為任何人所擁有。【1】這一名言某種程度上成為接下來二十年關注互聯網的知識分子們的座右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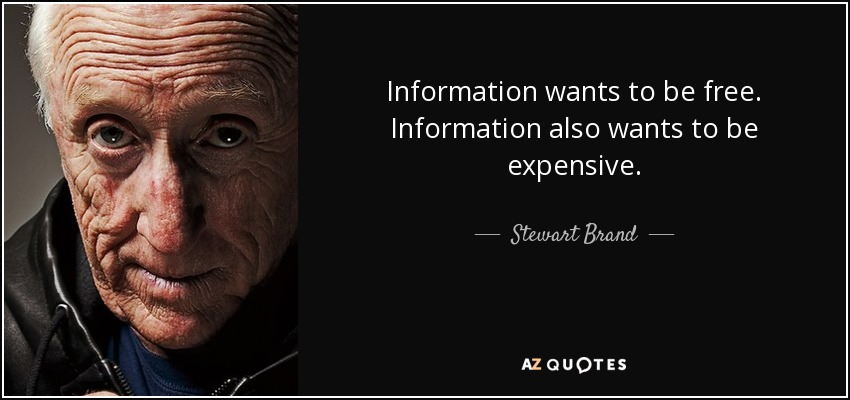
斯圖爾特·布蘭德
這些知識分子與布蘭德一樣感覺到數字革命將對財產權帶來深刻影響。以主張軟件不應有財產權而聞名的計算機程序員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表示贊同:“我相信所有大體有用的信息都應當是自由的。當我使用‘自由’一詞時,我指的不是價格問題,而是指複製信息的自由。”這一觀點由感恩而死樂隊(Grateful Dead)的前作詞人約翰·佩裏·巴羅(John Perry Barlow)進一步強調。巴羅堅持説:“未來必將獲勝;在網絡空間將沒有財產權。看哪!網絡共產主義。”
許多法律人提出同樣慷慨激昂但更加精準的主張。他們預測道:受到互聯網影響最大的財產權類型是著作權,著作權法將不得不大修,甚至可能被完全廢除。國會技術評估辦公室法律顧問羅伯特·科斯特(Robert Kost)回憶道,著作權是隨着印刷出版業的出現而誕生的。他解釋説,隨着數字媒體的出現,“信息正在恢復到其初始的、非財產的形式”,它“以比特流的形式跨國界流動”,而不需要有像書籍這樣的任何有形載體。他預測道,結果將是“著作權的終結”。
法學教授雷蒙·尼莫(Raymond Nimmer)和律師帕特里夏·克勞索斯(Patricia Krauthaus)表示贊同:“能使信息在全球範圍內移動的高速、互聯、大容量網絡的出現……戲劇性地改變了信息編纂、讓渡、審查和使用的方式。”他們預測道,由於這些變革,“著作權將變成過氣之物”,“著作權法的基本原理需要重新加以思考並進行修正”。
計算機使得信息可以被廉價而簡便地複製,互聯網則使之能一鍵傳送全世界。一些重大變革顯然正在發生。但信息真的想要免費/自由嗎?在網絡空間真的沒有財產權嗎?
所有權的邊界充滿爭議
在一段時間裏情況確乎如此,財產權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攻擊。20世紀80年代後期,廉價的數字化錄音技術,使一種曾經僅為一小撮邊緣藝術家熟識的音樂類型變得流行起來。這種音樂風格是由“採樣”(sampling)所創造的,也就是將現存唱片中的一些片段用在新的歌曲中。那個年代一些最具創新性的歌曲,就是利用早期作品的微小片段與新材料,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拼接成的密集拼圖。
在全民公敵樂隊(Public Enemy)的《與權力作戰 》(Fight the Power)中,一個4秒鐘的片段就包含了至少10個不同的採樣。野獸男孩樂隊(Beastie Boys)將200個採樣融入其CD《保羅的精品店》(Paul’s Boutique)的15首歌中。從1970年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的歌曲中截取的鼓手克萊德·斯塔布菲爾德(Clyde Stubblefield)的2秒鐘採樣出現在近200首歌曲中。
大量的這類採樣在新的背景中無法被識別出來。野獸男孩樂隊的亞當·約克(Adam Yauch)解釋道:“我們可能從唱片中截取一段短小的、不重要的聲音,將其速度調慢,並將之與其他30種聲音混雜在一起。”而在另一種極端情況下,一些採樣是從早期作品中截取長段的配樂音軌,易於辨認。
被用於採樣的原唱片基本上仍受到著作權保護,一些著作權人不樂於發現他們的作品成為他人賺取利潤的原材料。著名的新奧爾良公尺樂隊(the Meters)的吉他手裏奧·諾森特利(Leo Nocentelli)回憶道:“我曾經參加一個集會,集會上一個傢伙在電子琴上按了一下琴鍵,電子琴就響起‘哦!我的上帝!’像極了詹姆斯·布朗的聲音。這讓我很震驚。只要用手指按一下琴鍵就製造出詹姆斯·布朗的聲音,我覺得這是有問題的。”

公尺樂隊
公尺樂隊的歌曲後來被許多著名的説唱歌曲所採樣,但採樣者沒有歸認來源,也沒有給予任何補償。諾森特利抱怨道:“現在你最多能得到的就是:‘我在一張專輯裏聽到你的《娘炮的步伐》(Cissy Strut)’,然後拍拍我的背。不要只是拍拍我的背!——拍拍我的背,然後把錢塞到我的口袋裏。”
野獸男孩樂隊的《抱住它,揍它》(Hold it Now Hit it)中的一段採樣由“喲,勒羅伊!”這句説唱短語構成。這句短語截取自吉米·卡斯特(Jimmy Castor)1977年經常被採樣的一首歌。1987年,卡斯特起訴野獸男孩,該案可能是第一個與採樣有關的訴訟。卡斯特的律師布魯斯·戈爾德(Bruce Gold)解釋道:“我不否認人們將音樂片段拼湊在一起的創造性,正如我也不否認拼貼畫藝術家的創造性。但這並不改變這些人是否對其使用的原作品享有所有權利益的問題。”
未經許可進行採樣是違背正式的著作權法的,因為它侵犯了唱片和被採樣音樂作品所有者所享有的財產權。但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早期,採樣的現象非常普遍,關於採樣的許可卻是非常罕見的。代理嬉皮組合的律師勞倫斯·斯坦利(Lawrence Stanley)稱:“99%的鼓樂採樣是未付費的。所有人都從其他歌曲中截取鼓樂片段,在上面添加東西,放大它們,對它們做任何需要做的事情來製作自己的音軌。”【2】
音樂產業的實踐日漸偏離紙面上的法,因為法律是在大規模採樣不可能存在的時代寫就的。從一個角度看,採樣打開了一扇通往一種令人興奮的藝術努力形式的大門,這種藝術努力的可能性在若干年前還沒有人能想象得到。從另一個角度看,它使得大規模的竊取成為可能,而知識產權的觀念本身因此受到侵蝕。如果他人能夠複製和銷售歌曲中的一部分,那麼擁有對歌曲的權利又有什麼意義呢?
與此同時,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些最為著名的知識項目則根本不為任何人所擁有。這些項目中的第一個成果是GNU/Linux操作系統。這一項目由理查德·斯托曼於1984年啓動,並很快成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編寫和修改這一系統中的一部分的數千名志願者的成果。這些志願者包括芬蘭的程序員萊納斯·託伐斯(Linus Torvalds)。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萊納斯完成他的工作後,他的名字就被添加到操作系統的名稱上。十五年後,Linux成為微軟公司受財產權保護的Windows操作系統的一個重要的競爭產品。
2001年創建的在線百科全書“維基百科”,也是按照相同的原則(即全世界志願合作的作者共同創作)組織起來的。截至2009年,維基百科上已經有用超過260種語言編寫的1400萬篇文章,這些文章由大量志願者撰寫和編輯。沒有人因此獲得過分毫收入,但維基百科上科學詞條的準確性絲毫不亞於《大不列顛百科全書》。還有許多其他項目也沿着這一思路開展,包括古登堡項目(一個出版公有領域書籍電子版本的集體努力)、SETI@home項目(一項數百萬家庭計算機用户的合作,通過分析電波望遠鏡信號以搜尋地球以外的生命體)。
這些項目的成功都應歸功於互聯網。互聯網使得數量眾多的微小貢獻者能夠將他們的努力投向一個共同的目標。認真思考的觀察家們認為這種“同行生產”(“peer production”)——尤查·本克勒(Yochai Benkler)語——可能會成為未來的潮流。本克勒注意到:“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是一種更有效的集體行動實踐的出現。這種集體行動實踐是去中心化的,但它既不依賴於價格體系,也不依賴於協調的管理結構。”
互聯網提供了完成任務的第三種方式,信息的生產不是因為它可以在市場上銷售,也不是因為權威鏈條的上層命令其生產,而是生產者們自己未經協調的選擇的結果。在以這種組織形式為特徵的世界裏,財產的重要性將顯著降低。
也許對財產權最引人矚目的攻擊來自於納普斯特(Napster)軟件。納普斯特是1999年由西北大學的本科生肖恩·範寧(Shawn Fanning)發佈的音樂文件分享服務軟件。通過允許使用者複製儲存在其他用户電腦上的音樂文件,納普斯特創造了一個海量的、世界性的共享音樂收藏庫。在一年半之內,全世界的納普斯特用户就有數千萬之多。高等院校發現他們的網絡裏充斥着流動的音樂文件。唱片業對其未來感到擔憂,它將無法銷售任何產品,因為這些產品可以輕易地免費獲得。
納普斯特上共享的大部分音樂作品都是受著作權保護的,這就意味着大部分納普斯特用户使用該網站複製音樂時是在從事違法行為。然而,公眾的意見顯然與著作權法相左。在一個民意調查中,58%的美國人相信在線音樂分享總是或者有時是可以接受的;在對年輕人(即納普斯特最主要的用户)的調查中,這一數字則是69%。【3】
大部分使用者認為他們並沒有做錯什麼。而且,他們也非常清楚他們被音樂作品著作權人起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納普斯特興起的最大輸家,是唱片公司和持有最流行歌曲著作權的出版公司。他們不可能起訴數以千萬計的著作權侵權人。唱片產業曾經威脅到活頁樂譜產業的生存,廣播產業曾經威脅到唱片產業的生存,而現在文件共享則威脅到整個音樂產業的生存,因為著作權——整個產業收入的基礎——看起來已經躺在它的臨終牀上。
2004年,當谷歌宣佈其將掃描幾個最大的學術圖書館的書籍時,另一個挑戰來臨了。該公司打算使人們可以在線獲取那些已經不受著作權保護的作品,並允許搜索和顯示仍受著作權保護的書籍中的小部分文字內容。截至2009年,該公司已經掃描了超過1000萬本書籍。不同作者和出版商的反應各異。有些人歡迎這一項目,認為它提供了銷售更多書籍的機會。但也有很多人反對,認為這一大規模的複製構成了史上最大的著作權侵權行為。

谷歌複製所有這些書籍當然不是出於公共服務的目的。該公司打算銷售搜索頁面的廣告位。該項目的反對者認為,從書籍複製中獲得的這些收益應當屬於著作權人,而不是谷歌。谷歌打算放棄那些著作權人提出異議的書籍,但反對者們堅持認為,著作權法將獲得許可的責任施加在谷歌身上,而不是迫使作者和出版商承擔提出反對的責任。
谷歌很快發現它成為兩個著作權侵權訴訟的被告,一個是由作家公會(Author’s Guild)提起的,另一個則是由幾家主要出版商提起的。然而,全球性在線圖書館對很多人來説極富吸引力,而兩個訴訟的結果卻非常不確定,因此無法預測出版業的未來會是什麼模樣。互聯網看起來再一次侵蝕了知識產權的重要性。
數字時代財產飽受攻擊,而從來就不缺少對其原因的解釋。一種可能的解釋是,財產是一個最適用於有體物的概念,而正在興起的網絡世界則是由無實體的信息所構成的。約翰·佩裏·巴羅在他的《網絡獨立宣言》中宣稱:財產“以物質為基礎”, 它無法適用於網絡,因為“這裏沒有物質”。他總結道:“知識產權法無法被修補、改進或擴張,以包含數字化的表達。我們必須發展一套全新的方法來適應這種全新的環境。”
政治科學家黛博拉·哈爾伯特(Debora Halbert)表示贊同:當價值成為思想而非實物的一個屬性時,“舊的、破碎的知識產權制度的碎片可以被棄置,併為更適於信息時代的東西所取代”。根據哈爾伯特的觀點,“知識產權法是用來保護財產的,而法律的這一功能已經沒有必要存在”。
另一種理論是,財產權需要有穩定的所有權客體,因此無法與電子形式的信息流動性相匹配。最早研究互聯網法律後果的專家艾森·凱特什(Ethan Katsh)注意到:“沒有任何東西被固定在其他東西之上,詞語和圖像可以被移動和編輯,可以從屏幕上取下再放回去。”即使是傳統上的表達形式類別也失去了其意義。
凱特什問道:“既然數字信息是可轉換的,一個按鍵就可以使文本轉化成聲音,或者將聲音轉化成圖像,那麼任何傳統的指涉框架還有效嗎?儘管難以想象,但如果作品不再有固定的邊界,那會怎麼樣呢?”既然信息總是在流變中,還有任何“東西”可以被擁有嗎?凱特什問道:“在這種對信息的不斷變換的觀點中,所有權的邊界充滿爭議。
因此,擁有或佔有信息是沒有價值的,電子邏輯所鼓勵的使用和利用信息的機會才是有價值的。”早在1983年,當個人電腦仍是新興事物且互聯網僅為一小撮人知曉時,政治科學家伊錫爾·德·索拉·普爾(Ithiel de Sola Pool)就做出了類似的判斷。在一個文本總是不斷被複制和修改的世界裏,德·索拉·普爾預測道:“著作權的傳統觀念將變得過時。著作權植根於印刷技術”,在這一技術背景下文本是固定的。“電子出版並不類似於18世紀的出版作坊,而更類似於口耳相傳的交流方式,而著作權從未適用於後者。”
其他人則側重於虛擬世界複製的便利性,他們認為這將使財產的傳統觀念變得不可行。理查德·斯托曼評論道:“著作權制度是隨着印刷技術而興起的”, 對這一技術,大部分讀者自己無法使用。“數字技術比印刷出版更具靈活性:當信息具有數字形式時,你能輕易地複製並與他人分享。正是這種靈活性使其難與著作權制度兼容”。
隨着財產權價值一落千丈,它將變得越來越無關緊要。技術記者與投資人愛思瑟·戴森(Esther Dyson)論證道:“明顯的經濟事實是,即使你能向它們收費,複製件的價格也將一路走低”,因為當製作和發行複製件的成本如此之低時,複製件的供給將超過需求,後者受到消費者擁有的有限時間的制約。因此,“生產內容的產業必須創造出銷售複製件以外的方法來贏取利潤”。
在財產沒有任何意義的世界裏,為什麼還會有東西被生產出來?有些東西(也許數量還很多)可能因非金錢的原因被生產出來。尤查·本克勒預測“非市場的、非財產的動機和組織形式在原則上將對信息生產系統更為重要”。抱有商業動機的生產者將不得不銷售持續的服務,而不是傳統的產品。
《連線》(Wired)雜誌創始編輯凱文·凱利(Kevin Kelly)建議道:“有價值的東西將變成由複製件引發的、在網絡中結成的關係本身。當複製件的數量有細微增長時,關係的價值就如乘坐火箭般上升。”在納普斯特最流行的時候,記者羅伯特·萊特(Robert Wright)設想着音樂家可以如何利用這一商業模式。萊特説:“樂隊可以在網上免費發佈他們的音樂,然後通過在演奏廳或小型俱樂部表演獲得收入。但是,你會問,什麼樣的人會被吸引來從事音樂事業呢?那些熱愛音樂的人,那些為數並不少的真正的藝術家。
在一個沒有著作權的世界裏,吉米·亨德里克西斯(Jimi Hendrixes)和埃裏克·克萊普頓斯(Eric Claptons)照樣繼續玩爵士樂。”音樂產業已經有成功的範例:感恩而死樂隊允許歌迷免費錄製他們的演唱會,並通過銷售演唱會門票獲利。萊特總結道:“作為平衡,我期待後著作權時代能使名聲和收入在音樂家中間更均等地分配——並且,在這個進程中,使這些東西與音樂的品質成正比。這有什麼不好呢?”
20世紀60年代,計算機被理解為中央集權化的軍事—科學設施,但到20世紀90年代,計算機科學的社會學完全改變了,計算機成為20世紀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繼承人。【4】關於互聯網財產的討論充斥着歡慶共享、貶低私人權利訴求的烏托邦倫理。那些誇張地預測“財產死亡”的人可能已經將他們關於“什麼即將發生”的期待與他們關於“什麼應當發生”的偏好混淆在一起。但是,在網絡世界裏將沒有財產權,或者至少財產權將大量減少,這種觀點並不僅僅為那些天馬行空的思想者所持有。它為許多清醒的法律人和學者們所共享,他們看到周遭的財產權搖搖欲墜,於是從新的網絡化世界的本質中尋求解釋。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如此確定,互聯網意味着財產權的終結。聯邦法院法官弗蘭克·伊斯特布魯克(Frank Easterbrook)指出,沒有人能夠預知如何最好地治理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有些信息通過免費的方式分配是最佳的,但有些則最好通過付費的方式來分配。伊斯特布魯克建議道:“如果你以財產權為起點,你可以通過協商實現免費分配。而如果你以無財產權為起點,那麼當付費分配是最優模式時,你就很難採取最好的解決方式。”
法學教授尤金·弗洛克(Eugene Volokh)承認,互聯網上的信息可能是無體的、變動不居的,但“沒有理由認為作品的動態性與原有的著作權原則存在衝突。著作權法的基本思想——補償作者以使其得到創造的激勵——既適用於靜態作品,也適用於動態作品”。當商務部召集一個“知識產權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來解決相關問題時,小組的結論是,穩定的財產權對新作品的創造仍然是至關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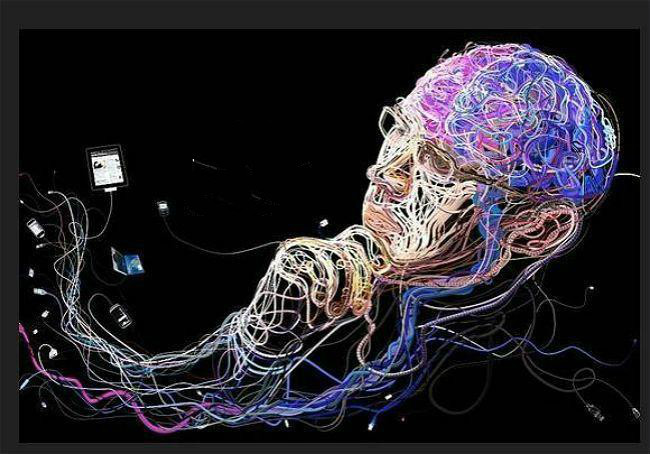
商務部報告稱:“現行著作權法僅需根據技術進步做出適當調整,以在洶湧而來的技術面前保持法律上的平衡。”財產權在互聯網環境下廣受嘲諷,但也許解決方案是進一步加強著作權。律師彼得·胡伯(Peter Huber)嗤之以鼻:“因為‘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或者因為‘信息想要免費/自由’,所有界定邊界的法律就將消失,這種預測絕對是錯誤的。”
也許,財產權將以難以預測的方式變革,在有些領域變得更強,在另一些領域則有所減弱。也許,過去使複製變得更加便利的技術變革,在不久的將來將使阻止複製變得更加便利,從而使著作權人能夠像在他們所習慣的有形世界中那樣主張在虛擬世界中的相同權利。所有人都同意,技術變革將對財產帶來影響,至於這種影響是什麼,人們卻少有共識。
信息也想索要高價(原文為“Information Also Wants to be Expensive”。)
採樣的黃金時代——或者黑暗時代,取決於您的立場——剛開始不久就終結了。第一個關於採樣合法性的法院判決是1991年由凱文·達菲(Kevin Duffy)法官所撰寫的。凱文·達菲法官是由尼克松任命的58歲白人法官,他對新技術帶來的藝術可能性沒有明顯的興趣。
這起案件涉及説唱藝人比茲·馬基(Biz Markie)的歌曲《再一次孤獨》(Alone Again)。這首歌包含了愛爾蘭歌手吉爾伯特·歐沙利文(Gilbert O’sullivan)的《再一次孤獨》(自然版)(1972年,這首歌在美國連續六週成為最暢銷歌曲)中的一段極易識別的鋼琴和聲。達菲一開始就寫道:“汝不應盜竊。”這也定下了下文的基調。下文徹底批判了這位法官所稱的“對法律和他人權利的漠視”。
在回應“採樣在音樂界是常見和被認可的實踐”這一論點時,達菲表達的僅僅是震驚:“這一著作權侵權訴訟的被告竟然試圖讓本庭相信,在音樂界,盜竊現象是猖獗的,因此他們的行為也是可以被原諒的。”他總結道:“這一論點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然後將該案移送美國司法部追究刑事責任。《再一次孤獨》被禁止發行。比茲·馬基將他的下一張專輯命名為《所有采樣都已被消滅!》。
這只是由一位初審法官所作出的一個判決,不過,隨後的案件都得出相似的結論。2005年,一個聯邦上訴法院判決認為任何未經允許的採樣,不管多少,都是對著作權法的違反。流行音樂已經改變了。音樂家們再也不能在一首歌里納入數十首歌的採樣,因為從大量著作權人那裏獲得許可既難操作又成本高昂。他們開始只在一首歌裏使用一個來源的採樣。在輝煌時期,採樣曾經成為一種新的拼圖式音樂,但現在它淪為對早期歌曲中為人熟知的片段的簡單複製。如果説這是技術與傳統財產觀念之間的戰爭,那麼,財產權取得了第一場戰役的勝利。
更多重新肯定財產權的主張接踵而至。在被認定為侵犯著作權後,納普斯特網站不得不關閉。新的公司嘗試過納普斯特軟件的幾種變體。卡扎(Kazza)和格羅克斯特(Grokster)不是將音樂文件集中存儲在它們的網站上,而是存儲在用户自己的電腦上。它們希望通過不直接參與複製活動而免於承擔侵權責任。格羅克斯特的律師論證道,由於它們僅僅生產了一種他人可以使用的工具,這類服務的提供者就類似於錄像機的生產者。
1984年,翻錄電視節目如同二十年後的文件分享一樣,是當時新的、充滿爭議的問題,最高法院判決認為,錄像機的生產者不因錄像機所有者的行為而承擔侵犯著作權的責任。但是,法院一致地拒絕了這一類比。戴維·蘇特大法官(David Souter)論證道:“分銷以促進侵犯著作權為目的的設備的一方,應當為第三方隨後的侵權行為承擔責任。”格羅克斯特和卡扎也被迫關停。
規模較小的文件分享服務一直在暗中繼續蔓延。唱片業不時向個人使用者提起訴訟,有時帶來令人震驚的結果。例如,2009年,因非法下載音樂,法院判令波士頓大學的一名研究生向四家唱片公司支付67.5萬美元賠償。不過,納普斯特案和格羅克斯特案使得文件共享技術的經濟影響大大受到限制。消費者由此轉向一些付費網站,如蘋果公司的iTunes網。在這類網站上,消費者可以通過支付較低的費用,獲得已獲著作權人許可的受著作權保護的資料。
與此同時,著作權本身也在逐漸強化。根據1976年的《著作權法》,著作權的保護期為作者終身加死後50年。對於法人作者,著作權的保護期為出版後75年。隨着20世紀接近尾聲,世紀初一些作品的著作權即將到期,其中包括一些仍能為權利人帶來可觀許可費收入的作品,例如迪士尼早期的動畫片以及喬治·格什温(George Gershiwin)的歌曲。
這些著作權人進行遊説,希望延長著作權保護期。遊説的結果是通過了1998年的《著作權保護期延長法案》(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 of 1998),將著作權保護期延長了20年,這同樣適用於1998年以前創作的作品。第一部有配音的米老鼠卡通片《汽船威利號》(Steam Wille)本來將於2003年進入公有領域,隨着著作權保護期的延長,直到2023年它依舊是迪士尼的財產。
埃裏克·埃爾德雷德(Eric Eldred)很快根據憲法對《著作權保護期延長法案》提出挑戰。埃爾德雷德是新罕布什爾的一位退休程序員,其業餘愛好是掃描已經進入公有領域的經典作品,並將它們放到互聯網上。著作權的延長意味着未來20年將沒有任何作品進入公有領域。埃裏克·埃爾德雷德想要掃描的其中一本書是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的《新罕不什爾》(New Hampshire)。如果沒有《著作權保護期延長法案》,這本書的著作權將在1998年到期。
埃爾德雷德的案件由法學教授勞倫斯·萊斯格(Lawrence Lessig)代理,他是著作權擴張的坦率批評者。萊斯格主張作者終身加死後70年的著作權保護期實際上等於無限期的保護,這與憲法上的著作權條款不一致,該條款授權國會制定“在一定期限內”的著作權法。他還主張,延長已經存在的作品的保護期將違背憲法著作權條款的前部,該部分規定著作權的目的是“推動知識的進步”。畢竟,延長的保護期將無法對在保護期延長之前就已經完成的作品起到任何激勵作用。
這一論點的弱點在於,在過去兩個世紀裏,對前幾部著作權法,國會都做了相同的事情:它曾經同時延長了新作品和已經存在的作品的著作權保護期。如果歷史實踐與憲法文本的文義解釋在憲法解釋中同樣重要,萊斯格和埃爾德雷德就面臨着難以逾越的障礙。這對最高法院來説就已經足夠了,它拒絕了埃爾德雷德的訴訟請求。著作權保護期限因此延長了。
著作權的強度也逐漸增大。媒體公司通過施壓要求對侵權人實施更嚴厲的懲罰,以打擊對知識產權的廣泛侵犯。這些努力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初見成果。在1997年《反電子盜竊法案》(No Electronic Theft Act of 1997)中,國會擴大苛以刑事處罰的著作權侵權行為的範圍 ,甚至像埃裏克·埃爾德雷德這種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業餘愛好者,也可能受到刑事處罰。1998年《數字千年著作權法案》(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of 1998)將製造和傳播用於規避反複製保護措施(這種保護措施越來越多地被加在音樂和視頻文件上)的軟件規定為犯罪行為。在20世紀80年代,著作權似乎被技術變革衝擊得奄奄一息,但到了世紀之交,著作權卻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大。
21世紀頭幾年的一系列司法判例加強了網絡空間中的其他類財產權。對網站進行未經許可的機器人搜索是否構成非法侵入(trespass)行為?2000年,在eBay訴其早期競爭者的案件中,法院回答説:是的。法院論證道:“如果eBay是一個有實體房產的拍賣場,它有權將場內的座位保留給潛在的競拍者,而拒絕沒有競拍意圖的個人(或者機器人)入場。”
垃圾郵件是不是非法侵入者?當英特爾公司一名心懷不滿的前僱員將他的滿腹牢騷以電子郵件形式發送給成千上萬的在職僱員時,英特爾起訴他非法侵入。加利福尼亞州最高法院以4比3的投票,認為這些垃圾郵件不構成非法侵入,但這只是因為它們沒有妨礙英特爾公司計算機系統的正常運作。法院清楚地指出,垃圾郵件有可能構成非法侵入,如果它過於頻繁,足以影響接受者計算機運行速度的話。域名是不是財產?在涉及一個極有價值的域名“sex.com”的案件中,一個聯邦上訴法院對此做出肯定的回答。法院判決道:“與公司股票、土地一樣,域名也是界定清楚的利益。與其他財產一樣,域名可以被估價,可以以數以千萬計美元被買賣。”網絡空間中的財產與在現實空間中的一樣普遍。
甚至谷歌圖書館(Google Books)項目(也許是互聯網對財產權最大的威脅)也發生了出人意料的逆轉。2008年,谷歌宣佈它已經與三年前提起訴訟的兩大原告集團達成和解。根據和解協議,谷歌可以對所有已經絕版的書籍進行商業開發,即使這些書籍仍處在著作權保護期內。事實上,谷歌幾乎成為在美國出版的大部分書籍的壟斷者。這是一個更重要的角色,一個比谷歌最初構想谷歌圖書館計劃時更具有盈利可能性的角色。
批評家們指出,這是一個很不正常的和解協議,它允許被告做的事情比它被起訴時所做的還要多。這個和解協議招致大量不同主體的反對。美國司法部認為這一和解協議可能違反了反壟斷法。版權局認為和解協議違反了著作權法。一些作者堅稱,當主要原告代表所有作者達成和解協議時,它們未能保護它們本應代表的階層的利益。德國政府和法國政府宣稱這一和解協議將損害其國民的利益(這些人很多都持有在美國的著作權),因此使美國違背了根據國際著作權條約所應承擔的義務。隱私權倡導者對谷歌將如何處理“誰正在讀什麼”的信息記錄感到擔憂。2009年秋天,協議雙方屈服於所有這些方面的壓力,宣佈取消該和解協議。他們開始就一個新的和解協議展開談判。
“信息想要免費/自由。”這是斯圖爾特·布蘭德的名言,但其講話的其餘部分卻很少為人們所記住。布蘭德繼續説道:“信息也想索要高價。它想要索要高價,因為其價值對接受者而言可能是無法估量的。”信息想要免費/自由,但它也想要成為財產。

布蘭德預測道:“這一緊張關係不會消減。它將帶來關於價格、著作權、‘知識產權’、臨時發行(casual distribution)的道德正當性等問題的無止境的激烈爭論,因為每一輪新技術都將使這一緊張關係變得更糟,而不是更好。”通過使複製變得異常便利,計算機和互聯網使知識產權的實施變得更加困難;但通過開闢銷售知識產權的新途徑,它們卻極大地提升了實施知識產權的激勵。對這兩個方面而言,所牽涉的利益都越來越大。
結果並非一些人所預測的財產權終結。相反,因應不斷變化的條件,財產權的範圍和強度在不同方面發生了不同的變化。如果我們以更長遠的視界看待眼前的這一幕,其結果並不那麼令人驚訝。互聯網並不是第一個威脅既有的財產觀念的技術變革。它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在數字時代,財產權最終在某些方面變得更強了,而在某些方面則有所減弱。但網絡共產主義卻從未到來。
手段與目的
最後,斯圖爾特·布蘭德的兩個命題都不是那麼準確。信息既不想要免費/自由,也不想索要高價,因為信息什麼都不想要,想要這些的是人。人們想要得到的東西以及這種欲求的強烈程度,隨着物質與智識環境的變化而變化。這些不斷變化的欲求常常導致他們思考關於財產權的新觀念。從放棄殖民時代的封建土地保有權,到21世紀初著作權的擴張,我們關於財產權的觀念始終處在流變中。
接下來會有什麼新財產出現?近些年,有人主張白色人種的身份是一種財產;本土文化是一種財產;人力資本是一種財產;婚姻地位是一種財產;工作既是一項財產,又是在持續運營的工廠中給予僱員財產權的一個理由。幾千年來,動物一直被視為財產,不過,兩百年前我們也可以將我們的人類同伴視為財產。
最近,有些人主張將動物視為財產是一種與奴隸制相似的可悲錯誤。有些人希望財產能夠受到憲法保護,以阻止可能減損其價值的幾乎所有政府行為,有些人希望財產不要受到任何保護,有些人則尋求兩者之間的某個立足點。這些論點中,有些將流行起來,大部分則可能不會。但有一點我們可以有把握地預測:它們將繼續推動我們對財產的理解往一方或另一方發展。
哲學家和法學教授偶爾會試圖尋找財產的“真正”本質,但這本書所講述的故事告訴我們,財產並不是那種有真正本質的東西。它只是一項為實現多種目的而存在的人類制度。如同過往那樣,這些目的因時而變,而隨着它們的改變,人們關於財產“真正”是什麼的流行學説也將改變。它是一件東西還是一束權利?它是人與物之間的關係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它是自然存在之物還是我們的法律創造?
一個人認為財產是什麼,取決於他想要用財產做什麼——即,他希望通過以某種特定的方式來看待財產從而推進的那些目標。對於那些希望幫助福利接受者對抗政府官僚的人,將福利視為財產是有利的,所以他們傾向於認為,財產權也包括福利。另一方面,那些更關心聽證所帶來的成本的人,則傾向於將福利排除在財產的定義之外。
那些希望名人們可以通過薦證產品而盈利的人,發現將名氣視為財產是有利的,而那些更擔心公共領域受到侵蝕的人,則不願苟同。財產本身不是目的,而只不過是實現其他許多目的的手段。由於我們不曾對應當優先對待哪些目的達成一致意見,我們也就不曾對財產達成一致的理解。我們的財產觀念常常被塑造,以服務於我們特定的目的。
隨着時間的推移,隨着圍繞於特定目的的新聯盟的形成,它們將推動財產的傳統理解朝一方或另一方發展。有時,這些聯盟是為了實現特定目的而毫不隱瞞地、公開地組織起來的,如20世紀末的財產權運動。有時,它們是很容易被識別的利益集團,如作為美聯社成員的報社,它們多年來通過遊説和訴訟創造了對新聞的財產權。
然而,在更多時候,這種聯盟既沒有組織,也不易於識別,它們是恰好往相同方向施壓的、具有相似利益的個人或集團。例如,並沒有名人的貿易組織採取協同行動來建立公開權。名氣之所以可以成為財產,是因為能從中獲益的分散個人,都能訴諸一個被廣泛共享的直覺,這一直覺認為他們應該享有對名氣的財產權。
有時候這些聯盟結成,是因為重新界定財產有利可圖。資產的價值越大,在這一資產上,創造和實施財產權的收益就越大。當技術變革增加了某項資源的價值,財產便隨之出現。在錄音技術發明之前,聲音從來就不是財產;照相機發明之前,名氣從來不是財產;廣播技術發明之前,電磁頻譜也從來不是財產。毫不奇怪,驅動這些變革的人正是那些獲利的人。
然而,有時候這些聯盟的結成更多地是因為意識形態,而非經濟原因。公職和人的勞動不再是財產,不是因為它們的價值降低了。相反,是因為將公職和人視為可以被擁有的財產變得在思想上難以接受。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當福利逐漸被視為財產時,其價值確實在逐漸增長,但將它們視為財產的主要原因是政治的:希望幫助窮人對抗冷酷無情又易於犯錯的官僚機構。當身體器官可以被移植時,它們就變得更有價值了,但至少到目前為止,將它們歸類為財產的企圖都遭到非經濟顧慮的挫敗。
在這一拉扯的過程中,各方面的倡導者過去已經、現在仍在繼續做出關於財產的各種論斷——關於它的起源、它的屬性、它的目的、它的外部邊界的論斷。幾乎我們所有關於財產的話語都曾經包含並依舊包含着這類論斷。然而,我們今天所談論的“財產”已經不同於1900年所説的“財產”,而後者也迥異於1800年所談的“財產”,以此類推。我們的財產觀念因時而變,從而與我們認為值得追求的目標的變化相匹配。那些變化在歷史進程的每個階段都充滿爭議,但爭論的焦點從來就不是抽象的財產本質。財產從來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注:
【1】該引言最初作為1984年的會議標語使用,後出現在Stewart Brand, The Media Lab: Inventing the Future at MI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8), 202
【2】New York Times, 21 Apr 1992 C13
【3】“Poll: Young Say File Sharing OK”, http://www cbsnews com/stories/2003/09/18/opinion/polls/main573990 shtml
【4】Fred Turner,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Stewart Brand, the Whole Earth Network,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本文節選自田雷老師主編的譯著《財產故事》的第14章財產權的終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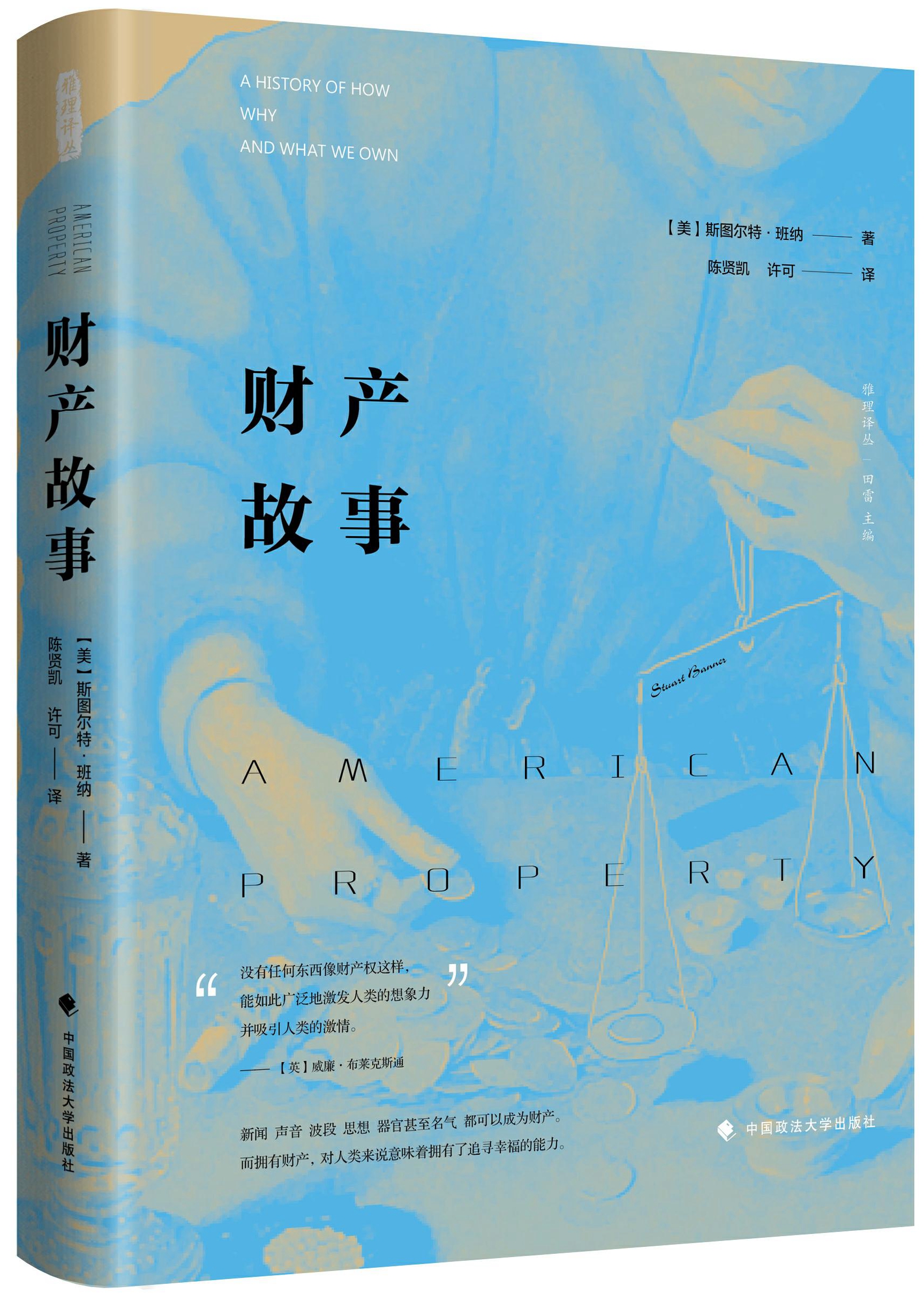
斯圖爾特·班納 著,陳凱賢 許可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