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戴錦華:今天的年輕人比我成熟,會接受什麼是不可改變的
據微信號“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7月7日刊文稱,在與一屆屆年輕學生的接觸過程中,今年59歲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戴錦華髮現,學生們的傳統文化知識和中國歷史知識越來越豐富,但與此同時,他們也顯露出了一種她從來沒有過的歷史體認——對中國傳統文化中權力邏輯的體認,甚至是對當權者的體認,這種體認不僅是知識性的,而且是身體和情感的。同時,這種體認也體現在了大量廣受歡迎的通俗文化作品中,比如近些年熱播的《甄嬛傳》和《琅琊榜》。這一對權力的內在的尊重,以及對革命非理性的恐懼,被戴錦華稱為一種“告別革命的共識”。
這也正是在7月1日中間美術館“新月:趙文量、楊雨澍回顧展”閉幕日的演講現場,當戴錦華面對滿滿一屋子年輕聽眾時,內心所感受到的“代溝”的來源。她坦言,在年輕人面前,她常常覺得自己太幼稚。她認為今天的年輕人非常成熟,所謂的“成熟”體現在他們會接受什麼是不可改變的,而她自己作為一個“50後”卻始終拒絕接受,“假設歷史沒有意義,判定未來也是沒有意義的,所以對歷史我不説如果,對未來我不説不可能。”
戴錦華提到,當中國崛起成為一個經濟學事實的時候,人們開始有意識地回收前現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但這種回收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新的喪失,而這一次,我們喪失的是20世紀中國的革命歷史。這一發生在過去10年間的過程,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的文化現代化進程形成了有趣的對照——後者正是以開啓現代中國歷史之名,交付出了此前悠久、延綿不絕的歷史與文化記憶。戴錦華因此將這次演講命名為《復得的和復失的:歷史與文化記憶》,在她看來,在過去100年間,前現代中國的歷史文化經歷了失而復得,而20世紀的革命歷史與文化則面臨着得而復失。這次演講,同時也是中間美術館發起的“中國作為問題”系列演講的開篇。

戴錦華在講座現場
魯迅以來的歷史想象:
“吃人”的歷史是對進步的反動
在演講中,戴錦華提出的第一個觀點是,中國現代歷史的啓動,是以付出了前現代歷史為代價的;或者説,“我們終於開啓了中國現代歷史的時候,也正是我們相當自覺地交付出了此前悠久的歷史和文化記憶的時候。”
戴錦華從中國革命的先師魯迅談起。在中國近代文學史的開篇之作《狂人日記》中,有一段很經典的描述,講的是“狂人”半夜讀史,發現這個歷史沒有年代,滿紙寫的都是仁義道德,“狂人”橫豎睡不着,就反反覆覆地讀,終於從字縫裏讀出兩個字——“吃人”。這是魯迅對於中國歷史與文化的診斷,也是一次審判——它也構成了幾代人對中國歷史的認知方式。也就是説,人們習慣把中國的歷史認知為一個“吃人”的宴席,在這個宴席上,吃人者被吃,被吃者吃人,沒有關於加害者和被害者的清晰區隔。類似的歷史想象在魯迅的作品中還有很多,比如他曾形容中國傳統社會是“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用“麻木的國民靈魂”來描述中國人的精神狀態等等。
戴錦華認為,以魯迅為代表的這種歷史想象取消了中國前現代歷史的時間性,時間在現代觀念中意味着一個發生、發展、變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不斷進步、不斷上升的過程;而一部沒有年代、只寫滿了“吃人”的歷史,也就是一部“空間化”的、沒有任何變化和進步的歷史。換言之,在魯迅的影響下,與他同時代以及後代的許多中國人不把前現代中國的歷史視作(現代意義上的)歷史,而將它視為永恆的自我重複——只有現代歷史才是線性的歷史,而這個歷史是一個非中國的歷史、是世界的歷史、是歐美主導的歷史。

寫滿了“吃人”的歷史
例如,開啓了中國現代歷史的五四運動,曾經也被明確地稱為一場“開啓了時間”的運動。這樣的一種歷史想象和歷史表述,不僅存在於我們開啓現代歷史的時刻,它還一直貫穿於現代和當代中國的歷史中——每當現當代中國歷史發生什麼重大演變,我們就一次一次地宣告:時間開始了。1919年我們宣告時間開始了,1949年我們又再次宣告時間開始了。
而在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反思熱潮中,這樣的邏輯依然在延續。在70與80年代之交,一部在美國的中國研究中並不重要的著作在中國廣泛傳播,甚至達到了人盡皆知、人手一冊的程度,這本書叫做《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它的主要觀點是,中國文化有着一個不變的深層結構,它的基本特徵叫做“東方專制主義”。這種思想的本土表述就是那本一度對中國社會產生過巨大影響的著作《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其作者是當時的一位年輕人,名叫金觀濤。“中國歷史的超穩定結構”是對那個沒有年代、寫滿了“吃人”的歷史的理論表述,它認為中國歷史有一個超穩定結構,這個超穩定結構決定了中國歷史永遠只能是週而復始的循環與重複,沒有任何進步和發展的可能性。按照這種觀點,“中國的一切都是在原地踏步中不停地循環,中國的生命觀是生死輪迴,自然觀是春播秋收,宇宙觀是滄海桑田,歷史觀是話説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王朝更迭,是一個由興盛到毀滅,由毀滅到興盛的循環往復、永無止境的過程。”這一過程內在地包容着一種不能自我生長的無力,或者説是一種自我毀滅的力量。在戴錦華看來,這是從魯迅到新時期的中國的一種歷史想象,同時也是每個中國人的自我想象。這種想象——即中國文化對於進步的反動和拒絕——造成了一種深刻的文化虛無主義。
五四以來的文化改造:
“反帝反封”的目標
讓現代中國文化失去了立足點
戴錦華的第二個觀點是,在中國現代歷史開啓的時候,中國人開始了一種深刻的、內在的自我改造,這種自我改造成為了文化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種極端深刻的文化內在流放——所謂的“中國經驗”被我們自己流放出去,或者説它無法再在我們的文化媒介中被直觀地把握。
她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文化實踐層面一個最重要的、最形而下的、最具體的組成部分——白話文運動談起。戴錦華指出,經由五四新文化運動,一種新的語言成為了中國文化裏主導型的媒介工具。按照白話文運動倡導者之一胡適的説法,白話文運動是一種文化民主化、平民化的過程,因為它是“我手寫我口”,而文言文則意味着口語和書寫文字的分離,因此導致了文化屬於貴族和少數人的結果。

胡適
但在戴錦華看來,白話文運動絕不是一個文字口語化的過程,因為在文言文主導的時代,古白話始終存在,也同樣是一種“我手寫我口”的語言形態。但現代漢語和古白話是兩種語言,只不過古老漢字的延續使得我們忽略掉了,現代漢語其實是一種非常年輕的新語言。中國古代漢語是以字為單位的,每一個字都是一個表意單位,而現代漢語的發明則意味着大量詞的出現。當兩個漢字組成一個詞的時候,詞的意思並不是兩個漢字意義的疊加,相反,它是一個文化西化的過程。比如“宇宙”中的“宇”指的是屋宇,是中國人的居住空間,而“宙”指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勞作方式;“宇宙”二字原本代表的是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下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而當它組成一個新詞的時候,它的意思完全變了。
她接下來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兩句響亮的口號,直到今天還被我們視為重要的政治、文化使命,那就是“反帝”和“反封”——前者針對的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後者則直指前現代中國的主流文化(也就是所謂的“打倒孔家店”)。戴錦華稱,她曾經一直認為“反帝反封”是非西方國家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必然要面對的雙重使命,直到20年前,她開始探訪亞非拉的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深入到這些欠發達國家腹地的時候,她才發現,這種“五四式”的雙重命題是中國的特殊情況。
絕大多數非西方國家和中國之間的一個重要不同在於:他們都經歷了極端慘烈的殖民歷史,他們的文化從前現代到現代的轉化過程不是自己主導發生的,而是在軍事佔領和政治控制之下被強暴的過程。因此,他們的主要使命是反帝反殖、驅逐外來統治者,而完成這一使命所依憑的武器,正是本土文化和民族主體身份。反觀中國,除了東北和台灣之外,中國主部並沒有經歷過殖民統治,只有在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中,我們才能有勇氣同時打倒兩個敵人,即“反帝”和“反封”。這一雙重目標的設定,也導致我們在現代中國文化內部失去了立足點。換言之,我們在建構一個現代中國的過程中,同時創造了一個自我中空的主體。
“中國崛起”以來的傳統復歸:
逃離革命意味着逃離了
中國文化的內在邏輯
最後,戴錦華談到了中國經濟崛起之後,中國人歷史知識和歷史意識的重歸。她首先指出,中國崛起不是一個內部的宣告,而是一個外部的指認。2009年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國第一次被放在了拯救者的位置上,並且是歐美世界仰望並期待的拯救者的位置上。當中國崛起作為一個經濟學事實、一個統計學事實、一個消費主義事實,開始由外而內地進入到中國的自我指認的過程中時,一個變化悄然發生了:中國開始從一個無名、病態的、例外的、弱小的國家漸次恢復它作為一個大國的國際地位,同時,我們開始回收前現代的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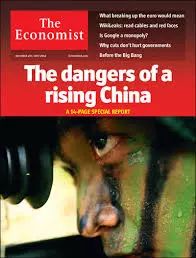
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崛起”的指認
中國人終於開始意識到,中國是唯一一個擁有着連續的文明歷史的古國,而其他很多輝煌璀璨的古老文明都被時間湮沒了、被殖民主義徹底地摧毀了。在重新迎回這段前現代歷史的過程中,也會發現,中國文化不是超穩定結構。從秦漢到明清,中國有着自身的歷史脈絡;清帝國淪亡的過程,也並不是文明對野蠻的征服,而恰恰相反是野蠻對文明的摧毀,是一個強盜的劫掠。於是,我們的歷史知識和歷史意識重歸了。
與此同時,**戴錦華髮現了一個令她感到警惕的事情,那就是年輕一代在歷史知識越來越豐富的同時,還伴隨着一種她從未有過、也從未曾嚮往過的歷史體認——對傳統中國文化中權力邏輯的體認,對當權者的體認——這種體認不僅是知識性的,而且是身體和情感的體認。**這種體認體現在大量的通俗寫作、演義、歷史文本,甚至是當代人的古文寫作中。電視劇《雍正王朝》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例子。在《雍正王朝》熱播期間,導演曾説,“這部戲我沒想説別的,只想説一件事,當家難吶!”這讓戴錦華感到非常震驚,因為在她整個成長,甚至直到死亡的過程中,她從來沒有想過,要站在當家者的角度去體會當家有多難;相反,她想的永遠是像她一樣的草民在種種權力的擠壓下生存得有多難。她以為,“我受到的所有歷史教育都是要教人傾聽歷史的無聲處,而不是傾聽大人物的洪亮言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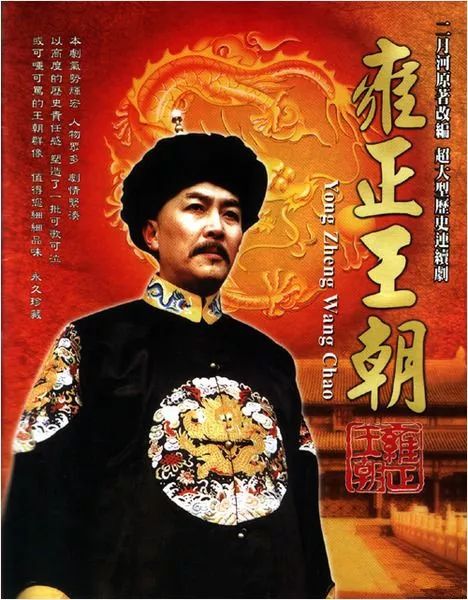
電視劇《雍正王朝》
除此之外,戴錦華還有第二個震驚。在與年輕學生的接觸過程中,她發現,當年輕一代的歷史知識已經如此豐富的時候,一個新的喪失發生了。換言之,人們在回收前現代中國歷史的過程,同時伴隨着對於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再次付出。於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便出現了:遙遠的是貼近的,而切近的是陌生的;歷史地平線的盡頭是1980年代,1980年代之前的歷史在年輕一代的認知中幾乎是一片空白。
在戴錦華看來,當我們再次付出了20世紀中國歷史的時候,我們也失去了20世紀中國自身的文化邏輯。20世紀的中國在四面圍困、腹背受敵的情況下,要活下去、走出一條路,這當然是國家的意志,同時也關係着每一個民眾的生存,是每一個民眾別無選擇、被裹挾其中的一個歷史過程,也是每個人生命的內在經驗,是中國歷史一個高度有機的組成部分。她認為,20世紀中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樣式的革命,革命之於中國至少意味着一種另類的現代化進程,因此,當我們用傳統與現代的簡單二元對立去看待中國的現代化問題,實際上也消解了20世紀中國歷史中的差異性元素——西方世界的現代化進程在中國行不通,因此中國被迫選擇一種極端的、激進的方式。
戴錦華認為,當我們放棄了20世紀中國獨有的文化邏輯的時候,我們也就無法真正重返前現代中國的歷史。因為,20世紀的歷史尤其是當代中國歷史,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永恆的謎題、永恆的痛苦和挑戰,那就是“在一個革命性的、實驗性的歷史進程中,我們將永遠遭遇到關於秩序和革命的雙重緊張”。我們或許永遠也無法逃離,當年的紅衞兵所面臨的無限忠誠和造反有理的命題。這一命題在戴錦華看來是內在於中國文化的,中國文化內在地包含了這樣一種文化張力,它也是中國文化自身的活力,在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的旁邊,是載舟覆舟、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歷史邏輯,這才是中國文化內在的自我更生、自我演進的邏輯。(作者/張之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