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新今文經學與現代革命志士
從帝制到共和,中國政制的現代轉型經歷了艱難曲折的百年曆程(1840—1949),古老的天安門前豎立起“人民英雄紀念碑”,標誌着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終於大局初定。如今的我們生活在新生的共和時代,雖然晚近半個多世紀以來,共和經歷仍然曲折艱難,畢竟已經進入後共和政治狀態。
**從英國艦隊炮擊國門到帝制瓦解,從“真假共和”之爭引發內戰和外敵趁虛而入到中共軍隊將外國艦隊逐出長江,從共和國在灰燼中重生到改革開放,儒家思想的經歷可謂一波三折。今文經學率先突起引領變局,隨後“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成為主流並在“文革”時期貫穿落實,改革開放之後儒家思想又死灰復燃。如今,儒學復興的學術景觀已蔚然可觀,不僅論説蜂起,而且內部相互攻訐日盛。**就此而言,在後共和時代的政治狀態中檢討儒家思想的百年經歷,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説不僅具有政治史學意義,而且具有政治哲學意義。
傅正博士的《古今之變:蜀學今文學與近代革命》篇幅雖小,涉及的問題卻不小。在筆者看來,本書的實際主題是“新今文經學與現代革命志士”——副標題點明瞭這一點。“古今之變”這個書名不外乎表明,對儒家而言,“革命”是一個古老語彙而非現代語彙。
晚清以來的現代革命堪稱獨一無二,僅僅因為這場革命的實質乃“古今之變”。因此,新經學與現代革命志士之關係究竟如何,與今天的我們並非沒有直接干係。畢竟,無論從制度還是思想層面上講,這場偉大的“古今之變”尚未塵埃落定。
回顧並檢討儒家思想與現代中國變局的關係,不可能不談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啓超。本書作者則告訴我們:還應該加上,不可能不談廖平及其弟子蒙文通!倘若如此,我們就得對學界已有的現代儒家思想的歷史地圖做出重大修正。

一、新今文經學的現代革命含義
經學有古文與今文之分,本是漢代重建國家秩序時當為哪些經書立學官之爭,因秦火而來的經文抄寫文字的差異,成為這場政治衝突的導火索。時過境遷,無論從學術上還是政治上講,古文與今文之分都早已失去意義。廖平在晚清時局中突然舊事重提,而且提出前所未有的判分標準:古文經與今文經之分不在抄寫文字和是否立為學官,而在崇舊制(周禮)抑或崇新制(孔子所立之制)。作者提醒我們,這個道理甚至“西漢大儒也不知道”(頁21)。**把這一經學議題轉換成政治議題便意味着,今人必須在損益舊制(帝制)抑或創立新制(民主共和)之間做出選擇。難怪劉師培、章太炎一類所謂古文派經學家也贊同廖平的判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贊同廖平的新今文學本身,毋寧説,他們欣賞其中所包含的革命正當性法理。
廖平經學的革命品質首先體現在,他並非如人們以為的那樣回到漢儒,而是“自創”出一個“新的今古文學説體系”。史學家們迄今仍津津樂道常州學派與晚清新今文學的連帶關係,經作者的考察,這其實是個莫須有的史學論題。**真實的史學論題毋寧是:既然廖平的今文經學觀“恢怪”得出奇且無所依憑,我們就應該問,如此革命性的經學觀是怎麼來的?**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是否得自廖平的啓發是現代儒學史上的著名公案,作者卻關心另一個問題:身處西南腹地的廖平何以可能會先於身處沿海的康有為發明如此革命性的經學觀。
作者首先以“晚清蜀學與經今文學的另一譜系學”為題嘗試回答這個問題,並用了三分之一篇幅講述廖平經學形成的地緣政治背景,以至於思想史研究成了政治史學研究。關於廖平的早年經歷,史學家們會津津樂道張之洞慧眼識珠或王闓運打造尊經學院的問學取向等等。在作者看來,這些都是不爭的史實,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其實是另一史實:
1874年,英國保守黨政府上台,一改克里米亞戰爭後期20年的對俄綏靖政策,轉而在東方全面遏制俄國擴張。從阿富汗到西藏,廣袤的中亞大地都成為了英俄爭奪勢力範圍的疆場。……在這種情況下,本來作為內地的川、滇、甘諸省突然成為了邊疆,成為了西方殖民主義勢力交鋒的前線。(頁31—33)
現代列強進逼中國不僅有海路(從沿海到內地),還有陸路(從中亞、南亞經新疆、西藏到內地)。經作者這麼一提醒,筆者才恍然明白,身處內陸腹地的廖平為何會具有全球政治地理視野。1898年,廖平刊印其“三變”期的代表作《地球新義》,提出孔子已知全球為九大州、中國為小九州的著名論斷(頁61—66)。憑靠重新解釋中國古代經典來建構一套儒家式的全球政治地理觀,是廖平經學中的一大亮點。廖平一生學術多變,這一點並未改變。

清末的中國版圖
作者沒有舉例讓我們領略廖平儒家式的世界政治地理説高論,筆者不妨引廖平在《地球新義》刊行20年後(1919)發表的一篇論述《詩經·國風》“五帝分運”的文章中的説法,以便讀者切實感受一下廖平經學如何“恢怪”得出奇。廖平文章説,他仍然堅持自己曾憑靠《周禮》中的“賦、比、興之名”推衍全球政治地理的“九國而三統之説”:
《王風》,《魯詩》以為魯,在東大統,以託伏羲,為海外東經、大荒東經。以中國為中,則日本以外之海島,當為今美洲。《豳》在雍,乾位西北,為少昊所司之分,為海外西經、大荒西經,為金德王之政。歐以中國為中,則應以歐洲當之。蓋就中國言,以美為東,以歐為西。就中土言,則以中國為東,美為西。《詩》之“中”字有二義,一指中國,一指中土言之。……孔子殷人,先就三統立説。且美洲非聖人舊,雖曰金統,要必由中以化外,故國少昊曲阜,以西方之中亦歸於東魯。如少昊以金德為帝,治五洲,其餘四洲之帝皆退位。以神主之,東洲則勾萌,本洲則祝融,中洲則后土,北洲則玄冥。以金德王,當在美洲立留都。
即便在當時的中國知識人看來,這樣的説法也明顯穿鑿附會得可笑,遑論今天的我們。儘管如此,作者的政治史學筆法提醒我們應該意識到,地理大發現始於16世紀,西歐人直到18世紀才大致形成明確的全球地表知識。德國大學在1874年建立地理系,標誌着科學的世界地理觀開始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爭奪全球支配勢力範圍的工具,麥金德在1904年提出的地緣政治觀堪稱最好的例證。廖平在1898年提出儒家式的全球政治地理觀,缺乏的僅是地理學的實證知識,相比之下,麥金德的政治地理學雖然有實證知識墊底卻缺乏德性。
因此,廖平的“地球新義”的問題並不在於他把剛剛得知的地理大發現知識塞進了中國古代經典,而在於他憑此將孔子推為世界教主:
《詩》之主教,則在東方。以孔居魯,少昊之都亦在魯,故曰“顛倒衣裳”。金德之帝,不在西洲,而在東洲。考三統九風,一統一君二臣,如《易》之三人行損一人,一人行得友二臣,以備二統之臣,君則自王之主國。如《邶》為王,則魯、週二統之《王》、《豳》退位,以《鄭》、《魏》為之臣。如一王而二伯,《王》為王,則《鄘》、《秦》為之臣。亦如《易》之三爻中,有一君二臣也。而一篇之中,又自分三統,有自應本風之篇,有附應二統之篇。可以考見,由斯以推,則一風分應三統,九風互相為君臣佐佑焉。(廖平,《詩説》,前揭,頁73)
可以看到,《王制》是廖平推衍全球政治地理的“九國而三統之説”的基礎。作者恰切地指出,廖平“完全以《王制》為繩準,只有符合《王制》的才配成為‘今文經’”——用廖平自己的説法:“至於今學,則全祖孔子改制之意,只有一派”(頁49)。由此我們得知,即便廖平的新今文經學譜系是偽造,也算得上哲人式的立法行為,用實證史學的腦筋來衡量,當然扞格難通——問題在於: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孔子退修詩書
法國著名思想史家哈扎德(Paul Hazard,1878—1944)在其名著《歐洲意識的危機》一書序言中曾説,伏爾泰的《論普遍歷史》幾乎在一夜之間取代了波舒哀的《論普遍歷史》:“大多數法國人一直像波舒哀那樣思考,突然之間,法國人像伏爾泰那樣思考:這是一場革命”。廖平把孔子推為世界教主,與其説必然與泰西的基督教迎面相撞,不如説與現代的文明進步史觀狹路相逢。因此,作者在“孔子的‘一神化’與文明進化史觀”這一標題下討論廖平的地理觀,恰如其分。如今的我們很清楚,無論基督教還是儒家的世界觀都面臨地理大發現以來形成的文明進化史觀的致命挑戰。
廖平區分“小九州”與“大九州”,“真三代”與“王之三代”,其根本時代背景是古人對於上古三代的信仰破產了,對上古三代的研究不再具有致用的價值。如此一來,經學就面臨覆亡的危險。(頁66)
廖平的新今文經學顯得是絕地挽救儒學的行動,但在作者看來,這似乎無異於儒家傳統的自殺。首先,由於“體現孔子‘因革繼周’之道的今文經少之又少,反映舊史的大多數經文又‘各就所見立説’”,廖平提出的今古文經學的區分標準就“撕裂了”體現古三代典章制度的六經的整體性,為後來經學的實證史學化大開方便之門。作者敏鋭地推斷,民國古史辨派將六經還原為史料,實起自清末今文家(頁51,比較頁83).
第二,把儒學打造為一神教,在中國“恰恰推動了歷史進步觀念的形成”。作者在上篇結束前添加了長篇“附論”,提出中國的現代歷史主義實際有“兩條路徑”。言下之意,本來是要抵制歷史主義的新今文學反倒開闢出了一條獨特的歷史主義路徑。
筆者感到困惑:按作者的辨識,廖平恰好要通過其確立的新今文經學標準阻斷對經學的史學理解,何以可能引導出一種歷史主義?作者沒有深究這個問題,他的關注幾乎完全被自己所發現的廖平經學的革命性質吸引。在結束對廖平經學的考察時,作者説,雖然廖平與康有為都以尊孔唯尚,但廖平經學更具革命品質:康有為憑靠新經學提倡改制,廖平憑靠新經學提倡革命,從而其經學主張更為激進。作者強調,這並非他自己的看法,而是廖平弟子蒙文通的觀點:“康有為雖然剿襲了廖平的觀點,卻從未剿襲到廖平學術的真精神,這個精神就是革命”(頁67)。顯然,作者更為關切這樣一個政治史學問題:蒙文通的經學觀可能比廖平更具有革命品質。
情形若真的像作者讓我們看到的那樣,後共和政治狀態中的新儒家們就得小心了:他們自以為在弘揚儒家傳統,沒準兒恰恰是在破碎儒家傳統。我們不能想當然地以為,只要是弘揚儒家就沒問題,毋寧説,關鍵問題在於如何弘揚以及弘揚儒家傳統中的什麼。
二、新經學與新知識人
結束對廖平新今文經學之革命性質的剖析後,作者戲劇突轉式地談起了一個看似與廖平的經學革命並不相干的論題:“本省意識、保路運動與蜀學認同”。由於這一部分的標題是“中等社會的革命”,筆者不禁好奇:廖平及其弟子蒙文通的新今文經學與“中等社會的革命”有什麼關係嗎?
為了更好地理解作者的論述,有必要簡扼回顧保路運動的來龍去脈。這一運動歷時數年,其高潮“成都血案”史稱辛亥革命前奏。事情原委大致是這樣:
1903年9月,清廷推行“新政”搞改革開放,允許民間集資辦鐵路、礦務、工藝、農務等公司,各省陸續成立私營鐵路公司集資修鐵路。清廷沒有想到,如此“新政”舉措會損害西方列強的在華利益,進而引發民間私營公司與西方列強所謂在華鐵路修築權的利益衝突。換言之,清廷高層對現代政治缺乏基本常識,竟然不知國家主權為何物。湖南、湖北、廣東三省紳商首先發起“收回路權”運動,並在1905年成功從美國人手中贖回粵漢鐵路和川漢鐵路修築權。在今天看來不可思議的是,愚蠢的清廷在1911年春東施效顰成立“責任內閣”後不久(同年5月),隨即頒發“上諭”宣佈商辦鐵路一律收歸國有,並派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強行接收湘鄂川粵四省的商辦鐵路公司,打算把築路權賣給英美德法四國財團。
湖南人首先起身反抗,在紳商組織下,長沙和株洲出現萬人築路工遊行示威,甚至包圍了巡撫衙門。湖北人隨後跟進,紳商組織築路工與前來強行接收的政府軍發生衝突,當場打死政府軍20餘人。成都的保路運動出現得稍晚卻更持久,組織性也更強,保路同志會成立10天就發展到十萬之眾。愚蠢的清廷仍然採取高壓手段,沒想到同盟會早已介入,與地方哥老會聯手,把保路同志會改為保路同志軍,準備武裝反抗。四川總督趙爾豐設計誘捕省諮議局議長及保路同志會和川路股東會要人,引發數萬人包圍總督府,趙爾豐竟然下令開槍,當場打死30多人。幾天之內,成都附近州縣保路同志軍二十多萬人圍攻成都。由於行動倉促又缺乏統一指揮,同志軍攻打成都十餘天未果,不然的話,辛亥革命的發生地就不是武昌了。儘管如此,新共和國開國元帥中,川人佔四位,湖南湖北各佔兩位,絕非偶然。

四川保路運動
顯然,**在作者看來,保路運動是所謂“中等社會的革命”。**作者關注這樣一個問題:清廷已經搞改革開放而且準備立憲,何以成了自掘墳墓。這明顯屬於政治史學論題,作者的論析甚至帶有歷史社會學史學的痕跡:通過考察保路運動與本省意識和蜀學認同的關係,作者希望解釋“靜悄悄的革命”何以最終引致“孫中山和暴力革命話語的成功”(頁95)。
作者讓我們看到,所謂“中等社會”這個概念的具體所指有不同的界定,但無論哪種界定都會包含新知識階層。作者還提醒我們:
“中等社會”的優勢在於,它作為當時人自己的術語,既是歷史研究的對象,又是分析歷史的框架。(頁102—103)
這當然不等於提醒我們,**20世紀末東歐的“公民社會”或“公共空間”看起來是在搞“靜悄悄的革命”,沒準會引致某種“暴力革命話語的成功”。其實,在西歐這樣的基督教傳統國家的現代轉型過程中,新知識階層的形成也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史學課題。要説中國的現代知識階層的形成有什麼獨特性,人們恐怕只能説,清廷新政搞改革開放時廢除科舉過於匆忙,沒有迅速建立由國家主導的新型國民學校和高等教育。**作者讓我們看到,一方面,大量年輕學子蜂擁東渡日本留學,另一方面,國內各地紛紛建立新式學堂,“學生成為了一個遊離於政治控制之外的特殊階層”(頁113)。
其實,從今天的經驗來看,年輕學子大量出洋留學不是問題,關鍵在於執政者是否對國內教育體制有形塑和掌控能力。作者讓我們注意到,清末新式學堂模仿海外新學,紛紛增設“歷史”“地理”科目。清廷固然多次頒佈了“奏定”學堂章程,但高層官僚缺乏明智的政治意識和應有的政治素質,意在激發愛國意識的教育反倒成了強化本省意識的催化劑。換言之,清廷並非沒有致力於形塑國家教育體制的形成,毋寧説,清廷高層完全不懂得應該如何形塑國民教育。單純的強制無異於毫無章法,以至於新學成了自掘墳墓的行為。
清廷高層不懂西方卻瞎學西方,尤其體現在1907年下諭各省“速設諮議局”,為議會政治做準備。從政治常識上講,清廷設立的這種“不受督撫節制的地方立法機構,等於給地方精英提供了一個可以對抗中央權威的平台”(頁139)。短短几年內,全國出現多起“開國會”的請願事件。在保路運動中,各省諮議局似乎起了不小的作用,起碼成都事件與總督趙爾豐誘捕四川諮議局議長有關。

清末的特殊階層——西學教育背景下的留洋學生
**作者用了大量篇幅論析晚清政府搞新式學堂和開設地方諮議局似乎意在説明,保路運動這樣的“中等社會”革命其實是清廷自作自受。筆者卻感到,這一論斷明顯有問題。憑常識也容易看出,即便沒搞新式學堂和開設地方諮議局,保路運動照樣會發生,因為,這一事件明顯是清廷執政者的政治素質差得不可思議所致。**畢竟,民間集資修鐵路的股東不僅有紳士、商人、地主,還有農民,而且據説農民購買的股份佔很大比例。因此,保路運動與清政府強行收回路權且不退還或補償民間集資有關,與清廷的教育改革失敗和開設地方諮議局談不上有直接關係。
作者提到傳統國家現代化轉型的一個重要特徵,即中間階層乃至下層民眾的參政。換言之,現代國家的建構必然要求中間階層乃至下層民眾的廣泛參與。如馬基雅維利所説,共和政制有利於政治體保持最佳的競爭狀態。對於增強政治體的強力來説,讓國民有政治參與感比龐大的税收更管用。**中間階層乃至下層民眾處於積極的政治狀態,政治體更有底氣保持強勢外交政策。因此,激活“中等社會”的政治活力,絕非意味着中央集權的君主制必然崩潰。**成都事件之後僅僅幾個月,由於武昌新軍被緊急調往四川鎮壓保路軍,武昌守備空虛,辛亥革命趁機就來了。如果清廷懂得利用民間自1903年以來持續不斷的“收回路權”運動,憑此力量強化國家主權,未必會有這樣的結果。
即便採用了歷史社會學的分析範式,想必作者也不至於會忽視這類常識性思考。因此,這一部分的論析意圖讓筆者感到難以琢磨。讀完附論“嚴復對梁啓超的批判:對中等社會的一種反思”,筆者才恍然大悟。作者説,他考察保路運動與清廷的教育改革和開設地方諮議局的關係為的是證明:
清廷改革的初衷固然正大光明,結局卻播出龍種收穫跳蚤,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事權往往落在了這羣毫無政治經驗卻自以為是的新式知識分子手中。正是這些人把改革引向了自我毀滅的道路。(頁179)
在“中篇”考察的附論中,作者看似要通過嚴復批評梁啓超缺乏明智來證明這一點。因為,在作者看來,“越是大的變革越需要依賴高政治素養的人,而不是讓更多本沒有政治經驗的人分享權力”(頁187)。因此,嚴復更在乎如何提高執政者的政治技能,而非啓蒙民眾。反觀梁啓超等人以似懂非懂的西學知識煽動民眾,其將有益於維新改革乎?(頁189)
作者筆下出現了明顯的自相矛盾,我們可以問:保路運動乃至辛亥革命是因為事權落在了“毫無政治經驗卻自以為是的新式知識分子手中”嗎?當然不是!情形明明是清廷執政者缺乏最為基本的政治素質和政治才幹。然而,完全可以理解,在我國的政治史學研究中,論者顯然不便從維持清廷統治的角度展開論述,否則會被視為替封建專制説話。
由此來看,筆者的另一個困惑也迎刃而解了。在結束保路運動與清廷的教育改革和開設地方諮議局之關係的考察時,作者提到,廖平不僅積極參與保路運動,而且在辛亥革命後成為四川樞密院長。作者似乎認為,這足以進一步證明,廖平的新今文經學“要旨在革命,而不在改制”(頁177):這時的康有為成了保皇黨領袖,“豈足與投身革命的廖平相比”(頁175)。在筆者看來,這同樣是明顯的似是而非之論。畢竟,即便情形如此,也不等於保路運動直接反映了廖平經學的革命性。我們當然更不能説,由於有了廖平的革命性經學,才有了保路運動這樣的革命行動——與這一行動有直接關係的是同盟會,而廖平並非同盟會秘密成員。
作者的曲折筆法暗中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廖平具有革命品質的經學究竟寫給誰看,或者説,廖平學術在對誰説話?接下來作者就轉向了廖平的弟子蒙文通,考察他如何推進廖平經學的革命性。
— 待續 —
本文轉載自“六點圖書”微信公眾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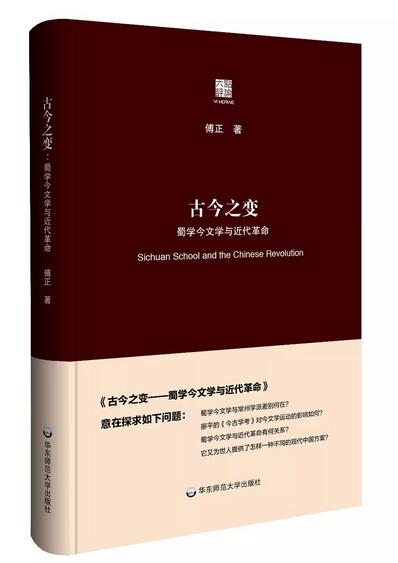
傅正 著《古今之變: 蜀學今文學與近代革命》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7/pp.2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