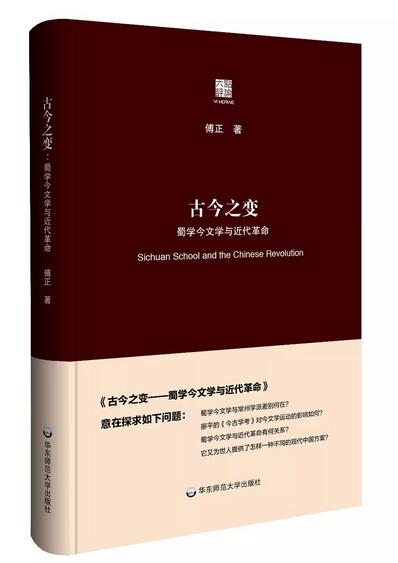劉小楓:新今文經學與現代革命志士
三、新今文經學與中國現代革命的正當性論證
[接續前文]作者在結束對“中等社會”革命的考察時問了這樣一個問題:
深受革命激盪感染的蒙文通,會否因其“素王革命論”而比主張“改制説”的康有為更切近於現代中國的核心政治問題呢?(頁177—178)
蒙文通成為經學家和文史家之前和之後,都應該算“中等社會”中的一員,倘若如此,他張揚“素王革命論”可以理解為既受“革命激盪感染”又對“革命激盪”做出解釋,這意味着對自我或自己所處的時代做出解釋。“素王革命論”並非蒙文通的發明,而是對廖平和康有為的新今文經學核心要點的推衍,其含義也許不難釐清,但要説清何謂“現代中國的核心政治問題”就難了。
按照作者的辨析,蒙文通的經學比自己的老師更具革命色彩。對蒙文通來説,不僅董仲舒之學是偽今文學,康有為之學也是偽今文學:董子主張改制論,篡改了主張革命的孟子真學,康學一方面主張孟子傳公羊微言,一方面又以董氏學説為今文經學要核,可見他不懂孟子(頁197)。蒙文通經學的革命品質,尤其見於他憑靠現代民主政治原則否棄古代儒家的政治理想:“《周官》不是理想制度,《孟子》所述的也不是理想制度。”這不僅“否定了清末以來今文家的‘孔子改制説’,更否定了孟子傳大同之道”。畢竟,即便在孟子那裏,革命也僅僅針對“貴戚之卿”,“與民主革命相去誠不可以道里計”——用蒙文通自己的説法,豈可“持之以致用於今日”(頁219,238)。

孔子書院典禮
蒙文通憑靠現代民主政治觀念裁決古典儒學,使得新今文經學的革命矛頭指向了儒家自身,與如今我們見到的好些新派儒家差不多。這無異於革儒家自身的命,以至於我們禁不住要問,為何蒙文通的經學觀會如此激進?
作者給出了一個頗富政治史學意味的解釋:**清末立憲和清帝遜位實際已經認可現代的“主權在民”原則,但“二次革命”置換了現代中國確立“主權在民”原則的歷史前提。**換言之,清帝遜位的意義史無前例,因為這相當於帝制禪讓給“主權在民”的共和制。從而,中國政體的現代轉型既實現了古今之變又並非是一場古今之變,畢竟,“主權在民”至少在觀念上符合儒家政治傳統。“二次革命”改變了這一歷史變局的含義:“主權在民”原則的確立不是君主禪讓的結果,而只能是革命的成果。這樣一來,“主權在民”的現代原則的確立必然與傳統的政治觀念發生斷裂(頁222)。

君主禪讓:古代中國政體傳統
作者進一步提請我們注意,蒙文通的經學觀產生於一個特殊的歷史語境:自“二次革命”以來,整個中國一直處於軍閥割據的分裂狀態,日本入侵才使得中國各派政治力量達成戰時統一。一時間人們覺得,基於國家統一的民主憲政終於有望:“抗戰”為民主“建國”提供了歷史契機。1938年,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抗日建國綱領》,甚至得到中共的認同。然而,作者敏鋭地看到,《抗日建國綱領》實際隱含着致命的內在矛盾,即“建國”與“抗戰”的矛盾:抵禦外敵的抗戰以國家的整全為前提,而時人卻企望靠抵禦外敵的抗戰來達成重建國家的整全:
難題在於,“抗戰”要保衞中國,“建國”卻説中國還沒有建成。一者是歷史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一者是革命斷裂意義上的中國,兩個中國很可能在邏輯上相互否定。人們又將如何解決二者之間的分裂呢?(頁227)。
換言之,為了實現世襲君主制轉型為現代式的主權國家,“二次革命”的政治理想讓文明中國近乎碎裂,國家也喪失了完整性,否則日本斷乎不敢如此肆無忌憚進犯中國。作者揪住這個中國現代轉型中的內在矛盾不放,進一步揭示其中所藴含的問題:抗戰以保存華夏文明傳統為戰時動員口號,而堅持抗戰的革命黨又以反傳統的“革命”起家。如此矛盾的荒謬性尤其體現於“漢奸”現象:
根據梁啓超等清末今文家的“新夷狄説”,夷夏之別由歷史進化程度高低決定。相比之下,日本文明開化程度深於中國,是故日本庶幾近乎華夏,中國則屬於新夷狄。無疑,在清末新政時期,非如此則不足以號召政界、學界學習列強。但在抗戰前期,如此則不啻於為投敵叛國辯護。顯而易見,“中日提攜”乃是“用夏變夷”,人們投身“新華夏”尚且應之不暇,又何必抗日呢?(頁230)
作者一路追究下去,一步步把政治史學式的提問上升為政治哲學問題,追問作為傳統符號的文明中國與作為現代政治單位的主權國家之間的悖謬關係:
倘若中國傳統一貫包含現代因素,則仁人志士又何必投身於革命呢?倘若革命本無必要,則由革命建立的現代政權豈非同樣沒有必要了?反過來,倘若革命是現代中國的必由之路,則豈不證明了中國傳統並沒有自動走向現代化的能力?(頁234)
看來,作者所説的“現代中國的核心政治問題”或“古今之變”的實際含義是:“主權在民”作為現代政制原則本來並不與中國傳統政治觀念牴牾,由於“二次革命”人為製造出牴牾,傳統與現代的對立才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思想難題。蒙文通的經學觀成於軍閥混戰到抗戰初期這段時期,從而內在地帶有上述矛盾,或者説,他下意識地致力解決這一矛盾。因此,作者給下篇擬定了這樣一個副標題:“蒙文通的革命儒學與現代中國之根由”。似乎,如果張揚古代儒家本來就有“主權在民”的革命論,那麼,傳統與現代的斷裂難題就會迎刃而解。
“革命儒學”這個指號意味着,蒙文通學問的關注重點實際已不是經學本身,而是革命論——作者告訴我們:
蒙文通敏鋭地發現,儘管近代革命家除了西學資源外,大可以利用法家、墨家、道家、釋家等學説,但傳統資源中只有儒家才是明確提倡革命的。(頁238)
**為了消弭現代革命與儒家傳統的裂痕,蒙文通致力從儒家典籍中找尋平民革命論的資源,就像如今不少新儒家從儒家典籍中找尋自由民主論的資源。**蒙文通之所以尤其看重轅固生,乃因為他把出自平民而登天子位的漢高祖比作湯武,這意味着“革命已經不再是諸侯或貴戚之卿的特權”(頁239)。因此,蒙文通比廖平更為自覺地致力搞清“革命”的確切含義——我們必須補充説,這當然指現代意義的“革命”含義。由此可以理解,蒙文通不僅與康有為劃清界線,而且在根本立場上也與其師廖平劃清界線。晚清新今文經學家從廖平、康有為到皮錫瑞,無不看重《王制》,蒙文通卻認為,這些前輩未必看到,《王制》“非特取消了鄉遂之別,更突破了平民、貴族的絕對界線”(頁253)。換言之,晚清新今文經學家都沒有看到,古代儒家已經有平民革命論。蒙文通在《孔子和今文學》一文中如此盛讚陳涉揭竿而起:
這一次人民大起義為儒生所擁護而打破了原有的成見,陳涉雖然失敗,而劉邦卻成了功。這讓儒生受到絕大的啓發。(頁239—240)
作者在解釋這段引文時説,司馬遷把陳涉列入“世家”,“體現了漢儒的平民思想,這是先秦儒家不具備的”,因為這意味着漢儒“把‘有德者’的資格徹底平民化了”。作者指出,蒙文通為平民革命提供儒家式正當性證明的最終理據在於:“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由此可以理解,蒙文通憑靠儒家政治思想傳統為平民革命提供正當性論證時,突出強調《王制》中所描述的國家權力階層的選拔方式:
鄉秀士完全可以憑藉自己的才能一步步升入國學,與“三公九卿大夫元士”處於同樣的地位。天子拜觀授爵都在國學中選拔,平民享有了與貴族同樣的晉升國家權力階層的機會。(頁253)
儘管如此,在蒙文通看來,“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並非漢初儒家的發明,而是漢初今文學家吸取墨家“選天子”和法家“明君權,削世卿”等主張的結果(頁256—258)。作者讓我們看到,為了替平民革命提供正當性論證,蒙文通致力動員諸子百家的資源,而非僅僅是儒家的資源——蒙文通眼中的漢代今文家革命論不過是諸子百家相關思想精粹的彙集。
問題已經上升到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學高度,筆者難免會想到一個問題:**“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與平民革命論是一個意思嗎?“平民享有了與貴族同樣的晉升國家權力階層的機會”,憑靠的是某個平民身上自然稟有且需要經過修養才得以煥發的政治德性,這意味着“平民”概念還不能與政治德性直接劃等號。我們顯然不能説,只要是平民就自然而然有晉升國家權力階層的權利。**廖平出身於貧寒農家,張之洞則稱,廖平是他在蜀中所見“天資最高,文筆雄奇拔俗”的志士。如果廖平有革命的權利,那麼,這種權利來自其“天資最高,文筆雄奇拔俗”,而非來自他的貧農出身。再説,既然《王制》已經規定國家權力階層的選拔方式,平民中的天素優異者有了晉升國家權力階層的機會,何以需要革命,又何來革命法權這樣的問題?何況,平民革命與法家的“明君權”豈不矛盾?

陳勝吳廣起義
但筆者轉念一想,情形又未必如此:**難道不正是因為“選天子”的理想自周制瓦解以來從未實現過,現代中國革命才獲得了正當性?從世界歷史角度看,近代西歐的革命訴求源於歐洲君主國的宗教內戰,人的自然權利因此成為“主權在民”的實際內涵。**與此不同,即便是中歐(如德國)或橫跨歐亞大陸的俄國,革命訴求實際源於世襲君主政體無法應對“主權在民”的新共和政體挑起的國際權力爭端。中國傳統的世襲君主政體即便老早就通過科舉制實現了國家權力階層的選賢制,依然無法應付險惡的現代國際政治狀態。換言之,廢黜世襲君主制的革命具有“現代根由”,而這個“根由”恰好與“選天子”的古代理想相符。這樣一來,“古今之變”就成了古今融貫。因此,作者禁不住説: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此話在今人看來不足為奇,但縱觀世界歷史,則不能不説這是一次歷史的大進步,遠超於歐洲、日本封建時期的思想。(頁240)
為什麼可以説“這是一次歷史的大進步”?因為,近代西歐的革命法理依據源於人的自然權利——所謂“天賦人權”,由此引導出來的革命結果未必是“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誰都清楚,如今的自由民主國家並非依憑德性選總統。相反,中國革命的結果卻始終不忘“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的古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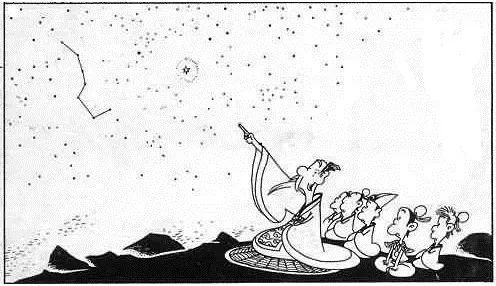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這當然不是蒙文通的看法,毋寧説,作者希望我們從蒙文通的“革命儒學”中進一步思考這樣的問題:即便《王制》為平民享有與貴族同樣的晉升國家權力階層的機會提供了法理,也不等於《王制》中的這一法理與現代的“主權在民”原則若合符節。蒙文通是睿智高士,不大可能真的不懂,平民革命與“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的革命並不同義。蒙文通專論今文家革命觀的主要文本有兩種,即作於1930年代的《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文言文)和作於1960年代的《孔子與今文學》(語體文),內容似乎完全相同。筆者拿不準,作者引用過的《孔子與今文學》中那段讚揚“人民大起義”的話,在《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中是否有過如此直白的表達。筆者倒是注意到,作者兩次提及蒙文通與革命軍儒將的私交,似乎並非信筆而至:在台兒莊戰役中戰死沙場的王銘章將軍(1893—1938)是四川人,參加保路運動時還不到20歲,但他的文史學識足以與蒙文通共同探討周秦民族史問題;嚴立三將軍(1892—1944)是湖北人,16歲就入陸軍小學,其文史學識卻非比一般,他懂得“學有漢宋之殊,宋儒於性德之奧抒發至矣,惟但有內聖而無外王,則於經世之旨不足”(頁195、236)。這讓筆者想到,中共將領中的儒將更多,《朱德詩詞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陳毅詩稿》(文物出版社,1979)、《葉劍英詩詞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就是證明。
看來,作者的曲折筆法隱含着這樣一種政治哲學思考:創生新共和的革命與其説是“中等社會”的革命,不如説是中國文明的中堅階層的革命。這個階層以德性唯尚,並不從屬於任何階層,因為,這個階層的形成端賴於以儒家教育為主體的中國文教不絕若線的養育。平民並非德性的符號,正如知識人甚至儒生也並非德性的符號——荀子説過,儒生也有“俗儒”“爛儒”。
**中國文明極高明道中庸的高明之處在於,讓無論出生於何種階層的人都向優良德性看齊。**周恩來出身官宦世家,是周敦頤的第33世孫,從小就自覺地以周敦頤為德性楷模,其高祖周元棠在青年時期留下的《海巢書屋詩稿》甚至陪伴他度過晚年的艱難歲月。毛澤東出身富農之家,其詩才因凌雲之志而蓋世無雙,作為王者其文史修養也前無古人。由此看來,**我們與其關注現代中國革命與古代儒家革命論的內在關聯,不如關注現代中國革命志士與古代德性論的內在關聯。**畢竟,這個問題關乎如何在後共和政治狀態中保有中國文明的優良德性傳統,以免中國文明的中堅階層整個兒成了自然權利論的信徒——這才是文明自毀的古今之變。

毛澤東與周恩來
餘論
作者在“導言”中提到筆者的舊作《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並謙虛地説,他的這部論著受到筆者舊著的啓發。確如作者所説,筆者舊著的主要目的“仍是想在中國傳統內部找到現代性危機的根源”,而作者得到的啓發是,從中“看到了一條彌縫傳統與現代裂痕的道路”(導言,頁13)。畢竟,由於時代語境和人世經歷的差異,筆者舊著關注的問題與作者所關切的問題有所不同。
1967年五月初的一天,筆者還未滿11歲,家父急匆匆跑回家,命我把家裏的《朱德詩詞集》燒掉。筆者後來才知道,這是“二月逆流”事件的結果。當時,學堂已經停課鬧革命,筆者在家無事,燒書時不是一把火燒掉,而是一頁頁撕下來,讀一頁燒一頁。筆者迄今感到百思不得其解:這樣的新共和開國元帥戎馬倥傯,為何與古人一樣詩情不斷,而且詩筆古雅?
家父命我一同燒掉的還有多卷本《沫若文集》,因為沫若自己宣佈,他過去的所有作品當付之一炬。筆者也是讀一頁燒一頁,那時筆者才小學四年級,僅僅對文集中講的故事感興趣。筆者迄今還記得的並非是沫若留學日本的經歷,而是他在北伐軍政治部的經歷和前往南昌參加起義途中的歷險。長大後每讀沫若的文史論著,筆者都會想起這位一代文豪曾有過的革命軍旅生涯。
《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沒有論及廖平,作者的這部論著讓筆者認識到廖平經學的革命品質,這是筆者的最大收穫。遺憾的是,作者沒有論及廖平的哲學。畢竟,廖平是哲人,其經學是哲學,如蒙文通所説,“廖先生説古文是史學、今文是經學(或哲學),的確是顛撲不破的判斷”(頁216)。因此,這部論著難免讓筆者想到一個問題:蒙文通的經學觀是廖平經學的推衍嗎?筆者的直覺恰好相反:蒙文通一再背離宗師。
蒙文通認同現代史學的觀點,《王制》不是孔子的設計,而是漢初博士的設計,這無異於腰斬了“知聖”論這一廖平經學思想的要核。自二變以來,廖平抨擊宋儒憑靠孟子建立的心性之學抹去人的德性差異不遺餘力,一以貫之地強調聖人與賢者的德性等差,蒙文通則要打通孟子心性之學與公羊學,因為他相信,“經歷了啓蒙的智識人不會再去相信那有如上帝般的孔聖人了”(導言,頁12)。就此而言,蒙文通的經學觀與廖平經學實不可同日而語。
2018年5月23日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本文轉載自“六點圖書”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