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上海書展|許子東:不能遺忘魯迅
澎湃新聞8月16日消息,8月15日的下午,上海市作家協會旁的作家書店座無虛席,趕來聽學者、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許子東教授和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陳子善教授對談的粉絲們擠滿了本不寬敞的空間。許子東這次主要是為了來宣傳他的新書《許子東現代文學課》。這本新書是他2016年起為香港嶺南大學的本科生開設的中國現代文學課的講稿,也是一本對現代中國文學感興趣的讀者都能讀懂的入門書。

上海國際文學周現場。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許子東教授和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陳子善教授。
在這場對談中,許子東着重談到了他重讀魯迅作品的過程中新發現的魯迅,當然,他也談到了張愛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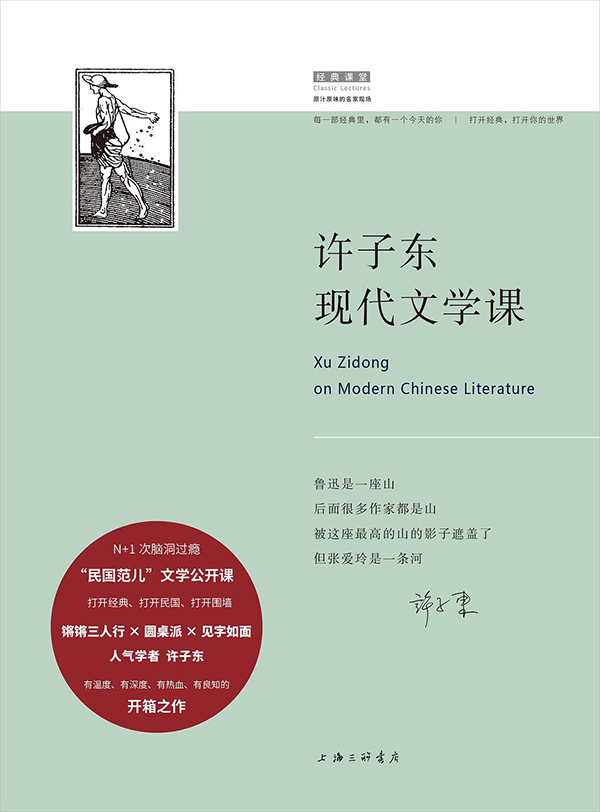
新書《許子東現代文學課》
魯迅最關心奴隸和奴才的問題
許子東認為,魯迅更應該感謝的城市其實是北京。“初到北京之時,魯迅還不是魯迅,而是周樹人。真正使他變成魯迅的,是北京這個城市。”按照一般的説法,魯迅原來是相信進化論的,他到上海以後才轉變為了一個階級論者。許子東則説:“我最近對於魯迅思想轉變論的一個觀點產生了懷疑,通過我大量的閲讀以後,我發現魯迅從來都是一個階級論者。”他提出魯迅一生關注的一個最大問題是“奴才”和“奴隸”兩者的區別,這也是魯迅一生無數次提到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奴隸’是一個有特殊意義的詞,在我們的國歌和國際歌的第一句,都用到了這個詞。而在中國這個詞有這麼特殊的地位,很大程度是因為魯迅。”許子東説,“我們現在提到奴隸,腦子裏會想到飢寒交迫、受苦的人。但問題是,如果穿得還好,吃得還好,如《卡拉馬佐夫兄弟》裏面寫的,‘又有了馬戲團,又有了麪包’,是不是人就願意放棄自由了呢?怎麼樣的情況才算是奴隸呢?”
魯迅曾在描述自己的經歷時提到“奴隸”一詞:袁世凱稱帝那一年,銀行宣佈鈔票不管用了,老百姓都非常驚訝。過了幾天又説,票子還管用,可以以之兑換銀元,但是兑換的比例很低。魯迅聽説存款貶值後,很有些恐慌,後來聽説鈔票可以換回現銀,雖折了大半,可是內心卻還是歡喜。他於是自嘲地嘆道:“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許子東笑着説道:“我回想自己,像這樣的事情似乎多了去了。比如,一次我把文章送到了編輯部,編輯部先説不能出版。過了幾天編輯部又打電話來告訴我:‘修改修改,刪掉一些,還能出版。’我當時心中大喜,而在喜悦當中我也產生了魯迅這種想法。”對於“奴才”和“奴隸”二者的區別,魯迅在三十年代這樣説道:“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隸,打熬着,並且不平着,掙扎着,一面‘意圖’掙脱以至實行掙脱的,即使暫時失敗,還是套上了鐐銬罷,他卻不過是單單的奴隸。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別人永遠安住於這生活。”魯迅的整體思想中一直貫穿着這個觀點。
許子東談到,魯迅對於整個中國歷史看得很悲觀。“魯迅認為中國過去只有兩個時代,一個是暫時坐穩了奴隸的朝代,一個是求做奴隸而不得的朝代。通俗地來説,這兩者的區別在於做了奴隸以後,是開心還是不開心。”魯迅在《華蓋集》中寫道:“暴君的專制使人民變成冷嘲,愚民的專制使人們變成死相。”魯迅對死相有一番解釋,稱其自己小時被大人訓斥,他低着頭看也不敢看,亦無法反抗,但是心裏卻是不同意的,臉上便裝出一副聽話的“死相”。“愚民專制與暴君專制的區別,就在於會不會講笑話:暴君的專制,允許人們冷嘲,但是不允許公開的反對,公開的反對肯定會被鎮壓;但是一些拐彎抹角的冷嘲,暴君是不理會的。”許子東説,“魯迅當時就生活在暴君專制的時代,他寫文章稍微一繞彎,袁世凱他們看不懂。所以北洋政府還給魯迅官職,一個月三百銀元,並沒有去找他麻煩。”
説到“奴才”時,許子東提到了魯迅的一篇散文詩《聰明人奴才與傻子》,他認為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奴隸與奴才的區別和兩者的對立。這篇散文詩的內容説的是一個奴才因為生活不好而抱怨,聰明人對他説將來會好的。奴才又碰到傻子,對傻子抱怨自己住的地方又熱又不透風,傻子便想去給牆上打個洞。奴才害怕主人生氣,就立馬叫了一幫奴才把傻子趕走。於是奴才去向主人邀功,説他們剛才趕走了一個要在牆上打洞的傻子,主人也答應獎勵他們。人們聽聞後紛紛慰問奴才,其中也包括那個聰明人。奴才感謝聰明人,説他有先見之明,聰明人説可不是麼。我們常説中國人是信奉中庸的。魯迅曾有個朋友給他寫信,其中談論到中國人的中庸。魯迅的答覆是:“我看未必。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做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兇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待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許子東説:“正如在生活中,如果某人完全失敗,他可能會把問題歸結到‘命’上,説自己倒黴,或者把整個問題推脱到歷史,説一句‘讓歷史來證明一切吧’。我覺得魯迅問題對於‘中庸’的解釋還是挺透徹的。”

許子東
張愛玲筆下最高尚的愛情是在她最差的作品裏
作為研究張愛玲的專家,許子東也少不了要談到張愛玲。他特別講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張愛玲在1945到1947年間一個字都沒寫,1947年認識電影導演桑弧後,她的創作往兩個方向發展,一是走向通俗,如寫了劇本《不了情》等,另一方面往革命文化發展。許子東特別提到張愛玲的《小艾》這個中篇小説,講的是一個受舊社會壓迫的女傭的故事。張愛玲離開上海到海外後就否定了這篇小説。
許子東談到張愛玲筆下所有的愛情都很自私、悲觀、不崇高,但唯有一次例外,《赤地之戀》女主角為了救男朋友,寧願去跟高官睡覺,這麼崇高的愛情恰恰出現在她寫得最差的作品裏,許子東認為這是非常弔詭的現象。
“虧得有晚年的《小團圓》,使我們看到,張愛玲不是一個拐彎的作家,她是一個繞了一個彎,又回來的作家。等到她沒有政治、經濟壓力的時候,她還是回來寫她自己。她自己否定了《秧歌》《赤地之戀》,按我的話説,就是入戲不深。”許子東談到。
許子東還提到18年前一次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會議上的小插曲,當時劉再復發言表示,如果中國現代作家只能選兩個,那就是魯迅和張愛玲,如果一定只能選一個,那一定要挑選魯迅。“劉再復認為張愛玲到了香港之後,變成了一個夭折的天才。當時夏志清也在,他馬上站起來反駁,他説張愛玲的夭折是為了錢。”許子東認為這代表了當時國內現代文學的主流觀點和海外現代文學研究的主流觀點的交鋒,到底魯迅和張愛玲誰才是夭折的天才。
許子東説他知道在座讀者更喜歡聽他講張愛玲,但他還是認為,再怎麼喜歡張愛玲都沒有問題,但是一定不能遺忘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