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修昔底德陷阱”是否真的適用於中美關係?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有關“修昔底德陷阱”的討論,從此概念2010年被美國哈佛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後就一直此起彼伏,未曾間斷。
認為“修昔底德陷阱”並非“鐵律”的學者們指出,艾利森對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中説過的那句名言(“伯羅奔尼撒戰爭無法避免肇因於斯巴達對雅典崛起的恐懼”)的解讀並非正解。還有一些人乾脆認為,這是“中國威脅論”的一個翻版。
特朗普上台後,中美兩國領導人之間一度出現的“融洽”氣氛,更加夯實了這種觀點。直到今年中美關係急轉直下,人們才開始冷靜面對現實,重新去掂量這一説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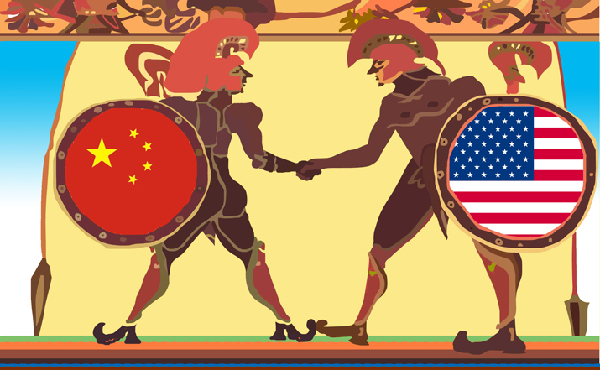
之所以出現對“陷阱論”的質疑,除了對修昔底德那句話以及古希臘那場戰爭的來龍去脈詮釋有所不同外,還有對雅典和斯巴達這兩個希臘主要城邦孰為“崛起國”孰為“守成國”的意見不一,以及對把這個語境放到中美關係中去加以討論不以為然。
其實,在整個這場討論中,許多人忽略了修昔底德這位古代哲人對人性的客觀認知。他認為,個體的政治行為與其所引發的國際政治關係,均建構在三個因素之上:恐懼、榮譽和利益。
既然這三個要素前兩者都與“人性”密切相關,利益本身也會激盪人性,那麼人與人和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就很難簡單地擺脱它們的影響。換而言之,建築在這三要素上的理論一定有相當大的普適性;即便不是“鐵律”,也能反映應當引以為戒和發人深省的規律。我們不該輕率地認為,只要竭力避免,不主動去“招魔”,就一定能繞過這個“陷阱”。
艾利森教授之所以提出“陷阱論”,從其本意上説,或許是不願意看到中美交惡和衝突,同時又認同修昔底德對人性的基本認知。而參與這個話題討論的學者中,很多卻是從各自的發展戰略和理想主義的角度去質疑和闡述的。由此得出的結論自然大相徑庭。
修昔底德本人對後世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就是創立了科學的歷史書寫法和現實主義政治學學科。那麼,我們在討論以他名字命名的“陷阱論”時,也應該秉承他的務實、客觀和科學精神,儘量擺脱各種意識形態的投射作怪。惟有這樣,我們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質,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脱困途徑。
美國的恐懼、榮譽和利益
若要把與人性密切相關的這三個特質用一句話來體現,恐怕莫過於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的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再次偉大”,説明美國人或美國政府認為自己的國家已不再偉大,已開始出現衰退跡象,或擔心偉大的美利堅在不久的將來有被其他某國取代的可能。美方強烈的危機感顯而易見,而這個危機感來自何處呢?在修昔底德眼中,答案也許只有一個:恐懼。現在的問題是,美國人的擔心是否有道理?有。
從1776年立國至1991年冷戰結束,美利堅在215年中,完成了從殖民地到世界唯一強國的成功之路。
它在頭一百年裏首先建立國內市場的統一(go west, young man去西部,年輕人/Manifest Destiny昭昭天命);
1882年,愛迪生髮明的第一個商用電力系統,使美利堅率先開啓了第二次工業革命,進入電氣時代,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
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利堅再攀高峯,實力急劇膨脹,到二戰結束時,它已擁有西方世界工業總產量的60%,對外貿易的三分之一,黃金儲備的四分之三,是當之無愧的世界最大資本輸出國和債權國;
1944年由44國簽訂的“佈雷頓森林協議”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系;美國戰後的軍力空前提高,軍事基地遍佈世界各地,成為世界頭號軍事強國;
1991年,蘇聯解體,其東歐勢力範圍也隨之分崩離析,曾經的美蘇兩極世界變為美國一霸獨強;
二十世紀後半葉,美國再開先河,啓動了信息革命,夯實了其主宰世界的地位。
美利堅始所未料的是,在自己“獨步世界”“傲視天下”的美好時光裏,昔日的“東方病夫”中國竟然在短短30年裏創造了美國兩百年才實現的奇蹟。最讓華盛頓捶胸頓足的是,這個奇蹟是中國人用自己的才智和勤奮藉助美國建立的國際體系“借雞生蛋”創造的。
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故事”似乎比當年的“美國故事”更不可思議。
“修昔底德陷阱”發明者艾里森在其《註定一戰:美國和中國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一書中指出,美中兩國的實力對比在1980年以後的30多年裏發生了巨大變化。二戰剛剛結束時,美國經濟在全球市場中所佔比例約50%,1980年時下降至22%;中國經濟自1980年代改革開放騰飛以來,美國經濟在全球市場中的佔比進一步下滑到2016年的16%,而中國則從1980年的2%,上升到2016年的18%。
這就不奇怪,為何對中國的擔心和不安會迅速在美國政界、軍界、學界、商界和民間瀰漫開來。那麼,“恐懼”一旦存在,人們一般的反應會如何呢?在期望逆轉和竭力維持的同時,人們會過度敏感,下意識和有意識地誇大外來威脅,會懷念過去的強盛,喚醒民族榮譽感。在這樣的背景下,特朗普的口號的確產生了效應,贏得了選票。
“讓美國再次偉大”,這裏既有榮譽,也有使命。恢復榮譽,無非就是要保住美利堅在全球的根本利益。將利益最大化,這才是個人和國家行為的最大原動力。
因此,特朗普及其團隊對華採取的一系列動作首先是基於在“恐懼、榮譽和利益”驅動下對中國崛起之速度和程度的一種判斷。顯然,美國認為中國的崛起已經危及到美國當前以及長遠的利益。去年年底,特朗普在《國家安全報告》中,正式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者”。所謂“模式之爭”“價值觀之爭”“體制之爭”雖然存在,但在修昔底德的體系裏,歸根結蒂還是那三個要素作祟的結果。
“陷阱論”——以中美的亞洲利益為例
那麼,“修昔底德陷阱”是否真的不適用於中美關係?
我們暫且不去糾結艾利森教授在書中例舉的那些歷史案例是否貼切,因為時移世易,我們終難找到能嚴絲合縫對上的例子。實際上,這些理論和案例更像星座算卦,每個人似乎都能從中看到符合的方面,也能看到不符合的地方。
我們暫且也不必把這個理論放到世界範圍內去檢驗,因為把一個尚不能算作國際強權的中國與一個徹頭徹尾的全球霸權美國放到這個語境中去比較,“陷阱論”會顯得相當牽強。
中國當然也有自己的全球戰略,但尚無力全球布控。若要説中國已經在這麼廣的範圍內對美國構成“威脅”,恐怕不是危言聳聽,就是別有用心。
所以,我們不妨把中美關係放到東亞地區去檢驗,或許更容易判斷出“修昔底德陷阱”是否適用於中美關係。
1)中美在東亞的自我定位
中國屹立亞洲東方,這是地理位置決定的,搬也搬不走,挪也挪不動。
歷史上,中國由於其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曾對東亞地區有過舉足輕重的影響。如今,無論是先進的日本和韓國,還是發展中的東盟諸國,雖然都強調自身文化的獨立性,卻無法否認中華影響的作用。
因此,“中國夢”所要振興的就是曾經對東亞和世界有過不小影響的中華盛世。不僅如此,在大部分中國人(包括領導人)的心目中,中華對東亞的影響雖然時弱時強,但基本沒有中斷過。所以,他們更傾向於説:東亞是中國的傳統“地盤”。
但實際上,中國在東亞的影響早就出現斷層。拋開16世紀早期麥哲倫對菲律賓的殖民嘗試(他本人亦在此地被土著人砍死)以及葡荷殖民者對馬來西亞的控制、17世紀初荷蘭對印尼的殖民、17世紀上半葉台灣44年的荷西時期不算,從1839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近代塑造和影響東亞的首先是歐美殖民列強。
後來,崛起的日本想以亞洲國家身份將歐美影響趕出東亞,結果失敗。二戰後至冷戰結束前,亞洲東部除中國、北朝鮮和印度支那三國之外,其他均在美國的影響和控制之下,它們中的許多國家與美國都保持着軍事同盟關係。
中國重新對東亞產生影響則是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後的事情了,而且,這種影響或吸引力更多不是通過政經和軍事實力或理念輸出贏得的,而是通過開放後的市場而產生的。
因此,雖然中國從認知上覺得東亞是自己的傳統“地盤”,但除了兩次熱戰之外(朝鮮戰爭和越戰),它在相當長時間內一直未去觸碰美國在東亞的存在和地位。當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司空見慣的豪邁心氣漸漸消退之後,中國看清了自身與美國懸殊甚大的力量對比。改革開放其實就是這份清醒帶來的產物。
那個時候,再有想象力的美國人恐怕也不會勾勒出一幅中國在短時間內趕超自己的畫卷,艾利森教授若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提出“陷阱論”,肯定會被人恥笑為“杞人憂天”。

2)通往陷阱的路徑
本世紀初(2001年)發生的兩個重大事件成為改變中美關係的里程碑:一個是基地組織(al-Qaida)在9月11日對美國本土發動的恐怖襲擊,另一個是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WTO)。
此後的幾年中,美利堅帶着若干“鐵哥們”忙着在阿富汗(2001年)和伊拉克(2003年)等地剿滅恐怖主義,為“9·11”雪恥。中國則在新融入的資本大家庭中學着如何走路、快行和跑步,“悶聲發大財”。
隨着國力的增長,中國變得越來越自信,對自己在東亞的話語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與“地緣野心”無關,而是實力的自然流露。直到中國在千禧過後的第十個年頭接受日本倡導的所謂“東亞共同體”設想後,情況才急轉直下。
以下列出的時間節點和重大事件清晰地描寫了通往“陷阱”的路徑:
2004年,在亞洲金融風暴影響下形成的“ASEAN+3”(東盟10國+中日韓3國)峯會框架內,中日韓啓動三國政府首腦不定期磋商機制。
2005年,“10+3”吉隆坡峯會上首次明確以“東亞共同體”為中心議題。
2009年,中日韓領導人北京峯會期間,敲定了未來合作的大方向:共建“東亞共同體”。
2010年6月,美國國防部長蓋茨(Robert Gates)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安全會議上,就中國艦船在宮古海峽公海訓練一事,公開指責中方,力挺日本;8月,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克勞利明確表示:“釣魚島在日本政府的行政管轄之下,而《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聲明,該條約適用於日本管轄的領土;9月,沉寂多年的“釣魚島”領土糾紛因撞船事件而突然爆發。
2011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在APEC峯會上高調提出“轉向亞洲”戰略。
2012年3月,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購買釣魚島設想;6月,美國防長帕內塔(Leon Panetta)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提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Asia-Pacific Rebalance);9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彥決定以政府名義購島,使釣魚島國有化,中日關係急劇惡化。
2013年,菲律賓向國際海洋法法庭提出、再由時任法庭庭長的柳井俊二(對華強硬的日籍法學家)任命仲裁人對中國提出仲裁案。
2014年4月,“美國-東盟防務論壇”在夏威夷召開,美國首度以東道主身份主辦美國與東盟之間的部長級非正式會議;5月,中國外長在上海“亞信會”第四次峯會上提出“亞洲事務應由亞洲國家主導”的理念。
回顧這段歷史,不難看出,“東亞共同體”——這個由日本倡導、韓國積極推動和中國最終接受的“未來暢想曲”給美國敲響了來自遠東的警鐘。
3)“東亞共同體”——美國的噩夢,中國的一劫
本來,一個由歐洲盟友組成的政治聯盟(歐盟)和統一貨幣(歐元)已讓華盛頓非常頭疼,如今,一個以歐盟和歐元為榜樣的東亞經濟和貨幣聯盟也在醖釀之中,這對美國來説不啻為一個很大的噩夢。
美國當時“大驚失色”和“細思極恐”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中國的力量已不能小覷,必須加以遏制;第二,自己的盟友日本有了異心,必須嚴加管束。
石原慎太郎是2012年3月提出購島建議的,但正式代表東京表態要購島是4月份在美國華盛頓的一次演講中,再次露出購島與美國千絲萬縷的聯繫。那麼,這位購島的始作俑者何許人也?為何偏偏是他出面做這件事呢?

石原慎太郎(圖/東方IC)
右翼政治家石原一貫反對“中國民族主義”。如果只是這一身份,他出面來購島必然會引發各種議論和猜測,但此人還是個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干將:1989年,他和索尼公司創始人盛田昭夫合著了那本很有名的書《日本可以説不》,對保護國美國開炮。這就為他這次出面購島披上了一件“不偏不倚”的外衣。
今天,我們雖然還沒有確切的證據證明“釣魚島危機”的突然爆發是美國幕後操縱的結果,但從上面羅列的一系列事件中不難得出其中的因果聯想。美國有動機、有傳統、也有能力做這類動作。
應該説,美國成功了:中日關係在過去的八年裏一直處於低谷,彼此之間的信任幾乎蕩然無存,留下的溝壑至今未能完全填平,“東亞共同體”作為一個令美國驚怖的願景也隨之歸於沉寂,無聲無息。
當然,“東亞共同體”的夭折不僅有美國因素在起作用,中日之間在爭奪未來主導權問題上未能及時達成一致,也是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2010年,中國的GDP正式超過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北京躊躇滿志,不願讓引領亞洲的機會像“大東亞共榮圈”時那樣再次旁落日本,而日本不久剛被迫交出第二把交椅,心有不甘,不願用自己親手染出來的布料替別人做嫁衣。
就這樣,一場看似偶然的“釣魚島危機”令“東亞共同體”這個未來暢想曲戛然而止,至今未能再續。
也正是在中日韓推動“東亞共同體”的當口,太平洋彼岸的艾利森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理論。這是巧合嗎?鑑於這位哈佛教授曾在兩屆美國政府中擔任過要職(里根總統的國防特別顧問和克林頓任內的國防計劃助力部長),深諳冷戰時期的克敵技巧,我們似乎有理由去質疑他提出“陷阱論”的動機,但我們不能,也不應該不嚴肅地去對待他做出的具體分析和提出的建議。
譬如,他指出,“陷阱”很大程度上源自誤解、誤讀和誤判;中美兩國同時存在的民族主義傾向(“中國夢”和“讓美國再次偉大”)一旦碰撞,後果不堪設想。他建議,雙方應放下“理想主義”大旗,迴歸以利益為基礎的現實主義談判,明確界定各自的核心利益,以此增加互信。
4)戰略誤判是跌入“陷阱”的機關
的確,“陷阱”的產生與各方根據自身的經歷、立場、利益和視角對形勢作出的種種判斷(也包括很多誤判)密不可分。
美國之所以決心遏制中國的崛起,因為它的判斷正是基於自身的經歷:1823年,時任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發表國情諮文,表明拒絕歐洲列強對美洲的殖民,歐洲列強如果繼續這麼做將被視為侵略,美國必將介入。這就是排除西葡英影響、將美洲當作美洲人的美洲的“門羅主義”。
基於這段經歷,美國當然擔心自己會重蹈當年英國在美洲的覆轍,被中國排擠出東亞。我們可以不説美國是在“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戴着這副有色眼鏡的美國人,怎麼看中國所作所為,都覺得透着中國版“亞洲門羅主義”的氣息。
不僅美國有這個擔心,它在東亞的盟友也逐漸產生了類似的擔心。它們雖然未必真正喜歡美國,但與新崛起的中國相比,似乎更希望美國在亞洲繼續存在。這裏有許多心理和歷史因素在起作用:拿日本而言,它承認美國比自己強,卻無法接受中國對其後來者居上的趕超;再譬如新加坡,自李光耀時代以來,它一直在大國之間保持平衡,但內心還是傾向於西方。
中方一再強調 “太平洋之大,完全能容下中美兩國”。該比喻的本意是讓美國人不要緊張和猜忌,中國即便影響力增加也不會危及到你美國在亞洲的地位,中國追求的是“和平共處”,而非“霸權易手”。
但在美國人的耳朵裏,此話語焉不詳、似是而非,甚至還可以將之解讀為“閃爍其詞”“話裏有話”。他們會問:“你中國是想和我美國在東亞利益均沾嗎?”對於在亞洲地位第一的美國而言,“均沾”就意味着要它放權讓利。
在東亞,美國是守成一方,中國是崛起新強,這是個不爭的事實。不管中方是否承認或者願意,中美在東亞其實已經接近或早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現在就看雙方如何看待和處理這個危機了。
身處陷阱邊緣或其中的中美兩國,彼此的較量大致會經歷以下兩個階段:
A)美國拒絕放權讓利
根據美國的傳統做派,美國是不會主動放權讓利的。這裏有價值體系、實際國力和自信滿滿等因素在起作用。美國國力雖然有所減弱,但還遠遠未弱到必須讓美國接受崛起國與自己分權分利的地步。
中美兩國如今都沉浸在各自的“復興夢”之中,這些理想主義的高調在本國固然能凝聚民意,捍衞榮譽,卻也可能嚴重影響國內的決策環境和國際運作中的迴旋餘地。從目前的情況看,要讓美國主動放權讓利不太現實,相反,特朗普的目標是要讓中國放血讓利。
B)美國不得不放權讓利
如果中國這次抗過了美國的第一波“組合拳”打擊,在經歷了短暫的波折後依然呈不可逆轉的發展勢頭,甚至更強,也就是美國的如意算盤落空,那麼,華盛頓有兩個選項:要麼破釜沉舟,與中國展開魚死網破的公開決鬥,要麼面對現實,重建平衡,答應與中國共享亞太地區主導地位。
從眼下的情況看,中美較量顯然還處於第一階段。守成的美國手裏牌似乎不少,但其最大的軟肋就是國內政局可能出現的變化;崛起的中國雖然在衝突中處於守勢,但其政體更具延續性和動員力,而且相對穩定,時間會給出答案。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