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進鋒 | 西周時期的縣
一、引言
縣在春秋時期得以廣泛設立,戰國以後逐步成為地方行政區劃中的重要單元。實際上,春秋時期的縣並不是忽然出現的,而是從更早的歷史時期發展來的。傳世文獻中有如下的一些記載:
東南四百五十里,曰長右之山,無草木,多水。有獸焉,其狀如禺而四耳,其名長右,其音如吟,見則郡、縣大水。(《山海經•南次二經》)
又東三百四十里,曰堯光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金。有獸焉,其狀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蟄,其名曰猾褢,其音如斫木,見則縣有大繇。(《山海經•南次二經》)
有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後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後。夏後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範氏其後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淮南子•氾論訓》)
一般認為,《山海經》是禹、益口述而世代相傳下來的,而禹、益是堯、舜時期的人。根據以上材料,堯、舜、孔甲、桀、紂時期似乎就已經有了縣。然而,這些資料多是後人追述,其內容是否為當時歷史的真實反映,值得懷疑,誠如顧頡剛所言,這些史料“在我們的理智裏已失卻了信仰”。客觀判斷,堯、舜、孔甲、桀、紂時期應當還沒有縣。在商代甲骨文中,並沒有出現“縣”字,這個時期也沒有縣。
探討春秋以前縣的發展歷程,需要從西周時期説起。
二、西周時期有無縣?
西周時期有無縣?這其中,最關鍵的點就在於免簠銘文(《集成》4626,西周中期)“鄭還 (林)、眔吳(虞)、眔牧”和元年師
(林)、眔吳(虞)、眔牧”和元年師 簋銘文(《集成》4279,西周晚期)“豐還左右師氏”中的“還”如何釋讀。
簋銘文(《集成》4279,西周晚期)“豐還左右師氏”中的“還”如何釋讀。
關於“還”字,過去學者提出如下一些釋讀方案:
(一)讀為“苑”。郭沫若主之、吳鎮烽從之。與之類似的,《銘文選》認為“還”讀為“園”,通假為“苑”。
(二)讀為“鹹”。楊樹達主之,他認為鹹應與(林)連讀;鹹林為地名。
(三)認為通假為“垣”,又或“假為環塗之環”,為環城之道。陳夢家主之。
(四)釋作“積”,通假為“環”。熊梅主之。
“還”在免簠和元年師簋銘文中都出現了,而且所處的語境近同。在這種情況下,檢驗某個“還”字釋讀方案是否正確的標準應該是:首先看其文字、音韻、訓詁是否正確;其次看它能否同時解釋通這兩篇銘文。如果某一方案在文字、音韻、訓詁正確的情況下,只能説通一篇銘文,而不能解釋通另外一篇,可以基本判斷其説不正確。
在(一)中,郭沫若、吳鎮烽在考釋過程中,並沒有對其説展開,因而我們並不知道其説法的具體指向,所以並不好辨析。好在《銘文選》進行了詳細的論述,我們可以通過縷析它的正誤,來看(一)的正確性。

郭沫若(左一)
《銘文選》在釋讀免簠銘文的時候,似乎將“苑”看成是和林、虞、牧性質相似的官職,類似於《周禮》中的載師或場人;然而,在釋讀元年師簋銘文的過程中,卻將“豐苑”看成是豐京的王苑,為一塊區域。二者的含義有差別。而且,《銘文選》似乎認為在免簠銘文中,苑和林、虞、牧是並列的,為頓號;在元年師簋銘文中,豐苑和左右師氏是相連的,左右師氏是捍衞豐苑的。二者的標點也有差別。兩篇相似的銘文,方案(一)理解起來卻有這麼多的差異,只能説明釋“還”為“苑”有問題。
在(二)中,楊樹達是在釋讀免簠銘文過程中,提出這種看法的。然而,“還”與“鹹”的古音並不相同,二者並不能通假;同時,用“鹹”來解釋元年師簋銘文的“還”,明顯扞格不通。可見,釋“還”為“鹹”不正確。如果按照(三),將“還”解為城牆或道路,則很難與之後的林、虞、牧或左右師氏來連貫理解,那麼,這種説法也不正確。在(四)中,作者提出“還”先讀為“積”,再通假為“環”。這種方案,轉了一大圈只不過到了別人的原點,顯然迂曲。同時,在第一步上,熊梅舉出了證據,但是在第二步上,她沒有舉出通假上的證據,存在着邏輯紕漏。黃錦前更是舉出諸多的金文證據,論證熊説不可信,可見,方案(四)也不正確。
1987年,李家浩在阮元、唐蘭等人的基礎上,釋“還”為“縣”,並在字形和字音兩方面進行了論證。其説因為證據確鑿,獲得了廣泛的認同。這樣,西周時期存在縣逐漸成為學者們的共識。
**在此,我們還可以補充一些西周時期存在縣的傳世文獻證據。**其一,《逸周書•作雒解》記載:
(周公)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為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
這則材料,過去被研究者普遍地忽視,主要原因在於大家認為“《逸周書》材料很有問題,不便充分相信”。然而,根據學者最近的研究,《逸周書•作雒解》是一篇反映西周歷史的可靠文獻。根據這則材料,周公在營建成周的時候,在郊、甸地帶設置了百縣。換句話説,西周時期是有縣的。
其二,春秋時期的魯國曾發生冰雹災害,執政者季武子向大夫申豐詢問關於制止冰雹的方法。申豐在回答問題的時候,言及了古代的縣制,他説: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遍,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悽風,秋無苦雨,雷不出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左傳•昭公四年》)
申豐在此所説的“古者”,應當不是春秋時期,而更像是西周時期。因為其間提到了“縣人”,所以這段文字也是我們瞭解西周縣制的珍貴史料。關於這段引文中的幾個職官,杜預解釋為“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輿、隸皆賤官”。楊伯峻進一步註解道:
據《周禮•遂人》“五縣為遂”,《地官》亦有“縣正”,縣人或即縣正。
而《周禮•地官•縣正》明確記載了縣正的職掌,“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裏,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可見“縣正”是管理縣的官員。這則材料進一步證明西周時期存在縣。
三、西周縣的第一種形態:縣邑之縣
既然西周時期存在縣,那麼此時的縣呈現怎樣的形態?根據相關研究來看,學者們的意見可以分為兩類:
1.多數的學者認為西周時期的縣只有一種形態。在這點上,不同的學者看法還有差別。其中,李家浩、魯鑫、李峯、黃錦前等人的看法相似,認為縣是國都或大城邑四周的廣大地區。與之不同,唐蘭、王暉等人似乎認為西周時期的縣已經等同於後來的郡縣之縣了。
2.還有學者認為西周時期的縣有兩種形態,分別為:中心城邑的周邊地區,外在呈現環狀地帶;包含中心城邑及其轄區在內的整個地區,外在呈現塊狀區域。
諸多説法到底誰對誰錯?接下來,我們將通過進一步的研究來辨析。
上文提及的《逸周書•作雒解》記載:
(周公)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
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為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郡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農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凡工、賈、胥市、臣僕,州、裏俾無交為。
《説文》:“郛,郭也”;《禮記•禮運》:“城郭溝池以為固”,孔穎達疏:“城,內城;郭,外城也”;潘振謂:“郭謂之郛,外城也”。《説文》:“制,裁也”;《大戴禮記•千乘》:“陳刑制闢”,王聘珍《解詁》:“制,裁製也”。《左傳•襄公二十一年》:“罪重於郊、甸”,杜預注:“郭外曰郊,郊外曰甸”;黃懷信也謂:“郊,邑外;甸,郊外”。以上引文可以根據含義分為兩段:第一段總講周公營建成周的狀況,以及成周的內外城規模和位置;第二段講洛邑郊、甸區域的範圍、具體劃分和不同人羣的居住區域。
這段材料只有第二段文字中出現了縣,説明當時的洛邑只在郊、甸地區設置了縣。根據內容,周初在營建成周的時候,曾將成周的郊、甸地區分成100個縣,每個縣有4個郡,郡下有鄙。同時,這些縣有大小之別:大縣築城,邊長為王城邊長的三分之一;小縣築城,邊長為王城的九分之一。
從中可以看出這些縣的特點:位於成周這樣的城市的郊區地帶;大小有別,但是都築造了城池;數量很多,有100個,是可數的;縣下還設置了郡,郡下設置了鄙;這些縣是附屬於成周的。
這段史料中出現了縣、郡的概念,那麼這些縣是否就是郡縣之縣?此處有必要先介紹一下“縣”的幾種含義和各自特徵。**根據研究者的總結,先秦時期的縣主要有三種含義:縣鄙之縣;縣邑之縣;郡縣之縣。後兩種縣,雖然在形態上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差別,主要體現在:其一,郡縣之縣不是采邑,而完全是國君的直屬地;其二,郡縣之縣的長官不是世襲,可隨時或定期撤換;其三,郡縣之縣的幅員或範圍一般經過人為的劃定,而不是天然形成的;其四,郡縣之縣以下還有鄉里等更為基層的組織。**筆者在綜合各種資料後,還再補充一個標準,即:其五,一個縣能成為郡縣之縣,還必須是郡下有縣,縣上有郡。比較來看,《逸周書•作雒解》的這段材料中雖然出現縣、郡的概念,但並不符合郡縣之縣的標準,只能是縣邑之縣。
總之,在《逸周書•作雒解》中,縣位於成周的郊區地帶;大小有別,數量很多;縣下還有郡、鄙這樣更小的社會組織;附屬於成周。它們是位於城市郊區地帶的附屬於城市的小邑,是縣邑之縣。這是西周時期縣的第一種形態。

西周娘娘寨城址
四、西周縣的第二種形態:縣鄙之縣
西周金文中的縣,和傳世文獻中的不一樣,呈現出另外一種形態。
金文中的縣主要見於以下兩篇青銅器銘文:
唯三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令免作司土(徒),司奠(鄭)還(縣)(林)、眔吳(虞)、眔牧。賜織衣、鑾。對揚王休,用作旅彝,免其萬年永寶用。(免簠銘文,《集成》4626,西周中期)
唯王元年四月既生霸,王在淢,甲寅,王格廟,即位,公入佑師,即立中廷。王呼作冊尹克冊命師,曰:“僃於大左,官司豐還(縣)左右師氏。易(賜)女(汝)赤巿、冋黃(衡)、麗般,敬夙夕用事”。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命,用作朕文祖益仲尊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元年師簋銘文,《集成》4279,西周晚期)
與討論相關的信息都位於以上劃線的部分,我們將重點縷析之。
免簠銘文中的鄭,即周穆王所都的西鄭,在陝西華縣北;林、虞、牧,分別相當於《周禮•地官》中的職官“林衡”“山虞”和“澤虞”“牧人”。元年師簋銘文中的“大左”是官名,“僃於大左”即職掌大左;“豐”即豐京,是周文王所營建的都城;“左右師氏”相當於左右虎臣、左右走馬,是一官職全稱。
在免簠銘文中,“林、眔虞、眔牧”不是與“鄭縣”並列的,而是“鄭縣”內部的職官。這一方面是因為“林、眔虞、眔牧”是職官,“鄭縣”是地區,二者性質根本不同,不宜並列;另一方面是因為將“林、眔虞、眔牧”看成是“鄭縣”內部的職官,“林、眔虞、眔牧”的地址就比較明確,符合金文的通常規則。同樣道理,在元年師簋銘文中,“左右師氏”是“豐縣”內部的職官。所以,免簠銘文的“鄭縣”與“林、眔虞、眔牧”之間、元年師簋銘文的“豐縣”與“左右師氏”之間不能斷讀,而應連起來讀。
關於以上銘文中“縣”的性質以及與“鄭”“豐”之間的關係,之前的學者有兩種看法:
**(一)認為“縣”是郡縣之縣;“鄭縣”“豐縣”是同位語結構,“縣”就是“鄭”“豐”;“鄭”“豐”本身就是縣。**如唐蘭,他指出:
由此可見此銘(筆者注:即免簠銘文)鄭寰即鄭縣。《禮記•王制》“天子之縣內”,鄭玄注:“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商頌•玄鳥》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周亦曰畿”。《周書•作雒》:“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為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可見周制縣大於郡,縣大約方百里,但由於地理不同,不能劃一,所以有大縣、小縣之分。《左傳•哀公二年》趙簡子説“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還用周制,秦制則郡大於縣。
可見唐蘭似乎將免簠銘文中的“縣”看成是郡縣之縣;他還認為鄭本身是縣。持相同看法的還有王暉。他認為西周金文中的“縣”,和春秋以及戰國以後的“縣”在性質上是基本相同的,即將西周金文中的“縣”看成是郡縣之縣;他還將鄭、豐本身看成是縣。

金石學家、文字學家唐蘭
這種看法不正確。因為林、虞、牧、左右師氏都是城市郊區的職官,它們不可能位於城市的內部。請看以下證據:其一,西周金文中有如下的內容:
唯十又二月初吉丁丑,王在宗周,格於大廟。榮伯佑同,立中廷,北向。王命同:“左(佐)右(佑)吳大父,司場、林、虞、牧。自淲東至於河,厥朔至於玄水。世孫孫子子左(佐)右(佑)吳大父,毋汝有閒”。對揚天子厥休,用作朕文考艽仲尊寶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同簋蓋銘文,《集成》4270,西周中期)
唯十又二月初吉,王在周,昧爽,王格於太廟,邢叔佑免,即命,王授作冊尹書,俾冊命免,曰:“令汝疋周師,司林。賜汝赤巿,用事”。免對揚王休,用作尊簋,免其萬年永寶用。(免簋銘文,《集成》4240,西周中期)
第一篇銘文中的林、虞、牧,與免簠銘文同。“場”與林、虞、牧並列,職務也相當,即《周禮•地官》中的“場人”。“自淲東至於河,厥朔至於玄水”,意為從淲水向東一直到黃河,其北方至於玄水;是場、林、虞、牧所在的具體區域。那麼,場、林、虞、牧似乎是位於城市的郊區地帶。第二篇銘文中的林,與免簠銘文中的林衡相同;此處的林衡本是由周師來管理的。根據學者的研究,西周時期設置了林、虞、牧類的職官來管理宗周畿內的山林藪澤,而山林藪澤往往位於城市外圍的郊區地帶,所以,此處的林衡位於城市的郊區。以此來看,免簠銘文中的林、虞、牧也位於城市的郊區。
其二,在元年師簋銘文中,“左右師氏”是豐地軍隊內部的職官。我們知道,**西周時期的城市從中心到外圍可分為“國”和“野”兩大區域,二者以“郊”為分界線;“國”從內到外又包括“國中”“郊”兩部分。周代在郊的區域設立“六鄉”;在野的區域設立“六遂”。而西周軍隊的編制和鄉的組織密切對應,軍隊的成員也主要來自鄉內居民。**換言之,左右師氏主要位於豐地的近郊,是郊區職官。
在(一)中,專家們把鄭、豐本身看成是縣,照此下去,“林衡”“山虞”“澤虞”和“牧人”“左右師氏”職官也位於作為城市的鄭、豐之內,即處於城區地帶。這與“林衡”“山虞”“澤虞”和“牧人”“左右師氏”位於城市郊區的事實,是矛盾的。據此,看法(一)並不正確。
**(二)認為“縣”是縣鄙之縣;“鄭縣”“豐縣”是偏正結構,“縣”是中心詞,“鄭”“豐”是修飾詞;“鄭縣”“豐縣”即指鄭的縣、豐的縣,為鄭、豐周圍的郊區地帶。**如李家浩,他認為:
周代的“縣”是指國都或大城邑四周的廣大地區,如《國語•周語中》:“國無寄寓,縣無施捨……國有班事,縣有序民。”這裏所説的“國”即指國都,“縣”即指國都四周的廣大地區。天子稱王畿為縣即由此而來。……西周文字資料中的“縣”屬於縣鄙之“縣”。
可見李先生將西周金文中的“縣”看成是縣鄙之縣,具體指代城市四周的地區。魯鑫贊同這種説法。李峯也認為這個區域“指的是一個城市的周邊地區”。黃錦前持相同的看法,他認為西周金文中的“縣”性質為縣鄙之縣,與後世郡縣之縣有別。
按:我們認為看法(二)是正確的。這是因為:
第一,縣在《左傳》中有用作郊區的例證。《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齊國的晏子説“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即郊野之地的人,進入國從政,縣也指郊野之地。據之,西周金文中的“鄭縣”“豐縣”就是指城市鄭、豐的郊區地帶。
第二,西周金文中一些詞語用法,也可以證明“鄭縣”“豐縣”是偏正結構,而非同位語結構;同時證明“縣”是城市的郊區地帶。西周金文記載:
唯正月初吉丁亥,王格於康宮,仲倗父內佑楚,立中廷。內史尹冊命楚:“赤雝巿、鑾旂,取五寽。司鄙,官內師、舟”。楚敢拜手稽首,揚天子丕顯休,用作尊簋,其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楚簋銘文,《集成》4246—4249,西周中期)
王曰:“恆,令汝更喬克司直鄙。賜汝鑾旂,用事。夙夕無廢朕命”。恆拜稽,敢對揚天子休,用作朕文考公叔寶簋,其萬年子子孫孫虞寶用。(恆簋蓋銘文,《集成》4199、4120,西周中期)
以上銘文中和直都是城市。“鄙”和“直鄙”是指和直的郊區地帶。所以,“鄙”和“直鄙”都是偏正結構,而非同位語結構。“鄭縣”“豐縣”與之結構相同,語境類似,當也是偏正結構。
不僅如此,古漢語中的縣、鄙時常同義,因而有很多“縣鄙”連稱的情況,如《左傳•昭公二十年》“縣鄙之人,入從其政,逼介之關,暴徵其私”、《呂氏春秋•孟夏》“命司徒循行縣鄙”,研究者因而指出“縣、鄙是對一件事物的不同稱呼,只有用詞上的不同……其所指是基本一致的,都是指環繞在中心城邑周邊的直轄區域”,可從。所以,“鄭縣”“豐縣”和“鄙”“直鄙”性質也相同,是城市周邊的郊區地帶。
總之,免簠銘文、元年師簋銘文中的“縣”是縣鄙之縣;“鄭縣”“豐縣”即指城市鄭、豐周邊的郊區地帶。這種縣的特點有:環繞城市地區,呈環形;範圍不定;是不可數的。西周時期的縣鄙之縣是城市周邊的郊區地帶。此可謂西周時期縣的第二種形態。
五、從金文“縣”字形義看西周時期縣的形態
接下來,我們可以從金文中“縣”字形義來進一步考察西周時期縣的形態特徵。
西周金文中有兩種形態的“縣”字。第一種形態作:

縣妀簋銘文,《集成》4269,西周中期
從字形上看,該“縣”字有三個組成元素:木、倒首、系。
《説文》謂“縣,系也”,字義應當是根據小篆字形而來的。但是,《説文》字義並沒有包含小篆中“倒首”的元素,更沒有體現金文中“木”的元素。從金文字體來看,這種形態“縣”像倒首懸繫於樹木上,表示附屬大型地域社會組織的小型地域社會組織。“縣”字的這種特徵可以得到字義和語境的印證。春秋晚期齊國的叔夷鍾(《集成》273)、叔夷鎛銘文(《集成》285)記載:
唯王五月,辰在戊寅,次於緇涶。……公曰:“夷……餘賜汝萊都脒膠,其縣三百。餘命汝司台萊邑,造徒四千,為汝敵寮。”
在銘文中,夷受賜的物品,既有萊都脒膠,又有其縣三百。萊,萊國;脒膠,就是萊都;萊都脒膠,是同位語結構。“其縣三百”就是位於脒膠周邊郊區地帶的、依附於脒膠的300個縣。可見此處的300個縣就位於城市脒膠的郊區,而且依附於脒膠。其中脒膠是大型地域社會組織,縣是小型地域社會組織。其中“縣”的字形就作“、”,與西周金文中的“縣”是同一形態。叔夷鍾、叔夷鎛銘文中縣的形態,和“縣”字形的特徵是一致的。
第二種形態的“縣”字形作:

免簠銘文,《集成》4626,西周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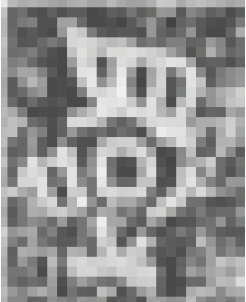
元年師簋銘文,《集成》4279,西周晚期
即《説文》中從辶從睘的“還”字。上文已經指出它通假為“縣”。
我們知道,通假字在本質上是替代字。通假字產生的具體原因有很多種,但是共通的原理都是古人在語音體系裏,找來的字音近同的替代字。實際上,與這個字讀音近同的字很多,這些字都可能成為該字的替代字。此時,與該字字音、字義皆近同的字,被選取的可能性更高。在免簠銘文和元年師簋銘文中,鑄造者選擇“還”來代替“縣”,正是這種情況。
在字音方面,“還”與“縣”二字音同是毫無疑問的。《説文》謂“還”“睘聲”,而“睘”與“縣”古音都屬匣母元部,雙聲疊韻。
在字義方面,“還”“縣”二字雖然都義項眾多,但是也有字義接近的點。古代從“睘”得音的字,往往有環繞義。如《漢書•食貨志》:“還廬樹桑”,顏師古注:“還,繞也”;《國語•越語下》:“還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地”,韋昭注:“環,周也”;《漢書•高五王傳》:“乃割臨淄東圜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顏師古注:“圜,謂周繞也”。同時,“縣”有“鄙”的含義。《左傳•昭公二十年》:“縣鄙之人,入從其政,逼介之關,暴徵其私”;《呂氏春秋•孟夏》:“命司徒循行縣鄙”,“縣鄙”連稱,正是因為二者同義。上文已經指出鄭縣、豐縣就是鄭、豐周邊的郊區地帶,這與“還”的字義也是一致的。
綜合而言,西周時期的金文中有兩種形態的“縣”字。一種作“”,義為系;由它所表示的縣,是一種依附大型地域社會組織的小型地域社會組織。一種作“還”,義為環繞;由它所表示的縣,指城市周邊的郊區地帶。
金文中的“縣”字和實際的縣是緊密聯繫的,二者呈相互對應的關係:“”體現的是縣邑之縣,附屬於城市;“還”體現的是縣鄙之縣,指環繞城市的郊區地帶。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西周時期的縣,既不像多數專家所認為的只有一種形態,又不像部分學者如陳劍所説的那兩種類型。西周時期的縣呈現這樣兩種形態:縣鄙之縣;縣邑之縣。其中,縣邑之縣是位於城市郊區附屬於城市的小邑;縣鄙之縣,為城市周邊的郊區地帶。那麼,這兩種形態之間有何關係呢?西周時期應該先有縣邑之縣,它們是位於城市郊區的附屬小邑。因為這類縣設置在圍繞城市的郊區地帶,而且設置得很多,分佈得很廣。慢慢地,設置這類縣的廣泛區域都可以用“縣”來稱呼。隨之,“縣”的內涵也發生了變化,有了意為郊區的“鄙”的含義。這樣就產生了縣鄙之縣。
總之,我們可以從金文中“縣”字的形義來進一步確認西周時期縣的形態特徵。西周時期有兩種類型的“縣”字:“”和“還”。西周時期兩種形態的縣與“縣”字是相互對應的,縣邑之縣由“”來表示,縣鄙之縣由“還”來表示。二者的區別非常明顯。西周時期兩種形態的縣之間有着密切的關係:先有縣邑之縣;因為它們設置在城市的郊區,且設置很多,所以慢慢地,整個城市郊區地帶都可以用“縣”來稱呼;這樣就產生了縣鄙之縣。
六、西周時期縣的來源及其在春秋時期的孑遺
先説縣邑之縣的來源與孑遺。
《逸周書•作雒解》中的縣邑之縣並非無源之水,無根之木,而是有着自己的源頭。殷商時期一些方國都城或中心城邑的周邊往往有很多附屬小邑,殷墟甲骨文中有如下的記載:
(1)癸巳卜,貞:旬亡。王佔曰:“有祟,其有來艱”。迄至五日丁酉,允有來艱自西,沚告曰:“土方徵於我東鄙,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合集》6057正,賓組)
(2)貞:呼比奠取炋、鄙三邑。(《合集》7074,賓組)
(3)大方伐□鄙廿邑。(《合集》6798,賓組)
(4)[呼]取三十邑[於]彭龍。(《合集》7073正,賓組)
(5)[□□卜,□]貞:旬亡。。允有來艱自西,臿告曰:“魌、夜、方、相四邑”。十三月。(《合集》6063正,賓組)
上引(1)辭中的“我”,過去一直被看成是商王。研究者已經指出這只是一種推測,“我”實際上是沚的自稱;此處的東鄙、西鄙是沚領地中心城邑的“東鄙”和“西鄙”;“二邑”位於東鄙之地。此辭説明,沚領地中心城邑的郊區地帶分佈着很多小邑。(2)辭中的炋、為地名,具體來説應該是中心城邑;“三邑”,從鄙來看是為位於炋、的郊區地帶。(3)辭中“□”可能是一處中心城邑;“鄙”即周邊的郊區之地。“廿邑”位於中心城邑□的郊區之地。(4)辭中的彭龍當為一處中心都邑,“三十邑”是附屬於它的;與第一、二辭對比,這三十邑應當位於彭龍的郊區地帶。與(1)對讀,可知(5)辭中的“魌、夜、方、相四邑”是位於臿領地中心城邑的周邊的。考古遺蹟中也有類似的證據。湖北的盤龍城一般認為是商代某個方國的都城。在盤龍城“宮城”周圍104萬平方米的範圍內,分佈着許多聚居點,各以民宅、作坊、農田、墓地,構成相對獨立的社會經濟生活的實體,同時又緊緊依附於方國上層貴族集團。這些居民點應當就是附屬於宮城的小“邑”。
這種中心城邑郊區有附屬小邑的現象,在西周時期仍然存在。宜侯夨簋銘文(《集成》4320,西周早期)中周王賞賜給夨“厥宅邑卅又五”,應當就是位於宜侯都城周圍郊區的附屬小邑。殷簋銘文也記載:
唯王二月既生霸丁丑,王在周新宮,王格大室,即位。士戍佑殷,立中廷,北向。王呼內史言命殷,賜巿、朱黃。王若曰:“殷,命汝更乃祖、考、友,司東鄙五邑”。殷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用作寶簋。其萬年寶用,孫孫子子其永寶。(《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4期第4—5頁,恭王時期左右)
銘文中的“五邑”位於某個中心城邑的“東鄙”,也是在中心城邑的郊區地帶。
這些中心城邑周邊附屬小邑的形態和《作雒解》中的縣邑之縣非常相似。《作雒解》中的縣應當就是由這種邑中的一小部分發展過來的。在《左傳•昭公五年》中,薳啓強所謂“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廣韻•緝韻》:“邑,縣邑”、《資治通鑑•周紀一》:“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胡三省注:“邑,縣也”,無疑都正確認識了縣的源頭。當然,這種邑中只是一小部分發展成了縣,更大一部分還保持着原來的狀態。那麼,縣和沒有發展過來的邑又有何區別呢?如《作雒解》的記載,縣應當經過了人為的劃定;另外,縣下可能有郡、鄙這樣更低級基層的組織;還有,縣對它所附屬的城市有着更強的依附性。
與此同時,《逸周書•作雒解》中的縣邑之縣在春秋時期仍然有孑遺。春秋時期仍然屢次見到這種形態的縣。
春秋晚期齊國的叔夷鍾(《集成》273)、叔夷鎛銘文(《集成》285)中的“其縣三百”就位於城市脒膠的郊區,而且依附於脒膠。《晏子春秋•外篇重而異者第七》記載: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谷,其縣十七。著之於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為其子孫賞邑”。
《晏子春秋》雖然成書年代較晚,但所記的歷史或有所本。張純一注:“狐、谷皆地名”。管仲為春秋時期齊國的卿士,所受采邑只有“其縣十七”,或許太少,所以研究者認為可能是“其縣七十”的倒裝,可從。在此,管仲所受的物品包括狐、谷與其縣七十。這裏的70縣應當是位於狐、谷的周邊,依附於狐、谷的。
再説西周縣鄙之縣的前世源頭和春秋遺留。
西周時期的縣鄙之“縣”應當是由商代表示中心城邑郊區地帶的“鄙”發展來的。《合集》7074“炋、鄙”是指中心城邑炋、周邊的郊區地帶。《合集》6798“□鄙”是指中心城邑□周邊的郊區地帶。《合集》6057中的“東鄙”“西鄙”是沚領地中心城邑周邊的郊區地帶的東部和西部。西周縣鄙之“縣”應當就來源於此。
從“鄙”到“縣”轉變的契機,應該是西周時期在城市周邊的郊區地帶設立了很多的縣邑之“縣”,逐漸地“鄙”就可以用縣來代替,“縣”就有了鄙的含義。
西周時期表示城市郊區的縣鄙之“縣”,在春秋時期仍然有孑遺。在《左傳•昭公二十年》中,齊國的晏子説:“……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徵其私”,這裏的“縣鄙”是與國都相對,是指國都周邊的郊區地帶。這些都是西周時期縣鄙之“縣”的遺留。
總之,西周時期形態獨特的縣邑之縣,並非橫空出世。殷商、西周時期很多中心都邑的郊區都有附屬小邑,其中的一小部分後來就發展成了縣。它們可謂西周縣邑之縣的源頭。縣和沒有發展過來的邑的區別在於,經過了人為的劃分;縣下有更低級的社會組織;對所附屬的城市有着更強的依附性。這種形態的縣,在後來的歷史時期並沒有絕跡,春秋時期仍然有孑遺。同時,西周時期的縣鄙之縣是由商代的“鄙”發展來的,它在春秋時期也有遺留。
七、西周時期縣在春秋時期的發展
西周時期的縣鄙之“縣”在春秋時期有發展,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周王國和諸侯國國境內,國都以外的地方都可以稱縣。《國語•周語中》記載周定王派單襄公去聘楚,假道於陳國。他發現陳國“國無寄寓,縣無施捨”,他還説到周制是“國有班事,縣有序民”。此處的“國”是指國都,“縣”與國都相對,是指陳國和周王國國都以外的廣泛的區域。《穀梁傳•隱公元年》:“寰內諸侯”,陸德明《釋文》:“寰,音縣,古縣字。一音環,又音患。寰內,圻內也”,楊士勳疏:“寰內者,王都在中,諸侯四面繞之,故曰寰內也”,可見這裏的“寰”即“縣”。這裏的縣指的是周王國內、王都以外的區域。其二,縣可以指代整個諸侯國周邊的地帶。《左傳•昭公十九年》記載:
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子產不待而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何國之為?”
大意是説鄭國會成為晉國的縣鄙,即晉國的周邊地帶。所以這裏的縣是指整個諸侯國的周邊地帶。
接下來看西周縣邑之縣的發展。
雖然有孑遺,但是西周縣邑之縣在春秋時期更多的是變化和發展。那麼,西周的縣邑之縣在春秋時期有何發展?與西周時期的縣相比,春秋時期縣有着諸多異同,我們可以通過考察這些因素,來看這種發展歷程。與西周相比,春秋時期縣不同的地方表現在:
第一,春秋時期縣可以指代整個城市。《左傳•襄公三十年》記載: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
絳是晉國的首都新絳,絳縣即指絳。可見,這裏的縣指的是整個城市絳。《左傳•成公十三年》記載晉國的呂相絕秦時説道:
利我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
楊伯峻引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謂:“河縣疑是河曲之變文”,若確如是,晉國在河曲建立了縣。杜預注:“箕、郜,晉二邑”,根據語境,河縣與箕、郜性質相當。所以,此處的河縣指的是城市河曲。另外,春秋時期楚國的縣,如商、期思、葉、沈、寢、白、武城、析、東西二不羹,都是整個城市。
第二,春秋時期縣的設置區域更加廣泛,大小規模相對自如。
晉國的絳縣位於新都的位置。楚國的商、期思、葉、沈、寢、白、武城、析、東西二不羹位於楚國的國都以外、邊境以內的地方。清華簡《越公其事》中有一些關於春秋時期越國縣制的材料,其中的“邊縣”就是指越國邊境上的縣邑。另外,春秋時期滅諸侯國所建立的縣,往往也是位於邊境的位置。可以説,春秋時期國都以外的地方都可以設置縣。
西周時期縣,如《作雒解》中的縣,雖然有大小之別,但相差應當不是很大。春秋時期則不一樣,有的縣是滅國建立的,面積一定不小。晉獻公十六年,晉滅耿、霍、魏三國,並設置了縣,那麼,這些縣的面積是十分巨大的。同時,有些縣的面積並不大。《晏子春秋•外篇重而異者第七》載齊景公對晏嬰説“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谷,其縣十七”,這裏的縣的面積應當就不大。可見,當時縣的大小規模比較自如。正是因為春秋時期有規模很大的縣的存在,所以存在從大縣中分立“別縣”的現象,如晉國的州縣是温縣的別縣(《左傳•昭公三年》);也存在將大縣分成多個小縣的現象,如晉國“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第三,春秋縣內的職官逐漸細緻化。從《左傳•昭公四年》的內容可知,西周時期縣邑之縣已經設置了“縣人”來管理,但是更精細的職官卻不見於記載。春秋時期則不同,縣內的職官呈愈發細緻化的趨勢。在《左傳•襄公三十年》中,晉國在絳縣設置了“縣大夫”“絳縣師”之類的職官。《左傳•莊公三十年》記載:“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秋,申公鬭班殺子元”,杜預注:“申,楚縣。楚僭號,縣尹皆稱公”,可見楚國在縣裏設置了縣尹職官。
清華簡《越公其事》中的相關內容,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春秋時期縣內的職官問題。
當時的越國在“邊縣”(即邊境上的縣)內部設置了一些官職來對其管理這些地方,這些官員的級別有高低之分。《越公其事》記載:
凡邊縣之民及有官師之人或告於王廷,曰:“初日政勿若某,今政砫(重),弗果(和)。”凡此類也,王必親見而聽之,察之而信,其在邑司事及官師之人則發(廢)也。(第39—40號簡)
簡文中第一次出現的“官師之人”是舉報之人,第二次出現的“官師之人”是被舉報之人,二者雖然同屬一個羣體,但卻不是同一批人,後者可能是前者的上司或者同事,可見縣內的“官師之人”數量很多;“司事”應是管理被舉報事務的最高職官。縣內的職官還有“司事及官師之人”(第40—42號簡)。根據《越公其事》第45—46號簡,縣內官員可被籠統稱為“執事人”。從這些簡文,我們可以看出春秋時期縣內的官員及其等級狀況:最高級別為司事,第二級別是官師之人(被舉報者),最低級別是官師之人(舉報者);他們可被籠統稱為“執事人”。
這些轉變的產生,都為後來縣邑之縣的進一步發展和郡縣之縣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那麼,**是什麼原因促使了這種差異的產生?一方面,這與春秋時期一些諸侯國的改革有關係。**我們可以從齊國的改革來管窺當時普遍的狀況:
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故政之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國語•齊語》)
此處“鄙”,是與“國”相對的,指國都以外的地區。可見,管仲在國都以外的地區設立了邑、卒、鄉、縣、屬五級大小相統屬的基層社會組織。他的這種改革是將之前城市的模式推廣到了全國,但是客觀效果卻是促使縣的形態的變遷。
**另一方面,這也與春秋時期的滅國戰爭有關。**許多大諸侯國滅掉小諸侯國後,往往模仿本國用縣管理城市郊區的方法,設立縣來管理新滅的諸侯國。《左傳•哀公十七年》記載“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這裏的申和息,以前是諸侯國,在此就被楚國設立了縣來管理。《左傳•宣公十一年》記載,楚莊王因為夏徵舒之亂,率領諸侯伐陳,“遂入陳……因縣陳”,陳國以前是諸侯國,在此也設立了縣。清華簡《系年》記載:“楚靈王立,既縣陳、蔡。……秦異公命子蒲、子虎率師救楚,與楚師伐陽(唐),縣之”(簡104—107);又謂“(楚)靈王先起兵,……為南懷之行,縣陳、蔡,殺蔡靈侯”(簡98—99),這裏的陳、蔡、唐本是諸侯國,別滅後都設立了縣。《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武公十一年“初縣杜、鄭”,稱縣的邽、冀戎、杜、鄭,被滅國前都是諸侯國。這推動了縣的設置區域和大小規模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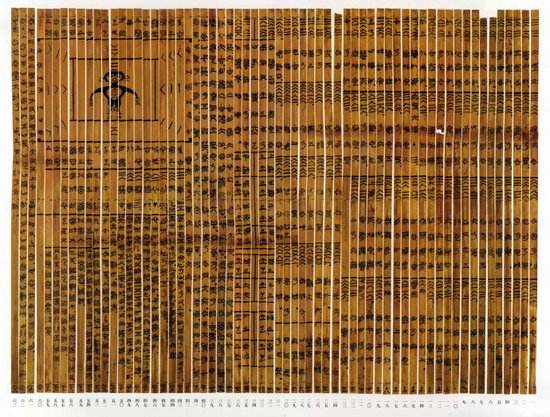
《清華簡》
當然,春秋時期的縣邑之縣與西周時期仍然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表現在:
其一,都有一定的統屬與被統屬關係。《逸周書•作雒解》中的“縣”統屬“郡”“鄙”二級更基層的地域社會組織。而《國語•齊語》中的“縣”統屬“邑”“卒”“鄉”三級更基層的地域社會組織,同時被“屬”這樣更大的地域社會組織統屬。這些為郡縣制度下,郡統屬縣關係的最終確立提供了範本。
**其二,都要依附於更大的社會組織。**西周時期的縣依附於更大的社會組織,《逸周書•作雒解》中的縣依附於成周。春秋時期不同諸侯國之間縣的形態差別較大,但是都依附於更大的社會組織的特卻是一致的。楚國攻滅其他小的諸侯國建立的縣,權、申、息、陳、鄭,都依附於楚國。秦國滅國建立的縣邽、冀、杜、鄭,都依附於秦國。上文提及的,齊國叔夷鍾(《集成》273)、叔夷鎛銘文(《集成》285)銘文中的“其縣三百”是依附於萊都脒膠的。這應當也是春秋時期設立的社會組織稱“縣”的原因。
其三,國君能很好地控制縣。《逸周書•作雒解》中的縣,周王一定能很好地控制。春秋時期的縣雖然位於不同的諸侯國中,有一些差別,但是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能被國君很好地控制。春秋時期的楚國、秦國在滅掉別的諸侯國之後都設立縣,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他們能通過縣來很好地控制這些地區。
春秋時期還有一些表面上看似屬於貴族的縣,實際上諸侯國君對它們有很強的控制力。《史記•吳世家》記載“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以為奉邑。……富於在齊”;《説苑•臣術》篇説齊景公因晏子食不飽,“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春秋晚期的叔夷鍾(《集成》273)、叔夷鎛銘文(《集成》285):“公曰:‘屍……餘賜汝萊都脒膠,其縣三百’”;《左傳•閔公元年》記載:“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這些縣表面上看似為貴族所有,但是它們在貴族絕嗣之後就很快被國君收回。實際上,諸侯國君對它們有很好的控制力。這正是春秋戰國時代縣被廣泛設立的原因。
總之,縣鄙之縣在春秋時期的發展表現在,既可以指代諸侯國和周王國國境內,國都以外的廣泛區域;也可以指諸侯國的周邊地帶。春秋時期縣鄙之縣的發展與縣邑之縣的發展是緊密聯繫的。西周縣邑之縣在春秋時期也有很大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兩個時期的差異方面。春秋時期縣在內涵、設置區域、大小規模和內部職官方面,均與西周縣有着較大的差別。這種差別是春秋初期諸侯國的改革活動和大諸侯國的滅國戰爭推動產生。同時,兩個時期的縣也有共同點,表現在:都有一定的統屬與被統屬關係——為郡縣制度下,郡統屬縣關係的最終確立提供了範本;都要依附於更大的社會組織——這可能是春秋時期新設立的社會組織稱“縣”的原因;都能被所有者很好地控制——這應該就是春秋戰國時期縣被普遍設置的原因。
【本文首發於《學術月刊》,觀察者網經“學術月刊”微信公眾號授權轉載。轉載時有所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