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緝思:不能因為要搞好中美關係,就犧牲中國核心利益
據澎湃新聞12月8日報道,四月的燕園已是一派春光,未名湖上碧波盪漾,博雅塔下鶯飛草長,而王緝思的一生,和這座中國頂尖學府緊密相連。北大附小、附中讀書成長,恢復高考後重返北大求學並留校任教,十餘年中國社科院任職經歷後又迴歸北大講壇,年近七旬的王緝思身上有着深深的北大烙印。
王緝思善於從中美雙方的角度思考對方有何關切,對不同觀點兼容幷包;也敢於對原有的認知大膽懷疑,對事實真相孜孜以求。儘管中美之間依然存在較大的戰略互疑,但這位熟諳大國博弈之道的北大學者對中美關係的未來仍有信心,他相信只要兩國政府理性思考、減少對抗的可能性,傾聽並尊重百姓心聲,中美能夠挺過終將過去的“暴風雨”,繼續向前發展。

治學四十載:長路漫漫
澎湃新聞:您是怎樣走上美國研究的道路?
王緝思:我進入北大國際政治系前是河南三門峽水電廠的工人,英語初步自學過一些,但是沒有去過美國,也沒有去過其他任何國家,對美國的認識僅相當於一個高中生的水平。總體上我對外部世界的認知是有限的。我在北大上了一年的本科後,就讀碩士研究生了。我的碩士生導師認為我的基礎太差,不適合研究美國、蘇聯這樣的大國,就建議我研究第三世界,在中東、東南亞和南亞中選一個作為研究方向。我選了東南亞,因為東南亞離我們近一點。
1982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北大派我去英國牛津大學做為期一年的訪問學者。當年牛津大學沒有研究東南亞政治和國際關係的學者。經過半年的學習,牛津的導師認可了我的學術水平,就讓我根據美國國務院解密的外交檔案,研究上世紀40年代後期的中美關係,具體而言就是為什麼美國要干預中國內戰,是不是擔心中國共產黨上台後會倒向蘇聯?因為那時美國剛剛公佈了一批相關的檔案材料。我以這個問題寫了一篇論文,導師很滿意。回國以後,我把這篇論文改成了中文,作為我的碩士畢業論文,原來的東南亞研究方向就放棄了。後來,我留在北大國際政治系當老師,因為我去過英國,就被分到了研究西方國家的教研室。我就這樣走上了美國研究的道路。
澎湃新聞:從最初的北大任教到進入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再到返回北大,您經歷了從高校到研究機構再回到高校的一個循環,這些經歷對您研究美國問題、中美關係有何影響?
王緝思:80年代中期,我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做訪問學者,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美國的東亞政策,回國以後就在北大開設了美國東亞政策的課程。後來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從北大調到了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於是就專門從事美國研究了。因為美國是世界大國,影響力輻射全球,我以前看過的有關東南亞的書,對我瞭解美國對相關國家的政策也有一定的作用。
在社科院美國所,因為我專門研究美國問題,而且中美關係又是熱門議題,所以我有機會參加和美國人的一些交流活動,還根據外交部以及其他一些部門的要求,參加一些政策諮詢會議,這種機會在大學裏是無法得到的,因為社科院是一個政府智庫,不是一個教學機構。
後來,我從社科院調回北大,從一個科研單位調到一個教學單位,又是一次轉變。我覺得這個轉變也不容易。回到高校以後,不僅要從事科研工作,還要從事教學管理和學術管理工作,我就不可能只關注美國了。有一個好處就是擴大了視野,因為給學生上課時必須講一些基礎知識,非洲、拉丁美洲、俄羅斯等等都會涉及到,這就使我的眼界開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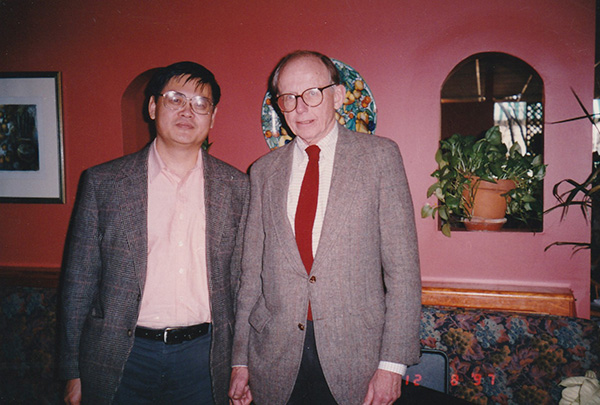
王緝思與薩繆爾・亨廷頓合影。
澎湃新聞:您長期擔任中華美國學會的會長、榮譽會長,您如何看待40年來中國的美國問題研究、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
王緝思:以前,不是我一個人對美國的瞭解有限,而是我們整個國家對美國都不大瞭解。從我開始研究美國問題到現在,是中國大發展的時期,也是中美關係大發展的時期,中美對彼此的認識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這裏面也存在一定的問題。我雖然去過美國很多次,但主要還是去華盛頓、紐約這樣的大城市,見的人也大多是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而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們到中國來也是見我這樣的人,交流一些中美關係的問題。這就會導致我們對對方整個社會的瞭解非常膚淺。
我們現在的研究中存在很多功能性的領域,比如説貿易政策、投資環境、氣候變化、生態環境、醫療衞生等等,每一個研究領域都離不開美國。但是如果只從一個領域去看,就容易失去對一個整體美國的理解。美國對中國的研究也是如此。美國有人研究中國的海軍發展、網絡安全、環境污染、產業政策、醫療衞生改革等等。過去美國老一輩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們看到更多的是宏觀問題,因為他們沒有機會去接觸微觀問題。而現在,如果只研究宏觀問題,在美國連博士學位都很難拿到。現在我們知道了彼此的很多細節,但是卻缺少了對宏觀問題的研究,這就可能產生“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問題。
對一個國家的認識要謹慎,要知道自己的認識是有限的,千萬不要相信一些人所説的“告訴你一個真正的美國是什麼樣”,因為沒有人知道真正的美國是什麼樣,我相信特朗普也不知道。對對方國家、自己國家以及整個世界的認識是無窮無盡的。這40年來,我們對美國、美國對中國的瞭解深入了很多,但這並不等於我們能夠準確判斷出美國未來的走向,美國當然也不能準確判斷出中國走向何方。
縱橫兩大國:上下求索
澎湃新聞:您在從事美國問題研究的過程中,也廣泛接觸美國的對華決策人士,有媒體稱您為“鑽進白宮心臟的中國行者”,您對服務於美國對華決策的“中國通”們有着怎樣的認識?
王緝思:我需要強調的是,在美國對於國內外事務的整體考量中,中國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不管是特朗普政府還是此前的奧巴馬政府,主要的工作重點還是放在國內,外交只是政府工作中的一部分。中國在美國政策議程中的地位,並不如一些中國人所想象的那麼高。最近十幾年,中國的地位上升得很快,但對華政策仍然不能説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部分。美國負責對華政策的相關人士,在美國的地位也比我們想像的要低。在美國國務院、國防部或者國安會的機構設置中,對華決策官員從屬於東亞或者亞太方向。所以,他們更多的是瞭解中國與日本、韓國等國家的關係,對於中國與印度、非洲或者拉丁美洲的關係,也並不太瞭解。中國的影響力正在上升,但是美國的決策機制還沒有發生變化,這就使得他們在思維上會存在漏洞,這是美國方面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澎湃新聞:如何看待中美間的“二軌”外交?如何看待學術研究者和外交實踐者之間的關係?
王緝思:現在,學者與外交官之間有很好的溝通,但是兩者的角色定位不一樣,所以他們關注的事情是不一樣的。學者更關心的是事實是什麼樣、為什麼是這樣,如果還能據此推導出未來的發展趨勢,就是一個很不錯的學者了。外交官也關心事實和原因,但是他們更關心的是怎麼辦。作為一個學者,不能輕易否定任何事情發生的可能性,但是外交官的工作就是促進好事發生,避免壞事發生。比如,作為一個學者,你可以根據客觀情況判斷説中美關係正在惡化,正在走向對抗。作為外交官,你應該説中美對抗會損害兩國利益,所以要增加互信合作,避免對抗。
有時,我也會被政府部門問到“怎麼辦”的問題。這時,我的身份定位就不僅是學者了,而是一個謀士。此時,不僅需要運用自己的學術知識,更重要的是知道國家需要什麼、如何實現。**在很多問題上,國家已經有既定的政策,或者説是國家的大戰略、中國國情決定了我們應有的立場。我們不能因為要搞好中美關係,就犧牲中國核心利益或者整體的立場。比如説我們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方面的立場,不可能因為要搞好中美關係就尋求改變。**外交官非常清楚這方面的情況,學者和外交官有更多的溝通,就能知道外交官想要的是什麼、他們會如何去獲得。學者對於外交官也有啓發作用,可以拓寬他們的思維,告訴他們一些事實背後的廣闊背景和看待問題的不同視角。學者和外交官之間的互補很重要。
澎湃新聞:近期美國出台了《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等一系列文件,將中國直接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這樣一種認知轉變背後反映出的是什麼?
王緝思:坦率地説,目前是自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來,美國對中國看法最負面、敵意最大的一個階段。從美國方面來看,一部分人從現實主義的視角看中國,他們看到的是中美兩國實力對比發生了變化,以及中國在戰略方面對美國的挑戰。他們認為,一個實力越來越強的中國將不可避免地侵佔美國已有的地盤。這些人對中國的警惕在增加,他們不大關注中國國內發生了什麼變化。另外一部分人是所謂的自由派,這些人看到的是中國國內的一些變化,但失去了對中國的信心。過去,他們認為美國與中國的接觸,可能會給中國帶來一些——在他們看來是——積極的變化,包括市場經濟更加發達、國有企業讓位於私企民企、政治上越來越自由化、吸收美國的思想文化等等。但這些都沒有實現,使他們有一種幻滅感。現在,這兩部分人合流了。我所認識的大多數美國人士,都感覺到這一新的對華負面共識已經出現或者達成。他們對美國對華態度的這種狀況也不一定滿意,但很少有人出來公開表示質疑。
另一方面,我們在重視美國語言表述的同時,更重要的是看美國實際做了什麼。最近,美國和法國、英國一起轟炸敍利亞,如果按照《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界定,中國是美國的最大“戰略競爭對手”,那麼美國就應該從敍利亞、阿富汗這些地方撤回來,集中力量對付中國。美國為什麼沒有這麼做?這就説明美國沒有一個明確的全球戰略和根據這個戰略制訂的對華政策,即使有也未必能實行。在具體事情上,美國並不一定能夠完全按照自己的設想去做。中美關係中除了貿易問題以外,沒有特別緊迫的問題需要馬上就解決。對美國而言,伊核問題、中東亂局、阿富汗問題、俄羅斯問題、朝核問題等都沒有解決,怎麼能夠把主要的精力從這些緊迫的問題上轉移,去解決那些並不十分緊迫的中美關係問題呢?中美貿易問題不是短期內形成的,也不是短期內就能解決的,特朗普想畢其功於一役,我們不能被他套住、嚇住。

王緝思率團拜訪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
文章經國業:為中國策
澎湃新聞:2012年,您和李侃如合作撰寫了《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直書中美決策層如何認知對方,當時出於什麼樣的考慮撰寫了這樣一份報告?
王緝思:2010年下半年的時候,我和李侃如同時發現,中美關係在往一個不穩定的方向發展。當時出現了南海問題、釣魚島問題,兩國間的經貿摩擦也越來越多,很多問題同時出現。我們覺得這些問題的背後是兩個國家之間的戰略互疑,也就是説中國對美國的認知,以及美國對中國的認知,都不一定準確。
李侃如提出來説合寫一份報告,我也很贊同,於是我們開始合作撰寫。在撰寫的過程中,李侃如去美國的政府部門採訪了一些決策者或者參與決策的人,去聽他們的想法。而我則是憑着自己的感受以及對中美關係的理解來寫。我寫的部分,容納了中國如何看待美國的各種觀點,其中有的觀點表露出對美國非常反感,覺得我們對美國的政策太軟弱了,有的觀點則認為我們對美國太強硬了,美國不像我們想象的那麼壞,應該進一步緩和或者改善中美關係。這基本上反映了中國認知美國的一些主要觀點。李侃如寫的部分,基本上也反映了美國政治主流對中國的看法。
我得到的批評也是來自兩個方面。有人説,中美戰略互疑沒有那麼嚴重,中國和美國的溝通很多,沒有互相之間的不理解。也有人説,報告對美國的批評還不夠,這根本就不是一個戰略互疑的問題,而是美國本質上就是我們的敵人。收到這兩方面的意見是正常的,如果只收到一方面的意見,那就説明我的報告可能並不十分客觀。李侃如得到的美方反饋也與此類似。而美方反饋給我的信息是,原來中國人對美國還有這麼多負面的看法,美方在和很多中國人接觸的時候只聽到了好的一面。
澎湃新聞:如何看待中美之間的戰略互疑?
王緝思:中美關係的問題是不是出在戰略互疑上?我在寫這份報告的時候就已經產生了懷疑。我們把對彼此的認知很直白地説出來,也許並不是一件壞事,但是難道戰略互疑就會因此而減少?我們在報告的最後提到,如果做不到削減戰略互疑,那就只能想辦法緩解危機,不讓中美產生全面的對抗。也就是説,這種戰略互疑是無法避免的,甚至可以説是很難減少、無法減少的。隨着中國國力的增強,中美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方面的分歧不但繼續存在,甚至越來越大,中美戰略互疑很有可能是增加而不是減少。
我們一般人都會認為接觸越多,相互之間的懷疑會隨之減少。但事實上,在政治問題上,很多時候接觸多未必就會減少懷疑,反而可能因為接觸增多,懷疑也隨之增加。比如,美劇《紙牌屋》裏的副總統和總統之間就有互疑,總統覺得副總統要篡權,副總統雖然嘴上不承認,但實際上就是想篡權。如果總統和副總統之間都有互疑,國家之間怎麼能夠避免?因為利益、價值觀、意識形態不一致等等,很難消除對方的懷疑。所以,問題不在於減少戰略互疑,而在於減少對抗的可能性。這是我寫這篇報告以來,思想上發生的一個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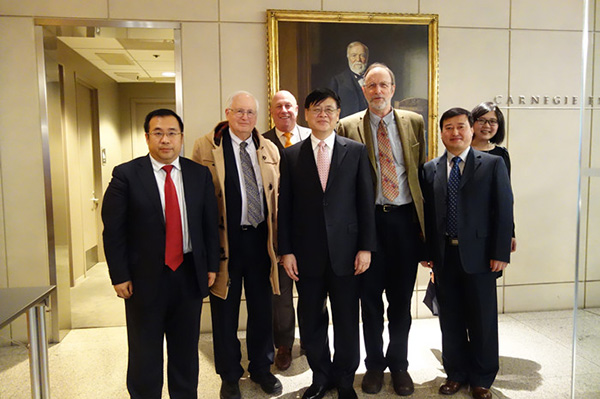
王緝思率團拜訪卡內基和平研究所。
澎湃新聞:您撰寫的《西進,中國地緣戰略的再平衡》一文也引起外界的廣泛關注,而當時的一個背景是奧巴馬政府提出的“亞太再平衡”。如何看待美國的亞太戰略對中國的影響?
王緝思:我在那篇文章裏寫道,“西進”不能稱為一個戰略,只能是一種思維方式和觀察視角,是對中國地緣政治定位的重新思索。“東方國家”是歐洲人給我們的界定,我們原本是一個“中間國家”,“西邊”是歐洲,“近東”是日本,“中東”是夏威夷,“遠東”是美國。我的意思是,我們既要往東看,也要往西看。古代的絲綢之路也表明,往西走曾經是我們的主要通道。
我認為“亞太再平衡”是“虛多實少”,美國雖然提出了這個戰略,但是實際上投放到亞太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力量都是有限的。我和我的研究團隊對奧巴馬政府時期總統本人以及其他美國高官的外訪活動進行過量化分析,結果表明,奧巴馬時期美國全球戰略的主要關注點和外交重點仍停留在中東和歐洲,亞太排在其後。所以,實際上美國的戰略重點並沒有完全轉移到亞太。
美國原來的戰略重點是什麼?這是一個可以探討的大問題。冷戰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們認為美國的戰略重點在歐洲,結果發生了朝鮮戰爭。後來,我們認為美國的戰略重點仍在歐洲,但是越南戰爭又打起來了。也就是説,我們認為的美國戰略重點,與美國實際上可能會做的事,不一定有直接的關係。美國實際做的事,很多時候並不是美國主動想要做,而是世界上發生了一些事,迫使美國必須去做。比如,美國最初並沒有想用主要力量去反恐,但是“9·11”改變了美國的政策方向。從國際關係與世界史的角度來看,很多事情的發生並不是由一個國家的意志所能決定的。
澎湃新聞:您將自己的作品集取名為《國際政治的理性思考》,應該如何“理性”地看待中美關係?
王緝思:我説的“理性”是指用比較理性的思維方式去看待,不能太感性和情緒化。作為學者,首先要知道事實是什麼,知道美國是個什麼樣的國家,中國是個什麼樣的國家,然後知道為什麼是這個樣子。至於怎麼辦,那就不是我的任務了。

《國際政治的理性思考》封面
作為一個普通的學者,我的願望就是希望中美關係能夠保持穩定,我覺得這也是中美兩國老百姓的願望。我不希望中美之間打仗,打仗會帶來很大的犧牲。中美之間出現問題,可以坐下來討論,有摩擦就想辦法化解。摩擦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中美之間不應該發生戰爭。理性可以讓我們避免人類遭受大規模的戰爭災難。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中美關係未來的發展趨勢?
王緝思:當前很多美國人都對中美關係的未來表示悲觀,但是我不悲觀。首先,美國如何將其對中國的反感、敵意轉化成實際的政策?美國人目前並沒有清晰的思考。美國接下來可能會有一些實際行動,比如説關閉幾個孔子學院、限制中國人赴美簽證、派級別高一點的官員訪問台灣等等,這些事情都有可能發生,中美之間的摩擦也會增加,但都會在一定的限度之內。中美之間不會發生全面的戰爭和對抗,不會回到冷戰前期那種相互隔絕的狀態。美國一些對中國有敵意的人所能夠造成的麻煩是有限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儘量去避免產生更大範圍的敵意或者對抗。
我之所以相對樂觀,還因為我一直記得和美國人交往中的一個例子。1992年,我去美國訪問,和美國一些人士探討中美關係。我當時覺得兩國關係很不好,因為美國威脅要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還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等。我遇到了年長的美國“中國通”鮑大可,他比我樂觀得多,我問他為什麼在這個時候還對中美關係、對中國那麼樂觀?他説:“我30年代生活在山西,那個時候的中國是什麼樣?今天的中國又是什麼樣?我沒有理由樂觀嗎?”我深深地記住了他的話。現在,我也會跟年輕人講我年輕時候的中國和中美關係,再看看今天的中國和中美關係,我們當然有理由樂觀了。
一個歐洲人問我,現在中美關係面臨的是暴風雨還是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是長期的、不可逆轉的,但是暴風雨是有可能過去的。我認為是暴風雨,而不是氣候變化。因為中國在變,美國也在變,我不相信中美關係還會回到過去的軍事對抗狀態。我們繼續向正確的方向前進,美國又有什麼可怕的呢?美國最終將會承認中國強大的現實,承認中國的改革開放具有進步意義。所以,中美關係的未來,一部分取決於美國,更大一部分取決於我們自己。我對中美關係的未來有信心,是因為我相信儘管前面道路上會有激流險灘,中國還會繼續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特約記者 張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