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者網專訪張廣天:自信不能是無端的,不能是倚仗過去的
1193年,南宋的臨安,一場大火之後,一個父親死了,但放不下他的兒子。為此,他的靈魂強盛起來,不願入土為安,遂暗中跟隨其成長、遷居,從南宋到金國,又隨蒙古西征進入歐洲。
其時,亞歐大陸各方思想和生活方式因戰爭而交織、融合、重鑄,一個全然不同以往、延續至今的嶄新中國文明正在誕生……
這是張廣天新作《南榮家的越》講述的故事。

書中描繪的時代,蒙古人的火炮轟開了歐洲諸國的門,中原文明隨之傳入。而西方的八剌禿(柏拉圖)、阿力司鐸(亞里士多德)、也裏失八(伊麗莎白)們也讓我們的祖先感到陌生驚訝。
近千年後,我們對這些異域文化早就習以為常,甚至它們的形象也已固化,但張廣天認為,今天的我們需要還原到最初驚訝的狀態,體驗一下最初的相識,這有利於比對認識。盲從只能局部放大他人,而不能真實面對他人,“拿那樣的驚訝與當前的匍匐做一種比較,在比較中至少令自己清醒一點”。
談及“文化自信”,張廣天認為自信不能是無端的,不能是倚仗過去的,“如果我們真的在乎文化自信,我們不應只從典籍和傳統中去尋找支撐點,我們更應該想到的是,我們是什麼人,我們每個個體又是怎樣的性情,一切世間所謂先進的優越的成就如何養我的性情。”

張廣天
以下是觀察者網採訪全文:
**觀察者網:《**南榮家的越》視角很獨特,讓一個亡魂來追蹤他的孩子,為什麼會用這種角度?
**張廣天:**一本小説在創作之初需要一種原動力,當這個動力來自一個父親對孩子的牽掛時,就會延伸到極致。比如,父親死了,孩子還在襁褓中,他如何放心得下。這麼想去,常常牽動我內裏最深的悲憫心,一日比一日巨大,乃至將我吞噬。有那麼一陣,它幾乎將我全部籠罩,推我的想象力到無窮,這便成了寫這部書的動機。
當然,在嚴肅的創作中,這種動力已不僅僅是最初的起因,逐步成為一種方法。其實,這並不只是一個角度,而是方法。靈魂的敍述使日常的敍述退場,獲得了一般敍述所沒有的體驗。截然不同的體驗必然會構成截然不同的結構、線索和關注點。《南榮家的越》需要這樣的方法。
**觀察者網:**您描述書中的時代:“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國在此刻被多民族多信仰的新中國覆蓋了”,這似乎也能用來描述現在的中國。您是如何理解“中華”和“中國”的?
**張廣天:**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揭示出烏拉爾山以東的民族與鮮卑人的淵源。從紅山文化到興隆窪文化,玉器的使用被推前到一萬年,更有俄羅斯西伯利亞的發現,證實玉器文明比一萬年更早就存在於鮮卑人祖居的北極凍土帶。從玉器形制和用玉方式來看,商以後黃河長江流域的文化是繼承北地傳統的。有史學家一直呼籲,説探索中華文明,要將眼光放到長城以北。

紅山文化玉龍
我個人認為,**以往我們從血緣、語言等方面的民族歷史研究已經不足以看清事實,應該從生活方式來研究史學。**比如,從人種血脈講,烏拉爾山以東的人羣都屬於蒙古利亞人種,即都是鮮卑人,只是遊牧的被稱作蒙古人,漁獵的被稱作通古斯人,而耕讀的被稱作漢人。
**中國並不是民族中國,也不是文化中國,而是生活方式淘選出來的中國。**所以,先人説“華夏”,意思是生活方式中的精華部分。當時認為漁獵和遊牧都比不上耕讀,所以耕讀成為中心,成為精華,文明之花,這就是中華的本義。至於中國,原本的意思是中原之國,精華之國,而國不過是做大了的邦與族姓而已,同族中的不同政權更替而已。
現在説中國,是晚清民國時確立的民族中國概念,是中華民國的簡稱,歷史上的人們沒有這樣的認識。另外,西方長久地將東方的文明地區概稱為“契丹”,因中世紀契丹建立的政權最早影響到歐洲。契丹在西方人那裏,也不是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地區,一個他們嚮往的比他們當時文明程度高的地區。馬可波羅和魯布魯克寫的遊記,都將大漠以南的文明地帶叫做契丹,只是我們漢譯本都譯成了“中國”。
**觀察者網:**這本書的一大亮點在於它描繪了東西方初次相遇時的心態,您認為有一種自然之驚、隨性之訝,沒有迷信、沒有污染。但是否這種驚訝只是一時的,我們終究要面對衝突與融合、選擇與被選擇的問題?
**張廣天:**當初驚矣,訝矣,之後固然要改變,改變得鬼化,又改變得神化。**正是鬼化和神化的不正常,失態,迷茫,才需要還原到最初的狀態。**讓我們來看一看最初的相遇,體驗一下最初的相識,這特別有利於今天我們來比對認識。**盲從只能局部放大他人,而不能真實面對他人。當然,僅僅停留在驚訝上,也不足以深入。**我是希望拿那樣的驚訝與當前的匍匐做一種比較,在比較中至少令自己清醒一點。
**觀察者網:**近代以來,不少國人在面對西方時往往有一種迷信和盲目崇拜,當然近年這種趨勢也在退熱。您説“文化需要還原,還原到可以認識的地步”,您認為當下的我們該如何正視西方?
**張廣天:**自五四以來,仁人志士們一直在追尋西方文明的種子移植過來的途徑,以及如何克服水土不服。我們也常常提文化自信,**只是自信不能是無端的,不能是倚仗過去的,而學習也不能僅僅靠趕超。**世間各地人羣生性不同,經千萬年征戰、融合、交叉、淘選,都是在生活方式這點上尋找出路。如果我們丟棄並遺忘了自己的方式,那麼其實我們失去的是我們的生性。
我歷來不同意性相近、習相遠這個説法,性萬千有別,倒是人們趨勢求利的習越來越靠近。一切想抹去人性豐富性和差異性的努力都已經失敗,一個需要遵從本性的現代化進程已經開始。
**如果我們真的在乎文化自信,我們不應只從典籍和傳統中去尋找支撐點,**我們更應該想到的是,我們是什麼人,我們每個個體又是怎樣的性情,一切世間所謂先進的優越的成就如何養我的性情。進步與落後,不能只從槍炮射程遠近來看,而要看怎麼對我有用。怡我性情者優,敗我性情者劣。
**觀察者網:**如何理解書最開頭的“虛心的人有福了。這話的原義是説,靈魂貧困的人有福了。”
**張廣天:**和合本聖經翻譯時,將希伯來語原義“靈魂貧困”譯作了“虛心”。虛心這個詞在中文中有特別的道學意味,彷彿是一種德行,一種操守,而靈魂貧困分明指的是另一件事。人活着,靠的是一點精氣神,這就是靈魂。
按中國古代的文獻,人之魂魄居住在五臟六腑中,乃臟腑之精微,其實就是物質,是物質的頂端品級。人道主義以來,西方強調人本精神,而中國自春秋以來也強調人的能力,人們從不同的文化中越來越沾沾自喜於人類的作為,這就是靈魂的強硬。一切主張造化在先的宗教,必定視命運為根本。在造化面前,靈魂倘強硬了,神的位置在哪裏呢?或者説,你那麼強硬,神怎麼幫你,神的福澤怎麼臨到你?你真的需要神的救贖嗎?
**觀察者網:**在書中,經常可以看到“心”與“理”的對撞,宋“歌舞演戲,還不忘教導勸誡”,所以要吃敗仗。是否“講理”的宋敗給了“隨心”的金?您提出“心學為體,諸學為用”該如何理解?
**張廣天:**這是哲學史的問題。宋元之際,正是心學與理學分立交織的時期。所謂心學,強調宇宙序令駐於每個生命體中;所謂理學,着重於事物之理。前者向內求真,後者向外格物致知。一個是理想主義先驗派,一個是實證主義經驗派。心學是承認命運的,是與造化渾然一體的,而理學主張人間規範,主張事在人為。
我在《手珠記》中提出“心學為體,諸學為用”,一方面是針對歷史上那個“中學為體”,另一方面是從信仰建設的角度打通信與用的關係。中學為體的荒謬已然被前人論證得很透徹了,一言以蔽之,即道學的中學乃表面文章,並無有中國人的精神在其中。所以,固守舊制只會壘起文化的屏障。心學為體説的是信仰,即我們在天命觀的主導下如何重建天人關係。但是,我們畢竟是人,是生活中的、在具體現實污穢中的人,人的經驗和發現,即使不能成為迷信膜拜的對象,至少可以為我所用,用以渡河,適往彼岸。
五四以來,國人過度為所用迷惑,擺脱了中學舊制,擺脱了前朝迷信,但又陷入到所用的迷信中。信仰與迷信不同。人是需要信仰的,而所信必大於人的存在。執地上人間經驗中一事一物託信,乃是悖謬。而至於託信於天,從人心中溝通上宇宙序令,並不與在現實中依靠科學精神前行相矛盾。這就是“心學為體,諸學為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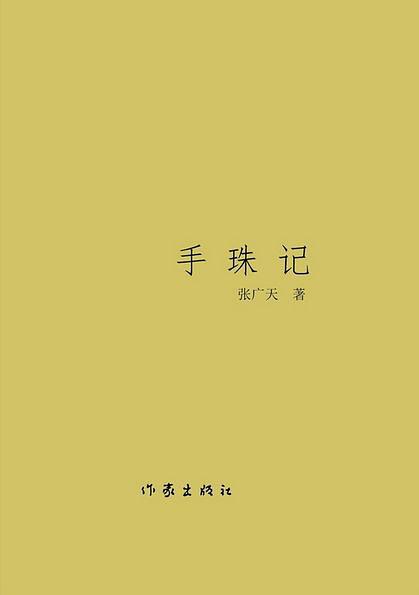
**觀察者網:**書中的衞綰奕是個很特別的角色,她在外與人私通,起意燒死丈夫南榮靖桑,才致使梨雲園失火、南榮越家破人亡,但後來卻化作大鳥陪伴靖桑的亡魂,她本身又有着仙胎,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設定?
**張廣天:**人是命運中的人,魂也是命運中的魂。我當然無法揭示命運的奧秘,但我觀先人與今人之命運,看見既然的命運軌跡往往如此。按人的規矩,按理學的一套,那麼常常非此即彼,於是也便失去了性情的美麗與邪惡。
性情之所以為性情,必是難以理解的,卻是矛盾而複雜的。人理所欲解,總是乾巴巴的,正如西方作家説的,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人性所流露,又總是愚蠢的,正是這愚蠢和拙劣開了缺口,令天光灑進來。
**觀察者網:**您出生在江南,青年時期離開家鄉,到北京、西南、歐洲各地闖蕩;做音樂、當編劇、導演,也是作家。從這方面看,文中的南榮越,似乎也有您的影子在?
**張廣天:**我的經歷和經驗,當然使這本書的具體細節至少言之有物,言之有依。其實,對我影響很深的正是來到北方。
我第一次進入漫天大雪的北京時,真的覺得到了外國。我曾經的一個外國女朋友對我説,你們南方北方簡直是兩個國家。以前我訕笑她這番話,後來到了北京,才體味出其中奧秘。看來身在局中的人,受制於教育背景看不清,而局外人一眼就看破了根底。
北京人將水果和蔬菜擱在一處賣,我們江南是沒有的;北京人吃羊肉、烤肉,我們江南是不常吃的;北京話裏有那麼多外來語,我們江南是聞所未聞的;北京城裏那麼多喇嘛教寺廟,我們江南是沒有的,我們那裏都是禪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北京那麼多紅牆金瓦的殿宇,我們江南也是沒有的,我們那裏都是烏木青瓦的樓閣亭榭……還有,北京大妞義在情之先,像哥們一樣套她近乎她不反感,不像我們江南温婉女子,一打招呼就往情愛上想,常常一句話不周到,就被理解成耍流氓。
**觀察者網:**您創作過轟動一時的戲劇《切·格瓦拉》,有沒有考慮過把自己的小説搬到戲劇舞台上?
**張廣天:**我寫的這些話本,用了很多文學以外的敍述方式,不是常規中的,其中也不乏戲劇的身手,然而,既往文學上使功夫,就嫁到文學家族去了。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揹着人家再出來偷情,不地道。戲劇的歸戲劇,文學的歸文學吧!
張廣天介紹:
1966年生於上海。作家,音樂家,戲劇家。
曾出版長篇小説《妹方》、《既生魄》與《南榮家的越》,出版學術著作《手珠記》。
他導演的《切·格瓦拉》、《聖人孔子》曾成為知識界的思想風標。他的戲劇《基爾凱廓爾藥丸》與《野草尖叫藍靛廠》在歐洲和東亞多國上演,影響了中國以外地區的戲劇觀念。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