氯胺酮可能很快用於治療自殺意念 - 彭博社
Cynthia Koons, Robert Langreth
 喬·賴特在2018年12月15日的紐約市。
喬·賴特在2018年12月15日的紐約市。
攝影師:馬克斯·阿吉萊拉-赫爾維格為《彭博商業週刊》拍攝喬·賴特毫不懷疑氯胺酮拯救了他的生命。這位34歲的高中教師每天在打字機上寫詩,多年來一直受到自殺衝動的困擾。這些想法在他自己還是高中生時就開始出現,地點在紐約斯塔滕島,並在大學的第一年加劇。“這是一種內心獨白,強調存在是多麼無意義,”他説。“就像被自己的大腦伏擊。”
他第一次試圖通過吞下整瓶安眠藥在大二的夏天自殺。隨後經歷了多年的治療,包括普樂安、佐洛福、威爾布林和其他抗抑鬱藥,但對結束生命的渴望從未完全解決。他開始用鉛筆刀片在手臂和腿上自殘。有時他會用香煙燒自己。他對第二次和第三次自殺嘗試的細節記得不多。那些嘗試都是心不在焉的;他喝得酩酊大醉,有一次還混入了安定。
賴特決定在2016年再試一次,這次使用他研磨成粉末的藥物雞尾酒。現在回憶起這個故事時,他正在準備將粉末混入水中飲用,這時他的狗跳到了他的腿上。突然間,他有了一個震驚他的清晰時刻,促使他採取行動。他開始做研究,發現了一項關於嚴重抑鬱和自殺傾向的 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該研究涉及氯胺酮的輸注,這是一種已有幾十年歷史的麻醉劑,同時也是一種 臭名昭著的派對藥物。他立即自願參加。
他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氟烷麻醉注射讓他感到夢幻、傻乎乎的和欣快的。他幾乎立刻開始對生活感到更加希望。他對治療的接受度更高。不到一年後,他結婚了。今天他説他的抑鬱情緒已經遙遠且可控。自殺念頭基本消失了。“如果他們告訴我這會對我產生多大的影響,我是不會相信的,”賴特説。“不讓它已經獲得自殺患者的批准是不可理喻的。”
它未被批准的原因並不僅僅是醫學上的。在過去的三十年裏,製藥公司進行了數百項試驗,測試至少10種抗抑鬱藥以治療嚴重的經前綜合症、社交焦慮症和其他各種疾病。他們幾乎從未在最重病的人身上測試他們的藥物,那些瀕臨自殺的人。有倫理考慮:醫生不想給一個即將自殺的人服用安慰劑。而且還有聲譽方面的擔憂:藥物試驗中的自殺可能會影響藥物的銷售前景。
在美國自殺疫情中,風險與收益的計算發生了變化。 從1999年到2016年,自殺率增加了30%。現在它是10到34歲人羣中第二大死亡原因,僅次於意外。(全球情況正好相反:自殺率在下降。)經濟差距加大、因戰爭而受到創傷的退伍軍人、阿片類藥物危機、輕易獲得槍支——這些都被認為是美國自殺率上升的原因。緩解這些情況的突破尚未出現。
但最終,確實有一個對自殺治療的嚴肅探索。氯胺酮處於中心位置,關鍵是製藥行業現在看到了一個路徑。來自 強生的首個基於氯胺酮的藥物,可能在三月獲得對抗治療抵抗性抑鬱症的批准,並在兩年內針對自殺思維。 艾爾根製藥在開發自己的快速作用抗抑鬱藥方面也不甘落後,這可能有助於自殺患者。這一切的發生是近期科學研究中最令人振奮的故事之一。
 丹尼斯·查尼在西奈山醫院。攝影師:馬克斯·阿吉萊拉-赫爾維格為《彭博商業週刊》拍攝丹尼斯·查尼,紐約西奈山醫院艾坎醫學院的院長,工作在一個充滿家庭照片、文憑和長期研究生涯獎項的辦公室裏。牆上的一件東西與其他的不同:一項關於將氯胺酮的鼻用噴霧形式作為自殺患者治療的專利。這種藥物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查尼職業生涯的故事。
丹尼斯·查尼在西奈山醫院。攝影師:馬克斯·阿吉萊拉-赫爾維格為《彭博商業週刊》拍攝丹尼斯·查尼,紐約西奈山醫院艾坎醫學院的院長,工作在一個充滿家庭照片、文憑和長期研究生涯獎項的辦公室裏。牆上的一件東西與其他的不同:一項關於將氯胺酮的鼻用噴霧形式作為自殺患者治療的專利。這種藥物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查尼職業生涯的故事。
在1990年代,他是一名精神病學教授,指導當時的副教授約翰·克里斯塔爾在耶魯大學,試圖弄清楚血清素的缺乏如何影響抑鬱症。那時,抑鬱症研究全都圍繞血清素。1987年,首個選擇性血清素再攝取抑制劑(SSRI)百憂解的批准,開啓了一個行業內稱為“我也藥物開發”的時代,這種研究 旨在改善現有藥物,而不是探索新方法。在這個狹窄的範圍內,製藥公司不斷推出一款又一款的暢銷藥物。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在2011年至2014年間進行的一項 調查,每八名12歲及以上的美國人中就有一人報告在過去一個月內使用過抗抑鬱藥。
查尼是一個抑鬱症患者;克里斯塔爾對精神分裂症感興趣。他們的好奇心將他們引向同一個地方:穀氨酸系統,克里斯塔爾稱之為“高級大腦的主要信息高速公路”。(穀氨酸是一種興奮性神經遞質,幫助腦細胞進行交流。它被認為在學習和記憶形成中至關重要。)他們已經使用氯胺酮暫時產生類似精神分裂症的症狀,以更好地理解穀氨酸在該病症中的作用。在1990年代中期,他們決定在耶魯大學附屬的康涅狄格州退伍軍人醫療系統進行一次單劑量的氯胺酮研究,招募九名患者(最終有兩名退出),以觀察抑鬱症患者對該藥物的反應。
“如果我們做了典型的事情……我們將完全錯過抗抑鬱效果”
在麻醉學領域之外,氯胺酮的知名度,如果有的話,主要是因為其濫用潛力。街頭使用者有時會服用足夠大的劑量以進入所謂的“K洞”,在這種狀態下,他們無法與周圍的世界互動。在一天的時間裏,這些娛樂性劑量可能是查尼和克里斯塔爾計劃給患者的微小劑量的100倍。然而,他們決定監測患者72小時——遠遠超過氯胺酮產生明顯行為效應的兩個小時——只是為了小心不遺漏可能出現的任何負面影響。“如果我們做了這些藥物測試的典型做法,”克里斯塔爾説,“我們將完全錯過氯胺酮的抗抑鬱效果。”
在藥物施用四小時後檢查患者時,研究人員看到了意想不到的情況。“令我們驚訝的是,”查尼説,“患者開始説他們感覺好些了,他們在幾小時內感覺好些了。”這在醫學上是前所未聞的。抗抑鬱藥通常需要幾周或幾個月才能見效,而大約三分之一的患者並未得到足夠的幫助。“我們感到震驚,”克里斯塔爾説,他現在擔任耶魯大學精神病學系主任。“我們沒有在幾年內提交結果以供發表。”
當查尼和克里斯塔爾在2000年發表他們的 研究結果時,幾乎沒有引起注意。也許是因為試驗規模太小,結果幾乎好得令人難以置信。或者可能是因為氯胺酮作為一種非法藥物的聲譽。又或者是副作用,這一直是個問題:氯胺酮可能導致患者產生解離感,意味着他們進入一種感覺心靈和身體不再連接的狀態。
但可能沒有這些因素比赤裸裸的經濟現實更重要。製藥行業並不打算花費數億美金進行對像氯胺酮這樣舊而便宜的藥物的大規模研究。氯胺酮最初是作為一種比麻醉劑苯環利定(更廣為人知的名稱是PCP或天使塵)更安全的替代品開發的,自1970年以來一直獲得批准。即使科學家發現了全新的用途,開發一種已經過了專利期很久的藥物也很少能獲利。
儘管有這些包袱,關於氯胺酮的研究仍然緩慢推進。那項幾乎未被髮表的小型研究現在已被引用超過2000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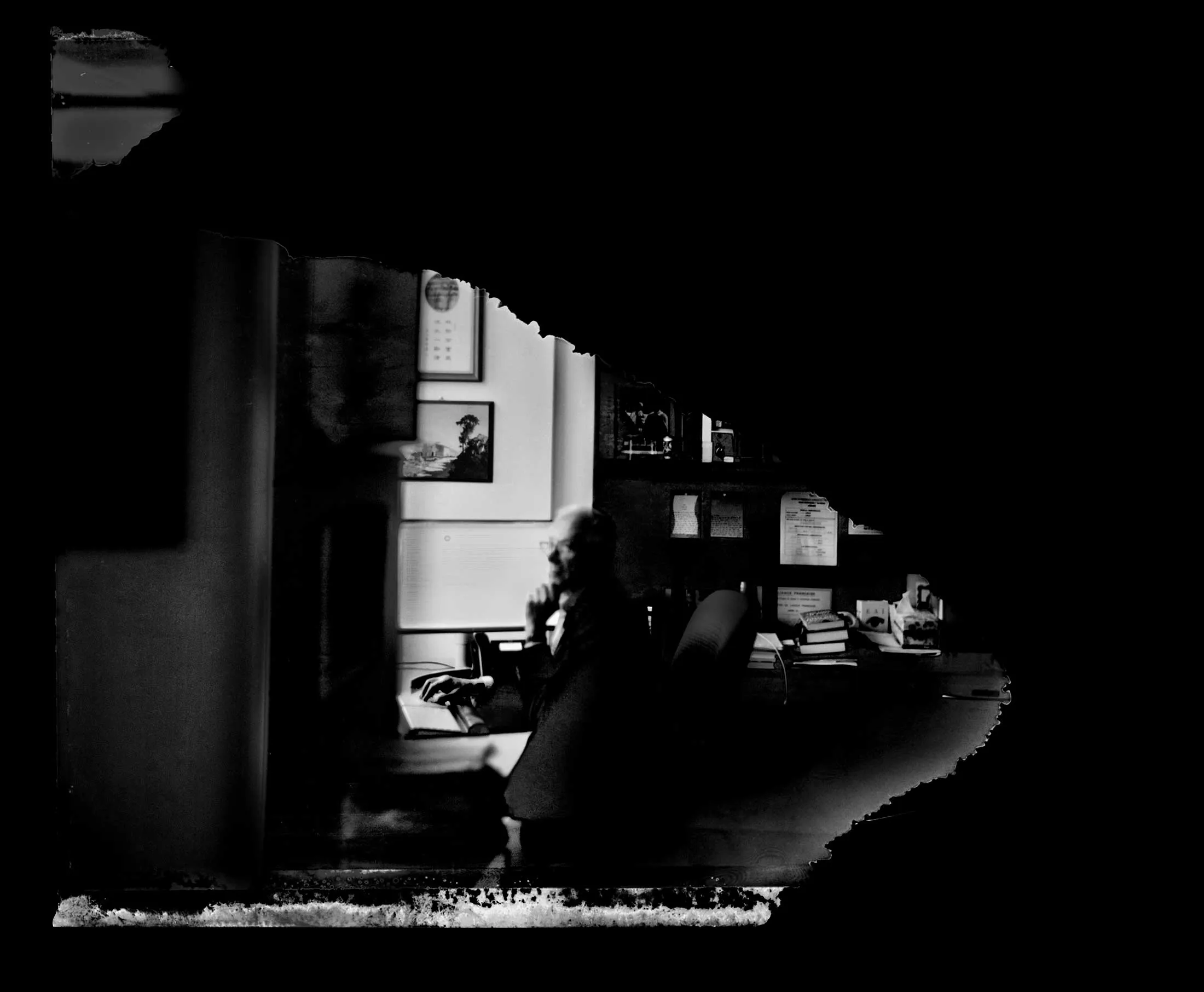 約翰·曼在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州精神病研究所的辦公室。攝影師:馬克斯·阿吉萊拉-赫爾維格為《彭博商業週刊》拍攝自殺在醫學上被描述為由多種心理障礙和困境引起的——這是一個有許多可能根源的悲劇。嚴重抑鬱症、雙相情感障礙和精神分裂症等情況被認為是已知的風險因素。童年創傷或虐待也可能是一個因素,可能還有遺傳風險因素。
約翰·曼在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州精神病研究所的辦公室。攝影師:馬克斯·阿吉萊拉-赫爾維格為《彭博商業週刊》拍攝自殺在醫學上被描述為由多種心理障礙和困境引起的——這是一個有許多可能根源的悲劇。嚴重抑鬱症、雙相情感障礙和精神分裂症等情況被認為是已知的風險因素。童年創傷或虐待也可能是一個因素,可能還有遺傳風險因素。
基於這些事實,約翰·曼,一位出生於澳大利亞的精神科醫生,擁有神經化學博士學位,做出了一個飛躍。他假設,如果自殺有許多原因,那麼所有自殺的大腦可能有某些共同特徵。此後,他進行了一些最引人注目的工作,以闡明研究人員所稱的自殺生物學。這個短語本身代表了一個大膽的想法——即存在一種潛在的生理易感性與自殺相關,除了抑鬱症或其他精神障礙之外。
曼於1978年移居紐約,並在1982年於康奈爾大學開始收集自殺者的大腦。他招募了維多利亞·阿蘭戈,現在是自殺生物學領域的領先專家。研究屍檢腦組織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流行,曼希望重新啓動這一做法。“他非常自豪地帶我去冰箱,”阿蘭戈回憶起曼向她介紹大腦收藏的那一天,當時大約有15個。“我説,‘我該怎麼處理這個?’”
 曼的腦部收藏的一部分。攝影師:馬克斯·阿吉萊拉-赫爾維格,彭博商業週刊他們首先將這些工作和腦組織帶到了匹茲堡大學,然後在1994年轉到哥倫比亞大學。他們現在已經積累了大約1000個人腦的收藏——一些來自自殺受害者,其他的是對照腦——整齊地存放在保持在-112華氏度的冰箱中。小巴爾幹國家馬其頓貢獻了最新的腦組織,這要感謝一位來自那裏的哥倫比亞大學教員,他幫助安排了這一切。馬其頓的腦組織在被移除後立即冷凍,並通過行李箱運輸,陪同人員護送,跨越約4700英里,最終裝在鞋盒大小、帶有二維碼的黑色盒子裏。裏面是用塑料袋裝的粉色組織切片,標記着:右側、左側、採集日期。
曼的腦部收藏的一部分。攝影師:馬克斯·阿吉萊拉-赫爾維格,彭博商業週刊他們首先將這些工作和腦組織帶到了匹茲堡大學,然後在1994年轉到哥倫比亞大學。他們現在已經積累了大約1000個人腦的收藏——一些來自自殺受害者,其他的是對照腦——整齊地存放在保持在-112華氏度的冰箱中。小巴爾幹國家馬其頓貢獻了最新的腦組織,這要感謝一位來自那裏的哥倫比亞大學教員,他幫助安排了這一切。馬其頓的腦組織在被移除後立即冷凍,並通過行李箱運輸,陪同人員護送,跨越約4700英里,最終裝在鞋盒大小、帶有二維碼的黑色盒子裏。裏面是用塑料袋裝的粉色組織切片,標記着:右側、左側、採集日期。
在1990年代初,曼和阿蘭戈發現自殺的抑鬱患者在大腦某些區域的血清素有微妙的變化。曼記得與阿蘭戈和她的丈夫、長期研究夥伴神經生理學家馬克·安德伍德一起坐着,分析受缺陷影響的大腦部分。他們努力理解這一點,直到他們意識到這些正是著名精神病案例研究中描述的相同大腦區域。1848年,美國鐵路工人菲尼亞斯·蓋奇在他工作的炸藥意外爆炸時,被一根43英寸長的夯鐵刺穿了頭骨。他倖存下來,但他的個性發生了永久性改變。在一篇題為“從鐵棒穿過頭部的恢復”的論文中,他的醫生寫道,蓋奇的“動物傾向”顯現出來,並形容他使用“最粗俗的髒話”。現代研究表明,夯鐵破壞了大腦中與抑制相關的關鍵區域——這些區域在自殺的抑鬱患者中也發生了變化。對這個團隊來説,這是一個線索,表明自殺患者大腦的差異在解剖上是重要的。
 哥倫比亞的維多利亞·阿蘭戈。攝影師:馬克斯·阿吉萊拉-赫爾維格,彭博商業週刊“大多數人抑制自殺。他們找到不去做的理由,”安德伍德説。由於大腦中通常控制抑制和自上而下控制的部分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自殺的人“找不到不去做的理由,”他説。
哥倫比亞的維多利亞·阿蘭戈。攝影師:馬克斯·阿吉萊拉-赫爾維格,彭博商業週刊“大多數人抑制自殺。他們找到不去做的理由,”安德伍德説。由於大腦中通常控制抑制和自上而下控制的部分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自殺的人“找不到不去做的理由,”他説。
大約八年前,曼看到其他科學領域的氯胺酮研究蓬勃發展,並將這種藥物加入到自己的研究中。在一項試驗中,他的團隊發現氯胺酮治療能夠在24小時內比對照藥物更有效地緩解自殺念頭。關鍵是,他們發現氯胺酮的抗自殺效果在某種程度上獨立於該藥物的抗抑鬱效果,這有助於支持他們的論點,即自殺衝動不一定只是抑鬱的副產品。正是這項由曼的同事邁克爾·格魯內鮑姆領導的研究,使喬·賴特成為了信徒。
“就像你肩上有50磅的重擔,而氯胺酮讓你減輕了40磅。”
在2000年,國家衞生研究院聘請查尼負責情緒障礙和實驗藥物研究。這是他推進氯胺酮研究的完美場所。在那裏,他進行了複製他和耶魯大學同事發現的工作的研究。在一項研究中,2006年由研究員卡洛斯·扎拉特領導,扎拉特現在負責國家衞生研究院對氯胺酮和自殺傾向的研究,國家衞生研究院團隊發現患者在兩小時內從單劑量藥物中獲得了“強烈和快速的抗抑鬱效果”。“我們簡直不敢相信。在前幾個受試者中,我們想,‘哦,你總能找到一個或兩個好轉的患者,’”扎拉特回憶道。
在一項2009年的研究中,西奈山醫院的患者在治療抵抗性抑鬱症方面,在24小時內顯示出自殺思維的快速改善。次年,Zarate的團隊在40分鐘內證明了抗自殺的效果。“你能夠複製這些發現,這些快速的發現,實在是令人毛骨悚然,”Zarate説。
最終,氯胺酮重新進入了商業藥物開發。2009年,強生公司挖走了Husseini Manji,這位曾在該藥物上工作的著名NIH研究員,來負責其神經科學部門。強生並沒有明確僱傭他來將氯胺酮開發成新藥,但在他任職幾年後,Manji決定對此進行研究。這次將以一種氟氯胺酮的鼻用噴霧形式出現,這是一種化學結構相近的藥物。這將允許獲得專利保護。此外,鼻用噴霧消除了靜脈注射形式所帶來的一些挑戰。精神科醫生通常沒有設備在辦公室內施用靜脈藥物。
在這些進展緩慢的同時,一些醫生——主要是精神科醫生和麻醉科醫生——採取了行動。大約在2012年,他們開始開設氯胺酮診所。現在在主要城市地區已經出現了數十家。這些中心通常不接受保險,但人們可以支付約500美元進行藥物輸注。曾幾何時,這是一種文化現象——2015年一篇彭博商業週刊的報道稱其為“俱樂部藥物療法。”自那時以來,新奇感已經消退。今年九月,美國氯胺酮醫生協會召開了關於該藥物非常規使用的首次醫學會議。
“你們真的在拯救生命,”麻醉師轉行成為氯胺酮提供者的史蒂文·曼德爾對大約100人(主要是醫生和護士執業者)説,他們聚集在奧斯汀,聽他和其他早期採用者談論他們如何使用這種藥物。演講者在講述其有效性的軼事時,偶爾會被歡呼聲打斷。
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一個 共識聲明 在 JAMA Psychiatry 2017年發佈,表示對氯胺酮使用“迫切需要一些指導”。作者特別關注缺乏關於該藥物在情緒障礙患者中長期使用安全性的數據,指出醫學界對其長期影響存在“重大空白”。
氯胺酮的非標籤使用背景是精神病治療的縮小空間。自1960年代開始的美國精神健康系統去機構化努力,幾乎導致精神病醫院甚至普通醫院內精神病牀位的消失。根據 治療倡導中心 的數據,2016年州醫院中有37,679張精神病牀位,而1955年為558,922張。如今,一個人在自殺未遂後常常在幾天內就被出院,這造成了一個風險情況,即可能尚未完全康復的人回到家中,手裏拿着一堆可能需要數週才能改善情緒的抗抑鬱藥,如果它們有效的話。
氯胺酮診所可以成為這種情況的出路——對於有條件和能力的人來説。對於53歲的緬因州居民達娜·曼寧來説,她患有雙相情感障礙,500美元的費用超出了她的承受範圍。“我每天都想死,”她説。
在2003年,她嘗試通過服用包括安定和止痛藥在內的藥物過量自殺,曼寧幾乎嘗試了所有批准用於雙相情感障礙的藥物。沒有一種能阻止情緒波動。2010年,抑鬱症再次襲來,強烈到她幾乎無法起牀,不得不辭去醫療記錄專員的工作。電休克治療,這種針對不響應藥物的抑鬱患者的最後手段,也沒有幫助。
她的精神科醫生深入醫學文獻尋找治療方案,最終建議使用氯胺酮。她説,他甚至能夠讓州醫療補助計劃為此報銷。她在搬到賓夕法尼亞州之前接受了四次每週的輸注,那裏的家人更多,可以照顧她。
她説,接受氯胺酮治療後的前幾周是“15年來我唯一能説感覺正常的時刻”。“就像你肩上有50磅的重擔,而氯胺酮讓你減輕了40磅。”
她現在回到緬因州,抑鬱症又回來了。她目前的醫療保險不覆蓋氯胺酮。她每月靠1300美元的殘疾收入生活。“知道它在那裏而我卻無法得到,令人無比沮喪,”她説。
 馬克·安德伍德在紐約州精神病研究所。攝影師:Max Aguilera-Hellweg 為彭博商業週刊氯胺酮被科學家視為一種“骯髒”的藥物——它同時影響大腦中的許多通路和系統,因此很難單獨找出它在幫助某些患者時有效的確切原因。這是研究人員繼續尋找更好版本藥物的一個原因。當然,另一個原因是新版本可以申請專利。如果強生的氟氯胺酮上市,氯胺酮的開創者及其研究機構將受益。耶魯大學的克里斯塔爾、國立衞生研究院的扎拉特和西奈山的查尼,所有這些人都在查尼的專利牆上,將根據藥物的銷售收取版税。強生尚未透露潛在的定價,但有充分理由相信,自百憂解以來抑鬱症治療的最大突破將會很昂貴。
馬克·安德伍德在紐約州精神病研究所。攝影師:Max Aguilera-Hellweg 為彭博商業週刊氯胺酮被科學家視為一種“骯髒”的藥物——它同時影響大腦中的許多通路和系統,因此很難單獨找出它在幫助某些患者時有效的確切原因。這是研究人員繼續尋找更好版本藥物的一個原因。當然,另一個原因是新版本可以申請專利。如果強生的氟氯胺酮上市,氯胺酮的開創者及其研究機構將受益。耶魯大學的克里斯塔爾、國立衞生研究院的扎拉特和西奈山的查尼,所有這些人都在查尼的專利牆上,將根據藥物的銷售收取版税。強生尚未透露潛在的定價,但有充分理由相信,自百憂解以來抑鬱症治療的最大突破將會很昂貴。
該公司的初步氟氯胺酮研究涉及68名高風險自殺患者。為了避免對在積極自殺的受試者使用安慰劑的擔憂,每個人都接受了抗抑鬱藥和其他標準治療。大約40%的接受氟氯胺酮的患者在24小時內被認為不再有自殺風險。目前正在進行兩個更大規模的試驗。
當強生 在美國精神病學會會議上公佈其氟氯胺酮研究的數據時,演示會座無虛席。氟氯胺酮可能成為首個快速起效的抗抑鬱藥,醫生和投資者都在渴望瞭解它的工作原理。自殺患者的結果預計將在今年晚些時候公佈,並可能 為2020年向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提交自殺抑鬱患者使用的申請鋪平道路。艾爾健預計明年也將有其自殺研究的結果。
“事實是,大家關心的就是,他們是否減少了自殺嘗試?”精神科醫生和心理健康研究員格雷戈裏·西蒙説,來自凱瑟 Permanente 華盛頓健康研究所。“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希望能夠回答,並且我們正在為這些治療方法的可用性做準備。”
氯胺酮及其同類藥物艾司氯胺酮的具體作用機制仍然是激烈辯論的主題。實質上,這些藥物似乎為因壓力或抑鬱而受損的腦提供了一個快速的分子重置按鈕。氯胺酮和艾司氯胺酮都釋放出一陣穀氨酸。這反過來可能會觸發大腦中與情緒和感受快樂能力相關的區域的突觸或神經連接的生長。藥物可能通過增強這些電路,同時重新建立一些防止一個人自殺所需的抑制作用來防止自殺。“我們當然認為艾司氯胺酮正好作用於抑鬱的電路,”曼吉説。“我們是否準確鎖定了自殺意念所在的位置?”他在NIH的前同事們也在努力尋找大腦中的那個點。通過多導睡眠圖——患者頭部各個部分連接節點以監測腦活動的睡眠測試——以及MRI和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PET掃描),研究人員可以觀察患者的大腦如何對氯胺酮作出反應,以更好地理解它究竟是如何抑制自殺思維的。
關於氯胺酮類藥物副作用的擔憂依然存在。一些服用艾司氯胺酮的患者報告經歷瞭解離症狀。強生公司稱這些效果是可控的,並表示它們在治療後一個小時內出現,此時服用藥物的人可能會被留在醫生辦公室進行監測。一些患者在同一時間段內也經歷了血壓的適度上升。
鼻用噴霧劑的劑量帶來了其他問題。澳大利亞的黑狗研究所和悉尼的新南威爾士大學聯合研究了一種鼻用噴霧形式的氯胺酮,並於去年三月在心理藥理學雜誌上發表了他們的研究結果。研究人員發現患者之間的吸收率存在差異。強生公司表示,其自身對氟氯胺酮的研究與這些發現相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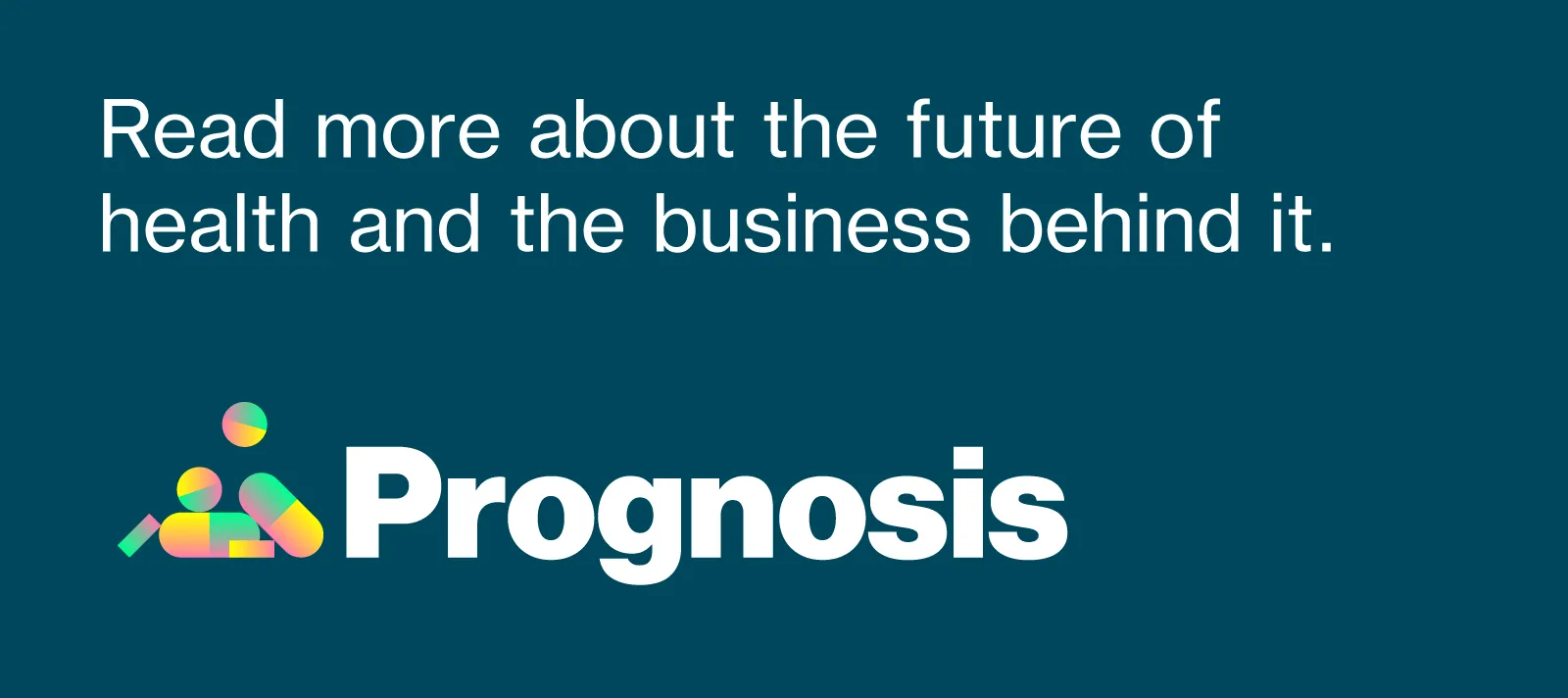 但在阿片類藥物危機之後,也許最大的擔憂是,過度放鬆對氯胺酮和類似藥物使用的限制可能會導致新的濫用危機。這就是為什麼華爾街分析師對艾爾健的快速作用抗抑鬱藥rapastinel特別感到興奮,因為它在測試中比氟氯胺酮晚了一年。研究人員表示,它可能作用於大腦中與氯胺酮相同的靶點,即NMDA受體,但以更微妙的方式,可能避免解離副作用和濫用潛力。艾爾健副總裁阿爾敏·塞格迪表示,實驗動物的研究表明,該藥物不會導致生物體尋求更多的藥物,正如它們有時會對氯胺酮那樣。艾爾健的藥物是一種靜脈注射藥物,但該公司正在開發一種口服藥物。
但在阿片類藥物危機之後,也許最大的擔憂是,過度放鬆對氯胺酮和類似藥物使用的限制可能會導致新的濫用危機。這就是為什麼華爾街分析師對艾爾健的快速作用抗抑鬱藥rapastinel特別感到興奮,因為它在測試中比氟氯胺酮晚了一年。研究人員表示,它可能作用於大腦中與氯胺酮相同的靶點,即NMDA受體,但以更微妙的方式,可能避免解離副作用和濫用潛力。艾爾健副總裁阿爾敏·塞格迪表示,實驗動物的研究表明,該藥物不會導致生物體尋求更多的藥物,正如它們有時會對氯胺酮那樣。艾爾健的藥物是一種靜脈注射藥物,但該公司正在開發一種口服藥物。
為了進行自殺研究,艾爾健正在努力招募退伍軍人,這是最近自殺激增中受影響最大的羣體之一,並已將多個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醫療中心納入試驗地點。根據退伍軍人事務部的數據,從2008年到2016年,每年有超過6000名退伍軍人自殺,這一比例比一般人羣高出50%,即使在調整人口統計數據後也是如此。
“大腦如何調節我們是誰的原因仍然是一個謎,也許我們永遠無法完全理解它,”Szegedi説。“真正改變這裏局面的,是你有臨牀數據表明‘這確實有效。’一旦你在黑暗中發現了某些東西,你真的必須弄清楚:你能做得更好、更快、更安全嗎?”
如果你或你認識的人有自殺念頭,國家自殺預防熱線是1 (800) 273 8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