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城市》談規劃如何跟隨房地產 - 彭博社
bloomberg
 位於紐約市中央公園南側的新超高塔樓中央公園塔、111 W 57街和53W53正在建設中。盧卡斯·傑克遜/路透社全球房地產的估計價值為217萬億美元,佔全球資產的60%以上。儘管其中四分之三的金額與住房相關,但這並沒有為許多人帶來安全的住所或繁榮:2016年,美國的住房擁有率達到了50年來的最低點,而在同一年,美國所有房屋銷售中有37%是賣給了缺席投資者。
位於紐約市中央公園南側的新超高塔樓中央公園塔、111 W 57街和53W53正在建設中。盧卡斯·傑克遜/路透社全球房地產的估計價值為217萬億美元,佔全球資產的60%以上。儘管其中四分之三的金額與住房相關,但這並沒有為許多人帶來安全的住所或繁榮:2016年,美國的住房擁有率達到了50年來的最低點,而在同一年,美國所有房屋銷售中有37%是賣給了缺席投資者。
隨着華爾街支持的邀請之家(由黑石集團擁有)現在成為全國最大的單户住宅房東——收購了許多十年前被止贖的同類物業——很難將住房擁有的承諾視為美國夢的一個原則。並不是説租房就容易得多:過去二十年,美國的平均入住租金已經翻了一番以上。
彭博社城市實驗室芝加哥以冷靜、派對和陽光克服了DNC懷疑者納粹掩體的綠意改造將醜陋的過去變成城市的眼球吸引者聖保羅的Cortiços如何幫助庇護南美最大的城市跨洲際公共交通競賽這些挑戰提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可以做些什麼?儘管許多城市規劃者希望解決住房危機,但獲得數百萬或數十億美元公共補貼的重建項目迫使他們做出妥協,塞繆爾·斯坦在他的新書中辯稱資本城市:紳士化與房地產國家(Verso,$17.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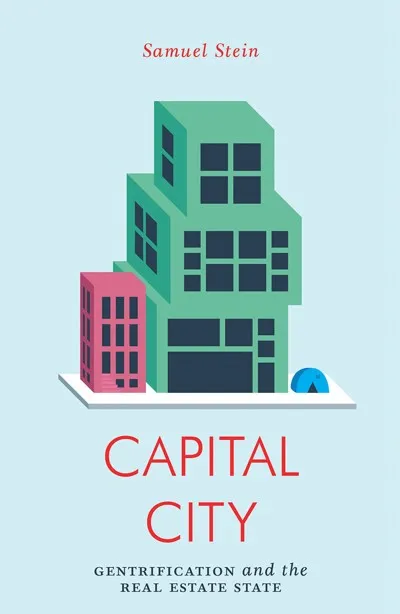 Verso斯坦認為,開發、金融和全球精英將財富停放在豪華住房中的綜合力量淹沒了規劃者的最佳意圖。隨着大多數工業活動被推向城市邊界之外,公共服務依賴於財產税,他認為,房地產已經主導了城市規劃;科技和金融部門對此依賴,並未提供任何政治制衡。
Verso斯坦認為,開發、金融和全球精英將財富停放在豪華住房中的綜合力量淹沒了規劃者的最佳意圖。隨着大多數工業活動被推向城市邊界之外,公共服務依賴於財產税,他認為,房地產已經主導了城市規劃;科技和金融部門對此依賴,並未提供任何政治制衡。
斯坦寫道,國家是“紳士化的中心參與者”。規劃者一方面通過土地使用和税收激勵吸引開發商和房東,同時另一方面通過便利設施吸引新居民和購物者——所有這些都推高了價格。“規劃者的使命是想象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但他們的日常工作涉及創造一個更有利可圖的世界,”他寫道。本書的一章追蹤了特朗普家族三代人的房地產交易,這些交易在不同時間受到公共政策和個人利益激勵的推動。
對於斯坦——一位在紐約市立大學攻讀地理博士學位的候選人、亨特學院的講師以及受過培訓的規劃師——規劃問題是理解我們當前經濟秩序的核心,尤其是在城市生活中的體現。CityLab詢問了他關於房地產的崛起、激進的規劃師以及有志成為規劃師的人應該如何看待這一角色的問題。(本次採訪經過編輯和壓縮以便於理解。)
您認為房地產的崛起和工業主義的衰退(工業主義需要低土地成本和可負擔的住房以供工人居住)正在如何改變規劃師與民眾之間的關係?
規劃師的響應能力確實在變得越來越困難。在房地產日益集中的資金中,規劃師對普通民眾的響應能力正在減弱,他們沒有一羣獨立的資本家、工業資本家在一旁對他們提出完全不同的要求。
我認為我們常常希望能夠告訴規劃師他們所做的事情是錯誤的,然後讓他們去做其他事情,但這並不是系統的運作方式。規劃師主要是遵循委員會和市長任命的規劃部門負責人的指令,而在大多數大城市中,市長們從房地產中獲得了大量資金,即使是那些承擔反對城市更新責任的人,比如紐約市。規劃師很難簡單地看到某些事情是錯誤的並加以修正。我不想讓他們逃避自己行為後果的責任,但我也不希望人們期待他們僅僅因為應該改變就去改變。在目前的結構下,這是一項非常困難的任務。
你為什麼強調在日益不平等的城市地區規劃的重要性?
在美國的背景下,規劃者被低估——不僅作為個體,規劃的行為也被輕視。我認為,任何人都應該弄清楚他們的城市發生了什麼,以及為什麼他們的住房成本如此瘋狂,而不是把所有責任都歸咎於規劃者,而是將他們作為一種切入點,理解資本、國家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關係。
“在房地產中金錢的日益集中,規劃者對普通人變得越來越不敏感。”我受過規劃方面的訓練,所以我理解他們是誰以及他們在做什麼,我確實相信他們是一羣非常友好的人。我把手稿發給了一位建築師朋友,這個説法引起了她的共鳴:她説,‘這真的很真實[規劃者是好人],而且沒有人會這樣説建築師。’所以有趣的是,這羣善意的人在某種程度上對工人階級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如此巨大的負面轉變。
你有一章專門講述特朗普家族的房地產事業——不僅是總統,還有他的父親和祖父。你認為他們的故事如何幫助解釋當前房地產和政治的動態?
現在他是總統了,我們往往會沉迷於所有的醜聞和日常的憤怒。但我想提醒人們,不僅僅是抽象的房地產資本在獲得權力。這在我們政治層級的第一位置上得到了體現。
[特朗普]家族讓我們看到城市規劃歷史的另一面——這不僅僅是規劃者及其對城市的影響,還涉及到是誰在推動他們做這些事情。特朗普家族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這一點,但關鍵並不是他們是例外;而是他們在利用公共政策和補貼謀取個人利益方面是普通的[因為他們從未處於紐約房地產的巔峯]。真正例外的是他們中的一個現在是總統。
你討論了一種激進規劃的遺產,這教會了積極的規劃者“雖然他們可能在工作場所是孤獨的,但他們在工作隊伍中並不孤單。”
長期以來,叛逆的規劃者歷史悠久,60年代和70年代出現了幾種不同的模式。曾經有過平等機會規劃者(PEO),試圖將城市規劃者與反城市更新運動聯繫起來。還有規劃者地下組織,這是一個更激進的規劃者運動,他們向活動家泄露城市正在做的事情的信息,並撰寫匿名證詞和給編輯的信件。
哈萊姆建築師復興委員會是一個有趣的歷史,規劃者積極提升哈萊姆工人階級想象自我決定在空間上會是什麼樣子的能力。然後你會看到 規劃者網絡,它源於[PEO],作為一個左翼城市規劃者的組織,可以與美國規劃協會對立。這個組織仍然存在,我認為它是希望超越新自由主義及其特定工作的規劃者的重要資源。
我認為這種激進的城市規劃者仍然有其角色,不僅在系統外,也在系統內。人們必須組織起來,而不僅僅是在個人的自由時間裏做,而是要集體行動,部分原因是為了擺脱對規劃者施加的羣體思維。當你在系統內部工作時,往往會被告知某些事情是不可能的,而實際上這些事情只是對掌權者來説不受歡迎。我認為,思維不同的規劃者在工作之外聚在一起,思考和制定策略,尋找他們如何能成為挑戰其上司的運動的資源,這一點非常重要。
你會對那些對城市規劃領域感興趣的人説些什麼,作為他們考慮這項工作的建議?
我會鼓勵他們始終保持批判性思維,不要氣餒。我認為規劃中有一種強烈的務實傾向,這在將激進思想轉化為可行方案時是有價值的。但這也可能抑制激進主義和遠見思維,甚至是烏托邦主義,而這在知道我們希望在哪裏時也是有用的。
我鼓勵人們堅持這些衝動,找到與他們有相同想法的人,或者挑戰他們自己思維的人。在孤立中,系統吞噬我們,但集體行動可以讓我們想象出更好的城市規劃方式,並與那些挑戰他們的社會運動相連接。關鍵在於不去強加那些作為專業規劃者施加給我們的限制,而是成為這些運動的資源,幫助他們取得成功。
更正: 本文的原始版本錯誤地識別了塞繆爾·斯坦的博士候選人身份;他是在紐約市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