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郊區的另類歷史 - 彭博社
Amanda Kolson Hurley
 史蒂夫·布朗斯坦/蓋蒂以下是新書的摘錄《激進的郊區》(貝爾特出版,$16.95)。
史蒂夫·布朗斯坦/蓋蒂以下是新書的摘錄《激進的郊區》(貝爾特出版,$16.95)。
在1960年代初,馬爾維娜·雷諾茲寫了一首名為“小盒子,”靈感來自於在灣區一個新的郊區住宅區開車經過一排排相似的淡色房屋。(她的朋友皮特·西格在1963年用這首歌取得了成功。)雷諾茲將這些千篇一律的房子視為居住在其中的人的從眾心態的象徵和塑造者——那些只渴望打高爾夫球和撫養將來會住進“千篇一律”盒子的孩子的醫生和律師。
彭博社城市實驗室芝加哥以冷靜、派對和陽光克服DNC懷疑者納粹掩體的綠意改造將醜陋的過去變成城市的眼球吸引者聖保羅的公寓如何幫助庇護南美洲最大的城市僅使用公共交通的跨洲競賽但雷諾茲錯了,關於住在這個郊區的人的身份,達利市,位於舊金山以南。這裏最初並不是她想象中的喝馬提尼的醫生和律師的家,而是那些在戰後住房繁榮中最後一批進入的工人階級和中下層(白人)奮鬥者。
然後,僅僅在雷諾茲寫下這首歌幾年後,菲律賓人和其他來自亞洲的移民開始抵達達利市。雷諾茲所鄙視的“嘈雜”建築對他們改造和擴建大家庭的房屋來説是可行的,達利市成為了美國的“菲律賓人首都”,在美國擁有最高濃度的菲律賓移民。
陳詞濫調和誤解仍然在大眾想象中定義了郊區,這讓我感到瘋狂。我住在馬里蘭州的蒙哥馬利縣,位於華盛頓特區之外。我是一個郊區居民,但我的生活並不圍繞修剪整齊的草坪、地位焦慮或對同質性的渴望。我的郊區經歷是乘坐公交車,周圍的人用西班牙語和法語克里奧爾語聊天。我的鄰居來自西藏、巴西和肯尼亞,還有辛辛那提。我的兒子在一所反映美國今天多樣性和頑固不平等的學校上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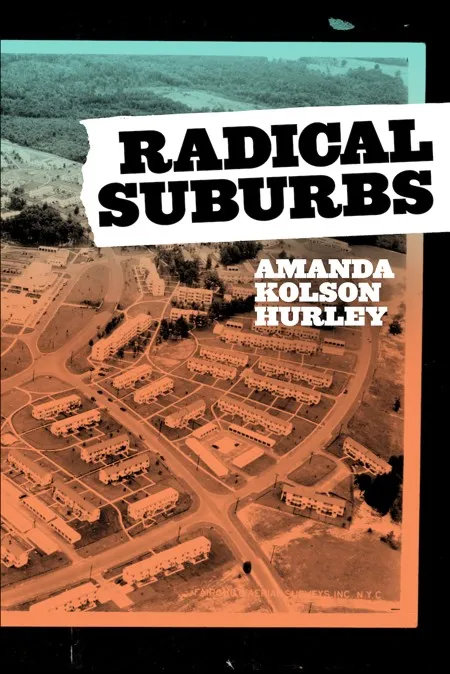 貝爾特出版大多數美國人所知道的郊區基本故事大致如下: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富人的鄉村度假勝地和“電車郊區”在城市的邊緣出現。然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道路和廉價的政府抵押貸款吸引了數百萬白人從城市的公寓和排屋遷移到新開闢的郊區小區。他們中的許多人是為了逃避非裔美國人最近遷入的社區和學校,這種破壞性現象被稱為白人逃離。
貝爾特出版大多數美國人所知道的郊區基本故事大致如下: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富人的鄉村度假勝地和“電車郊區”在城市的邊緣出現。然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道路和廉價的政府抵押貸款吸引了數百萬白人從城市的公寓和排屋遷移到新開闢的郊區小區。他們中的許多人是為了逃避非裔美國人最近遷入的社區和學校,這種破壞性現象被稱為白人逃離。
郊區是這些白人中產階級美國人可以將自己與感知的城市弊病隔離的地方,在一個靜態和受管控的環境中,私人空間、財產擁有、種族同質性和核心家庭是主導價值觀。
這並非不真實——但遠非完整。激進的郊區是關於一波波理想主義者,他們在1820年代開始在美國東部城市外建立替代郊區,並持續到1960年代。這些羣體有着非常不同的背景和動機,但他們都相信地方社區在塑造道德和社會價值觀方面的力量,以及郊區土地提供的自由,以新的方式生活和建設。
與那些深入美國內陸定居孤立公社的羣體相比,這些人可以用一個聽起來矛盾的短語來形容,稱為實用的烏托邦者。靠近城市讓他們能夠在有經濟支持和緊急出口的情況下嘗試新的生活方式。現在,在一個可以合理地説——國家的未來懸掛在郊區在接下來的20或30年內的作為上,他們的歷史表明,勇敢的社會和建築實驗並不是郊區所陌生的。事實上,這是一種郊區傳統。
郊區並不是美國或甚至西方的發明。郊區的存在與城市一樣久遠。在公元前第三個千年,烏爾的郊區延伸到城市之外數英里。在古羅馬,城市的邊緣是貴族們保持“鄉村”度假的地方。但這個區域也是羅馬人推開他們不想看到、聽到或聞到的地方——例如,像製革和制磚這樣的有害工業。
即使在中世紀,城牆也並不是看起來那麼堅固的界限。郊區區域超出了它們的範圍,人和貨物往返流動。“在歐洲及其他地方,‘有牆的中世紀城市’多次擴大其圍牆區域,以容納其邊緣地帶併為未來擴展做準備,”城市學者施洛莫·安吉爾寫道。妓女、吉普賽人和麻風病人常常被迫生活在 城外,字面意思是“在城市之下”。這個術語本身就暗示了保護牆的高度以及那些在其懷抱之外的不確定地位。
美國的郊區早於歐洲殖民化的歷史要久遠得多。在聖路易斯附近,考古學家最近發現了一個900年前的卡霍基亞郊區的遺蹟,曾是墨西哥以北最大的美洲原住民城市。(這個古老郊區的遺址位於現代的伊利諾伊州東聖路易斯鎮,“在一個破舊的肉類加工廠和一個現在關閉的脱衣舞俱樂部之間的半路上,” 正如NPR報道的。)
波士頓、紐約和費城在獨立戰爭之前就已經有了郊區。正如在歐洲的情況一樣(並且仍然如此),這些郊區主要是為低社會經濟羣體而設。精英們則留在市中心。但19世紀中葉,第一批我們容易識別的郊區開始出現——包括弗雷德裏克·勞·奧姆斯特德的 伊利諾伊州的河濱和新澤西州的盧埃林公園。這一時期也恰逢家庭崇拜的興起,提倡家庭主婦作為 “家中的天使,”以及位於遠離城市污垢和罪惡的安全距離的獨立郊區別墅,作為理想的美國家庭住所。
 一幅理想化的中上層家庭生活的庫里爾與艾夫斯石版畫。國會圖書館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圍繞美國城市繁榮發展的富裕郊區,英美家庭生活在優雅的維多利亞女王風格和都鐸復興風格的房屋中,如堪薩斯城的 鄉村俱樂部區、費城的栗子山和加利福尼亞的比佛利山莊。工業和大多數商業活動常常被驅逐出這些郊區,黑人和猶太人被限制性契約禁止購買房屋。
一幅理想化的中上層家庭生活的庫里爾與艾夫斯石版畫。國會圖書館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圍繞美國城市繁榮發展的富裕郊區,英美家庭生活在優雅的維多利亞女王風格和都鐸復興風格的房屋中,如堪薩斯城的 鄉村俱樂部區、費城的栗子山和加利福尼亞的比佛利山莊。工業和大多數商業活動常常被驅逐出這些郊區,黑人和猶太人被限制性契約禁止購買房屋。
然而,即使在它們的全盛時期,精英聚居區也不是城市邊緣的常態。農業在這裏仍然蓬勃發展,通常由外籍和非白人農民進行,同時工廠也在侵佔。貧民窟點綴着城市的邊緣,還有一些簡陋的開發項目,人們在荒地上建房,挖井,養雞和牛,種植蔬菜。在他的書中 他們自己的地方,歷史學家安德魯·維斯講述了查格林瀑布公園的歷史,這是克利夫蘭一個自建的黑人郊區,發展到擁有數百名居民、四座教堂、一所小學和一個社區中心。
在19世紀及20世紀初,公社、殖民地和其他有意的定居點也不斷出現在城市附近。 在 許多 例子中,一個名為哈莫尼斯的獨身德語宗教團體在1820年代建立了一個美麗而繁榮的小鎮,名為經濟鎮,位於現在的賓夕法尼亞州阿姆布里奇。靠近匹茲堡市場對他們的製造業和旅遊貿易(該鎮有一家酒店,甚至還有一個博物館,這是美國最早的博物館之一)至關重要。
和諧派沒有私人財產,所有物品共同擁有,鎮上的建築反映了這一點,基礎設施如共享的麪包烤爐和為節日盛宴準備的社區廚房。不相關的成年人有時一起生活,這與現代的羣體住宅並無不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對和諧派的社會制度讚不絕口——只是沒有宗教。這個教派逐漸人數減少,最終在1905年解散。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對和諧派的社會制度讚不絕口——只是沒有宗教。十年後,即1915年,一羣鬆散的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在紐約登上火車,抵達新澤西州中部,在那裏建立了一個殖民地和進步學校——並避開了城市裏的警察審查。當他們從水塔上升起紅旗時,當地人爬上去將其扯下。但他們或多或少被放任自流,斯特爾頓殖民地在大蕭條和許多政治鬥爭中持續到1950年代。
一些居民通勤到紐約,乘坐早上5:45的火車去服裝區工作或出售他們養的雞蛋。他們中的許多人住在基本的兩到三間房的小屋裏。他們在流行之前就已經是微型房屋的居民——並不是因為對極簡主義的渴望,而是因為那是他們唯一能負擔得起的。出租任何空餘房間給房客是補充收入的常見方式。隨着無政府主義作為政治運動的衰退,一些殖民者逐漸離開,而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入伍時附近一個大型軍營的開放加速了斯特爾頓的滅亡。
 一個孩子在新澤西的斯特爾頓殖民地的小屋前拉小提琴。一些中產階級的訪客對粗糙的建築和基礎設施感到震驚,但居民們,主要是工人階級的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儘管資金有限,仍然能夠在這裏購買土地並建造房屋。特別收藏與大學檔案,拉德格大學圖書館戰後,私人房屋建築商——憑藉大規模生產的技術和政府政策的支持——在數千平方英里的郊區鋪開了他們的“盒子”。但對新的住宅區來説,存在替代方案和挑戰。
一個孩子在新澤西的斯特爾頓殖民地的小屋前拉小提琴。一些中產階級的訪客對粗糙的建築和基礎設施感到震驚,但居民們,主要是工人階級的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儘管資金有限,仍然能夠在這裏購買土地並建造房屋。特別收藏與大學檔案,拉德格大學圖書館戰後,私人房屋建築商——憑藉大規模生產的技術和政府政策的支持——在數千平方英里的郊區鋪開了他們的“盒子”。但對新的住宅區來説,存在替代方案和挑戰。
例如,一位名叫 莫里斯·米爾格拉姆 的不尋常的房屋建築商幾乎在其後院挑戰了萊維頓的白人至上主義。作為一名前社會主義活動家,米爾格拉姆於1954年開設了一個名為康科德公園的綜合性住宅區,包含140棟房屋。它位於費城東北部,距離賓夕法尼亞州的萊維頓幾英里。購房者包括幾對跨種族夫婦、一些共產主義者和許多不墨守成規的人。他們的孩子們一起玩耍,而他們的父母則組成了一個保姆合作社,以及保齡球、攝影和縫紉俱樂部——就像其他新郊區的居民一樣。
“郊區打破種族壁壘,” 紐約時報 的標題宣佈。“費城的新私人住房項目整合了黑人和白人——沒有發生任何事件——沒有一個家庭從理想和韌性建立的殖民地搬走。”
 1957年在康科德公園舉行的每月鄰里會議,如《黑檀》雜誌所描繪。莫里斯·米爾格拉姆檔案 [Coll. 2176],賓夕法尼亞歷史學會康科德公園離萊維鎮足夠近,以至於在1957年,當萊維鎮的第一位黑人居民黛西和威廉·邁爾斯遭到憤怒人羣騷擾時,鄰里派出一個跨種族小組前去守護他們的家。
1957年在康科德公園舉行的每月鄰里會議,如《黑檀》雜誌所描繪。莫里斯·米爾格拉姆檔案 [Coll. 2176],賓夕法尼亞歷史學會康科德公園離萊維鎮足夠近,以至於在1957年,當萊維鎮的第一位黑人居民黛西和威廉·邁爾斯遭到憤怒人羣騷擾時,鄰里派出一個跨種族小組前去守護他們的家。
即使在其反文化的變體中,戰後郊區的規劃仍圍繞着全職媽媽、爸爸和小杰克與小莎莉展開。如今,美國的單身人士、單親家庭和多代同堂的家族數量超過了有幼兒的核心家庭。千禧一代由於工資微薄和大量學生貸款債務,往往無法負擔他們成長時的郊區分層住宅。而且即使他們能買得起,很多人也不想買。
這成為無數趨勢文章的素材,但千禧一代確實有對城市生活的偏好。民意調查 顯示他們重視能夠步行到商店和餐館以及短途通勤。年輕成年人還報告稱,他們在城市中比前幾代人在同一生活階段時更快樂。
我們可能正處於“偉大的反轉”,正如作家艾倫·埃倫哈特所稱:全國從戰後富裕郊區和貧窮城市的模式,迴歸到精英城市和低端郊區的歷史常態。即使我們不是,然而,日益加劇的社會不平等和人口變化——尤其是氣候變化——使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我們的郊區是為誰和什麼而存在。
目前,一些郊區正在適應新的現實,轉變為擁有步行市中心、輕軌線路和更密集住房形式的“城市郊區”。這種有意識的城市化在滿足年輕人偏好方面是聰明的。但這也是唯一負責任的做法。聯合國氣候變化政府間專門委員會在2018年10月的報告中警告説,我們只有短暫的時間窗口——直到2030年——來降低排放,以避免災難性的變暖,而做到這一點將需要“在社會各個方面進行快速、深遠和前所未有的變化”。
研究表明,蔓延式土地使用通過去中心化工作和服務並促使我們更多開車,從而增加温室氣體排放。到處開車的人也更少活動,因此更容易患上糖尿病等慢性疾病。郊區,像城市一樣,需要更多的社區,讓居民可以步行滿足日常需求;優先考慮行人、自行車和輕軌及公交車的街道;以及高質量的公共空間。改造郊區,引用艾倫·鄧漢-瓊斯和瓊·威廉姆森的話,她們寫了一本同名書籍,是“本世紀的大項目”。
 不幸的是,郊區在那些能夠改善它們的人中間存在一種污名:建築師。設計精英們多年來交替地對郊區表示贊助或抨擊,自從1933年國際現代建築大會稱郊區為“在城市牆壁上翻滾的一種污垢”以來。
不幸的是,郊區在那些能夠改善它們的人中間存在一種污名:建築師。設計精英們多年來交替地對郊區表示贊助或抨擊,自從1933年國際現代建築大會稱郊區為“在城市牆壁上翻滾的一種污垢”以來。
比利時建築師萊昂·克里爾聲稱:“郊區恨自己”,他以對傳統城市主義的讚美而聞名於世,發表了許多爭議性的著作和漫畫。對克里爾來説,郊區本質上是寄生蟲,是一種惡性腫瘤。“它知道自己既不是鄉村也不是城市,想要征服世界,因為它無法與自己和解,”他寫道。“郊區通過包圍城市來扼殺城市,撕裂城市的心臟。郊區只能生存,不能生活。”
早期實驗性郊區的居民認為他們生活在殭屍社區的想法是可笑的,他們相信自己是開拓者,並熱情地投入公共生活。在馬里蘭州的格林貝爾特,一個由聯邦政府作為新政的一部分建立的進步示範城鎮,一些居民認為他們提供了一種沿着不同、更合作的路線重繪社會的模式。一位格林貝爾特居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給華盛頓一家報紙寫信時説:
我們在格林貝爾特學會了,儘管作為個體我們是微弱的,但作為一個羣體我們有力量。我們學會了團結社會行動的重要性和潛力——如果我們的民主要生存,我們的人民還必須學習什麼更偉大的教訓呢?
喬恩·索托·斯科特,一位退休的大學教授,曾在斯特爾頓殖民地長大,他告訴我:“我認為這是任何人都能擁有的最好的童年。”勞拉·托馬斯,一位退休的數學老師,記得在1960年代以極大的懷疑態度去看弗吉尼亞州的綜合新城雷斯頓。她是非裔美國人;她為什麼要搬到弗吉尼亞呢?但她最終在那裏定居,組建家庭,並參與了公民團體雷斯頓黑人焦點。
早期居民對這些實驗性郊區生活在“殭屍社區”中的想法會感到可笑。“無論[雷斯頓的創始人羅伯特]西蒙做了什麼,無論信息是什麼,無論他如何宣傳——我無法確切説出,”托馬斯説。“他吸引了在種族和社會經濟上非常不同的人。但他們在對待人的觀點上有共同點。這成為了雷斯頓的普遍特徵。”
克里爾的話背後是對郊區混合特質的厭惡——它如何混淆城鎮與鄉村、人造與自然的明確二元對立。我聽到過同樣的情緒,抱怨郊區是“兩種世界的最糟糕之處”——比鄉村更擁擠和繁忙,卻比城市更無趣。
但如果我們選擇擁抱郊區的中間狀態,而不是譴責它呢?在過去的150年裏,郊區居民生活在大型公寓和小棚屋、現代公寓和新哥特式豪宅中。他們是租户和房主、家庭傭人和企業高管。他們既培育翡翠般的草坪,也種植農作物。他們尋求逃避社會進步,追求擺脱常規的自由。
嚴厲的分區和土地使用法規可能試圖讓時間靜止,但郊區的未來並沒有什麼是註定的,而大多數美國人都生活在這裏。與其對郊區的問題感到絕望,我們應該受到郊區歷史的啓發,努力去解決這些問題。正如斯特爾頓的無政府主義者所知,以及在萊維頓的邁爾斯家旁守夜的康科德公園居民所知:郊區是我們所創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