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們正在尋找超越阿片類藥物的新方法來緩解疼痛 - 彭博社
Naomi Kres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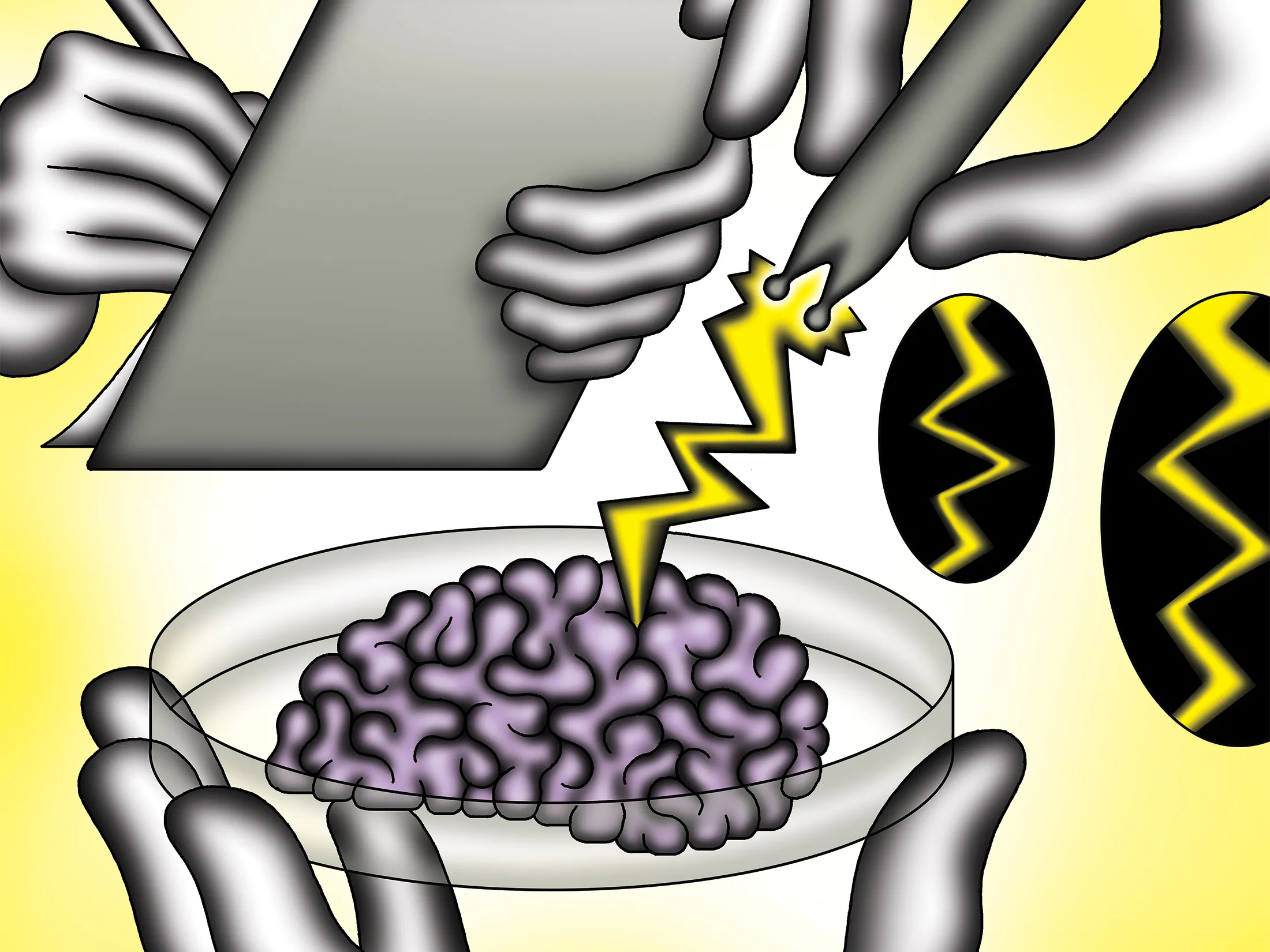 插圖:Alexis Beauclair 為彭博商業週刊蘇珊·哈拉的腳部疼痛開始時像針刺一樣,隨後發展成閃爍的火焰。每個月,哈拉都發現自己在不同的醫生辦公室裏,等待另一種疾病被排除在外:沒有不安腿綜合症,沒有風濕病,感謝上天,沒有多發性硬化症。
插圖:Alexis Beauclair 為彭博商業週刊蘇珊·哈拉的腳部疼痛開始時像針刺一樣,隨後發展成閃爍的火焰。每個月,哈拉都發現自己在不同的醫生辦公室裏,等待另一種疾病被排除在外:沒有不安腿綜合症,沒有風濕病,感謝上天,沒有多發性硬化症。
最終,挪威奧斯陸大學醫院的醫生診斷她患有小纖維神經病,這是一種由於神經錯誤放電而引起的疾病。“這讓我感覺很好,我不是在幻想什麼,”71歲的哈拉説。但找到有效的治療方法卻很難。一些藥物對疼痛沒有效果;一種通常用於癲癇的藥物讓她變得健忘,無法走直線。
彭博商業週刊印度腐爛的稻米加劇了對莫迪食品政策的不滿Bogg Bags,這種手提包的“Crocs”,如何贏得美國媽媽的青睞美國芯片引導的俄羅斯導彈擊中了6歲女孩亞當·紐曼的最新項目是WeWork的競爭對手在忍受了十多年痛苦後,哈拉同意成為一個不尋常測試的唯一受試者。一組德國科學家從她的皮膚中提取了細胞樣本,然後在一個細緻的、持續數月的過程中,將其重新編程為一種幹細胞,再轉化為神經細胞。通過微小的電擊,他們發現了一種藥物——通常用於癲癇患者——似乎能夠在細胞層面阻斷疼痛信號。在使用它的五天內,她幾乎沒有疼痛。
超越阿片類藥物
美國的羥考酮HCL和羥考酮HCL/對乙酰氨基酚處方。
數據:交響健康
哈拉的經歷説明了一種更有針對性的疼痛治療方法。在阿片危機的背景下,政治家和醫生都呼籲尋找一種替代曾用於各種疼痛的麻醉藥物。需求非常迫切:從1999年到2017年,美國約有40萬人死於阿片類藥物過量,根據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統計。國家衞生研究院去年幾乎將對阿片替代品研究的資金增加了一倍,達到11億美元,通過一個名為HEAL(幫助長期結束成癮)計劃。“如果我們能替代整個阿片藥典,我想每個人都會非常高興,”德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新成立的高級疼痛研究中心主任、神經科學教授泰德·普賴斯説。
最近在疼痛治療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最顯著的是一種新的偏頭痛藥物類別。但許多新出現的阿片替代品都失敗了,包括輝瑞公司和禮來公司試圖復興一種稱為神經生長因子抑制劑的關節炎藥物類別。輝瑞和禮來表示,他們正在分析患者試驗結果,並將與監管機構討論這些結果。瑞士製藥公司諾華公司在今年早些時候因動物試驗中的肝臟安全問題記錄了3億美元的減值,促使該公司放棄了一種有前景的治療方案。而去年底,癌症市場領導者羅氏控股公司放棄了一種旨在阻斷一種稱為Nav1.7的鈉通道的化合物,該通道在神經中傳遞疼痛信號。
新的治療方法可能需要幾十年才能開發出來,但科學家們正在逐步接近,因為一羣較小的參與者正在研究從RNA測序到改良自蝸牛毒和辣椒的解決方案。價格正在為一家初創公司提供建議,該公司正在啓動其首個旨在替代阿片類藥物以緩解即時和長期疼痛的人體試驗。另一家他共同創辦的公司正在探索一種新型實驗性癌症藥物MNK抑制劑是否能夠通過阻止神經元在刺激不再存在時仍然發送持續的“疼痛”信號來停止慢性疼痛。
第三家初創公司EicOsis是幾乎偶然研究的一個例子。它由布魯斯·哈莫克創立,他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昆蟲學教授,花費了五十年研究一種幫助昆蟲代謝其所需激素以進行變態的酶。與明尼蘇達大學獸醫麻醉和疼痛醫學副教授阿隆索·古埃德斯合作,哈莫克注意到這種對昆蟲有益的酶可能對哺乳動物有害。兩人開始測試阻斷該酶是否會對馬匹的疼痛產生影響。
突破發生在哈莫克和古埃德斯被叫到一匹名為Hulahalla的馬廄時,這是一匹血統中有賽馬皇室的4歲母馬——她的曾祖父是三冠王得主西雅圖斯流——她突然因一種稱為蹄葉炎的蹄部炎症疾病而無法行動。當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護理人員決定唯一人道的做法是安樂死Hulahalla時,古埃德斯請求嘗試他們開發的化合物。在同一天,這匹馬就恢復了行走。
 鞦韆和古德斯與Hulahalla。來源: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哈莫克説,科學界的一些人嘲笑對馬和寵物進行測試與人類相關的想法。但在一系列學術論文顯示出類似結果後,EicOsis籌集了足夠的政府撥款資金以進入人體試驗。
鞦韆和古德斯與Hulahalla。來源: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哈莫克説,科學界的一些人嘲笑對馬和寵物進行測試與人類相關的想法。但在一系列學術論文顯示出類似結果後,EicOsis籌集了足夠的政府撥款資金以進入人體試驗。
“對於我們這些在學術界的人來説,基本上沒有辦法從一個想法變成一種藥物,”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疼痛中心主任羅伯特·格雷奧説。“現在發生了很多事情。在藥物發現方面,學術界正在進行大量創新,這些創新正在轉化為小公司。”Neurolux,源於NIH資助的研究,銷售一種可以植入基因改造小鼠大腦的無線控制研究工具。裝有該設備的動物頭部有發光的紅色或藍色點,研究人員可以利用光來控制它們的神經迴路——本質上是在實驗中打開和關閉它們大腦中的疼痛通路。
長期目標是展示是否可以使用這種稱為光遺傳學的技術來緩解疼痛,格雷奧説。這意味着使用基因療法將來自不同來源(如藻類)的光敏蛋白引入大腦和脊髓的神經元。研究人員可能會利用光“入侵神經迴路並隨意控制其活動”,並阻止它們傳遞疼痛信號,格雷奧説。首先,他的實驗室必須證明該設備可以在比小鼠更大的動物身上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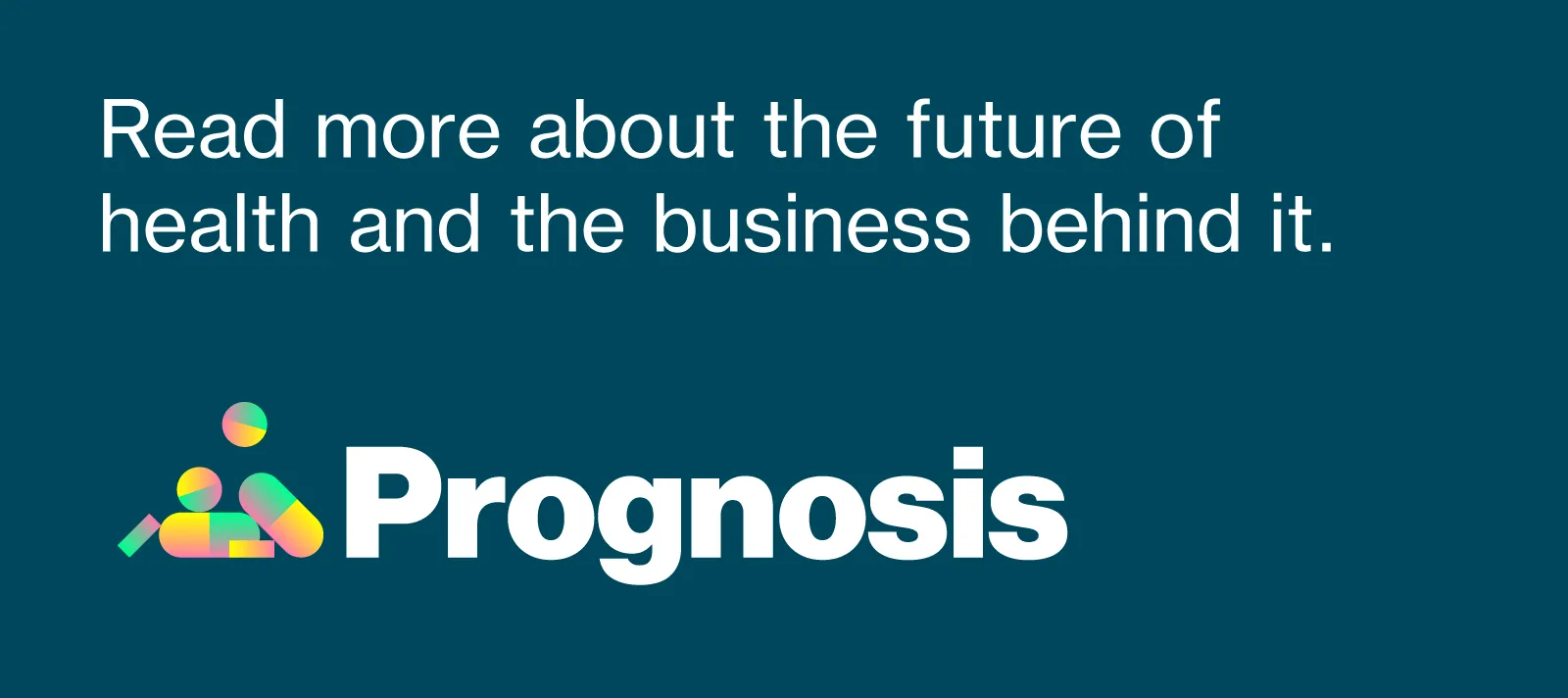 其他人正在推動在實驗室中操縱人類神經細胞的極限。這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研究:你不能從活人身上切除神經進行研究而不造成持久的損傷。在德克薩斯州,普萊斯從接受過罕見脊柱手術的癌症患者那裏獲得了一些神經細胞。其他團隊,比如幫助哈拉的德國團隊,正在培養培養皿中的神經細胞。目標是直接在人體組織上進行實驗。“疼痛是如此複雜的體驗,”德國亞琛大學的生理學教授安吉麗卡·蘭佩特説,她為哈拉找到了治療方案。她説,疼痛並不是在檢測刺激的神經元中發生的——“這實際上是在大腦中的一種體驗。”
其他人正在推動在實驗室中操縱人類神經細胞的極限。這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研究:你不能從活人身上切除神經進行研究而不造成持久的損傷。在德克薩斯州,普萊斯從接受過罕見脊柱手術的癌症患者那裏獲得了一些神經細胞。其他團隊,比如幫助哈拉的德國團隊,正在培養培養皿中的神經細胞。目標是直接在人體組織上進行實驗。“疼痛是如此複雜的體驗,”德國亞琛大學的生理學教授安吉麗卡·蘭佩特説,她為哈拉找到了治療方案。她説,疼痛並不是在檢測刺激的神經元中發生的——“這實際上是在大腦中的一種體驗。”
蘭佩特舉了一個例子,講述了一名在比賽後滿身淤青的足球運動員,卻無法記起她是如何受傷的。“當你用錘子砸到手指時,通常會感到疼痛,但在某些情況下,這並不會疼,”她説。淤青意味着感覺神經元在活動,但“因為你分心了,你的大腦關閉了來自周邊的輸入,所以你沒有感到疼痛。”
有時,奇蹟療法並不如它們看起來的那樣。蘭佩特的團隊給哈拉的藥丸是一種名為Vimpat的抗癲癇藥,由比利時製藥公司UCB SA生產。它的副作用使其作為止痛藥的前景在十多年前就被扼殺了。UCB沒有回應評論請求。儘管該藥物有效控制了哈拉的疼痛,但使她站立不穩,最終她又開始出現記憶問題。最終,哈拉決定這比疼痛更糟,在與她在奧斯陸的醫生諮詢後,她停止了服用Vimpat。她通過沿着峽灣散步和與朋友一起看電影來分散注意力。“我寧願過上我可以享受的生活,也不願意服用這些藥物,”她説。
哈拉説患者需要新的選擇,她渴望幫助研究人員找到這些選擇。目前,她通過在上牀前將腳放在浴室瓷磚上降温來緩解夜間疼痛,然後試圖在腳再次變熱之前入睡。而在糟糕的日子裏,她乾脆待在家裏。“我只是關上我的門,”她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