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為何避免停滯 - 彭博社
Richard Florida
 位於加利福尼亞州門洛帕克的家,謝爾蓋·布林和拉里·佩奇於1998年在此創辦了谷歌。保羅·薩庫馬/AP就像底特律與汽車或匹茲堡與鋼鐵一樣,硅谷與科技是同義詞。在她的新書 代碼:硅谷與美國的重塑*,*瑪格麗特·奧馬拉以歷史學家的視角審視了這個現代美國曆史上關鍵地點的矛盾。
位於加利福尼亞州門洛帕克的家,謝爾蓋·布林和拉里·佩奇於1998年在此創辦了谷歌。保羅·薩庫馬/AP就像底特律與汽車或匹茲堡與鋼鐵一樣,硅谷與科技是同義詞。在她的新書 代碼:硅谷與美國的重塑*,*瑪格麗特·奧馬拉以歷史學家的視角審視了這個現代美國曆史上關鍵地點的矛盾。
儘管它被認為是創業的熱土,奧馬拉展示了政府支出在硅谷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這些支出通過斯坦福等研究型大學進行,或作為聯邦合同分配給科技公司。她描繪了硅谷如何不斷重塑自己,創造出一個又一個前沿產業——從半導體芯片和個人電腦到生物技術、移動設備、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她追溯了它從1940年代的軍事擴張和冷戰時期的誕生,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浸潤於灣區反文化的企業家的崛起,再到現在,以及對科技的反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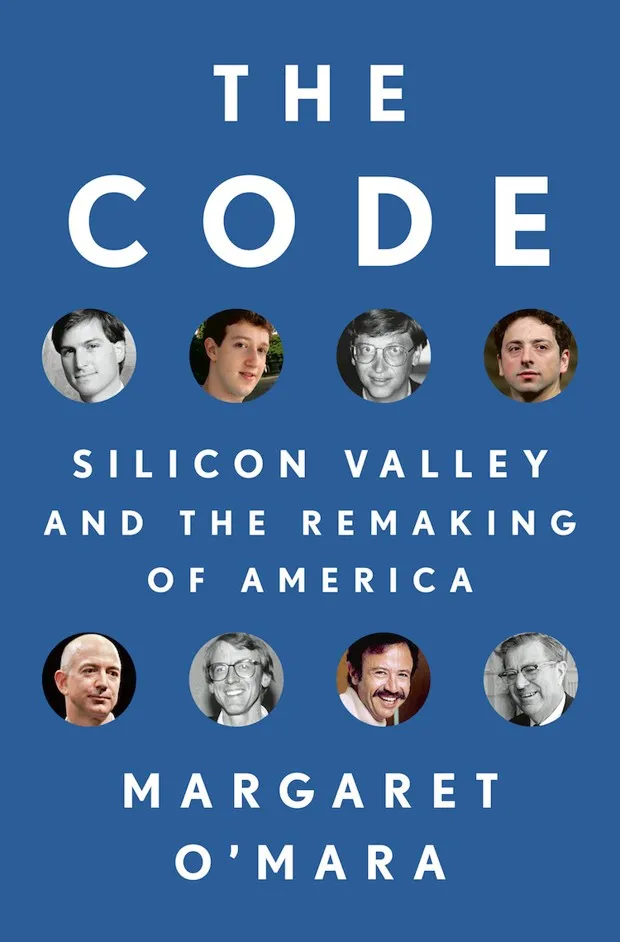 企鵝出版社奧馬拉是華盛頓大學霍華德與弗朗西斯·凱勒歷史教授,最近她與我談論了這本書。我們的對話經過了長度、清晰度和流暢度的編輯。
企鵝出版社奧馬拉是華盛頓大學霍華德與弗朗西斯·凱勒歷史教授,最近她與我談論了這本書。我們的對話經過了長度、清晰度和流暢度的編輯。
彭博社城市實驗室聖保羅的貧民窟如何幫助庇護南美洲最大的城市僅使用公共交通的跨洲競賽悉尼中央火車站現在成為建築目的地隨着住房成本高漲,民主黨人磨練YIMBY信息讓我們從頭開始:硅谷是如何形成的?
硅谷真正的轉折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如果你回到1920年代,那時的聖克拉拉谷是加利福尼亞的一個農業谷,以全國梅乾生產的首都而聞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其後,這股與軍事相關的政府支出浪潮開始席捲太平洋沿岸,直接投資於技術和科學。這是軍事工業綜合體的一部分。
推動這一切的動力是大政府。這並不是總統説:“我們將在北加州建立一個科學城市”,許多世界領導人隨後宣稱過。是通過斯坦福大學、伯克利大學等大學以及洛克希德等私營企業和國防承包商進行的大規模政府支出。
你寫道:“整個企業建立在鉅額政府投資的基礎上……從太空時代的國防合同到大學研究撥款,再到公立學校、道路和税制。”這不僅僅是大政府,還有與之相結合的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創業引擎和大學。
有些事情只有政府才能做。這是投資於藍天研究,而不僅僅是軍事、五角大樓的支出。這也是太空競賽——NASA。在太平洋西岸,你會發現這些國防中心,比如西雅圖和洛杉磯的航空航天。
硅谷專注於為軍事和太空競賽提供小型電子產品。費爾柴爾德半導體是風險投資支持的初創公司的祖父;它的大部分業務來自政府合同,來自NASA的微芯片技術。當政府購買東西時,它促進了生產規模的擴大,並降低了私營部門的價格。因此,政府成為了市場的推動者。
大學對高科技產業的重要性一般如何,斯坦福大學對硅谷的重要性又如何?
人們往往忽視斯坦福的獨特性。首先,作為一所私立大學,它能夠完全重塑自己,並取消某些部門——這是公立大學無法或不應做到的——其次,它自1950年代以來的令人難以置信、極具創業精神的做法。態度是:“我們將與行業合作,我們將建立培訓你所需的那種人的實驗室。”這並不一定是每個高等教育機構都想要追求的目標,但這是一個關鍵部分。
弗雷德裏克·特曼是1950年代建立斯坦福工程項目的院長。他在帕洛阿爾託長大,是斯坦福教職員工的兒子。他去麻省理工學院讀研究生,並與冷戰科學和技術政策的設計者合作。他在1940年代寫信給一位同事,説:我們有一個時刻,斯坦福可以成為像哈佛或麻省理工學院那樣具有重要意義的世界級大學。
風險投資怎麼樣?
硅谷早期的風險投資是舊經濟與新經濟交織的絕佳例子。它的現代化身是由像 喬治·多里奧 這樣的哈佛商學院教授創造的——他在40年代與一羣波士頓的富裕銀行家合作,籌集資金投資於這些從大學基礎研究中嶄露頭角的年輕科學公司。硅谷的版本則是由管理舊家族財富的年輕人啓動的。同時,政府也通過小企業投資公司提供幫助,這個奇怪的小創意源於1958年的小企業法案。它成為一個極其慷慨的工具。
然後是朋友之間互相幫助的網絡,讓彼此能夠接觸到這些資本來源。硅谷的原始風險投資者之一,瑞德·丹尼斯,告訴我,在早期,這實際上就像在桶裏打魚,機會實在是太多了。
 瑪格麗特·奧馬拉吉姆·加納那麼,許多風險投資者來自成功的公司,並從企業家和技術專家轉變為投資者嗎?
瑪格麗特·奧馬拉吉姆·加納那麼,許多風險投資者來自成功的公司,並從企業家和技術專家轉變為投資者嗎?
這建立了一種模式,直到今天仍在繼續。他們開始挑選下一代的贏家,並將他們的管理經驗帶入下一代。這對於理解硅谷的再生至關重要,它能夠從一種技術轉向另一種技術。但這也有助於理解一個盲點——在公司目標、什麼是優秀的科技企業家、創始人應該是什麼樣子等方面的視野狹窄。這些盲點近年來已成為硅谷的重大負擔。
安娜莉·薩克斯尼安的書中核心理論區域優勢是硅谷與匹茲堡和底特律等老工業地區的不同。這些地區被鎖定在某種技術和產業中,無法超越。而硅谷則非常獨特,它在技術之間跳躍。
這些不同代的技術看似彼此獨立,但它們是相互構建的。你有微芯片,它產生了微處理器,然後是計算機芯片,這使得個人計算機成為可能。硅谷感覺像是被位於西雅圖的微軟吞噬,但就在關鍵時刻,互聯網出現了。互聯網再次發揮了硅谷的優勢,以及自始至終所做的事情:製造非常小的電子和通信設備。這些核心競爭力實際上是所有這些連續技術代的核心。
[硅谷]遠離金融和政治的中心。我稱之為“創業加拉帕戈斯”——這是一種跨代的風險投資家、律師事務所、投資公司和營銷公司的網絡。
你指出,硅谷與更廣泛的流行文化一起發展,從1950年代的乾淨利落的軍人類型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嬉皮士和反文化類型。
第一代人非常注重短髮、白襯衫和窄領帶;他們對正式政治並不特別感興趣。下一代是反文化,但有一個前提。他們參與了伯克利和斯坦福的反戰抗議。他們想要推動社會變革,計算機是工具。一旦每個人都有了計算機,我們就會糾正所有的不公正。
這種強烈的技術樂觀主義將所有世代聯繫在一起。他們共同相信,技術將成為我們改善世界的一種手段。政治和社會運動的複雜性與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是正交的。我們現在發現,這些技術工具實際上加劇了其創造者希望消除的一些社會分裂。
“這種強烈的技術樂觀主義將所有世代聯繫在一起。他們共同相信,技術將成為我們改善世界的一種手段。”西雅圖產生了一些最大的和最重要的科技公司——微軟和亞馬遜,更不用説波音了。作為一個高科技中心,它適合什麼呢?
在經濟上,西雅圖一直是一個比硅谷更傾向於大公司的城市,經濟的繼承由單一行業或公司主導和定義:波音,然後是微軟,現在是亞馬遜。波音的工程能力仍然是經濟中的一個重要因素。西雅圖也是每個大型科技公司的大型分支機構以及許多小型和中型初創公司的所在地。大約四分之一的這些初創公司是由微軟的校友創辦的。西雅圖的科技生態系統比硅谷年輕。但硅谷和西雅圖之間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相互聯繫。微軟的一些早期風險投資來自硅谷。亞馬遜也從硅谷獲得了相當一部分早期資金。傑夫·貝索斯本人也在谷歌早期投資了股份。
我們一直在追蹤的一個趨勢是高科技從郊區的極客地帶轉移到像舊金山和紐約這樣的城市中心。這説明了硅谷什麼呢?
我的第一本書 [知識之城,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於2005年出版] 完全是關於郊區的高科技。看到過去幾十年發生的事情真是一段旅程。這是一種部分社會學和部分技術現象。
[有] 更廣泛的迴歸城市:城市是富裕年輕人的地方,他們可以住在任何他們想住的地方。在1960年代,工程師們的部分吸引力是購買位於帕洛阿爾託和門洛帕克的漂亮牧場房屋。而這並不是25歲的人現在想做的事情。這是城市復興和這些真正充滿活力、令人興奮的城市社區崛起的一部分。需要招募和留住最佳人才的公司;如果你在一個酷炫的城市、酷炫的社區有一個酷炫的空間,那就是一種優勢。
但對我來説,另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創業與1999年或2000年時的不同。那時,你必須在一個辦公園區租用空間,並用隔間和服務器室填滿它。所有這些都是前期資本成本。在像紐約這樣的地方,你永遠無法獲得規模的商業房地產。現在,你可以在雲端獲取計算能力和存儲數據。你的創業公司可以是一個高性能的筆記本電腦和布魯克林的一家咖啡店,你可以成長為一個WeWork空間。現在你可以負擔得起在紐約、舊金山或西雅圖的酷炫社區,因為你的佔地面積更小。
這對其他城市意味着什麼?
地理從來不是靜態的。底特律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是世界上最具創新性的城市。沒有哪個地區的輝煌歲月會永恆。當我與20多歲和30多歲的人交談時,他們對最大科技公司的主導地位有很多質疑。我認為他們也關心生活質量:我是否願意將我的生活交給這個?
這並不是所有人;仍然有很多人湧向硅谷。但我認為,隨着科技作為一個行業的發展,或許“其他”地區有了更多的空間,這在幾十年前可能並不存在。當新興科技中心從這些高房價市場中退潮時,這一切可能會改變。總有一天會出現崩潰:這是一個過山車般的行業。
在我大部分的生活中,科技樂觀主義佔主導地位。現在出現了反彈。這發生得非常快。
五年前我開始寫這本書時,從硅谷到華盛頓特區,每個人都在不帶諷刺地談論科技如何改變世界。而現在,氣氛發生瞭如此戲劇性的轉變。氣氛如此陰鬱,以至於我發現自己有些抗議:“我們口袋裏有超級計算機。讓我們欣賞一些好東西。”
現實在中間。我們不應該成為硅谷的啦啦隊員,也不應該將其完全摧毀。在這些城市也是如此。人們會停止想要住在舊金山或西雅圖嗎?我不這麼認為。它們是不錯的地方;它們提供許多其他地方無法提供的東西,這不會就這樣消失。你如何找到一些平衡?
像舊金山這樣的城市的魅力部分來自於它的獨特性,那些不屬於超級富裕科技世界的人。你如何保持這一點?你如何保持城市的質感和那些讓城市如此偉大的東西?坦率地説,我認為科技在這些城市中是很好的,從密度和可持續性的角度來看。讓我們想想如何開放它,並且共存。
舊金山和西雅圖有慢性問題,這些問題已經惡化。它們已經有了嚴重的交通問題。它們有嚴重的住房負擔能力問題。而現在,科技的快速增長使所有這些問題變得更糟。但並不是説科技最初造成了這些問題。
如果HQ2的搜索達成了什麼,那就是明確了對科技的反彈,以及對我們——“我們”指的是地方政府——將做多少努力來吸引這些公司的質疑,這樣做是否有益。答案介於數十億美元的税收減免和“別打擾我”的之間。
答案是找到某種方式共同合作並向前推進。科技公司,尤其是大型公司,需要認識到它們的公民責任。説“比爾·蓋茨應該給一億美元來解決這個或那個問題”是很簡單的。但政府將需要對個人和公司徵税。經過數十年的緊縮,結果是一個非常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系統,這並不令人驚訝。
“説‘比爾·蓋茨應該給一億美元來解決這個或那個問題’是很簡單的。但政府將需要對個人和公司徵税。”硅谷在性別和種族方面的多樣性並不多。這是根深蒂固的,還是有跡象表明它可能正在改變?
這是根深蒂固的,同時也在改變。在50年代和60年代,許多重要人物和投資者都去了哈佛商學院,但當時女性並未被錄取。女性也不被允許主修化學或工程。
[有]緊密聯繫的商業網絡——人們僱傭他們認識的人。努力工作與玩樂的強烈倫理從一開始就是硅谷科技的標誌。他們下班後一起去喝酒。這變成了一個非常男性主導的世界。在此之上,還有這種毫不掩飾的批評的極具競爭性的氛圍。
毫不奇怪,能夠忍受的女性寥寥無幾。她們中的許多人只是説:“我不想忍受這些廢話,”然後她們就離開了。1960年代的廣告狂人時代的美國企業被困在琥珀中。
但我確實看到事情在改變,原因如下。因為如果上一代的贏家在挑選下一代的贏家,我們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女性。她們現在有資源並且彼此建立了網絡;她們正在創造自己的團體版本。是的,這可能會有自己的偏見和排斥。但我對硅谷在過去幾年中談論多樣性或缺乏多樣性的方式感到振奮,這是以前從未談論過的。
科技作為一種精英制度的整體觀念受到了某種程度的打擊,正如它應該的那樣,因為它並不是一種精英制度。科技越來越成為來自中上層階級背景的人的領域,他們不僅能夠進入斯坦福或麻省理工學院的精英項目,還能夠自籌資金創辦初創公司,因為也許他們的父母在幫助資助。我們在慶祝企業家時並沒有足夠談論這一點。這並不是説你不應該慶祝企業家精神,並鼓勵人們實現他們的創新夢想。但你必須認識到,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輕鬆做到這一點。社會可以通過哪些方式來幫助鼓勵和識別偏見的存在?
中國、歐洲及其他地方科技中心的快速崛起是否對美國在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構成威脅?
硅谷成功的關鍵在於美國的移民政策。1965年的移民改革為這一波令人難以置信的新美國人打開了大門,包括那些來到硅谷並以不成比例的數量創辦公司的人員。人員和資本的自由流動是美國做得比其他地方更好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麼世界各地的“硅谷某某”沒有完全達到最初的成就。
這並不是説美國是唯一的,其他地方就無關緊要。硅谷是一個全球網絡。我們是全球科技經濟的一部分。美國科技經濟之所以如此重要,部分原因在於它與世界各地的市場、技術人員和科技中心相連。關閉大門並説:“我們是第一,我們對其他地方的貢獻不感興趣,”實際上是自我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