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視頻時代:我們分享着每個人的自戀_風聞
海螺社区-译介传播思想、文化、艺术动态2019-01-14 19:43
王雨童|作者
在抖音上呆十分鐘,你會覺得自己在千星之城中穿梭。上一個視頻還在為青藏線上的卡車司機遇難而唏噓,手指一劃,下一個視頻中韓國天團聲光雪亮。世界的數量一如佛教所述,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眩迷效果也不逞多讓:用户在每個15秒的短視頻中迅速沉浸再迅速抽離,週而復始。刻意抹掉了時間顯示的應用界面讓每個人都體驗着“此間樂不思蜀”,只有在年底APP彈出用户年度報告的時候才會發出驚呼:我竟然在這上面花了那麼長時間?!短視頻讓人上癮,2016年上線、2017年躥紅並牢牢佔據着短視頻界C位的抖音是典型但不孤立,快手、美拍、火山、西瓜、梨視頻、秒拍、小咖秀、微視在手機應用商店的列表裏擠作一團,幾億下載量似乎不言自明地自賦了合法性:“這是一個短視頻的時代”。
短視頻app大集合
一、美好生活的幻想鄉
加拿大傳播學家馬歇爾·麥克盧漢那句著名的“媒介即訊息”流行或説訛傳了幾十年,卻始終常用常新:媒介的固有屬性會對受眾的感知產生影響,繼而改變媒介所承載的內容本身。短視頻應用也是如此,幾秒到十幾秒的短暫時光、海量的視頻數量和炫目的視頻效果,已經決定了內容的新奇、膚淺、情緒化和娛樂至死。根據秒針與海馬雲大數據的《2018抖音研究報告》,頭部視頻(流量最大)內容上,美好生活類佔40%,在互動量上遠大於其餘類別。“美好生活”專指“生活裏的小確幸”,包含美食美景、萌寵萌娃、時尚美妝、生活記錄和“高顏值小哥哥小姐姐”。其中,“小哥哥”“小姐姐”是對長相姣好而沒有專業演藝經驗(也就是“素人”)的年輕主播的愛稱,相比較“網紅”這一稱呼中攜帶的性成熟意味,“小哥哥”“小姐姐”更符合年輕羣體審美上的幼化和去性化傾向,也意味着更容易產生社交關係。要成為收割流量的“小姐姐”,必須擁有鮮明而一定程度超越日常的人設,無論是古風、洛麗塔還是歐美風。以古風播主為例,寬袍大袖的古裝和精心打理的妝容和髮型是必要元素,有人伴隨古風歌曲起舞,有人重現着古裝劇裏的劇情,有人選擇古典院落、園林或是山水作背景來完成自我景觀化。在抖音官方創立並推廣的“#原創國風計劃”標籤下,數量繁多的視頻已經有4.5億次總播放量,足見其擁有廣泛的受眾。“古風”或“國風”已經很難再用亞文化來概括了,也很難如其愛好者所願那樣保持純粹和界限分明,美國文化研究學者迪克·赫伯迪格認為,亞文化被主流文化收編的過程中消費主義是重要動力,它將本來具有邊緣性和圈層標識功能的亞文化符號迅速收編和改造為主流文化中可販賣的元素,同時也召喚了更大多數的青少年參與自我形象的塑造。“國風”之“風”這個構詞上仿擬“和風”的詞指的是“像……的方式”,本身就有模擬、表演、仿造之意,據此超離日常生活的邏輯。藉由扮演,抖音成了一塊轉移、變形和釋放現實慾望的“飛地”,“小哥哥”“小姐姐”和他們百萬千萬的粉絲也以此定義網絡空間。
抖音上的古風小姐姐們
幻想鄉的造夢工具充分,短視頻應用為古風愛好者提供了得心應手的表演環境:單人就能拍攝,強大的美顏和濾鏡,特效營造亦真亦幻的效果,豐富的音樂庫。古風“小姐姐”們鍾愛伴隨古風樂曲起舞,然而中國古典舞並不是首選,由抖音用户獨創的手勢舞才是最主流的舞蹈。這種舞蹈用手指和手臂擺出簡單的造型,簡單易學無難度。手勢舞滿足了抖音短視頻對模仿和傳播的要求,也讓成為“國風美少年/少女”的門檻低到稍微抬抬腿就能跨過去,攔住你奇妙變身的唯一門檻便是服飾本身。一套衣服的曝光壽命只有15秒,因為唱跳的高度同質,如果不及時更換形象,觀眾很容易就感到厭倦。反之,美顏和濾鏡打造出的仙境也是最好的導購廣告,擁有流量的播主可以將淘寶鏈接直接放在視頻界面,一鍵直達同款美夢。然而對於佔抖音用户85%的90後來説,一套中等價位的淘寶漢服也要四百元,據調查漢服愛好者平均擁有2-3套漢服,“小姐姐”不僅意味顏值吸引力,更意味着裝滿小裙子的衣櫃。短視頻為用户營造出的唯一的夢境就是消費主義營造出的匱乏和渴望。
二、新玩法與舊規則
儘管短視頻在一個個瞬間的夢幻泡影中製造了前所未有的傳播現象,但在其他方面上,它仍然分享着許多傳統媒介古老甚至陳舊的秩序。比如,短視頻應用紛紛加強音樂功能,但這並沒有掀起一場聲音對畫面的介質革命。視覺依舊在“美色享受”上佔盡優勢,“古風小哥哥/小姐姐”中有一類是古風音樂的演唱者,他們的音樂被廣泛使用,但本人仍要靠顏值吸引粉絲。以擁有百萬粉絲的古風歌手“楊小揚”為例,符合鮮肉審美的外表、精心修飾的古裝打扮讓他迅速成為“小哥哥”中的翹楚,而資歷更老、作品更多的古風歌手卻因為沒有露臉視頻而粉絲數量稀少。
除了視覺中心主義外,“技術中立”和“去中心化”可能是短視頻應用更大也更美好的謊言。抖音、內涵段子、火山視頻等一系列“頭條系”短視頻的創始人張一鳴曾宣稱:“(今日頭條APP)沒有編輯團隊,不進行人工干預,全靠算法學習進行個性化的機器推薦,也不進行內容的加工生產,只做內容分發”,“頭條系”短視頻共享同樣的算法推薦系統,核心就是通過數字統計將馬太效應發揮到極致。當一個新視頻被上傳後,系統會根據播主標籤、視頻內容標籤和社交關係等參數開始第一輪推薦,點贊、轉發、評論等數據高的視頻有機會獲得第二輪、第三輪的流量推薦,因此紅火的唯一要素是尋找最大的公約數,在每一輪推薦中獲得足夠的數據。如張一鳴所述,短視頻平台並不對內容做任何加工,也沒有精品推薦機制,最核心的評價機制就是“數量”,被更多的人看到,獲得更多的粉絲、點贊、轉發和評論。這必然會要求大量模擬而非原創作品的出現,而每個內容原創者都儘量讓自己的作品簡單易學,每一個“抖音爆款”無論是《我們一起學貓叫》等神曲還是一款又一款的手勢舞,背後都是平台算法機制在無形地加以牽引誘導。在文化層面上,抖音爆款構成了理查德·道金斯所説的“迷因”(meme)傳播現象,以模仿和複製的方式大量傳遞文化符碼,然而背後的機制不再只是共有的隱秘社會心理,也不訴諸於時代精神、民族意識或是區域結構等經典文化流行的解釋因素,有的只是循環性強的簡單旋律在算法加持下的無限放大。以古風音樂為例,《牽絲戲》或《典獄司》等歌曲還能以質量較高、知名歌手創作、《盜墓筆記》同人音樂等原因解釋其爆款,《我的將軍啊》《生僻字》《琵琶行》等更多的音樂則很難辨識出其在同類音樂中脱穎而出的品質。在短視頻中,“傳播”變成了同內容無關,同受眾也未必有關的奇異過程,“傳播”本身被工具化,被降格為僅是技術手段,這是短視頻造夢的悄悄掩蓋起最糟糕的現實。

“你越喜歡我越可愛”,短視頻的算法推薦原則就這麼矛盾,也因此清晰地暴露出現實邏輯的赤裸河牀:如果不服從關於“造夢”的既有規則,如果不提供本質上是熟悉、温馨、安全、舒適的體驗,你就無法獲得臣服後被獎賞的快感。49.1%的抖音頭部內容發佈者是非明星或機構的普通人,區分他們與千餘粉絲的普通用户的並不是內容質量,而是一套歸順、習得與獎勵的狹窄規則,和被大數據之神眷顧的運氣。
三、獨角戲不散場
當美國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在1956年的《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中提出**“擬劇”論,用戲劇表演的原理來闡釋人的社會行為時,理論試圖關照的社會生活是由大量直接、穩定而緊密聯繫的羣體構成的,因此他在書中提出“戲班”作為羣體契約性表演的概念。**而今天,當年輕的抖音用户無視周圍環境,凝視着手機的前置自拍鏡頭,扮演着《牽絲戲》裏的美優伶或是《盜將行》裏的江湖大盜時,他們在對誰表演,又在表演着什麼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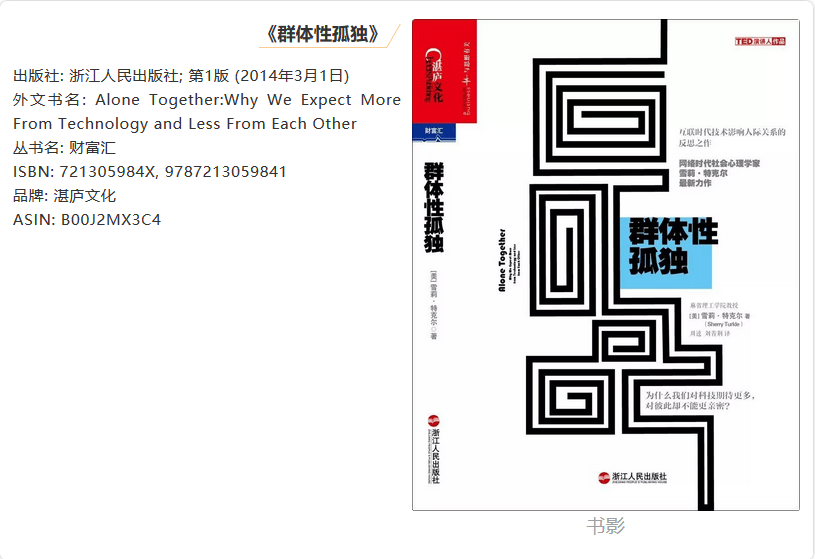
在此,雅克·拉康對主體的認知前所未有地適合這個時代:如果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主體建立在父親、兒子、母親和其他女性這四個角色上,則拉康的主體從頭到尾都只有主體和鏡子,絕對孤獨的主體通過鏡子的種種誤認建立與世界的幻覺,一切錯認、安慰、治癒或者失落都是獨角戲。前置鏡頭有如一面單面鏡,觀眾藏在鏡後當着舒適的窺視狂,播主則在明知鏡後有人的情況下怡然欣快地展示着自我的自戀。即使早在1979年克里斯多夫·拉斯奇就宣稱資本主義社會進入了“自戀主義時代”,機器作為中介參與自戀文化仍是新現象。已經有研究證明,媒介放大了這種自戀。在《羣體性孤獨》中,雪莉·特克爾認為青少年有意識在社交軟件上塑造虛假的自我形象並不應該僅僅指責個人,而是在媒介無意識餵養下形成的自戀慣習:“在傳統的精神分析中,人們説自戀時並不是指那些愛自己的人,而是指脆弱的個性……自戀者僅以量身定做的表達來與別人交往。這些表達是脆弱的自我所能處理的一切。我們很容易想象無生命力的夥伴能夠起到這樣的作用,是因為一個機器人或計算機中介程序可以調整好以便滿足人的需求。但是一個脆弱的人也可以通過選擇性和限制性的與人接觸,從而獲得支持(也就是通訊錄中最受歡迎的人)。”短視頻平台算法的“智能學習”通過喜歡/拒絕的指令貼合用户的口味,它在越來越精準地推送出用户喜歡的視頻的時候,將人不知不覺變得眼裏只有自己的舒適小天地。因此,比起憤怒於“媽媽死了小女孩在抖音上要求一萬個贊”類似新聞,理解並警惕新媒介越發平滑無際的運作機制更有意義:媒介形成迴音壁,自戀便是他們與“世界”建立起聯繫的情感方式。

2013年,牛津詞典編輯部把年度熱詞頒給了**“selfie”(自拍)**,“自我”迅速佔據了取景框乃至人類意識的中心。尚不足十年,“自拍”在人類自我展示的技術中地位搖搖欲墜,美顏相機甚至是短視頻後來居上,PS、濾鏡、一鍵美顏、貼紙、配樂等修飾地位直線上升,真實呈現“我”這個主體的形象並不重要,按照大數據精確總結歸納出的樣板來塑造出一個表演中的主體才真正重要。人與機器的關係早就取代了人與人的關係,更切近的是人對人的慾望也消失,被人對機器的慾望所替代。短視頻用户在盡力扮演想象中的古代生活,這完全不意味着他們想回到古代生活,也不意味着他們不知道古代生活並不浪漫,他們只想對着機器扮演一種不同於現實的生活,享受古裝、音樂和濾鏡共同營造的快樂,儘管這種快樂早已在破口欲出之際碎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