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思想史在當代中國的重要性_風聞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特聘教授2019-01-30 13:36
我想了很久,覺得這次的內容,應該把思想史研究的過去、我們現在對思想史的思考,以及當下我們學術界的思想史研究狀況融入進去。也就是説,既想把我們研究的古代思想史和對當代中國思想的一些想法結合起來,又想把學院的思想史研究和我們對當代中國的一些觀察結合起來。所以,我選擇的題目是“為何思想史在當代中國仍然如此重要”。這幾年,我每年都去普林斯頓大學做訪問教授,訪問教授有一個規定的工作,就是做一個公開演講,二〇一〇年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第一次公開演講講的就是這個題目。
那麼,為什麼我要反覆強調思想史的重要性呢?
思想史在中國為何很重要
現在西方學界,思想史研究並不是熱門,中國思想史研究更不是熱門。我的朋友黃進興院士,現在擔任台灣“史語所”所長,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傳給我,談到思想史在西方學界的衰落,在文章開頭他引用保羅·康克林(Paul K. Conkin)的話説“思想史曾有短暫的輝煌,眼前卻是四面楚歌,而前景黯淡無光”,在文章的最後他又用了朝鮮戰爭時期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的名言“老兵不死,只是逐漸凋零”(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來形容現在思想史研究的狀況。
可是很有趣的是,這也許是西方思想史研究的狀況。中國大陸學界卻相反,思想史研究一直是熱門,而且近幾十年更熱。作為五四一代知識界領袖人物的胡適,最初的著作是《中國哲學史》,但後來他堅持改稱為《中國思想史》,而且也編寫了好幾次《中古思想史》的提綱和講義;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李澤厚寫了《美的歷程》,這本書其實並不只是談藝術的,而是講思想文化的,所以,馮友蘭先生曾經稱讚“這是一部文化史”。李澤厚還在思想史研究領域寫過三本書《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國現代思想史論》,這些著作曾經是“文化熱”的重要歷史資源。
他在裏面提了很多對後來有影響的説法,比如什麼是“孔顏樂處”、什麼是文化心理積澱等,這些都是思想史領域裏的話題。後來,在中國文化、社會、政治領域產生了很多新話題的著作,也都與思想史有關,比如余英時先生有關“士”或者“知識人”的思想史著作,比如我自己寫的《中國思想史》。出乎意料的是,我的這本書出版了十幾年,現在仍然在不斷地再版,印數累計已經到了七八萬冊,這樣的現象是很超乎尋常的。在當代中國,連原本是文學和哲學的研究者,不少也轉向思想史,甚至有人覺得,現在的“思想史熱”已經造成了中國“學術格局的失衡”。
並不是因為我做思想史研究,就在這裏老王賣瓜自賣自誇,説中國的思想史研究很熱。其實,只要瞭解中國當代思想和學術的人都知道,近十幾、二十年中,思想史研究尤其是中國思想史研究,在中國大陸的影響不止在思想史學科內,而且影響到學科外;不僅刺激了有關“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討論,而且促進了歷史學科其他領域研究方法的轉變,甚至引起了對文學史、藝術史、政治史等學科的反思。特別是,它還引發了對當下中國思想、政治和文化的重新省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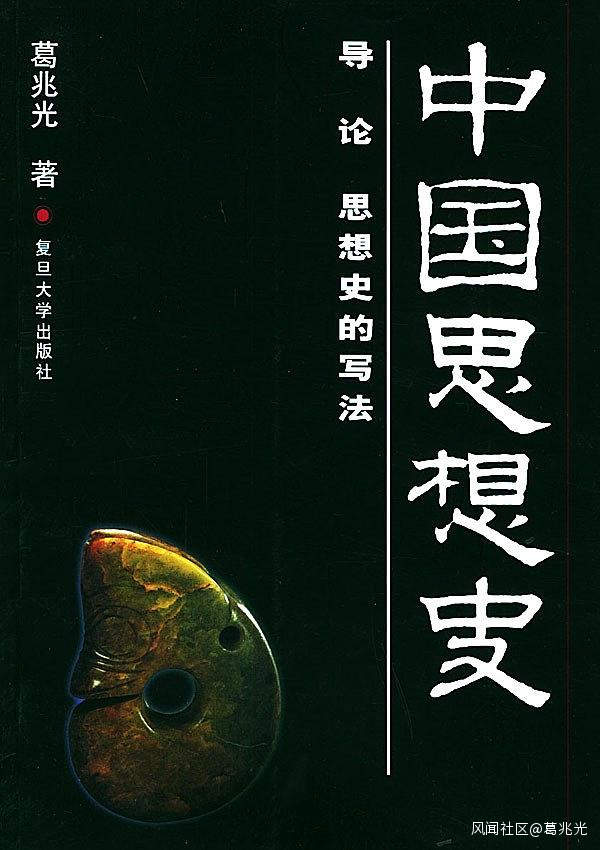
那麼,為什麼偏偏是思想史研究在當代中國起了這麼大的作用?為什麼思想史研究在當代中國受到這樣多的關注?我想,有三個關鍵詞一定要注意,那就是在中國人文學者心目中始終處在很核心位置的歷史、思想和政治。
首先是“歷史”。因為中國有長久的歷史傳統,所謂“國可亡,史不可亡”,反過來説“欲亡其國,先亡其史”,就是説,“歷史”是民族或國家的認同基礎。從古代中國的“有史為證”,到現代中國的“歷史經驗值得注意”,什麼事情都先要參考“歷史經驗”,後要有個“歷史結論”。昨天我看《華盛頓郵報》的網絡版,説中國某學者要討論當代國際關係,拉上了儒家,特別是荀子,要從荀子那裏找討論國際關係的靈感和資源。當然,歷史在各個國家都很重要,比如我們看到很多波及國際或國內的學術爭論和政治爭論,都集中在歷史教科書上。例如日本、韓國的歷史教科書,以及前幾年俄羅斯不斷重修的歷史教科書等等。
其次是“思想”。思想也很重要,過去中國人愛講“本末”“道術”“道器”,如果不講“道”,不講“體”,一切都不算數,都是枝梢末節。我一直覺得,現在中國仍然在“未完成的現代過程”之中,仍然是在晚清、五四那個從“技術”到“制度”、從“制度”到“文化”、從“文化”到“思想”不斷尋求變革的歷史延長線上,那些重要的價值像民主、自由、科學、公平、正義等,始終需要在觀念層面得到確認,並且在制度層面加以落實。
所以這是“道”,中國人講“道”是最根本的,雖然現在也像莊子説的那樣“道術將為天下裂”,可是,中國人還是要尋找根本的“道”。“道”是什麼?就是思想。思想是管一切的硬道理。胡適在六十歲的時候接受採訪,他回答記者説,他並不想直接從政,因為“思想文化的途徑有其巨大的力量,有其深遠的影響”。林毓生教授曾經説過一個現象,“中國習慣於最終在思想文化層面來解決問題”。比如剛才説的,晚清在面對西潮的時候,最開始學技術,就是堅船利炮,認為我們只要師洋人之長技就可以制洋人;可是後來這樣行不通,就引進制度,成立了總理衙門來處理外交及法律事務,再後來又廢除科舉,結果還是不行;最後就上升為“道”和“體”,在思想文化層面來解決問題。
所以,中國有這樣的一個歷史傳統。中國的文人士大夫,如果能進“文苑傳”,被歷史銘記,當然是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就算入了“文苑傳”,也只是個文人,一為文人便無足取。所以,更進一步最好能進“史林”,能被承認是個史家,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比較了不起;可就算入了“史林傳”,也大不了是個寫歷史的,司馬遷就説自己是被“俳優視之”。所以,理想的是入“儒林傳”,成為一個儒者,能夠“致君堯舜上”;可是,進入了“儒林傳”也還是不夠的,最頂級的是能入“道學傳”。“道學傳”裏面的人都是講“道理”的,就像宋代趙普講的,“道理最大”。
“政治”也特別重要。中國自古以來政治權力高於一切,政治上的“國是”可以籠罩和改變經濟制度、社會風貌、文化趨向和日常生活,不過,政治不易討論,所以看起來是説“過去故事”的思想史研究,其實往往就是在對古代的檢討中,讓某些現代價值獲得歷史合理性,從而改變政治。
正像梁啓超《新民説》所説的,思想常與政治變化有關,而政治變化又必以思想為基礎。之所以要討論思想史,就在於思想和政治、歷史和現在關聯得太深了。在中國這種歷史傳統很深的國家,在中國需要思想指引的時代,“讓歷史歸零”是不可能的,“把政治忘掉”也是不可能的,怎麼辦?仍然是林毓生教授説的,“借思想文化來解決問題”。
而且,大家都明白,中國是一個政治意識形態影響很大的國家,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現代。當“政治”不能被直接談論時,就剩下兩個詞“歷史”和“思想”,而歷史和思想結合在一起,就是思想史。那被遮蔽而不能討論的“政治”怎麼辦呢?於是,思想史就通過思想和歷史曲裏拐彎地討論着政治,這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當我們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我們能非常清楚地體會到思想史討論背後往往有它的當代關懷。所有的學術研究,我以為只有當它與政治,也就是學者對當下的關懷,有聯繫時,它才會產生較大的影響。
在這一點上,中國和海外是不一樣的。我們在和歐洲、美國、日本同行一起討論的時候,經常可以發現這種不同。記得有一次在日本,我和日本思想史學會的幾個著名學者討論了五個小時,他們始終不能明白一個問題:為什麼思想史在中國能這麼火,思想史著作能賣到幾萬本。
而日本的思想史著作在日本如果能賣到三千本就了不起了。我的一個朋友,他是日本東京大學的教授,也是日本思想史學會的會長,他反覆問我這個問題。我就説,以我的猜測,日本思想史研究在日本,和公眾的當下關懷及政治問題有點兒脱節,因此成為純粹專業性的學院研究,這樣就很難激起社會反響,這一點和中國的情況是不同的。
所以,我特別要提醒的是,在中國,專業學者、自由文人、知識分子、論政者之間,很難有清晰的界限,對文化、學術和思想的歷史清理,背後常常有現實的政治目的和批判意圖,人們希望從歷史中尋找現實的批判資源、認同基礎和價值觀念。所以,歷史學在人文學科裏面一直很重要,也很敏感。這些年來中國的變化太劇烈,屬“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至今還在變局之中。
以前説“天不變,道亦不變”,現在天翻地覆,“道”就得“變”了。“道”就是思想,思想應當向什麼地方變?這是知識分子特別想知道和討論的。所謂五四時代“借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方法”,或者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藉助歷史批判現實的傳統”,始終是知識界的習慣。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才能明白,在中國,“學術”不僅僅是“專業”的或“知識”的領域,常常也是一種思想批判和政治表達,“文化”“學術”“思想”的研究領域,都是如此。
因此,思想史研究在中國很重要,它的興起和興盛,就需要在這一傳統和背景下觀察。
思想史為何在當下中國仍很重要
剛才我們説思想史為什麼很重要,現在我們要説思想史為什麼在當下中國仍然很重要。道理很簡單,是因為在中國,思想與文化的延續性很強,當下的很多思想問題,都可以追溯到歷史。
那麼,為什麼中國歷史、思想、文化的延續性如此之強呢?我想有三個原因:
第一,聖賢和經典的權威。在很早以前,聖賢和經典的權威就被確立了起來,而且它們與政治彼此融洽,保證各自的權威。我們現在説經典或者儒家經典,在兩千多年以前,甚至在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前,就已經有了“經”的説法。董仲舒把儒家經典從一種學説變成了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從皇帝到民眾都必須接受的政治意識形態。由於得到了政治權力的支持,因此兩千多年以來儒家經典一直都在影響着我們的生活、指導着我們的觀念,而且也形塑了中國依賴經典權威和思想慣性來解決問題的傳統。第二,藉助考試製度。
任何東西都沒有教科書厲害,教科書是最有力量、最影響思想和觀念的東西,特別是當它與每個人的利益相關時。能否通過考試,決定了你能否通過這一途徑流動到社會上一階層。讀書人要通過考這些知識的科舉來進入上層,所以大家都依賴和擁護儒家經典。舉一個例子,在古代朝鮮,只有兩班知識分子有資格參加科舉,因此他們捍衞儒家學説尤其是程朱理學的意念和決心比中國人還要強烈。
大家覺得朝鮮文人很固執,但這不是由於他們的性格,是因為兩班壟斷了科舉考試的資源和權利,通過這些知識可以流動到上層階級,所以他們當然要維護;在日本通過學習儒學和經典沒有辦法升遷,日本沒有科舉制度;而中國的大部分知識分子還是要通過這些知識的考試來進入上層的,所以他們也當然會非常維護這些知識。
第三,一直以來,我們的官學和私學力量很強大,加之政治制度的支持,所以,中國古代思想和文化傳統是綿綿不絕的。正是因為這種綿綿不絕,有人會説,我們現在仍然生活在歷史的延長線上。
也許有人會質疑説,我們現在和過去已經有很大變化了,歷史斷裂了。在近代歷史裏,中國經歷了若干看上去使得“歷史斷裂”的大事件: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海戰和第二年的《馬關條約》,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一九〇五年的廢除科舉,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有人也許會説,五四運動之後,中國不是向“西”轉了嗎?的確是向西轉了,但傳統是不是因此斷裂了呢?不見得。我的看法是:五四所批判的傳統,基本上是一個名為“傳統”的假想敵,它不見得真正地清除和批判了傳統,甚至五四本身可能就是一種傳統。
當然,這個問題十分複雜,在海內外都有很多爭論。美國華人學者周策縱先生,曾寫過一本書專門討論五四運動,大家可以去看。他提到的一種看法就是,五四運動是反傳統的傳統,它仍然是在延續一種傳統。所以,如果説我們現在仍舊是生活在傳統的延長線上,那麼,描述過去思想的歷史,實際上也是在討論我們現代人當下的處境。
大家注意一個時間點,中國的思想史熱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後形成的,凡是熟悉當代中國的人都知道,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學界曾經有過文化史熱,有過學術史熱,其實這是一個既斷裂又延續的過程。所以理解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社會、政治和文化,是理解思想史熱、學術史熱很重要的背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思想史研究之所以引人矚目,是因為它同時在自覺地回應着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它在回應新的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的變遷所帶來的思想世界的混雜,這需要重新回顧過去,重新梳理脈絡找到思路;二是,它在討論中國思想史中的問題的同時,也在回應東洋和西洋各種蜂擁而入的新理論、新方法;三是,它在回應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近三十年間中國不斷出現的各種新史料的刺激和挑戰。

先講第一方面。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世界和中國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可能有人會認為,歷史在這裏轉彎了,後面一個時代的問題變了。但我想提醒的是,歷史在中國並未“終結”。只是因為情勢有了變化,問題變得複雜,所以導致了表面的“轉向”與“分化”,在社會的轉向和分化中,思想也在轉向和分化。八十年代同一的思想崩潰了,各自的觀察立場和思想資源不同了,思想取向有差異了。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各種取向和各種資源在沒有經過梳理和整合的情況下一擁而入。
本來,傳統時代的儒家和孔子被民主觀念打倒了,佛教、道教被科學思想看成迷信了,傳統政治意識形態被認定是保守僵化的;但後來,現代民主科學思想又因為“現代性批判”的風潮變得令人懷疑。可是,當孔子又被抬出來的時候,又出現了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嫌疑,而後現代思潮一時十分流行和時髦,但又因為過於超前而不合時宜。在中國思想世界裏,好像已經沒有共同的標準,這使得過去為社會變化進行解釋的“思想”,和原本很清晰的作為知識基礎的“學術”,都發生了混亂。
在這個充滿變化的新時代中,思想史學界就有了很多需要回應的新問題,要告訴我們,“思想”是怎麼變得混亂的?如果要重建中國的思想世界,什麼是可以發掘的傳統資源?什麼是需要重新確立的價值?什麼是能夠呈現中國的思想?
再説第二方面。二十世紀以來,這一百年裏中國在向西轉,即所謂從“在傳統內變”轉向“在傳統外變”,學科制度、研究方法、表述語言都西化了。如果僅僅是一個西方化還好辦,可是,八十年代以後,各種新的理論(主要是西方理論)進入中國,在經歷了一陣“拿來”和“實用”的風潮之後,人們開始反思和檢驗這些被應用在歷史解釋中的各種理論,大家感到很困惑,在這些問題中,有很多仍然需要從思想史角度去思考。舉一些例子。
一、對於古代中國政治文明的整體估價。大家過去有的會強調古代中國對文官制度的建設、對社會流動的推動,文人士大夫對皇權的制約力等,或者強調它的缺乏制度與專制集權。現在由於有了對歐洲歷史背景的警惕和所謂後現代、後殖民主義的理論,似乎覺得這些原本簡單的評價好像有些不太對頭。可是,反過來説中國古代沒有“專制”,是不是就對頭呢?問題一方面涉及歷史,一方面指向現實。這需要思想史家去探討。
二、中國文化的再評價。中國傳統文化只是漢族文化嗎?“國學”是否可以窄化為儒學與儒經?中國是否有一個“複數的傳統”呢?佛教和道教在這個傳統中應該如何評價?它可能成為建構現代中國的文化基礎,併成為對抗西方文化的資源嗎?這也需要思想史家去琢磨。
三、所謂“現代性”的理解。藉助西方對“現代性”的自我反思和後現代理論對現代的瓦解,現在有人覺得中國傳統也許正是西方文化的“解毒劑”,這使得一切本來自明的歷史變得不明確了。可是,到底真的歷史是這樣,還是隻是一種反抗現代性的論述策略或者西方後殖民主義理論的翻版呢?對歷史的追索和對當下的思考,也由此在思想史裏面連在一起。
四、如何理解古代帝國和現代國家?對於王朝作為國家的歷史正當性,對於歷史上的中國認同,好像也有問題了。古代中國對於世界和國家的看法,和其他民族與地區為什麼不同?這些不同如何影響了現在的中國國際政治和國內民族觀念?歷史上只有一個簡單的國家認同(政治認同),還是可以有不同的文化認同、歷史認同和政治認同?
五、一些關鍵觀念的重新認識。由於現代中國跟古代中國聯繫得很緊,所以,中國進入現代和世界之後,思想世界在複雜狀態裏掙扎,出現了多面糾纏的現象。很多觀念要重新界定和梳理。第一比如“國家”,一方面在觀念上接受了以民族為國家基礎的方式,建設現代型的民族國家;一方面又認同中國歷史上以文化為國家基礎的現實,總覺得必須捍衞漢唐天下帝國。
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又比如“現代”,一方面把西方現代國家的法律、民主、科學看成是走向富強的必然和理想的途徑;另一方面又把西方列強看成是弱肉強食,導致中國積貧積弱,覺得中國應該另闢蹊徑,走出一個新的現代。這也是一個複雜的矛盾。第三“文化”,中國人習慣於把自己當作為東方文化的代表,與西方相提並論,所以始終糾纏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可是以上這些東西,如果不從古代中國思想史中去梳理和理解,它的來源和去向也是無法理清的。
近幾十年裏,很多過去天經地義、不容置疑的思想或觀念都在被質疑。可是在中國,由於這些思想或觀念都與政治相關,而政治性的話題很難在公眾社會和學術世界中表述,制度性的問題又主要是行政官員的事情,所以知識界習慣的仍是“借思想文化來解決問題”。可是,過去的哲學史或者思想史——我們常常開玩笑,用李零的話説,過去的思想史好像是“大號哲學史”——是否可以理解中國的思想、信仰和知識?那種唯物對唯心、進步對落後樣式寫出來的思想史,是否可以重現古代場景,是否可能回應當代的思想關懷?
我一直強調,過去的中國思想史著作,基本上是儒家“道統”敍事,東洋或西洋的近代哲學史敍事加上馬克思主義歷史敍事的三結合,主要作用是“建立系譜”(書寫正當性思想的脈絡)和“表彰道統”(對於正統思想的凸顯),意識形態性很強,所以必須改變。思想史寫法的改變,在中國實際上就是在破除固執的舊觀念和舊方法的籠罩。
最後是第三方面。近幾十年來,新資料在不斷增加。首先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由於考古發掘不斷出現新材料,開始對以前的思想史研究提出挑戰。首先是馬王堆、張家山、睡虎地、銀雀山、走馬樓、郭店、雙古堆、裏耶、懸泉置等各種考古發現和各種簡帛資料;其次是西洋和日韓各種有關中國的文獻資料的引入;再次是各種圖像資料的解讀以及電子數據庫和出版物的增長。這些都給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很多資料,迫使中國思想史研究者不得不回應它們所提出的問題,改變過去哲學史或思想史的既成脈絡和固定結論。
這些考古新資料的發現,使得先秦所謂“軸心時代”的思想世界大大豐富了,好些以前覺得不可靠的古書被平反了。比如馬王堆帛書裏的《老子》乙本後附的《黃帝四經》《易傳》和《五行》,過去沒見過;郭店楚簡裏最早的《老子》,以及從未見過的早期宇宙論《太一生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回購的楚竹書裏的哲理著作《恆先》和早期帝王世系《容成氏》;特別是清華簡,聽説也發現了好多類似《尚書》的文獻,都很了不起。
就是看上去和思想史不沾邊的新發現,像長沙走馬樓吳簡,也給思想史研究帶來很多信息,值得思想史家去深思有關古代國家對地方控制能力的問題。美國學者費正清曾説,中國傳統社會的管理只到達縣一級,縣以下是由地方家族宗族力量來控制的。吳簡是否挑戰了這個説法?秦漢以來中央專制是否已經滲透到基層?這些問題都涉及思想史的思考。
傅斯年當年説“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是史學變化的最簡單途徑,一旦史料擴充了,歷史就不同了。可是最近幾十年,思想史不需要那麼麻煩到處去找東西,很多新材料新文獻很現成地就來找思想史了!如果容許我簡略概括,在這方面有幾點很重要:第一,讓我們“重返古層”。這裏我用了日本學者丸山真男的概念,就是重返思想和文化的深層和下層,因為近年來考古發現、邊緣史料、圖像資料越來越多,讓我們關注到了少數精英之外的其他人。過去我們寫思想史、哲學史,基本上圍繞老子、孔子、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這些精英來寫。
可是我們現在從地下挖出來的,很多的是占卜、巫術、房中、兵書之類。這説明,那個時代普通人甚至貴族的觀念世界,遠不像我們現在想象的都是精英的理性的大思想家。這樣,思想史還是否只寫老子、孔子、墨子?難道就不寫寫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想法是怎麼樣的?第二,讓我們“走出疑古”。這是李學勤先生的説法,雖然這個提法有些片面和極端,不過我覺得這還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趨勢或者啓示,現在包括馬王堆、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在內的很多材料,就是在催促我們改變觀察歷史的方法。這改變了我們寫哲學史、思想史的套數。第三,“發現四裔”。
各種各樣來自日韓蒙越的新文獻,讓我們開始注意到歷史上的中國與周邊的互相觀察,也注意到所謂“朝貢體制”或者“冊封體制”下,中國和周邊的微妙關係,更注意到漢族中國以外的各種族羣、宗教和禮俗在漢族中國的投影,所以開始反省原來研究的偏向,開始意識到過去被“中國”研究所忽略的“四裔”,也就是傅斯年稱為“虜學”的學問。
因此,開始出現的問題就是,要改變過去傳統思想史的寫法。我們所學習的哲學史和思想史,可能並不是一個真的、活的古代,而是一個被抽離出來,做成標本的古代。我經常説,魚是在水裏面遊着的,不是在盤子裏躺着的,在盤子裏躺着的是死魚,在水中游的才是活魚。可是,過去的思想史展示出來的,就是裝在盤子裏,端上桌子的東西。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因有三:第一,它是以精英和經典為中心的。過去的思想史是大號哲學史,而且這個哲學史只是一個個哲學家的歷史。第二,它常常是以人或者以書為章節的。包括現在的文學史也是這樣。孟子一章,墨子一章,不如孟子的人物就只能是一節,如果更小的人物那就連一節都不夠,幾個人合一節。第三,是以道統為中心的。
即是以歷史上被官方和主流意識形態欽定的那個主流為中心的。胡適曾經用英文在美國雜誌上批評過馮友蘭,説馮友蘭的哲學史是以正統性來劃分的,不是正統的東西就不在哲學史裏,他的批評有一定道理。比如佛教、道教和下層民眾的所思所想,就無法在哲學史或思想史裏面得到充分討論。可是,那樣的思想史能讓人真的回到歷史中嗎?能讓人去思考當代的問題嗎?
傳統的思想史根本無法承擔這樣的任務,但是,大家知道,“讓傳統歸零”,這只是幻想,傳統無法歸零,我們還生活在歷史延長線上。這個時候,思想史研究就有了用武之地。
因此,在歷史研究領域,中國學術界出現了和西方學術界很不同的取向,如果説,西方歷史學界逐漸從思想史轉向社會史或新文化史,那麼,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之後的中國,則出現了很強烈的、持續至今的“思想史熱”。
思想史在將來的中國為什麼還會很重要
不過,大家也可能已經注意到了,現在説的這個“思想史研究”,實際上是一個很開放的領域。正因為思想史把邊界搞得很開放,所以,它能夠連接各種各樣專門領域,容納各種各樣文獻資料,社會、文化、經濟、風俗、宗教、政治等內容,都被它包容進來了,整編到思想史的大脈絡裏面了。
像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雖然他説是關於政治文化的研究,可是我們仍然把它當成開放的新思想史著作,這種思想史特別容易引起各不同專業學者的關心。應當説,這十幾年來,中國大陸的思想史研究狀況有很大的變化,容我簡單地歸納我覺得變化很大的幾個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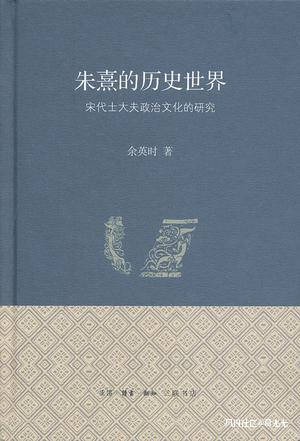
一、新文獻與新史料的充分運用與“眼光向下”的研究趨向,促使思想史研究思考精英和經典思想的“制度化”“風俗化”和“常識化”。思想史不再僅僅是關注思想的“提出”(提出的可能是少數天才,也可能提出了就湮滅了),而同樣要關注思想的“實現”。實現了的是在社會生活裏面稱為制度、常識和風俗的思想,也是真正在歷史上產生作用的思想,這樣我們就得關注風俗史、教育史、制度史等等,不能把電光火花一樣的少數天才當思想史的基本脈絡,當思想的連鎖環節。
舉一個宋代的例子,如果大家都以理學為中心,那麼北宋濂洛之學出現,理學家那種倫理道德嚴格主義就應當在北宋確立地位。可是,如果你注意到北宋殺人祭鬼的流行、薅子棄老風俗的普遍(“棄老”就是類似日本《楢山節考》説的事情),注意到北宋司馬光勸諫皇帝勿看女子裸體相撲,就知道理學家那種倫理嚴厲化的思想,差不多要在南宋以後才成為制度、共識和基本常識。這是一個歷史過程,也是思想史過程,你必須眼光向下看更普遍的社會生活常識。
二、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思想史和知識史的融合,把思想史真正放入知識語境中,拓寬了思想史的視野,也夯實了思想史的基礎。舉一個例子,為什麼“道”和“太極”如此受人重視和景仰?如果你仔細把知識史與思想史結合起來研究,就會知道,古代人對“道”的想象、對“太極”的命名,與古代人對天象的觀察、體驗和想象有很大關係,那便是對北極(大熊星座)的崇拜。
北極那個點有幾個特點:第一,永恆不動,古人認為天道左旋,但有一個地方是始終不動,以靜制動的,那便是北極;第二,北極有顆星,就是北極星,北極星在天穹上沒有對稱點,它是獨一無二的,所以,它叫“一”,也叫“太一”,也叫“道”,叫“北極”也叫“太極”。這樣解釋,便把知識史和思想史聯繫到一起了,思想之所以合理,是因為有知識作為它的基礎。
這方面例子很多,像我就曾經以古代地圖來討論思想史問題,也曾經用朝鮮史料裏大明衣冠的記載來討論清代族羣意識和東亞文化認同,美國的艾爾曼教授也曾經討論過明清科舉中間有關科學技術的考題是否反映中國人的觀念變化等等,這都是過去思想史研究不涉及的話題和資料,它使得思想史和知識史之間不再有鴻溝。
三、思想史的研究空間變得更大了,我們現在的研究範圍,拓展到所謂“西域”與“東海”,這促使思想史研究者思索超越民族國家與恪守民族國家之間的難題,而且也要解決漢族與異族思想的交融。這恰恰就是我們為什麼要提倡“從周邊看中國”這個研究課題的原因。
思想史會始終重要嗎
但是,要使思想史研究在中國一直成為社會關注重心,最重要的,還是中國思想史研究者能否在歷史討論中保持對現實的針對性,能否診斷當下的思想問題。近來,我們一直在關注和追問一些既有關歷史,又有關現實的思想史問題。比如,中國傳統對內的一統觀念和對外的天下觀念,如何影響着今天中國的國內管理制度和國際秩序構想?
傳統的家國體系、君臣關係和禮儀制度,如何影響着今天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傳統儒佛道的三教合一關係,如何影響信仰立場和批判精神的確立,以及宗教信仰對政治權力的制衡作用?我身處中國,我的體會、我的經驗和我親歷的歷史,讓我更多地去思考今天中國的思想狀況,並且從這些思考出發,反省過去幾千年的思想史。近二十年來,中國思想世界越來越複雜,不同思潮的起伏變幻、衝突論爭,給思想史研究者提出了新問題,需要思想史去回應。畢竟,中國有一個習慣在歷史中尋找合理依據、在思想中解決根本問題的傳統,中國當代思想也總是需要在過去思想史,特別是近代思想史中,獲得合理性的來源。
因此,我相信,雖然在歐美思想史研究已經“漸漸凋零”,但是在中國學界,思想史研究至少仍然會在一段時期內保持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