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博士的悲催婚戀:你睡過100個,我哭過10000場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40432-2019-02-17 08:56
文:周衝 來源:周衝的影像聲色

親愛的小夥伴們,
大家好,
我是周衝。
這幾天我們全公司的人,都在泰國旅行。
你們在哪兒玩呢?
今天給大家推薦一篇非常虐心的實錄故事,
我相信,
每一個看到後來的人,都會哭成淚人。
世間渣男千萬種,
但你一定要好好活出自我,
活出光芒,
讓自己有選擇。
我認識他的時候,他25歲,是個温暖的男子。
不抽煙,不喝酒,生活習慣很好。不用走近他,他都會大老遠跑來,伸出雙臂攬我入懷。

那時候,我們都不用開口説話,眼睛對視一下,便知對方心中所想,會心一笑。
性愛也歡娛,接吻時渴望時間停止,擁抱時渴望就此老去。
業餘的時候,他會寫一些詩。深情的,哲理的,逗逼的,深沉的……透過那些詩行,可以窺見一個乾淨而有夢想的靈魂。
偶爾去寺廟上香祈福,聽着“一聲佛號一聲心”,我以為我找到了終生的歸宿。
他也總是在我耳邊呢喃,“我是你一生一世永遠的家”。

諸如此類的話不計其數。
當時聽來,是為誓言,後來發現卻都是思想荼毒,祛毒需要經歷刮骨之痛。
一切的變化,開始於他決定創業。
他決定創業的時候,我剛懷了身孕。
但他説,要是我不創業,哪裏有錢買房子給你和寶寶住,又怎樣買上車,接送你和寶寶呢。
我同意了。
他應酬開始變得非常多,回到家還要工作到深夜一二點。
一開始,我更多地是心疼他,想着要不要勸他不要創業了。
因為我總覺得他一個月12000,還有其它兼職收入五千多,我一個月收入也一萬多,兩個人小三萬,完全夠用,幹嘛把原本可以家人在一起的時間,都給了外人。
這樣,真的,值得麼?
但我並不想打擊他的創業積極性,這些話,便都放在心裏。

他找到了創業合夥人,一家公司的董事長,四十多歲,聽説丈夫已經得了癌症去世了,有兩個兒子。
我全身心信任他,也不曾懷疑他們的關係。
從我懷孕第二個月開始,他基本都是在出差,不再回家。但是照舊每天各種信息和電話關心我,我也不曾懷疑。
我以為,一個做出諸多誓言和承諾的男人,一定也會去踐行他的諾。
畢竟,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我一直有一個讀博的夢想,想着孩子要是生下來,恐怕我便不能全職工作了。
於是同他講,我申請個博士,可以有更多的時間照顧家庭,你也可以毫無後顧之憂地創業。
他也支持我的夢想,便擊掌同意。

當然不想因為讀博而分開異地生活,所以特地諮詢了德國的教授,可否在中國寫論文。
教授考慮到我要照顧孩子,以及也需要家人幫襯的現實狀況,同意了。
教授説我可以跟他每週末視頻通話,溝通學業問題。
如果需要去德國學校裏參加某個學術會議,或者某個學術項目的話,我可以現買票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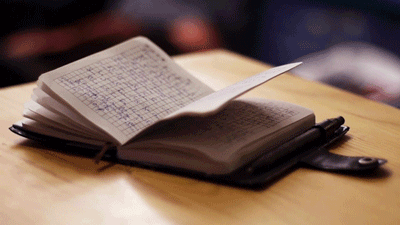
但最初那幾個月,還是需要到德國辦理一系列瑣碎的手續,包括註冊等等。
我趁着身子還能走,便整裝上路。
臨出發前,他把我擁在懷裏,對我説,“你放心,你老公我不會出軌的,別人摸我哪裏我都不會有感覺的,我身心都是你的。”
我刮他鼻子,“我都沒懷疑,你瞎擔心什麼。”
他説,“我是擔心你,怕你被別人勾搭了去,我知道,那裏有個比我還早認識你的人,喜歡你很多年了。”
我哈哈大笑,“孩子都有了,瞎操心。”
我叫他在家乖乖等我。
他説手續辦的快一點,辦完了我去接你。
我剛到德國的時候,還沒有申請獎學金,吃喝住都要用錢。
而各種手續並沒有預料的簡單,原本以為一個月可以辦完。
結果三個月也沒有,德國的辦事效率,實在低下。
他創業開始不斷地投資,公司也還沒有盈利,還要想辦法籌款,沒有餘錢接濟我。
我只好一邊忙改研究計劃,準備申請獎學金,一邊開始在各處打工。
因為學生籤是沒有太多時限工作許可的,只能去餐廳幫忙,去包裝廠打工。

好在德國來錢比較快,在包裝廠包裝一天的東西,一般他們那些學生每天能賺八九十歐,就是正常速度裝。
我懷着身孕,按理應該慢一些,每天賺個五六十歐就好。
但是想到他也缺錢,硬是咬着牙每天早早去搬貨。
別人十點上工,我八點便去。
推着貨物車,去倉庫把啤酒一紮扎,宣傳頁一摞一摞,化妝品一箱一箱,紅牛一排一排,一趟趟搬到自己的工作桌周圍。
然後一整天站在那個工作台旁邊包裝。
一天下來,我可以拿到一百四十歐這樣子。
別人中午去外面餐館吃飯,我為了節省時間多做一些活,都是從家裏自帶一個三明治,中午草草吃了了事。
就這樣,這份工作一直做到懷着身孕第七個月的時候。
後面還怕老闆看出我身孕拒絕我打工,穿很寬大的衣服遮蓋。
自然是很危險的工作,尤其是每裝完一箱,都要摞到貨物板上,需要摞五層,我都是踩着啤酒才能把第五層搬上去,有幾次差點小產,請過幾次小假休息。
我把賺到的錢,留下夠自己吃喝用的,其他拿去支援他。
想着他總要見客户,穿的更該體面,在德國買好幾套西服,稍微貴重些的手錶,都給他寄過去。
我只告訴他,這些錢就是打工賺的,在德國打工也不累,跟玩一樣。
他不要,我硬是要給他。
我説等你創業成功了,加倍還我唄。
我感覺到小生命在肚子裏,一天比一天越來越有活力。
而他的信息,卻一天少過一天。
我隱隱覺得不對勁。
我懷孕第八個月的時候,每天肋骨疼的哭都不曉得怎樣哭。
找他説説話,他基本不在。
電話也打不通。
以前我曾經去另一個城市工作,他受不了分離,我才去那裏報道一個星期,他就巴巴地跑到那裏去,叫我辭職回去。
他説你不在,睡不着覺。
如今我懷着小寶寶,他卻總是不在。失望是自然的。
終於有一天,我同他講,“不管任何時候,如果你愛上了別人,請坦白告訴,因為我一直尊崇人應該為了愛在一起。****”
但是他從不承認不愛了,而且説創業的事情焦頭爛額,也沒心情愛上別人。
他説我是懷孕期,過度敏感,他愛我和肚子裏的孩子都來不及呢。
我辦完各種複雜的手續,正要回去的時候,醫生同我講,怕是你不能飛了,飛機上可能會羊水破。
我無比難過,因為我幾乎每天都在承受相思苦。
他發信息安慰我,“別擔心,生完孩子我去接你們回來。愛你們,大小寶貝。”
我就安慰自己,好吧,堅持一下,我對肚子裏的寶寶説,“你快點出來吧,爸爸好來接我們。”
臨產前那個月,我肚子大的起牀都困難,特別想老公,發信息給他,他回覆的字都是:在開會,開完會回覆你。
然後等一天,沒有任何其它回覆。
生孩子的那一天,我難產,二十四個小時在拼命。他敷衍問了一句,再也沒信。
將我帶到醫院,陪伴我的是早在我讀碩士時候就追我,但總是被我冷冷拒絕的德國帥哥M。
孩子生下來,他沒有視頻孩子一眼。
我不想主動問,也不急着問他何時來接了,因為我想我大概能猜出來他那邊發生了什麼。
我曾經試着問了一次,“你是有了新的女人麼?”
他的回覆的語氣讓我感到陌生而冰涼,“我正煩着,公司的事情好多,另外,你能不能不要那麼敏感,專心養胎。”
從認識他,到有了寶寶,我們在一起好幾年,從未對彼此説過“你別煩我”這種話,就算是吵架的時候,也不曾用過這種疏離的詞彙。
以前他有問題,或者我有問題,我們就把問題拿到桌面上説,去溝通和解決問題。
如今,操啊,老子啊,幾乎每個句子都是。
我的的確確感覺到他在創業上面遇到了什麼問題,我問他,“我能幫你麼?”
他卻不願意把公司裏的事情告訴我了。
他説:“那些都是男人需要解決抗的事情,你就專心養胎照顧好自己就可以了。”
我再問,他就生氣。
我突然覺得我們之間隔了很深的溝,一個我不相信會出現的溝。
孩子生下來,太小了,太脆弱了,怎麼可能帶上飛機。
於是只好繼續等,他也不提來接我的事了。
我又等了四個月,前前後後十一個月在德國,孩子四個月大的時候,我獲得了國家獎學金。
也是時候回家了。
他母親都養了好多雞,準備給我補身子用的。
鬼門關走一遭,我彷彿看到了另一個人的人性中可怕的部分。
但我自我麻木,自我欺騙。
我愛他,只要回去他還是對我們母女兩個好,我就當他是忙創業無法分身顧我們母子好了。
因為是辦理獎學金手續,帶着孩子不方便。
M和他的母親説,這孩子我們視若親生,你有什麼不放心的,我們幫你看着,你去辦理完獎學金再來接她。
但是我生完孩子回去的時候,機場剛見面,他打量了一下我,一個擁抱都沒給。
就彷彿,我不過是路過的一個陌生人。
十個月懷胎,辛苦打工,四個月每天做奶牛,半夜寫博士論文,我自然是憔悴的。
懷過孕生過孩子的人都知道,懷孕對身體有影響。
剛生完孩子,我的身材還沒有完全恢復,有些臃腫。
他沒有擁抱我,也沒有説一聲,“老婆,辛苦了。”
而是一聲不吭,將我接到一個賓館,家也不讓我回。
一整天,我自己在賓館睡了一天。
晚上他來叫我去吃晚餐,整個晚餐都是帶着耳機子,一直刷手機,連我獨自鬱悶地喝掉兩瓶啤酒都不曉得。
他知曉我辛苦,帶我去電影院看電影。
從電影院出來的時候,我像以前那樣拉他的手,他本能地將我推開很遠。
我一下子愣在那裏,“老公?我是你的老婆,是你孩子的媽媽,是你的女人!”
“我最煩別人説我是你的女人,我是你的男人諸如此類這樣的話!”
他聲音特別大特別兇,眉目之間透着兇狠,是我不曾見過的模樣。
我的眼淚一下子就湧了出來,他一下子生了氣,“不許哭,哭會把我的財運哭沒!”
“可你説過,生完孩子接我和寶寶回家,説辛苦我一個人度過這個難過,回來在你懷裏好好哭一哭……”
“你煩不煩?!”
他丟下我,兀自走了。
我站在那裏,覺得彷彿被全世界給拋棄了。
他走出很遠,見我還在原地,又氣勢洶洶地回來,“你是傻了麼,走不走?!”
我跟着他渾渾噩噩的回到賓館,而回到賓館之後,他説還有應酬就離開了。
我也不想留他了,我只想見我的寶寶,分開一天,我都想的要命,要去視頻寶寶。
而我的老公,提都沒有提一聲孩子。
我辦手續整整十幾天,家門一次也沒進去過。
我住在賓館的時候,他連我的手都不願意碰一下。
我問他如果你有女人了,就告訴我,我會自動離開。
可他説他沒有女人,只是工作太累。
我心中已經不信了。
為了打消我的疑慮,他帶我一起參加一個應酬,讓我看看是不是他真的很忙。
對,的確很忙,要踩線,奔波很多,晚上的酒局,能從九點持續到凌晨四點。
但我發現眼前這個人我不認識了,他不是我的老公吧——
我的老公身上散發着乾淨的氣息,這個男人身上散發着污濁的氣息;
我的老公身材勻稱,眉清目秀,見人如見畫,走路輕閒,會照顧身邊的女人和孩子;
這個男人已經有了啤酒肚,額頭上有了皺紋,走路很快,都是等着別人給他開門。
怎麼短短一年時間,我的老公變成了這般?
以前他帶我出去見朋友一起吃飯之類,總時時關照我,還要在他朋友同事們面前炫耀我。
但是現在,早餐的時候他會跑到另一位創業合夥人那裏,也是一個四十二三歲的女人面前,誇她花容月貌,有才華,出口成章。而把我,他的老婆,視作無物。
晚上的酒局上,我看到他非常自然熟練地點煙抽煙,誇誇其談,給那些女人們也點煙,順便也給自己點一支。
我待不下去了,默默離開了酒席。
等到深夜,他終於回來,看到我在哭,他説他看不得我流眼淚,他説女人的眼淚真的會敗壞財運,又離開了。
那個時候我覺得天已經塌下來三分之二了,我還抱着最後一絲希望,那就是,他還沒有見到我們的寶寶。
辦完手續我立即返回德國,開始着手辦理女兒的手續,前前後後奔波,又一個月過去了。
我終於可以抱着女兒一起回來。
一個人抱着孩子的旅途,艱辛異常,但我確定她這麼可愛,一定會贏回爸爸的心,一路上心裏都是一家三口團聚在一起的情形。
飛機上,小寶寶一路子大概受不了顛簸和氣壓,哭鬧異常,我眼睛也沒有閉一下。
到了北京又候機,兩個多小時,又轉機。
最後三個小時,寶寶哭的撕心裂肺,每一聲啼哭都像刀子一樣紮在我的心上。
我趨近崩潰,跟着落淚,還好乘務員以及身旁的乘客多多幫忙,甚至還有一對夫婦專程下機等着我,幫我拿行李。
過完邊檢出來的時候,我和孩子可以説風塵僕僕了,恨不得立即躺倒在地。
見到他,他卻滿臉不悦,第一句話是,“我求你們回來了麼?”
廣州下起大雨,大雨嘩嘩的。
我的眼淚也要流出來,可我拼命忍着,就是不流眼淚。

我就是憑藉母親的本能抱着孩子不倒下去。
他沒帶雨傘,進車之前,我把孩子好好護在懷裏,小心翼翼上車,他滿是不耐煩。
我知道,家門他肯定是不讓進了。
我跟寶寶直接到了一家酒店自助公寓。
這麼久以來,我受的苦,原本都是心甘情願的,全部化作憤怒和不滿,一股氣倒給他,我還説,“你若沒有女人,如今打死我都不信。”
“叫你不信,”他一腳把抱着孩子的我踢倒在地。
這個時候,我才發現我一直深愛的人,居然是一個畜生。
孩子被嚇得大哭,他吼孩子,“哭什麼哭,沒看到大人吵架麼,真沒有靈性,有靈性的話就不會哭了!”
我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這個人,“孩子她才六個月大……”
他大概也覺得錯了,默默坐到沙發裏,開始打開電腦工作,不再理會我和寶寶。
然後我和寶寶在極度的疲憊當中睡過去了,醒來的時候他早已不在。
但是他公司裏用的手機落在沙發裏,我打開,看到他跟他的創業合夥人在很多地方親密相依偎在一起的照片。
可我沒有功夫去傷心,酒店公寓裏有個小灶台,但是沒鍋也沒有碗盤。
我得給孩子做輔食吃,外面依然大雨,我在公寓借了把傘,帶着孩子去買鍋具和碗,順便買了些水果。
要活下去哩。
就這樣,在賓館待了三天,他大概發現賓館實在不適合照顧孩子,提出帶我和寶寶回家。
可是回到家,我立即發現,那是有其他女人住過的屋子,粉色的新地毯等等,都太明顯了,還有彩色的氣球,這玩意,他一個大男人不會買給自己的。
他拿那個氣球遞給寶寶玩,我也不説話,直接拿過氣球給扔掉了。
他説,“你有病啊。”
我説,“我沒病,你自己是不會買這種氣球的,只有跟女孩子在一起才會。”
“你個神經病,”他罵我,然後解釋道,“這是我跟兩個兄弟一起過元旦買的。”
恰好那兩個兄弟也都跟我是好朋友,我把彩色氣球拍了照發給他們,他倆問我,“嫂子,這是啥玩意?”
再去卧室,卧室裏的牀單上還留着愛愛的痕跡。
我説,“你真的確定讓我和寶寶睡留着你們精液的牀單?”
他説你愛住不住,不住就滾。
結果我真抱着孩子打算離開,並且已經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又上來把我和孩子一起踢倒,“你真他媽有病!誰讓你走了?!”
自那以後,喜歡仰睡的小寶寶,總是側着身,緊緊地靠在我的懷裏才能睡覺,兩個小手一定要摸着我的耳朵,生怕一鬆手我就不見了,到後來寶寶會走路會跑會説話了,晚上睡覺依然拒絕自己睡,依然是側着,緊緊貼在我胸前,小手摸着我的耳朵。
直到她睡熟,我才能起身去工作。
但我到那個時候,還是傻地沒有開竅,我強忍着劇痛,返回德國。
回去把這事情告訴我的教授一家,自然還有一直關照我的M。
M説,其實,我早就知道他不靠譜。
你如何知道,我一驚。
“你跟他剛認識一年不久之後,就懷過一次。”他嘆氣,“可是他讓你流掉了。那個時候我就想拿什麼東西敲醒你,叫你離開他,可是你拉黑我,刪除我……”
可你是如何知曉我給他流過一個孩子的?
其實還用問麼,興許他早已找到我,一直默默關注着我,只是太清楚我這人若是不到黃河,是不死心的。
M唯有等我自己清醒的那一天。
我和寶寶返回德國之後,他卻突然又熱情起來,畢竟是在一起多年的妻子,畢竟是自己的孩子,猛然一走,他才覺知孤獨。
他説,“老婆,我想你了。”
日日信息又多了起來,我又心軟了。
M説,忘記他,離開他,不要再回去了。
我不聽,過了四個月,又承受不住相思苦,回去了。
回去,他對我很好,帶我吃好吃的,又像以前那樣跟我膩着,工作的話,各自做自己的。
兩口子,誰家沒個坎坎坷坷。
我這樣想,過去的就過去了吧。
不,過去並沒有過去,過去已經鋪陳了足夠毀滅的種子。
有一天,我跟他一起出去參加項目,他給客户介紹公司,並拜託我做一天他的助理,我幫他放映他硬盤裏公司文件夾裏的公司介紹。
之後又是酒局,他也忘記把他的硬盤收回去。
我因身子不好,提前回賓館休息,躺下了猛然記起來,他的硬盤還在我這裏,一股好奇心驅使我去打開它……
畢竟,曾經我們毫無隔膜和隱瞞,而公司裏的狀況,究竟如何了,他總不告訴我,我想硬盤裏大概有公司的東西。
對,打開那個硬盤,就彷彿開啓了潘多拉的盒子。
我心目中我人生中的最愛,我為之拼命的愛郎,那個説是我一生一世的家的男人,在我懷孩子生孩子養孩子的時候,揹着我,做下這麼多不可理解不可接受的事情。
網盤裏分門別類好幾個文件夾:
清楚記載着哪一天跟哪一個女生在哪裏上了牀,附帶無數的豔照,其中也包括跟這位創業合夥人的照片。
除了這位創業合夥人,這個四十多歲的女人,其他基本都是大學在校或者剛畢業的女生。他寫着哪裏的誰,哪個大學的。
而其中有個武漢的,在我和寶寶進來之前,一直住在這裏。
原來,這就是我回不去家的原因。
他的行程也清清楚楚:
我臨產前十天,他專程買票去武漢上了這個女孩;
我在產房拼命的時候,他又跟這個女孩子碰面,還把她接到了家裏;
我曾經在卧室的牀單上發現愛液的地方,裸照裏恰恰有一張是那個女生裸身躺着的地方。
我一陣反胃,嘔吐不止,震撼太大,腦子很久都是空白的。
我把幾張他跟不同女人的照片發給他。
他很快回來,回來的時候我已經喝的醉醺醺了,我不知道如果不醉,我拿什麼熬過這種打擊。
然後我穿着衣服把自己泡在浴缸裏,隔着門問他,“不愛了,我可以理解;要是因為我不在,找人發泄性慾,我也還能勉強理解;但是,自己十月懷胎剛生完孩子的老婆進不了家門,這種事情,你如何做得出?孩子出生,不曾視頻一眼,這種事情,如何做得出?老婆抱着孩子,不管她身子如何,那麼大力氣踢倒,如何做的出?寧願去上那些風花雪月場上不乾不淨的女人,也不碰自己尼姑了這麼久的老婆,如何做得出?”
他給我跪下,求我原諒。
他説,“因為我覺得自己無能,在你面前,更覺得無能,不碰你,是因為我覺得我髒了……我對不起你們娘倆,我會彌補你們。”
“怎麼彌補?!”
“我會加倍賺錢,努力彌補你們!”
“誰稀罕你的臭錢!”我收拾了行李箱,奪門而出。
他一次次拉住我,吻住我全是淚水的臉,求我留下,但我的心,碎碎的了。
而且我不確定如果在一起,還能否重回以前,因為信任這個東西,一旦被摧毀,就很難重建了。
我執意離去,他一直跟在我身後,出租車來了,我坐進車裏,把他攔在了外面。
興許是天意?
車裏,正響着“一聲佛號一聲心”的曲子。

廣州啊,我每次想起廣州,印象裏,它都在下雨。
我離開的那個夜晚,它也在下雨。
那些雨,就好像在看一齣戲劇一般,不時地嘲笑我一下,再不時地嘲笑他一下。

我沒有等往返票上寫着的去德國的日期才回,而是買了最快返回德國的票。因為我知道,這短短一年我生養孩子的時間,已經考驗了一個人。
我也突然意識到,這個世界上誰是最愛我的那個人。
對,是那個我讀碩士時候苦追我,卻被我拒之門外的那個人;
我回國拉黑不願意理會他的追求信息,而他卻一次次到中國尋找我的人;
我孕檢的時候他總出現帶我去診所的人;
我去打工他總攔着我不叫我去的人;
我生孩子時候叫天天不靈,喊地地不應的時候,他開着車,帶着早已準備好的住院行李的人;
那個説“你不答應嫁給我,我便做和尚等你的人”;
那個為了能娶我,拼命工作買了房子,又辭掉工作,親自裝修房子等着我的人;
那個出去撿了好看的小石頭,回家總要刻上我名字的人;
那個我生日,要親自給我烤蛋糕的人;
那個孩子出生之後,小心翼翼把孩子託在手掌心裏的人,視孩子為己生,或者説甚若親生的人;
那個我身體太累,起不來牀,抱着孩子去打疫苗的人;
那個我夜半正在工作,突然發現窗外有人走過,打開窗,發現窗子上給我留下熱騰騰飯菜的人。
對,M,我一直都不知道,原來有個人,愛我勝過愛我自己,他不曾有過任何誓言,卻用行動踐行着他的真愛,默默守護着我。
而我一直以來,把所有的力氣用在了一個曾經乾淨,最後卻淪為濁物的人身上。
曾經那個他,在我心裏鑄就的信念和美好的世界,在剎那間傾塌。
如果沒有那個小寶寶,我想我一定會傻傻呼呼地去跳樓,如果沒有M一直默默守護着我,我一定很難走出來。
我母親都説我,就你這塊料,要是沒有M,早死了。
我知道,我心裏都知道。過去的那個我,其實也死了,只是肉身活着而已。
我恨不得飛機飛的快一點,再快一點。

飛機落地,我出來的時候,看着M一手抱着娃娃,一手拿着玫瑰花在等着我。
天知道我剛經歷了怎樣的地獄,我飛奔到他的懷裏,哽咽不語。
我説——
我指着寶寶,“不管以後我們兩個會發展成怎樣的關係,她,從頭到尾,只有你一個父親。”
可他説,“還能是怎樣的關係,你要不要我,在我心裏,你都是我的女人。”
經歷這件事之後,我對性愛有了心理陰影,我無法觸碰男生的身體,任何觸碰都會讓我回憶起那些一張張不堪入目的裸照,還有懷孕時候一天天流的眼淚。
所以M試着要我的時候,我就把他推開。
M理解我,也不多問我,他等我自己釋懷。
我不開心了,他就開車帶我到城市最高的地方,爬到城堡上,俯瞰整座城市。
他知道我喜歡看星星,看月亮,特意在三樓開了一個天窗,在天窗下面安置了一張牀。
晚上,我想一個人的時候,他就帶着寶寶在樓下玩,我就自己躺在三樓天窗底下,望着星空和月亮出神。
一聲佛號一聲心,那一世,這兩首曲子我再也沒聽過。
除了這兩隻曲子,我初初生完孩子那四個月,每天晚上抱着孩子哄睡,都要哼唱“蟲兒飛”。
現在,我已經不記得蟲兒飛的歌詞了,只知道,那首曲子哼的是相思。
後來聽一個曾經的同事説他負債很多,每天處理不完的煩心事。
有一次他的妹妹也找到我,同我講:
“我母親在家裏暈過去了,他離家近,可是父親打他電話一整天都沒找到人,又同我講,家裏沒錢,哥哥從畢業到創業,家裏其實一分錢都沒給過。
他越是急着賺錢,卻彷彿錢總賺不來,都是我和妹妹每個月幾百塊錢那樣接濟母親,你知道,我給人做指甲一個月也賺不了太多。
母親生病的時候,我大老遠從北京回去的,我哥哥沒回。”
我不大相信,因為我跟他在一起的那幾年,他經常帶我一起回家看父母的。
她的妹妹説,有什麼不信,“他現在同我母親講話都是用那種不耐煩的粗話,他媽的之類。”
“他是苦悶,煩躁,無處發泄,所以把最難聽的話罵給自己最親的人吧。”我説,“我那時候回去的時候,他也罵我的,他説他媽的真煩,他情願抱着手機也不願意同我講話。他跟外人説話總是恭恭敬敬,非常禮貌,跟我要麼不説話要麼一句夾帶一個操或者老子之類。”
對,創業之後的他,完全變了,不再寫詩,整個人也不再散發着乾淨的氣息。
雖然不曾看他手機,但有時候看到他放在那兒的手機上會跳出來某個銀行的催還貸款信息。
當然,還有探探的提示。
他很少找我問孩子的事情,也不曾提出視頻看她。
有時候節日了,他會發個紅包,通常是521,或者1314這樣,但是我從來不接,那錢便就無聲無息的自動退回去了。
後來他大概手頭寬綽了,會支付寶打不少錢給我,但我原數返回,後來索性把他支付寶拉黑了。
我不是傻,也不是不需要錢,我只是覺得,有些東西是錢彌補不了的。
而且我也不知道那些錢上面,到底有多少女人的身影。

周衝,2015年離開體制,放棄公職,從事自由寫作。出版《我更喜歡努力的自己》等多部暢銷書。本文經授權轉自微信公眾號“周衝的影像聲色”(zhouchong2017),這是一個文藝而理性的公眾號,以文藝的筆調,以理性的思維,剖析人間事與人間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