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廬與郭沫若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之爭_風聞
管见天下-2019-03-27 10:18
轉自《中共黨史研究》 作者:何剛
學術因相激而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亦是在長期的學術爭鳴中發展壯大起來的。這種爭鳴既有馬克思主義史學與馬克思主義史學以外各種史學思潮、學派之間的競進,也有馬克思主義史學內部不同學術觀點和學術主張之間的論爭。特別是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呈現蓬勃發展之勢,繼郭沫若之後,湧現出了包括呂振羽、侯外廬、翦伯贊、范文瀾等在內的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他們“信仰相同而觀點各異”,進行“相互間的刺激與鼓勵”,在堅持以唯物史觀為理論指導的共同研究範式之下,不約而同地對郭沫若史學進行了坦誠熱烈的學術批評。這場學術批評的發生自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總的來説是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的歷史研究服務於現實政治革命的具體體現,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蓬勃生命活力的生動寫照。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古史分期討論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開始把唯物史觀同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他們一方面開始思考史學理論的建設問題,糾正此前在理論理解與運用上的偏差,另一方面反對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公式化”“教條化”。無可否認,《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當初在處理馬克思主義概念與理論範疇時確有“機械主義”之弊,郭沫若自己後來也承認這一點,説自己在研究方法上犯了“公式主義的毛病”,“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觀的公式,往古代的資料上套”。稍後繼起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批評郭沫若“公式主義”的基礎上,開始注意將唯物史觀揭示的一般歷史規律同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具體情形相結合,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的早期進步。在這一過程中,侯外廬以深厚的理論功底和對中國古史的獨特理解,加入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隊伍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與郭沫問題的討論就頗具代表性。

侯外廬
在中國社會史論戰期間,侯外廬正着手翻譯《資本論》,無暇顧及古史研究和分期討論。更主要的是,他當時“不肯放棄謹慎的態度。看了當時論戰雙方的文章,覺得郭老從中國古代的勞動手段而分析中國社會階段之功績,確有其重要的價值;但忘卻了社會構成的生產方式,委實值得討論。而羣起攻擊郭老的文章,則又都沒有搔到癢處”,所以,“對於古史,亦以為稍緩從事,有益於己也有益於人”。因此在古史分期討論的30年代,侯外廬並沒有急於參加。及至40年代,侯外廬開展古史研究伊始就非常注重在人類歷史一般規律下探索中國歷史進程的特殊性,如他指出,郭沫若對中國歷史發展階段的劃分“陷入了公式主義的泥沼”,忽略了中國歷史的“東方的特殊性”。
侯外廬於1943年1月出版的《中國古典社會史論》,不拘泥於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結論,而注重以中國歷史事實為出發點來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他在自序中明確提出了古代社會史研究的三原則:“首先弄清楚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理論”,“斷定‘古代’是有不同路徑的”;“謹守考證辨偽的治學方法”;“把中國古代散沙般的資料,和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古代發展規律,作一個統一的研究”即“歷史科學中關於古代社會的規律的中國化”。可以看出,侯外廬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探討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推進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中國化。在他看來,亞細亞生產方式是“研究的關鍵”,在解決這一問題的基礎上,中國城市國家的起源和發展、中國古代變法的特殊途徑、國民階級在中國古代的難產和形成、氏族制在中國古代的殘存意義以及土地國有的大生產製等問題,才會順然地得出合理解釋。
而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引用了馬克思的經典論述——“大體説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指出馬克思所説的“亞細亞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共產社會,“古典的”是指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封建的”是指歐洲中世紀的經濟行幫制和政治上的封建諸侯,“近世資產階級的”則是現在的資本制度。按照這一演進規律,郭沫若開始了中國歷史的階段劃分。自此以後,對“亞細亞的”生產方式的不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們不同的古代社會性質分析和階段劃分。所以,“亞細亞的”問題往往成為古史分期爭論的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主要的也是首要的理論問題,可謂“研究的關鍵”。幾十年後,侯外廬仍説:“從事中國古史研究的同志,不應該回避這個問題,而要去了解它,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認真研究它。”所以,侯外廬重視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理論延長工作,以此來探尋中國古代社會的特殊規律。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中國化是侯外廬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所取得的理論成就的集中體現,也是他對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的重要貢獻。
由於人們接受蘇聯、日本學者的見解或受其影響,亞細亞生產方式在此前的社會史論戰中眾説紛紜、觀點各異。侯外廬沒有輕易採取其中的任何一種現成説法,而是根據在翻譯《資本論》過程中積累的深厚理論功底,進行了獨立探索。他首先從界定“生產方式”這一基本理論範疇入手,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體現了古代東方土地氏族國有的生產手段與集體氏族奴隸的勞動力二者間的結合關係。“亞細亞古代”與“古典古代”是同一歷史階段(奴隸社會)的兩種不同路徑,二者不存在順序的先後,只是在文明發展路徑上,各自走着特異的道路:古典的古代走的是家族——私產——國家,國家代替家族的“革命”道路;亞細亞古代則是由家族而國家,國家混合着家族,走的是“維新”道路。前者是所謂“正常發育”的文明“小孩”,後者是“早熟”的文明“小孩”。總之,在侯外廬看來,亞細亞生產方式是指經由氏族制發展而成的奴隸制,亦即氏族集團奴隸制。在古代中國,社會進入文明時代後仍然保持着氏族組織,是屬於“亞細亞的古代”類型。侯外廬正是以此理論為指導,對中國古代發展進程及特殊規律作出系統全面的研究。這裏僅舉兩例以示説明。
第一,正是由於亞細亞生產方式中“氏族公社的保存”和“土地私有制的缺乏”等因素,使侯外廬同郭沫若的最初研究一樣,對殷代社會發展水平的估計過低,認為殷代的主要生產部門仍然是畜牧業,奴隸勞動沒有大規模地應用到農業土地生產,其生產方式是“氏族共同體所有的畜牧生產手段與氏族成員主要的共同勞動力二者之間之結合關係”,殷代應處在氏族社會的末期。同樣源於對氏族制殘餘的強調,侯外廬不僅將中國奴隸社會的開端往後推延,而且將奴隸制在西周的發展水平估計過低,並認為奴隸制經過春秋戰國,一直到秦漢之際方才結束。儘管如此,在西周社會性質的判斷上,侯外廬與郭沫若“同屬一派”,主張“西周奴隸論”。後來侯外廬也説:“四十年代,對周秦社會性質的論斷,郭老和我大體是一致的。”
第二,侯外廬考察了“城市國家”的起源和發展問題。他認為,這種亞細亞特性在中國古代“城市國家”發展過程中有着鮮明體現。他説,古代的“城”“國”二字同義,築城就是營國,“城市=國家”。在中國古代城市國家從殷末開始的成立和發展過程中,“邑”是國家成立的雛形,武王克商之前的作邑作邦、武王周公時代營國封國,是中國城市國家形成的兩個步驟。而研究古代城市國家,又必然涉及城市和農村的關係。侯外廬認為,封疆之內為“國”(又叫作“都”),封疆之外的部分為“野”(其範圍便是“四鄙”),這便是歷史第一次城市和農村的劃分,並形成了城市支配着農村的特殊關係。這種支配關係是通過依據而不是破壞氏族制度方才建立起來,也就是氏族貴族的土地國有和氏族奴隸的集團勞動者二者結合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緣故。可以看出,正是由於侯外廬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獨到見解,使他看到了中國古代城市國家的成立和發展與“古典的古代”有着顯著的不同特點,作出了頗有新意的分析,並對郭沫若在處理這一問題時的“公式化”傾向進行了批評。他説:“我以為研究中國的古代社會,要依據古代國家的一般規律……同時還要研究各個類型的特殊規律。郭氏的缺點之一,便是把西周和西洋的古典時代看作一樣,沒有一個字討論周代國家成立的兩個階段。”

郭沫若
除古史分期外,侯外廬和郭沫若在這一時期的學術討論還集中在屈原研究上。針對郭沫若的屈原研究,侯外廬曾説:“我完全懂得詩人郭沫若之一向愛詩人屈原的道理,但是,我不同意史學家和思想家郭沫若對屈原的評價。”同時,他也“決定寫一部古代思想史,作為古代社會史的姊妹篇,從而使歷史和思想史相互一貫地自成體系。因看到郭沫若同志對於屈原思想的討論,更增加了我的興趣,推動了我寫作的勇氣”。所以,在閲讀到郭沫若1941年12月21日在中華職業學校作的演講《屈原的藝術與思想》後,侯外廬對郭沫若“提出了異議”,相繼撰寫了《屈原思想的秘密》《屈原思想淵原底先決問題》等文。
根據侯外廬後來的總結,他們對屈原的分歧,本質上源於各自對儒家思想的不同評價。郭沫若肯定儒家思想,認為當北方的奴隸解放運動和革命思想已經激盪到南方的時候,屈原在“思想上便是受了儒家的影響”, 懷有儒家思想,接受了奴隸解放的時代潮流,這讓他在文學革命上真正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徹底創立了一種體裁。但是,屈原的政治理想是以德政實現中國統一,其悲劇在於他的理想與楚國當時的現實相隔太遠,“因而演出了殉道者的悲劇”。侯外廬則認為,屈原的理想“是在舊的奴隸社會所依據的氏族制度的廢墟上,恢復美政”,他的詩在反映人民戰亂痛苦和怨憂的同時,也表現出對“舊時代的魂魄”的“追求召喚”。因此,“屈原的悲劇是歷史的悲劇”。所以,二人辯論的關鍵點是,儒者屈原的理想“究竟是社會進步的理想,還是倒退的奴隸制殘餘的夢想”。
其實,可以看出,與其説郭沫若與侯外廬的分歧在於對儒者屈原的不同評價之上,不如往更深一層分析即可看到,二者分歧的根源正是他們基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的不同理解而對屈原所處的春秋戰國社會性質的不同分析,即他們對屈原的研究同各自的古史研究緊密相連。這一時期二人在古史研究和分期上的主張大致是一致的,都主“西周奴隸論”,將東周的春秋戰國視為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轉變的時期。侯外廬説:“關於中國周秦社會史的論斷,我和郭先生雖然各有重點的注意,大體上是站在一邊的。”二者的區別就在於前述有關中國奴隸社會形成路徑的不同理解之上。此時的侯外廬注重社會生產方式的發展,已經開始用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來分析中國古代社會,然後“在亞細亞古代社會發展規律探明的前提下,對先秦諸子思想學説產生、發展的背景和實質,作出科學説明”。侯外廬明確指出,發掘屈原的思想秘密“涉及中國古典社會的一般性問題”,即“它的亞細亞生產方法的特殊性問題”。所以,雖然他同意郭沫若認為春秋戰國是一個大轉變時期,但同時指出郭沫若忽視了這種轉變因為“活的社會發展之不足”和“死的古舊的社會制度(主要是氏族制的殘餘)所束縛的奴隸制”而導致的“長期間新時代的難產性”。
對於“亞細亞古代”與“古典古代”的理論區分,郭沫若是反對的,他相信人類歷史發展符合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共同規律,視“亞細亞”為“原始公社式的”。即使到了五六十年代,他在承認各個民族也具有各自特殊性的同時仍強調:“儘管那樣,一般的規律總是不能含混的”,“我們今天既承認了馬克思學説是真理,社會發展可以劃分為五個時期,在我們中國就不能要求例外”,“假使經過仔細周到的研究,而中國的古代發展和馬克思的學説不盡相符,那便可能是馬克思學説有欠妥當的地方。但我們今天能夠這樣説嗎?不能夠。為什麼不能夠?是説馬克思學説是教條,不敢違背嗎?不是,而是我們的研究根本就還不仔細,不周到”。當然,此時的郭沫若似乎沒有注意到侯外廬屈原研究背後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他對侯外廬的批評主要不是有關“亞細亞的”理解以及整個社會史問題,而是認為侯外廬不該用“現代的觀點”,將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思想斥之為反動:“我們不可以拿我們現在二十世紀的現代的眼光去看,要辯證地從歷史的發展上去看。不能説在現代這些思想有一部分是落後了,而公式地斷定這些思想本質地便是反動的。”在這裏,郭沫若顯然把侯外廬當成新史學陣營中的“機械公式化”傾向加以批判,而沒有意識到侯外廬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中國化的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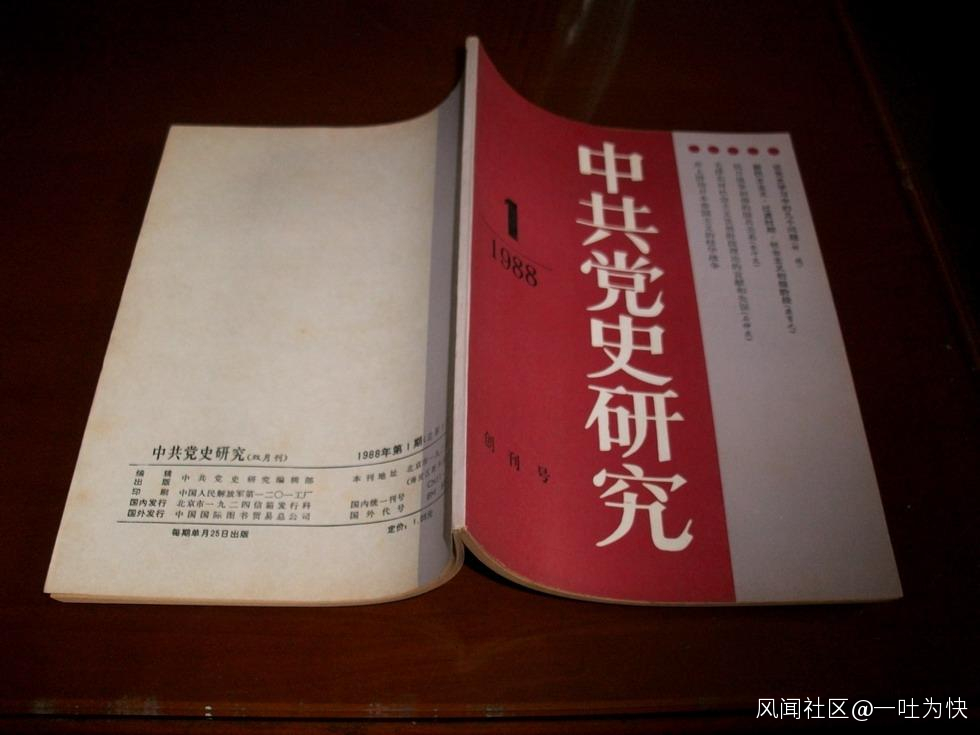
(本文首刊於《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1期,原題《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史學陣營對郭沫若史學的評論》,作者何剛為樂山師範學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