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我們都會變成故鄉的“局外人”_風聞
未读-未读出版社官方账号-未读出版社官方账号2019-04-11 09:33

深讀第54期,相比於其他的假期,清明似乎總是自帶一種不同的氣質。倒也不是多麼傷懷,但是總會靜下心,想起一些人或物。一起爭奪吃食的兄弟姐妹、一起嬉戲笑鬧的夥伴、口袋裏總是裝着很多故事的祖母,甚至承載了無數記憶的那條河那座橋……
將這所有一切集結在一起的就是故鄉,那個即使去過再多的遠方,也仍會時時掛念的地方。
而如今對於大部分人來説,每次返鄉,彷彿都會經歷一場故鄉的“否認”。那些曾經親近的都日漸生疏,舊友見面的欣喜總會演變成因無話可説而強行進行的寒暄。一茬又一茬的孩子繼續成長於此,但看你的眼光都是無一例外的異樣,彷彿你與這個地方從無關聯,不過是一個“局外人”。
本期深讀,就為你講述作家徐則臣在故鄉的所感所聞。
無法返回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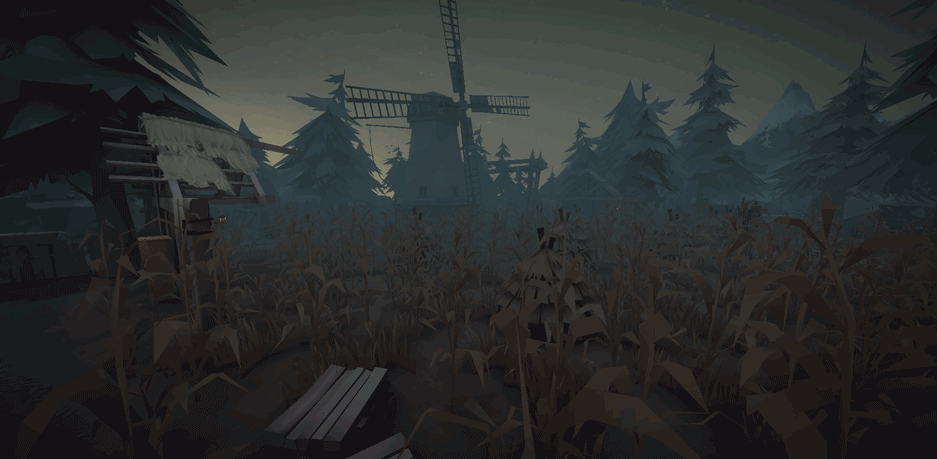
晚上七點鐘村莊就已進入了深夜,四下裏漆黑一片。天有點陰,遙遠處的星星閃耀清光,稀少而清醒。沒有人聲,房門和緊閉的窗户遮住了鄰居們的生活。偶爾,一塊方形的燈光從窗玻璃中映出,更顯出夜的黑。只有散落在各個角落的狗叫還張狂和充滿熱情,不懈地從大地上與黑夜一同升起。
曾聽人説過,鄉村裏的陰氣太重,原因是遼闊而潮濕,人煙稀少。也許是吧,白天冷白的村莊到了夜間一派讓人憂傷的滯重,人氣不旺則地氣應是太盛吧,寒冷從人和動物足跡陳舊的大地上沉沉升起,變成了與史前無異的寒夜。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和冷。
我提着電瓶燈從房前經過,燈光像明亮的喇叭果斷地切入黑暗,我聽到了自己的腳步聲,突然害怕了,擔心看不見的地方里被燈光驚醒的東西一起向我撲過來。光從我手中發出,搖搖擺擺,我成了黑暗的大地上唯一的目標。有那麼一瞬間我想,如果它們衝上來,我就完了。它們是什麼我不知道。然後聽見風經過枯樹枝,發出旗幟抖動的獵獵之聲。鄉村的上空活了起來,單調的嘈雜,風不是排山倒海地來,而是東拉西扯地去,把混沌的夜豁開了一個個冰冷巨大的黑口子。
在這夜裏一切都是孤單的。我提着燈走在隔一條巷子的老二嫂家門口,門敞開着,含混的燈光像個醉鬼直直地摔倒在門前。豆腐房裏蒸汽濛濛,二嫂在蒸汽裏挽起了袖子,面前是一口大缸,她指點着十八歲的女兒張開紗布,熱熱鬧鬧的鮮豆腐就要上筐了。提前做好了豆腐,明天一早擔着在街巷裏叫賣。
鄉村的悽清和寒冷的確是年甚一年了。為什麼我説不清。我知道燈光之下和黑暗之中的他們的生活也會理所當然地十二分熱鬧,但不能改變我的感受。他們都學會了躲在家裏,各自的生活秘不示人。他們留下的巨大的寂靜的空間裏只有我,一個從鄉村走出去的人,走得太快太遠時間太長,當我回來的時候,已經成了一個外鄉人。我懷念童年時光中鄰里們無間的往來,煤油燈無法照徹的夜裏交融一起的歡樂。我懷念那時的黑暗。我關上燈回到了黑暗,可是,我能回到那些無間的歡樂裏嗎。
半個月亮爬上來

好多年了,我只在寒暑假時節匆匆地在家小住,用母親的説法,屁股還沒把板凳焙熱就走了。短短的時間裏,我很少走過頹廢的後河橋去到對岸,再向北走就是我家的菜園子。我也很少去,尤其在冬天。我知道這時候的菜園子形同虛設,一畦畦田壟了無生氣,只有幾株瘦小的菠菜和蒜苗,因為寒冷而抱緊了大地。無數年來菜園子們都是這麼度過它的冬天,可是此刻,我總是能發現它們的陌生。而陽光是多麼的好。
祖母坐在院子中的藤椅裏,半眯着眼,陽光落滿一身。多好的天,祖母説,照得人想睡覺。然後自顧説起話來。祖母也許知道我會坐下來認真聽。我喜歡聽她講述那些陳年舊事,尤其從寫小説之後,特別注意蒐集那些遙遠的故事。
對我來説,祖母那一代人的時光已經十分陌生了,對於今天的世界,那是些失蹤了的生活,如果祖母不在太陽下講述出來,它們就永遠不會回來了。祖母講的多是這個村莊裏多年前瑣碎的恩怨情仇、奇聞怪事。每一位祖母都是講故事的好手,這絕非作家們為了炫耀師承而矯情編造的謊話。
祖母們從她們的時光深處走過來,口袋裏的故事我們聞所未聞,更具魅力的是她們講故事的方式,有一搭沒一搭的,想到哪説到哪,自由散漫,間以咳嗽和吐痰的聲音,不時拍打老棉襖上的陽光,然後就忘了剛剛講到的是誰家的事,提醒也無濟於事,她又開了另一家人的故事的頭,從老人的死説起,從小孩的岀生説起,或者從哪一家迎親時的牛車和一個大餅説起。那些已經有了黴味的故事被抖落在太陽底下,也像被子那樣被重新晾曬。

祖母年邁之後,講述往事成了她最為專注的一件事。聽父親説,祖母睡眠很少,夜裏一覺醒來就要把祖父叫醒,向他不厭其煩地講過去的事。那些事祖父要麼經歷過,要麼已經聽過無數次,反正他已是耳熟能詳。**但祖父還是不厭其煩地聽,不時憑着自己的記憶認真地修正。**他們在回首過去時得到了樂趣。
人老了,就不再往前走了,而是往後退,蹣跚地走回年輕時代,想把那些值得一提的事、那些沒來得及做和想的事情重新做一遍想一次。他們想看清楚這輩子如何走了這麼遠的路。祖母顯然常常沉醉在過去的時光裏,或者真是太陽很好讓人想睡,她講着講着就閉上了眼,語速慢了下來,彷彿有着沉重的時光拖曳的艱難,講述開始像夢吃一樣飄飄忽忽。
午飯之後我又聽了半個下午。三點鐘的時候太陽依然很好,我也挺不住了,不得不回到房間把推遲的午覺撿起來。
一覺混沌。醒來時已經五點多,天色黯淡,夜晚迫在眉睫。陽光消失不見了,我大夢醒覺的不知今夕何夕的滿足感陡然敗落,心情也跟着壞了下來。真想閉上眼接着睡過去,以便在一片大好的陽光裏重新醒來。但是此刻睡意全無,母親正張羅着晚飯,讓我起牀,一會兒就該吃晚飯了。
看來夜晚無法避免。
祖母説

從十二歲時出門,讀書,工作,再讀書,一晃又是十二年。每年回家兩次,名為歸鄉,實是小住,總是鬼攆着似的匆匆去來。回到家也難得外出,關在房裏讀寫,偶爾出去也只是房前屋後遛上一圈,漂泊不得安寧的心態常讓我感覺自己是故鄉的局外人。除了周圍的鄰居,稍遠一點的都在逐漸陌生,那些曾是我的同學和少時玩伴的年輕人,多半已經婚嫁生養了。生疏是免不了的,要命的是他們的孩子,完全是用異樣的眼光看我,好像我與這個村莊無關。
儘管這樣,我依然沒能太深地發現村莊的變化,大約是這種變化正在緩慢進行,而我一年兩次的還鄉多少也對此有些瞭解,孩子們的成長與誰家的一座平房豎起來並不能讓我驚奇。都是生活的常識了,有些東西的確在人的心裏也展開了它們的規律,它們的生長節奏不會讓我們意外,也就無法把它稱作變化。
我常以為我的村莊是不會變化的,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相同,院門向南開放,白楊和桑樹還站在老地方,後河水的榮枯也只是遵循着時令的安排。當我從村莊後面的那條土路走向家門時,沿途一成不變的景物令我失望。我就想,還沒變。外面的世界一天一個模樣,故鄉卻像脱離了時光的軌道,固執地守在陳舊的記憶裏,生活彷彿停滯不前,一年一年還是老面孔。
若是從生活質量論,現在的鄉村絕不是一片樂土。小城市正跑步奔向小康,大都市早已在籌劃小資和中產階級的生活,而鄉村,比如我的家鄉,多年來依然沒有多少起色。當看到他們為人民幣深度焦慮,而將正值學齡的孩子從教室裏強行拽出來的時候,我是多麼希望她也能與時俱進、富足祥和啊。那些田園牧歌的美譽,那些關於大自然的最矯情的想象,加在鄉村的枯腦袋上是多麼的大而無當。
生存依然是日常最重大的話題的村莊,要田園牧歌和大自然的想象幹什麼。看到他們和若干年前一樣扛着鐵鍬茫然地走進田野,我常覺得自己在這片大地上想起詩歌是一種罪過。他們當然需要詩歌,但更需要舒服滋潤的一日三餐,和不再為指縫裏的幾個硬幣斤斤計較,需要所有的人都和他們一樣,把糧食高高舉過頭頂。

可是祖母説,村莊一直在變,一天和一天不同。她又向我歷數我離家的這半年中村裏死了多少人。祖母越來越執着地談論死亡了。這幾乎是年邁的一個標誌,在鄉村像老年斑一樣不可避免。祖母八十了,有理由為眾多的生命算一算賬。
祖母説,東莊的某某死了,才六十八歲;南頭的某某得了癌症,沒錢治,活活疼死掉了;路西的某某頭天晚上還好好的,一早醒來身子就僵了,那可是個能幹的女人,六十五歲了還挑着一擔水一路小跑;後河邊上的某某也死了,一個炸雷轟開了柴門,把他赤條條地劈死在牀上,那聲神出鬼沒的雷怎麼找到他的呢,不到六十,剛剛把白鬍子蓄了兩寸長;還有賣燒餅的媳婦,一口氣生了三個丫頭,剛得了個兒子沒滿三歲,莫名其妙地一頭鑽進燒餅爐裏,拽出來時人已經燒焦了。
祖母坐在藤椅裏,在陽光下數着指頭,講述死亡時只看天。她説日子一天一個樣了,他們那一代人差不多都沒了,出門滿眼都是不認識的人。他們都走了,少一個人村子裏就空出一塊地方,能感覺出來院子裏的風都比過去大了,沒人擋着,風想怎麼吹就怎麼吹,來來往往都不忌諱了。
這是祖母的變化。村莊越來越讓她不認識了,世界因為死亡在一點點地殘缺,她所熟悉的那個村莊在逐漸消失,屬於他們的往事和回憶被死去的人分批帶走了,剩下的最終是面目全非的別樣的生活。在祖母變化的生活裏,不停地走進陌生的面孔,那些身強力壯、朝氣蓬勃的年輕人,而這正是我所不解的,他們像血液一樣奔突在村莊的肌體裏,但是為什麼多年來故鄉依然故我, 連同我們的土地都要為糧食焦慮?
—座橋

從落成到廢棄,四十年間都沒有一個正式的名字。我們隨口叫它“後河橋"。因為河在村後,橋在河上。當初落成時是個什麼模樣,我不知道,那時我還沒有出生。即使參與建造的匠人也記不起來了,雙手扶起的建築和日子一樣多,誰記得一座普普通通的河上橋呢?但我知道四十年後它的模樣。已經沒有人再從上面經過了。
通往田地的道路幾年前重新整修,渡河的責任落到鄰近的另一座高大的水泥橋上。而它低矮,大青石上只能堆積厚厚的黃土。它破敗不堪,橋斷路也斷。過了橋上岸是一片瓜地,偷瓜的小孩也只能一跳一跳地從後河橋上謹慎地通過,那一處一處坍塌的土石,置在河水的邊緣,像年邁的老人坐卧在陽光裏,守着過去繁華的記憶,等待有朝一日河水也遠離了它,記憶也拋棄了它。
儘管低矮,橋還是有它熱鬧的過去的。
我的有關後河橋的記憶始於一場大水。在我們那裏有如此大水實屬罕見。説水大,也僅僅是那個夏季水漫過了橋,到達我幼小的膝蓋的高度。水把泥土全捲了起來,一派混沌。
我隨姐姐去菜園裏割韭菜,兩人循着過去的感覺,試探着在看不見橋面的深水裏拉着手向前走。橋上來來往往的都是喜氣洋洋的人們,誰見過這樣的大水?一個個都穿着小褲衩,拎着漁網,哈哈哈地從這頭走到那頭,盯着橋面和離橋更遠的地方,希望有一條魚能跳起來落進網裏。我清楚地記得一條大魚躍出了十幾年前的後河水面,我看見了,是一條大青魚。很多人都看見了,他們一起往魚躍出的地方撲去,然後一塊兒倒進魚消失的地方的深水裏。
後來水落下去了,辣辣的陽光把泥濘的橋面烘乾了。我跟着姐姐去橋邊的青石上洗衣服。應該是為了一條花手絹吧。母親説,誰洗了就歸誰。我很少用手絹,但是喜歡手絹上的圖案。所以當姐姐從盆裏拿出那條手絹準備洗時,我一把將它奪了過來。我來洗,我在對面的一塊青石上説。姐姐不讓,她早就夢想能夠擁有一條屬於自己的手絹。姐姐猛地伸手到對面去抓,我閃了她一下,姐姐就鑽到水裏去了。科學的説法是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慣性了。
我為此得意,但過了—會兒還不見姐姐露出水面,我急了,大聲喊叫在橋那邊捶衣服的人。一個本家的堂哥立即跳進水裏,摸索了半天,才在橋洞裏把姐姐給拉出來。救上來她好久沒能説話,睜開眼後,突然放聲大哭。**堂哥説,讓她哭吧,哭完了就不委屈,不害怕了。**後來姐姐告訴我,她其實很想從水裏出來的,可是水位太高,頭觸到橋面的石板也找不到空氣,姐姐説她怕極了,因為到處都是暈暈乎乎的水。
再後來水就幹了。村裏決定把水抽乾撈魚。河底見淤泥的那天我也去了,實際上我每天都去,放了學背上書包就去。如果運氣好可以撿到一條魚,運氣不好還可以看看抽水機怎樣把水喝下去又吐出來,看看穿一身皮衣服的年輕人在及腰深的淤泥裏跋涉,身子前傾,不像走倒像爬。
那天我見到了一條大鮎魚,孤零零地躺在橋洞裏的石板間。石板上長滿了青苔,茸茸的涼濕滑膩。為了不讓別人發現, 我坐在一塊大青石上,垂下的雙腿恰好可以遮住那個藏魚的洞。
沒有人注意這邊時,我才跳下橋,伸手去抓那條魚。可是魚身上覆滿粘液,根本抓不住。我急得都能聽見自己轟隆隆的心跳聲。焦急和祈禱都幫不上忙。我被一個叫東方的小孩推到了一邊,愣榜地看着他把手指摳進魚鮑,穩穩地拎起它,跳上橋跑回家了。這是我整個童年第一次捉魚,驚險而無所得。常常想起這事時都要笑,不就是將手指摳進魚鮑裏嘛,可是我當時不懂這一點。
如今我也看了二十多年的後河橋,它老了,癱瘓了,破敗了,幾乎被人遺忘。後河的水變得混濁骯髒,再沒有人抱着木盆去橋邊捶衣服了。通往田地的路也斷了,再沒有人想着要走過後河橋。後河橋在我家屋子後不遠,連母親也很少對我説,後河橋怎麼樣怎麼樣了。還能時時想起它的,大約也就是那些曾把童年遺落在橋邊的人,如我者,還有現在正在成長,時時覬覦對岸瓜地的一羣偷瓜的小孩。
這個冬天我又來到後河橋上。到處是沒落的遺蹟,殘缺爪整。讓我驚心的是兩行車轍印,峻峭艱深,碾起的泥濘翻卷在兩邊,堅硬如鐵。因為前面又坍塌了一處,這車轍只剩下了掐頭去尾的一個片段。不知道是哪年的轍印,大約也沒人能夠記憶起來。它像這座蒼老的後河橋的一個斷章。哪一天連這轍印也被雨銷蝕了,後河橋也許就消亡了,不再是橋,只是一堆糾纏在一起的青石和泥土。
本文所選片段摘錄自《從一個蛋開始》,有刪節, 徐則臣 著,2019年2月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品,已獲得授權。
🖼️
編輯 = 鏡子
圖片來源 = GIPHY
商務合作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