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克 | 巴黎燒了嗎:聖母院大火的啓示_風聞
保马-保马官方账号-2019-04-17 08:13
當地時間4月15日,位於巴黎市中心、西岱島上的巴黎聖母院屋頂起火,建築損毀嚴重。這座在二戰中倖免於難的天主教堂,卻在法國的多事之春裏被付之一炬。它曾親眼見證拿破崙的加冕式,亦曾數次經歷易主之後的巴黎,政治與宗教一次又一次地將它當作角力場。只是眼下,它不僅不知道該拿“黃馬甲”們怎麼辦,也不知道要如何處理難民的身份政治問題,甚至連自己麾下的神父都無力約束,這個古典時代的產物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火焰中一去不返。或許這場意外,意味着這樣一個時刻的到來: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係。
原文載於澎湃思想市場,標題為保馬自擬。感謝澎湃授權保馬發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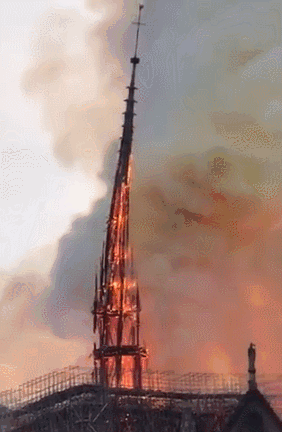
〇 法國當地時間4月15日,巴黎聖母院Cathédrale Notre Dame de Paris的尖塔在烈焰中坍塌。
巴黎聖母院大火,
燃燒在**“政”與“教”的交匯點上**
“巴黎絕不能淪於敵人之手,萬一發生此種情況,他在那裏找到的只能是一片廢墟!”
1944年8月23日,當二戰盟軍展開反攻,兵臨巴黎城下時,希特勒給巴黎守衞司令肖爾鐵茨發去一道密令,在他眼中,這不啻為一封巴黎的死刑判決書。然而,這位深受希特勒信任的高級將領,最終還是背叛了元首,並未執行他原本最擅長的焦土政策。聖母院、凱旋門、艾菲爾鐵塔等地標性建築,因此有幸留存到今天。這正是美法記者科林斯和拉皮埃爾聯袂作品《巴黎燒了嗎?》所描繪的那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4月15日晚上,當巴黎聖母院被熊熊大火吞噬之時,許多人不約而同地想起這本《巴黎燒了嗎?》。頗為弔詭的是,當年希特勒失敗前夕的這封密令,不經意間在75年之後部分地化為現實。
雖然聖母院大火只是一個偶發事件,但在文藝青年的痛心疾首之外(從事發當晚初步清點情況來看,損失比預想中要小),聖母院的熊熊火光,或許還能照亮當下黃馬甲、大辯論、全民公投、身份認同、政治領袖、文化反思等一系列深層問題。而自大革命以來,法國的政教分離(laicité)制度歷來是聚訟紛紜所在,我們不妨以“政”與“教”兩條線索,來審視這場火災的時代背景。
- 1 -
被搶頭條的總統
在傍晚6:50聖母院傳出火情之前,整個法國關注的其實是另一件大事——總統馬克龍原定在當晚八點對全國發表講話,就此前持續了整整三個月的“大辯論”進行總結。
所謂“大辯論”,並非如中文字面意思傳遞的像是一場針鋒相對的國際大專辯論賽;毋寧説,這是一場聲勢浩大的集思廣益。自去年11月以來,深受“黃馬甲”運動抗議之苦的馬克龍,從今年1月15日發起一場全民大討論,議題集中在“生態轉型”、“税收制度”、“民主體制”和“國家與公共服務重組”四個方面,希望能借此機會修復中央-地方關係,汲取施政新思路,並從抗議運動中“解套”。

〇 自去年11月開始的法國“黃馬甲”示威運動。
然而,在一萬餘場集會、兩萬七千封郵件和193萬條公民建議之外,法國媒體普遍對這次“大辯論”的成效持謹慎與懷疑態度。反對者自然將這種辯論斥之為“誇誇其談”,支持者也難言樂觀。因為“大辯論”本身是各種不同意見的交流和碰撞,而聽取和接受哪些意見,這本身就構成了一種政治決斷。無論如何總結,都會被反對者斥之為玩弄“障眼法”。正因如此,馬克龍原定於4月15日對這場辯論的總結陳詞,就成為法國上下最為關心的話題。
然而正是在這個關頭,巴黎聖母院的一場大火,完全改寫了劇本。當傍晚火勢剛露頭時,馬克龍的總結陳詞還只是有被“搶頭條”的危險;但當火勢一發不可收拾之際,總統講話就連二條也保不住了。很快,總統府宣佈講話延期至次日。而馬克龍率一眾高官趕赴聖母院視察火情,同時發推文稱“像所有同胞一樣,我今晚很難過地看到法國這部分付諸一炬”,隨後他在電視鏡頭前,矢言將團結全法國“重建聖母院”。
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已經延續五個月、22輪的“黃馬甲”運動,正在演化成為“硬核”反對形態,很難通過經濟上作出綏靖或文化上喚起共情來消除。聖母院大火也不乏陰謀論的解釋版本——原定八點發表講話,結果七點就失火,天下哪有這麼湊巧的事?聖母院失火對誰最有利?當然是馬克龍啊,不用在全國人民面前“尬聊”了……
陰謀論的荒謬顯而易見。馬克龍的尷尬,不過是向後推遲了24小時而已,問題依舊擺在那裏。當初憑藉普遍不滿情緒而崛起的年輕總統,正在品嚐這種不滿情緒迴旋鏢的苦果。對他而言,黃馬甲、大辯論與聖母院大火相互交疊,構成了極為微妙複雜的發言時機。掌握得當的話,或許能成為凝聚人心、擺脱困境的一個契機;但反過來説,同樣可能是一個全民士氣受挫、不知伊于胡底的“連環劫”。
- 2 -
泥沼中的教會
在聖母院大火之後,即將到來的復活節,大概會是法國教會近百年來最為悲情的一個復活節了。這種悲情無疑主要來自於這場祝融之災,但在更大背景下,法國教會也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形象和道義危機。
4月15日晚間,法國主教協會主席Eric de Moulins-Beaufort代表教會高層,對這場大火表達痛惜之情,稱巴黎聖母院是“和平、美、信仰(不僅僅是基督教信仰)的象徵”,這次事件將是一個巨大的傷口。
這位主席固然不幸,剛剛上任十餘天就遇到這種百年不遇的悲劇。但整個法國天主教會其實也和總統馬克龍一樣陷入泥沼。在法國主教協會管理層新舊交替之際,上屆主席Georges Pontier曾發出警告,法國天主教會正處於“麻煩深重”的境地。究其原因,仍然和整個天主教會近年來頻繁曝出的孌童醜聞及體制性缺陷不無關係。在Pontier看來,雖然教會已經開始採取措施,但對於重建教會權威,並沒有完全做好準備。
這種“麻煩深重”的最典型事例,便是震動法國教會的前任里昂大主教Barbarin因為庇護涉嫌性侵的神職人員,被世俗法庭判決有罪,處以六個月徒刑(附緩刑)。隨後Barbarin赴梵蒂岡覲見教宗方濟各請求辭職,卻被後者拒絕。儘管如此,Barbarin還是宣佈退休,以便為教會止損。
而從更加廣闊的視野來看,法國天主教會的另一個對手,或許是以世俗化為核心的現代性本身。根據一份不完全統計,近三十年來,法國民眾的宗教信仰比例有大幅走低之勢。1986年,82%的法國人是廣義基督徒(其中絕大部分是天主教徒,新教徒只佔微不足道的1%),而15.5%的人沒有宗教信仰;30年之後的2016年,基督徒比例縮減至51.1%,而無信仰者則增至近四成(39.6%)。在這種背景下,無論對法國人還是外國人而言,巴黎聖母院越來越成為一個旅遊勝地,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本身的宗教意義。
如果説,聖母院這場大火的確勾起了法國人心底和歷史緊密相連的某種宗教情懷,而巴黎民眾佇立街頭遙望聖母院、齊聲吟唱歌詠的畫面也讓無數人動容,但它似乎很難同這種世俗化大勢相抗衡,更遑論逆轉。這種感動是真切的,但放在歷史長河中看,它也是倏忽即逝的。
- 3 -
已經多難,如何興邦
從工程學角度來説,巴黎聖母院的尖塔並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意義,歷史上也曾經歷損毀並重建。剛剛被焚燬的尖塔,不過是19世紀的作品,相對800年曆史的聖母院,可謂是相對較新的部分。
但從另一重意義來説,這場巴黎聖母院大火,大概會是自911之後最具象徵意義的一幅圖景——紐約雙子塔的倒掉,是西方世界現代資本主義遭受重創;而巴黎聖母院尖塔的坍塌,則是古典時代的一曲輓歌。正是在這重意義上,尖塔在烈焰中倒下,會格外具有震撼效果。

但區別在於,當雙子塔倒掉時,美國人在震驚之餘,會自然而然地發問——“他們為什麼恨我們?”隨即整個國家同仇敵愾,槍口共同對外(至於行事是否明智,則另當別論),而法國此次聖母院大火,雖然在技術層面無疑可以找到罪魁禍首,卻很難在政治決斷層面委過於人。這或許將構成一個無法排遣的內傷,對整個民族士氣的一次嚴重打擊。
進一步而言,這種偶發事件,和法國近年來頻繁遭受的恐怖主義襲擊又有不同。類似2015年《查理週刊》血案的恐襲,本身的確可以在政治上區分敵我,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動員效果。但和當年的911事件相比,後者的威脅是外部性的,可以輕易區分出“我們”和“他們”;而法國所面臨的恐襲威脅則是內生性的,肇事者多為在法國(或者比利時等歐洲鄰國)出生長大的移民後裔,“我們”與“他們”的界限已經模糊不清,這也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法國和歐洲面臨的最重大挑戰之一。
〇 大火過後的巴黎聖母院內部。
巴黎的城市銘言,是“漂浮而不沉沒”(Fluctuat nec mergitur),如今聖母院浮在塞納河西岱島上,幸運地逃過希特勒的魔爪,卻毀於火災,看上去像是歷史所開的捉狹玩笑。當然,無論花費十億還是百億歐元,聖母院終將重建,**唯一的問題是,當新的尖塔重新矗立起來時,俯瞰的將是怎樣一個國家?**或者説,這個已經多難的國家,在左支右絀、內外交迫之間,將會如何興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