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自然》:自然環境變遷與德意志的現代化_風聞
大忍怀里的垃圾君-书读越多越反动2019-04-20 12:32
站在大壩上眺望的自然風光到底有多自然?
這句不乏諷刺意味的問句所指向的正是征服自然的開發主義和保護自然的浪漫主義之間戲劇性的交匯處:深受自然之力(例如洪水)所擺佈的人類,除了基於恐懼的敬畏之外,或許很難對自然有別的感情。而經歷了激烈的征服和改造之後的人類,卻站在自己所建築的宏大工程之上(比如大壩),冥想環保主義與迴歸自然的情懷。
“我們應該以自然為師”,沼澤畫家莫德索恩(Otto Modersohn)在日記裏寫到,但又緊接着補上一句,這是他“在穿越運河上方的橋”時想到的。
類似於此的辯證關係便構成了大衞·布拉克伯恩(David Blackbourn)所撰《征服自然:二百五十年的環境變遷與近現代德國的形成》(台北:遠足,2018)的兩條主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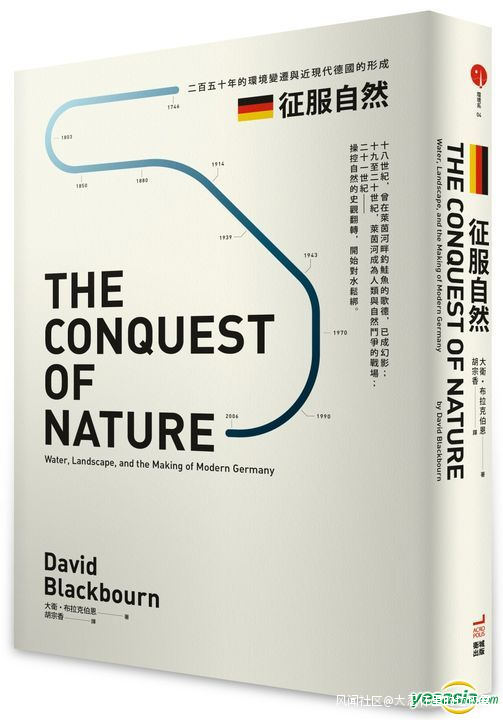
這本書雖然以自然作為研究的客體,但顯然是人類活動才構成了變遷的動力。故事就以18世紀普魯士對於奧得布魯赫沼澤的開發為起點,着重闡述腓特烈大帝,這位人類戰爭史上璀璨巨星,如何組織起應對自然的戰爭。無論是對人還是對自然,腓特烈大帝最得力的工具無疑都是軍隊,以及軍隊背後嚴密的官僚體系。後者在福柯形容的“古典時代”所帶來的測量、統計工具的幫助下,致力於國土控制的合理化,而奧得布魯赫沼澤這類存在顯然破壞了某種“秩序感”因而必須被改造。軍隊就是這一計劃最有力的工具,不僅是河流改到了濕地排幹,甚至隨之而來的移民的組織,都帶有普魯士國家嚴密的軍事化特色。
在德意志的西部,巴登的圖拉(Johann Gottfried Tulla)則利用拿破崙取締神聖羅馬帝國,重新洗牌德意志政治版圖的機會,將整治萊茵河的計劃推行開來。此類馴服自然的過程在整個十九世紀持續不斷,包括為德意志海軍事業奠基的雅德灣(後來的威廉港)建設、東菲士蘭的運河和濕地改造直到十九世紀末,由奧托·因茲(Otto A. L. Intze)所領導下的德意志築壩大業的“黃金十年”。這些工程不僅是德意志自然地貌天翻地覆的改造,也展現出德國工業化進程的激烈程度。但是這種對激烈的現代化征服,無論是對於自然還是對於社會的,都造成了一種浪漫主義的“反動”。從普魯士時代開始,就存在着對於改造計劃的反對,尤其是到了大規模築壩的時代,懷疑之聲更是此起彼伏。當然從現在的角度考察,這些工程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的變遷(我不太願意使用“惡化”這個詞)也可以作為反對激烈改造的論據。
但是這種浪漫主義的反動卻表現在納粹身上,並與種族主義掛鈎。但是納粹的環保主義同樣是三心二意的,至少,納粹對於東歐領土主張的合法性論述中所強調的一點,就是斯拉夫人無力開發東歐的資源,而只有德國人才能將灰色的土地改造為綠色的莊園。但事實是,納粹制定了無數野心勃勃的計劃卻在執行上眼高手低,東部變化的戰線是一個原因,但德國人即便是在波蘭的開發上也是十足的粗放而低效,種族主義並未帶來環保主義者所期待的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反而造就了最粗劣的生產方式。直到戰後,德國人才真正能夠在環保和開發之間找到某種平衡點,但這很難説就是故事的終點。
這本書讓我們關注到歐洲國家在近代,其對於國內的殖民的激烈程度其實並不亞於在殖民地的作為。現代化作為綜合性的意識形態,在改造自然的同時也改造社會,改造本民族的同時也強迫其它人接受相似的方式。這種方式的基礎,從腓特烈大帝的例子上看,就是官僚與軍隊的結合,及其控制方式的擴散化過程。但是作為其反動的浪漫主義同樣無法遏制這一趨勢,倒不如説,反而是其發展至極端的體現。德意志對於自然開發的歷史及其思想正是在這一方面成為全世界可資借鑑的事例,作者敏鋭的發覺到了這一點並以優美的筆觸將其娓娓道來,是一本值得閲讀和反思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