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初有道:西漢《太初曆》的創制與校驗|天行見物理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19-04-24 09:54
撰文 | 李輕舟(《大學科普》編輯部)
來源:《物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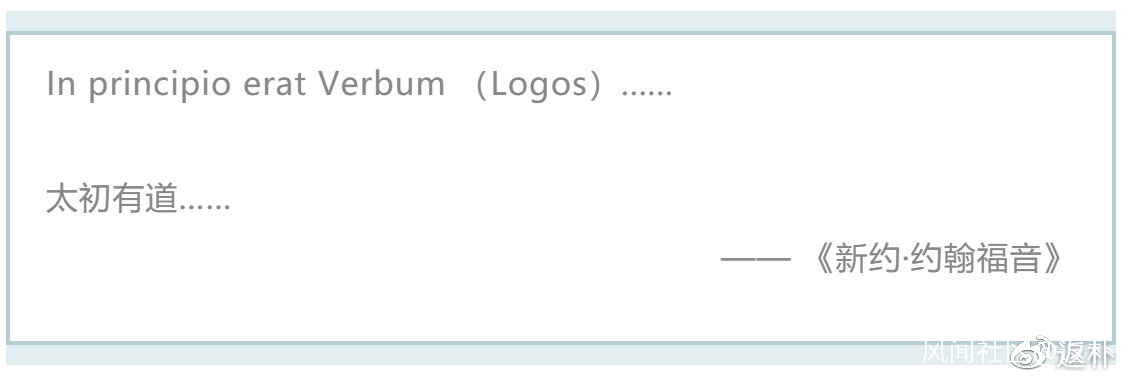
受 命 而 王
漢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對帝國的最高統治者漢武帝來説,這一年貌似乏善可陳:鑿空西域、北逐匈奴、南兼夷越、東並朝鮮、封禪泰山……煌煌功業,俱為往昔榮光。要去遠征大宛的貳師將軍李廣利尚未出兵,唯一能留諸後世的莫非只有建章新宮神明台上的銅仙承露盤?
也就在這一年,“公羊經學”巨擘董仲舒在茂陵家中病逝。作為漢帝國意識形態的締造者,他的身後留下了垂憲漢家的整套“ 話語”(Verbum/Logos)—— 正是這套“ 話語”維繫着“天”與“人”、“君”與“臣”之間的微妙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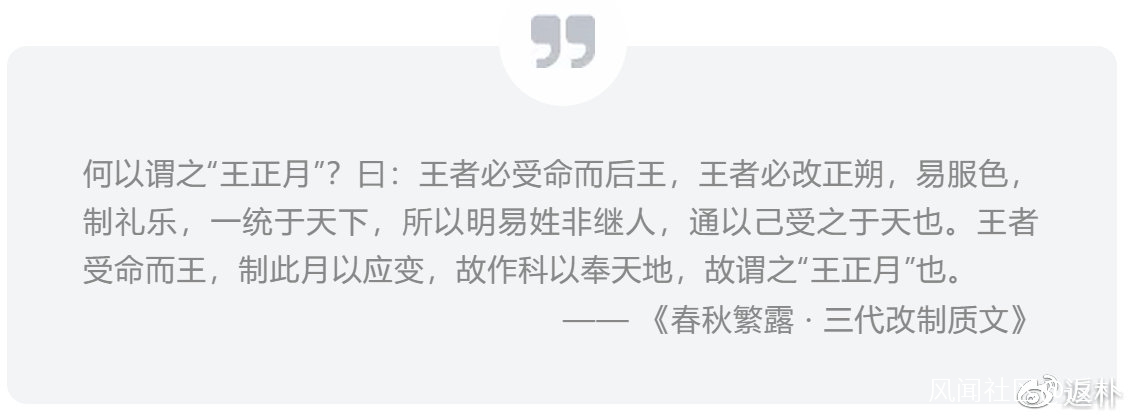
彼時,漢室肇基已逾百年(自劉邦封漢王始),如日中天。漢武帝的雄心不再滿足於現世天下的九五之尊,遂步秦皇后塵,逐漸墮入形而上的迷夢,一面忙於求仙長生罔顧黎民社稷,一面又急於昭示海內自己“受命而王”……
敬 授 民 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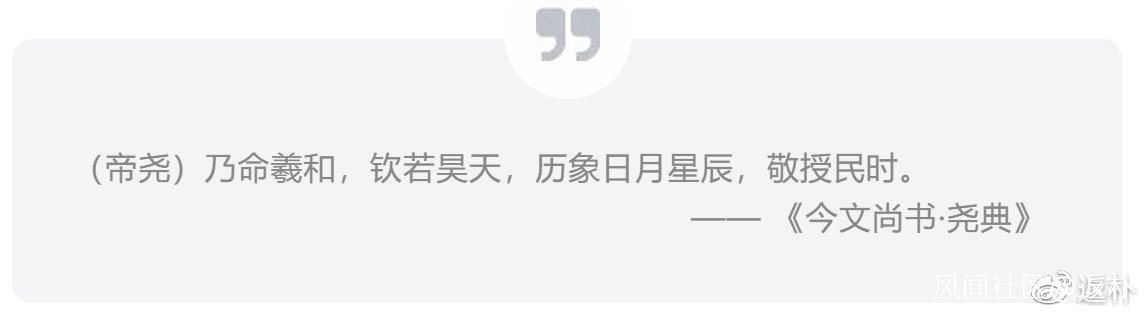
所謂“敬授民時”,就是君主向萬民頒佈曆法,以明四時更替有序。華夏自古以農事立國,在儒家的觀念中,上古先王“躬稼而有天下”(《論語·憲問》)。故而曆法之於君主和萬民有形而下與形而上兩重意義:就形而下來論,君主頒行的“曆法”即“農事之法”,就是為了指導萬民進行農業生產;就形而上來説,君主頒行的“曆法”關乎“政統之法”(即政權合法性),既然以“天子”自命,代天牧民行化,如果連天道運行的四時倫序都不能掌握,如何昭示海內自己“受命於天”?
為此,深諳此道的漢武帝在這一年接觸了兩撥人。先是方士出身的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聯合太史令司馬遷上奏“曆紀壞廢,宜改正朔”(《漢書·律曆志》)。隨後,武帝就此事下詔詢問位列三公的儒臣——御史大夫兒寬,兒寬與眾博士商議後上奏“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同上)。
霍去病墓“馬踏匈奴”石雕(複製件,作者攝於陝西曆史博物館)
“改正朔,易服色”——這樣的建議,於漢室,不是第一次。早在漢文帝一朝,就有大文豪賈誼、方士公孫臣和新垣平先後倡言,而文帝“謙讓未遑”。武帝初立,推行“建元革新”(公元前140年),儒臣趙綰、王臧等也有此議,終為奉行黃老之術的太皇太后竇氏(當時實際的主政者)扼殺……
改 歷 易 服
“正”為“正月”,即一年之始月;“朔”為“朔旦”,即一月之始日。“正朔”合用,狹義上即指一年第一月的第一天,而廣義上則可作曆法的同義語。“服色”之説源於先秦陰陽家鄒衍的五德終始理論。秦始皇以周德火,秦取代了周,取水克火之意,故當德水,服色尚黑。而曆法自然就要用冠名五帝之一的《顓頊歷》,因為按陰陽家的理論,傳説中的顓頊亦德水(所以也叫“黑帝”或“玄帝”)。
漢初承續秦制,“正朔”與“服色”都沿襲秦朝舊制。持這種立場的代表是曾為秦“柱下史”的開國功臣張蒼(文帝時為丞相),作為一個明習天文歷算的大學者(張蒼出大儒荀子門下),竟然反對賈誼等人改歷易服(德土而服色尚黃)的主張,卻堅持這種既不開新朝氣象又不合天文實際的前朝舊曆,令他的同行晚輩司馬遷亦感費解。
數十年的爭訟終於在元封七年畫上了句號。漢武帝下詔改元太初,命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人為漢家造新曆——《太初曆》。
六 歷 紛 繁
到漢朝初年, 除沿襲的秦朝《顓頊歷》外,大致還有所謂的《黃帝歷》《夏曆》《殷歷》《周曆》《魯歷》得以傳續,合稱古六歷。這些曆法未必如其冠名,很可能是先秦陰陽家等學派託偽所作。據後世史家和天文歷算家的推測,古六歷皆屬“四分曆”,區別在於曆法的推算起點(曆元或上元)與歲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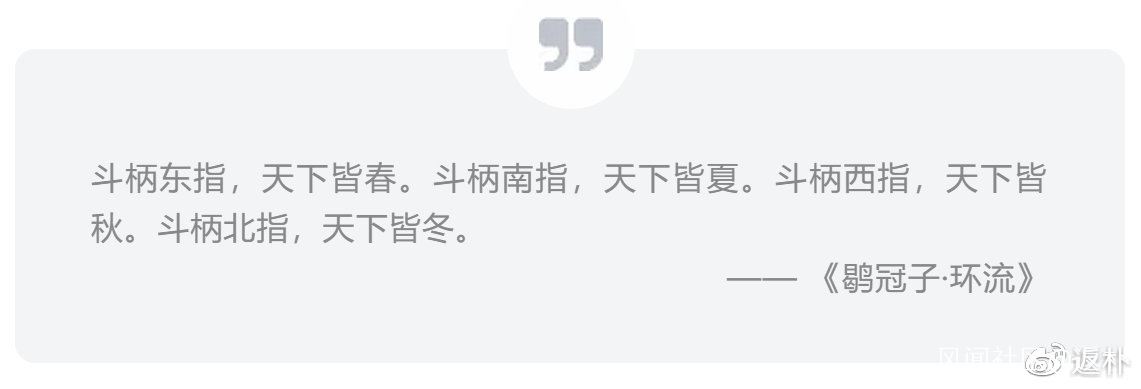
劃分周天的十二次與十二辰(蘇州石刻天文圖,南宋黃裳繪製,公元1247年刻石)
不論何種曆法,不論是紀年、紀月還是紀日,在物理上就是一個計量時間的問題,首先要解決的是找到合適的時標(timing mark),它既要有較好的週期性,也要便於觀測。比如春秋戰國盛行的歲星紀年,即以歲星(木星)約十二年運行一周天(相對於遠處恆星背景)為依據,將周天(先沿天赤道,後發展為沿黃道)等分為十二次,自西向東分別為:星紀、玄枵、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和析木。這便有了《國語·周語》中“武王伐殷,歲在鶉火”(即歲星在鶉火之次)之類的説法。而黎民農事更關心的是一年中春夏秋冬四時,這就要依賴鬥建,即北斗斗柄的指向,據此又將周天(沿天赤道)分為十二辰,與地平面的十二地支方位對應,自東向西分別為: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和亥**[1, 2]。由此便可協調四時與月份。比如夏正建寅、殷正建醜、周正建子而秦正建亥,就是説《夏曆》以斗柄指寅為歲首的正月(朔,下略), 那麼按“夏正”,《殷歷》以十二月為歲首,《周曆》以十一月為歲首,而秦朝的《顓頊歷》以十月為歲首。至於一月中的時間,自然就要用到月相的變化(實際是日月相對位置決定的),周初的金文中便有“初吉”(朔)、“ 生霸” (生魄)、“ 既望” 和“ 死霸”(死魄)的説法[3]**。
一套曆法體系不會只取決於單一的時標,作為陰陽合曆,至少要有兩個重要的參數,其一是以太陽運動為時標的迴歸年(觀測方法是立圭表測日影長短的變化),其二是以月相變化為時標的朔望月。但是,地、月、日之間的運動(以地球為參照即日月視運動)是不均勻的,兩個時標之間沒有簡單的公度關係。就此而論,編定曆法就是協調不同時標的週期性——古希臘的幾何體系偏重空間週期性,而古中國的算術體系偏重時間週期性。
明代圭表(複製件,作者攝於北京古觀象台)
古六歷皆屬“四分曆”,所謂 “四分”就是指它們的迴歸年都取
日, 而朔望月都取
日。12個朔望月比一個迴歸年少10到11天,三年左右偏差就會超過一個月。這就需要“置閏”,《説文解字》上講“閏,餘分之月,五歲再閏。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從王在門中”,也就是説以置閏月來糾正這個偏差是天子的職責。先秦“四分曆”的置閏法取19個迴歸年與235(=19×12+7)個朔望月相等,即十九年七閏法——這就是天文學中的“默冬週期”(Metoniccycle),得名於古希臘天文學家默冬(Μέτων)。
雖然有置閏法來糾正偏差,但“四分曆”,具體到太初改歷的背景就是《顓頊歷》,其迴歸年和朔望月仍皆大於更精確的現代取值。那麼長期使用(至少從秦朝到太初改歷之前)帶來的誤差積累勢必會發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乃至“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漢書·律曆志》)——這大概就是司馬遷等人在上奏中説的“曆紀壞廢”,也是“公羊經學”那套神秘主義的話語體系下隱藏的實實在在的改歷動因。
疇 人 制 歷

先期組建的改歷團隊“不能為算”,於是朝廷又自官方和民間招募治歷者共二十餘人。在這些參與改歷的“疇人”中,鄧平、方士唐都(司馬遷的父親太史令司馬談曾“學天官於唐都”)和巴郡隱士落下閎三人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他們所造新曆優於其餘17家曆法,最終於太初元年夏五月頒行天下。
今日所見之《太初曆》,實乃西漢末年劉歆增補而成的《三統曆》,載於東漢班固的《漢書·律曆志》,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有完整文字記錄的歷法。除了天文學上的成就(測定五星會合週期與以135個月為交食週期)外**[4]**,《太初曆》之革新主要有兩點:其一,恢復夏正,以建寅月為歲首;其二,廢《顓頊歷》的歲終置閏,保留十九年七閏法,納入“二十四節氣”,以無中氣月置閏。“二十四節氣”是十二節氣與十二中氣的合稱,大致起源於先秦,是對迴歸年(對應於太陽在黃道上的運動)的二十四等分,依次為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和大寒。其中奇數項為節氣,偶數項為中氣。如前文所述,12個朔望月小於一個迴歸年,則一個朔望月小於兩個節氣的時間間隔,這就可能出現一個月只有一個節氣或一箇中氣的情況。《太初曆》便以沒有中氣的月份為閏月。以建寅月為歲首和以無中氣月置閏,更好地協調了日月時標的週期性,尤使月份與四時相匹配,頗利農事。
不同於過去的“四分曆”,《太初曆》屬於“八十一分律歷”(“八十一”這個數緣於“以律起歷”,開啓了兩漢以來樂律與曆法附會的形上學傳統),其朔望月取
日,據十九年七閏法可得迴歸年為
日。也就是説,《太初曆》的兩個重要參數都大於《顓頊歷》的,與現代值的偏差也更大,故長期的誤差累積也不可小覷。承擔了《太初曆》運算重任的落下閎對這個隱憂的預見是“後八百歲,此歷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益部耆舊傳》),而實際上《太初曆》每125年即差一日,頒行188年之後,東漢王朝就不得不改歷了。
落下閎與渾儀塑像(作者攝於四川閬中錦屏山)
是 非 堅 定?
漢昭帝元鳳三年(公元前78年),《太初曆》在頒行27年之後,就迎來一次的大考驗。時任太史令的張壽王突然發難,上書漢昭帝“ 今陰陽不調, 宜更歷之過也”(《漢書·律曆志》)。漢昭帝很重視,下詔讓主歷使者鮮于妄人與之詰問,張壽王不服。於是鮮于妄人建議朝廷組織天象實測來校驗,獲得了漢昭帝的批准。自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到元鳳五年十二月,漢庭在上林苑的清枱(靈台)校驗了十一家曆法,排列次序。張壽王所治《殷歷》誤差很大。到元鳳六年,又校驗了一次,還是《太初曆》第一,而張壽王仍不罷休,屢遭彈劾,最終下獄。經此事之後,“自漢歷(《太初曆》) 初起, 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事實上是三十年),而是非堅定”(同上)。
在這場歷時三年的歷法之爭中,張壽王的固執和漢昭帝的重視都頗值得玩味。張壽王的“固執”或可理解為,由於“四分曆”本身的參數優勢,支持並傳續古歷(比如通過調整曆元)的勢力仍然強大。但漢昭帝的“重視”未必完全是從形而下的角度出發,那麼貴為天子的他到底在擔心什麼?要弄明白這一點,需要回到張壽王上書中的四個字——“陰陽不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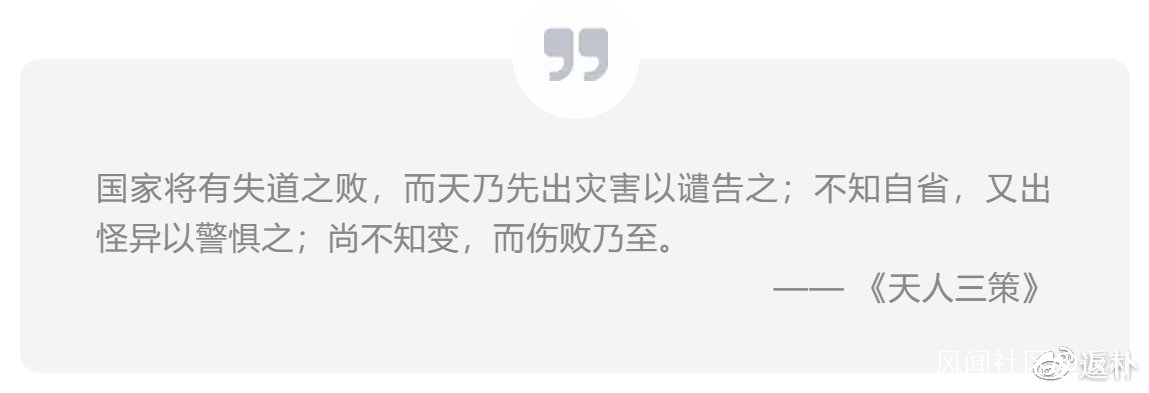
在董仲舒留下的話語體系中,這四個字對應於上天警示君主的“災異”——就在元鳳三年春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 (《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董仲舒的門人、擔任符節令的儒生眭弘給漢昭帝上了一封匪夷所思的奏疏,他將這些“災異”理解為民間有“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同上),進而建議漢昭帝順應天命,禪位讓賢……
歸根結底,所謂“災異”不過是維持君臣微妙平衡的一種手段。其中的神秘主義色彩,如果不是事後神話,那肯定就是事前造勢——幾乎所有人都能看出,這些“災異”指向了漢室繼承危機(即衞太子與鈎弋子的儲位之爭),而危機的種子在武帝晚年的“巫蠱之禍”時(公元前91年)就埋下了。昭帝朝秉政的大將軍霍光毫不猶豫地誅殺了妖言惑眾的眭弘。五年後,那個流落民間的皇曾孫劉病已(衞太子劉據之孫)登基,即漢宣帝,徵召眭弘的兒子為郎官。
史書沒有記下漢昭帝對這場風波的反應,但從事後他對校驗漢歷的重視程度來看,他對“陰陽不調”背後的政治暗流不可能毫無察覺。而我等亦可從元鳳三年這兩場不大不小的風波中窺見,中國傳統曆法如何在現實功用與神秘話語的張力下曲折發展。
參考文獻
[1] 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 郭沫若全集·第一卷·考古編. 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 155-342
[2] 吳宇虹. 巴比倫天文學的黃道十二宮和中華天文學的十二辰之各自起源. 世界歷史,2009,(3):115
[3] (日)藪內淸. 殷暦に関する二、三の問題. 東洋史研究,1956,15(2):235
[4]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天文學》編輯委員會. 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學.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0. 565
**版權聲明:**本文選自《物理》2019年第1期,獲授權轉載自“中國物理學會期刊網”。
《返樸》,致力好科普。國際著名物理學家文小剛與生物學家顏寧聯袂擔任總編,與幾十位學者組成的編委會一起,與你共同求索。關注《返樸》(微信號:fanpu2019)參與更多討論。二次轉載或合作請聯繫[email protected]。
特別提示:「返樸」正在求賢,有意者請戳“求賢”聯繫我們,等你來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