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思考,要不要給歐洲黑暗的中世紀翻個案?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27909-2019-04-26 14:43
或許我們先反省這樣一個論斷,中世紀到現代的過渡是理性觀念取代宗教觀念,恰好相反:正如美國現代哲學家懷特海非常中肯地評論説:整個中世紀哲學,和現代思想相比,是一種“無邊無際的理性主義”。
思考這個問題的契機,是工業革命為什麼首先發生在英格蘭這個問題,而非大航海時代一開始的受益者伊比利亞半島的雙雄或者荷蘭。
啓蒙運動不是突然發生的,它的種子和源頭,追來追去還是要追溯到中世紀那裏。
十三世紀的經院哲學的集大成者托馬斯·阿奎那和十八世紀的康德有什麼差別?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是,在前者看來,整個自然界,尤其是朝着作為“第一因”的上帝敞開的這個自然世界,顯而易見是可以為人類理性所能理解的。而對於在啓蒙世紀之末從事著述的康德來説,人類理性的範圍已經急劇縮小了(當然理性的定義也被修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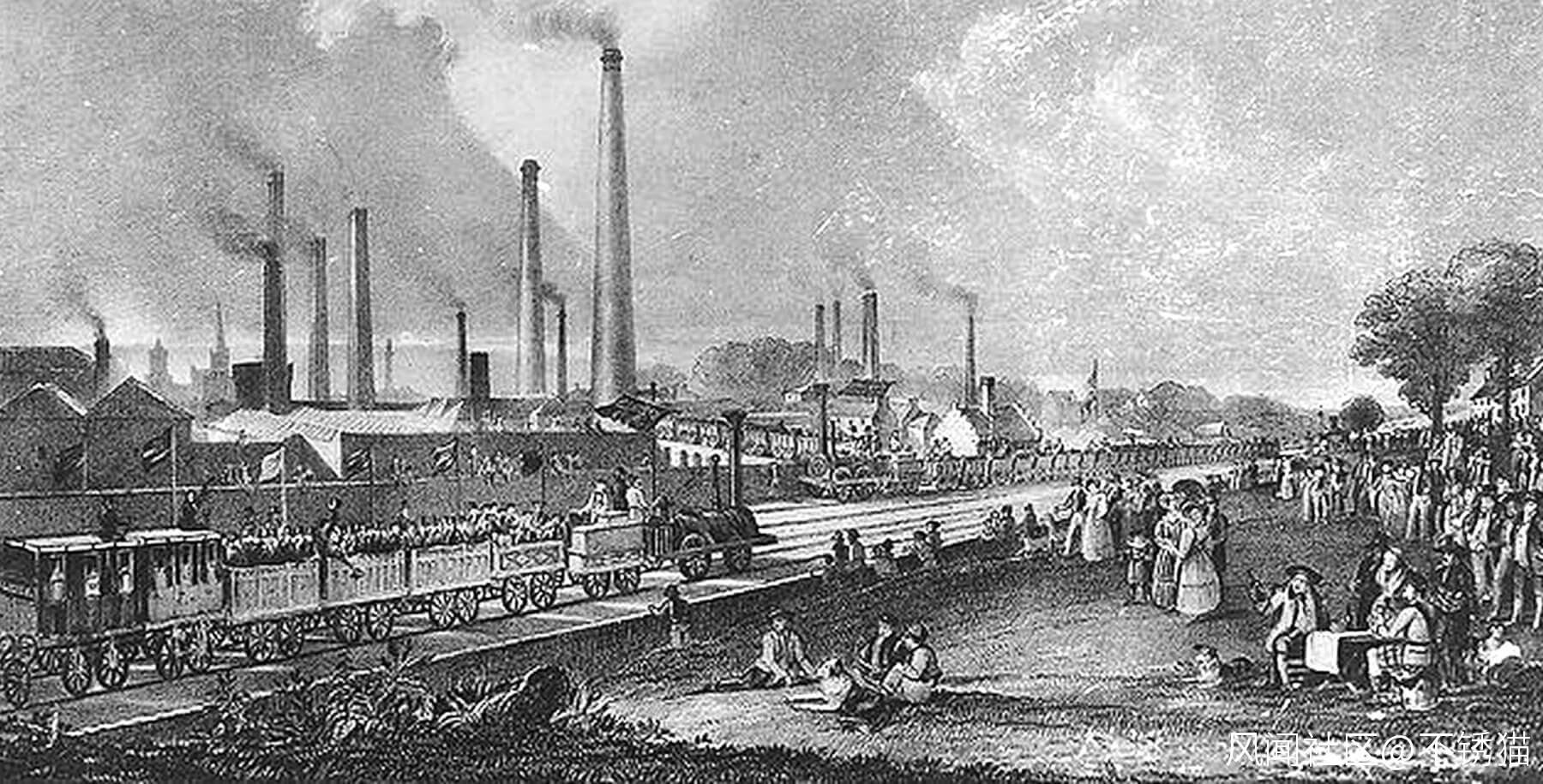
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
中世紀哲學家這種**“無邊無際的理性主義”**與後來思想家們對人類理性隨隨便便使用完全不同,他們將人類理性像一種溶劑一樣應用於人間天上的所有事物。中世紀哲學家的理性主義為人類理智所不能把握的信仰和教條的玄秘所遏制,但也正是這些信仰和教條作為人類心靈中理性和情感、理性和非理性之間至關重要的溝通渠道之種種象徵物,被人賦予了非常真實豐富的意義。
中世紀哲學家的理性主義,從中世紀進入現代世界的入口處站立着科學精神,啓蒙運動的精神、新教和資本主義。乍一看,新教的精神和科學的精神沒有什麼關係,因為在宗教問題上,新教全力強調作為信仰論據的非理性事實,而不是象中世紀神學那樣給信仰勉強加種種理性的結構,這樣,才有馬丁・路德那著名的咒罵:“理性,這個婊子”。
然而,在世俗問題上—特別是在它對待自然的關係方面一新教與新科學非常協調一致。新教從中世紀基督教中剔除了大量的偶像和象徵物,揭去面紗,顯示大自然是一個與精神相對立、要由清教徒的熱忱和勤奮將其征服的客體,新教就像科學一樣,幫助現代人去實現它的宏圖,使大自然非神靈化,從大自然中清除所有人類心靈投射在其中的象徵性偶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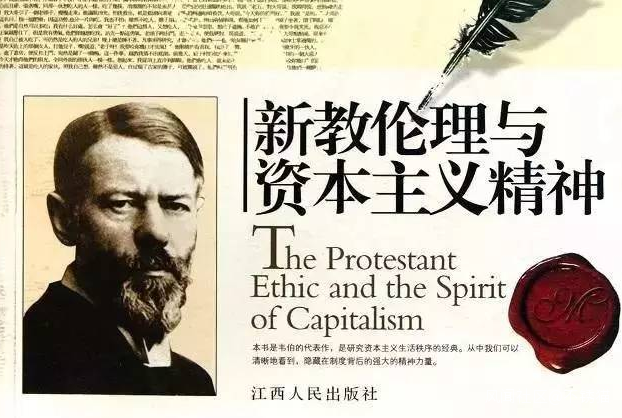
這場鬥爭在二十世紀達到了最高潮。
從理性的觀點看,任何信仰,包括對理性本身的信仰,都是悖論,因為信仰與理性是人的心靈的根本不同的功能。但是,基督教的特殊內容增強了它的悖論性質:神之子成了人,死了,又死裏復生了。在這個問題上,聖保羅知道他的對手不僅有希臘哲學家,而且還有虔誠的希伯來人。他告訴我們,對於希臘人,基督教是愚蠢;對於猶太人,基督教是醜聞。
如果説希臘人要求智慧,則另一方面,猶太人就要求神蹟,也就是要求一個確定的奇蹟性事件,來證明這個拿撒勒人耶穌確實就是那個上帝曾允諾派來的彌賽亞。保羅心靈地位最重耍的信條,不是道成肉身(也就是説,無限的上帝成了有限的人,這在後來的基爾凱戈爾看來,完全是基督教的悖論和醜聞),而是耶穌復活。(事實上,説聖保羅對道成肉身有一個明確的學説,是大可懷疑的),奧古斯丁也常被列為存在主義的先驅者,而旦實際上他比德爾圖良所發生的影響更大。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問:人是什麼?
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則問:我是誰?這樣一種轉向是決定性的。
教會在組織機構上的統一也有助於此。既然教會已經宣佈了它對一條又一條教義的信仰,中華司機哲學家就可以被允准自由地如其所願成為理性的,因為他的非理性部分已經包含並表達在教會的組織機構裏,並且因此能夠自己照顧自己。
世俗歷史學家常常指出,中世紀教會把一種可恨的限制加到中世紀思想家們的自有理性上。
這從現代世俗心靈的觀點看,貌似是真的;但是,這根本不是中世紀思想家們自己對他們所信膠條的感受方式。他們體驗到這些教條乃是有生命力的心靈液體,理性本身在其中運行和發生作用,並且因此是理性的秘密源泉和支撐。

奧古斯丁某種程度上繼承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
這要留待後來的新教哲學家像抗的這樣的,才能體驗到理性和教條之間的這種致命卻又必要的分裂,而且是以這樣一種方式:康德認為上帝存在的證明實際上是建立在一種無意識的信仰基礎上,中世紀思想家平常視為理性的東西其實是信仰。而且,這類錯誤之所以發生,究其原因並不是由於那些思想家缺乏邏輯的敏鋭,而是由於他們的理性本身紮根於他們的歷史存在——簡言之,“信仰時代的存在”。
以亞里士多德著作的形式體現出來的希臘理性在西方聲譽日隆。12、13世紀的哲學家們作出了驚人的努力,才促成了信仰和理性之間最後的中世紀契約。
13世紀和14世紀初葉綜合的時刻來到了,它產生了或許堪稱人類鍛造出的最漂亮的文明,但這和一切死亡之美一樣,它也是一種帶有時間性和不穩定性的創造物。哲學家們必須為填補裂痕作出如此驚人的努力,從這個事實中我們便可看出,生命和理性之間的平衡該是多麼微妙脆弱,而且,它們之間的和諧也不可能是説要就有的。中世紀的和諧是以昂貴的代價換來的。
托馬斯•阿奎那的思想是這種綜合的終極成果,他認為人,實際上是個半人半馬的怪物,一種自然和神學層次之間分割開的生物。就自然層次而言,托馬斯的人是亞里士多徳式的,是一種以理性為中心、以理性靈魂為實體形式的生物。
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裏有一段話,雖然説理性是我們的其正的和實在的自我,是我們個人身份的中心,但身為基督徒的聖托馬斯在評論這段話時,不僅不動聲色,反而還以一種坦然同意這些説法的態度來解説它。

托馬斯·阿奎那,中世紀經院哲學的集大成者
然而,在《神學大全》裏,他反覆地説這種思辨的或理論的理性是人的最高功能,所有別的功能都隸屬於它。誠然,這種理性動物在自然層次上是隸屬於超自然的;但還是通過理性的洞見——屬於上帝的本質——激活並純化意志。這實際上是一種綜合,但是我們已經離開《聖經》的人或早期基督徒的經驗向前到很遠的地步,他們的信仰是被看作某種穿透一個人精神的“內臟”和“腹腔”的東西。
而且,儘管有了這種綜合,儘管有了這樣一個事實:哲學家們到了這個時期已經接受信仰與理性一致這個假定,然而,生命和理性之間的關係這個古老問題仍然沒有消失。它只不過是轉入地下,然後又突然從別處冒出頭來:這次是在意志主義同理性主義之間的論戰中冒出來。
聖托馬斯之後,司各脱及其信徒倡導一種同托馬斯派正相反對的學説,即意志髙於理性的學説。在亳無節制的理性主義時代,這樣一種學説雖説是一種微弱的回聲,卻能使人想起聖保羅吶喊的原始基督教的呼聲,那時,聖保羅説也來到世上,不是要把智慧帶給哲學家,而是要把拯救的意志帶給全人類。
司各脱是個方濟各會僧侶因而也是個奧古斯丁主義者,他也記得聖奧古斯丁《懺悔錄》中的存在主義呼聲。聖托馬斯這位理性主義者竭力論證人身上的理性優先於意志,因為既然我們只能欲求我們所認知的東西,理性就必定決定意志。
司各脱這位意志主義者卻回答道,意志決定理性轉向的理念,因此説到底,它也決定理性終認知的東西。照這樣提出問題,這個問題就像雞和蛋孰先孰後一樣不得解決。
而且實際上,這個理性或意志何者第一位的問題,是哲學中一個很古老又最令人傷腦筋的問題,是隱藏在蘇格拉底不斷追問背後的問題:
蘇格拉底總是問是否真的美徳即知識?意志的所有邪惡都只是無知的形式嗎?或許這個問題必須換個方式提出來所謂思想者是指正在從事思想的具體的的人本身。或許接着這個問題往下走,我們可以從中世紀思想史脈絡中,找到為何啓蒙運動的風吹到英國和比利紐斯山以南,呈現出了不同面貌,工業革命首先從英國,而非葡萄牙和西班牙開始。

毫無疑問,沒有中世紀思辨哲學的滋養,就沒有英國培根爵士的經驗主義和實驗主義的誕生
而且英國在13、14世紀的哲學思想,已經為17、18世紀的實驗科學準備足夠的彈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