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與電腦究竟有多像?——從神經達爾文主義到達爾文機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19-05-17 14:30
撰文 | 顧凡及**(復旦大學生命科學院)**
埃德爾曼(https://s3-media1.fl.yelpcdn.com/buphoto/3tHuhMv3wsCW6AaK-WS8lA/o.jpg)
今年的7月1日是美國生物學家埃德爾曼(Gerald Maurice Edelman)誕辰90週年紀念,而今天(5月17日)則是他的5週年忌辰。縱觀他半個多世紀的科學生涯,前一半貢獻給了免疫機制的研究,其高潮是1972年與英國生物學家波特(Rodney Robert Porter)分享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最後的35年則傾注給腦科學研究,特別是意識研究和神經機器人研究。而達爾文主義的羣體、競爭和選擇思想則貫穿了埃德爾曼的科研始終。本文並非是埃德爾曼的傳記,也不全面介紹他對科學的貢獻,而僅介紹他對腦的一些獨特見解和探索,特別是有關腦與機器的問題。筆者以為其中既有發人深省之處,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值得人們深思。趁此機會,筆者也發表一點個人看法以與讀者共同商討。
神經達爾文主義
在免疫系統中,人們早就知道抗體有一些特別的部位可以與任何外來分子或抗原進行部分匹配,這對免疫防禦至關重要。但是抗體怎樣和抗原匹配?傳統上認為,抗體環繞着抗原摺疊,並且以適當的形式把形成的摺疊保持下來,這是一種“指令性”的理論。埃德爾曼卻發現事實並非如此:變異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抗體,每種抗體都有不同的結合位點。當各種各樣不同的抗體碰到某個外來分子以後,只有那些適合外來分子(抗原)結構的抗體會被選中增生。這和物種進化過程中羣體通過變異和選擇適應環境很類似,雖然兩者在時空尺度上相差很大——他把前者(抗體的變異和選擇)稱為是一種“軀體選擇”。
埃德爾曼在做出這樣的發現之後,開始考慮**腦功能很可能也像免疫機制一樣是作為兩種選擇過程——自然選擇和軀體選擇——的結果而產生的。**人腦是漫長的進化過程中自然選擇的產物,除此之外,腦與神經迴路的結構和功能也可能是在發育過程、後天學習過程中由神經元羣競爭和選擇的結果。這一思考最終轉化為1987年出版的《神經達爾文主義》[1]。這本書剛剛問世就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和爭議。
埃德爾曼認為,達爾文主義的精髓是從羣體的觀點出發去考慮問題:一個羣體中的個體具有各種各樣的變異(即多樣性),這是自然選擇所必需的“競爭”的基礎——自然選擇就是從一個物種羣體中分化出那些能適應環境的個體,並讓它們繁殖下去。要而言之,選擇性系統需要在有各種變異的個體中不斷產生多樣性,按照這些變種能否適應環境進行選擇,並且更多地繁殖(也就是放大)那些更能適應環境的個體。埃德爾曼發現免疫系統是這樣,腦也一樣:每個腦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其個體性和多變性。腦的所有組織層次上都表現出這種多變性,它使腦在面對未知世界的各種信號時,得以選擇和增強那些能使機體適應環境的神經元羣之間的聯繫。他由此提出了“神經達爾文主義”,其主要內容是:
1. 發育選擇
雖然腦的宏觀解剖結構是由遺傳因素決定的,但每一個個體的神經元在突觸水平上相互聯結並組織成功能性神經元羣卻是在生長和發育期間由軀體選擇確定的,處於同一神經元羣中的神經元之間聯繫更強。這個過程使神經迴路產生了巨大的多樣性——沒有兩個人的同一腦區會有完全相同的突觸結構。因其高度的功能可塑性和多樣性,神經元羣能自我組織成許多複雜且適應性強的“模塊”。
2. 經驗選擇
從發生直到死亡,在腦的整個發育過程中,各種各樣的神經元羣中都在不斷地進行着突觸選擇。期間,神經元羣之間的聯繫既可能加強也可能被削弱,並受到“價值”的約束。所謂“價值”,是指動物先天對環境和動作後果的利害判斷。埃德爾曼認為,價值系統是由一些神經迴路構成的,它們彌散性地投射到廣大腦區,並分泌各種神經遞質或神經調質作為價值信號。動物通過其價值系統調整行為、適應環境;價值系統向腦的其他部分發出非特異性的調製信號,從而改變突觸效能以滿足機體的整體需求;主體的行為結果也會不斷修飾這一調製過程。
3. 復饋
復饋是指不同腦區之間不斷進行着的雙向信號交流,由此把這些腦區在時空兩方面關聯起來。復饋使得不同腦區中神經元羣的活動同步化,並把它們綁定成某種整體。因此,復饋是在時空上協調各類感覺事件和運動事件的核心機制。
腦不是計算機
從數字計算機誕生之日起,人們就一直把計算機稱為“電腦”,直到今天也還有許多人認為腦就是一種計算機,只要計算機的運算速度和存儲量足夠,那麼就可以完成腦的一切功能,甚至全面超越人腦[2]。他們忽略了腦和計算機的許多本質差別,所以他們的結論也就有了問題。
埃德爾曼在提出神經達爾文主義之後,就一再指出,腦是進化的產物,是一種選擇系統,這種選擇體現在上面所講的發育選擇、經驗選擇和廣泛的復饋聯結之上。腦有極其豐富的多樣性,從各種層次來説,都沒有兩個腦是完全一樣的;而計算機則是人設計出來的產物,是一種指令系統,同一型號的計算機在結構上完全一樣,邏輯是計算機的主要工作原則。
具體來説,按照埃德爾曼的看法[3],腦和傳統意義下的計算機存在下列差別:
01
沒有兩個腦像同一型號的計算機一樣會完全相同,即使同卵雙胞胎的腦也不會完全一樣。腦中所有的聯結都不精確,都要隨發育和經歷而不斷變化,發育過程和後天經歷都獨一無二地印記於每個腦中,每一天,腦中的突觸聯結都會發生或大或小的變化,所有這一切都有賴於這個腦的特定歷史。這種千差萬別使得每個腦都獨一無二——個體差異並不只是噪聲或誤差,它們會影響到我們記憶事情的方式,也是腦能夠適應將來可能發生的、無數不可預測事件並對其起反應的關鍵因素。
現在還沒有哪一種人造的機器在設計時會把該類機器的多樣性作為一條主要原則來加以考慮。相反,在人造系統中,同一型號的機器,結構都是完全相同的,不同種類結構元件的數量要儘可能少,同一種元件要規範化,並且要儘量減少冗餘。而腦則可以通過許多不同的迴路實現同樣的、或類似的功能,埃德爾曼稱此為“簡併”,這大大增強了腦工作的魯棒性。腦所接收到的信號並不像給計算機的數據那樣精確。腦要依靠其記憶和“價值”對這些信號進行知覺上的分類,也就是把不同的刺激分成一些對其生存有意義的類別。計算機則根據預先規定好的編碼方案把接收到的信號轉換成確切無誤的代碼。
02
腦中存在大量的復饋聯結。在腦內相互聯結的區域之間,不斷髮生着並行的遞歸性相互交換,這些相互交換在時空兩個方面不斷地協調着這些區域的活動。這種相互交換(也就是復饋)不同於單純的反饋,它有許多並行的通道,並且沒有特別的指令性誤差函數。復饋最令人驚異的結果之一,是分佈在許多不同功能區的不同神經元羣的活動能夠大範圍同步。由復饋所聯結起來的、分佈各處的神經元的同步發放是知覺過程和運動過程整合的基礎。這種整合最終導致知覺分類,使得腦為了“適應”,能夠把一個對象或是事件從背景中區別出來。計算機靠的是中央處理器、時鐘和各種算法、指令,來協調功能上分離的各個區域,而腦則並不依靠這一切。
03
在計算機中,存儲(也就是記憶)是把外界信號經過編碼以後一絲不差地寫入到存儲器中,當讀出時又完全恢復原樣,所以存儲的信號是對原信號的一種表徵。但是腦中的記憶是非表徵性的。埃德爾曼認為,在價值約束的條件之下,從外界或者腦的其他部分來的信號,會從現有的大量可能迴路中選取某個迴路,並改變其突觸效能或強度。至於是哪些特定的突觸發生改變,則取決於以前的經驗,也取決於價值系統。當以後“回想”時,不一定得百分之百觸發原先那個迴路,而只要產生與過去類似的反應即可,這就成了“復現”或“不重複做某個智力活動或身體活動(埃德爾曼認為這就是記憶的含義)”的基礎。這種觀點認為,記憶是由所有神經迴路中某些選定出來的子集合的活動動態地產生的。這些子集合是簡併的,也就是説不同子集合可以實現同樣的功能:比較可以發現,不同子集合包含的迴路並不完全一樣;但是激活任何一個子集合,都能夠復現某個特定的輸出。正是由於神經迴路具備這種簡併性,當外界條件發生變化和有了新經驗的時候,特定的記憶就可以發生變化。因此,在一個簡併選擇性系統中的記憶是一種重建而不是嚴格複製。決定記憶分類的並不是預先設定好的某些代碼,而是先前的網絡羣體結構、價值系統的狀態,以及在特定時刻所執行的身體動作。這種記憶方式雖然犧牲了精確性,卻為聯想和創造性創造了條件。
04
腦中存在有一些特殊的有彌散性投射的核團——價值系統。遇到突發事件,價值系統會向整個神經系統發出信號通知;它也會根據個體行為的利害(獎懲)而大範圍地改變突觸強度。獎勵將使動物以後在類似環境下加強同樣的行為,懲罰的作用則正好相反。所以,埃德爾曼認為腦並非圖靈機,這和現在某些人工智能專家的看法正好相反[4]。
如果腦不是一種圖靈機,那麼對它的工作就需要另作解釋。埃德爾曼認為神經達爾文主義就可以給出較好的解釋:腦在進化中由自然選擇(它決定了價值約束和腦的主要結構)產生出來之後,每個個體腦都要經歷軀體選擇。**腦並不受一組有效程序的指導,而是為一組簡併的有效結構所支配。**這種結構的動力學決定了它的相關活動是由選擇引起的,而不是由邏輯規則產生的。與此相反,現行計算機的運作則完全基於邏輯之上。埃德爾曼有一個大膽的猜想:不管是有機體還是將來某一天造出的人造物,一共只有兩種基本類型——圖靈機和選擇性系統。因為只有這兩種基本的思維模式:選擇主義和邏輯——腦和計算機正是這兩種不同模式的典型。
達爾文機系列
雖然腦和傳統計算機(在馮·諾依曼架構的意義下)從工作原理上來説有着本質的區別,但是埃德爾曼相信,按照腦的選擇原理構造出的人工裝置,可以執行腦的某些功能。構造的關鍵在於機器的結構和動力學性質,而並不在於其構成材料。在現階段,用計算機模擬腦的某些局部組織和功能是有可能的。埃德爾曼在晚年建立了一所神經科學研究所,該所研製了一系列稱為“達爾文機”(Darwin series of automata)的仿腦機(brain-based devices, BBDs)——之所以稱為達爾文機,是為了紀念選擇進化理論的奠基人達爾文。
這是一些由計算機“腦”控制的、可以在實際環境中自由行動並執行特定任務的機器人。通過無線傳輸信號,機器人把它的傳感器所接收到的信號傳輸給“腦”,“腦”經過一系列工作之後,再把運動命令傳輸給機器人。一開始,仿腦機中的“神經元”是按照已知的解剖結構聯結成迴路的;但是在和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中,迴路中的神經元之間的連接權重會按照某種獎懲原則發生變化。對每個仿腦機來説,這種變化的模式都是獨特的,因為它們的經歷不一樣。
雖然這些機器還遠談不上有意識,但是它們已經可以不需要明確的指令,而是通過競爭和選擇來實現知覺分類、學習、建立條件反射、學會情景性記憶、並在真實世界中定位和尋找目標[5] 。埃德爾曼的主要目的是用仿腦機來檢驗他對腦工作機制的一些設想,當然他也承認還需要對各種動物做實驗。然而,在同一動物身上很難(甚至不可能)同時(甚至先後)在分子到行為的各種層次上記錄腦和身體的活動,這樣也就很難、甚至不可能發現複雜神經過程和行為所必需的多層次相互作用。而使用達爾文機則可以詳細研究這種跨層次的相互作用,從而幫助我們認識腦的多層次作用及其與行為的關係。
1981年以來,埃德爾曼開發了一系列的達爾文機,開始是一些軟件,從1992年開始構建硬件。達爾文機的控制中樞是根據脊椎動物腦的組織結構建立起來的,它通過經驗進行學習。和傳統的機器人不同,達爾文機是一種“選擇系統(selectional system)”,而不是“指令系統”,也就是説,**它是通過從許多不同的仿真神經迴路中進行選擇來學習的,而不是按照事先編制好的程序指令來工作的。**埃德爾曼等人開發了一系列不同型號的仿腦機,模仿不同腦區的功能,本文只介紹某些典型的型號及其模仿的腦功能[6]。
1. 運動控制和運動
圖1. 達爾文機在路徑中穿行。經過幾次摸索,基於小腦模型結構的達爾文機就可自行學會在複雜的過道中行走而不碰到路邊的東西。[7]
圖1是一個基於小腦模型結構的仿腦機。它根據視覺運動線索,採用預測控制,可以學會在彎曲小徑中穿行而不碰到兩側的交通錐。開始時,它的行為很笨拙,只有碰到障礙物或離障礙物很近時,才觸發紅外傳感器,採取“反射”行動躲開或是停下來;但是在經過學習以後,它靠自己運動所產生的光流信號就可以預測環境,從而使穿行越來越順利[7]。
2. 學習記憶系統
圖2. 達爾文機10號在迷宮中找“看不見”的目標(見左側示意圖)。中間的方框表示迷宮,其右上角的黑圓表示“看不見”的目標,四周的彩色條表示在迷宮四邊牆上顯示的圖形標記,數字表示在四次實驗中,達爾文機(中心的圖標)的四個不同的出發點。實際情形見右側圖。[8]
達爾文機10號(圖2)主要模仿的是腦中一個稱為海馬的結構及其附近的腦結構(圖3),它能模仿莫里斯(Morris)著名的水迷宮實驗:在迷宮中找到目標。
莫里斯的水迷宮實驗是這樣做的:把老鼠放到一個盛滿了牛奶狀液體的池子中,在液麪下隱藏着一個老鼠可以安身的平台,老鼠在亂遊一氣之後,發現這個平台可以休息。池子周圍的牆壁上畫有不同的標記。經過幾次以後,不論在什麼地方把老鼠放入池中,它都會徑直遊向平台。如果破壞了老鼠的海馬,它就再也做不到這一點了。
圖3. 人腦中的海馬結構(來源:http://www.goodtherapy.org/blog/blog/wp-content/uploads/2015/04/hippocampus-female-brain.jpg)
埃德爾曼及其同事在迷宮的牆上塗上不同寬度的色條作為視覺線索。經過一番探索,達爾文機10號從任何起始點都可以憑記憶和牆上的線索直接走向某個隱藏地點(只有當機器正好位於這個地點時才會接收到一個紅外線的獎勵信號,在其它地方用它的“視覺系統”是看不到這個信號的)。如果完成訓練後暗中把平台移走,達爾文機10號會和老鼠一樣,在原來有平台的地點打轉。達爾文機10號的訓練完成後,埃德爾曼可以找到驅動機器運動的神經單位,然後追溯所有神經單位之間相互連接的類型和強度的變化過程,結果發現,可能有大量各不相同的路徑和迴路都能最終驅動10號機走向平台。也就是説,不同的結構可以產生相同的輸出——這正是埃德爾曼曾經對神經系統工作原理做出的猜測:“簡併”。這一研究表明他的猜測很可能是對的,但要做動物實驗卻很難。
3. 價值系統和動作選擇
圖4. 達爾文機7號在撿取頂上有條紋圖形的方塊。[9]
達爾文機7號有20,000個仿真的神經單位和450,000個突觸聯結。它可以在環境中自由行走,避開障礙物,去取它看到的東西。它有兩個攝像機作為“眼睛”和一對微音器作為“耳朵”,在其“手掌”上還有測量電導的傳感器。設計者只在達爾文機7號的“腦”中設置兩條初始“價值觀”:①光亮是好的,②拾取到的物體的表面電導高是好的;其它一切就要靠它自己和環境打交道來獲取了。
當達爾文機7號在實驗室裏遊逛時,它會遇到一些頂上塗有條紋記號或圓斑記號的金屬積木。當它拿起上面有條紋記號的積木時,發現其表面電導高,它就知道這是“好味道”,而如果它取起上面有圓斑的積木,發現表面電導低,它就認為是“壞味道”。這樣它就把“味道”和看到的圖像聯繫了起來,經過多次這樣的經驗以後,它就只靠視覺來拾取有好味道的積木(圖4),這實際上是模仿了操作條件反射。一開始(仿真)神經元是按照已知的解剖結構聯結成迴路的,但是在和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中,這些迴路中的神經元之間的連接權重會發生變化。而對每個仿腦機來説,變化的模式都是唯一的,因為它們的經歷不一樣[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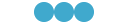
仿腦機的特點是它能直接和環境互動,主動從和環境打交道的過程中進行學習,而不是由程序員規定輸入,也不是由程序員規定每一步動作所需遵循的程序。筆者以為,這些是動物和傳統計算機的實質性區別之一。這種區別就像是隻能由別人放給你看旅遊錄像片和你自己到當地一遊的差異。事實上,即使是人,如果從小就缺乏和環境的互動,特別是與人類社會的互動,就不可能發展出高度的智能。仿腦機在這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儘管取得了這些不俗的成就,埃德爾曼仍舊很清醒。2007年,他説道:
仿腦機依然還只處於它的早期階段。……仿腦機的長遠目標是發展出一種有意識的人工物,雖然機器意識充其量也還只是一種遙遠的希望。我們成功地建造了各種仿腦機,它們有很好的記憶系統,能夠進行知覺分類,在這方面開了一個好頭,如果在十年以前,這會被認為是科學幻想[10] 。
他還説道:
我認為很有可能在將來某一天造出一台有意識的機器。但這還是一個很遙遠的目標,而且即使真做到了這一點,這種機器還是不大可能挑戰我們至高無上的地位。要知道腦必須依附於身體,而我們又身處某種生態龕或文化之中,這很難複製,哪怕只是模仿想[11]。
埃德爾曼希望他的達爾文機不僅有助於闡明神經系統的活動機制,而且有朝一日也可以付諸實際應用。但他在2014年過世,沒有機會看到這一天了。
除了上面介紹的這一系列問題之外,埃德爾曼後半生的腦研究還集中在意識領域,並寫了一系列專著[3,5,11,12,13]。本文篇幅所限,在這裏就不展開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讀一下筆者今年重譯的《意識的宇宙》[3],這是埃德爾曼在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幾點思考
在今天人工智能的熱潮中,人們自然會想到埃德爾曼的這一系列研究和人工智能的關係問題。他的思想對我們有什麼啓發?是不是其中也有可以商榷之處?筆者想就此發表一點管見,和讀者共同探討。
01
其實,人工智能是面大旗,在這面大旗之下,聚集了許多目的根本不同的研究者,他們研究的問題分屬不同的子學科。在這方面,王培教授已經有大量論述[14],他指出:“在人工智能的旗幟下,不同的人實際上在幹不同的事:有構建腦模型的,有模擬人類行為的,有開拓計算機應用領域的,有設計新算法的,有總結思維規律的。雖然這些研究都有價值且有聯繫,但它們不可以彼此替代,而把它們混為一談則容易導致思想混亂。”按照王培的分類,其中的第一派被稱為“結構派”,這一派認為,既然人類智能是人腦的產物,那麼似乎“儘可能忠實地模擬人腦結構”就是實現人工智能的最可靠途徑了。“各種腦模型試圖不僅在細節上(如神經元及其相互聯繫)而且在大尺度上(如層次和區域)都忠實於人腦結構”著[14]。
王培認為,“儘管結構派的理由看上去很有説服力,但在人工智能界只是個少數派。除了其複雜性令人望而卻步之外,這一思路最常被人挑戰的問題是其必要性。人腦作為進化的產物,其結構自然會反映某些歷史的偶然性。作為一個生物器官,人腦結構的生物性特徵對於機電設備來説也未必都有被模擬的必要。即使是在神經網絡模型中,人腦也一般只是被用作靈感的源泉,而非設計的依據。”[14] 筆者以為這些説法很有見地。按照王培的分類來看,埃德爾曼的仿腦機無疑屬於結構派,其研究目的主要是闡明腦功能。當然埃德爾曼也希望把他的研究成果付諸實用,但是否真能得到推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利用仿腦機,埃德爾曼驗證了他的某些假設是否有可能在神經系統中實現(例如簡併),但仿真畢竟只是仿真,只是對假設的支持而非證明——最終的證明還得靠生物學實驗。
02
另一個關鍵問題是腦和計算機的關係。沒有人會反對從腦研究中尋求啓發,以幫助解決工程技術問題。關鍵是,在人工智能的進一步發展中,究竟是必須照搬腦機制來解決問題呢,還是僅從腦研究中尋求啓發,而所用的手段主要還是工程技術手段?筆者的管見是傾向後者。
埃德爾曼所指出的腦和計算機的區別,當然指的是腦和傳統馮·諾依曼架構下的數字計算機的區別。我以為他所講的實質在於腦的多樣性、在硬件上的競爭和選擇。在可預見的未來,機器都不會採取這些作為設計的原則。非表徵性記憶和目前的存儲根本不同,但是如果僅就記憶這一功能來説——而不計聯想和創造——沒有一位工程師會喜歡存儲之物在每次取出時都會改變或重建。另外,在神經科學界,主流見解似乎仍認為記憶是一種表徵。筆者以為,埃德爾曼的非表徵記憶假説對於理解虛假記憶(這是經常發生的)很有啓發。同時,由非表徵記憶方式帶來的聯想和創造,也回答了筆者自己一個長期的疑問:“我們的記憶既然那麼不可靠,那麼工程技術從生物記憶中可以學習些什麼?”目前對此問題的研究還很少,由此還應該思考些什麼,都值得探討。
至於埃德爾曼所講的其他各點,他在世時情況確實大體如此,不過,經過這些年的技術發展,腦與機器的界限多多少少變得不那麼絕對了。比如説,現在計算機的輸入已經不一定要求程序員給出嚴格的代碼了,圖像和語言都可以作為輸入,計算機所接收的信息也不再必須是程序員“喂”給它的了,像達爾文機這樣的機器已經可以主動給自己輸入;雖然現在的計算機還幾乎沒有用到復饋,但是像遞歸神經網絡這樣的軟件已經有了復饋的萌芽;而現在大紅大紫的強化算法則與“價值系統”執行着同樣的原則;甚至軟件上的遺傳算法和進化算法也用到了競爭和選擇的思想。**但這些依然只是原則上的借鑑,而不是細節上的照搬。**在細節上,兩者的差別依舊很大,例如對接收到的輸入信號,現在的計算機極少對多模態信號進行綜合,也不會對其進行知覺分類。主動收集不精確的外界信號也依然只是例外而非常規。當然,人們可以爭辯説隨着研究的深入,這些差別都是可以彌合的。此話雖然從原則上來説是不錯的,但是否實際可行,以及帶來的好處和代價都還是問題。因此埃德爾曼所指出的腦與機器的差別,值得我們深思,對於我們向腦學什麼,以及怎樣學都會有啓發。筆者以為,從實際應用方面來看,必須從工程實現的可行性出發,看腦的哪些原則可以作為借鑑,哪些性質則在目前無法照搬、或解決不了實際問題。現在的自動駕駛汽車並沒有採用仿腦機的路線,用的還是人工智能技術就是一個例子。
03
還有一個反過來的情況:目前的神經科學和認知科學也借用了大量信息科學的概念,如“表徵”、“編碼”、“計算”等。當然,多學科交叉對於打開思路、借用其他學科的成果很有益,但是我們也不能陷入盲目,而應該思考這些概念是否適用於腦,以及適用的範圍。有些概念如“表徵”、“編碼”等在感覺信號接收的早期階段有意義,但是一旦進入到知覺階段,我們感受到的就不再是刺激的表徵,而要加上記憶和價值約束以後的意義。再舉一例,筆者曾經問了許多專家:腦中的“計算”究竟是什麼意思?指的就是數字計算機中所執行的那些操作嗎?如果是的話,腦是如何具體實現這些操作的?如果腦中的計算就是計算機中執行的那些操作,那麼現有的計算機只要加快速度和增大存儲量就應該能執行腦的任何功能,包括創造性和意識在內,這是頗成問題的;如果不是,那麼腦中的計算究竟指的是什麼?有哪些超出圖靈意義下的計算?可惜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人給筆者一個令人滿意的回答。因此,如何恰當使用這些概念也都值得生物學家仔細權衡。
04
關於“機器是否可以有意識”這個問題,埃德爾曼是謹慎的,不過筆者並沒有他那麼“樂觀”。為了解開意識這個“世界之結”,埃德爾曼提出了一個“動態核心假設”[3] :如果腦中有對意識作貢獻的“核心”,那麼組成這個核心的神經元羣必須通過復饋構成一個整體,同時又保持各自的功能特異性,每個神經元羣中的變化都必須也引起核心中其他神經元羣的變化,並且核心的組成部分是隨時間而變化的——這一設定就稱為“動態核心假設”。按照這一假設,該核心就具有埃德爾曼所認為的意識的兩大特性:整體性和複雜性(信息性)。
然而,在這一假設中,他完全迴避了意識最核心的性質:主觀性和私密性——儘管他也承認私密性是意識的主要特點。他所做的計算機仿真或是仿腦機實驗雖然表明人工裝置也能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整體性和複雜性,但是並沒有絲毫主觀性的痕跡。所以他的假設只是意識湧現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近年來人們津津樂道的一些理論——如迪安提出的意識的“神經全局工作空間假設”[15] 、埃德爾曼的合作者託諾尼提出的意識“整合信息理論”[16] ——也都有同樣的問題,都是提出了意識湧現的某些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因此,現在還看不到任何跡象,能在可預見的未來取得這方面的突破。當然,既然作為物理系統的人腦能夠有意識,那麼從原則上來説,有朝一日仍有可能造出有意識的機器。不過,即使真的造出了這樣的機器,人們也依然難於判斷它是否真有內心意識,因為即使是對除了本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動物,也還存在一個如何判斷他們也有意識的“他人心智”的問題呢。因此以筆者管見,談論“人工意識”現在還為時尚早,是否需要讓機器有人工意識也是個大問題。沒有意識的人工智能再強大也依然只能是人類的工具,就像原子能一樣,為善為惡完全是使用者的選擇。只有當人工智能萬一真有了自己的意識,才會發生許多人當今談人工智能色變的危險。
當然,上述僅僅是筆者的管見,像埃德爾曼這樣的智者在其千慮中也可能有一失,而愚者千慮或許也可有一得,謹與讀者諸君共同探討。不管怎麼説,埃德爾曼給我們提出了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無論答案是什麼都對腦科學和人工智能的健康發展會有助益。
致謝
本文最後一節中所思考的觀點,曾和Karl Schlagenhauf博士多次討論。定稿曾請王培教授審閲,特此致謝。
參考文獻
[1] Edelman G. (1987) Neural Darwinism: The Theory of Neuronal Group Selection[M], Basic Books, New York
[2] Kurzweil R (2005) The Singularity Is Near: When Humans Transcend Biology[M], Viking, New York.
[3] Edelman G and Tononi G (2000) A Universe of Consciousness: How Matter Becomes Imagination, Basic Books, New York
中譯本:埃德爾曼和託諾尼著,顧凡及譯(2019)意識的宇宙:物質如何轉變為精神(修訂版)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上海
[4] 尼克(2017)人工智能簡史。人民郵電出版社,北京
[5] Edelman G (2006) Second Nature: Brain Science and Human Knowledge,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6] Krichmar J (2008), Neurorobotics [J] Scholarpedia, 3(3):1365.doi:10.4249/scholarpedia.1365
[7]McKinstry, J. L., Edelman, G. M., and Krichmar, J. L. (2006). A cerebellar model for predictive motor control tested in a brain-based device.[J]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103, 3387-3392.
[8] Krichmar, J. L., Seth, A. K., Nitz, D. A., Fleischer, J. G., and Edelman, G. M. (2005). Spatial navigation and causal analysis in a brain-based device modeling cortical-hippocampal interactions. [J] Neuroinformatics 3, 197-221.
[9] Krichmar, J. L., and Edelman, G. M. (2002). Machine Psychology: Autonomous Behavior, Perceptual Categorization, and Conditioning in a Brain-Based Device. [J] Cerebral Cortex 12, 818-830.
[10] Edelman GM (2007) Learning in and from Brain-Based Device. [J] Science 318:1103-1105
[11] Edelman GM (2004) Wider than the Sky: The Phenomenal Gift of Consciousness [M] Yale Univ. Press, New Haven
[12] Edelman GM (1990) The Remembered Present: A Biological Theory of Consciousnes [M].Basic Books, New York
[13] Edelman GM (1992) Bright Air, Brilliant Fire: On the Matter of the Mind [M] Basic Books, New York
[14] 王培(2015)當你談論人工智能時,到底在談論什麼? [J] 賽先生,2015-08-07 。還有系列文章都可以在他的個人網頁(https://cis.temple.edu/~pwang/)中找到。
[15] Dehaene S. (2014) Consciousness and the brain: deciphering how the brain codes our thoughts. [M] New York: Viking Press.
[16] 託諾尼G.著,林旭文譯. (2015) PHI:從腦到靈魂的旅行[M] . 北京: 機械工業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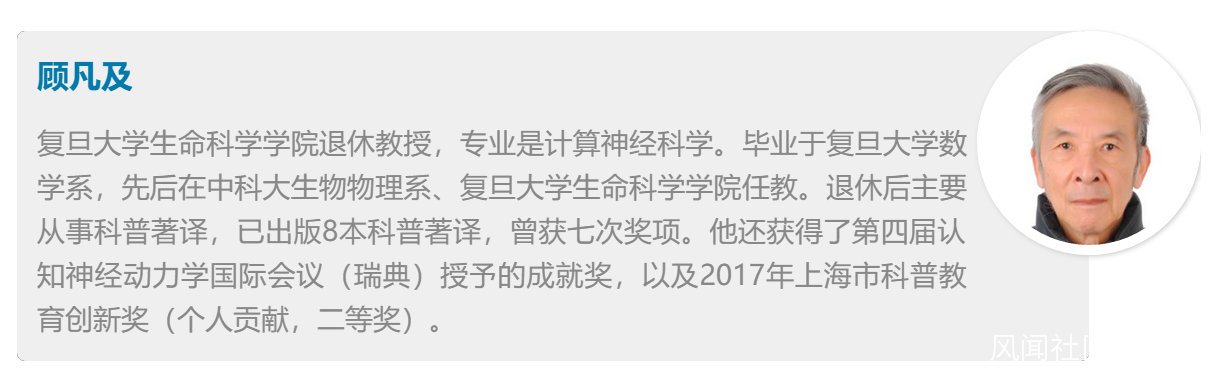
版權説明:歡迎個人轉發,嚴禁任何形式的媒體未經授權轉載和摘編。
《返樸》,致力好科普。國際著名物理學家文小剛與生物學家顏寧聯袂擔任總編,與幾十位學者組成的編委會一起,與你共同求索。關注《返樸》(微信號:fanpu2019)參與更多討論。二次轉載或合作請聯繫[email protected]。
相關閲讀
3 離“缸中之腦”還遠,但離我們的生活很近——八位專家評“復活死亡大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