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食講座二 | 許準:包產到户四十年,中國農村到底變成啥樣了?_風聞
食物天地人-食物天地人官方账号-一个关注三农、食物、性别…众多议题的志愿者网络~2019-05-17 22:47
· 食物主權按 ·
10月13日,在美國霍華德大學經濟系任教的許準老師為我們帶來了一場講座,題為“包產到户四十年,中國農村怎樣了?”。本文是對許準老師講座的文字整理。講座中許準老師通過批判性地分析傳統官方話語對這段歷史的敍述,嘗試為我們還原包產到户政策實行以來的歷史真相:
★ 包產到户這個名詞是怎麼來的?
★ 包產到户有沒有為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做出貢獻?
★ 包產到户是不是農民的自發運動?
★ 包產到户發生的國內國際背景是怎樣的?
★ 為什麼包產到户這場巨大的改革沒有像國企改革一樣遭遇大規模的反抗?

責編 | 侯農 侯戈 人民食物主權志願者
來源 | 人民食物主權
*****
自1978年小崗村的十八個農民按下手印時算起,包產到户至今已有四十年的歷史,但它並沒有離我們遠去,它依舊對中國當下的政治經濟問題產生着深刻的影響。如何看待包產到户關係到我們理解現代中國的基本立場。我先介紹一下自己的思考歷程:在以往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包產到户被表述為中國近現代史中少有的讓人心情愉悦的事件。課本中即便講述到“土改”這類讓人振奮的歷史事件,到最後也總要加上一個所謂“左的錯誤”的評價。在這類話語表述下,包產到户、改革開放擁有着天然的合法性——包產到户好得很!這個“好得很”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農業增產、農民增收,似乎把田一分,大家就自然富起來了;另一方面,包產到户是農民的發明創造,是底層羣眾的呼聲,是政府在不得已的條件下對農民要求的妥協。從高中到大學,這種歷史觀一直主導着我的思考方向。我讀大學的時候,聽過林毅夫的課。林曾在國家農委系統工作,後來在美國讀了博士,他一直鼓吹包產到户這個改革對中國農業生產的貢獻。由於他的文章在國際學界都有很大的影響力,我當時也覺得他的課很有説服力。
然而,後來當我面對現實的變化,包括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羣眾自發的鬥爭等等問題,我開始重新思考這些歷史事件。這些思考導致我在大學畢業之後對毛時代的感情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重要的影響來源於我對韓丁(William Hinton)《翻身》一書的閲讀,後來我把他的書基本上都通讀了一遍。韓丁親身實地見證了中國的土改、文哥(諧音),八十年代之後他又多次回到中國,他對中國農村改革有着非常客觀和真實的評價,這對我的觸動很大。而正是韓丁的書又促使我去閲讀毛主席的相關論著。我的新書《從人民公社到資本主義》(From Commune to Capitalism)只是為毛主席、韓丁的書添加一些腳註而已,他們其實已經將很多基本問題論述清楚了,我所做的只是對一些細節進行補充。

韓丁(右一)在山西張莊與鄉親們趕馬車勞動
圖片來源:映像雜誌新浪博客
包產到户還是包乾(gān)到户?
在正式開始講座之前,我們先辨析一下這次講座的題目,事實上,“包產到户四十年”的説法是不準確的。“包產到户”並非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主線,聯產承包責任制並不必然意味着包產到户。70年代末期,中國農村的改革具有多種多樣的形式,包產到户只是其中的一種,比如當時還有包產到組。所謂包產,指的是生產隊或者更高一級的上級給農户個人或者生產組分配一個生產任務,比如今年要生產一萬斤糧食,生產出來的這一部分交給社裏面,超過一萬斤以外的就可以按照其他方式分配,比如自己拿50%等等。這就是所謂的包產到户,但包產到户的真正問題是——誰來包?從歷史上來看,是農村集體來包,因為很大程度上歷史預設了一個完備的集體經濟的存在。
而聯產承包責任制則是包乾到户(大包乾),也就是將土地分給個人,所有的生產資料都分給個人,沒有任何人下達生產任務,也沒有任何集體協調,説白了就是愛幹不幹全歸自己。有些歷史材料裏面會提到“雙包”,指的就是包產和包乾,但是最終作為一種模式在全國範圍強制推行的是包乾到户。很多人對這兩個概念的理解都存在偏差,我當年在人民大學教課的時候,就跟同學們討論過什麼叫“大包乾”(gān),但很多學生直接就把它念成“大包乾”(gàn)。這麼讀就好像大包乾是一種獨特的生產製度,好像承包了之後就讓你趕緊幹活,生產效率特別高的一種生產製度,但是實際上這裏面的“幹”只是把東西分乾淨的意思。
除了“大包乾”一詞之外,許多學生甚至不少農村研究學者對於“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個概念也存有誤解。他們往往根據教材,想當然地認為聯產承包對應着中國農村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聯產代表着集體、統一,承包的意思則是分到户。但是這個所謂的“聯產”其實是當時的筆桿子在鼓吹改革的時候創造的一個術語,聯產的意思是收入聯繫產量,幹多少就能收入多少。在他們的敍述當中,當時老的人民公社的問題就是不聯產,你的收入跟你的勞動貢獻並不能掛鈎,而他們認為有效的改革方式就是讓收入聯繫產量,建立一套收入聯繫產量、土地承包給個人的生產製度。所以聯產承包責任制跟集體調控沒有任何關係,就是徹底的分田到户。之所以要玩這個文字遊戲,我的猜測是,因為當時宣傳部門希望藉此能跟社會主義扯上一點關係,避免大家的反感。在接下來的講座中,出於大家的習慣,我就繼續使用包產到户的説法,但是大家要知道其實它背後的真正含義是“大包乾”。
包產到户真的能夠解放生產力?
包產到户是不是真正地解放了生產力?對於官方而言,這根本不構成一個問題,因為官方話語將其不加批判地視為一個全新的模式。它不被看作是資本主義的,因為農村土地仍歸集體所有,並非個人所有,而且也不允許土地買賣。然而,現實卻是中國農村正經歷着快速資本化的過程。當下中國農村的生產關係已經跟90年代的完全不同了。根據我的估算,中國目前有四千萬的農業無產者,這是一個龐大的數量。從農村家庭收入來看,中國農村家庭收入的百分之六十都來自工資,已經超過了傳統小農的農業收入。在農村商品化發展起來的領域中,分化的現象也很嚴重,大的農户主導了農業生產流程。比如生豬生產領域,2015年,中國大規模生豬飼養場有90多萬個,這些大的飼養場每年的生豬產量比剩下的4600多萬個小農場的產量總和還要多。換算成比例的話,就是前1%比剩下的95%的產量都要多。這説明生豬生產進入了被大規模生產者壟斷的時代,具有着明顯的資本主義特徵。因此,不管官方如何給農村改革的起點定性,最後產生的結果就是中國農村在往資本主義的方向發展。
雖然官方宣稱包產到户提高了生產效率,但從糧食、棉花、油料等作物的產量統計數據來看,很難看出包產到户有特別的效率。舉一個例子,在從1956年建立起高級社到1980年集體經濟開始被瓦解的這一時期,糧食單產每年平均增加2.79%。而從1984年整個農村改革完成一直到當下的這一段時間當中,單產效率的增長卻是非常緩慢的,單看糧食的話可能年均增長率只有1.3%。如果我們一定要説這個包產到户對提供生產率是有效果的,那麼只能看1980-1984年的數據。在這個時間段內中國農業生產出現了一個驚人的增長,糧食單產每年增長超過7%,即便跟1969-1973年期間年均5%的增長相比也毫不遜色。導致這個增長髮生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呢?如果跟很多國內外學者一樣將其歸因為包產到户,那麼這個論證過程就完結了:包產到户的前四年,中國農業高速增長,原因就是包產到户制度有助於生產力的提高。
然而,有批判態度的人都會質疑這個論證過程的邏輯是否完備。美國學者利斯金(Carl Riskin)在80年代進行的一個研究認為,中國農業在1980-1984年的產量增長是因為1984年徹底取消人民公社,地方上公社時期的糧食儲備一下子被農户瓜分了,而這個被瓜分的部分也被計算進了當年的糧食產量中,所以1984年出現瞭如此大的增長。儘管利斯金的研究也不能被證明為完全正確,但是他啓發我們質疑這種論證邏輯。
從農業的生產條件方面來説,1984年前後許多中國農業的生產條件的確發生了巨大變化:化肥產量翻了一番,化肥質量有了很大的進步,70年代末期雜交水稻的推廣,80年代初期中國農業整體風調雨順,受災面積非常小,氣候條件十分適合農業生產。這些因素都影響着當年的糧食產量。但這裏值得提及的是,化肥的普及與雜交水稻的培育主要依靠的是毛時代的積累。化肥設備是在七十年代初期,中國在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關係逐漸緩和時通過“四三方案”進口的,但到了70年代末期毛主席去世之後,這些設備才真正投產,才開始推動農業生產。我們知道農業綠色革命有三個要素:化肥、良種(對化肥、農藥有反應的種子)以及水利設施。但這生產條件的進步靠的都是毛時代人民公社的積累,只是到了這些積累開始發揮作用促進農業生產的時候,人民公社反而已經被瓦解了。
從生產積極性的角度來説,70年代末期開始,政府大量提高普通糧食收購價格。如果農民生產的糧食超出了上交國家的份額,那麼他剩餘的糧食(“議購糧”,即超出統購糧份額之外的糧食,其價格受市場影響較大)的收購價格被提高了50%,這是非常高的增長幅度。並且,國家同時還下調了農村糧食的統購數量。這最後帶來的結果就是即便你的糧食產量沒有什麼變化,你的收入都會增長;當然,你生產的更多收入自然也就更多了。這是對農民的大規模補貼,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理解為對農民的收買。在農村改革的過程中,隨着糧食的流通越來越市場化,糧食進入流通的份額也在增加。我們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發現,80年代包產到户的過程中,大量因素共同發揮着作用,推動了中國農業產量的提高,因而導致最後很難説清楚到底什麼才是根本原因。
當文字敍述無法解釋這些現象時,我們還可以藉助統計學,當然統計學模型也並不一定能夠給出正確答案。我們前面提到的林毅夫九十年代曾經用統計學方法論證包產到户政策提高了中國的農業產量。他從國家部委拿到了第一手數據資料,瞭解到當時各個省的具體生產情況,包括有多少公社實行包產了,有多少面積,有多少機械、牲畜投入,複種指數是多少等等。根據這些數據,他做了一個統計研究,結論是80年代中國農業生產效率的增長,這其中有一半是包產到户的貢獻。這篇文章奠定了學術界對包產到户的基本理解和定位,這也就是西方媒體常説的中國解決了好幾億人的貧困問題,其中包產到户佔了一半功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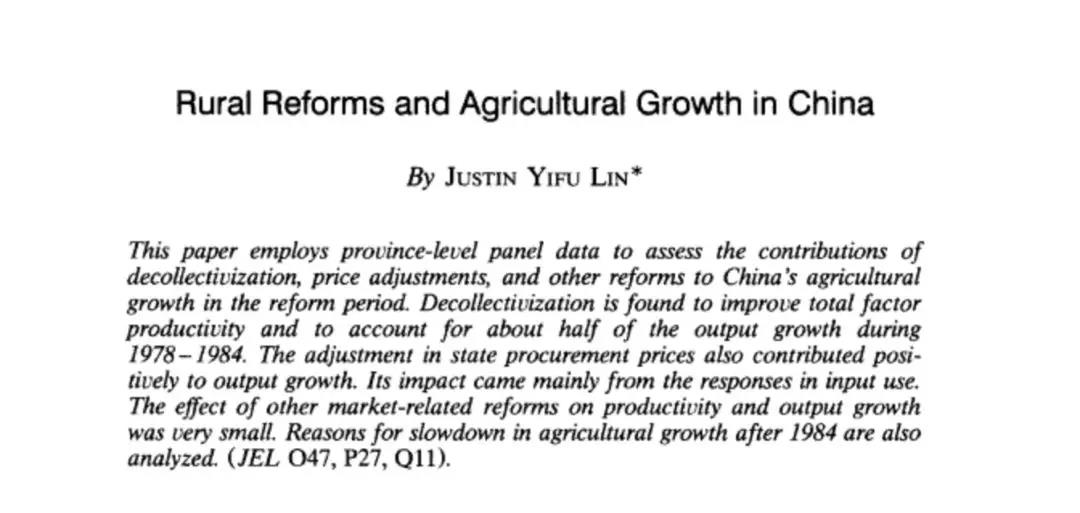
林毅夫著名的論文“中國的農村改革與農業增長”,1992年3月刊載於《美國經濟評論》
圖片來源:www.jstor.org.
不過,如果我們仔細看這篇文章,就會發現其論證過程中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問題之一就是林毅夫使用的包產到户數據本身就是一個有問題的指標。因為按照慣例統計都是在冬天進行的,比如在年末有多少地區已經完成包產到户了。比如,1982年的數據實際是1982年12月31號的統計結果,但是當時很多情況是秋收之後,生產隊才實行包產到户。這意味着,1982年的生產數據名義上是包產到户之後的產量,但是實際上當年1至10月的生產主體卻都是村集體。如果我們將林毅夫的統計數據滯後一年,也就是把1982年12月的統計數字放入1983年的數據裏進行分析,這樣可以確保避免將集體誤認為個人。經過調整之後,最後的結果就會發生變化:模型當中的其他係數、變量、標準差都沒有改變,只有包產到户這一個變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它的係數變得很小,從統計學上説它並沒有發揮什麼作用。我不迷信任何統計模型,但是經過這樣一個簡單的調整,林毅夫的數據結果就消失了,這至少説明他的論證不可靠,我們無法根據這樣一個模型得出“包產到户提高了中國農業的產量”的結論。況且,按照統計結果,真正發揮作用的還是化肥。前面我們已經説過的,化肥生產主要依靠的還是集體時代的積累。
因此,合理的結論應該是:包產到户之後農業增產依靠的還是農業集體時期的遺產,沒有這些積累,所謂的奇蹟不會發生。雖然我們認為包產到户實際上並沒有帶來增產,但這也不排除某些生產隊的個例,可能它就是之前集體經濟搞得不好最後包產到户之後,農業產量真的就突飛猛進了。但是對於人民公社建立得比較好的地方而言,這種情況是不存在的。西方學者Louis Putterman等對河北大河鎮的研究,Chris Bramall對於四川盆地的研究,韓東屏對山東即墨以及黃宗智對長江三角洲的研究中,他們都得出了包產到户並沒有帶來農業生產增長的結論。
包產到户真的代表的是農民的意願?
官方常常將包產到户宣傳成一場自發的羣眾運動,自然而然地推廣到全國,政府似乎處在一種妥協的狀態。這種觀點背後有着這樣的意識形態:市場越自由,效率就越高,農民就越幸福。效率與自由似乎在目前的制度中能夠得以完美的結合。那麼包產到户的過程是不是真如官方宣傳的那樣呢?我可以明確地説,不是。我們只要查閲當時官方出版物,便可以在其中看到這樣的表述,即明確而自豪地宣稱包產到户的改革是在黨的領導下完成的。因此,包產到户從一開始就是自上而下推動的,且具有高度政治化的特徵。
判斷政治化主要有兩個要素。第一個因素是是否存在中央政府、黨組織的直接干預。關於這一點,地方誌的記錄都很直接,那就是一般包產到户開頭是推行不下去的,都是上面來人之後推動才得到執行的。所謂的自發實際上是不瞭解中國政治生態的一種政治想象。第二個因素是包產到户是不是羣眾的自發意願。當時似乎流行過一些民諺,譬如,“上面盼,下面望,中間有個頂門槓”,“大包乾,直來直去不拐彎”。這些都成為當時官方證明包產到户是民眾自身意願的證據。問題是為何每個省都創造出了同樣的民諺?難道全中國農民在創作民諺這件事兒上想到一塊去了?這顯然都是杜潤生所指導的農委秀才們想出來的話,硬生生套到基層農民的身上。這些是政治宣傳的慣例,將中央政策推行不下去的責任推到了幹部的身上。
那麼,是不是基層幹部在阻礙包產到户的推行呢?1980年小平同志直接表示“包產到户要搞一搞”,當中央都明確表過態後,幹部還要對着幹,堅持不搞包產到户的話,這分明就是政治自殺。但感人的是,即便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很多幹部寧願承擔着巨大的風險堅持反對中央的決議。譬如,上海當時明確提出“不分田,不分口糧田,不搞分產單幹”,當然最後被上面批評之後,上海取消了所謂的“三不”。雲南與上海的情況類似,被批評之後緊跟政策,開始搞包產到户。北京的例子更有意思。在人民公社時期,北京、上海的城市郊區,江蘇、東北和新疆等地區的集體建設都發展得很好,因此北京大部分公社是堅持不包產的。全北京只有一個所謂的“冰棍隊”,因為集體經濟搞的很差,沒有做出什麼成就,就在北京率先落實了包產到户的政策,成為了北京包產到户的起點。胡yao邦看到了這個案例後立刻批示:“據我看北京郊區還有些幹部對責任制不通,甚至以各種藉口來抵制,這一定要教育過來。”北京的包產到户是靠着冰棍隊和胡的指示才推廣開來的。還有吉林省,當時吉林也不願意搞包產到户,1980年萬li副總理去吉林視察,在吉林直接説人民公社制度不好,要改革。但是很多吉林的地方幹部都意識到如果搞了包產到户,把大機器、大騾馬、積累下來的家底都分掉了的話,自己所擔負的歷史責任就太大了。很多老黨員當時討論大包乾責任制時甚至表示:“沒有集體就沒有社會主義,不搞社會主義怎麼實現共產主義!”
當時還有一些説法認為,很多幹部反對包產到户,是因為幹部們害怕失去對農民的控制。這些説法是不成立的,因為分掉集體財產對幹部來説是有利可圖的,他們完全可以利用自己在公社時期積攢的人脈關係網絡為自己謀取私利。比如,集體企業私有化過程中,一般都是承包給幹部或其親友,投機的幹部完全可以從中大撈一筆。不僅從經濟利益的角度看是這樣,從政治生涯來看更是如此。比如河北省的白石,在包產到户的時候不過是一個搞農村技術研究的副處級官員,但在這個歷史節點中他寫了一些鼓吹包產到户的文章,迎合了當時的宣傳需要,於是他一路高升,直接升至省委常委,後來他還寫了篇《我從副處級一步跨進省委常委》的文章誇耀自己的這段經歷。這説明跟上形勢的好處是大大的,而中間有個頂門槓的説法是講不通的。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為站出來為反對包產到户的幹部正名,他們的行為邏輯不是私人利益,而是出於對社會主義的情感,他們是在用自己的政治生命做賭注。這樣的例子很多,浙江、甘肅、河南等地都有。杜潤生在自己的回憶錄裏面都曾直白地提到,在很多地方都是胡yao邦這樣的重要高層政治人物親自下去推,甚至直接更換地方領導人才實現包產到户的。
另外,從對集體農業的歷史評價中我們也能發現一些端倪。小平同志在改革初期做了很多次重要的政治講話。在“團結一致向前看,解放思想”這個講話中基本上沒有怎麼提農業,他主要的關注點在城市在工業上。在1981年六中全會形成的第二個歷史決議中,他對文哥進行了徹頭徹尾的批判,但説到這個時期的農業生產時,他的表述卻是“實現了穩定的增長”。在一個總體上很負面的評價當中,這已經是非常高的評價。不過,如果承認了這一時期農業實現了穩定增長的話,那後面很多話就變得不好説了,所以後來無論胡yao邦還是趙zi陽,在十二大做政治報告的時候就改變了口徑,説文哥時期,農業是停滯的,並且將停滯的原因歸結為“左的錯誤”,甚至使用了“極左的錯誤”這種表達,換言之,他們徹底否定了集體農業的實踐。
1984年之後全國農業產量出現了長時間的低迷,直到90年代初期才重新恢復到1984的水平。也就是説,在吹得神乎其神的包產到户真正徹底實行之後,農業產量反倒下降了。在這一現實情況下,官方對集體農業的批判又説不出口了,開始説農業生產的增長還是依靠了之前集體時代的基礎。1989年江ze民在國慶講話上,沒有説“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而是將家庭二字去掉,表述成“聯產承包責任制”。有傳言説小崗村農民集體上書要求總書記把話講清楚,還要不要家庭聯產了,所以後來又改口説“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了。這些都只是故事。今天官方已經不講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了,而是講家庭農場好,土地要適當流轉集中。經過這麼一梳理後,我們就會發現,以前的説法是大農場搞不好,中國農業太特殊只能搞小農場才有效率,但現在這些話官方也不説了,反倒是説大農場也行,土地像公社時期那麼大也可以,但你要在老闆的手下幹,你不能是集體的。這就是政治風向的變化,不過我剛剛描述的只是現象變遷,如果要真正理解這些變化還是需要從具體的政治經濟矛盾入手,尤其是要了解當時的階級鬥爭情況。
包產到户實施前後的國內外形勢

國內:城市工廠改革遭遇阻力
改革初期並沒有把農業作為重點,當時的重點主要放在城市,畢竟按照官方的説法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了,現在的主要任務是實現現代化。這個現代化指的就是工業化,學習的對象是日本、西德。但是工業領域的改革面臨着很多問題,很多地方不是想改革就能改下去。1979年的小説《喬廠長上任記》就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工廠換了廠長,新上任的喬廠長是一位留蘇的技術專家,他的愛人是廠子裏的總工程師,他倆想一起改變工廠的制度,這其中就包括讓一千多個臨時工下崗。他們希望以此提高效率,實現對工人更高的掌控,但這個改革最後陷入了僵局,因為工人羣眾寫信向上級反映,認為這個廠長在瞎搞。這個小説實際上反映了當時以喬廠長為代表的改革派實際上很難再往前走一步。小説的結尾是上級給喬廠長打了電話,表示我們上級支持你的改革,下一個階段安排你出國看一看國外先進的經驗,回來繼續改革。
我們從這個小故事中就不難發現,在經歷了毛時代及文哥之後,城市的工人階級擁有了大量正式或非正式的權力。這時,如果按照城市改革的方案,也就是搞責任制,將權力下放給各個企業,讓各個企業脱離統一的計劃管理,成為相互競爭的關係來搞的話,這個改革實際上是沒有辦法推動下去的,因為這系列的改革需要一個“聽話的”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的力量還很強大的情況下,將權力下放給各個企業本身,最終的結果就是企業只能不停地給工人發獎金,因此80年代早期是工人階級待遇最好的時期。但是這麼做並不能達到中央建立所謂新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目標,反而帶來了很多問題,包括財政問題、通貨膨脹、經濟秩序的紊亂等等。

蔣子龍小説《喬廠長上任記》|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對於當時的政府來説,這些問題都是很棘手的,他們亟需找到一個突破口推動改革開放,這個時候他們很自然地找到的一個點就是農村。相比於城市工業來説,農村確實面臨的問題更多,雖然整個毛時代中國農村的糧食產量增長速度很快,但人口增長得也很快。文哥時期雖然已經有了温和的計劃生育制度,有了各種人性化的宣傳,譬如“一個少了,三個多了,兩個正好”,但由於人口基數很大,導致的結果就是雖然總產量在增長,但是人均產量增長得不快,甚至很多年保持持平的狀態。除此之外,很多地方的農業機械化相當不足,農民無法從繁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但如果具體地去看各個地方的集體化案例,無論是杜潤生還是韓丁做的調查都認同“三分法”,也就是地方上三分之一的公社做得好,三分之一公社一般,還有三分之一的公社不好。這些做得不好的公社就成了可以“突破”的地方。另外還有一個問題,雖然毛時代人民公社在經濟上實現了生產關係變革,但政治上的關係還沒有完全實現社會主義化,人民公社的等級化問題依舊存在。這些因素疊加起來,農村就成為一個可以“突破”的口。此外,為將改革推行下去,政府還藉以提高農產品價格,給農民具體金錢上的優惠等舉措收買農民。我認為,這一系列的做法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自上而下的、有意為之的行為。
在這一過程中,官方對包產到户的宣傳也頗有講究。他們從來不説自己是分田單幹,反覆強調只是對社會主義的改革,依舊屬於社會主義的範疇。針對這一問題,當時《人民日報》就爆發過好幾次爭論,記者吳象(曾擔任萬li的秘書)就説,“當時很多同志提出意見,説包產到户如果搞不好,就會滑向分田單幹,就會倒向資本主義”,他一面説,“這些同志的擔憂是正確的”,但另一面,他只是在抽象的層面上認為這個説法是有道理的,一旦到了具體的問題上,説法就又變成了一定要搞包產到户,包產到户是重中之重等等。這就是當時宣傳的一貫手法。
那麼,包產到户到底產生了哪些政治後果呢?首先,農業生產者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消失了,被打散了的農民已經沒有任何力量可言了。在以前農民羣體還是一個需要被慎重考慮的對象,但是現在農民羣體就已經沒有什麼話語權了。其次,工農聯盟被打破了,農民告別人民公社之後就成為了工人的競爭者,於是作為城市工業改革硬骨頭的工人階級的地位也就發生了變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説,農村改革非常重要,這也是為何官方要將包產到户塑造為農民自發的、純經濟的、代表羣眾呼聲的行為,我認為,這是對他們真正目的的掩飾。
從對農村的直接影響來看,包產到户導致的一個很明顯的趨勢,即城鄉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從八十年代末到現在,城市和農村居民之間人均收入比例一直在上漲,1990年城鄉居民收入比例是2.2,而到了2010年這個比例就到3.1了。據説近幾年數據上已經實現持平了,可能還有一定的下降,但這個我就不太確定了。另外,政府對農村的基礎設施的投入減少得非常明顯。在70年代,政府的農村支出當中有40%的支出用於基礎設施的建設,1990年下降到22%,到了2010年也不過25%,這遠不及集體時代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視。從中央財政對農村的開支來看,下降趨勢也非常明顯。
國際:世界範圍的第三世界國家去革命化的浪潮
包產到户的中國故事並非中國特有,而是過去的一兩百年間第三世界國家普遍經歷的事情。單看二十世紀,從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到六七十年代坦桑尼亞,再到2000年的津巴布韋的土地改革,這其實都屬於同一波的改革。其核心是土地的再分配:把地主等不勞而獲的人的土地剝奪過來,分給實際上在土地上耕種的人,實現耕者有其田,這就是第一波的農村生產關係變化的主線。這是一個將落後的、反動的農村土地生產關係變為現在更進步、現代的農村生產關係的過程。
將傳統的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變成現代的生產關係主要三種歷史路徑:第一個是資本主義的路徑,出現了農業資本家和無產者,形成僱傭關係;第二個是社會主義,搞社會主義集體,大家共同勞動,消除剝削;第三個實現小生產者,也被稱作“第三條道路”,其實質是走民粹主義的路線,這一路線認為農民小生產者本身可以形成一種生產關係穩定下去,既不搞集體,也不會有資本主義的剝削,不存在階級,農民就是農民。這三種觀點在土改的問題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要通過土地革命將舊的土地關係變革掉,但在土地革命之後三派的區別就很明顯了。如果搞資本主義的道路,就要鼓勵土地集中、農民分化、市場競爭等等;如果要搞社會主義,就要像毛主義説的那樣把農民組織起來,一起往社會主義的方向走;如果是民粹派的話,則認為大家都太着急了,最好要等一等再看。
這一類似的局面也曾出現在中國的歷史中。毛時代,毛主席有着明確的進行社會主義道路目標,民粹派也會將土地改革的最終目標設定為社會主義。比如,鄧zi恢就是一個典型,他認為當時推進人民公社的速度太快了,雖然以後的確要搞社會主義,但是這麼快,農民會不認可的。毛主席就批評了他,説他是“小腳女人走路”。劉shao奇就可以算作資本主義這派的一個例子,他認為農村應該扶植富農,發展資本主義可以先把生產力搞起來,當然他對於社會主義也有一個美好的預期,那就是等到資本主義發展起來,我們再把它給剝奪了直接進入社會主義,也就是“豬養肥了再殺”。從五十年代早期一直到大躍進結束之後,搞社會主義的這一派經歷了好幾輪鬥爭,但代表了普通貧農、下中農利益的社會主義這一派在歷次爭論中都可以站穩腳跟,並非因為他們的強大,他們的勝利取決於毛主席、中央層面的支持。然而,到了80年代,走資本主義這一派和民粹派合流,形成合力將社會主義這一派從議事議程上抹除了。我們都知道有這樣的三派:資本主義右派、社會主義左派,民粹中間派。但是到了社會主義這一派被消失之後,學術政治討論中,民粹派好像就成為了左派。80年代之後的語境中,民粹派也不反對資本主義了,認為搞資本主義也可以,但是要注意搞資本主義會遇到的各種問題,強調對農民要温柔一點、人道一點,但這並不妨礙它總體上是認可將經濟制度變成資本主義式的。
在世界範圍內,情況也是類似的。在第一階段,即使美國也會支持世界上其他國家搞土地改革,畢竟這可以避免共產革命。但是到了第二階段,也就是七十年代末期,土地改革就從國際機構的議程中去除了。主流話語強調,只要搞市場經濟就可以很有效率,不需要再搞原來的那套土地改革了,只要有“市場基礎的土改”就可足夠了。毫無疑問,所謂的“市場基礎的土改”實際上就是沒有土改,更不可能有原先土改的進步性。在拉美,我們也可以看到民粹派的興起,他們聲稱自己要搞的是獨特的農民道路,但這背後的實質還是資本主義的大農場,其原因之一也是原來真正左的那一派都被排擠掉了。如果要在中國語境下找對應的人物的話,杜潤生的門生周其仁就是典型的資本主義派,是一個臭名昭著的右派學者;當代左派也成為了民粹主義的代表就是温鐵軍,他既解構現代化大農場,反對搞資本主義大農場,但是也反對搞集體,他認為最好的就是維持現狀,維持他所謂的“千百年不變的小農經濟”。
**為何改革開放時期,**農民沒有形成大規模的反抗?
90年代的國企改革侵犯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在全國爆發了大量的反抗運動。但是為何被包產到户損害了切身利益的農民為什麼沒有站出來反抗呢?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70年代末期的農民羣眾還是相信政府相信黨的,再加上前面提到過的政府強制性執行的手段和對農民的收買措施,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釋這種現象。
但我們還要注意另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雖然人民公社在農業、教育、醫療上取得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巨大成就,人民公社內部依舊存在着自身的問題,這個問題主要又可以分為兩個,一個是經濟問題,一個是政治問題。
首先來看經濟問題,最直接的表現就是農民收入低的問題。當時的農產品收購價格不高,導致很多公社社員一年到頭都看不到現金,到了年終結算的時候,甚至收入還抵不過支出,一直欠着社裏的債。實際上這是中國當時實現資本積累的一個方式,中國要發展必須要有最初的積累。但毛時代的這個策略已經是一種最人道的選擇了。這個問題是容易解決的,只要提高一下農產品價格,減少積累提高消費。因此,農民收入低的問題是能夠得到解決的,而真正不好解決的是政治問題。
這個所謂的政治問題也就是毛主席自己曾經提到過的等級問題:在社會主義工廠和村集體中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還得不到貫徹,如果農民和工人依舊覺得有等級,覺得自己被壓迫剝削的話,那麼社會主義實踐是一定搞不好的。雖然生產資料已經是公有的了,經濟基礎已經是集體的了,但是如果生產關係不配套就會拖累發展。
我曾經採訪過武漢的新四軍老同志古正華,他做過多年農村調查,給我講過一個有趣的例子。在湖北的一個縣,一個生產隊隊長一大早要求一個社員去幾十裏外的地方去修水壩,隊長在佈置任務的時候,這個社員的妻子也在場,向社員使眼色讓他不要去,當時這個社員就不理解妻子為什麼要阻礙他的工作,也就沒有太當一回事,但是在前往水壩的路上,越想越覺得自己妻子的眼神不對勁,他就立刻回家,結果發現隊長強姦了他的妻子。盛怒之下,他把隊長赤身裸體地就綁起來扭送到上級,要求嚴肅處理。然而最終的處理結果卻是上級又把隊長送了回來了,給的理由竟然是因為生產指標還沒有達到,我們一時也找不出能夠取代他的人,我們還需要他,所以還是讓他回來當隊長吧。這個例子説明,在中國當時的環境裏面,公社內部的等級的區分還是很難避免的,這也是後來搞文革的出發點之一。但是文革對這種等級化的生產關係的觸動有多少?有的人很樂觀,認為文化大革命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有的人,包括我自己則認為,這個運動最後只能是“風吹草”,好了一時而已。再舉一例,當時有一個生產隊,一個隊裏的全體領導在社員面前做自我審查報告,社員自由表達意見。但是審查大會開了三天之後,領導説革命已經結束了,我們還是回到日常的生產過程中,一切照舊。至於為什麼文化大革命最後沒有達到最初的目標,這就不是我們這次講座涉及的話題了。
正是因為這些問題的存在讓部分農民對包產到户產生了一種不切實際的想象。似乎包產到户之後,農民就能夠從這種等級關係中解放了出來,再也沒有人對自己指手畫腳了。獲得了自由、“平等”的農民將發揮自己的能動性,提高自己的生產效率。關於這一點,大家可以讀80年代早期的一篇鄉村小説——何士光的《鄉場上》。小説講述的是原來村裏面有個總受欺壓的人物馮幺爸,分田到户之後他覺得自己的腰桿子直起來了,種什麼怎麼種都是自由的,充滿了對未來的美好想象。在當時,這種“包產到户之後,原來公社時期的等級問題就得到了解決”的觀點成為了一種重要的宣傳手法。中央開取消集體農業的會議的時候,杜潤生大談公社造成了不平等,而薄一波明確説農村公社一樣有剝削,言下之意就是把公社分掉就能解決剝削問題了。但從現在來看,公社集體分解之後,權力的分化和等級問題一點也沒有消除,反而越來越嚴重。原來上級最多也就是指示你乾重活,至少雙方在經濟上還是比較平等的,但是現在經濟上的階級分化非常嚴重。所以農村的包產到户並沒有真正解決人民公社時期農村面臨的問題。
問答環節
**問題1:**目前的土地確權問題是中國農民最關心的問題,它意味着農村土地向私有化邁了一大步,有什麼辦法阻擋這個趨勢嗎?
答:首先,“土地確權”(land entitlement)很明顯不是一個漢語常用詞,這是很多國際組織比如世界銀行在發展中國家推動的一個項目。它的理念是要將土地的私有化進行明確。雖然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但是在世界上其他國家尚未有成功的反抗經驗。很多國家的農民是分散的,在國家權力主導執行的背景下是沒有辦法反抗。
**問題2:**講座中提到了大家對人民公社的不滿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生產關係中等級化、不民主,一方面是積累率過高的問題。我想問的是:為什麼有的公社不存在幹部的腐敗問題?有沒有幹羣關係良好的公社的例子?另一個問題是毛時代中國農業的積累率有多少?跟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積累率是不是真的太高了?
答:關於第一個問題,在實際上經濟單位的管理當中,社員並不期待老好人,這樣的人也是搞不好集體的。公社的領導必須要有領袖氣質,有權威、有想法,能夠依賴羣眾,發動羣眾。我聽説過一個小故事,有這麼一個生產隊,之前的幹部特別的腐敗,經濟上多吃多拿,亂搞男女關係,甚至對插隊的女學生動手動腳。他們這個隊搞得是一盤散沙,大家也是出工不出力。後來上面下派了一個新的幹部,這個新幹部堅持每天很早第一個上工,自己賣力幹,主動主持村裏的事情,搶在羣眾面前自己幹,受了他的感染,村子的面貌有很大的改觀。在其他生產條件都沒有變化的前提下,當年產量翻了一番。後來這個幹部生了一場大病,到了縣裏面看病住院,村裏的羣眾都是走了一百里地去看他的。所以説換了一個領導,確實會產生了巨大的作用。
針對第二個關於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積累率的問題,如果看統計數字的話,並不能完全反映出當時的分配的關係。比如説,在基礎設施的建設上,國家並不需要進行額外的分配,完全都是農村自己承擔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的,它並不在積累裏面,但實際上還是靠農村的勞動力的大量累積建設起來的。從這個角度看,公社除了拿到的僅有的一部分收入之外,還承擔了很大一部分基礎設施建設的勞動。80年代之後農村再也做不了大型的基礎設施建設,很大原因就是因為農民已經組織不起來了。如果將其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相比,後期蘇聯的積累和消費比例中是消費的比重更大一些。蘇聯解體之後社會主義僅存的堡壘就是集體農莊,這些集體農莊堅持要搞社會主義。但是實際上在搞社會主義集體化的時候,蘇聯農村是最慘的也是死人最多的,但最後反而又是他們堅持捍衞集體主義制度。
在這個問題上,的確沒有輕鬆的答案可以選。對於我們這樣的落後國家來説,要麼是搞資本主義,少數人富得流油,有一幫狗腿子能夠沾點好處,勞動者勒緊褲腰帶,一代又一代,永無出路;要麼是社會主義,大家都是勞動者,一起過平等的苦日子,而且過了最艱苦的時間,日子會越來好。搞積累吃苦是免不了的,就看是奔哪個前途去了。而且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工業會逐漸反哺農業,這個在毛時代的公社裏面已經能看到了明顯跡象了,比如大量發展的社辦企業等,這些都説明,當時的高積累是必要的,而且是階段性的。
想了解更多?搜索許準老師的新書《從人民公社到資本主義: 中國農民如何失去集體農業併成為城市貧
困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