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中藥的故事和啓示_風聞
diewisch-历史唯物观察者-2019-06-11 07:43
評論裏説我發的話題都是”引戰“,那是當然的,話題性強、要説的話多才有必要單獨發帖。喜歡把人拉黑也沒有説錯,我一直很讚賞B站的會員註冊機制,避免了社區氛圍低齡化。能好好用討論就好好討論,不能好好討論就請離開。我戾氣重,希望討厭的人最好再也遇不到。我也不會迎合某些幼稚言論,也沒想用什麼乾貨拉人氣,帖子沒什麼營養,請有些人把時間用在更有內容的文章裏。
本文討論的依舊是中醫藥如何與現代科學接軌的方法,覺得中醫不是科學,或者不能用科學思維解讀的,可以關閉頁面了。不願意搞懂什麼是“科學”或者“科學思維”的,我發帖子其實都可以不用點進來。
正文開始前先插一段。
大家都學過馬克思主義,其關於真理的論述中有:
真理不是抽象的,任何真理既是客觀真理,又是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具體的統一。
真理是有條件的,任何真理都有自己的特定的對象、範圍和條件,如果超出這一具體規定,真理就會變成謬誤。
真理是個過程,其把真理如實看作是主體向客體、主觀向客觀無止境的接近,而不是一種一經達到便永遠不變的靜止狀態。
有一位中醫師網友告訴我中醫理論是”絕對真理“,是不允許反駁質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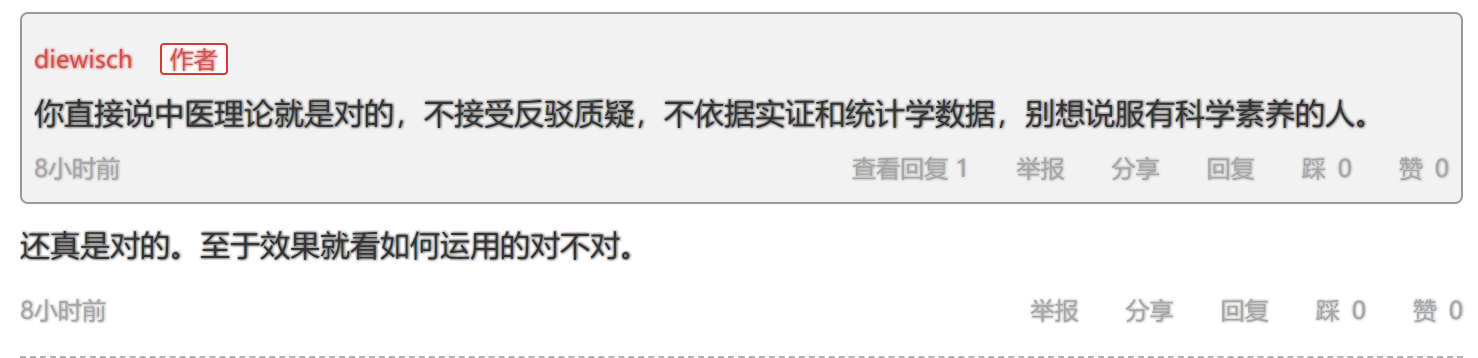
我想起來某些宗教,也聲稱自己在追求“真理”,或者宣稱自己掌握了“真理”。比如“真空家鄉,無生老母”的白蓮教,號稱念上面的口號就能百病不生、逢凶化吉。如果有人問那要是不靈怎麼辦?不靈,就是念的人心不誠,和無生老母沒有關係。中醫效果不好,是醫生水平低,中醫理論是不會錯的。
---------------------------------------------------------------------------------------------------------
古今中外,尋找新藥的途徑有很多種,我挑選了3個有名的中藥故事來談談中藥現代化的話題。
一 雲南白藥的傳説
提起雲南白藥,人們都會知道,這是一種珍貴的藥品,可以治療內傷、外傷、骨折……也可以用它止血。它由雲南民間醫生曲煥章於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研製成功,原名“曲煥章百寶丹”。問世百多年來,雲南白藥以其獨特、神奇的功效被譽為“中華瑰寶,傷科聖藥”,也由此成名於世、蜚聲海外。那麼它是怎麼得來的?這裏有個傳説。
1880年出生的曲煥章,1902年就研製出了百寶丹,那時他才年僅22歲,如此年輕的一個山村郎中是怎樣研製出日後聞名天下的雲南白藥的呢?而那些流傳於街頭巷尾、茶樓酒肆的故事,相對於白藥淵源本身來説,似乎顯得更為神奇。傳説有一天,曲煥章上山採藥,看見兩條蛇正在纏鬥。過了一會兒,其中一條敗退下來。這條氣息奄奄的蛇游到一塊草地上蠕動了起來。此時,奇蹟發生了,不一會兒,蛇身上的傷口變得完好如初。曲煥章等蛇遊走後,拿起那草仔細辨認,他認定這草一定有奇效。於是,綜合民間傳説和自己平時療傷止血的經驗,曲煥章終於創制出了百寶丹。
二 砒霜和雄黃的妙用
在歷代“本草”裏,砒霜和雄黃都是大毒之品,而且二者都是砷劑,古人應該不會想到,當代的幾個中國血液病醫生竟然“化腐朽為神奇”,把它們搬到了現代醫學的舞台,成為戰勝“急性早幼粒性白血病”(APL)的利器。中華醫學會血液分會“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中國診療指南(2018年版)”稱: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APL)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絕大多數患者具有特異性染色體易位t(15;17)(q22;q12),形成PML-RARα融合基因,其蛋白產物導致細胞分化阻滯和凋亡不足,是APL發生的主要分子機制[1,2]。APL易見於中青年人,平均發病年齡為44歲,APL佔同期AML的10%~15%,發病率約0.23/10萬[1]。APL臨牀表現兇險,起病及誘導治療過程中容易發生出血和栓塞而引起死亡。近三十年來,由於全反式維甲酸(ATRA)及砷劑的規範化臨牀應用,APL已成為基本不用進行造血幹細胞移植即可治癒的白血病。
1971年,哈爾濱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的藥師韓太雲下鄉巡迴醫療,發現東北林甸縣一個公社衞生院的一位民間中醫能治癌症,能讓大腸癌、肝癌和食道癌等患者“起死回生”,於是幫他改為針劑(時間是1971年3月,故而命名為“713”針劑或“癌靈”注射液,由砒霜、輕粉、蟾酥等中藥組成)。後來,省衞生廳派以張亭棟為組長的調查隊前去考察,張亭棟與韓太雲從1972年開始合作開展此項研究工作。他們首先從分析砒霜、輕粉、蟾酥的毒副作用入手,對這三種中藥分別在臨牀上進行了對照,做了一定的動物實驗和臨牀觀察,確定治療用量,並對砒霜、輕粉、蟾酥三味藥進行篩選。
張亭棟發現輕粉中含有汞,可影響腎功出現蛋白尿,蟾酥具有升高血壓和強心作用,注射後病人會產生難耐的頭痛,因而把蟾酥和輕粉都去掉了。結果單味藥砒霜的療效並不降低,由於砒霜的主要成分是三氧化二砷,於是就直接使用,效果進一步提高。
1996年世界著名學術刊物《血液學》(Blood)發表了由陳竺和張亭棟撰寫的論文。該雜誌點評認為,這是一篇創造性論著,首次發現氧化砷誘導白血病細胞凋亡,這是繼維甲酸之後,中國學者在血液學研究領域內的又一次重大突破。世界著名雜誌《科學》也發表了題為“古老的中醫學又放出新的光彩”的述評。相關藥品通過美國FDA特批正式上市。
古代醫書《景嶽全書》、《世醫得效方》及《奇效良方》中已經有青黃散的記載。20世紀60年代,血液病專家周靄祥教授就用青黃散(青黛、雄黃)治療白血病,並報告治療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獲得完全緩解,長期存活達20年。其後國內也有報告青黃散治療白血病有效。顏德馨教授1964年報告採用中藥“55”治療急性、慢性白血病26例,“55”方由雄黃等藥組成。
1980年,黃世林教授研製以雄黃為君,青黛為臣的複方黃黛片用於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CR達95%以上,90%以上的患者可獲得長期無病生存,乃至根治。
三 獲得諾獎的青蒿素
傳統中醫理論認為:瘧疾因外感瘧邪、疫瘴濕毒之氣或風、寒,暑、濕之氣,內則正氣損傷而發病。早在《黃帝內經》時代,《素問·瘧論》就對瘧疾的病因病機、臨牀表現都有詳細的介紹,對瘧疾的休作有時、寒熱交替都做了規範性闡述,是後世醫家理論的複製模板。其中,不僅有“夫痎瘧皆生於風”,“夏傷於暑,秋必痎瘧”的經典表述,而且強調常常由於幾種病因(如暑、寒、濕、風)相加而發病。例如《瘧論》謂:“夏傷於大暑,其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水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秋傷於風,則病成矣”;“其間日發者,由邪氣內薄於五藏,橫連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衞氣俱行,不得皆出,故間日乃作也”;“此皆得之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此榮氣之所舍也”;“瘧氣者,必更盛更虛,當氣之所在也,病在陽,則熱而脈躁;在陰,則寒而脈靜;極則陰陽俱衰,衞氣相離,故病得休;衞氣集,則復病也”;“夫瘧者之寒,湯火不能温也,及其熱,冰水不能寒也”。後世醫家又發展了“瘴氣學説”,認為南方山林的瘴毒之氣所致者,往往疾病較重,易於內犯心神及使人體陰陽極度偏盛。如《景嶽全書·瘧疾》稱:“凡往來嶺南之人及宦而至者,無不病瘴而至危殆者也。土人生長其間,與水土之氣相習,外人入南必一病,但有輕重之異耳。若久而與之俱化,則免矣。”
直到1880年法國人Laveran在瘧疾病人血清中發現瘧原蟲;1897年英國人Ross發現蚊蟲與傳播瘧疾的關係,它的真正病因才弄清楚。屠呦呦以及她的工作團隊希望在中國傳統醫學中尋找對抗瘧疾的物質,他們查閲大量古代醫學典籍,察訪民間藥方,拜訪各地在世的老中醫,選出約2千個有關對抗瘧疾的藥方,篩選後集中針對200種中草藥的380個可能藥方研究。
屠呦呦在多種場合表達了她對傳統中醫藥和晉代醫藥學家葛洪的感激之情,她的創造性思維來自於《肘後備急方》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正是其中的“水漬”和“絞汁”讓她琢磨出青蒿素可能不耐熱,只能用低温萃取的想法。
故事的啓示
雲南白藥2002年,想要打入美國市場,向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申請把雲南白藥酊作為膳食補充劑(相當於國內的“保健品”)上市。一種國家絕密級保護產品,卻“屈尊”降格為“膳食補充劑”,公佈披露了其配方,包括田七、冰片、散瘀草、白牛膽、穿山龍、淮山藥、苦良姜、老鸛草等八味藥,但同樣未公開草烏成分。2014年雲南白藥正式承認,其產品配方中含有毒性中藥材草烏(斷腸草)。作為藥物在美國上市必須有臨牀試驗能夠證明其療效和不良反應,雲南白藥並沒有這方面的數據,證明不了,所以只能申請作為保健品上市。
雲南白藥的例子告訴我們,即使在實踐中能證明有效性,依然要弄明白各個成分的作用,搞清楚它的安全性。中藥走出國門,必然要面對顯微鏡的審視。對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質疑,你不能拿出一本藥典一部內經跟別人説:”書上寫的不會錯,雖然有毒但是在這裏沒有毒“。你是解釋還是傳教?不説中醫各學派對經典理論的解讀不同,就是把經典使用的古語翻譯成外語都困難重重,所以最具説服力的還是臨牀實踐數據。但臨牀實踐數據是有標準範式的,要打消別人的不信任,必須要有符合標準的統計學數據。雖然標準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卻是最公正的。
中醫還有一個優勢,不會因為疑難雜症就開不出藥方,比如那位中醫師就宣稱哪怕沒有發現過的病中醫也能治。我們知道治療有安慰劑效應,哪怕給予患者虛幻的治療,只要有治癒的信心,病人也會覺得自己好起來。過去日本醫屆就喜歡搞這套。醫生信心滿滿地告訴病人這個病可以治,就是一種安慰劑。雖然是不治之症,但中醫還是能夠按照君臣佐使開藥方,從概率上説,不治療肯定好不了,能治療至少有了好的可能性。而恰巧,這個藥方有效成分對應病症。《倚天屠龍記》張無忌自己看醫書給常遇春針灸,常遇春傷是好了,但折壽40年。反正”賭一賭,摩托變吉普;拼一拼,吉普變馬丁;試一試,白紙變金錢;賭一賭,摩托變路虎”。
從中藥治療APL研究過程來看,中藥的君臣佐使也並不一定都是合理有效的。本來,用中藥複方或者辨證論治治療疾病,是中醫的臨牀特色,但是如果在科學研究上(特別是臨牀研究)仍然採用複方或辨證論治,卻只能驗證複方的臨牀療效(嚴格地説也很難做到)或者探討治療機制,卻難以進一步提高療效。科學研究的目標和結果都是精細化、精確化,對於臨牀醫學而言,最重要的進步是對療效的提高,而不是堅持特色。有些中醫大家認為,到了現代,化學發展到可以提取和分析各種組分後,就逐漸瞭解了各種化學藥的療效、病理、作用機制,已經完全可以取代所謂“四氣五味”、“寒熱温涼”、“君臣佐使”的類比推理和模糊分類。類比推理的邏輯學遠遠不及歸納法和演繹法,其模糊性和或然性仍然需要進一步的實驗求證,並不能直接構築科學理論。如果堅持“複方道路”,即使我們可以確定複方的療效,如果不去尋找是那種組分或單體在起作用,如何進一步探討有效藥物的血藥濃度及其量效關係,就無法將臨牀療效進一步提高。
青蒿與治療瘧疾有關的記載不多,《本草綱目》稱其“治瘧疾寒熱”;《本草新編》謂之“退暑熱。”據《中藥學》教材,它的其他功用是清透虛熱,涼血除蒸,而且苦、辛,寒,歸肝、膽經。屠呦呦研究青蒿素的過程是對傳統中藥理論的一種否定和遺棄。如果屠呦呦仍然拘泥於傳統中醫理論的認識,就不會採用鼠瘧疾模型篩選藥物,也不會看到《肘後備急方·治寒熱諸瘧方》的“青萬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就靈機一動採用乙醚提取青蒿素。事實上,科學創新就意味着突破傳統理念,採用新理論、新技術從而發現新事物、新規律。中藥研究,可以採用“拆方”的途徑,分析中藥複方起效的化學成分,在化學成分明晰的前提下探討臨牀療效的進一步提高的途徑(如血藥濃度與量效關係、藥代動力學、生物合成方法等等),着眼於尋找新的疾病干預的高效化合物。屠呦呦發現了青蒿素、張亭棟發現了三氧化二砷,他們的成果並且連連獲獎,證明了這一方向大有可為。
這裏在插一句,在我寫文過程中,中醫師對屠呦呦和中醫治療瘧疾發表了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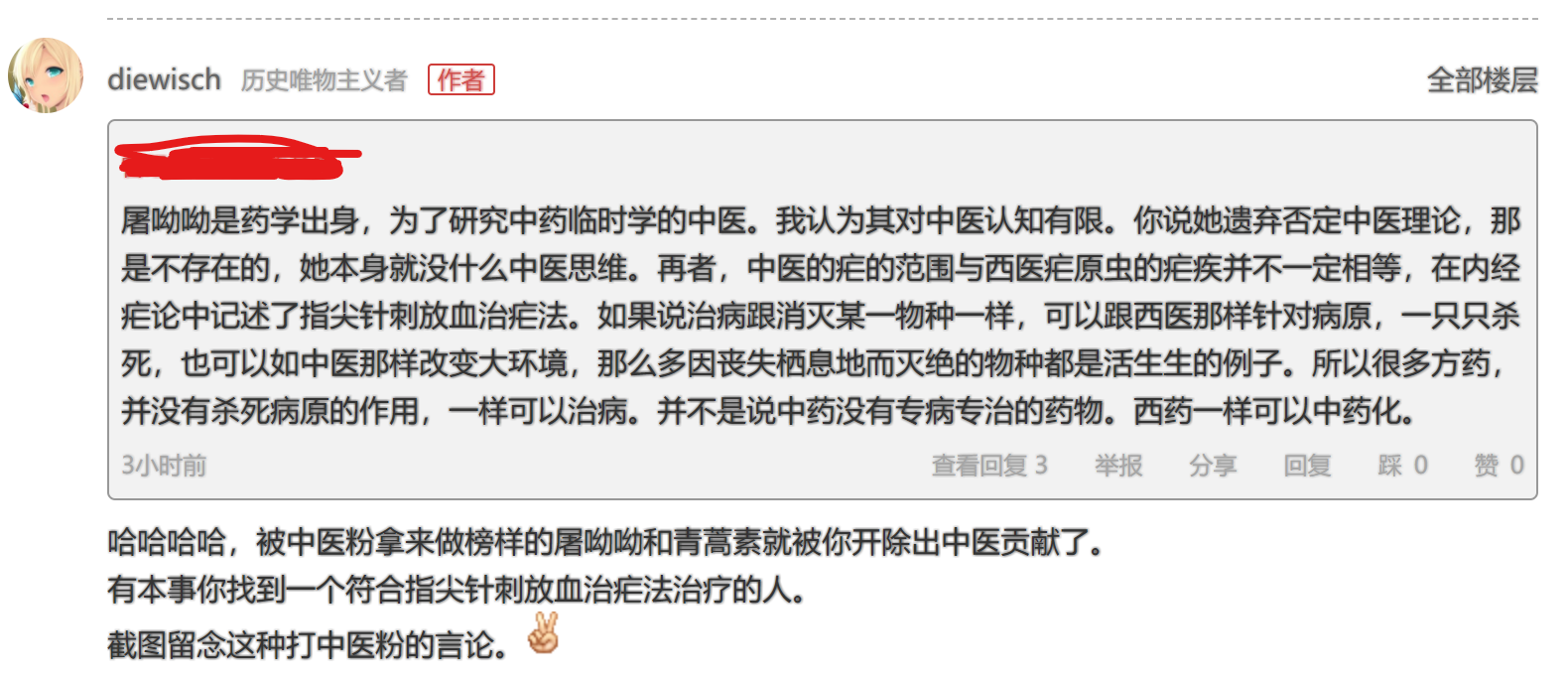
下次看中醫粉拿青蒿素和屠呦呦為中醫辯護,可以説職業中醫從業人員認為青蒿素和屠呦呦與中醫無關。快雪時晴網友評價“中醫碰瓷西醫”,也是有那麼點道理。
一點思考
已故的中藥藥理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李連達,曾給出中藥研究的三部曲,
第一步是:證實該方(或製劑)是否安全有效?可用於臨牀?
第二步是:研究什麼成分有效?
第三步是:研究為什麼有效(作用機制)?
全方研究是第一步研究,確認該藥是否安全有效?通過系統藥理、毒理及初步臨牀觀察,初步確定是否可用於臨牀,值得進一步研究,再進行後續研究。拆方研究是第二、三步研究,研究其有效成分及作用機制,在全方研究之後再進行拆方對各單味藥、各組分、各成分進行研究。在研究有效成分的同時,對各單味藥、組分、成分及不同配伍的藥理作用及作用機理進行研究。
大家是相信按照以上步驟研究的中藥,還是相信那位中醫師網友的按照藥典直接開方的中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