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寶國:東晉南朝的士族子弟也有不少窮人_風聞
瘟疫公司搬砖部-最近在看《宋案重审》2019-06-12 01:15
在東晉南朝史籍中,常常可以看到“少孤貧”的記載,其中不乏士族子弟。《晉書》卷九二《袁宏傳》:
侍中猷之孫也。父勖,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
《宋書》卷七三《顏延之傳》:
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含,右光祿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
《宋書》卷七七《顏師伯傳》:
琅邪臨沂人,東揚州刺史竣族兄也。父邵,剛正有局力,為謝晦所知。……值晦見討,晦與邵謀起兵距朝廷,邵飲藥死。師伯少孤貧,涉獵書傳,頗解聲樂。
《宋書》卷九三《王弘之傳》:
琅邪臨沂人,宣訓衞尉鎮之弟也。少孤貧,為外祖徵士何準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並貴重之。晉安帝隆安中,為琅邪王中軍參軍,遷司徒主簿。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為烏程令,尋以病歸。
《梁書》卷一四《江淹傳》:
濟陽考城人也。少孤貧好學,沉靖少交遊。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
《梁書》卷三六《江革傳》:
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尚書金部郎。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興吾門。”九歲丁父艱,與弟觀同生,少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勖,讀書精力不倦。
《陳書》卷三四《顏晃傳》:
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嘗使於府中,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尚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答曰“猶當少於宮中學士”。當時以為善對。
類似的記載還有,如《梁書》卷二六《傅昭傳》:“晉司隸校尉鹹七世孫也。祖和之,父淡,善三禮,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劉誕,誕反,淡坐誅。昭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者,宗黨鹹異之。十一,隨外祖於朱雀航賣歷日。”這裏雖然沒有用“少孤貧”三字來形容傅昭,但實際上他也屬於此類。
南朝著名詩人顏延之因為家境清貧,30歲還沒有結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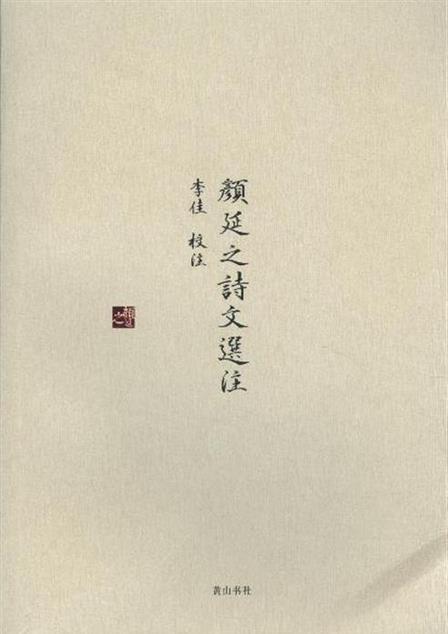
為什麼會有這樣多的士族子弟都是“少孤貧”呢?這首先是與當時人的壽命有關。從史料上看,當時不少人的壽命只有四、五十歲。南齊蕭嶷臨終時召子子廉、子恪説:“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幾何。”[1]蕭嶷病逝是在永明十年,年僅四十九歲。任昉,齊時與蕭衍同為“競陵八友”,卒於梁時,也是年僅四十九歲。“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沈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2]當時人也意識到南方人壽命不長。《南史》卷六二《顧協傳》:“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也。……張率嘗薦之於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為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便稱敕喚出。’於是以協為兼太學博士。”
三十多歲就“已老”,四十多歲就去世了,後代自然就會“少孤”,如任昉,“及卒,諸子皆幼”。[3]但是何以會一“孤”即“貧”呢?這又與家庭的經濟狀況有關。
通常認為,永嘉之亂後南遷的僑姓士族在江南廣佔土地,建立田園別墅,經濟上很富足。但是這個看法其實並不完全符合實際。《晉書》卷七四《桓衝傳》:
初,彝亡後,衝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温乃以衝為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為質,幸為養買德郎。買德郎,衝小字也。及衝為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衝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
《晉書》卷七五《王湛傳附王嶠傳》:
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為丹楊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
《南齊書》卷五二《王智深傳》:
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莧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其衣食。卒於家。
《梁書》卷四九《袁峻傳》: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
東晉梟雄桓温年少時,曾用自己的親弟弟桓衝換羊肉給母親食用

士族家貧的例子還有很多,不一一列舉。這與我們通常想象的士族多擁有大地產的情形是很不相同的。當時在建康的中央官吏俸祿並不豐厚,嚴耕望發現“自東晉以下,史傳中常見有以家貧為藉口乞為縣令者。晉世,如孫盛、幹寶、羅企生,皆以家貧親老為辭由佐著作郎求補縣令。(盛為瀏陽令,寶為山陰令,企生為臨汝令。)各見本傳。又《李充傳》,為徵北參軍,以家貧苦求為縣,乃除剡縣令。《江逌傳》,為驃騎功曹,以家貧求試守太末令。而《温嶠傳》,子放之,為黃門侍郎,以貧求為交州,朝廷許之。是且以貧求為遠州矣。宋世,如王僧達以家貧求郡,關康之以母老家貧求為嶺南小縣;齊世,如沈衝以母老家貧求為永興令。各見本傳。”[4]當時地方官收入頗豐,嚴耕望列舉有“公田與祿田”、“資給”、“送迎錢”等項。其中單靠“送故”一項,就收入驚人。對此學者多有論述。[5]以家貧為理由求縣令,西晉已有,如胡毋輔之“闢別駕、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6]但大量出現確如嚴氏所説,是從東晉以後才有的。
渡江南來的“朝士”大多居住在建康,除俸祿以外,他們並沒有什麼別的收入。顏之推曾説:“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為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為之,未嘗目觀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7]顏之推自幼生活在南方,他對“江南朝士”的描述不會是沒有根據的。按他説,這些過江的“朝士”多數並沒有土地,而是靠俸祿為生。既然以俸祿為生,則父輩中年殞沒,子弟就很容易陷入“少孤貧”的境地。由此可知,像謝靈運那樣“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者其實是少數。[8]《宋書》卷七一《徐湛之傳》:孝武帝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王僧綽門户荼酷,遺孤流寓,言念既往,感痛兼深。可令歸居本宅,厚加恤賜。’於是三家長給廩。”徐、江、王三人均因捲入政治鬥爭而中年喪命,“長給廩”是個別情況,一般官員死後不可能有此待遇。
“少孤貧”的例子主要出自過江北人,南方本土較少。但也不是絕對沒有,如沈約即是。這是需要解釋的。
《梁書》卷十三《沈約傳》:“少時孤貧,丐於宗黨,得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憾,用為郡部傳。”沈約的例子可能有一些特殊性。他在《宋書》自序中介紹自己的家世説:“史臣七世祖延始居(武康)縣東鄉之博陸裏餘烏邨。王父從官京師,義熙十一年,高祖賜館於建康都亭裏之運巷。”按此,從沈約祖父開始,沈氏這一支就遷到了建康,時間在東晉末。《沈約傳》又説:“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誅,約幼潛竄,會赦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按此,沈約離開建康,“流寓孤貧”,回到家鄉是因為特殊的政治原因。如果一切正常,他應該是一直生活在建康。從“丐於宗黨”一語看,沈氏家族當時在家鄉吳興並沒有什麼家業可以憑藉。他的“少時孤貧”或許可以由此解釋。
《陳書》卷一八《沈眾傳》:“侯景之亂,眾表於梁武,稱家代所隸故義部曲,並在吳興,求還召募以討賊,梁武許之。及景圍台城,眾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京邑。”沈眾是沈約之孫。按他説,沈家在吳興有“家代所隸故義部曲”。這很可能是沈約以後才有的。
沈約家族的事蹟提示我們,江南本地士族與僑姓士族終究有所不同。吉川忠夫曾注意到,侯景之亂後一些南方土著士人回鄉裏避難。他分析説,“大概是因為他們在鄉里擁有某些生活的基礎。”[9]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侯景亂後極少能見到僑姓士族逃難到地方。這些家族大多都是居住在建康。他們在南方是沒有“鄉里”的。因此之故,侯景之亂後他們所受打擊也最大。顏之推《觀我生賦》自注述及侯景之亂説:“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譜》;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10]
二十四史之一的《宋書》作者沈約年少時,曾因貧窮而被族人侮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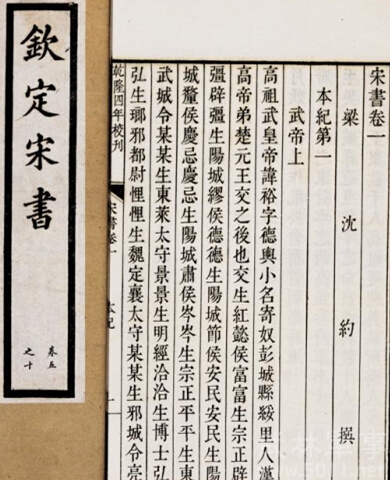
就南朝實際情況看,在維持家族政治地位、社會地位方面,最重要的並不在經濟上是否富有,而在於文化。前引“少孤貧”的南朝士族人物,最後得以進入到社會上層基本都是靠文化。前引江革的例子最具典型性。江革“六歲便解屬文”,其父江柔之“深加賞器”,以為“此兒必興吾門。”類似的例子在南朝很多。
因為文化對於家族政治地位、社會地位的維繫具有重要作用,所以這一時期的一些戒子書都很強調學習的重要。王僧虔在《誡子書》中直言道:“吾不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11]王筠與諸兒書論家世集雲:“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範蔚宗雲崔氏‘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12]《顏氏家訓·勉學》篇:
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曰:“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檐車,跟高齒履,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宴,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揭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以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現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
顏之推親歷江陵朝廷的覆滅,爾後又由南入北,對文化的重要性感觸更多。他親眼見到了“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顏之推所説“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一語極重要。在需要靠文化維繫家族地位的時代,士族子弟卻是“多無學術”。這也註定了士族社會終將難以為繼。從表面上看,南朝史籍中王、謝等一流家族的人物仍然很多。這似乎足以顯示當時士族社會的昌盛。但是,須知經過二百多年的自然繁殖,這些家族人口眾多,與見諸記載人物的相比,未見記載的人物其實更多。見諸記載的,多是在文化上有突出表現的人,這隻能是少數。再往後看,經歷北朝隋代,一直到唐初還有表現的南方士族人物也大都是因其文化上的業績而被記錄下來。
[1]《南齊書》卷二二《豫章文獻王嶷傳》。
[2]《南史》卷五九《任昉傳》。
[3]《梁書》卷一四《任昉傳》。
[4]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387頁。
[5]參見週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送故”條,中華書局1985年版。
[6]《晉書》卷四九《胡毋輔之傳》。
[7]《顏氏家訓·涉務》篇。
[8]《宋書》卷六七《謝靈運傳》。
[9]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220頁。
[10]《北齊書》卷四五《顏之推傳》。
[11]《南齊書》卷三三《王僧虔傳》。
[12]《梁書》卷三三《王筠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