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與李鴻章平分朝政?慈禧向十一國宣戰?這些都是唐德剛的謬誤_風聞
瘟疫公司搬砖部-最近在看《宋案重审》2019-06-22 18:15
文:陳曉平
自1999年嶽麓書社推出了超級減肥版的《晚清七十年》以來,該書被無數名人非名人反覆推薦,儼然成為中國近代史的“必讀書”,唐氏也被捧上了神壇。由於“糖粉”陣容強大,批評的聲音幾被淹沒。雖然唐德剛關於北洋海軍“主炮晾衣”一説,已被海軍史研究者陳悦駁得體無完膚,多數人並沒意識到唐氏治學粗疏,是一以貫之的。從專業角度看,《晚清七十年》可説是浪得虛名之作,硬傷太多,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本文擬引用可靠史料和學界研究成果,略舉數例,暴露唐氏史學功力的不足,讀者自可舉一反三,重估該書實際價值。近幾十年晚清史研究成績斐然,史料整理和考證方面成績更加突出,已非唐氏所能想見。
本文所引《晚清七十年》原文,用的是遠流版五卷本,為免繁瑣,僅注出冊數和頁碼,如第四冊第87頁,注作“四,87”。
“李鴻章是榮祿的政敵,李之下放廣州就是受榮祿排擠而去的”?(四,87)
李鴻章和榮祿的關係,唐德剛並不瞭解。除了甲午慘敗讓榮祿對李鴻章有些微詞之外,從我所蒐集的幾百條榮、李關係史料中可以看出,兩人長期以來私交甚好,政治上緊密合作,互惠互利,理念上大體都屬“洋務派”範疇。
早在光緒三年,榮祿籌設神機營機器局,即曾請李鴻章推薦洋務人才,李也鼎力相助,推薦了著名科技專家華蘅芳。光緒十四年李鴻章在給李經方家信中,特地囑咐兒子去看望榮祿,提醒“葉[榮]仲華交好廿年,晤時問伊腳氣好否,洋醫有效否。爾須稱老伯、小侄,不作官話”。戊戌政變時奏請太后訓政的楊崇伊,既是李鴻章的兒女親家,也是政治盟友。楊崇伊事前專門到天津與榮祿密商。政變後英、日為營救張蔭桓,託李鴻章通過榮祿向太后進言,卒得減罪流放,也可見出李、榮兩人關係非同一般。關於李鴻章外放兩廣總督一事,徐一士在《凌霄一士隨筆》中分析:“當召劉譚來京,兩江總督系以江蘇巡撫鹿傳霖署理,而兩廣總督則特簡鴻章往署。蓋榮祿助鴻章得之,已預為真除地矣。”“百日維新”之前,李鴻章被光緒帝逐出總署,此後即投閒置散,沒有得到任何實缺,此時得授兩廣總督,正是求之不得。江蘇、廣東是富庶省份,晚清官場皆以兩江、兩廣總督為極優之缺。李鴻章本人也感覺到後起滿洲權貴排擠開明漢族大臣,希望離開北京是非之地。這次外放,實是榮祿鼎力相助,唐德剛居然視作“排擠”,真是南轅北轍了。
北京陷落後,榮祿暫駐保定,慈禧曾令榮祿入京作為“會辦全權大臣”參與談判;李鴻章接到榮祿通過袁世凱轉遞的密信,奏請讓榮祿回“行在”當差,一方面可通過榮祿説動慈禧徹底調整政策,另一方面也為榮祿解圍,是“投桃報李”之舉。儘管榮祿在圍攻使館過程中採取“明攻暗保”手法,向使館輸送食品,促成駐京公使與本國通電報,但他手下的武衞中軍畢竟曾參與圍攻使館,使他不適宜出任談判角色。李鴻章這個果敢行動收到明顯成效,榮祿到西安的第三天,清廷即開始大規模懲辦“肇禍諸臣”,將端郡王載漪、莊親王載勳等人革去職爵暫行圈禁。兩人配合十分默契,“政敵”之説,可以休矣!
“李鴻章命于式枚草遺折薦袁世凱代己為直隸總督”?(四,184)
李鴻章臨終推薦袁世凱的神話,只因《李文忠公全集》《文忠公遺集》沒有收錄李鴻章遺折,以訛傳訛達一個世紀。這封遺折,在《西巡大事記》及《一士談薈》一書均有全文,沒有隻字提及袁世凱。袁世凱研究專家劉路生在前人研究基礎上作了嚴密考證,徹底排除了遺折、附片保薦袁世凱的可能。由於李鴻章事先未作安排,臨終時已口不能言,這份遺折是由其幕僚于式枚在李氏去世後草擬的,不是出於李鴻章口授,故《李文忠公全集》編者吳汝綸、《文忠公遺集》編者李國傑不予收錄。在得到李鴻章死訊後二三個小時,諭旨即命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顯示太后此前已拿定主意。如果有太后以外的因素,列強的推崇、榮祿的提攜比較關鍵,盛宣懷也出力不少,與李鴻章沒有絲毫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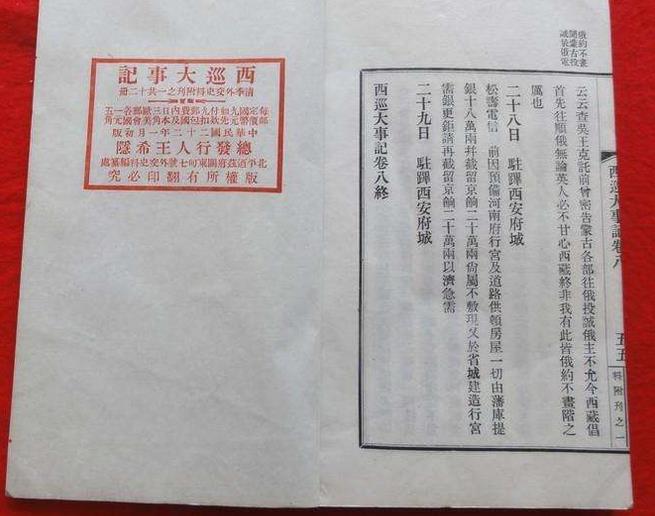
翁同龢****和李鴻章“平分朝政”?
該書第三冊如此談論翁同龢:“在小皇帝日漸長大,垂簾老太后預備‘歸政’之時,同龢正是當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銜的‘協辦大學士’;兩入‘軍機’,兼總理各國事務。他與那時權傾朝野的李鴻章,簡直是平分朝政。”(三,173-174)。
事實是,從來沒有存在過李鴻章和翁同龢“平分朝政”的時期。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李鴻章繼曾國藩之後任直隸總督,後兼北洋大臣,二十多年裏一直是太后深所倚畀的重臣。而翁同龢初入軍機在光緒八年(1882年)十一月,領班的是威望素著的恭親王奕訢,根本輪不到翁氏掌權。光緒十年三月,恭親王和翁同龢等全班軍機大臣同被罷免,醇親王奕譞以皇帝本生父隱執朝柄,以禮親王世鐸為傀儡,以孫毓汶擔任中樞實際辦事角色。直到甲午戰爭爆發,翁同龢再入軍機,十一月奕訢也再次出任領班,翁同龢一直未能掌握中樞大權。次年李鴻章被“留京入閣辦事”,被奪了實權。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奕訢去世,十多天後翁同龢被“開缺回籍”。翁同龢對朝政的主要影響力在財政方面(擔任户部尚書),甲午期間對光緒帝主戰起了重要作用,其他時期和朝政的其他方面,影響較小,實在談不上“平分朝政”。李鴻章長期以文華殿大學士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節制主要國防軍淮軍、直隸練軍,實際主持海軍建設和對外交涉,淮系勢力遍佈各地,論實際權勢,翁同龢望塵莫及。翁開始對大政發生重大影響時,李鴻章很快就成為“空頭大學士”。就算是在翁同龢權勢巔峯時期,軍機處有恭親王奕訢、禮親王世鐸班次在他之前,另有李鴻藻、剛毅等人分薄他的權力,光緒二十一年後軍權主要落在榮祿手上,總理衙門由奕劻領銜。“平分朝政”,從何説起?
“翁同龢是康、梁等激進派的家長與護法”?
唐德剛説太后“首先她就把翁同龢罷官,趕出政治圈。翁是享有‘獨對’之權的光緒帝智囊。他作為享有清望的狀元老臣,也是朝中開明派的班首;更是康、梁等激進派的家長與護法。翁氏一旦被黜,光緒就失去一個首席謀臣、一箇中間橋樑和一個翼護新黨的家長。一箭三雕,翁同龢在六月十五日被‘開缺回籍’。兒皇帝也就被完全孤立了”。(三,232)
康梁流亡海外,為了增強他們在海外華僑界的號召力,將翁同龢尊稱為“維新導師”,此後即以訛傳訛,真相完全被謊言掩蓋。其實只要仔細閲讀《翁同龢日記》,就不會得出這種荒謬的結論。孔祥吉通過核對原稿,已證實通行版的《翁同龢日記》並沒有太多刪改,可以放心使用。
康有為的進用,翁同龢初期出力甚多,但後來感覺康四面樹敵,又開始退縮。正當光緒雷厲風行推行維新事業之時,翁氏這種出爾反爾甚至當面抗旨的做法,令光緒十分惱火。據《翁同龢日記》載,在《定國是詔》頒佈前,光緒傳達慈禧有關變法的指示,是“今宜專講西學,明白宣示”;反而翁氏自己説“西法不可不講,聖賢義理之學猶不可忘。退擬旨一道”。結果,在他起草的《定國是詔》中,將變法綱領調整為“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大大降低了慈禧“專講西學”的激進調門,也顯示了翁同龢的保守傾向。在接待來訪的德國亨利親王時,光緒帝與之行握手禮、賜坐,遭到翁同龢極力阻撓,甚至在接見時大聲呵斥德國隨員,顯示翁氏仍固執“天朝上國”觀念,不願以平等之禮相待。
翁同龢在康有為急需支持的關鍵時刻,堅決與之劃清界線。四月初七日,光緒命翁同龢通知康有為再抄一份“進呈”圖書(《日本變政考》、《波蘭分滅記》之類),翁答:“與康不往來”;皇帝追問為何如此,翁答“此人居心叵測”;皇帝再問“前此何以不説”,翁答“臣近見其《孔子改制考》知之”。第二天,光緒又問康有為進書之事,翁還是説“與康不往來”,導致皇帝“發怒詰責”。翁同龢最初推薦康有為是出於傳統的“自強”動機,也曾欣賞康的才華,但在進一步瞭解康的為人、“託古改制”等離經叛道的想法之後,撤回了對康的支持。將翁説成“激進派的家長與護法”,與史實完全不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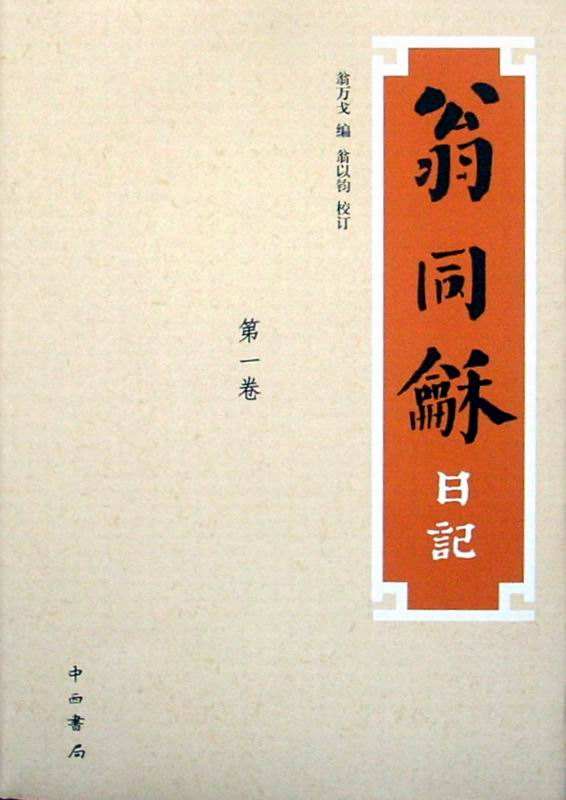
光緒帝罷免翁同龢是慈禧太后逼迫的?
翁同龢因支持維新而被慈禧罷黜,這是康梁流亡海外時有意製造的神話,後來被不少史家全盤接受。但是,早在1957年,蕭公權先生在用英文寫成的《翁同龢與戊戌維新》長文中,即指出:“翁氏小心謹慎的變法路子與光緒無限的狂熱相沖突,光緒準備擺脱當時也已失去慈禧寵信的翁同龢。……翁損壞了多年來他所培養的與光緒之間的信任與融洽的關係。就光緒看來,翁對他不敬是很不好的;但其先鼓勵他變法,讚揚康有為,繼而突然撤回,取消前言,實在令人難以忍受。”蕭公權的研究得到了該領域主要學者後續研究的證實,如吳相湘、楊天石、孔祥吉等。翁同龢罷官出於光緒帝主動,慈禧只是順水推舟。
一般人喜歡用“帝黨”來稱呼光緒帝最信任的臣子羣體。在下《定國是詔》前後,原來帝黨中堅的汪鳴鑾、長麟、志鋭、文廷式等已遭斥逐,朝中主要帝黨人物是翁同龢和張蔭桓兩人,而張有後來居上之勢。張蔭桓因推薦康有為、辦理外交和借款受到持續攻擊,光緒希望翁同龢能站出來維護張蔭桓,翁氏不僅不配合,還極力想劃清與張蔭桓、康有為的界限,目的在於為自己洗刷。
皇帝要他力保張蔭桓,也是為了整個“帝黨”共同的利益,翁同龢的回答是“不敢阿附”,完全失去人臣之禮。以地位來説,張蔭桓僅是侍郎,身為帝師、協辦大學士、尚書、軍機大臣的翁同龢,將“阿附”這樣的字眼用在張蔭桓身上,他對張的嫉妒已顯露無遺。此舉顯示翁氏毫無風度,極端失態,等於譏諷光緒過分寵信張蔭桓,抱怨自己不受重用。
四月初十日,恭親王奕訢薨逝,翁同龢失去了朝中最後一個靠山。二十六日,光緒到頤和園見太后,顯然有所請示;第二天即頒下親筆硃諭令翁同龢“開缺回籍”。清代制度,皇帝“上諭”一般是口述後由軍機大臣傳知軍機章京繕寫,重要機密由軍機大臣親自繕寫,都用墨筆;只有最重要的內容,才會由皇帝親自用專用的硃筆書寫。硃諭中特別提到“每於召對時,諮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無常,詞色漸露,實屬狂妄任性”,這都是皇帝此前召見翁同龢時情景的真實寫照。如果是太后強迫光緒書寫,而光緒依然寵信翁同龢的話,斷難寫得如此具體生動。
榮祿打算“殺袁而並其軍” ?(五,90)
書中對榮祿的描寫很多都純粹出於想象,毫無史料依據,例如説榮祿在光緒二十二年“有心找個藉口,殺袁而並其軍”,簡直就是小説家言。榮祿作為後起“軍事洋務派”代表人物,因國家財力不足,暫時擱置海軍,大力主張用西法訓練陸軍,袁世凱正是榮祿物色到的得力練兵人才。甲午戰敗後,袁世凱得到李鴻藻推薦,先在榮祿負責的督辦軍務處效力,接下來創辦新建陸軍,出任山東巡撫,到繼李鴻章之後出掌直隸,幾乎都是榮祿一手栽培。可以説,沒有榮祿,就沒有袁世凱;榮祿權傾朝野,也得到袁世凱實力的支撐。唐德剛居然想象出榮祿想殺袁世凱這樣的天方夜譚,我就不想再饒舌了。
“告密”辯誣
袁世凱“告密”導致戊戌政變發生,長期以來似乎已成定論。這種説法甚為不妥,完全站在康、梁一方説話。唐德剛也不加分辨地沿用了“袁世凱告密”的説法。站在中立的立場,袁世凱身為前任直隸按察使、候補侍郎、新建陸軍統領,向中央政府報告叛亂密謀,是他應盡的責任。事實上,按照大清律例,任何普通臣民都有報告謀逆密謀的義務,何況他是掌握軍權的二品大員。經過茅海建的精密研究,光緒不認可他本人知悉“圍園錮後”密謀。光緒四歲即入宮由太后撫養,在慈禧積威之下,加之長期以來“以孝治天下”的傳統,不太可能同意這種犯上作亂的激進主張。可以説,“圍園錮後”密謀,是在皇帝不知情的情況下策劃的。袁世凱揭露密謀,本是份內之事,何必一定要用“告密”這種含有貶義的詞語。
“袁世凱那時所統率的‘新建陸軍’七千餘人,兵力為諸軍之冠”?(三,236)
這是治史很不用心的人才會鬧出來的笑話。據台灣學者劉鳳翰的精密研究,當時在京畿地區三大國防軍中,宋慶的毅軍12000人,聶士成的武毅軍15000人,都是經歷過甲午陸戰的百戰之師;董福祥的甘軍12000人,也是長期在西北作戰的勝利之師。此外,直隸淮軍與練軍有26100人,慶親王奕劻統率的神機營19510人,端郡王載漪統帥的虎神營約10000人。僅就人數來説,“新建陸軍”不僅不是“諸軍之冠”,連第5名都排不上。
有人或許會以為,“新建陸軍”雖然人數較少,但經過德式訓練,或許實力最強。這也是極大誤解。“新建陸軍”由胡燏棻初步訓練的“定武軍”改編而成,由袁世凱接手,這支新軍根本沒有實戰經驗,而宋、聶、董三軍都是身經百戰的將領,所部是有豐富實戰經驗的精鋭之師。新建陸軍從來沒有打過什麼硬仗,而聶、宋兩軍在天津保衞戰中曾讓八國聯軍吃盡苦頭。
早在1964年,劉鳳翰《袁世凱與戊戌政變》一書已經刊行;1978年,劉鳳翰又出版了900頁專著《武衞軍》,對榮祿統率下的宋慶、聶士成、董福祥、袁世凱各軍有極為詳盡的研究。劉鳳翰是台灣著名的軍事史學者。以唐德剛和台灣學界的聯繫,這種疏忽絕不應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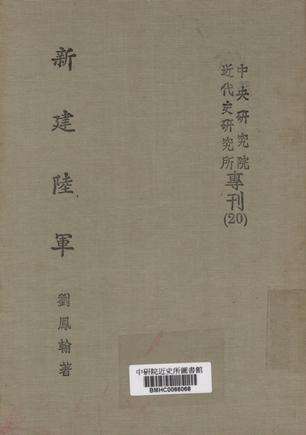
“袁氏在小站防制革命黨滲透新軍”?(五,88-89)
這是典型的“關公戰秦瓊”式笑話。唐德剛説:“袁軍中無日本留學生。其原因蓋有二端。日本軍制原襲自德國。袁軍既亦採德制,延有德國教習……又何須作日本的再傳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學生原為革命之淵藪,為防制革命黨人滲透北洋新軍,乾脆不用留日學生”(五,88)。前半段沒什麼錯誤,後半段就純屬胡説。
袁世凱開始在小站訓練“新建陸軍”是光緒二十一年十月(1895年12月)。這一年雖發生廣州重陽之役,香港興中會人數極少,用的主力是出錢招募的遊勇,孫中山、楊衢雲此時被通緝剛開始流亡,在日本根本就沒有跟留學生接觸。革命黨跟留日學生大規模結合,是1905年日俄戰爭以後的事。況且在光緒二十一年,並無中國學生在日本學習軍事。甲午戰前,清廷派學生到英國學習海軍(嚴復等),到德國學習陸軍(段祺瑞等),當時中國人眼裏哪有日本?中國學生到日本學習軍事,是戊戌前後日本放寬限制、並通過做張之洞的工作而達成的。
“慈禧太后向十一國宣戰”?
1900年列強和清廷開戰,其原因至為複雜。但具體到“宣戰”這個細節,事實是極端清楚的。慈禧太后從來沒有向列強宣戰過。人們可能會説,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不是有個《宣戰詔書》嗎?其實,那天發佈的上諭(“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是頒給國內臣民的。上諭歷數道光以來中國“一意拊循”、洋人“益肆梟張”的事實,關鍵在於指出“昨日公然有杜士蘭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認為是列強“自取決裂”;緊接着頒發的另一道上諭則指出“洋人肇釁猝起兵端”。可見,這個上諭無論如何都不能稱為“宣戰詔書”或“宣戰照會”。第一,上諭認為已經開戰,發動戰爭的是“洋人”,也就是説,這個命令是應戰;第二,上諭明確提到“杜士蘭照會”,明明知道無論是宣戰還是提出要求,在國際慣例上是以照會形式向對方提交的。而這份上諭,從來沒有提交給駐北京或天津的外交官,而是對國內臣民的戰爭動員令。
發佈這個上諭的前提,是雙方已經開戰,即處在實際的戰爭狀態。正如太后五月二十一日御前會議上親口所説:“現在是他開釁,若如此將天下拱手讓去,我死無面目見列聖!就是要送天下,亦打一仗再送!”説雙方此前已處在實際戰爭狀態,有很多證據:一、各國駐天津領事推法國領事為代表,在五月二十日發出“杜士蘭照會”即最後通牒,要求大沽炮台守軍在第二天凌晨二時撤出。這份最後通牒實際上到二十一日清晨五點鐘才到達直隸總督府,而大沽戰鬥已經打了幾個小時。五月二十日,“西摩聯軍”與董福祥甘軍姚旺部在廊坊也已展開激戰。更早一天,天津河東陳家溝洋兵攻擊義和團,“制台竟傳令開炮……水師營開炮幫打。”很明顯,在五月二十五日上諭發佈前的五、六天,已發生中國正規軍與列強軍隊之間較大規模的戰鬥,何勞過了這麼多天再來“宣戰”?這份上諭,只是一份給國內臣民的戰爭動員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