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態”何為?——UNStudio的未來觀_風聞
全球知识雷锋-以雷锋的名义,全世界无知者联合起来!2019-06-30 16:09
作者:孫志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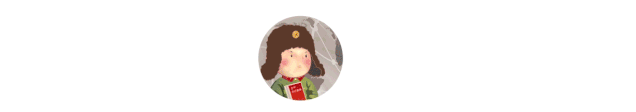
一方面我們學習高度複雜的技術創新,另一方面我們能輕而易舉地引用大量建築學文化,如今似乎“萬物皆可建築學”,從文學到時尚到哲學……
當你前進時物體從視線陸續消失,你漸漸把它們甩在身後,而你自己才是真正運動着的物體。你可以在錯誤的起點進入正確的空間,甚至在錯誤的空間找到合適的位置,建築不斷展開,令你驚喜不已。
導語
本篇講座由AA drl碩士、UNStudio建築師姚遠推薦
“Motto Continued….Future proofing the future(延續箴言…用未來保證未來)”,這是我在2018年7月於上海UNStudio首次見到Ben van Berkel:他身形消瘦,聲音沙啞,完全沒有大師氣場。他闡釋UNSense的主題“Future proofing the future”時説:第一個“未來”是指創造智能未來,後一個“未來”則是未來生活,即UNSense致力於研究未來建築與人的交互——通過在建築設計中植入新科技使它更智能。不論在演講還是評圖,Ben説得最多的詞就是“Healthy Environment”,他説環境包含生活環境和建築系統,而健康環境的關鍵是建築的感官(Sense)能對人的行為(Human Behavior)作出智能的回應……UNstudio近年來項目中對人居環境和綠色建築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Ben於2018年創立UNStudio姊妹科技公司UNSense,目標是在城市領域運用技術干預手段,改善人們的身體、心理和社會健康狀況。
Ben總會選擇更加Bold的big idea、big movement的方案進行深化,例如在某辦公區競賽中UNStudio能拔得頭籌的關鍵就在於為業主設計了全新商業和辦公模式,並將之完美融合進空間。Ben的草圖非常簡略,甚至只有寥寥數筆,正如他評圖也簡短犀利,這意味着他能迅速抓住項目的本質。
Ben van Berkel在上海Unstudio展示UNSense,© 姚遠
UNStudio與其它外企事務所頗為不同——上海和香港分公司是與荷蘭事務所相互獨立的,所以上海和香港UNS雖然時常突破創新,但有時也陷入想法龐雜、翻覆反覆的桎梏。荷蘭事務所每次都會提出大概念,總體邏輯十分清晰;而上海事務所的設計則更為多樣,甚至可能推翻之前的思考,這兩種大相徑庭的工作模式在碰撞中會產生不少火花,這或許是UNStudio命名的由來——通過網絡協作的方式讓各體系產生碰撞,從而迸發新概念。正如斯賓塞·約翰遜所説:“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本身”,這是UNStudio的真實寫照:它始終處於動態之中,就像一個生命力極強的自足物體,不斷吸收建築學以外的知識,並不斷迭代更新。在這種語境下,UNS的作品就不能被冠以簡單的形態特徵,它更像在複雜多元的生態下萌發的新物種。
講座正文
感謝Brett Steele,我每次回到AA總會感到很愜意,因為這房間的所有細節我都記憶猶新。今晚我不會詳述所有項目,而是着重探討一下UNStudio的實踐發展歷程——建築學與實踐之間總會產生對話,保持與實踐的對話是很必要的。我們不斷反思自身,於是得出一個顛撲不破的信條:如果你懂得如何做好設計,並願意花心思自我提升、梳理實踐,你就會勻出更多時間優化設計。
所以我們事務所秉持的信念就是探求設計的源頭和方略、建築的潛在影響、行業的曲折變化……這也是我此次講座標題“動態至關重要(Motion Matters)”的靈感,你或許不認為“動態”有多重要,但它對我意義非凡。無論何時推敲項目,你都會得出物質和思維上的“動態”,“動態”會創造變化,它概括了建築的過去、現在和充滿各種未知的未來,這是實踐建築師無法忽略的。
網絡式工作理念
現在我來談談實踐歷程和網絡式工作理念,在90年代後期我們通過“圖解(diagrammatic)”和“數學模型(model)”的策略來探究合作設計的模式,最近我們開始用“原型(prototype)”來思考了,我們自始至終把“概念模型”的衍變和團隊間的知識共享作為核心主題。這些眾多的原型往往是展廳、傢俱或其它裝置產品,我們會通過創造原型來研究設計。近來我們的重心從網絡平台向搭建知識共享平台轉變,創建了建築可持續性平台(ASP)、空間組織創新平台(IOP)、智能參數平台(IMP)以及創新材料平台(SPP)等主題。
UNStudio創立了四個知識平台:ASP代表建築可持續性平台;IOP代表空間創新組織平台;SPP代表智能參數平台;IMP代表創新材料平台。
在協作過程中磋商的同時我們還要收集知識,這種跨學科的團隊使工作流程高效統一,這種知識交流當然不能侷限在我們這個“所有人都會做設計”的共創型組織內,因為從網絡上還能獲取從工作室和實踐中無法得到的知識。這種知識共享不僅侷限在事務所,我們會篩選網絡上無法直接獲取的前沿知識在建築實踐中發揮作用,這些知識與事務所同期進行的項目實踐是緊密結合的,而非單純的技術交流,所以這不僅能提供足夠的研究基礎以發展出精準的概念模型,而且能更有效地交流相關知識,解決項目深化時遇到的特定問題。
跨學科的影響力
我們主張跨學科交流,與其它學科構建對話,所以你們該能想象曾經我們必須解決兩三個不同領域的難題,如今各種內行專家屢見不鮮,但仍然要求我們在各平台中培養專業技能,這也意味着在實踐中僅扮演建築師的角色是遠遠不夠的,你必須在事務所的工作之外訓練新技能,我們也會成立專門的研究組為設計團隊提供相關研究,或許在幾年的磨練中你發現自己對可持續性很感興趣,你或許會轉入“智能材料組”或“創新項目組”,所以這是一個學習成長的循環,你需要時刻將自己置於實踐中。早在十年前我們就倡導在設計項目時努力拓寬想象力和學科的邊界,一個世紀之前你們還在討論美學和功能主義。我的意思是科學世界中的架構已經完全改變了,一方面我們學習應用系統和高度複雜的技術創新,另一方面我們能輕而易舉地引用大量建築學內的文化特質,當今建築師似乎能引用萬物,“萬物皆可建築學”:從文學到時尚到哲學……因此我想説的是專業的邊界已延伸(elongated)到如此之遠,獲取新知當然是有趣的,但將它們整合到規範系統中更為緊要,最終這種工作模式有利於培養控制我們設計手法的新觀念,所以如果我們與顧問合作、獨立工作或與同事協作,參與度的重要性就愈加凸顯了。
今晚我的討論中最期待建立的對話反而發生在過去,那時的科學家和藝術家們會聚在巴黎或維也納的某家古色古香的咖啡廳一起暢談文學、科學和藝術史,例如這張圖中的維也納的葛林斯德咖啡廳(Café Griensteidl),某科學家或許會和Clint Cearley(20世紀美國插畫家)或埃貢·席勒(Egon Scheiele,20世紀初重要表現主義畫家)探討自然科學,科學家拿着他最新發現的分子圖向朋友們展示,也許Clint就會從圖上的這些分子結構中獲取繪畫創作的靈感。如果你穿越回那個時期,就會發現藝術家的創作都深受科學家的影響。例如貝蒂·弗裏丹(Betty Friedan,美國當代女權活動家和社會改革家)正在撰寫關於女權的理論,Clint或許就開始發表反對意見:“你怎麼可能深刻理解女性呢?你並沒有像我這樣細緻描摹過女性,我才是真正進入女性世界的。你只是作為思考者提出理論,但我作為藝術家更接近女性的內心。”
Café Griensteidl, Vienna
那時的科學家和藝術家會在特定地點產生對話,但今天我們可以擁有全球沙龍,每天從全球各個角落迅速獲取信息,我們甚至可以與陌生的學者們和世界各地的藝術家產生交流。那個時代的魅力吸引我反覆談及上個世紀的藝術家,他們對“某個手勢代表特定的社會禮儀(social code)”的現象很痴迷,例如這幅埃貢·席勒的畫,他並沒有集中筆墨去描繪古典主義的肖像畫,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手勢傳達的意藴遠大於臉部,這幅肖像畫的結構展現的龐大細節甚至表達了比畫作本身更多的涵義。這還不算什麼,當我看完《Wet and Reckless》後,這段歷史開始深深地吸引我的關注——科學家和藝術家在對話中重新審視對方的作品。
Communicating insight, Movements and gestures as social codes,《Self Portrait With Hands on Chest》, 1910, Egon Scheiele,埃貢·席勒作品表現力強烈,描繪扭曲的人物和肢體,主題多是肖像,作品中人物多是痛苦、無助、不解的受害者,神經質的線條和對比強烈的色彩營造出的詭異而激烈的畫面令人震撼,體現出一戰前人們在意識末日降至時對自身的不惑與痛苦的掙扎情感
“原型”與“細節”
當我回顧去年的所有項目,發現我們的作品確實愈發充滿秩序,尤其是我們不再在一個設計裏注入過量野心,而是集中表現幾個主要細節,這使設計更為豐富清晰。其中三四個奇妙的細節讓我記憶猶新,例如這個最新簡潔的傢俱叫做“SitTable”——你既能坐在裏面又能坐在桌旁,它極受初創企業的歡迎,因為它以一抵六——你可以用它來工作、午餐、討論、團隊合作,它更像是一個建築意義的物體,有了它你無須購置其它傢俱了。其實不止是傢俱,我們在展亭設計中也探討了更大尺度的細節與要素,這些都是“原型”和“理論模型”,後來我們稱之為“設計模型”,這些理論模型幫助我們審視設計中的方方面面,工程學會反過來激發建築學的創作,二者相輔相成,這種模式簡直是為我們量身定製的。
“SitTable”,Prooff,2010
我也要討論擺脱傳統的線性(linear)設計思維的方法,如今我們製作模型不需要拘泥於線性了,數字化工具可以激發我們對於空間和功能的想象和洞察力,同時從時間和成本提高建造的可行性,但這不應成為阻礙思考的桎梏。業主也往往對作品有獨特的形體要求,有時必須三個月就要成果。例如要你在伯納姆短期內做一個建築,這時快速想出新形式、蒐集密集的信息、充分整合現有資源顯得尤為重要。
Burnham Pavilion,Millenium Park, Chicago, USA
在這個案例中,窗既是關鍵細節又是建構要素,由於展亭位於芝加哥千禧公園的公共廣場,營造公共空間的同時也必須通過對角線的視線關係來回應“伯納姆規劃”(“伯納姆規劃”正是源於Daniel Burnham和Edward Bennett在1909年做的“芝加哥規劃”)中這座城市的對角線佈局。這種對角線關係從城市衍伸到街道,最後作用在建築的剖面上,在廣場上塑造了全新公共空間。人羣的日常活動對展亭場地的激活不僅發生在白天,夜晚變幻的燈光同樣突出了公共性。
伯納姆展亭夜景,芝加哥
另一個重要細節便是“天花板”,這是我們90年代中期做的位於荷蘭奈梅根的博物館項目Het Valkhof Museum,天花板和樓梯是建築中絕無僅有的重要元素,樓梯指引你通向展覽空間,而天花板則將你的視線引向場址上的羅馬牆壁和廢墟遺蹟,這也是博物館中所展陳的一段歷史的縮影,與考古陳列品息息相關。這裏的天花板不僅承擔着引導視線的功能,它還是地勢在建築中的內在反映,由於起伏的地形在荷蘭並不常見,所以我們對每一米的高差都感到很驚喜。
Het Valkhof Museum, Nijmegen, Netherlands, 1995-1999
你會發現天花板既與地形呼應,又與景觀發生了視線關係,而中央樓梯則是公共建築中聯結不同功能、產生公共活動的關鍵元素。多功能樓梯構成了建築的核心,寬闊的台階既連接了通向二樓的空間,同時將前廳與地下一層展覽區域相互連接,承載各種展示活動。在這個項目中,天花板和樓梯這兩個元素就是重中之重,其中樓梯還承擔着柱子、結構加固、屋頂懸臂的效用。
Het Valkhof Museum底層平面圖,© UNStudio Architecture
雙重解讀
接下來我想談更大尺度的細節,這遠遠不止眼睛所見的“形式”那麼簡單,就像矗立在鹿特丹的這座伊拉斯謨斯大橋(Erasmus Bridge)早已突破了單純功能性建築的觀念,人們常説它的靈感或許源於一隻天鵝、“跪着的人”抑或其它別稱,但對我們來説它的造型參照了鹿特丹海港的魚叉(grain),固若金湯的海港象徵着這座創新型城市曾有的漫長工業化歷史,但是急速擴張的城市化已逐漸侵蝕這一切,將鹿特丹從這段歷史中近乎抽離出來。
伊拉斯謨斯大橋,鹿特丹,荷蘭,1990-1996
這座斜拉索橋以橫跨水面的無比優雅的姿態,連接着鹿特丹城市北部和新興發展的南部Kop van Zuid,從對這座橋的解讀中你可以看出對歷史的雙重理解。我們使用了淡藍色,因為它能吸收天光和環境的光照從而反映出更豐富的色調和明亮的效果,有時它會在陰沉灰濛的天幕下消隱,有時又在日光下熠熠閃光。
我們追求的就是變化,而非重複使用概念模型和元素,在滿足特定項目功能的同時保有“實驗性”和“可操作性”,從而規避一成不變的慣用風格。在伊拉斯謨斯大橋之後我們便開始對材料的色彩與性能進行試驗,同時也將對建築活動的解讀與肖像畫的賞析進行類比,例如這座位於紐約北部的郊區住宅,或許因為業主是酷愛黃金的俄羅斯人,我們對這種概念進行了操作:不止黃金能反射光亮,玻璃也能反射場地周邊的景觀,如果你從落地窗望進去只能見到壁爐的大致輪廓。此時對材料功效的雙重解讀顯得尤為重要,我們稱之為“殘留影像(after image)”,即沒有使人們產生直觀理解的圖像。就像你觀覽了充滿意趣的書或畫作後被深深吸引,我們當然也會產生相似的心境,但如何將這些片刻的想法組織起來,才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材料的二元性
例如這座位於阿姆斯特丹東北部的莫比烏斯住宅(Mobius House)僅用兩種材料建成,我們通過莫比烏斯帶將混凝土和玻璃互相穿插,螺旋交纏的形體使兩種材料忽內忽外地展現出來,這是環境交流、流線演繹、路徑交織、空間重疊、公共與私密混合的概念延伸到材料上的表達。那麼如何處理內與外的關係呢?我們將混凝土結構延伸到建築內部,澆築成了傢俱;玻璃也融入結構之中創造出室內隔斷,引入自然採光,材料的重疊搭接創造了立面的全新形式,微妙地打破了勻質的常態。這也是我們與業主溝通得到的靈感,他不希望行人從外面看到傢俱裝飾與室內全貌,但仍想要留出少許遐想空間與畫面吸引路人窺探的好奇心。
Mobius House,阿姆斯特丹,荷蘭,© UNStudio Architecture
我們創造了內與外、家庭與自然、生活與工作的對話——使用者的流線在兩個樓梯處被扭轉,形成了無限循環的路徑和無盡延展的大空間,自然美景透過玻璃延伸進室內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他們在這個莫比烏斯結構中聚會、起居、工作(人們90年代早期就流行在家辦公了)和休眠,打破了枯燥和靜態的流線,產生了無盡延伸的生活體驗。
Mobius House室內空間
材料的二元性,雙重解讀
所以這種材料效果也與雙重解讀有關,例如開放的結構和立面可以與景觀產生對話,或許這棵樹在鬱鬱葱葱的時節也能與建築短暫地進行對話。像這樣的實驗室建築必須有封閉的空間供特定的科研項目使用,但有些研究也需要公共空間進行交流,因此格羅寧根科研實驗室中心的大空間給了科學家們聚會、暢談、分享最新研究成果的機會。
Interior for Research Laboratory Groningen
大樓梯既是聯通所有空間的樞紐,又可激發社會可持續性,這種手法也延用在我們此後的許多項目中。我們當然也需要電梯,但此建築中的電梯頗難尋覓,這就使工作環境中的人們不得不更頻繁地走樓梯。
Interior for Research Laboratory Groningen
另一個項目場地位於荷蘭Bergen小鎮的近海區域,環境十分怡人。它立面上這種纏繞的(intertwining)形式使我們瞬間想到少女(Sheila)交纏的雙手,開敞的部分也使日光滲透進建築中其它房間。
“虛空間”
梅賽德斯奔馳博物館,斯圖加特,德國,2001-2006,© UNStudio Architecture
如果我要探討想法的把控、新的形式與概念的生成、主要元素的組織以及整合設計的方法,就絕不能侷限於某個轉瞬即逝的點子,其中最重要的一環當然是“虛空間(void space)”。我曾集中筆墨談過不少處理“虛空間”的手法,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當你走進斯圖加特的梅賽德斯奔馳博物館時彷彿走入夢境一般,就像駕駛着轎車環繞着整個空間馳騁,有時你甚至分不清究竟是車在飛馳還是你在移動。
該博物館複雜的幾何構造將結構和設計的組織加以整合,成為了紀念這個傳奇汽車品牌的新地標建築
當你在坡道周圍走動時,可以看到汽車從或高或低、或近或遠、或正或斜地交替出現,你可以通過很高的樓梯進入收藏區,然後會發現自己正處在與汽車等高的位置上。也許在博物館裏被陳列的展品正是作為觀者的你自己,所以你同時處於許多空間之中,這裏引入對“虛空間”的雙重解讀就是為創造一種奇妙體驗——你時刻能感受到公共空間的其它部分,或許是建築中的另一種可能的循環或路徑。
該館基於三葉形,從低層逐漸升高,呈螺旋狀圍繞中心大廳
當你仰頭時無法看清項目的全貌,而拾階而下時便突然發現整個建築的功能與活動像卷軸般緩緩在你眼前鋪展開,三葉草形狀的展覽空間可以帶來全景式的概覽。我們要創造一個能夠激發想象的環境,而不受限於固定領域。通過將作品與附近的其它作品、其所在空間以及外部世界相關聯,能輕而易舉地產生強烈的視覺體驗,例如在這個博物館裏你可以看到汽車以外的東西——看到外面的路和斯圖加特郊外起伏丘陵上的葡萄園。
參觀者們從中心大廳開始,上到頂層,之後走上兩條主要通道,隨着逐漸向下走而按順序展開,© UNStudio Architecture
你會看到虛空間的豐富的肌理和繁複的功能,第二層的光線緩緩滲透過來。傳統公建的空間組織都很難擺脱層級和進深,但在這裏我們思考的是如何整合公共活動,就像你可以順着兩組螺旋坡道走下來,也可以選擇直接乘電梯上去。展開剖面圖中的動線是極其自由的,你可以選擇在兩組交織的螺旋坡道中的任意一組去走,途中隨時改變路線甚至多次折返,可向上也可向下返回至地面,然後繼續行走。當你沿着坡道而下時能真切感受到空間的複雜性和豐富性,當你前進時物體會從你的視線內陸續消失,你漸漸把它們甩在身後,汽車與機器依舊在動,而你自己才是真正運動着的物體。無論何時你都很難知道確切方位,你可以在錯誤的起點進入正確的空間,甚至在錯誤的空間找到合適的位置,建築不斷展開,讓你驚喜不已。
梅賽德斯奔馳博物館流線剖面展開
The Absence
虛空間的肌理也從室內投射到了室外,這也是我們最近做設計頻繁使用的手法——將內部肌理外化。至於如何將文脈投射到建築中,我們也總結了不少參照和經驗,例如當你進入斯圖加特城必然先驅車駛入環形高架,從高處緩緩進入城區,這種日常性的城市層面的動線與這個項目的手法異曲同工。
奔馳博物館一層平面圖
建築的立面絕不是對文脈的簡單呼應,它更像是內部肌理的外部表達,當你俯瞰環繞博物館的高架時,這種場景會喚醒一系列體驗:汽車緩緩駛入建築,再螺旋軌道上展開,好像永遠不會停止。當然它除了滿足功能和回應基地,更是為了解答建築學本身的問題和疑慮,我們過去三十年的建築思考集中在能否用更富動感的造型來替代現代主義方盒子,建築師會用不同語彙來解釋“非線性”,“傾斜”似乎就意味着另類,但我們主張將“傾斜”作為促進流動性、方向感以及人們交流的手段,在牆壁、地板和天花板上設計出一定角度可以更醒目,將分散空間的注意力最小化。尤其在博物館裏重複使用的傾斜元素與曲線元素的結合、傾斜表面與對稱曲線的融合,曲率和傾斜度的融合會產生摺疊的地平面,更能使立面上呈現出深度錯落有致的空間。
當你走進博物館,就會頓覺這些思緒一齊湧上心頭——如何處理建造、功能、基礎設施的聯繫,如何處理光線,如何將文脈反映到概念中,如何處理虛空間……這些虛空間正是我們希望體驗的關鍵所在,因為如今想再去博物館中展陳汽車是十分巨大的挑戰,什麼是汽車?我們把它看作工業產品嗎?就像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懸於大廳的那架直升飛機?它是文化象徵嗎?是藝術作品嗎?在闡述建築時,這種雙重表達被我們反覆追問。
居住與景觀的對話
這種對“虛空間”的處理手法近來也多次被我們化用到城市設計策略中,例如在新加坡有很多讓人大跌眼鏡的有趣的法規和新穎的基礎設施政策,它不僅規定了高層建築的高度和麪積,還要求設計師重點考慮住户們的觀景視野。它在我心裏是最美的花園城市,因為它對景觀的設計已深刻滲入規劃進程中,成為建築環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它們規劃部門所言:將景觀引入建築,使人們生活在景觀裏。這張是我們最近完成的對住區項目的研究,分析了塔樓的視野在不同標高之間是如何變換的,城市中所有的“虛空間”都能被我們察覺,因為每棟建築都有自己歸屬的區域,但它的內部關係未必與城市的組織規劃有關,它們更像是多層建築與周遭環境中固有的自然景觀產生呼應並將景觀的概念。
新加坡住區城市研究
所以Ardmore公寓塔樓底部充分展現了開敞性、貫通性和透明性,通過開放的框架支撐凸起的結構,意在解放地面,有效組織公共便民設施,並將景觀元素融入建築中。如果你想理解這些大玻璃窗與飄窗是如何交織的、建築立面是如何組織的,就需要先了解對景觀的思考在此次設計中的重要性。
Ardmore公寓大樓,烏節路,新加坡,2013
公寓立面上的元素幾乎都由曲線構成,似乎在模仿自然界中的有機體。每户都設有大面積的凸窗和雙層通高的陽台。在室內能夠享受到陽光的沐浴同時欣賞新加坡的城市美景
你站在大窗前,城市的全景畫卷便一覽無遺,雖然户型都是大開窗的通透界面,但陽光並不能直射進房間,因為公寓交織的表皮可以實現持續的日照屏蔽,凸窗為玻璃提供了遮陽,最大程度降低了陽光的熱量。正是出於可持續性的考量,我們對立面的韻律和細節做了特殊設計,虛實相生,各個角度都採用了截然不同的形體輪廓——混凝土板、陽台、凸窗、開洞有機變化。所有的承重結構元素均分佈於建築側邊,而在中間幾乎看不到建造的痕跡。
除了開闊的全景視野和獨樹一幟的立面,我們還設計了大空間。在一年四季的特定時間,你可以打開起居室的窗户,然後穿堂風會從整棟公寓通過(ventilate),帶來混雜青草香氣的清風,雙層通高的大陽台更是加速了空氣的流動。每隔四層重複循環不同角度的立面——陽台和凸窗創造了通透性,混凝土牆面形成了私密性的封閉空間,這些材質的區分也將立面劃分成不同層級,公寓的正反兩面因此形成了鏡像關係。從遠處看,大樓似乎各視角都姿態各異,而當你靠近圍着建築物走動時就會發覺,露台空間與室內日常生活融為一體。
我們使用圓潤的玻璃打造出無柱牆角,在視覺上更為通透,將室內空間和室外陽台、建築與環境相互交融。讓我們回到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項目的建造看似極其複雜,其實我僅使用了17種不同元素並將它們在各方向上進行鏡像變化或扭轉,這些操作就是為了讓建造更便捷,增加可行性,所以這項浩繁的工程很快就落地了。
夜幕降臨時,城市亮起了萬家燈火,你會發現“虛空間”逐漸隱去,城市與公寓間產生了清晰的對話。
我們把從新加坡高層住宅項目中總結出的經驗運用到最近法國經濟適用房(affordable house)的設計中,韓國的這個住宅也是類似的手法:鏡像、元素的重複、循環的規律,我們總共只用了6種元素就產生了這棟公寓形態各異的居住空間。眾所周知韓國的住宅樓幾乎沒什麼識別度,稱謂也往往是數字編號,但我們希望使這片公寓在環境中脱穎而出——它還擁有獨特的樹種與景觀,你甚至可以站在街道上指認出自己家的房間。
Eunma住宅,大峙洞,首爾,南韓
延續性的思考
早先我在談公共建造(Public constructs)時提到過“延續性(Duration)”的想法,也可以換種説法叫做“無限的容量(The capacity for endlessness)”。例如這幅概念示意圖,從睡眠到工作再到起居,這些行為活動在四個象限中相互關聯,反覆循環,生生不息,類似的解讀也在新加坡住宅項目中有所體現。
無限容量,延續性,公共建造
莫比烏斯住宅使用模式
梅賽德斯奔馳博物館的三葉草形的組織模式,這種延續性的概念取材於基礎設施空間的體驗,環繞博物館行走就像駕駛在高架公路般輕鬆自由。這種形式是無限循環的,如果你用筆順着圖案去描畫線條就會發現筆端永遠不會停止。
這裏我不得不再次提到“雙重解讀”,這關乎我們如何理解建築師期冀在設計中創造出的圖景。例如這間位於紐約的閣樓(loft),業主是一位藝術收藏家,他希望永遠與自己的珍貴藏品生活在一起。我和他跋山涉水考察了不少場地,終於在紐約找到了這間閣樓。
Collector’s Loft,紐約
我和他強調了建築中平台裝飾(deck)元素的重要性,例如在立面上打造一塊富有持續動感(dynamic)的陳列畫作的空間,他可以在公寓日常生活的同時展示自己的藝術藏品,我認為這些裝飾框架與藏品本身同樣重要。
延續性的概念或許運用在處理表皮上更合時宜,例如這幅奧地利象徵主義畫家古斯塔夫·克林姆特(Gustav Klimt)繪製的《未完成的一位女士肖像》,如果你把每幅肖像畫的臉部都拆解成黑色和白色的孔洞,那可識別性就會大大降低,我們可以把黑色孔洞理解成“面具”。這與建築的原理極其相似,在開敞空間中你的視線容易被四面八方的扭轉、柔化、彎折的曲面吸引,白牆不再被視為單一表面,黑洞也不再被理解成大空間,但延續性空間依然能打動你,引導你穿過空間的表面。
《portrait of a lady unfinished》, 1918, Gustav Klim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