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萊姆怪,蓋裏的魚,千萬次試錯——第二次數字化革命帶來的設計解放_風聞
全球知识雷锋-以雷锋的名义,全世界无知者联合起来!2019-07-10 23:25
作者:郭璞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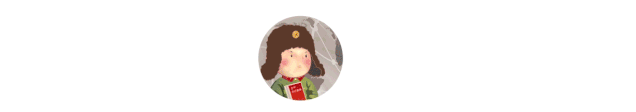
“在結構設計的例子中,試錯對人類來説非常愚蠢,對機器來説卻是非常適用。”
“我們擁有比其他行業更快的即時反饋迴路,我們能更直觀地領會到人工智能遊戲的精神。”
“在某種意義上,使用電腦更接近中世紀而不是現代,這也延續並詮釋了高迪復興中世紀的夢想。”
推薦語
本篇講座由Mario學生、UCL碩士黃芫推薦
Mario不輕易以era來斷定一股風潮或變化。他認為第一次數字化轉變(The first digital turn)改變了設計和製造的方式:從手工藝時代,每一個產品代表生產者的一個簽名和著作權,設計師即生產者製造產品;到十九至二十世紀的大規模機械標準化製造,大數量複製品的生產平分了機器、模具和模板的成本。設計師通過模板傳達設計,機器作為生產者製造產品。作為當時設計工具的CAD/CAM則使用平立面轉譯了設計師的思考和著作權,無論是直線還是樣條曲線。
講座中提到的Blob一詞來自1958年的美國電影變形怪體(The Blob),用來形容混沌的膠水一樣變化的形態(見電影海報中紅色的怪物)。在與電影同一時期的紐約,Frederick Kiesler則在嘗試把blob形態建造出來,起名Endless House。當他在小比例模型和各個平立面中嚴謹的表達了自己的設計,工人們依舊無法原尺寸準確的建造出來,最終妥協般的建造了一個更大比例的模型,在紐約MoMA展出(1960)。設計師-圖紙-生產者-產品的關係在blob的例子中遇到了傳達阻礙。
左圖變形怪體(The Blob)電影海報;右圖Endless House小比例模型(部分),拍自Wiederentdeckte modern I: Friedrich Kiesler @ Martin-Gropius-Bau 2017
當進入第二個數字化轉變(the second digital turn),新的數字化工具改變了設計師的思維方式,由邏輯和最優選生成形態,而不是相反的從自由形態上找尋數學表達式以定格設計。當設計的本質變成數字化語言,新的數字化建造工具得以更直接地繼承、轉譯和參與設計,弱化了繪圖方和施工方的作用,指導甚至完成產品建造。數字化建造的成本在於材料和時間,摒棄了傳統建造中模板對產品差異性的限制,使同批產品在同坐標上的信息可以零成本地相異。這在建築學中就意味着符號的限制、機械標準化和阿爾伯蒂式的著作方式的結束,多樣性對象和普遍參與性的著作權的開始。
導語
Mario
感謝大家的到來。今天我將要向你們介紹計算機輔助設計的新方向:先進的電子計算機技術如何改變建築設計領域。這也是我新書的主題。據我所知,在場的大部分人不是建築師、設計師或者相關專業的學生,因此我將做一個更全面的介紹來引入我的主題。
建築師的職責是什麼?這是一個十分常見的問題。任何一位建築師都會告訴你,建築師的職責是建造建築,宏偉的建築。但是,這一説法從技術上來説並不完全準確。因為嚴格來説,建築師既不砌磚,也不切割石塊;既不攪拌水泥,也不深挖基礎——不做任何一項涉及體力勞動的工作。
作為一名建築師,我承認我們的確建造了建築,但僅僅是通過繪製建築的設計圖紙。首先,設計師畫出清晰的設計圖,然後把圖紙交給負責建造的施工方。設計師不參與建造,而施工方則不被允許修改設計。
我們交給施工方的圖紙被稱作藍圖(blueprints),因為它曾經被印製為藍色。儘管現在它們無須印製也不再是藍色,但我們依舊這麼稱呼。藍圖使得我們的職業不被視作一門手工藝,而是人文藝術中的一門腦力活。
我們不會爬上腳手架,也不會在雨雪天氣或者烈日下辛苦勞作。我們在乾淨整潔的事務所中工作,享受着暖氣和空調設備帶來的舒適。而且在大部分時候,我們比實際建造建築的工人們薪資更高。我們只需要繪製圖紙而不必下場施工,這是這一職業的好處。壞處則是我們受制於描繪建築藍圖的工具,比如,你想出了一個絕妙的建築,卻無法畫出設計圖,便無法實際建成。
正文
土豆與鞋盒
很多幾何造型像鞋盒一樣易於建構和繪圖,只需要八個點或者三個點加三個方向就足以描述。另一類幾何造型則像土豆,從外觀上看,沒有任何一條線是直的。用粘土捏出一個土豆很簡單,但為它建立精確的模型和繪製詳細的圖紙卻很困難,更不用説根據圖紙去製作一個土豆了。你可以設定成百上千個三維點,然後用大量的剖面表達其形態,但是這種耗時過長的方法並不實際。直到電腦普及後,其強大的計算能力為土豆式建築的興起創造了條件。
正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計算機輔助設計高度普及之時,幾世紀以來建築師們對於數字建築的渴求驅使他們狂熱地建造起了土豆式的建築。如果你在電腦上搜索“參數化建築”等關鍵詞,你就會發現很多這種土豆式的東西。當然,它們的曲線形態遠比土豆的線條要平滑和精確,其中藴含着某些數理邏輯。
蓋裏:流線型建築的由來
在90年代中期,我的同事提出把這種新型的數字化形態稱為滴狀物(blob),靈感來源於50年代的科幻電影。今天則被改稱為參數化設計。但事實上,如果我們瞭解這些建築出現的時間進程,便會認識到,它們不是土豆,也不是滴狀物。這些都是魚一般的建築。
El Peix 雕塑,奧林匹克中心,Frank Gehry,1992
這一切都是從這條巴塞羅那海灘上的大魚開始的。在海灘上方而非水中,有一隻巨大的金屬魚漂浮在半空中。這是弗蘭克·蓋裏第一次使用軟件進行計算機輔助設計的作品,也是他明星建築師之路的起點。
當時已經小有名氣的建築師弗蘭克·蓋裏為何決定要用計算機輔助設計的方法來建造一條魚呢?他會需要什麼樣的軟件以建出魚身般流暢的曲面模型呢?考慮到魚在水裏的運動方式和船類似,故而可能和船體有着同類的光滑流線。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造船者已經掌握了製作船殼和水相接之處的彎曲木板的技術。想象一下,木船的結構框架是給定的,然後你必須把這塊木板條釘在船的框架上。當船在水中移動時,會產生摩擦或阻力。如果板條不光滑,船就會開始搖晃並變慢,故而它們必須是光滑的。
這種船體上彎曲的木板條叫作“樣條曲線”(splines)。這個詞在字典中被標註為17世紀技術用語。建造船體的工匠運用手工藝技巧以不同的方式彎曲每一根木條,使得它們以最流暢的方式連接起一組固定點。現在,船殼接觸到迎面水流的這條線被稱為“流線”(streamline)。這條流線必須平滑以避免摩擦或阻力。長期以來,船都是這樣建造的。又因為空氣動力和水動力原理相似,飛機也是這樣建造的。
戰鬥機機翼設計,康奈爾大學機械工程師團隊
數字化的起源:從DS汽車説起
這張照片是二戰時期在康奈爾大學機械工程系拍攝的。這是一個設計戰鬥機機翼曲線的工程師團隊,他們正在用手工測量獲得這條曲線的曲率。這完全取決於所選用材料的彈性,也就是相應木材的種類。如果選擇松木,你會得到一個特定的曲線。如果是冷杉或橡樹,那就會生成另一種。這就是當時的情況。甚至在飛機和飛機的機翼都是大批量生產的二戰期間,他們仍然是採用這種手工製作的方式。
DS汽車,Flaminio Bertoni&André Lefèbvre,1955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汽車工業也一直採用手工製造的方式。這是有史以來最著名的流線型汽車DS*。
注:該車設計於50年代早期,於56或57年投入使用。DS出自法語單詞Deesse,譯為“女神”。順便一提,這份傑作完全是由一位意大利工程師設計的。
雖然這是戴高樂將軍的車,但一切都是手工製造的。從最初的黏土,到定稿時的硬木,這輛車的設計也完全是手工藝性質的。因為沒有人能夠準確畫出所有技術圖上必須的曲線,所以這款車也不存在設計圖。汽車設計稿實際是一個用木頭做的汽車模型,保存於巴黎市中心的一個原子彈掩體內,冷戰時期如果發生什麼危險,設計方案就會被保留在那裏。當工程師們出於實際原因需要繪製藍圖時,他們會到地下的原子彈掩體裏,按比例對木製模型進行一條條線的測量,並根據需要繪製出藍圖,非常艱苦。
這就是為什麼在50年代後期同在巴黎的雪鐵龍和雷諾兩家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打電話給各自的頂級工程師説:“我們知道你們是如何手工製作汽車的,這種做法已經持續了幾個世紀。但你們是當今世界上最好的工程師,不是應該用我們在學校學過的微積分函數和座標值來記錄這些曲線麼?我們可以記錄拋物線,雙曲面,橢圓,圓。為什麼我們不能只用三個字母和一點係數在三維中標記出任何曲線呢?你們不能用數學的方法來使之更精確嗎?將來終有一天我們甚至會用電腦來做這件事。”
於是,兩個團隊開始在完全保密的情況下分別在雪鐵龍和雷諾兩個公司進行相同的研究,即找到用數學來記錄曲線的方法。我們只知道雷諾研發團隊負責人的名字,而雪鐵龍方負責人的名字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不為人知。這是技術史上令人着迷的一段故事。這些人顯然彼此認識,在同一所學校學習過,甚至可能一起在尼日利亞服過役,他們的妻子很可能是巴黎市中心同一個俱樂部的成員,但是他們必須秘密地進行競賽性質的工作。
雷諾團隊很快就取得了一些成果。60年代初,他們在雷諾首席執行官面前進行了一次著名的演示。他們拿來一張鈔票,上面有法蘭西銀行出納員的簽名,由許多圓圈組成。他們把這些手寫的任意曲線轉換成公式,接着把這些公式輸入繪圖儀。繪圖儀成功地繪製出了不同比例尺的簽名。因為這是一個沒有大小的數學符號,所以在任何比例下這個簽名看起來都是一樣的。這是一個奇妙的,極有説服力的演示。
但是雷諾的首席執行官認為他們花了兩年才將簽名轉譯為數學公式,而當時電腦在巴黎還尚未普及,用同樣的數學方法記錄一輛車的所有形態信息會花費太多時間,因而這一成果沒有實際用途,只能發表在一些古怪的數學雜誌上。這就是首席執行官勸説首席設計師皮埃爾·貝塞爾(Pierre Bezier)發表他的純數學理論的故事。文章在1966年被髮表,僅僅在幾年之後,電腦就出現了。這些數學在學術期刊上發表,成為當時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公開資源,每個人都對此痴狂。
雷諾公司為計算機輔助設計開發了自己的軟件Uniserve。在法國,飛機制造商達索系統公司(Dassault Systèmes S.A)開發了自己的軟件CATIA。美國的麥克唐奈·道格拉斯公司(McDonnell Douglas,美國航空製造公司和國防承包商)、通用汽車公司和波音公司開始使用它。波音公司對其進行了重大改進。他們把數學符號概括成非均勻有理B樣條曲線(Non-Uniform Rational B-splines,縮寫為NURBS),這個詞在工程學院有被戲稱為“沒有人真正理解的B樣條曲線”(No One Understands Really B-splines)。我們現在可以更好地從數學上去理解雪鐵龍的成果。但是和國有企業雷諾不同,私營公司雪鐵龍的高層認為這是一個商業機密。他們把這項技術保密了20年,因此公眾並沒能從這一成果中獲益。這些曲線現在被稱為貝塞爾曲線,源於皮埃爾·貝塞爾。
二次貝塞爾曲線的結構
第一類數字風格:蓋裏的魚
説回到1990年前後,弗蘭克·蓋裏事務所正面臨我在前面提到的問題。因為他們知道軟件發展的歷程,認為飛機制造商而非造船商會有他們設計魚式建築所需的技術。當時弗蘭克·蓋里社會聲望並不高,只是在建築圈內小有名氣。他和麥克唐奈·道格拉斯公司的工作人員通了一次未被錄音的電話,但是我們可以想象出公司負責人接到電話的驚訝與拒絕的過程。
但是弗蘭克·蓋裏並沒有放棄,他嘗試打電話給好朋友比爾·米切爾(Bill Mitchell)。他是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主任,計算機輔助設計的創始人之一。他認為蓋裏應該向巴黎達索公司的工程師們求助。他們製造的戰鬥機幻影十分昂貴,只有法國軍隊能買到。他們還有一個非常複雜的軟件來設計曲線,只有他們自己的工程師能使用。蓋裏和他們通話後達成了合作,一隊達索工程師前往洛杉磯,他們一起簡化了CATIA以用於建築設計,並開發了用於製作魚式形態的工具。
蓋裏非常滿意並一直使用它來進行曲面建築設計。他在世界各地建造此類建築並登峯造極。我從蓋裏本人那得知,最初他們想做的是一條鯉魚,但看起來並不太像。但不久後他又用CATIA建造了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此後他繼續在世界各地設計同種類魚式建築,這成為了蓋裏的標誌性風格。例如,洛杉磯迪士尼音樂廳。
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Frank Gehry,1997
洛杉磯迪士尼音樂廳,Frank Gehry,2003
路易威登基金會藝術中心,Frank Gehry,2014
他成功地將CATIA的簡化版用於建築併為之申請了版權。我們稱之為Digital Projects。他創立了一家名為蓋里科技(Gehry Technologies)的獨立公司,為其他沒有相關專業知識的公司提供此類建築的設計服務,從而積累了大量資本。最終他賣掉了這家公司,但名字依然叫蓋里科技。
由於CATIA過於複雜和昂貴,大多數建築事務所和學生無法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更廉價易學,但不夠精良的曲線建模軟件,例如Rhino, Maya, formZ。你可能聽説過其中一些名字。它們都是在90年代發展起來的,現在已經廣泛普及。所以在我講述後再看到這些包括建成與未建成的建築案例,你應該把它們視作魚而非滴狀物。
第二類數字風格:狗
但是如果你去一些學校中看看當下學生或者教授做的前衞創新設計,會發現其風格和魚這類完全不同。這就是我在書中所述的第二種數字風格,它是支離破碎的,其中的連續性已被離散性所取代。它是粗糙而非光滑的。
因為我用類比來闡述觀點,所以我決定稱呼其為狗式建築。有趣的是,我在國外教認真的美國學生時,他們在課後詢問我指的是哪種狗,並且畫了一幅漫畫圖來展示並不是所有的狗都是複雜混亂的,有部分可以用連續簡潔的線條概括。
現代主義的狗
後現代主義的狗
漫畫中的一切都是流線型的。這些現代主義的狗身體線條像魚一樣順滑,而魚看起來像一枚彈道導彈。與現代主義有關的一切都是流線型的,連狗也不例外。魚還算正常,它本質上就是流線型的。但狗不應該是流線型的,卻也被製造了出來。這張照片中的毛線狗才是我所想的後現代的狗,它給人一種離散和混亂的複雜感。之前的那隻狗是乾淨的,但我想在正常的生活中,這隻狗實際上是相當髒的,不容易被簡化成流暢的線條。
問題是既然計算機輔助設計很顯然是由工具水平和機器性能的發展驅動的,為什麼當下計算機輔助設計的風格會從魚轉向狗?是因為90年代的軟件更傾向於魚而今天的軟件更傾向於狗嗎?計算機今天仍然在做20年前甚至30年前所做的事情,但是更快,更強大,也更廉價。
人工智能對於設計領域的影響
在過去的5到10年裏,我們已經習慣於使用豐富的數據庫資源,甚至發明了大數據這個概念來定義資源豐富的新環境。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數據是稀有和昂貴的,現在卻無處不在且廉價易得。這是同樣從10年前開始的人類學意義上的劇變,人們開始渴望擁有更多的數據。而這一渴望近幾年來已經成為現實,我們擁有的數據甚至超出我們所需。
我們用大數據或者其他術語來定義同樣的機器學習,深度學習,人工神經網絡等等,有人認為其中一些已經與人工智能的概念有關。這對於我這個年紀的人來説這很新奇,我們過去認為人工智能是未來某一天才會出現的東西,現在卻被告知我們已經使用它五年了。我不知道人工智能是什麼,但我可以告訴你,當我們開始在工作中實際使用這些工具時,設計領域將會發生什麼。我會給你們看幾個例子讓你們有個概念。
我們在學校學習到人類記錄曲線的常規數學方法。微積分的神奇之處在於,僅通過運用x,y兩個字母和a,b,c三個係數,我們就能記錄無數個點。在這條拋物線上有無限個點,但是隻要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數學公式就足夠記錄曲線上所有的點。這是一種非常聰明的方法,它將大量的數據壓縮在簡潔的符號中。這太容易記住了,以至於我即使在100年前讀過一次後從未使用,現在也不會忘記。
我們就是這樣記錄曲線的,而且越來越多的機器或人工智能也會這樣做,但不是使用函數,而是列出一長串的點。每個點的x值都對應一個y值,它們位於曲線上。當我還是個高中生的時候,我為了檢查一個點是否真的在拋物線上,列了這個表,但你不能真的用這種方式標註每一個點。求出函數公式的目的正是為避免逐個指出每個點,因為公式在一行中便能指出所有點。但是電腦可以在一眨眼的時間裏操縱10億個點的列表,這在建築設計中已經開始應用了。
蓋達爾·阿利耶夫文化中心,Zaha Hadid,2012
這是由扎哈·哈迪德在她逝世前建造的最後建築之一。我想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魚類建築了,你可以從月球上用肉眼看到它。但是它的數學腳本最多隻有兩行或三行。建築的流線型曲線看起來很熟悉,因為我們瞭解支撐它的數學。數學已經存在很久了,微積分是17世紀末發明的。貝塞爾曲線是在1958年到1964年間發明的。數學方法不一定需要計算機,但有了計算機,計算速度更快。
數字怪誕,Michael Hansmeyer,2013
邁克爾·漢斯邁耶(Michael Hansmeyer)最近建造的這座3D打印石窟,使用的是迄今為止最大的商用3D打印機。你可以用3D技術打印房間大小的一塊積木。這些3D打印結構的每一部分都被打印成一個三維像素(voxel)。三維像素是物質的一個小單位,它就像體積組成的最小單位原子一樣,是單獨計算和相互分離的。
細部組件裝配過程
如果你仔細看,那就是洞穴的核心。這個洞穴是由3D打印的40億個三維像素一個一個拼接出來的,每一個三維像素都經過記錄、計算和製作。對於數十億個三維像素,每一個都有一個表示和計算的方法。計算機可以在一眨眼的時間內運行這個計算法列表,這種對我們來説荒謬的工作方式,對於一台機器來説是完全合理的。
如果這個構圖看起來有點古怪,那是因為指導外部形態的內在不可見邏輯不屬於我們頭腦的自然邏輯,它是機器的人工邏輯。我們用公式計算是做不出來的,只能通過列出一系列點的表格來確定其形態,但是能用手或計算器來記錄的點數量有限。這裏的40億個點是大量且複雜的數據,只有機器可以處理。這就是機器和我們思維方式的不同。
ICD/ITKE Research Pavillon,Achim Menges,2012
另一個例子,它是由阿希姆·蒙斯(Achim Menges)在德國斯圖加特的一個公共空間實際建造的一個小亭子。德國建築在建造之前,你需要進行結構計算,以確保這座建築能承受某種強度的風和雪的重量,諸如此類的要求。你提供的結構計算必須通過權威機構的驗證,從而證明建築結構是安全的。
這個由細絲製成的建築是怎麼計算出來的?我們本可以用這些在學校學習過的數學公式來單獨計算每根細絲,但是在這殼裏可能有400萬根燈絲,全部計算完大約需要六年時間,所以我們不會這麼做。實際上設計師沒有使用傳統的結構公式,而是藉助計算機進行有限元分析。
它的工作方式是,首先模擬一個特定的負載,其中紅色的就是有問題的部分。然後通過一次又一次地調整與不斷地嘗試,直到你看到全部都是綠色的。這意味着它經受荷載不會坍塌,你就可以採用這個成功的模型來建造了。
問題是在過程中,你也不知道哪一次嘗試會有最優的結果,故而必須不斷嘗試。為了使進展更快,我們要求機器進行自動模擬試驗,我們可以稱之為優化(optimization)。假如機器在一個小時內進行了100萬次試驗,其中一些可能是可取的,機器發現的最優方案將被建構,但是沒有人知道是試驗中哪些更改導致了最優的結果。
這個案例也是按照我告訴你們的方式計算出來的。為什麼這個結構能立起來,而無數個在計算模擬中的結構卻不能呢?沒有人知道。但在模擬中,我們知道它確實經得起考驗,就可以進行建造。所以我們所説的模擬和優化是通過大量試驗和錯誤的計算得出的。或者換句話説,就是在不知道為什麼有效的情況下找到科學的好方法。
結語
計算機和人工智能都是設計人員的好幫手
簡而言之,人工智能很明顯是可行的。我們已經可以用它來解決任何其他方法都無法解決的問題。但人工智能的工作方式與我們不同,這可能是我們稱之為人工智能的一個原因,因為我們大腦的有機邏輯不是這樣運作的。在函數的情況下,我們不能逐個計算400萬個點。在結構設計的例子中,我們不能連續運行4百萬次試驗。因為這會花費很長時間,但是機器只需要20分鐘,所以試錯對人類來説非常愚蠢,對機器來説卻是非常適用。
14年前Gmail推出時,我們就能很輕鬆地查找一個公式了,因為使用這類型的搜索引擎不需要親自在分類中尋找。想想我剛才所説的,我們人類所做的事情——收集、組織數據,並組織它們的結構從而使它們變得更精簡實用和容易理解,這就是傳統科學和數學的思維方式。計算機搜索速度很快,通過對簡單分類過程的處理,便可以找到最好的解決方案,故而這種針對人類緩慢搜索方式的分類過程通常是不必要的。
舉例來説,當我們在電話簿上的100萬個名字中尋找某一個時,因為採用了字母排序法,我們不需要瀏覽整本電話簿。但是計算機能在兩秒鐘內讀出100萬個名字,所以對我們來説必不可少的排序法對機器來説是不必要的。
圖書館裏的書同理。我們把書按照某種分類邏輯系統擺放在書架上,這樣我們在尋找某一學科的書籍時就知道在哪裏了。如果你想找一本關於文藝復興16世紀佛羅倫薩教堂的建築書籍,有了書架上相應的代碼標記數字,就不用花費大量時間去瀏覽圖書館裏所有書的標題,而可以直接到對應書架上找到你要找的書。
電腦可以快速查找,用虛擬現實技術我們也可以做到。想象一下,當所有的書準備存入書庫時,你無須僱用圖書管理員,而是用一個射頻識別的小芯片給它們貼上標籤,不做任何分類地把它們放在一座書山裏,再買一副虛擬現實眼鏡。當你在書山上尋找那本書的時候,你一問那本書在哪裏,你的視野裏就會顯示紅色的點標,機器搜索代替了圖書管理員的分類方法。
搜索還是分類?人類選擇分類,人工智能則選用電腦搜索。但這種方式做出來的建築並不是我喜歡的。我喜歡的是土豆式和魚式的建築。通過我前述的案例,很明顯,建築設計領域是人工智能的現成試驗場,因為我們設計的東西是如此簡單和廉價,我們使用的軟件是如此的初級。
對於我們做的方案,驗證是即時的。從早晨開始建造,夜晚來臨前我們就能確認建築結構是成立還是坍塌。如果它壞掉了,就不能用了,我們必須再試一次。因為我們擁有比其他行業更快的即時反饋迴路,我們能更直觀地領會到人工智能遊戲的精神。這不是我們的遊戲,而是你們計算機工程師想出來的。所以我應該在這裏停下來並開始傾聽。我想我們還有幾分鐘的時間。謝謝你們!
問答環節
Q1:你説你實際上是古典建築方面的專家,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建築也與數理關係緊密,那麼你認為現今的參數化設計是它們的進化版,還是完全不同呢?
A:建築總是受制於建造它的工具,這是不可避免的。在某種程度上,每種表達都取決於我們用來實現它的工具。你可以認為語言是自然的,但事實上,當你的想法是通過字母或語法表達出來時,你也可以用這些工具來表達對傳遞信息的反饋,這種反饋迴路在每個人的表達中都是存在的。建築與繪畫相比較,技術瓶頸的影響是更大的。畫家固然會受限於他所使用的畫布的類型和他在畫布上繪畫的技術。但是繪畫技術上的限制,如果與建造一個巨大建築的技術含義相比較的話,並不算什麼。
因為建築在建造之前必須被測量尺寸,故而格外受制於量化的工具。在希臘或羅馬等古典建築時代,當今很重要的成本估算不算什麼,比例對他們來説才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你可以從羅馬或希臘的建築的建造方式中瞭解到他們用來量化的工具不是基於數字的。相較於印度教和阿拉伯語的數字,希臘和羅馬的計數方法較差,所以他們不能用它們來計算任何東西。但他們的幾何是一流的,我們現在仍然在使用。所有這些量化都是通過歐幾里得幾何工具實現的,而我們今天使用的基於算術的工具還不存在。希臘人總是不信任數字,他們更喜歡石匠的典型工具羅盤上的幾何圖形。
古典建築和諧的數學比例源自於幾何的運用,這就是為什麼基於數字而非幾何的17或18世紀新古典主義建築和它們看起來是一樣的。但是如果用專家的眼光審視,便會發現它不再是由歐幾里得的幾何決定了。它源自於純粹的算術。我剛剛告訴你們貝塞爾和法國團隊所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將量化過程從代數轉化為微積分的。
有了笛卡爾、萊布尼茨和牛頓,我們還不能解決拋物線、雙曲面等等問題。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説,貝塞爾的成就是所有數學家夢想的頂峯。你可以用數學公式記錄一切,天空中的一朵雲,田野裏的一朵花,自然界中的任何形式都可以被寫成數學符號。當然,我們不需要記錄雲或花。我們需要記錄的是汽車的車身。這很複雜,但有了電腦,就變得容易了。這就是為什麼當電腦普及的時候,我們做的第一件事用它們來製造魚而非土豆。我們稱土豆為自由形式,因為它不包含數學。從某種意義上説,我提到的那隻狗,更接近土豆而不是魚。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説,24年後我們又回到了土豆的時代。
回到你的問題,如果你像一位科學歷史學家一般觀察你在每一個時間點看到的建築形式,就可以從它的物理形狀中瞭解到這些量化的工具對實現它至關重要。這並不意味着在每個時間週期都可以這樣做。我只能解釋某些時間段的建築。
Q2:你能用這些魚狗和直線的故事解釋一下安東尼·高迪的作品嗎?
A:在90年代,高迪是數字化術語的開端一個非常重要的標誌人物。他的作品不能用這些故事來解釋,因為高迪不屬於任何歷史時代。這是一個孤立的天才,由於一系列特殊的情況,他被允許在巴塞羅那做一些事情,這是一個在理論上是不存在的奇蹟。高迪想要重現中世紀建築大師的建造方式,所以他在建造時沒有做記錄。在中世紀,建築藍圖並不存在。工匠,設計師和建造者之間沒有分別。建築大師們在工地上一邊構思一邊施工。
1890年到1910年,因為他的意識形態、信仰和靈感,在工業城市巴塞羅那的安東尼·高迪想要復興中世紀的建造方式。他不是要復興一種風格,而是要復興中世紀建築工地的社會組織,所以他想要施行一種設計師與建造者不分離的方式。建造者是大師級的,他決定着每天要建造什麼。在一個工業化的世界裏,本不能那樣做。但在當時的巴塞羅那,他找到了決定用這種方式建造一座大教堂的英明贊助商。因為這座中世紀的大教堂的設計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只要有人願意建造,這座建築就會不斷成長,這座教堂的建造現在仍在繼續。
在90年代中期,馬克·伯裏(Mark Burry),從高迪停下的地方用計算機輔助設計重新開始。因為用電腦工作時幾乎可以在一台機器上同時完成設計和製造,他認為用電腦輔助更容易再現中世紀的建造方法。將圖片顯示在屏幕上的工具也可以將其打印出來,設計師和製造者之間的距離被你使用的工具拉近了。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使用電腦更接近中世紀而不是現代,這也延續並詮釋了高迪復興中世紀的夢想。這是一個有趣的故事。謝謝你的提問。
我想,儘管高迪自己建造並領導了這個過程,他還是有一些大教堂的圖紙。請問高迪用了什麼技術繪製草圖?
A:他有示意圖而非藍圖。因為立體切割(stereotomy)是中世紀切割石頭的技術。你無法用圖紙表示,但也有教工匠如何製作的方法。針對一些複雜曲線,他使用了懸鏈線模型來確定一些拱的形狀和它們的荷載。在這個過程中,他很可能引入了一種中世紀建築工人不知道的技術,所以他很可能也調整一些自己的規則。
我認為高迪有建築建成後繪製的示意圖或草圖,但沒有技術圖紙。因為藍圖是設計者給建造者的指示,這與他的精神背道而馳。在中世紀的事物體系中,這種分離是不存在的,你需要包攬思考和建造。作為一個工匠,你沒有藍圖,也不會收到要執行的藍圖,每天早上由你自己決定要做什麼,這就是中世紀。
我所描述的建築專業是在文藝復興時期確立的,當時人文主義者是一羣勢利的人,他們認為設計師應該創造,而且創造思維應該具有高於實際建造手工藝的智力價值,但這是一項15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現代發明。在中世紀,這種分割並不存在。這就是高迪想要復興中世紀的原因,他不喜歡現代化,儘管建造聖家堂的錢是由巴塞羅那的現代工業發展賺來的。
注:建議對比閲讀雷鋒第19篇講座,墨爾本大學Mark Burry教授講座《前數字時代的天堂之謎——詳解高迪的參數化創新》
Q2:非常感謝你的演講。八九十年代,計算機輔助設計技術出現後,有些東西開始變得十分相似。例如,汽車行業中,奧迪看起來像寶馬之類的。你認為,有了人工智能機器,是會產生更多這樣相似的情況,還是會有更多樣化的東西在它們的設計中出現?
A:這是真的,尤其是在汽車設計方面,正如你指出的那樣。這些曲線,樣條,數學運算在當時所有汽車製造商使用的軟件中都是一樣的,但軟件是不同的。每個軟件都有自己的調整。我不是一個特別的專家,但是格雷格·林恩對汽車設計非常感興趣,他是一個真正的專家和鑑賞家。他能通過觀察一輛車的車身,判斷出是用哪個版本的軟件設計的。每個軟件都有一些微調留下痕跡。因為每個word版本剪切和粘貼的工作方式是不同的所以有時候你可以分辨出是用哪個版本寫出的文章。
早期你可以這麼做,因為在90年代世界上汽車行業中一共只有大概25種軟件被使用,如果你在那個領域,你就會知道所有的軟件。現在,我們可能正在轉向一個變化比適應快得多的時代,因此我的猜測是,識別我們正在使用哪一款工具的索引跟蹤不再那麼容易。在90年代,一種軟件大概有25種變體,現在大概有1000種。所以我認為人工智能工具帶來的複雜性將使這種詞彙遷移工具的痕跡不那麼明顯。
講座原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Verq5DSdKU
文中使用的圖片來自網絡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