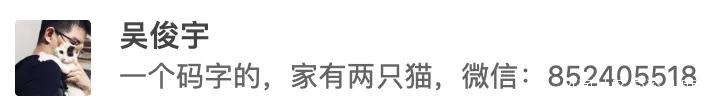搖滾甚至沒到春天_風聞
深几度-深几度官方账号-2019-07-19 11:56
文|吳俊宇
一
前《三聯生活週刊》的王小峯可能是中國最好的音樂記者。
從1989年開始發表音樂評論,他在多家音樂媒體任職,後來還出版了西方流行音樂的百科全書《歐美流行音樂指南》。
不收車馬費,不接受改稿,不諂媚採訪對象,寫一個明星和一個明星鬧崩,但卻能讓明星對他保持敬重。不管是哪個圈子、行業、領域,這種記者都很少見。
這位“憤怒樂評人”後來卻幾乎徹底離開了公共輿論場,選擇不再寫樂評。有人説,他不再寫樂評的原因是,“覺得現在已經沒有音樂了”。
王小峯後來開了一家名叫“不許聯想”的淘寶店,沉迷做T恤衫,把音樂符號、文學符號融入衣服之中,用另一種含蓄內斂的方式進行自我表達。
2018年,“不許聯想”上線了一件The Beatles樂隊相關的T恤,上面印着Yellow Submarine(黃色潛水艇)。
懂的人才知道,這件T恤的意義,不懂的人只會覺得,這是一件童裝。
王小峯幾乎很少對現在的音樂節目做過多點評。不管是《我是唱作人》還是《樂隊的夏天》,他幾乎都不去接茬。
在鮑勃·迪倫生日那天,王小峯寫了一個名為《唱作人》的文章。裏面講述了崔健、竇唯、張楚這幾位八九十年代的搖滾先驅陷入創作困境的故事:
崔健好多歌曲子早就寫完了,但是寫不出歌詞,每句歌詞都要字斟句酌…….老崔是用一種倔勁兒寫出那些歌詞的;
竇唯總説歌詞寫得不好,後來他乾脆不寫詞了,做純音樂他更擅長一些。什麼竇唯成仙了,這叫了解自己;
張楚一出道就給人一種詩人歌手的形象,他的很多歌詞現在讀來仍然很牛。但他不擅長作曲,當年錄製《孤獨的人是可恥的》,把製作人賈敏恕頭髮都急白了。張楚根據合同要出第二、第三張專輯時,開始懷疑人生:一張專輯為什麼非要十首歌,一首不行嗎?
王小峯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鮑勃·迪倫作為創作型歌手能保持自己的創作青春?
他的回答是,他有深厚的文學功底,他混江湖之前,常常在圖書館裏看報紙,研究過去人們的行文習慣,用詞方式。
王小峯最後總結,“現實是殘酷的,你有幾滴墨水,晃盪兩下大家就知道了。”
二
《樂隊的夏天》中一些樂評人頗為無厘頭的評論總讓人陷入嚴重自我審美懷疑。
盤尼西林樂隊的主唱小樂在唱完《羣星閃耀時》之後,大張偉又開始了插科打諢。
小樂一副拽拽的表情説,“那是你沒聽明白”,“人性裏有好多東西,每個人心裏都有善與惡,有的時候會有太陽,有的時候會有月亮,我更想表達在夜晚裏的東西,那些所有的荒謬的、破碎的,都結集在夜晚變成星星……”
説完這段後,大張偉對小樂説:你做搖滾樂為什麼要這麼裝呢?你這樣以後人生路會很坎坷的。
看到這段時,忍不住關掉了電視。
朋友對小樂評價是,“年紀輕輕,油膩得不行,是個傻子,能力完全跟不上想法”。
我也認可,但我對大張偉的這套表現着實沒有太多好感。
“人性這根曲木,絕然造不出任何筆直的東西”,這麼簡單的道理在這裏,就變成了“裝”。
娛樂綜藝終究只能娛樂。馬東那個著名的“95%和5%”的理論在這裏再一次生效了。
2年前,馬東在接受許知遠的採訪時説,“這個世界上大約只有5%的人有願望積累知識,瞭解過去。那95%的人就是在活着,就是在生活。”
為了保證95%的觀眾的節目效果,只能讓大張偉用這種插科打諢的方式為原本嚴肅的問題增添笑料,卻無法把5%的事情説明白。
可以確信的是,大張偉絕對知道小樂在説什麼。大張偉曾經是個夢斷搖滾的人,他有着“過來人”的經驗。
1998年大張偉剛出道時,他的“花兒樂隊”平均年齡才16歲, 被視為是“最有前途的搖滾樂隊”、“中國新音樂的希望”、“世紀末華人樂壇的奇蹟”。那時才14歲的大張偉被崔健、許巍帶着,被搖滾圈當成是“第三代搖滾領軍人物”。
然而大張偉看着一羣做搖滾的人天天混跡酒吧賺吆喝,越來越清楚,搖滾沒出路。最後他在春晚上唱起了《嘻唰唰》、《倍兒爽》這樣的口水歌。春晚導演組聽了《倍兒爽》都高興瘋了,一宿沒睡着覺。
大張偉的劇變讓曾經的伯樂罵他背叛搖滾樂。大張偉的回答是,他是個有“生活負擔的人”,爸媽都下崗了,需要錢。
後來,有媒體把對大張偉的採訪直接凝結成了這樣一句話——只有做“嘻唰唰”這樣的歌才能賺錢養家,再唱搖滾我就仨結果:改行、自殺、神經病。
大張偉什麼都懂,他甚至看透了很多人聽搖滾樂只是為了瞎湊熱鬧。
他沒辦法從中得到真正的認可。2016年,《人物》 雜誌顧玥在採訪大張偉時,大張偉透露了這樣一個信息:
好多人就是他媽膚淺到讓你髮指。我當時(花兒樂隊剛出道)弄朋克的時候,底下一排小女孩堵着耳朵這麼看我,看我跟掛鞭似的,她們老覺得我是鞭炮那個範兒的……她們喜歡壞的那種感覺,但是他們根本不喜歡那種音樂。我就是因為看他們前面第一排全是堵耳朵的,我覺得這種音樂不能幹。
只不過“段子手”的人設和“背叛搖滾”的經歷,告訴他必須“懂裝不懂”。
我不否認盤尼西林樂隊的小樂有野心,也不否認他的野心可能配不上當下的才華。
你從這首《羣星閃耀時》之中就能明顯發現,他化用了奧地利小説家茨維格《人類羣星閃耀時》的書名。《人類羣星閃耀時》之中有這樣一段話:
那些歷史的尖峯時刻都需要太長的醖釀時間,每一樁影響深遠的事件都需要一個發展的過程。就像避雷針的尖端匯聚了整個大氣層的電流一樣,那些不可勝數的事件也會擠在這最短的時間內發作,但它們的決定性影響卻超越時間之上。
稍微深究一點都明白,小樂希望自家樂隊的影響力“超越時間”。
《羣星閃耀時》這首歌獻給“海龜先生”的李紅旗,更是有種希望他們這代搖滾人就能夠出人頭地的“虛妄感”。
畢竟中國搖滾地下小眾太久了。
三
盤尼西林樂隊很優秀,但的確還是差了那麼一口氣。《樂隊的夏天》裏很多樂隊的音樂也的確沒那麼好,卻非要樂評人“硬拗”,你才能讀懂其中的好。
後來憋不住去問懂行的人搖滾樂歷史譜系,他輕而易舉告訴我當年這行的豐碑是誰,哪張專輯才是經典,哪些人因為哪些事情隕落之後,哪些人後來因為什麼事情抑鬱了、瘋掉了——這也引出了我對“魔巖三傑”的好奇。
重新翻開“魔巖三傑”的專輯,突然意識到,好的東西終究是好的東西,哪怕你不懂你也知道,擺在那兒就知道是好的東西。
從去年開始,就對“魔巖三傑”墜落的故事有些好奇。
“魔巖三傑”指的是台灣滾石唱片公司下屬魔巖唱片的三位簽約藝人——竇唯、張楚、何勇。
1993年,魔巖負責人張培仁簽下竇唯、張楚與何勇三位創作型歌手。1994年春天竇唯、張楚、何勇同時推出三張專輯,分別是《黑夢》、《垃圾場》和《孤獨的人是可恥的》。
他們曾經是1994年香港紅磡“中國搖滾樂勢力演唱會”的代表性人物,“魔巖三傑”影響了一代人。
去年許知遠專訪張楚的節目讓我對這個唱《姐姐》和《孤獨的人是可恥的》的人頗有好感。
張楚年輕時長得像瘦版佟大為,歌聲意氣風發,但1997年之後便從雲端墜落懸崖——再也沒有太多優秀的作品。
20多年過去後,他蒼老的不成樣子,額頭上有十幾道抬頭紋。
在接受許的採訪時,張楚精神恍惚,大談自己相信“911是美國為了控制世界”。這種精神狀態讓你覺得“很扯”。
今天《樂隊的夏天》之中不管是“新褲子”、“海龜先生”以及“盤尼西林”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或多或少都會提到1994年的紅磡,或者是“魔巖三傑”中的某位人物。
然而在1994年紅磡的頂點之後,“魔巖三傑”逐漸淡出舞台。
用何勇那句經常被媒體引用的話來説就是:“我們是魔巖三病人,張楚死了,我瘋了,竇唯成仙了” 。
四
死、瘋、成仙,成因複雜。
天災人禍、江郎才盡、商業壓榨、歷史潮流……無法足以概括。
任何事物都是衝上頂峯容易,持盈保泰太難。增長拋物線的前半段往往是最誘人的,後半段卻讓人不忍卒讀。往往登頂就意味着接下來要面臨滑坡。
雖然當時的搖滾愛好者以為紅磡是中國搖滾的起點,但恐怕只有“魔巖三傑”才能意識到,那是拋物線的頂端。
2009年,《南方週末》在《何勇:李素麗,你漂亮嗎?》這篇文章中提到了這樣一句話:
紅磡演完之後何勇有了不好的感覺,覺得自己要停一停,歇一歇。改革開放了,中國樂手卻從未接觸過商業合同,每個人都在摸着石頭過河。
這兩句話60個字,其實透露了兩個信息。
這代中國搖滾歌手是在80年代社會開放氛圍下誕生的,但是90年代的時代劇變迅速讓滋養他們的文化土壤沖刷殆盡。
張培仁過早把不成熟的“魔巖三傑”推上香港紅磡的舞台,其實是在過早透支三個人的商業價值。實際上當時三個人對紅磡演唱會並沒有那麼認可。
後來的事情更是無厘頭。
1996年首都工人體育館舉行的“流行音樂20年”晚會,何勇唱《姑娘漂亮》時腦子抽經,跳上鋼琴喊了句“李素麗你漂亮嗎”。
李素麗是北京21路公交車售票員,也是當時全國上下學習的全國勞動模範。
何勇此舉是為了出氣,主辦方封殺崔健,他純粹在用這種方式發泄不滿,後來他説:
我對主流的這種演出很排斥,他們不讓老崔演,好像是因為商業的問題,我當時覺得又氣又怨。我覺得勞模應該是崔健這樣的個體户,人家才是真正白手起家的。
何勇闖下大禍,也被封殺。
當年香港紅磡演唱會本身就有“偷渡”的成分,某種程度上是上面“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結果。何勇的叛逆觸及到了一些不該觸及的底線。
張楚也沒好到哪兒去。1997年,張楚發行了《造飛機的工廠》,這張專輯在商業上極度失敗。這種失敗其實歸根究底還是張楚不想迎合主流音樂,非要“擰巴”。“擰巴”不出結果後,張楚從北京回到西安,開始了長達八年的抑鬱症。
張楚後來復出時在單向街的一場論壇裏説,“90年代的文化是從哲學、文學去講很多問題。可是到了後來,我們就説生活吧,生活都變成這樣了,大家被生活直接調度到這樣一個時代。”
何勇恐怕早就看到了這點。
“魔巖三傑”之中,何勇最典型的裝扮是海魂衫繫上紅鞋帶,最“暴躁”的颱風骨子裏透徹叛逆。
在《姑娘漂亮》這首歌之中,何勇面對喜歡的姑娘只能説“你説要汽車你説要洋房我不能偷也不能搶,我只有一張吱吱嘎嘎的牀我騎着單車帶你去看夕陽”。
可最後“姑娘姑娘你鑽進了汽車,你住進了洋房”。
何勇在最後問了一個終極命題,“交個女朋友還是養條狗?”
這種話語和“To be or not to be”一樣,其實是對即將洶湧而至時代潮流的無賴嘲諷。
其實,你説何勇是無賴,倒不如説他是無奈。
五
這終究是個娛樂和消費的年代,商業和技術勢如破竹。
在消費和技術、控制與被控制的浪潮之下,我們成了馬爾庫塞所説的“單向度的人”。
搖滾終究是個叛逆的東西,不叛逆就不是搖滾。
The Beatles當年火遍英倫三島和美洲大陸的時候,主唱列儂面對美國越戰,喊出的口號就是“要做愛不要作戰”。
1968年列儂提出的這個口號後來還影響了捷克年輕人。
界面記者朱天元在採訪東歐文學研究者景凱旋之後有一篇名為《中國作家在表現我們共同經歷的時候,沒有東歐作家的深刻與力度》的報道。這篇報道之中記載了一個細節:
今天的布拉格小城還有一個列儂牆,上面全是塗鴉。當時,捷克女歌手瑪爾塔·庫碧索娃翻唱的披頭士《Hey Jude》單曲版創下了捷克流行音樂的暢銷記錄,併成為了“布拉格之春”的重要象徵。
深受列儂影響的捷克搖滾樂隊“宇宙塑料人”,在1976年創作了一首歌《百分百》,歌詞寫道:
他們害怕老人的記憶/他們害怕年輕人的思想和理想/他們害怕葬禮,和墓上的鮮花/他們害怕工人,害怕教堂,害怕所有的快樂時光/他們害怕藝術,他們害怕藝術/他們害怕語言這溝通的橋樑……那麼,我們到底為什麼要怕他們?
可叛逆的東西也會被規訓和懲罰。
現狀給人的空間越來越狹窄,我們如同被夾在政治和商業之間的“三明治”,在狹窄的空間之中難以轉身。
狹窄的“三明治”容不得叛逆,“單向度的人”是不會叛逆也不敢叛逆的,搖滾只能不鹹不淡隔靴搔癢,在一個安全範圍內有限叛逆,最終成為商業的俘虜。
那代搖滾人的根基早就沒了。“魔巖三傑”的戛然而止,這歸根究底還是一個歷史年代隕落的結果。
王小峯不寫樂評了,張楚江郎才盡了。
張楚2016年復出時,他倆在一場論壇中坐在一起。王小峯説,“如果説張楚有一天突然紅了,那一定是對當下這個時代的諷刺。”
每一個人搖滾人甚至每一個人音樂人都向往“魔巖三傑”的歷史地位,每一個人搖滾人甚至每一個人音樂人都敬重“魔巖三傑”的自由叛逆。
每一個人又都清楚,歷史地位、自由叛逆不能當飯吃,更重要的事情是生存,是活着,是把自己的日子過好。
一代人終將老去,但總有人正年輕。可年輕人越來越聰明瞭,知道不能去碰老人的壁。
沒人敢叛逆又期待別人叛逆,這種擰巴又雞賊的心態這就像是一個列隊,每個人都往後退了一步,只有“魔巖三傑”還站在那兒,於是“魔巖三傑”被釘在了歷史的天花板上,他們成了符號和象徵。
搖滾無法出圈是肯定的。知乎上有一個名為周楠樂評人評價説:
你指望一幫中年人為一塊若即若離的虛擬大餅掙的你死我活本來就是不現實的……這些樂隊平均年齡真的35歲往上了,對火不火也就那麼回事了。火兩年然後呢?不還是跑音樂節跑LiveHouse。
《樂隊的夏天》在這個夏天留下來的意義是,它至少會讓一羣人更願意瞭解搖滾,雖然可能搖滾圈會多一羣湊熱鬧的人,搖滾樂隊們的商業環境以後會好一些。
樂隊有夏天,可搖滾沒有,甚至春天都還沒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