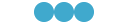引力波諾獎得主巴里什:一個起死回生的接盤俠 | 展卷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19-07-20 12:06
「以引力波探測進程為主線的《捕捉引力波背後的故事》固然可以歸到物理學史名下。但與古典的物理學史敍事截然不同的是,本書的敍事結構屬於科學社會學——典型的例子是巴里什(Barry Barish)何以問鼎諾獎,這在古典的物理學史敍事模式中幾乎不可理解——作為“背後的故事”,其側重既不在引力波探測的物理原理(廣義相對論、引力物理、天體物理等),也不在工程實現的技術細節(激光干涉儀、數值相對論等),而是物理學共同體在現實社會(甚至可以説是世俗社會)中的科學活動——頗有太史公之“紀傳體”遺風——也就是作者在前言中所謂“並不侷限於相關科學知識的普及,而是更注重挖掘科學突破背後的人物、社會背景、政策抉擇以及各種不為大眾所知的過程和細節”。」
——「返樸」編委 李輕舟
本期推薦《捕捉引力波背後的故事》。
返樸微博評論被點贊最多(截至7月27日中午12點)的2位讀者可獲贈《捕捉引力波背後的故事》一本。****
返樸微信公眾號留言被點贊最多(截至7月27日中午12點)的四位讀者可獲贈《捕捉引力波背後的故事》一本,點擊“閲讀原文”參與活動。****
**撰文 |**程鶚
1994年初,LIGO面臨着生死存亡危機。韋斯、德瑞福、索恩組成的三駕馬車早因為德瑞福被驅逐而散架,他們的車伕沃格特這時也被拋棄。虎視眈眈的國會正在尋找各種理由削減、甚至隨時可能完全砍掉項目的預算。國家科學基金會則因為項目本身的管理混亂凍結了大部撥款。這一般就是他們資助的項目被判死刑之前奏,很少能有再度復活的先例。
加州理工學院自然不甘心。他們又一次需要找到一個足以力挽狂瀾的領頭人,而他們也再一次有着瞌睡遇見枕頭的好運氣:因為國會撤銷了超級對撞機項目,大批高能物理的佼佼者突然失去了職業生機,正在茫然賦閒、另找出路。他們雖然專業上與引力波不那麼搭界,卻都是操持大科學、大項目的行家裏手。而他們之中便有自己校內的巴里什(Barry Barish)。
//////////
巴里什的祖父母輩都是從東歐逃到美國的猶太人,在美國中西部內布拉斯加州定居。他的父母都在那裏出生、長大、相遇。母親中學畢業時得到內布拉斯加大學錄取和獎學金,可她保守的父母堅持家族傳統禁止女性上大學。她後來離家出走,早早地結婚生子。巴里什的父親則因為自己的父親早逝,從中學起就不得不輟學養家。因此他們倆都沒能受到大學教育,因為這番經歷和猶太人傳統,他們一直重視子女教育,將大學夢寄託在年幼的巴里什身上。
巴里什自己從小喜歡讀小説,夢想的是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中學時讀了經典小説《白鯨記》(Moby-Dick)後,他卻被其中極其詳盡地描述鯨魚生理結構的長長一章內容給鎮住了。由此他幡然醒悟:既然寫小説也需要掌握這麼多科學知識,那還不如干脆去學理工科。
巴里什八九歲時就隨家庭離開了中西部,搬到加州洛杉磯,在陽光海灘邊長大。這時他最希望的是能進附近的加州理工學院。不巧的是他中學是春季畢業,加州理工學院卻只在秋季招收新生入學。他只好先去了位於伯克利的加州大學,打算在那裏先混半年。不料他卻又很快愛上了那個校園,打消了轉學的念頭。
他開始上的是比較實用、有職業前途的工科專業,但發現處處不如意:上繪圖課因為沒有一絲不苟而被責備、上化學課因為擦洗試管不夠乾淨被扣分、上測繪課因為扛着怪怪的測量儀器滿校園跑被嘲笑……終於,他受夠了,稀裏糊塗地找到了物理系,一個不需要整天“刷盤子、扛大活”的清淨專業。
那是1950年代,勞倫斯(Ernest Lawrence)正在伯克利發明他的粒子迴旋加速器。還是大學本科的巴里什喜歡沒事就溜進他的實驗室觀察,自己學會了操作那個古怪的新大傢伙。在他自己還沒有完全弄明白怎麼回事時,他參與設計、操作的加速器在1955年發現了“反質子”(antiproton),後來贏得1959年諾貝爾獎。
1957年巴里什大學畢業時,伯克利還有政策不招收本校畢業生上研究生,以避免所謂的“近親繁殖”。他申請了加州理工學院,順利被錄取。不料伯克利這時變了卦,又決定要留下包括他在內的少數幾個優秀學生。於是他再度捨棄加州理工學院,留在了伯克利。
他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研究生。與本科時一樣,他總是在迴旋加速器實驗室自己折騰,想獨立做科研,甚至拒絕找教授做導師。系主任對他無可奈何,“自薦”當了他名義上的導師,簽字認可他自行其是。
1962年巴里什獲得了博士學位。為了不與新婚妻子分離,他繼續留在伯克利做博士後,繼續折騰他的加速器。加州理工學院一名年輕教授注意到他的才幹,鼓動他加盟加州理工學院。巴里什對這所他兩度擦肩而過的學校也依然一往情深,尤其覺得她注重於尋找年輕新人,給他們良好的環境讓他們自由發展,不像東部傳統名校只喜歡四處挖角、尋求已經事業有成的名人。於是他欣然應聘。到校後,他很快與那裏的費曼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兩人經常在校園裏一起吃午飯、神聊。從來沒有什麼導師的巴里什後來説費曼是對他人生、事業影響最大的人。
只是巴里什在加州理工學院校園內的時間並不太多,因為學校自己沒有加速器。他只能穿梭於有加速器的國家實驗室、大學之間,設計、實施自己的試驗。隨着加速器規模越做越大,他自然地成為與大科學同生共長的新一代物理學家。在其後他的職業生涯中,他在布魯克海文、費米、斯坦福等實驗室之間遊刃有餘,幾乎在美國所有大型加速器上都做過不同課題的試驗。
1960年代末,他與幾個朋友合作在斯坦福直線加速器中心新落成的加速器上做了第一個試驗。折騰了一陣後他覺得沒有什麼前途自己提前走人了。六個月後,剩下的三個合作者發現了質子內部的夸克結構,後來獲得1990年諾貝爾獎。巴里什也因此成為他們終身的玩笑對象。
巴里什自己當然也沒閒着。高能物理試驗規模大、週期長。這個領域大多數物理學家傾其一生專研於某一兩個課題,不斷地精益求精。巴里什則有所不同。他興趣廣泛,經常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研究領域包括首次通過中微子碰撞測量到“弱中性流”(weak neutral current)、發現中微子存在質量和“振盪”的證據等等。此外,他還花了十多年時間尋找尚且不確定是否存在的“磁單極”(magnetic monopole)。
//////////
1990年代初,超級對撞機事業正是風生水起。這行業的物理學家除了在國會內外為預算撥款吵得不可開交外,他們內部還一直進行着與引力波項目非常類似的龍爭虎鬥,甚至也有着他們自己的“德瑞福”、“沃格特”——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丁肇中(Samuel Ting)。
與德瑞福相似,丁肇中工作勤奮、精於創新,但同時也自以為是、專橫跋扈,在同行之間口碑不佳,不被認為是一個具備團隊精神的人。不同的是他早在1976年便因為發現“J/ψ介子”獲得諾貝爾獎,因此享有着相當高的地位,不像德瑞福那樣依然會受制於人。
超級對撞機選定了兩個大實驗項目,丁肇中負責其中之一。他提出一個7億5千萬美元的預算,並一再拒絕能源部將其縮減到5億以下的要求。靠着他的名氣和組織能力,丁肇中已經在中國、蘇聯和歐洲幾國聯繫到合作伙伴,自認為可以自行解決短缺的資金,反對能源部插手干預。這個矛盾在審核過程中不斷激化,最終導致丁肇中與能源部以及對撞機項目總主持人徹底鬧翻,不歡而散。丁肇中自己全身而退,被遺棄的團隊只好尋找一個能夠收拾殘局、挽救實驗的能手,當時被選中的眾望所歸者便是巴里什。
1993年的巴里什
巴里什很快整合了隊伍,從頭重新設計、計劃,贏得了能源部、超級對撞機領導的認可,保住了這個重頭項目。他也因此成為超級對撞機的主要領軍人物之一。然而,就在他雄心勃勃準備甩開膀子大幹一場時,超級對撞機突然被國會撤銷,所有與之相關的項目便都嘎然而止。已經58歲的巴里什迷茫彷徨,只好收拾心情,準備再繼續去尋找他的磁單極。
//////////
早在1976年索恩向加州理工學院提議開展引力波探測實驗時,巴里什就是審查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在那之後,他一直作為同事遠距離觀望着這個項目的進展和混亂。
沃格特被基金會催促得焦頭爛額時,還曾找過巴里什求教如何對付。巴里什向沃格特出示了他為自己的對撞機項目按部就班準備的各種材料和報告給沃格特做範本。不料沃格特只是掃了一遍後便嗤之以鼻,反過來教訓巴里什不應該如此順從官僚管理,浪費時間精力做這種沒有意義的紙面文章。巴里什只得苦笑。
直到沃格特與基金會徹底鬧翻後,加州理工學院臨時組建了一個監督委員會處理後事。作為委員會成員,巴里什看到了基金會內部的同行評議報告,才開始深度瞭解這個項目內部的麻煩。這些報告的主調便是項目已經病入膏肓、無可救藥,只能撤銷了事。而這時,委員會也幾乎一致地推薦、鼓動“賦閒”中的巴里什再一次扮演接盤俠,出馬拯救LIGO。
巴里什對探測引力波這個課題本身很是憧憬。他知道,雖然在德瑞福、索恩、韋斯這些引力波領域的人看來,建造激光干涉儀極其複雜、工程浩大,在他這個習慣於在高能粒子試驗中修建超大型設備、設計各種精準探測器的行家來説卻還只是小巫見大巫,比超級對撞機的規模已經差了一大截子。如果召集起因為超級對撞機而“失業”的團隊,他有把握承擔這個項目,但問題在於他是否能夠收拾起眼前已有的爛攤子。
穩重的巴里什提出給他一個月的時間做一個深度調查。他必須在確信自己能夠促使項目成功的條件下才會同意接手。
可是,接下來的一個月裏,他卻是越來越鬱悶。LIGO的問題比他想象的還更嚴重得多。因為沃格特對官僚的厭惡,他們幾乎在1989年提交給基金會的那份申請後就再沒有什麼系統的文字材料。那之後的五年裏,除了在國會爭取到撥款,很難知道他們在技術上取得了什麼進步。瞭解內情的是具體的工作人員。他們在經過了德瑞福、沃格特兩次大動盪之後噤若寒蟬,各自將資料牢牢地鎖在自己的文件櫃裏,對公開合作十分牴觸。
一個月很快過去了,巴里什沒能説服自己他能保證項目成功。但他已經沒有更多的時間可以斟酌、彷徨,而同時探測引力波的魅力也越來越令他無力自拔。他只好退而求其次,説服自己也“沒法證明這個項目就不可能成功”。於是,帶着一絲盲目的樂觀,他決定走馬上任。
1994年2月,LIGO又有了新的主要負責人。
本文摘自《捕捉引力波背後的故事》,標題為編者所加。欲購此書,可掃描下方圖中二維碼,或點擊“閲讀原文”。
獨家書評
欲往從之梁父艱 ——讀《捕捉引力波背後的故事》
****撰文 |李輕舟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
—— 張衡 《四愁詩·其一》
韋斯、索恩、巴里什(從右到左)榮獲201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蒙科學出版社錢俊先生惠賜程鶚博士新作《捕捉引力波背後的故事》,囑我撰文評介。我與作者素昧平生,今承展卷受教之誼,不揣冒昧,略陳固陋。
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的贊評中説:“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然而,事非經過,難序內中關節條理;身陷其間,難為執正持平之論。“實錄”二字看似容易,實則是要求史家開啓“上帝視角”,通貫時間,俯瞰眾生——如果沒把自己修煉成“拉普拉斯妖”,這就是個mission impossible。即便是mission impossible,也攔不住凡人著史的熱情,他們索性各挾“傲慢與偏見”自成一統,史筆之下,別立乾坤。
古典的物理學史(包括自然哲學史)敍事者,自不例外,多少應有馬赫(Ernst Mach)、勞厄(Max von Laue)、薛定諤(Erwin Schrödinger)那樣在歷史維度上(也在邏輯維度上)重構知識體系的雄心。隨着古典主義(或者説古典審美)的退隱,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以及隨之而來的冷戰)以來,“猛虎獨行”逐漸讓位於“羣狼分食”、“大兵團作戰”和“軍備競賽”漸成燎原之勢,物理學的世界反而日趨原子化,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旨在營造體系的宏大敍事成了明日黃花,或許在彭羅斯(Roger Penrose)那裏尚有幾分餘韻。
以引力波探測進程為主線的《捕捉引力波背後的故事》固然可以歸到物理學史名下。但與古典的物理學史敍事截然不同的是,本書的敍事結構屬於科學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ce,以科學為研究對象的社會學)——典型的例子是巴里什(Barry Barish)何以問鼎諾獎(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美國超導超級對撞機項目的興廢),這在古典的物理學史敍事模式中幾乎不可理解——作為“背後的故事”,其側重既不在引力波探測的物理原理(廣義相對論、引力物理、天體物理等),也不在工程實現的技術細節(激光干涉儀、數值相對論等),而是物理學共同體在現實社會(甚至可以説是世俗社會)中的科學活動——頗有太史公之“紀傳體”遺風——也就是作者在前言中所謂“並不侷限於相關科學知識的普及,而是更注重挖掘科學突破背後的人物、社會背景、政策抉擇以及各種不為大眾所知的過程和細節”。簡而言之,即引力波探測進程中的那些人和那些事。此中有列國爭衡,有部門博弈,有人事紛擾,有名利糾纏,有説不盡的“欲往從之梁父艱”,恰如書中引述韋斯(Rainer Weiss)和索恩(Kip Thorne)不約而同的感嘆“真正的奇蹟不是我們終於找到了引力波,而在於我們當初居然沒把這事徹底搞砸”——當今意義上的“科學無坦途”,此之謂也。
德克薩斯州地下廢棄的為超級對撞機挖掘的巨型地道
1970年代的索恩在黑板上講解引力場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一部通俗或普及作品,本書在涉及某些物理原理或技術細節時,難免會用一點兒譬喻性(直觀圖像)的闡釋(在以普及物理知識為主的書中更為常見),而這類譬喻,縱然是來自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本人,離開了必要的數學表達,也不過是不問究竟的“方便法門”,必然會掩蓋些許知識細節,易使未經系統學習的受眾望文生義,不得要領,有的甚至會干擾某些讀者將來的系統學習。這本是數理科學類通俗或普及作品的“原罪”,幸而作者在正文後的註釋中為有志成為“探險家”的讀者留有大量重要文獻,堪為渡人梯航。此外,單就“講故事”而論,作者行文曉暢,主次分明,百年曲折,循序展開,即使讀者無意加入到“人類心智早已開始的最偉大之冒險”(費曼語),亦能作個“觀光客”收穫良好的閲讀體驗。
荷蘭布爾哈夫科學博物館(Museum Boerhaave)東牆上紀念廣義相對論的圖像。上面是恆星光線因為太陽質量而彎曲的示意圖,下面是廣義相對論場方程(引自《捕捉引力波背後的故事》)
當然,直到今天,許多引力波探測的相關材料還未脱離“新聞”的範疇,大量工作仍處於正在進行時,道阻且長。現在就下歷史結論,為時尚早,亦無必要——“風物長宜放眼量”,真正引領“探險家”不畏“梁父之艱”者,不是結論,而是前方閃耀的問題。
附:末了,謹補綴幾處,與方家共參詳。
1. 費曼的“粘珠論”(p15):1957年,費曼(Richard Feynman)在北卡大學教堂山分校會議(即GR1)上以sticky bead argument論證引力波具有能量。此處的sticky bead,許多中文文獻譯為“粘珠”(有的甚至譯為“粘性水珠”)。誠然,sticky確有“粘性”之意,但結合該思想實驗的物理情境,sticky bead似應理解為“棍上的算盤珠”——費曼在巴西講學期間(1949~1952)曾同一個推銷算盤的日本人比賽速算(事見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 Adventures of a Curious Character. W. W. Norton & Company, 1985.)。
2. “整個恆星便會在重力壓迫下急劇塌縮”(p45,後文亦有多處出現“塌縮”):collapse,天體物理中的規範用詞應是“坍縮”。另,在此處相關的中文語境裏,“重力”一般指隨天體自轉(與天體表面相對靜止)的物體所受引力之豎直分量(另一分量為垂直指向自轉軸的向心力),在文中所述恆星坍縮的情境中,應用“引力”,而非“重力”。
3.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簡稱CERN”(p61腳註):CERN源自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前身歐洲核子研究委員會的法文全稱Conseil Européen pour la Recherche Nucléaire。
4. 加文(p67):1957年,加文(Richard Garwin)曾與萊德曼(Leon Lederman)共同完成了一個驗證弱相互作用下宇稱不守恆(楊振寧和李政道於1956年提出的設想)的實驗。
5. “那是1950 年代,勞倫斯正在伯克利發明他的粒子迴旋加速器”(p84):勞倫斯(Ernest Lawrence)發明並改進迴旋加速器是在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
6. “不僅引力與電磁力相比本身就顯得微弱”(p91):用兩個質子來做比較,則庫倫力與引力之比的數量級為1036;用兩個電子來做比較,則比值的數量級達到1042。
7. “地球的周長大約 4 萬千米”(p93):應明確為“地球大圓的周長大約4萬千米”。
版權説明:歡迎個人轉發,任何形式的媒體或機構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和摘編。轉載授權請在「返樸」微信公眾號內聯繫後台。
特 別 提 示
1. 進入『返樸』微信公眾號底部菜單“精品專欄“,可查閲不同主題系列科普文章。
2. 『返樸』提供按月檢索文章功能。關注公眾號,回覆四位數組成的年份+月份,如“1903”,可獲取2019年3月的文章索引,以此類推。
相關閲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