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triz Colomina:現代建築是冗長的肥皂劇_風聞
全球知识雷锋-以雷锋的名义,全世界无知者联合起来!2019-07-29 20:10
作者:孫志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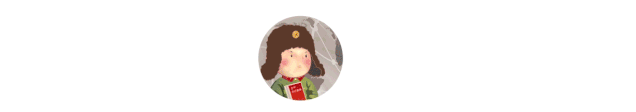
“我最近很少聽到Elia Zenghelis的抱怨了——早年他經常吐槽自己不遺餘力地參與實踐,但主流媒體卻只青睞庫哈斯,從不認可其他合夥人的貢獻。”
“建築史就是對話的歷史。”
“宛如幽靈的女性建築師無處不動人心魄、引人關注、舉足輕重,但奇怪的是她們都蹤跡全無、隱於幕後、不被認可,她們註定永恆困擾着建築學。”
“我們被共同的對現代建築的濃厚興趣牽引到一起,起初我們對彼此的思想激動萬分,就像兩隻海豚在觀點和想法的海洋裏上下遨遊。”

推薦語
本篇講座由曾師從於Beatriz的王子耕推薦
我在普林上學的時候上過Beatriz的一門課,叫“THE PERVERSIONS OF MODERN ARCHITECTURE”(現代主義的顛覆),副標題叫作“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It, But Were Afraid to Ask”(所有你想知道但不敢問的)。這門高階歷史課就是各種現代主義建築師八卦的串燒,它希望攪起現代建築的一潭死水,去揭示建築行業令人震驚的複雜性和豐富度,以及這個領域的各種怪癖和古怪。
Beatriz的方式就是局內人的飯局,飯局故事永遠比媒體世界精彩。她想顛覆的是對現代主義歷史書寫中的蓋棺定論的集體認識,探究建築和建築文化的生成機制、明星建築師體系下的英雄主義在媒體語境下的形變。她認為現代主義之所以現代,並不是因為人們通常理解的使用所謂現代材料,也不是因為空間的概念演變和去裝飾化,而在於它們和包括出版物、競賽和展覽在內的媒體的結合。而這種結合因為媒體的屬性而具備的欺騙性是對個人史和建築史的某種編篡,這種力量會讓某些人站在神壇,某些人默默無聞,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而這個講座關注的是現代建築著名案例背後的女性力量。有意思的是,昨天一個美國東岸的建築學院男性院長跟我説:我作為一個白男,如果現在退了,在美國的大學不會找到任何領導工作。
講座正文
我很榮幸應邀至此,在這做首場講座時我還是無名之輩,當然不是説我現在是個人物——因為86年我才開始撰寫學位論文。我在這間講堂做過三場演説,這也是對現代主義建築和大眾媒體思考的起點,我很喜歡和你們探討這類議題。
關於“合作”的問題如今愈趨緊要,是我們亟待解決的困境。一方面,它是廣義建築學中當代討論話語體系的根基,就像你希望更深入體驗SEER軟件平台一樣,因為它能使分散在五湖四海、各行各業的人們匯聚在同一個項目上出謀劃策。另一方面,理解傳統語境下建築的生成過程對歷史學者們來説是至關重要的,而現在建築愈發成為合作性領域——當然你很難讓建築師們認可這條無需贅言的事實,為什麼我們如此糾結這個問題呢?就像電影到了尾聲,你會在熒屏上標註所有的演員、化妝師、髮型師甚至提供餐飲酒水的服務人員的姓名,但我們行業不會這樣,我們在這種情況下甚至懶得多標註一個人名。
現代建築的秘密
即便是哈佛GSD的偉大女建築師們也概莫能外,例如大家都祈請文丘裏的妻子Denise Scott Brown也被授予普利茲克建築獎,但仍被拒絕了——為何它們建築公司明明認可Denise Scott Brown的功勞而普獎卻覺得這是無足輕重的?我認為這是所有人都需要深思的——這也是開啓演講的議題,你們從這個段落便能讀出女性在廣義建築學中的處境:《現代建築的秘密:我們不需要另一個英雄》(The Secret Life of Modern Architecture:We Don’t Need Another Hero取自擁有黑人和印第安人血統的美國著名女歌手蒂娜·特納的同名熱門歌曲,旨在質疑並破壞既存的權力結構,試圖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提供一種新鮮的語法,探索了個體自主思考與行動的潛能)。
現代建築的秘密:我們不需要另一個英雄
它的副標題是《你在或不在:現代建築的幽靈》(With or Without You: The Ghosts of Modern Architecture),因為在官方名單中女性建築師的姓名愈趨作為男性的附庸而被標註(如果她們被標註的話)。這是1903年的一位正在修復柏林市政廳屋頂的女性建築師,我們能看出女性從事建築業已有極漫長的歷史,只是我們很少注意她們而已。
你在或不在:現代建築的幽靈
柏林市政廳,德國,1903年
因此我説女性是現代建築的幽靈,例如看到這張照片,大家都情不自禁地發問:站在舉世聞名的巴塞羅那德國館前地毯上注視着展館的女子是誰?毋庸置疑這就是莉莉·瑞希(Lilly Reich),她不僅是密斯設計這座建築的密切合作者,還是密斯去往柏林後一直留守場地的藝術總監,此外同期她還在巴塞羅那策劃舉辦了不止23場精彩絕倫的工業展覽,所以她在這座展館設計過程中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
莉莉·瑞希(Lilly Reich)是德國現代主義設計師,在建築、傢俱、室內設計、裝飾藝術和服裝等方面都有出色貢獻
但我們仍約定俗成地説巴塞羅那展館是密斯的作品,而莉莉·瑞希在展館未開幕時審視(inspect)它的建造過程,所以我説女性是現代建築的幽靈。這是Lotte Stam-Beese(建築師和城市設計師,曾參與並主持鹿特丹戰後重建設計)在1927年的作品《Self Portrait》,這張照片是奧蒂·伯傑(Otti Berger),她在包豪斯時號稱“最有天分的學生”,設計風格極具表現力,但她最終被納粹逮捕並帶到了奧斯威辛集中營,於1944年與世長辭了。她們是包豪斯的重要成員——在這裏學習設計併成長為有能力選擇自身命運的人,當我們目光穿越歷史煙雲回望這段百年軌跡,女性的名字不該被忘卻。
左:Lotte Stam-Beese,右:Otti Berger
女性是幽靈?
讓我們回到“幽靈”的議題,這些圖片就很能説明問題了——宛如幽靈的女性建築師無處不動人心魄、引人關注、舉足輕重,但奇怪的是她們都蹤跡全無、隱於幕後、不被認可,我覺得她們註定永恆地困擾着建築學科,但治癒這種痼疾絕不僅是在建築史中添上幾個乃至數千個姓名那麼簡單的事。它不只是人類正義性或歷史準確性的問題,而是一種更全面地理解建築和它複雜成因的途徑。建築中的合作性是根深蒂固的,它更像電影而非視覺藝術,至少不像所有傳統的視覺藝術,但它也不很像電影——這一點很少被大家認可,就像內心深處的秘密被我們隱瞞至今。
所以我贊同一種説法:我們已經在現代建築史中“直截了當地”增添女性姓名這個方面做得很完善了,但根本上需要反思的還是建築生成的問題,以及某個人物為何能在其中獲得特權和榮耀。我並不是説不被認可的女性就不該接受更多專業訓練,而是想要更好地瞭解建築領域,我們需要解放新潛能,所以言語間的鴻溝、理解偏差、機構間警惕十足的保守主義都需要我們三思。暗示對方是輔助者、次要工作量完成者,表達合夥關係和平等地位,這本就是正當可取、無可厚非的,而它會滋長差異性和複雜性,或許會產生更具細微差別的生產模式和話語體系。
不是秘密的秘密
我給大家講一個自己探討合作問題的故事,約20年前我受邀去西班牙首都馬德里演講,剛好那也是我的故鄉,當時我已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到處演講——在耶魯、哈佛、普林斯頓和AA都有踏足,但你們知道在自己的國家你永遠都是無名之輩(笑聲)。所以他們最終認為我是值得一邀的,當地的男性主導的建築協會也同意我去演講,當時我還在查爾斯和蕾·伊姆斯(Charles and Ray Eames)那裏工作,所以講座主要關於他們的作品,尤其是我正參與的Eames House項目。讓我驚訝的是,晚宴後討論會的話題都集中在蕾·伊姆斯的畫家出身的作用上,以及她師從漢斯·霍夫曼(Hans Hofmann,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先驅,代表作品《門》)的學習經歷——他們似乎確實知道不少內幕。
Eames House,查爾斯&蕾·伊姆斯
當我展示項目的圖片時也談到漢斯·霍夫曼的畫作是如何在天花板上水平懸掛以及蕾·伊姆斯是如何跟着霍夫曼求學的,但自始至終從未展開篇幅去講蕾·伊姆斯的作用,所以他們引出這個話題使我倍感意外——他們對蕾·伊姆斯在合夥關係中所發揮的作用充滿興趣,在座不少聲名顯赫的西班牙建築大師,有些甚至在GSD任教,但沒有一個是女性。也正因我在講座中從未談到蕾·伊姆斯所作的貢獻和功勞,所以我認為在西班牙的討論會談這個話題是不合時宜的,我對此也了無興趣,那種情形下的討論重點也就順其自然地偏移(drift)了。
Eames House,查爾斯&蕾·伊姆斯
我們還聊到莉莉·瑞希,討論了她在密斯的建築設計中扮演過的諸多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例如1927年她和密斯受德國絲綢製造商協會委託在柏林“Die Mode der Dame”展覽中為德國絲綢業合作設計“天鵝絨和絲綢咖啡廳”(Silk and Velvet Café),他們僅通過懸掛在不同高度的絲綢和黑、橙、紅、黃等各色天鵝絨在連續空間中劃分不同的功能,這些色彩斑斕的織物(draperies)懸掛在直道和彎曲鋼管上,巧妙地溶解在整個公共空間中。
莉莉·瑞希1932年應密斯之邀任教於包豪斯,1947年逝於柏林
天鵝絨和絲綢咖啡廳(Silk and Velvet Café),柏林
在場所有人出乎意料地認可密斯在與莉莉合作之前的確沒有過此類風格的作品,這種通過懸掛表面(suspended surfaces)對空間進行根本限定的手法早已成為密斯的“馳名商標(trademark)”了,甚至在他的經典作品布爾諾圖根哈特別墅(Tugendhat Villain Brno)和1929年的巴塞羅那德國館中都能依稀看出蛛絲馬跡。這些話都説進了我的心坎裏,當然我從未公開表達過這些觀點——只是在研討課中有所涉獵,但在寫作文本中隻字未提。
圖根哈特別墅(Tugendhat Villain Brno),布爾諾
可見他們都認可莉莉·瑞希的個人貢獻,其中某位和我熟識的著名建築師説這就像建築圈裏不可明言的潛規則和深藏的小秘密(dirty little secret),這是所有建築師都保守的秘密,心知肚明卻永不宣之於口。其實這些掌握西班牙建築學院、主導各類機構的話語權的男性都對此有清晰的洞察和認知,所以在晚餐後的討論會上情不自禁地有感而發——就像他所承認的那樣,我也贊同這就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小秘密。
圖根哈特別墅(Tugendhat Villain Brno),布爾諾
現代建築的秘密像極了家庭裏的秘密:所有人都知道某件已發生的事,但大家都不願提及,或許因為我們當下的文化取向——大家往往都接觸熟人,所以這些小秘密並沒有逐漸被揭開(unveiled)。正如我們更關注“為什麼”而非“是什麼”,不再關心建築結構和建造工藝以及早期歷史學者的興趣點,更關注人際關係,所以從前隱於幕後的建築實踐中的細枝末節逐漸走向眾目睽睽之下。
巴塞羅那德國館,1929年
作為媒介的現代建築
公眾的關注點已從作為單一人物的建築師和作為某個實體的建築轉移為將建築視作合作產物,例如查爾斯·伊姆斯(Charles Eames)和John Entenza,大家為何時常在談論查爾斯·伊姆斯與他的Eames House時理所當然地忽略John Entenza?他身先士卒地在加州推動調研和案例考察,對項目貢獻匪淺,何以被輕描淡寫地忽視?所以合作也是多層次的、紛繁複雜的。今天我們對建築的關注早已被分配到項目中的各方專業人士身上:合夥人、工程師、景觀設計師、室內設計師、設計員工、建造者……甚至攝影師、平面設計師、評論家和博物館館長,這些在媒介中產出作品的人們也全都獲得關注了,所以在媒介中產生和作為媒介傳播的現代建築如今是絕無可能被忽略的。
Charles Eames和John Entenza
這是Julius Schulman拍攝過的理查德·諾依特拉(Richard Neutra,維也納建築師,曾在維也納技術大學研究Adolf Loos)在Palmer Street做的住宅或者建築師Pierre Koenig設計的洛杉磯斯塔爾住宅(Stahl House)的著名照片,可以説如果沒有這些珍貴相片,作品就永遠難以尋覓了。理查德·諾依特拉曾談到他的攝影師Julius Schulman,年輕的Schulman還在做時裝攝影師時就受僱於理查德了,對建築的拍攝還是一竅不通,理查德訓練他逐步走上正軌——他説這項工作同樣拯救了自己,因為膠片具有強大的魔力,光面照片(glossy prints)也比粗獷的混凝土、不鏽鋼乃至建築概念更易於被公眾關注,所以他認可攝影師工作的價值。
左:Palmer Street住宅,右:洛杉磯斯塔爾住宅
就連甲方這種過去被視為建築的“難題”和建築效果的見證者的角色如今也被當成設計過程中活躍的合作者,例如芝加哥著名醫生範斯沃斯就是密斯的經典作品範斯沃斯住宅的業主,所以許多聲明顯赫的建築作品都有甲方的功勞,這一點Alice T. Friedman深有體會,例如Alice在密斯工作室中與Mairon Goldschmitt在自宅項目中積極合作,這種戰後時期開創的全新合作實踐模式已愈加難以忽視,幾乎無法想當然地歸功於某位大師級人物提出的“史詩級概念”。
芝加哥單身醫師範斯沃斯女士——範斯沃斯住宅業主
範斯沃斯住宅,美國,1945年
Alice T. Friedman與Mairon Goldschmitt
MOMA在1950年舉辦過芝加哥建築事務所SOM(Skidmore, Owings and Merrill)的展覽,原本是不會羅列個人姓名的,但最終展覽手冊的封面目錄還是記錄了所有設計師。果然不出我所料,SOM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女性建築師Natalie de Blois的姓名被遺漏了——當他們羅列所有姓名時,男性的名字赫然在冊,但Natalie卻無影無蹤,即使她是參與所有項目的偉大建築師——包括Leber House、Pepsi Build和伊斯坦布爾的希爾頓國際酒店(Hilton International in Istanbul)。
SOM(Skidmore, Owings and Merrill),芝加哥
Natalie de Blois,SOM女建築師
Leber House,Pepsi Build,Hilton International in Istanbul
她在SOM從未得到過認可和職位晉升,所以最後離開了公司。我引用《財富雜誌》(Fortune Magazine)是因為當下的建築師和建築機構甚至比不上大眾媒體了,你能看到雜誌斬釘截鐵地將Natalie de Blois列為做過Union Carbide Tower項目的初步草稿圖的高級設計師(senior designer)。這張是她與菲利普·約翰遜(Philip Johnson,美國建築師、評論家、理論家,被埃森曼稱為美國建築界的“教父”)和馬里奧·薩爾瓦多里(Mario Salvadori,著有《建築生與滅:建築物如何站起來》)的合影,菲利普·約翰遜是很瞭解她的才華和貢獻的,然而公司完全不認可她,MOMA也在手冊的標註名單裏中不出現她的隻字片語。
《財富雜誌》將Natalie de Blois列為高級設計師
合作的新議題
其實在戰後的歲月裏,所有建築大師都在關鍵項目中嘗試合作,例如密斯與菲利普·約翰遜合作完成紐約西格拉姆大廈(Seagram Building),其中加拿大建築師Phyllis Lambert作為委託者、管理者和建築師的身份參與(intervention)項目,若非她的參與,這座堪稱20世紀最傑出的建築將沒有問世的機會。正是Phyllis Lambert用她獨具一格的伯樂般的慧眼挖掘出優秀建築師,説服他的父親西格拉姆併力薦傳統建築師密斯來做這個項目,所以是她的舉足輕重的作用成就了建築師和這座建築。
1943年瓦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創辦了年輕建築師們的合作聯盟,在1963年便與Emery Roth & Sons事務所合作泛美大廈(Pan Am Building)項目。如果你想聽其它案例可以去查閲更多文獻,例如華萊士·哈里森(Wallace Harrison)工作小組設計的紐約曼哈頓聯合國新總部大樓。雷姆·庫哈斯認為這種合夥關係往往會被我們忽略,即便它們常給建築帶來更多光怪陸離(idiosyncratic)的特色。
瓦爾特·格羅皮烏斯1943年創辦年輕建築師合作聯盟
泛美大廈模型,格羅皮烏斯&Emery Roth & Sons
泛美大廈,格羅皮烏斯&Emery Roth & Sons
聯合國新總部大樓,曼哈頓,華萊士·哈里森設計團隊
庫哈斯想表達的是1930年以後大師出現了反常,他説:“當他1930年開始與莉莉·瑞希合作時,密斯給大家留下了戲劇性的印象——顛倒與反常,從她的天鵝絨和絲綢咖啡廳到約翰遜的四季酒店,其中的聯繫是什麼?誰佔了優勢?”。這種觀點也正中我的下懷,庫哈斯明顯是站在建築師而非評論家和歷史學者的立場上直抒胸臆的,即使他所説的有悖事實——莉莉·瑞希早在20年代中期就開始與密斯合作了,但在關於合作的問題上他説的完全正確。
字幕:當他1930年開始與莉莉·瑞希合作時,密斯給大家留下了戲劇性的印象——顛倒與反常,從她的天鵝絨和絲綢咖啡廳到約翰遜的四季酒店,其中的聯繫是什麼?誰佔了優勢? ——雷姆·庫哈斯,1996
左:天鵝絨和絲綢咖啡廳,右:四季酒店
讓我們回到初始的議題——“合作”,它是現代主義的秘密,也是建築師心底的秘密,更是建築的本土文化生活,工作和生活都在一起的建築師們對此的理解更為深刻。夫妻檔合夥人需要在家庭生活和工作生活中找出明確的界定,所以我認為庫哈斯對合作問題的體察更像是個人化和自傳式的(autobiographical),因為OMA就是由兩對夫婦聯合創立的,扎哈·哈迪德中途加入OMA工作了一年時間,但最終還是怏怏不樂地離開了。所以庫哈斯和妻子Madelon Vriesendorp、Elia Zenghelis(希臘建築師,於1956-86年在AA教學)和前妻Zoe Zenghelis多次參與建築實踐——至少初期是這樣,而我最近也很少聽到Elia Zenghelis的抱怨了——早年間他經常吐槽自己為OMA的實踐不遺餘力地付出,但主流媒體卻總是隻青睞一個名字,大眾提到建築作品就直接聯想到庫哈斯,絕口不提OMA事務所,從不會認可其他合夥人的貢獻。
OMA由庫哈斯夫婦和Zenghelis夫婦聯合創立
夫妻合作的模範
蕾·伊姆斯和查爾斯·伊姆斯夫婦在20世紀50年代為後輩夫妻們提供了處理合作關係的範本——這裏的合作對象是指存在親密關係的雙方,艾莉森和彼得·史密森夫婦(Alison and Peter Smithson)的合夥關係甚至成了羅伯特·文丘裏和妻子Denise Scott Brown仿效的模範,下一代的恩瑞克·米拉萊斯(Enric Miralles)和前妻Carme Pinos也從其它夫婦中脱穎而出,他們都無比嚮往史密森夫婦的關係——兩人年輕時在烏爾比諾大學(Urbino)求學並相識相知,烏爾比諾是意大利中心的暑期學校,歐洲各地建築科班出身的學子們紛紛來此與吉安卡羅·德卡羅(Giancarlo De Carlo)一道學習兩個月。
左:查爾斯&蕾·伊姆斯,右:艾莉森&彼得·史密森
左:羅伯特·文丘裏&Denise Scott Brown,右:恩瑞克·米拉萊斯&Carme Pinos
其實瘋狂的個人崇拜和頌揚某位建築師的神話、鼓吹孤傲的天才,就是對建築的最為落後(regressive)和保守(reactionary)的理解。不幸的是我們的大環境依然瀰漫着這種風氣,所以向史密森夫婦學習是很有必要的,它時刻提醒我們女性建築師在合夥關係中獲取平等地位經歷了不止半個世紀的艱辛。藝術家瑪格麗特·麥克唐納(Margaret McDoland)和她的丈夫查爾斯·倫尼·麥金託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19世紀末20世紀初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先鋒室內設計師)合作,莉莉·瑞希與密斯合作,夏洛特·貝里安(Charlotte Perriand,現代主義早期法國最有影響力的傢俱設計師)與柯布西耶合作,艾諾·阿爾託(Aino Aalto)與阿爾瓦·阿爾託合作,但她們的非凡影響力從未得到充分認可。
左:格麗特·麥克唐納&查爾斯·倫尼·麥金託什,右:莉莉·瑞希&密斯
左:夏洛特·貝里安&柯布西耶,右:艾諾·阿爾託&阿爾瓦·阿爾託
只有查爾斯和蕾·伊姆斯在成立之初就將兩位創始人的姓名放在相對平等的位置,也只有在史密森夫婦這裏才能看到女性的姓名被放在首位,女性的作品得到完全認可,我不得不説美國東海岸的學術機構尤其是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紐約時報》甚至哈佛大學都沒有做到這一點。
查爾斯和蕾·伊姆斯成立之初就將兩位創始人姓名放在平等位置
史密森夫婦將女性姓名被放在首位,對女性的作品完全認可
以致《紐約時報》評論家Esther McCoy極度不安地給伊姆斯寫信道歉,並解釋了時報文章刪去Ray的姓名的來龍去脈,她説:“親愛的理查德和蕾,《紐約時報》的文章使我十分難堪,它也一定給你們造成了痛苦,原本該是5000字的段落後期按照要求削減至3500字,Paul Goldberger收到文章後便給我來電説寫得不錯,然後將我移交給編輯助理Barbara Wyden,這個人總是有無止境的抱怨,這裏不再詳述。最終我和他就兩件事進行據理力爭:首先是Ray的姓名必須出現,其次是“chaise”不能寫成“casting couch”……二十年來我一直都和編輯們和睦相處,如今到了1973年我遇到了兩位難以理喻的傲慢的編輯,他們指責我不瞭解廣大受眾羣體,但這純粹是一派胡言,廣大受眾絕不會反對女性的姓名被標註在自己的作品上”。
《紐約時報》評論家Esther McCoy
字幕:親愛的理查德和蕾,《紐約時報》的文章使我十分難堪,它也一定給你們造成了痛苦,原本該是5000字的段落後期按照要求削減至3500字,Paul Goldberger收到文章後便給我來電説寫得不錯,然後將我移交給編輯助理Barbara Wyden,這個人總是有無止境的抱怨,這裏不再詳述。最終我和他就兩件事進行據理力爭:首先是Ray的姓名必須出現,其次是“chaise”不能寫成“casting couch”……二十年來我一直都和編輯們和睦相處,如今到了1973年我遇到了兩位難以理喻的傲慢的編輯,他們指責我不瞭解廣大受眾羣體,但這純粹是一派胡言,廣大受眾絕不會反對女性的姓名被標註在自己的作品上。——Esther McCoy
這就是像Esther McCoy這樣的評論家們遭遇的阻力,但如果説《紐約時報》是糟糕的,那紐約當代藝術博物館就更差勁了,因為它們從來不認可蕾·伊姆斯的成就,在作品展覽中只標註查爾斯的姓名——寫着“查爾斯·伊姆斯於1946年設計的新傢俱”,更可悲的是伊姆斯工作室的老員工們也得不到對自己作品的署名——Gregory Aime、Coliver Toya、Herbert Matter和Griswold Raphael……結果自然就是他們全都辭職了,MOMA或許認為只標註查爾斯·伊姆斯的姓名會收穫不錯的反響,但這對事務所造成了很大後果——此時是事務所最高產、成果最豐碩的瞬間了,之後大家都離開了。其實他們私人關係極好,例如這是Herbert Matter的兒子Alexander Matter,他正騎在膠合木製的大象上玩耍,員工間的私下關係頗為親密,只是這種愚蠢的行為將它們全都葬送了。
作品展覽中只署名查爾斯——寫着“查爾斯·伊姆斯於1946年設計的新傢俱”
左:伊姆斯工作室老員工Gregory Aime、Coliver Toya、Herbert Matter和Griswold Raphael,右:Herbert Matter的兒子Alexander Matter
史密森的狂熱崇拜
而在1950年盛大的設計展覽中查爾斯和蕾·伊姆斯再次受邀參展,名冊再次沒有標註蕾·伊姆斯的姓名,還有Edward Hofmann,我印象中她參與了所有作品的工作,但也未出現在名冊中,只在手冊最後一頁寥寥幾行標註了她:展覽與手冊策劃助理,遠沒有表達出她真正的工作量。
1950年展覽名冊再次沒有標註蕾·伊姆斯的姓名
Edward Hofmann
甚至1973年的《紐約時報》的Arthur Drexler撰寫的介紹查爾斯·伊姆斯的設計展的文章,也沒有以妥當的方式標註蕾·伊姆斯,只提到她是“一位助理”,如果説這種媒體機構難以認可伊姆斯夫婦的合夥關係的話,史密森夫婦就截然相反,他們非常崇拜伊姆斯夫婦,經常寫深情洋溢的便箋給他們。
史密森夫婦與這對年長的夫妻往來書信中填寫的地址格式和語言習慣是相當私人化的,從信箋存檔中可以看出稱呼都是親暱的“RC”、“R和C”和“A和P”,結尾也大多是感情奔放的(effusive)表述——例如“我們經常想念你們”、“無盡的愛”,字裏行間都是充斥着景仰之情的表述,每封信中都高度認可伊姆斯的作品,説這些作品是指引他們實踐的珍貴圖騰、魔法徽記和榜樣範本(pardigms)。
史密森夫婦與伊姆斯夫婦往來的書信
例如對於伊姆斯設計的椅子,史密森夫婦會寫道:這椅子就像從另一個星球降臨的希望的訊號,如今只有這把椅子才適合在室內出現,是絕無僅有的能放在客廳的椅子。他們説伊姆斯的椅子是屬於使用者的,不準確,是專屬於這對夫婦的。
伊姆斯夫婦設計的椅子
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觀察時説密斯的椅子也是屬於使用者的,也有人説它早已融為建築的一部分,不屬於使用者,我覺得所有人都會贊同這一點,但我曾看到SANAA的西澤和妹島一起坐在其中一隻椅子上翻閲書籍,正是他們在巴塞羅那德國館設計了美麗的裝置,他們很合適——我是指身體在密斯的椅子中感到很舒適。
巴塞羅那德國館中密斯設計的椅子
西澤立衞和妹島和世坐在密斯設計的椅子上
伊姆斯選擇和排布的手法也受到史密森夫婦的褒揚,他們説:“這種設計手法接近於插花的藝術,增添了功能空間的高雅品味”,他們還聲稱要將這種手法化用到自己住宅的設計與佈置之中,伊姆斯總是向美麗的事物致敬,這是非同尋常的,但在我們的現實世界中,美麗的事物似乎總被理解成缺乏社會責任。
對於伊姆斯獨樹一幟的拍攝技術,史密森夫婦寫道:“我們是伊姆斯作品的忠實傾聽者和觀眾,對任何作品都充滿迷戀,我們將吸收他們對平面色彩選用和刻畫物體中的經驗作為工作的重要環節,我們敏鋭地觀察伊姆斯作品的方方面面,力求在每個案例中都展現出他們的優點”。
伊姆斯夫婦的作品照片
同時史密森夫婦借鑑了優秀的手法並充分吸納,例如從伊姆斯的椅子中獲取靈感從而順利做出改良,正如他們曾寫過傢俱設計的心得:在項目的第一張室內草稿圖中,我們意識到了存在的大問題:什麼才是應該在我們傢俱中出現的?我們需要的是彰顯文化和技藝的物體,而不是倒退成法國暢銷的、曾被柯布西耶使用過的Thonert椅子,我們要做一款你認為它會時刻跟隨你的椅子,在每個房間都伴隨着使用者,甚至跟着你去海灘”,所以這就是史密森夫婦設計的椅子。
史密森夫婦改良前後的椅子設計
讓人大跌眼鏡的是,這個設計剛出世就被恩瑞克·米拉萊斯和Carme Pinos借鑑了,他們重新設計了住宅並佈置了室內。史密森椅子完美展現出了他們所説的取自伊姆斯椅子的特色,它們佔據了Thonert椅子騰出的空間,雖然他們源自同一建築時期。例如史密森的住宅明顯是從伊姆斯夫婦那裏獲取的靈感,但同時是有區別的,它們屬於使用者而非建築。所以史密森逐漸取代了伊姆斯的地位,不斷吸取他們的操作手法而非形式上的細枝末節。史密森和伊姆斯關鍵的區別並不是史密森對伊姆斯某些層面無止境的借鑑,而在於兩對夫婦呈現自我的方式以及他們表現出的感情。
建築界的“教母”
最重要的是,當一對夫婦與另一對組合在一起時,他們家庭生活(domesticity)的理念便會發生化學反應,產生奇妙的共性,正如彼得·史密森對伊姆斯的早餐桌進行沉思,這張早餐桌就像是一種建築形式,這也能追溯到瓦爾特·格羅皮烏斯和艾斯·格羅皮烏斯(Ise Gropius)在馬薩諸塞州的家裏的早餐桌。最後一張是某個下雪的清晨艾莉森在Fonthill的鄉村住宅坐在早餐桌前的照片,所以它們都體現出一種概念意義上的家庭生活。
伊姆斯夫婦的早餐桌
瓦爾特·格羅皮烏斯和艾斯·格羅皮烏斯的早餐桌,馬薩諸塞州
艾莉森·史密森的早餐桌,鄉村住宅,Fonthill
在同一篇文章裏彼得梳理了從文藝復興時期至今的建築歷史,其實這就像一個六口之家——萊昂·巴蒂斯塔·阿爾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建築師、作家、詩人、語言學家、哲學家)、Francisco di Giorgo代表文藝復興的時代,而密斯、伊姆斯和史密森則代表現代建築的三代人。你們看到海報上的字了嗎?Piper Editorial是在此舉辦過的一場講座,這張海報就是哈佛的一位學生在彼得·史密森從倫敦來電的遠程口頭指導下完成的。
文藝復興時期的三代人&現代建築時期的三代人
因此文藝復興和現代建築時期都有三代人,史密森夫婦繪製了不少譜系圖,我難以置信的是他們堅持將自己納入現代建築的譜系,並在文章中用如此明智的方式進行交流——史密森夫婦將自己視為密斯的傳統理念的沿襲者,我也很難釐清(disentangle)彼得自己的思考是什麼。他的作品是從密斯的巧思中獲取的靈感,甚至自己都無法區分哪些是獨立思考,哪些是源於密斯,但可以説密斯是他們必然景仰的超級英雄,而伊姆斯夫婦則像他們摯愛的表親,是二戰前後第二崇拜的偶像。
史密森夫婦
彼得在1956年展覽的講座中把展館設計與伊姆斯住宅聯繫起來,他指出伊姆斯夫婦都對密斯1934年繪製的玻璃住宅(Glass House)項目草圖無比諳熟,這再次説明不同項目衍生出不同的譜系(genealogies),這是很有趣的。讓我們再次回到女性的議題,彼得·史密森是首批指出現代建築界女性重要性的建築師之一,他在文章中不斷強調女性的地位,稱之為“母系(female line)”——這是一種永恆傳承(inheritance)、綿延至今的價值,他還提到幾個名字:莉莉·瑞希、夏洛特·貝里安、蕾·伊姆斯……這種“母系”當然還會繼續傳承下去。在彼得看來,艾莉森·史密森就是眾多他需要致以崇高敬意(homage)的“教母(founding mothers)”之一,在建築業我們總是討論“教母(founding fathers)”,我還真是第一次聽到“教母”這種説法。史密森比同時期的歷史學者和評論家對於女性在建築歷史上的存在更敏感,但他們所説的女性通常是夫妻檔中的一員,如果缺了一位有影響力的重要人物,就並不在他們認可的所謂合夥關係之列。
現代建築的英雄主義
瑪格麗特·麥克唐納和麥金託什,你們可能從來沒聽説過瑪格麗特·麥克唐納,麥金託什用了他整個人生在表達自己既平庸又天才,我不禁回想起20世紀早期某個時候,瑪格麗特·麥克唐納和麥金託什剛在一起,他們共同在維也納舉辦了一場展覽,所有的報刊雜誌都在議論瑪格麗特·麥克唐納,説這位紅色頭髮的女強人做了偉大的項目,幾乎沒有提到麥金託什,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呢?為何當時的記者和評論家們都只關注她?而18年後我們談到麥金託什時並不知道他一直在説自己是普通人,而瑪格麗特·麥克唐納才是極具才華的。
左:瑪格麗特·麥克唐納,右:查爾斯·倫尼·麥金託什
他為什麼這樣説?肯定是有原因的對嗎?瑪格麗特·麥克唐納和查爾斯·倫尼·麥金託什,夏洛特·貝里安和柯布西耶,莉莉·瑞希和密斯……這也是每對夫婦區別於其它夫妻的方式。正如艾莉森所説:我能看到蕾·伊姆斯所有的貢獻和她對自己內心真正想要的目標的不屈不撓追求的韌性(perseverance),儘管秘密在揭開之前我們誰也不知道真相。
蕾·伊姆斯
當寫到密斯時,彼得突然彷彿自言自語地評論道:我想更多地瞭解莉莉·瑞希,在對這句直言不諱的評論的腳註中他又寫道:我想更多地瞭解莉莉·瑞希,通常大家都不會在學術書籍上寫這種話對嗎?他是指《Ludwig》書中出版的密斯與莉莉1933年拍的照片,這本銀皮書主要介紹紐約當代藝術博物館珍藏的密斯的傢俱,但他沒説到照片中密斯與莉莉坐在同一條船上,他們看向彼此的方向,但凝望的視線從無交集。
莉莉·瑞希與密斯,1933年
我感興趣的不止異性戀組合,例如彼得討論的現代建築的英雄主義時期的約翰內斯·戴克爾(Johannes Duiker)也引起了我的好奇,彼得寫道:我無意於探究戴克爾和貝魯納·畢吉伯(Bernard Bijvoet)間的恩怨情仇,我只是將他們視為豐碑式的人物,其實戴克爾和畢吉伯合作完成過大量建築——包括位於荷蘭希爾弗瑟姆的聞名遐邇的Zonnestral Sanatorium和阿姆斯特丹不少學校的活動區……我們聽説過這些項目是合作的嗎?當然不是,我們傾向於認定這是戴克爾的作品,同樣的事情就在畢吉伯前往巴黎參加聚會和與人合作時發生過數次,去年在美國的博物館舉辦過一場精彩的展覽——充滿詳盡的文檔和不俗的材料,可憐的畢吉伯雖然參與了項目合作,但他的名字甚至從始至終未出現在記檔中。
約翰內斯·戴克爾&貝魯納·畢吉伯
左:Zonnestral Sanatorium,希爾弗瑟姆,右:阿姆斯特丹學校
因為他們的合作發揮了效果,而戴克爾從未單獨做得比與畢吉伯合作時更出色,正如艾莉森曾告訴我當她得知恩瑞克·米拉萊斯與他前妻Carme Pinos離婚時很悲痛,這兩人也非常不悦——似乎是他們自身原因導致感情破裂的,恰好1992年他們同時在紐約,我便邀請他們來普林斯頓大學演講,然後米拉萊斯對我説:“貝奧特利茲,合作產生的合力遠大於各部分的總和,大家都貢獻出力時就會產生奇妙的效果,我們兩人的任何一方都再也不可能達到從前合作時的成就與高度了”,果然一語成讖。我們繼續談畢吉伯:畢吉伯與他的妻子孩子抵達巴黎,他的妻子正是戴克爾的妻子,什麼意思?他們一直住在同一間公寓,最終畢吉伯與妻子離婚然後娶了戴克爾的妻子Erminne,總之整個現代主義建築史就像是大型連續肥皂劇,我們對此諱莫如深,但我們不得不研究它,既然它極其有趣我們為什麼不能聊?它能揭示很多曾發生過的真實故事。
畢吉伯與戴克爾的妻子Erminne
回到英雄主義時期的開端,這本是我最喜歡的講現代建築的書籍,從中我們明顯看出史密森夫婦對合作很感興趣,在他們看來,建築史就是對話的歷史。封面上並不是約定俗成地印着一位英雄主義建築大師,只有密斯和柯布西耶在邁爾霍芬(wiesenhof)的土地上討論項目,柯布西耶和格羅皮烏斯在巴黎的咖啡廳不斷爭辯和交流。
左:密斯和柯布西耶,右:柯布西耶和格羅皮烏斯
合作的價值
國際現代建築協會(CIAM)和“十次小組”(Team 10)為他們提供了參與更廣泛對話的契機,而國際現代建築協會的成員們到了“十次小組”的新環境下更像是英勇的戰士。所以艾莉森也説過“十次小組”是一個小型家庭組織,每個成員都千差萬別但大家彼此都知根知底,所以合作總能產生更棒的想法,這就又回到了合作的話題,他們合作中每個人所發揮的價值遠大於獨立工作的成果。
國際現代建築協會(CIAM)是在瑞士成立的首個國際建築師非政府組織,全稱Congrès International d’Architecture Modern
“十次小組”(Team 10)是以史密森夫婦為首的青年建築師組織
恰逢Pierre Jeanneret去世時,艾莉森做過一場感人肺腑的報告,艾莉森和彼得寫道:我們有各式偉大的住宅,例如範斯沃斯住宅和幾年前的魯道夫住宅(Rudolf House),最早的記錄是來自1946年6月27日的《建築師》雜誌,主要講述了已逝的建築師Pierre Jeanneret的思想,這座住宅就是他與法國建築師Jean Prouvé愉快合作的結晶——Prouvé在選擇合作者方面的確很不幸。史密森夫婦通過演示Pierre Jeanneret與Prouvé合作的住宅來向他致敬,他們將他從柯布西耶的巨大光環中摘取出來,講他的合作過程、Prouvé遇到的問題和幸福的婚姻。他或許很值得我們學習,因為Prouvé與眾多一脈相承的優秀建築師合作過,包括法國著名建築師託尼·嘎涅(Tony Garnier)、柯布西耶和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y)的建築師……
艾莉森致敬Pierre Jeanneret的報道
Pierre Jeanneret與Jean Prouvé合作
Jean Prouvé曾與眾多優秀建築師合作
我記得Jeanneret發明了那個世紀最難以捉摸的合夥關係,但他確實對柯布西耶的作品產生過啓迪。我對柯布西耶做過不少研究,因為我的學位論文就是關於他的,所以花了數年時間研究他,但我從不知道他竟這麼矮,並不是説他是大高個,他確實身形較為矮小(笑聲)。
Pierre Jeanneret與柯布西耶
我曾帶領學生去印度昌迪加爾授課,當地人無比崇拜Jeanneret,因為他花了數年時間參與建設這座城市,他熱愛印度——甚至死後想葬在那裏,然後我開始關注Jeanneret,這時才覺察我們從前對此人知之甚少,這張照片是他與柯布西耶在海灘上打拳擊。
昌迪加爾,印度
Pierre Jeanneret與柯布西耶在沙灘上打拳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