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維:中美貿易戰,是一場冰凍和平之戰_風聞
大牧_43077-2019-08-01 13:42
潘維:中美貿易戰,是一場冰凍和平之戰作者:潘維
本文轉載自:科工力量(ID:guanchacaijing)
在21世紀第一個二十年行將結束時,國際關係呈現出美中嚴重對峙的新局面。如何理解美中對峙,理解這個新的世界大局?
用歷史的眼光看現在,是理解現在的普遍和有效辦法。但歷史眼光有方法論問題,歷史不重複,太陽下每天都發生新鮮事。21世紀的國際關係正在發生重大變化。
理論為理解過去和現在提供了大多數概念,援引各種現成的國際關係理論也是辦法。儘管社科理論對未來的預見力並無根據,但理論翻新,為新事提供包含舊事的新解,能促進知識進步。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什麼,有什麼用?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戰爭與和平;能解釋戰爭的原因與和平的條件。
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認為,破解戰爭與和平的密碼藏在國際“結構”裏。國際結構即大國相對實力的狀態。主要大國間相對實力的變遷塑造結構變遷,結構變遷塑造戰爭與和平。
現實主義理論把自己溯源到《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作者是古希臘雅典城邦的修昔底德。書成時,2400年前的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還正在進行。該書主要敍述雅典城邦與斯巴達城邦的利益衝突,但其中有句近乎常識的判斷:戰爭的根本原因在於斯巴達對雅典迅速崛起的恐懼。現實主義理論之源就是這一句話。
 戰爭形勢圖,紅色為雅典陣營、藍色為斯巴達陣營、灰色為中立陣營、綠色為非希臘世界、黃色為波斯帝國。(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戰爭形勢圖,紅色為雅典陣營、藍色為斯巴達陣營、灰色為中立陣營、綠色為非希臘世界、黃色為波斯帝國。(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在抵抗波斯侵略希臘的戰爭中,雅典一舉上升為主力。驕傲的雅典在戰後大力對外擴張,壓迫其他城邦繳納保護費。由於斯巴達強大,與雅典一樣是希臘城邦效法的典範,所以是雅典擴張的障礙,雅典採取了敵視斯巴達的政策。修昔底德不知道: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雙方都是輸家,出兵幫助斯巴達、給雅典最後一擊的波斯也是輸家;贏家是半島北方名不見經傳的“馬其頓”。
實力對比變化的“結構”能解釋“誤判”?雅典能否與斯巴達合作,讓兩匹馬共同拉動希臘城邦世界?因“恐懼”而發動戰爭的斯巴達一定要恐懼、必須發動戰爭?
國際結構的變遷取決於國內狀況。外部壓力可能促使國家衰弱,也可能促進國家強大;缺乏外部壓力的效果也一樣。核武器本身不是結構,卻塑造“結構”。核武器是否改變了戰爭的原因與和平的條件,甚至改變了戰爭與和平的定義?
國際關係理論不只有“結構現實主義”。但“其他”理論大體屬於唯心的“理想主義”,不強調物質實力,也不強調戰爭,主要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長達70多年的和平。有的理論強調“觀念”塑造國家利益,強調“觀念”實力的分佈,演變成今天的“軟實力”概念及“講好中國故事”;有的強調以“自由市場觀念”為基石的“國際機制”導致和平;有的強調全球經濟分工導致合作與和平;還有的強調“政治文化”,即各國不同政體及文化傳承導致戰爭與和平,如中華文化偏好和平、美國文化偏好戰爭,自由民主制導致和平、其他制度導致戰爭。還有強調性別的,稱女性領導外交國防導致和平,男性導致戰爭。
然而,迄今為止,各大國都注重物質實力對比和更先進的武器,關注核武器及其擴散,關注影響實力對比的結盟交友。地緣政治研究顯然還是國際關係研究的基本功。
翻新現有的理論,有助於理解美中對峙的國際新態勢。
一、不變的國家:國際關係的主體
自美中對峙開始,以往半個世紀裏被津津樂道,幾乎被提升為“國際體系單元”的跨國公司、國際NGO、官方和非官方的國際組織,全都黯然失色。國家(nation,加“民族”二字,譯作“民族國家”,是蛇足),特別是大國、超級大國,還是組成國際關係的主體,中小國家是大國結盟交友的對象,這個判斷已經熬過了半個世紀的挑戰。
與21世紀之前相比,國家有什麼變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關係變成了“大國”甚至“超級大國”間的事。傳統的歐洲列強和亞洲的日本變成了“中等國家”。春秋末的吳越爭霸曾震動中原。但僅半個世紀後,起初有數百成千城邦/國家的“春秋”時代就被僅有7大國的“戰國”時代終結。吞併了吳國的越國被楚國吞併,什麼“震動”都沒有。
土耳其的搖擺,南亞的印巴對峙,阿拉伯人與波斯人在中東的對抗,並非文明的衝突,而是域外大國地緣政策的結果。
現實主義強調地緣政治,即強調地理條件的結盟交友政治,以改變大國間的實力對比。然而,從根本上説,是大國間相對實力的增減塑造了結盟交友狀態的變化。
若形不成統一的對外政策,區域經濟共同體無力構成國際體系的單元。這些區域經濟共同體有大有小,大中套小。其內部關係各自不同,有的緊密、有的鬆散,不過這些僅能反映經濟聯繫的鬆散或緊密,無力形成穩定的、統一對外政策。
因為協調對外政策,東盟引人矚目。但在大國對峙的撕扯下,東盟對外政策協調很有限。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各種經濟共同體沒有明顯進步,因為被各種外部勢力任意撕扯。南美洲的經濟共同體能否進步到歐盟的程度?共同的語言和宗教,以及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的均衡性,如人均GDP都在1萬美元上下,似乎意味着統一對外政策的巨大潛力和希望。但南美洲與美國近在咫尺,很難辦成不符合美國利益的事。
歐盟是另類。那個超國家的奇特結構遠遠超出了“經濟共同體”範疇,經常制定統一的對外政策,成為當今國際關係裏舉足輕重的一方,難以預料的因素不定哪天就刺激出一個近5億人口的“歐羅巴合眾國”。然而,正如比利時的政治被荷蘭語區和法語區撕裂,布魯塞爾的權力不在布魯塞爾。不僅柏林和巴黎在對外政策上的一致性不太穩定,歐盟內部東西南北的各方勢力比日耳曼和拉丁的“兩分”複雜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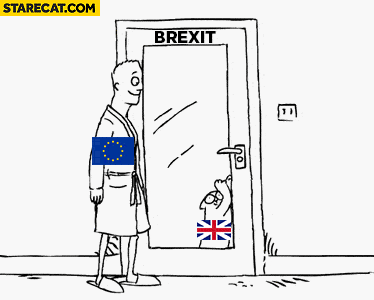 歐盟也不是百分百團結(圖片來源見水印)
歐盟也不是百分百團結(圖片來源見水印)
而且,面對強大俄羅斯軍事力量的歐盟,並無統一的軍事力量,要依賴美國保護。若非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登陸歐洲,西歐會被戰勝德國的蘇聯吞併。諾曼底登陸與其説是給了法西斯德國最後一擊,不如説是美國拒止了蘇聯西進。歐洲民眾感激美國保護了其自由生活。
為什麼“民族鬥爭高於階級鬥爭”?就促進文明演進而言,人類羣體間的生存競爭遠比羣體內成員間的競爭更重要。原本遊蕩的狩獵採集部落聚合為定居的城邦,城邦聚合為國家,國家聚合成大國,幾乎就是人類文明史的全部。
超級大國可以被擊敗,卻難以被消滅,重新崛起的希望比中小國大得多。成為超級大國有四大條件:廣土、眾民、先進強大的軍隊,第二次核打擊力量。俄羅斯有廣土,卻缺乏相應的眾民;印度和日本有眾民、卻缺乏相應的廣土;巴西有廣土眾民卻缺乏強大和先進的軍隊,也沒有核武器。
二、新興力量:核武器與長期和平
在21世紀,長期和平是可以預見的。由於本國戰爭力量不可靠,所有“舊”文明都從長期和平中看到了“復興”希望,並努力追求復興。長期和平就是復興的“戰略機遇期”。不僅中國想“偉大復興”,還有阿拉伯、伊朗、土耳其、印度、俄羅斯、歐盟。自二戰後贏得了絕大多數“戰役”卻從未贏得過“戰爭”,世界霸主美國也要從世界各地收縮,從而“再次偉大”。
強盛的阿拉伯帝國曾持續了500年,但那帝國800年前就滅亡了。缺少強大國家為依託,阿拉伯人復興的希望最渺茫,土耳其和伊朗的情況也類似。而行將擁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印度則滿懷希望。在復興大潮裏,中國潛力最大,廣袤國土上有佔世界1/5的人口,加上1萬美元的人均GDP,加上先進強大的軍隊,再加第二次核打擊力量,中國的崛起正在迅速改變國際結構。
結構變化會導致戰爭?雅典的迅速崛起會導致伯羅奔尼撒戰爭?是結構迅速變化還是敵意和恐懼導致戰爭?這些也許不再重要。關鍵在於,什麼導致了長達70多年的世界和平?
“第二次核打擊力量”指的是在遭受飽和的核攻擊後,依然擁有徹底摧毀對方的核報復能力,即讓雙方同歸於盡的能力。
由於第二次核打擊能力,“冷戰”中出現了“核威懾”理論。這個理論的邏輯分三段:
1. 第二次核打擊能力確保雙方相互摧毀,同歸於盡,戰爭從此不再有勝負;
2. 為勝負而進行的常規戰爭會“升級”,越接近失敗就越接近於使用核武器;
3. 一旦使用核武器,核威懾失效,人類末日就降臨。
換言之,核武器僅能用於(心理)“威懾”,是“絕對武器”,不是“常規”武器,不是“可使用”的武器。
第二次核打擊能力是保障大國間不發生戰爭的絕對力量,從而維護了世界的長期和平。有核國家集體承諾對無核國家不使用核武器。也就是説,非核國家大多處在核保護傘下。
由於第二次核打擊力量,和平是可以預期的。於是,極的數量,即“單極、兩極、多極”,同國際關係的“穩定性”,即大國間發生戰爭的概率,沒關係。當沃爾茲的“結構”與戰爭無關,就與和平也無關,沒有戰爭也就無所謂和平。
然而,有三個現象令人困惑。
第一,在美蘇爭霸的“冷戰”時代,為什麼雙方都沒有“足夠”的概念,各自積累了多達兩萬個核彈頭?
第二,明知常規戰爭有“升級”到核戰爭的可能,也就是“戰敗/戰勝”已經不可能,為什麼超級大國迄今還在激化針對彼此的常規武器競賽?
第三,美國明明懂得常規戰爭有“升級”可能,為什麼還在不斷公開談論製造和使用“戰術核武器”,也就是“能使用”的核武器?“核威懾”理論發明於美蘇冷戰期間,美國學術發達,對核威懾的理論研究最深入,為什麼反而是美國在挑戰核威懾理論?
第一,核威懾的本質是心理戰。世上從未有過核國家對核國家的戰爭,核威懾理論未經現實檢驗,使用核武器和行使核報復有不確定性。如此,囤積比對方更多的核彈頭,為的是向對方不斷昭示核報復的決心,從而降低不確定性和賭博心理。
第二,“打贏”了冷戰,美國再無平衡其軍事實力的對手,賭博心理大幅增強。美國因常規軍力優勢而偏好“戰爭邊緣政策”,本意是使對方因承受不住心理壓力而投降。但心理壓力是雙方的,戰爭邊緣政策可能失控,導致戰爭。一旦有大國捲入,常規戰爭會升級,有升級到核戰爭的不確定性。
核威懾是心理戰。據説,在蘇聯對華使用核武器的壓力下,毛澤東曾向美蘇雙方公開自己的戰略:若蘇聯核打擊中國,儘管中國核彈頭數量少,運載工具飛行距離有限,但會全部扔到亞洲的美軍頭上,打破美蘇核平衡,並讓中國人迅速移居廣袤的西伯利亞。核威懾崩潰的前景不確定,但這種不確定就是確定。
核威懾理論繫着全人類的生存,“潘多拉的盒子”絕對不能被打開。核威懾理論未經實踐檢驗,卻不可檢驗,不能失效。使用“戰術核武器”的國家必須遭到所有核國家至少“對等”的核報復。這種共識不難形成。
核武器的“不可使用性”,能解釋核大國間常規武器競賽的不斷升級。然而,因為中國的剋制,美國打擊中國的軍事威脅貌似佔了上風,卻極其危險。中國一貫在“忍無可忍”之後才“後發制人”,追求一擊制勝,絕地反擊沒有升級的階梯。
而今常規武器競賽進入了太空、進入了網絡世界、進入了數字般精準的對生產和生活基礎設施的廉價打擊。而且,高爆彈藥運載工具的飛行速度達音速的5倍甚至10倍,防不勝防。然而,在數字技術門檻不斷降低的時代,打擊技術的壟斷期限越來越短。無論軍事打擊伊朗還是朝鮮,美國的勝利都不是確定的,美國顯然已經意識到這個現實了。
用“網軍”進攻他國的“超限戰”,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使用化學武器一樣,會反噬自身,美國早晚也會理解這個邏輯。
換言之,由於存在“絕對武器”,長期的世界和平可以預期。然而,這世界真的不再有戰爭與和平問題了?
三、戰爭的新定義:冰凍的和平
傳統戰爭的目標是摧毀對手的軍事力量,間接摧毀支撐其軍事實力的經濟主權和經濟實力。若不可能摧毀對手的軍事實力,是否可能直接摧毀對手的經濟力量?
熱戰是政治的最極端手段。20世紀後半期,美蘇間採取除熱戰之外的一切政治手段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美蘇“冷戰”是21世紀新型戰爭的前奏,但其目標還是傳統的,即摧毀對手的軍事力量,導致對方崩潰、投降。
用非熱戰的種種政治手段摧毀對手的經濟力量,顯然也是戰爭。經濟是靠交往獲利成長的。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新型戰爭的基本形式是用政治手段切斷對手的國際交往,封堵與對方的交流,諸如商品、人員、技術、通訊、金融,等等。
這手段似乎不新鮮,“經濟制裁”是老套路。然而,在傳統戰爭中經濟制裁是輔助手段,在新型戰爭中是主要手段。經濟制裁原是大國對付中小國家的辦法,在新型戰爭中則針對超級大國。
新型戰爭發生在超級大國間,在全球供需鏈上的其他國家鮮少能獨善其身,所以也是新型的世界大戰。
在這新型戰爭中,美國進攻,中國防守。美國發動了閃電戰般的“脱鈎”突襲,中國乃至全世界陷入恐慌。
在21世紀,戰爭與和平融為一體,戰爭與和平可以有新的定義。冷戰爭就是冷和平,冷和平就是冷戰爭,戰爭的烈度用相互交往關係的冰冷程度衡量。冰凍和平(freezingpeace)就是在進行戰爭。冰凍的和平(frozen peace)是戰爭的最高點。交往增多就是緩和;緩和到正常温度就是一般意義上的和平。
若美國認定中國經濟實力來自中國經濟與美國經濟“掛鈎”,用政治手段強行“脱鈎”就可能使中國經濟衰敗。若美國認定中國的國際經濟競爭力來自中國“官民一體”的經濟結構,以“脱鈎”壓迫中國自行拆掉這結構也可能使中國經濟衰敗。
自“常平倉”以來,特別是“鹽鐵官營”以來,官民一體的中國經濟結構已有兩千七百年曆史。這個經濟結構是中華“大一統”的前提,而今在國際上被廣泛認為是中國經濟競爭力的核心。
美國發動戰爭的目標是摧毀中國經濟實力。“貿易不公平、偷竊技術產權”之類的外衣終將被剝掉,真實目標是中國“經濟結構”,手段是與中國全面“脱鈎”。脱鈎是大棒,不得不暫時維持的掛鈎是胡蘿蔔。寄希望於中國內部的“內應”,美國誘使及迫使中國拆掉自己經濟結構的攻防戰將越來越激烈。
在供需全球化的時代,發動針對世界第一大生產和市場國的世界大戰,看上去不僅瘋狂,而且荒謬。儘管現在不可能預言結果,但從邏輯上看,美國處於“失道寡助”的境地。切斷中國與世界經濟交往的努力,甚至可能演變成美國的自我封鎖,所以眼下幾乎沒人認為美國能取得這場新型世界大戰的勝利。
然而,脱鈎戰在我們眼前發生了,攻方控制着主動權和節奏,正產生經濟、政治、社會的嚴重後果。而且,與西方社會經濟隔絕的蘇聯也是超級大國,確實在“冷戰”中崩潰了。蘇聯當權者認為,美國對蘇聯的要求與蘇聯全面進步的必然方向“相向而行”。期待“融入”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蘇聯選擇了“自殺”。
最好的前景是多數國家,包括其他大國,選擇中立,與雙方保持經濟交往。最壞的前景是中美完全脱鈎,中國被迫建設獨立於美國的產業鏈,並開拓國內外新市場。在未成現實之前,我們不可能猜得到兩個或若干個獨立產業鏈共存是怎樣的狀況。就已知條件而言,中國產業鏈的成本遠低於美國,還在欠發達國家中持續攤薄。而在政治穩定的前提下,產業鏈競爭力取決於成本。
 中國製造以涉及到方方面面,且物美價廉(圖片來自百度百科)
中國製造以涉及到方方面面,且物美價廉(圖片來自百度百科)
資本肯定是逐利的。避免最壞前景,我們本應寄望於“資本沒有祖國”。但在戰爭條件下,資本有祖國,遵守本國法律。
為避免“冷凍的和平”融化,美國進行“長臂管轄”,不許包含美國公司技術成分的中國產品銷往國外。然而,“長臂”的耐久力很可疑。喪失了中國市場,美國技術公司靠什麼生存?
四、舊理論:中美髮生對峙的原因
中美對峙本會發生在21世紀初,突發的9.11事件把美國的注意力轉移到“反恐”。由於越反越恐,中美對峙被拖延了近二十年,其間中國經濟實力大幅增加。美中衝突若在21世紀初發生就不會如此激烈,目標也未必是遏制中國經濟。
到底是什麼導致了2018年3月開始的中美對峙?
對峙發生時,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很大,美國經濟持續上升,甚至有過熱的疑慮,但此時雙方經濟狀況與美中關係基本無關。
雙方的經濟狀況在貿易戰一年半以後的現在開始顯現不同:美國的戰爭威脅在中國引發了資本恐慌和外流;而收入持續上升的美國消費者對中國產品價格的微漲卻沒什麼感覺。真正脱鈎後會怎樣,我們很難假設。
很少有人相信美中對峙源自意識形態或政治體制差異,但雙方都有人聲稱:美國“容許”與中國加深經濟交往旨在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使之向西方政治體制方向演化。當這個目標遭到明顯失敗,美國就發動了絕交戰。
加深經濟交往為的是改變對方政治體制?美國與沙特阿拉伯關係密切,顯然不是因為沙特會把自己的政治體制改成美國體制。俄羅斯今天的政治體制顯然比蘇聯時代更接近美國體制,但美俄關係依舊冷淡甚至緊張。
資本不是傳教士,中國經濟起飛是中國勞動者用血汗換來的。1989年後,美國的“制裁”僅勉強支撐了兩年,1992年中國GDP增長率高達17%以上。資本不可能拒絕參與高速增長的經濟,不會拒絕中國人勒緊褲腰帶建起來的先進基礎設施,更不會拒絕非常廉價、勤勞、聰明的“民工”以及沒日沒夜的加班文化。資本偏好穩定的開放政策和安定的社會政治環境。2001年中國加入WTO不是美國的恩惠,不是因為美國要改變中國體制,而是中國做了大量讓步,給了國際資本發揮本性的巨大空間。
在美國花掉三、四萬億美元的“反恐戰爭”中,華爾街的資本熱烈歡呼中國變成了“世界工廠”,中國的“民工”還上了《時代》週刊的年度封面。美國金融海嘯把紐約股市的道瓊斯指數從1萬多點砸到了幾千點,然後又大翻轉,狂飆猛進,升到2萬多點,金融資本大賺特賺。人口眾多,地域遼闊平坦,有發明創造的沃土和極為充裕的廉價農產品,加上自產並操縱國際貨幣,美國人民過着優越生活,有足夠的資格讚美或譏諷中國的“血汗工廠”和“世界煙囱”。

2009年,《時代》週刊封面上的中國民工(圖片來自《時代》)
可就在最近十年裏,中國拋棄“世界工廠”和“世界煙囱”稱號的速度與獲得這稱號的速度幾乎一樣快。中國產業升級,開始進入高附加值和高科技領域,與發達國家開展競爭。華為公司擁有的5G技術專利讓人隱約看到美國高科技壟斷崩潰的前景。
早在奧巴馬時期,美國政府就呼籲製造業迴歸美國,至少是高科技製造業迴歸。但“工廠”已經遠離了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哪怕在微芯片領域,美國也長於設計,短於製造。靠發明創造,靠操控國際貨幣和國際金融,美國賺容易錢、賺大錢。擁有高達6萬美元以上的人均GDP,比西歐和日本高出2萬美元,美國真能復興製造業?
與中國在商品市場競爭中落敗的前景,特別是在美國賴以為生的高科技領域落敗的前景,使美國恐懼,促使美國發動了斷絕與中國經濟社會往來的絕交之戰。
美國稱中國為“修正主義國家”,指的是中國正在獲得“不服從領導的能力”,從而“修正”國際關係結構。至於現行的、促進經濟全球化的國際規則,中國要維護,美國要“修正”。
美國有些當權者希望,西方基督教世界團結起來,以“十字軍”的精神結成“神聖同盟”,削弱中國“修正”國際結構的能力,維護大航海以來持續了四百年的“西方”全球優勢。然而,這世界並沒有“西方”優勢,只有“國家”優勢。美國的優勢不等於英國的優勢,英國的優勢也並不等於西班牙、法國、德國的優勢。
中國的“復興夢”與美國“繼續偉大”的霸主夢不兼容。説中國快速崛起引發國際關係結構變化,引發美國恐懼,引發戰爭,不就是從修昔底德到沃爾茲的論斷?
五、理論翻新:重新理解中美對峙
舊理論需要翻新,有兩大原因。
第一,美中和平可以被冰凍,但同樣被冰凍的還有傳統意義上的戰爭。儘管美國軍工聯合體豢養的“旋轉門”官員需要以談論“戰爭”、談論“戰勝”來支撐國會的軍費撥款。但無論他們“談論”什麼,都無力發動傳統“熱戰”,至多能冰凍和平。
第二,中國並沒有稱霸世界的能力,當然也沒有意願。中國是個“貿易國家”,是經濟動物,不可能成為世界的政治和軍事領袖。直到19世紀初歐洲開始工業化,中國人口是世界的三分之一,經濟體量也佔世界三分之一,卻在政治和軍事上沒什麼影響力。而今,中國的出生率比日本還低,面臨每80年人口減半、一個半世紀後成為人口中等規模國家的窘境。
稱霸世界的必要能力包括以下三種:經、劍、文字。
不擅長創造“經”,就缺乏對其他國家人民的精神感召力。中國無力提供關於人類“未來後世”的精神支柱,比如“聖經”和“可蘭經”,比如“自由民主”和“共產黨宣言”。長期的小型自耕農曆史塑造了世俗的實用主義,中國的“精神生活”強調現世而非來世。
中國的經濟實力能支撐強大軍事力量,但中國擁有遠超其他國家軍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缺乏隨時隨地使用軍事力量的意志。持續兩千多年修築長城,進行昂貴的被動防禦,體現寧願花錢保平安不願出擊的悠久傳統,只有強敵入侵才能激發出中國的尚武精神。
簡化通約的字母文字是溝通全世界的基本渠道。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不使用字母文字的國家,與其他國家的人民極難溝通,所以有“華不治夷”的中國祖訓。象形文字在中國沒有衰落跡象,但也絕無成為世界語言的可能。中國的國際化非但沒能讓漢字普及,英文反而在中國舉辦的國際會議上成為工作語言。中國或能普及雙語,但那是遙遠的未來。
換言之,僅憑經濟實力,中國遠不足以當世界領袖。出於“誤判”,出於對“結構”的迷信,美國對中國發動了攻擊。
如同印度的復興,中國的復興不值得美國恐懼。那不意味着戰爭,不過是交易發達,多種文明交融,倡導不對彼此使用武力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位於歐亞大陸邊緣的中國崛起,是“世界文明”誕生的前奏。
中國有了“不服從領導”的能力,確實能削弱美國的世界霸權。但美國不需要、也不可能長久維持世界霸權。一旦和平被冰凍,美國和中國經濟,乃至整個世界經濟,都會在新型戰爭的寒風中衰退。而且,世界其他大國沒有維護美國霸權的重大利益。美國的脅迫可能一時奏效,但持續力非常可疑。美國缺乏必要的實力去給其他大國提供圍堵中國的利益。脅迫他國組成針對中國的“神聖同盟”,將讓美國難以進行“戰略收縮”,甚至可能再次“對外過度擴張”。換言之,向雙頭或多頭共治的世界和平轉移,明顯對美國更有利。
誤判是國際關係行為的常態,恆定需要花代價予以修正。
儘管復興之夢的“戰略機遇期”將繼續誘惑一切有夢之國,國際關係已經發生了兩大顯著的變化。
第一,冰凍和平之戰,要求修正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定義,也要求修正對世界經濟“相互依存”的認識。冰凍和平以摧毀對方經濟為目標,在供需全球化條件下用各種政治手段與對方全面脱鈎。但脱鈎及摧毀對方經濟難在短期內完成,所以冰凍和平對雙方而言都是持久戰。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是前車之鑑。
第二,因“誤判”發生美中對峙,要求修正對“結構”的認識。常規戰爭越來越困難,“不服從領導”的能力越來越普遍,絕非中國獨有。中國的脆弱性是顯而易見的,否則也不會招致美國主動發起猛烈進攻。那麼,是結構變遷導致“誤判”,還是“誤判”導致結構變遷?什麼終結了舊時代?第二次核打擊技術,蘇聯崩潰導致開放世界還是中國崛起?無論如何,關於實力分佈“結構”的認識已有粗糙之嫌了。
新的重大事件是知識進步的契機。沃爾茲的“結構”屬於20世紀及以前。儘管今天我們無法預料冰凍和平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