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錯過軍事革命,是因為仗打得太少嗎?_風聞
瘟疫公司搬砖部-最近在看《宋案重审》2019-08-10 13:54
文:維舟
中國是發明火藥和槍炮的國度,但在明清時代的數百年裏卻漸漸落後,到鴉片戰爭時面對西方的堅船利炮,清軍已不堪一擊。到19世紀末,列強無一不是工業化國家,世界軍事力量格局的不均衡性前所未有,直至1950年代初朝鮮戰爭和越南獨立戰爭,這一局面才宣告終結。回顧這段歷史時,一個很難迴避、也最讓人感興趣的大謎團是:中國是什麼時候開始落後的?更進一步説,中西方走上不同道路的“軍事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背後,其決定性因素是什麼?
軍事大分流
和經濟史上的“大分流”一樣,軍事史上這同樣是一個大問題,因為這實際上涉及到的是“中國為什麼沒能自發實現現代化”的問題,又或者説,“西方究竟做對了什麼”。
從一系列標誌看,中國原本在很長時間裏都領先於西方:不僅率先發明瞭火藥,而且也最先應用於軍事技術,學界公認槍炮是中國發明的;現存最早的金屬原型銃是西夏晚期(13世紀初)製造的,而西方使用槍炮的最早記載只能追溯到1320年代中期,晚了一百多年;1363年的鄱陽湖之戰,是歷史記載中第一次明確使用火器的水戰;1370年中國就出現了鐵製炮彈,而歐洲晚至15世紀末;明朝初年,中國軍隊已有10%的士兵裝備火銃,1466年更高達30%,這相當於歐洲16世紀中期的水平。不僅如此,中國的軍事思想也同樣領先:1550-1664年間中國出版了多達1127種軍事手冊,對練兵新技術的熱衷不亞於歐洲,戚繼光的明軍是當時除西歐之外唯一嚴格運用步兵操練的軍隊,且率先發明瞭火槍輪射技術。孫來臣等史學家甚至認為,近代軍事革命源於中國而非歐洲,明代中國是第一個“火藥帝國”。
既然這樣,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裏?以往的解釋大多傾向於從文化特徵、政治結構等深層次的因素入手,認為這是由於中國社會重文輕武,儒家不鼓勵軍事研究;長期的閉關自守阻礙了交流學習和技術發展,導致孤立與停滯;甚或是保守的文化“天生拒絕改變”。但研究軍事史的美國學者歐陽泰(Tonio Andrade)在《從丹藥到槍炮》一書中一一反駁了上述觀點,因為這很難解釋中國直至晚明所表現出來的技術創新與軍事表現。在他的前一本書《決戰熱蘭遮》中,他就已經提出了這樣的看法:1661年鄭成功率軍擊敗盤踞台灣的荷蘭殖民軍,證明西方當時在亞洲的強制性權力有限,歐洲人擴張依靠的優勢與其説是科技或經濟組織,不如説是政治意志;雖然他承認文藝復興堡壘與舷側炮戰艦是當時荷蘭人的兩大優勢,但鄭成功的獲勝表明東亞社會與歐洲一樣沿着類似的現代化道路進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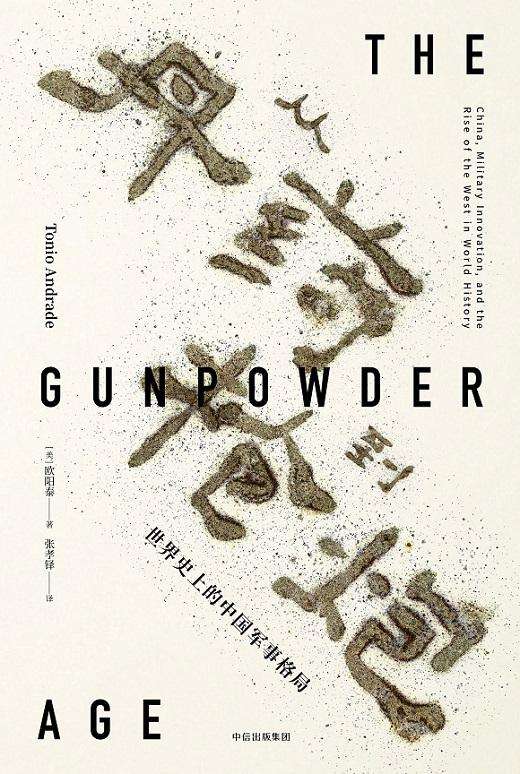
如果説東西方之間的差距在16-17世紀還難以察覺,那麼到1800年左右已經擴大成為鴻溝,這意味着,歐洲在此期間迅速拉大差距,是得益於其迥然不同於中國的內在動力,這種動力究竟是什麼?歐陽泰在分析歷史之後認為,原因之一是歐洲當時長期的分裂局面,導致各國都必須拼命革新軍事技術,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下來;這種“戰爭驅動的軍事革新”在中國歷史上並非沒有過,然而在1450年之後,中國的戰爭越來越少,烈度越來越低,到1693年清軍擊敗噶爾丹之後更迎來“康乾盛世”這一長期和平,戰事頻率、軍事革新都大幅減緩,僅有的盜匪叛亂與騷動,則無須作出重大改革便能輕鬆應對,而這段時間卻恰好是歐洲軍事革新大加速的時期。不僅如此,還有一些學者認為,明清時代的中國參加了太多“錯誤的戰爭”,諸如抵禦遊牧民族、鎮壓叛亂之類差不多隻是警察行動,不能像西歐列強的對外征服那樣可以獲得發展的動能。
但他並不僅僅滿足於用一些寬泛的理由去解釋這一現象,在比較中西戰爭形象、軍事思想和戰法細節之後,他發現一個值得注意的有趣現象:14世紀末期以後,當歐洲的火炮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頻繁地用於轟擊堡壘時,中國的火器卻仍然都是小型武器。這不僅是因為戰爭烈度的問題,還意味着中國火藥武器的發展受限於某些特定的原因:中國的城牆不像歐洲那樣是石砌的,而是黃土實心的高牆,比歐洲的堡壘厚十倍,牆體還是斜的,這三大特點(厚度、泥心、坡度)使得它特別抗炮擊。在這種狀況下,中國在軍事革新的方向不是費力研發出可以摧毀城牆的火炮,而是殺傷士兵。的確,這一點在中國軍事思想上也可以得到驗證,因為自《孫子兵法》起,中國的戰略思想一直強調“上兵伐謀”,直接攻城是下下策,即便要開戰,最要緊的也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不僅如此,中國最早的火藥武器,最重要的用途也不是轟炸城牆,而是為了破壞敵軍陣型。歐陽泰甚至質問道:“如果歐洲人遭遇的是中國那樣的城牆,他們還會想方設法研發出以擊碎城牆為目的的火炮嗎?”
這些解釋看起來的確能給人很多啓發,特別是他通過對鄭成功收復台灣的熱蘭遮之戰、清軍擊敗俄國殖民者的雅克薩之戰這兩場戰役的研究,證明那種“傳統儒家文化導致中國現代化失敗”的正統觀點並不可信。因為近代史已經表明,軍事技術是跨文化交流中傳播最為迅速的——無論是什麼樣的文化,沒有人希望自己在戰爭中失敗,因而只要衝突維持一定的頻率與烈度,這種地緣政治的不安全感遲早都會迫使人們響應挑戰,採納並革新軍事技術。就像晚清時在列強所施加的持續外部威脅之下,據説是“頑固牴觸變革”的中國人也很快醒悟過來,改革者才有機會獲得推動變革的持續動能。從17世紀與歐洲軍隊遭遇時的表現看,當時中國人的調適能力並不差。
變革的內驅力
照這麼説來,中國之所以沒能實現軍事現代化,只是因為打的仗太少了?曾率軍擊敗拿破崙的英國威靈頓公爵曾説:“勝利是僅次於失敗的最大悲劇。”其意無非是説,勝利常帶來驕傲輕敵和鬆懈的情緒,軍隊在和平時期疏於操練,很可能就為下一次失敗埋下了伏筆。在東西方的這一“軍事大分流”中,如果明清時的中國“天下大亂”,是否反而“形勢大好”?在我看來,問題恐怕並非如此。
乍一看,歐洲的軍事革新乃至現代化事業,的確在某種程度上得益於頻繁的戰爭催生的動能,但必須看到的一點是:在很多地方(以及歷史上的大多數時期),頻繁的戰爭帶來的不是技術變革,而是社會的徹底破壞。對中國這樣的農業文明來説,大量壯勞力脱離農業生產去打仗,本身就是對經濟繁榮的巨大破壞,更不必説戰爭帶來的殺戮、掠奪和干擾了,這並不必然催生軍事技術革新。因為相比起同時期歐洲那種“資本密集型”的戰爭,中國打的卻是“人力密集型”的戰爭——自先秦以來,中國戰場上打贏一場戰爭,靠的就往往不是更先進的軍事技術,而是組織更嚴密、紀律更嚴格、人力總動員化的軍隊,考古發現已經證明,最早統一天下的秦帝國軍隊,其實論武器還遠不如山東六國先進。

歐洲近代的軍事革新,有一個基本前提,即財政-軍事國家的興起,使得激烈競爭的國家不僅能充分利用境內的税收資源,而且槍炮的裝備運用確實能帶來好處,這樣才能激發各國不斷去優化它。與中國相比,同時期歐洲衝突雙方的軍隊規模大多較小,因而新式槍炮的威力更有可能帶來決定性影響。在1700年之前,除了法國之外,沒有一個歐洲國家的軍隊規模超過10萬人;直到拿破崙戰爭時期,歐洲一場戰爭中一支軍隊在交戰時的平均規模才超過5萬人。因此,歐洲的戰爭模式更多取決於專業化軍事人員、技術和資本的投入。須知,巨型炮的製造、運輸、開炮,都靡費巨大,16世紀的加農炮每射一發,相當於一個步兵一個月的軍餉——所謂“大炮一響,黃金萬兩”,決非無根之談。軍事革命所帶來的好處,起初並不明顯,卻需要投入大量資源,那説到底自然還是因為火炮能迫使敵軍投降,帶來巨大的“投資回報”。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1776年著成的《國富論》中也提到,火炮是昂貴的,防禦火炮的城堡也一樣花費巨大,所以戰爭藝術的革命傾向於在富國發生;照此推論,最終只有高效、中央集權的現代政體才能在高度競爭的戰爭環境下勝出。
然而,正如趙鼎新對東周儒法國家的競爭模型所證明的,中國走上的卻是另一條道路:依靠對人力的徹底組織和績效激勵。中國的戰略思維對“贏得戰爭”的界定、如何贏得戰爭,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路徑。歐洲的軍事革命模型,正如歐陽泰所概括的,是“修建城堡以及集結軍隊開銷巨大,所以政治領袖通過更加普遍的課税,以及財政、金融創新,創設了吸納税收的新辦法。不能完成這一任務的國家消失了,成功的國家留存下來”,但中國所投入的最主要資源卻不是資金,而是人力。
人類學者約瑟夫·泰恩特在《複雜社會的崩潰》一書中説:“技術革新,特別是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制度化的各類革新,是人類發展史上一個非同尋常的現象。它需要某種程度的研發投資。這種投資在人均生產幾乎沒有剩餘的農業社會是很難實現的。技術革新通常因勞力短缺而起,而古代社會幾乎不存在這種情況。”中國正是一個勞動力不僅沒有短缺、且常有剩餘的社會。半個世紀前,約翰·羅林森曾根據傳統觀點認為,“中國不是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持試驗開支,也不是缺少技術條件”,實現現代化的最大阻礙是儒家思維“對試驗的牴觸”;但實際上,中國傳統社會的剩餘資本是很少的,也缺乏像歐洲那樣活躍的競爭機制投入到軍事技術的研發上去。與同時期西歐、日本那種兵農分離的軍隊職業化方向不同的是,明清時期中國嚮往的是兵農合一的體制,其最大好處是低成本維護社會穩定,而非高投入研發軍事技術,鍛造專業軍隊。

歐陽泰的論述中一個潛藏的判斷是:只要面對激烈而頻繁的戰爭局面,不同社會遲早都會做出類似的反應。這或許可稱為“趨同進化”,就像鯨魚在海洋壞境中也會演化出流線型的身體,但即便如此,它的身體結構和魚畢竟還是有着本質的差異——面對軍事變革,不同社會恐怕也是如此,雖然它們會應變,但應變的結構性動力和方式還是不一樣的。如果説中國沒能自發催生軍事革命是因為戰爭不夠頻繁,那麼奧斯曼帝國可不缺,它也不缺資本和轟開歐洲式城牆的巨炮(事實上,1453年攻破君士坦丁堡城牆的巨炮,就是由匈牙利工匠烏爾班研發的,他是在基督教這一方找不到資助才投奔奧斯曼蘇丹的),在16世紀也與西方“以相同步調”在向火藥武器的支配性軍事角色發展(見哈濟生《伊斯蘭文明》),為什麼它這個火藥帝國(Gunpowder Empires)也沒能自發催生軍事革命?
軍事革命的發生是及其複雜的過程,需要有強大的內在驅動力才能產生變革所需要的臨界規模。槍炮的確在歐洲引發了軍備競賽,為戰爭的資本投入帶來重大變革,但到17世紀的三十年戰爭時,法軍指揮官也已發現,圍城戰吞噬大量物資,但奪取的城堡無論戰略價值還是經濟價值都可能是有限的。為了同時確保行動的有效性和財政上不至於崩潰,國家在軍事方面實行了轉包,允許企業與個人參與供給、維護軍隊所需要的物資與人力。在英國有“女王的海盜”,國家不出錢就得到了一支海軍;哈布斯堡王朝的地中海槳帆船隊是由私人承包商建造、投資的,他們可以從財團募資,自己從事私掠或把船租給國家;更普遍、也是利潤最豐厚的則是遍及西歐各國的軍械、彈藥補給,熱那亞、漢堡和阿姆斯特丹都是供應中心,外包到什麼程度則視情況而定。在這種情況下,軍用和商用沒有明確的界限,軍事領域的創新,立刻回饋給了社會,觸發了良性循環。《戰爭的果實:軍事衝突如何加速科技創新》一書曾指出:在那個年代,軍事需求對技術創新的影響“力量最強也最多樣化”,“產業先驅和金融先驅敢於冒險興建規模龐大的產業鏈,不過是因為他們拿到了政府的合同,向軍隊供給制造大炮的金屬”。
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戰爭的頻率才會催生軍事變革,因為這説到底有賴於激發社會主動創新的活力——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讓企業和個人切實感受到軍事技術方面的創新有可預期的回報。西歐各國在“軍事-財政”國家建立的近代化過程中,將國家本身變成了一個超級規模的企業,同時通過利潤的分享、外包,使參與其中的企業和個人從中獲益。由於社會資本並不像中國、奧斯曼帝國這樣僅僅集中在政府或少數人手中,這就帶動了社會整體的創造力,最終社會所有重要部分都必須專業化、制度化,並通過持續的技術創新和市場擴張模式,資本得以系統性地再投資與增值。到17世紀初,這些金融-軍事企業(financial-military enterprises)的人可以頂着國家的名號做生意,正是這樣的社會活力使西歐能有效地應對多元技術專門化的需要,因為後來的變化證明,步槍、手槍之類機動性更強的小型武器,比僅僅依賴巨炮的國家力量更有能力進行小規模的靈活行動。在1617-1850年間,英國專利局錄入的手槍技術專利不足300個,但在1850-1860年間的十年裏,槍械技術得到爆發式發展,超過600個相關專利得到批准。哪怕英國軍隊上層的多數指揮官們也像中國人一樣本能地牴觸變革,但這樣的社會活力卻不可遏制。
被歐陽泰忽視的另一點是:他太多聚焦於陸戰中的巨炮攻城,但事實上海戰中使用槍炮的價值更為明顯,因為不僅船隻本身就能給笨重的大炮賦予機動性,而且海外征服的獲益更為顯著。如果説陸軍還能依靠人力的密集投入獲勝,那麼海軍卻是一個相當耗錢的技術兵種。這方面歐洲遠遠走在中國前列,英國早在1340年的斯魯伊斯海戰中就已使用槍炮,葡萄牙人到1419年就已部署裝備槍炮的艦隊,最終發展出稱霸海洋的側舷炮。與陸戰相比,建造、維持一支艦隊更需要資金、技術的密集投入,卻要不了多少人力——1588年號稱規模空前的西班牙“無敵艦隊”,也不過3萬名士兵和水手。與此同時,一支海軍的存在,也以海外貿易和市場作為依託,否則它也只是無用的擺設。工業革命出現在依賴海外貿易、掌握海權的英國手裏,這並不是偶然的。

只有回顧這些歷史,我們才能充分理解,為何中國錯失了軍事大分流的機會——這遠遠不只是一個軍事層面的問題,而涉及到社會的整體變革。軍事技術的創新與變革,有賴於整個社會提供強大的內驅力,正如《企鵝歐洲史》第六卷所言,當時歐洲國家在軍事方面的轉包,作為軍事“放權”(devolution)和軍事“革命”(revolution)同等重要,因為正是這才激發了全社會的企業家精神。保羅·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國的興衰》中曾指出:“歐洲的船長、船員和探險家們最重要的不同在於,他們擁有可以實現其野心的船隻和槍炮,並且他們來自一個熱衷競爭、冒險和創業的政治環境。”恐怕正是這些差異,而非單純戰爭頻率與烈度的高低,才真正決定了中國與西方在近代的命運。
*已刊2019-06-14《第一財經日報》,標題改作《中國錯過武器革命,是因為仗打得太少嗎?》,現有改動
-----------------------------------------------------------------------------
勘誤:
p.19:人類學家查爾斯·洛林·佈雷斯(Charles Loring Brace):此處恐應指“佈雷斯四世”(1930-),他是人類學家,而Charles Loring Brace(1826-1890)是其曾祖父,慈善家
p.65:證據的缺乏絕不是缺乏火炮的證據:這句話很拗口,原意似指相關文獻記載的缺乏不是歐洲早期沒有火藥武器的證據
p.73:勃艮第的第一任大公是勇敢者腓力(Philip the Bold, 1363-1404):勃艮第公國在9世紀末就已建立,第一任大公是Richard the Justiciar(921年去世),但勃艮第確實是歐洲第一個公國,此處應有誤
p.80:學者伍子胥:伍子胥似很難被稱作“學者”,宜作“謀士”為好
p.81:商朝城市鄭州:商朝並沒有一個城市叫“鄭州”,這裏確切的稱呼應是“鄭州商城”,即在鄭州發現的商代城市遺址,有人認為這是隞邑
p.99:歷史學家還用這個理論去解釋歐洲以外的歷史:北非伊斯蘭國家、奧斯曼帝國、印度、日本、韓國。按,此處所指是15-17世紀的情形,朝鮮半島正處於李氏朝鮮王朝,Korea宜譯為“朝鮮”
p.120:歷史學家邁克·羅伯茨:前文p.99譯作“麥克”
p.138:世人多將(長筱之戰)勝利:同頁上文作“長篠”,是;p.141同改
p.139:一夥由許氏兄弟領頭的海盜……徐氏兄弟和其他海盜羣體均有往來:“徐氏”應為“許氏”,即當時的許棟四兄弟
p.209:江蘇、江西和安徽總督:這是英文直譯,但在中文應稱作“兩江總督”
p.217:[甲午戰爭中,中國]敗於面積僅為自己十分之一的亞洲鄰國:當時外蒙未獨立,日本的面積僅為中國的1/30
p.238:崇禎年間(1627-1644):崇禎帝於天啓七年(1627)年八月登基,但崇禎年號卻是從次年開始,因此這裏嚴格來説指的是崇禎帝執政期間,而非“崇禎年間”
p.256:約翰·海格(John Haeger)引用學者李馳的話,説在宋代,“和平的文化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這讓中國人的體質日益虛弱,直到他們再也無法對敵北方的騎兵弓馬”:按,這裏的“李馳”,恐應為李濟(Li Chi)
p.293:但不認為科學對大分流有特殊影響:應為“在大分流中”或“對大分流”
p.303:David Kang把中國在東亞的地位稱為“位尊者”(hegemony),而不是“霸權者”(hegemony),他指出東亞的地緣政治歷史提供了一種超級強權國的行為模式,區別於標準的新現實主義模式。按,這裏兩處英文完全一樣,疑有誤,第一處或是supreme?
p.304:Victoria Ter-bor Hui:這位學者是許田波,其所著《戰爭與國家形成》有中譯本,但她名字的第二字拼作Tin而非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