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霍爾、卒姆託必讀——Pallasmaa談“作為體驗的建築”_風聞
全球知识雷锋-以雷锋的名义,全世界无知者联合起来!2019-08-15 22:03
作者:俞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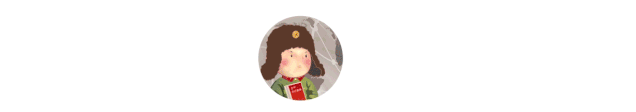
在建築設計中問題和解答是同時出現的,所有那些讓我們感動的建築都更接近於個人的告白,而非對一個問題的解答。
建築不僅將空間馴化,它同時還是抵抗時間流逝所帶來恐懼的堡壘。
我必須承認這些私人的、頗有坦白性的敍述,比起所謂滿足科學標準的理論和經驗主義的研究,更能將建築存在主義與詩意的本質穩固在我心中。
譯者寄語
剛從認識的人手上接到這篇講座時,我誤以為是一場類似於Herman Hertzberger(赫曼·赫茲伯格)的講座——討論“人”對建築的意義。當然,翻譯的時候我發現自己犯了個大錯誤:Juhani Pallasmaa討論的並非Hertzberger所探討的世俗的人,而是一個哲學的人。在講座中,Pallasmaa從現象學與哲學的觀點入手討論了建築作為一種高度複雜的藝術形式,是如何通過感知和身體成為我們心理世界的一部分、乃至最終具有在細胞和基因層面改變人類的能力的。
Pallasmaa的演講提供了一個看待建築未來道路的廣大視野,同時對想要理解斯蒂文·霍爾、卒姆託、斯卡帕等一系列建築師的人來説,Pallasmaa和他的“體驗”也是不可或缺的理論線索。雖然這確實令人振奮,但是我內心總泛着嘀咕:“好像有哪裏不對?”就在這時那個人又發來一張照片。
《DOMUS》雜誌2019年三月刊,掃描:孫志健
文中兩人對“斷頭台設計是否能產生美”產生了對話,最後兩人都無法否認它設計上的智慧,卻只能通過道德批判和用一句“唯一令人安慰的就是它已被塵封”曖昧不明地草草結束。其實歷史上斷頭台的發明原本是因為儈子手難以保證一刀斃命而常使得被處刑者在痛苦中死去,為了保證一擊必殺,讓人在沒有痛苦的情況下死去,斷頭台便應運而生了。在啓蒙主義和大革命的背景下,斷頭台可被視為尊重人道主義、非常進步的發明。從這裏可以看出,一旦結合歷史背景,我們便能輕易明白“美與進步的理想”是多麼容易被操控與濫用,遠沒有美與進步的追隨者所堅稱的那樣堅不可摧。
某種程度上講,這篇講座可以通過“斷頭台美學”的案例去理解,Pallasmaa的觀點極具啓發性,他將建築瞬間抬到了足以決定人類命運的關鍵地位,這個觀點宏大且充滿夢想,而與個人體驗的聯繫無疑為其渲染了浪漫主義色彩,但就如“斷頭台是否是美的”的討論一樣,這種討論是脱離歷史與社會語境的。
Pallasmaa認為無數要素互相連接影響的外部環境過於複雜,我們是無力應對的,唯一的辦法就是用模糊應對模糊、用情感應對複雜環境。在我看來,這種模糊對模糊,就如同《阿甘正傳》般的傻人有傻福,不僅拒絕了對外部環境的認真探索,還充滿了不確定性與風險。
Pallasmaa的觀點將建築拉上神壇,但同時建築之外的更多樣的大環境去哪兒了呢?正如那句“一切脱離劑量談毒性都是耍流氓”,Pallasmaa強調建築的影響的同時,並未討論這種影響有多具決定性以及它是如何影響的,所謂“決定地位”缺少細節。這裏的“人”迥異於Herztberger觀點裏世俗、熟悉的人,是一個抽象、沒有臉的人。
在Pallasmaa口中建築有着結構主義、環境決定論的意味。建築能夠改變人,而人的能動性卻只體現在他/她可以改變環境,除此之外,好像人絲毫沒有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社會不存在,我們以極度個人化的方式體驗環境,人與人之間沒有影響和聯繫。
同樣,談論願景而非細節會導致最終結果的無限個人化,在不同實踐者間產生極大差異。而更大的風險在於,強調一種純粹的美學,如同布爾迪厄所説,最終可能淪為上層階級鄙視下層的武器。
正如那兩位討論“斷頭台美學”的人,他們脱離了社會歷史,卻想為斷頭台作一個美學判斷,可又迷惑於為何美的東西卻造成如此血腥的結果,最後當然只能以道德批判和貌似深切的告誡草草收尾。
講座正文
通常每次講座我都會換標題,但這次我破天荒地直接挪用了筆記上的標題。建築理論的教育和實踐一貫將建築看作視覺上理想化和審美化的空間、材料、結構和形式,且不斷研究它在歷史、功能、工藝和形式方面的特性,這些分析主要還是集中在建築的物質(physical objects)與空間屬性上。
因為建築學自身沒有一致的理論體系,所以我們為了追逐利益或風潮,習以為常地從其它學科借鑑調研的觀點與方法。這樣借鑑常常導致水土不服,給最終實際的建成建築帶來巨大問題——例如語言學和解構主義理論便是這樣的例證。
建築與科學準則
儘管我常被稱作理論家,但我仍質疑為建築學找到一種綜合理論的可行性,因為這種現象固有的內在複雜性、矛盾性和無法相容的狀態使找到這樣的理論極為困難。但是對藝術來講,因為它們相對的藝術自主性,就本體的立場而言,它的複雜性和矛盾性是遠不如建築的。早在1955年,我的偉大同胞阿爾瓦·阿爾託就在芬蘭建築師學會的就職演説中明確指出了建築項目固有的內在矛盾性:“無論我們的任務是什麼,是大是小,在任何情形下……對立的事物都必須和解……幾乎任何正式的工作都牽涉數十上百乃至成千上萬個矛盾因素,這些因素只能通過意志的行動迫使其達成功能上的協調——這種和諧除了通過藝術沒有別的辦法可以達成。單個技術與機械要素的最終價值只能事後去衡量。一個和諧的結果是無法通過數學、統計學或概率演算來獲得的”。
考慮到一些芬蘭最權威的思想家和科學家就坐在台下,這段阿爾託60年前“藝術勝於科學”的宣言頗為大膽。阿爾託關於藝術具有的結合一切力量的觀點最近得到了維托里奧·加萊塞[1]的支持——他同時也是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的最初發現者之一。他説:“從某種角度看,藝術的力量比科學更強大,憑藉價格更低廉的工具和更強的結合能力,相較自然科學所用的客觀方法而言,藝術直覺以一種更加詳盡的方法,向我們揭示了我們是誰。作為人類意味着我們擁有追問我們自己‘我是誰’的能力。從人類誕生之初,藝術創造力就已經以最純粹和高級的形式展現了這種能力。”
注[1]:Vittorio Gallese,他主張人們能夠直接從經驗角度理解和把握他人思想的基本機制並不是概念性推理,而是通過鏡像機制對被觀察的事件的直接模擬。
建築學固有的非科學的屬性來自這樣一個現實:建築學的實踐同時採用事實與夢境、知識與信仰、推論與情感、技術與藝術、智識與直覺以及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維度。此外,它既是手段又是結果——是取得功利和實踐目標的手段,作為結果便是藝術表現(artistic manifestation),傳遞文化、心理、情感品質的價值。簡而言之,建築作為一種現象和人類的活動,從概念上就很“不純粹”和“混亂”了,以至無法在單個理論體系中被邏輯化地構建起來。
所以將建築囊括在一個理論中的行為在我看來——就如同想要為生命建立一個理論一樣——註定徒勞無功,由於它的複雜性,建築就註定不是從一個理論而是從反覆和具身的(embodied)行為中產生的:融合理性和情感、知識和直覺。
當然在設計的過程中大可有基於理論且完全理性的部分,但從整體上來講,這個過程是在不斷反覆中自成一體的。建築設計就像其它創造過程一樣,是由主觀的自我引領(self-piloting)行為引導的,配以紮實的實踐(task)的沉浸式的具身的辨認過程(immersive embodied identification)。建築設計融合了理性與情感、知識與直覺,而非執行一種基於理論的、理性和方法化的、可預期的步驟。
設計過程並非一條理性的道路,它包含數不盡的互相交疊的分支、死路、新起點、猶豫、暫時的確信……最終一個可以接受的結果才緩緩浮現——作為這個過程的終點。
因為建築本質上的內容是存在主義的,它的設計過程不可能像解決一個問題那般理性順暢。在建築設計中問題和解答是同時出現的,所有那些讓我們感動的建築都更接近於個人的告白,而非對一個問題的解答。
詩學和現象學的研究方式
從另一個方面看,也有人試圖以詩意格言(poetic aphoristic)或散文的方式,藉由主觀和個人的邂逅(encounter)來接近建築這個現象,就像許多前沿建築師的著作中所述——從賴特、柯布西耶到阿爾瓦·阿爾託、路易斯·康,甚至在斯蒂芬·霍爾和彼得·卒姆託身上都有體現。
在這些著作中,建築擺脱了一切科研的野心與論證,以一種充滿詩意和隱喻(metaphorical)的方式表達出來——這些論述往往取材於作者的個人經歷、觀察和生活的投影。我必須承認這些私人的、頗有坦白性的敍述,比起那些所謂滿足科學標準的理論和經驗主義的研究,更能將建築存在主義與詩意的本質穩固在我心中。
歷史上有三種尋求意義的方式:神話和宗教、藝術、科學,這三者間很少有互動,且每個領域中的努力都難以作用於別的領域。藝術和建築的詩意體驗與存在主義的內核必須被邂逅、感受和生活過才能被理解,理智的分析在這是根本行不通的。
誠然在結構表現、形式、尺度與心理學的影響上有無數領域可以甚至可能也該用科學方法去研究,但一個實體的體驗和心理上的意義只能通過存在主義的方式被邂逅和體驗。
過去幾十年間,一種將“與建築和環境現象學的邂逅”和“第一人稱的經歷”作為基礎的經驗主義的探索方法已逐漸獲得廣泛支持,這種方法根植於埃德蒙德·胡塞爾、馬丁·海德格爾、莫里斯·梅洛-龐蒂、加斯東·巴舍拉和不少當代哲學家的思想中。
這種承認具身體驗(embodiment)重要性的現象學探求方法被諸如施泰因·埃勒·拉斯姆森、克里斯蒂安·諾伯格-舒爾茨、查爾斯·摩爾、大衞· 西蒙、羅伯特·莫加洛爾、卡斯滕•哈里斯[2]等人的著作引入建築學中,我也相信1994年由斯蒂文·霍爾、佩雷茲·戈麥茲和我共同完成的《感知的問題》同樣幫助了這種思想在國際建築學界中傳播。
注[2]:Karsten Harries,耶魯大學哲學博士,現任耶魯大學哲學系教授,關注主導科學技術的客觀化理性的正當性和限度問題。
體驗的意義
建築所具有的詩意和存在主義的特點其實是一種心理的特質,這種建築的藝術與心理的本質來自個人對作品的體驗。在他創見性的《作為體驗的藝術》一書開頭,約翰·杜威[3]這位富有遠見的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這樣説道:“在普遍的理解中,藝術作品常常被等同於建築、書籍、繪畫或雕塑,被認為是與人類的感知所分離的。但因為實際的藝術作品其實是那件東西給予人的體驗與其在體驗中產生的影響,其結果就使得理解產生了障礙……當那件藝術品既脱離了它原始的狀態,又脱離了被體驗時的情形時,一堵牆出現了,幾乎使其偉大之處難以被人瞭解,但美學理論卻依然試圖(在脱離了情景的情況下)討論這種偉大之處。”
注[3]:John Dewey,美國哲學家和教育家,實用主義的集大成者,他使實用主義成為美國特有的文化現象。
在這裏,杜威將創作一幅藝術作品的情形和作品之後與觀眾相遇的情形聯繫起來,無論哪個情況下心理與感受的“真實”都佔據主導地位,使作品的存在徹底變成了人的體驗。杜威指出:理解藝術現象的困難正源於我們將藝術作品當作物件去學習的傳統,而將其置於人類經驗和意識之外。杜威還這樣寫道:“在一般看法中,帕提農神廟是偉大的藝術作品,然而只有當成為人的體驗時,它的美學價值才成立。藝術永遠是人類和他們的環境交互所帶來體驗的產物,建築正是這種交互所帶來互惠性的一個顯著例子……建築對於後續體驗的重塑比起其它藝術形式更直接普遍……建築不光能影響未來,它還記錄並傳遞着過去。”
在這個觀點中,杜威給予了建築一個“主動塑造者”的角色:不光與體驗的本質相關,還與我們對於時間的流逝與歷史的理解休慼相關。我認為建築創造了感知經驗與理解人所處具體情況的框架和基礎,而我的觀點正是圍繞這一認識展開的,正因如此,與其説建築是設計的最終產物,不如説建築本質上就有這種媒介角色。
建築體驗中的時間
時間維度和時間體驗的重要性往往沒有受到建築研究者的充分重視,卡斯滕·哈里斯對於建築中時間對人的心理意義有着重要論述:“建築不僅將空間馴化,它同時還是抵抗時間流逝所帶來恐懼的堡壘。”
因此美的語言本質上就是時間無法改變的真實的語言,“對於時間流逝的恐懼”成了我在建築實踐中一個無比重要的概念,建築是我們對抗這種恐懼的最強有力的武器之一。
自從希格弗萊德·吉迪恩的《空間,時間和建築》發表以來,建築的藝術已被理論化成了現代物理學意義上的時間——空間連續體,但在人類生活的“現實”中,這兩種維度有截然不同的本質,並且時間的維度在我們建築體驗中有着獨立的心理地位。我們有着深切的存在主義的需求去感受到我們與時間和空間的連結——我們同時居住於時間和空間之中,且為人類自身的目的,這兩個維度都被建築表達和馴化。
建築馴服了空間的廣闊無垠和時間的無窮無盡,使人類的心智能夠忍受它們。體驗的重要性已被其它藝術形式例如劇場電影和音樂所捕捉,但其與建築這樣的物質和實用性的物體乃至更大環境間的關係卻從未被很好地理解。
幾年前,羅伯特·麥克卡特和我選擇了前文提到的杜威的“帕提農聖廟是一件藝術品”的這句話作為我們的一本名為《作為體驗的建築》的書的主題語,以此紀念這位哲學家的著作。我們最後為這本書的標題與出版商爭吵了兩年之久,但他們最終還是動用自己在合同紙面上的權力將這本書命名為《理解建築》。這當然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主題,而且這個書名也過於虛張聲勢了——這就是典型的對“經驗的和心理的建築學”的冥頑不靈的抗拒,同時還持續強調建築中的理性與理智,認為“理解”就是勝於體驗的。
邂逅建築
體驗的研究方法着重於“真實的建築現實”與“感受的個人”之間的邂逅,正如杜威所説,這一點實現了建築這個維度。現象學方法試圖接近現象而不帶先入為主的觀念,試圖通過感性去辨認在個人化的邂逅中所產生的情緒和意義。在體驗中,建築超越了原本構架成為外在世界和內在自我之間的媒介,投射出感知與理解的獨特框架。
這種交流必然是一種交換:我進入了空間,而空間也進入了我、改變了我以及我的體驗,和我對於自我的理解。媒介對所有的藝術形式都是最關鍵的,龐蒂對此有非常堅定的認同:“我們並非來看藝術作品,而是要看這個作品所表達的世界”,這位哲學家起初就拒絕了大多數人對“藝術作品和建築僅是自我表達”的理解,這是極為關鍵的,建築和藝術的意義是在它們本體之外的,因為它們可以觸及比自身遠得多的地方。
經驗主義的研究方法中一個基本出發點便是超越物理與心理、內在和外在世界的邊界,達成融合或連續。Rainer Maria Rilke一直是我心裏排在第一位的詩人,他將他內在心理上感受到世界的空間轉化成一個優美的概念——Weltinnenraum,而藝術的體驗造就了內心世界。龐蒂啞謎般地暗示道:“這個世界是完全內在的,而我全然存在於我自己之外”,這似乎直指內在和外在時間相互交纏、密不可分的關係。
用直覺感知建築
資深建築師總能憑藉直覺理解建築塑造、改變和調整我們心理的“現實”,藝術家們通過直覺去感受心理和神經的現象,使他們比心理學家和神經學家辨認出它們要早了幾十年——這正是Jonah Lehrer那本發人深思的《普魯斯特是一位神經科學家》的主題。
在他六十年前的著作《通過設計生存》中,Richard Neutra早已發現生物學和神經科學的現實,並且提出讓那個時代大為震驚的建議:“我們的時代的特徵是生物科學的系統性興起,並逐漸遠離18和19世紀那種過度簡化的機械觀點——當然我們不否定那些觀點曾帶來一時的好處。現今這種全新看待生命和事物的方法可能藴藏並帶來設計中的新領域與標準”,其後他還説:“在今天,設計也許會深遠地改變人類的神經構成。”
Alvar Aalto同樣本能地意識到了生物學正是建築學的基礎,他説:“我願意講一下我個人情感的觀點,那就是建築和它的細節,某種程度上全都是生物學的一部分”,環境對人的神經系統和大腦的直接影響已被今天的腦神經科學證實了——當大腦控制我們行為,基因控制我們的大腦構造時,環境可以塑造基因的功效,並最終影響大腦。
“環境的改變會改變大腦,並因此改變我們的行為。通過設計我們所居住的環境,建築設計改變了我們的大腦與行為”,這個來自Fred Gage(神經科學家,ANFA神經科學建築學會的創始人之一)的觀點使我們能夠理解非常關鍵的一點:我們在設計物理世界的同時其實也在設計我們神經的、體驗和心理的狀態。這一理解強調了建築師工作中所藴含的人類責任[4]。我自己以前認為建築是關於美的,但幾十年後的今天,建築的圖像於我已成了心理的圖像、人類的狀態或心智的圖像。
注[4]:與人權(human rights)對應的人類責任(human responsibilities)
我同樣逐漸理解到了建築師擁有共情能力是多麼重要,能夠去想象並與“市井小民”共情——借用阿爾託的概念,阿爾託總説市井小民(little man)是他最終的業主——是非常珍貴的。這一個物質與心理世界之間的交界面事如此的重要,以至哲學家與神經科學家們例如Alva Noë日益關注這兩者間的連續性,並以此構建我們對於人類意識的認識。杜威認為“心智是一個動詞”,而我想説建築也是一個動詞,因為它真正的本質永遠是一種對於動作的邀請。正是這動詞般勾起人的主動探索和搜尋的傾向,使得建築和人類的心智被結為一體。建築永遠是一個保證,供應着人類的秩序、可預測性與安全感。
直到最近,建築都被認為是一種視覺藝術形式,被人們通過視覺感知和評判,關於這點,最出名的表達當然是柯布西耶的信條:“建築是精心挑選的體量在陽光下巧妙、正確、精彩的佈置”,過去幾十年中,許多當代思想家比如David Michael Levin和Martin Jay都已指出視覺的統治地位。
我也詳細分析過西方工業與消費主義文化下視覺的主導地位,並認為視覺具有的導向性讓我們僅僅成為局外人和旁觀者,而全方向接受型的知覺——聽覺、觸覺、嗅覺甚至味覺使我們成為局內的參與者。我們甚至可以懷疑:飄忽不定、淺嘗輒止的目光會不會比專心致志的目光對空間的體驗有更大的意義?
瓦爾特·本雅明早已指出建築如同電影一樣主要是一種觸覺的藝術形式,Merleau-Ponty最終將所有的知覺囊括入他對知覺感受的理解中:“我的感受(因此)不是一種視覺、觸覺和聽覺的總和,我以我的整個存在來感知,我抓住事物的獨特結構與獨特的方式,用我的全部感官。”
作為一個孜孜不倦探索了建築現象五十年的建築師、作家和教師,我毫不猶豫地相信如今對於建築體驗最重要的知覺絕非視覺,而是讓我們感受到“存在”的那些感官。建築是一種感官上對於存在和自我具身的體驗,對於存在在這個世界中的體驗,而不是僅僅視覺或別的亞里士多德所説的五感的體驗。在前面MP的觀點中,“我以我的整個存在來感知”也就是這樣具身的、存在主義的體驗。
幾年前我曾與一位在二十年前紐約的一場暴力襲擊中完全喪失視覺的法國藝術家有過交談,他雖然失明卻剛在華沙執導完一場芭蕾舞劇,並正孤身前往格陵蘭。我問他:“你怎麼能在看不見的情況下完成這些事?”他這樣回答:“我用我的整個身體去看”。所以當我們面對世界時,正是通過所有感官去看待環境的,這就是基於我們存在和自我的知覺。龐蒂“世界的肉體”的概念很好的解釋了這一點:“我們的身體在這個世界,如同心藏在生物中:它讓可見的景象始終活躍,它從內部維持生命的呼吸,有了它,系統才得以建立。”我們存在於世界的肉體中,並且憑藉成為這個肉體的一部分,我們獲得了我們的存在。龐蒂評論Paul Cézanne“讓我們感覺到了世界是如何撫摸我們的。”
我會認為建築甚至走得比那些畫作還要遠,因為它讓我們能夠棲居在世界的肉體的本身之中。建築為我們在這存在主義的肉體中提供了物理與心理的雙重居所。
建築還會激活和強化我們對自我的感知,因為我們對建築的感受總是個人且獨特的,建築能彰顯我們每個人的獨特之處,甚至如果我不能將意義投射到我對於一個地方、空間或房子的感受,那這根本就不算建築,只是物理結構而已。正如Jean-Paul Satre所説,當我閲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時,我也會將我自己的感覺投射在拉斯柯爾尼科夫上——能在閲讀時在想象中體驗空間和時間是人類最驚人的能力。
Elaine Scarry在最近就研究了文學這種能激發和傳遞空間、場所和情景的體驗的能力:“為了達到現實世界的豐富活力,口頭藝術某種程度上必須要模仿現實世界的持續性(persistence)與理所當然性(givenness)(這是最重要的)。明白無疑的是,口頭藝術那種教育的特性滿足了對於模仿理所當然性的要求”,當我在米開朗基羅的勞倫先圖書館(Laurentian Library)中感受那種深切的惆悵時,我所面對的正是自己心中惆悵的感覺,而這位偉大建築師具身的姿態性語言釋放和強化了我的這種感覺。甚至可以説我正是通過米開朗基羅的肌肉才感覺到這些的,因為他的建築、形狀與輪廓所秘密地作出姿態,就如同它們是人的身體、我自己的身體一般。藝術的偉大饋贈就是藉由一位偉大藝術家的感性表述,我們就可以短暫體驗這個世界和自己。
感知、體驗與想象
感知並不是體驗,它們只是由刺激所激發出的,缺少背景、判斷以及意義,感官的感知與記憶和想象互動才能產生完整的體驗。這樣的體驗有獨特的背景與價值,在建築設計中最重要和珍貴的技能就是能憑直覺或模擬出物理世界中不存在的實體所帶來的體驗。
憑藉直覺猜想單個形式或物體所帶來的體驗相對容易,但想象廣大和複雜的空間實體所帶來的氣氛或是感覺就需要非凡的想象技巧了。這樣的想象同樣需要有移情[5]的能力,移情的概念來自十九世紀晚期的美學理論,但是到了現代我們卻將它忽略了。
注[5]:Empathy,即前文的“共情”。
不過,隨着人們日益增長的對體驗的興趣,對移情的興趣也逐漸浮現,人們花了很長時間才理解我們到底是如何體驗世界的,而建築正是其中一部分,這是因為我們被我們互相分離的五感所帶來的感受迷惑了。
為這五個亞里士多德的、古典的知覺,我們可以一個個地找出它們對應的生理器官,但我們卻無法找出那存在知覺(existential sense),感受我們的存在的知覺,找到對應的器官,因為它是來源於我們對於存在於這個世界這個狀態的,綜合的理解。即使瞎子或者是聾子也能體驗到自身的存在。不過,斯坦納的哲學分出了十二種知覺,其中一種就是自我意識知覺,此外還有生命知覺,自我動作知覺。這三種非亞里士多德的知覺,我覺得,一起塑造了存在知覺。而我們正是主要通過這種知覺來感受建築。此外,我們所接受的對於知覺是如何工作的理解過於簡單了。從最近的新知識來看,這甚至可能是完全錯誤的。不過討論這個並不是今天的主題。這裏Alva Noë的一個問題就足夠了:“視覺世界是否就是一場極大的幻覺呢?”這個有些讓人啞口無言的問題正是我們建築師需要去思考的。
關係性的現象
我們對於知覺和他們的功能和交互越來越多的理解最終是我們改變了對於體驗的看法。但人類的意識有存在於何處呢?在Alva Noë的書《我們的頭腦之外:為什麼你不是你的大腦,和其他從意識生物學學到的事》中,他認為科學家尚未成功的找到意識到底是什麼,是因為他們在錯誤的地方——我們的大腦中——尋找答案。在他的看法中,當然我也非常認同這一點,意識是沒有辦法被找到的,因為意識不是一個東西,而是人的心靈與世界之間,產生的一種關係型的現象。
我認為藝術體驗也是這樣一種關係性的現象,發生在詩意的對象與感受的心理之間的。對於氣氛的感受同樣是一種難以捉摸的現象,也正是因為它是一種關係性的,而不是可以定義,可以命名,可以度量的對象,或者一個“東西”。借用一下Tonino Griffero的概念,他是一個“準物體”。它同樣誕生自無數的,相互對立的元素之間的關係與相互作用,這些元素或許是比例、物質性、觸感、亮度、温度、濕度、聲音、顏色……它們一起創造了“氣氛”,或者實際上就是我們的體驗。我們必須承認,所有的藝術和詩意的體驗都是相似的關係性體驗,而他們的本質,意義和情感特點出自無數元素和特性與人類的神經系統和意識之間的動態互動。這樣體驗才得以產生。藝術與詩意的體驗同時也激發了我們最深層的集體的,生物學的記憶。我們的體驗與我們的個人的過去和人類作為生物的歷史共鳴。
在我們周圍,一種對氣氛、氛圍、感覺、情緒和協調這些現象,還有對於真實多感官的和同時的感知的本質的瞭解的興趣已經興起。這種對於體驗的新興趣正在將研究的方向從形式和形式的結構移向情緒的和動態的體驗與心理的過程。非常明顯的是,當我們將注意力從物理現實移向心理和情感的現實的時候,研究的方法也會相應地改變。為了學習藝術與建築地體驗性的本質,我們需要相關的哲學視角,還有對於感知與心理的現象、記憶和想象的理解和直覺。
為了能理解人類的體驗,我們必須離開“準科學”的量化流程,去擁抱通過我們生活的行為直接去體驗建築與生活的勇氣與渴望。
講座原址:https://youtu.be/HyJbWdQ_hvA
推薦閲讀:雷鋒第74篇 雷暢譯 Pallasmaa講阿爾託《流水的網紅建築,鐵打的阿爾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