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豔 | 警惕文學對時代的“碰瓷”_風聞
保马-保马官方账号-2019-09-06 08:33
編者按
隨着科技的發展,新媒體傳播的日益壯大,文學似乎逐漸失去了時代話語的把控能力。在民眾期盼針砭時弊,敢於直指社會黑暗面的文學作品出現的同時,作家羣體卻由衷地感覺到話語權失落帶來的危機。他們希望通過關心現實、重述歷史來緩解與時代脱節的焦慮感,但更多的時候,這些作家既沒有對現實深刻的體驗,也缺乏對歷史同情的理解,卻藉着與現實“碰瓷”和歷史“勾搭”來收穫各種文化資本和藝術“美譽”。保馬今日推送的文章關注作家與時代的關係,意在為這個“浮躁的”“缺乏對文學的關注與容忍”的時代正名,批判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固守個人經驗,不尊重歷史與現實,使文學作品走向自我滿足、自我封閉的現象
本文原刊發於《光明日報》,後加以修訂,收錄於作者的首部文學評論集,入選“微光·青年批評家集叢” 第三輯, 2020年即將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感謝文章作者霍豔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警惕文學對時代的“碰瓷”
文| 霍豔
4月4日,婁燁的《風中有朵雨做的雲》“如期上映”。
在上映之前,照例是刪減、“不可抗因素”、撤檔風波——文藝片宣傳的“慣用”手段。婁燁2012年的一條微博被翻出來:“不要害怕電影!電影沒那麼可怕,也沒那麼重要。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政體因為電影而感到恐懼,那絕對不是因為電影太強,而是因為他們自己太脆弱了。”
這個引號顯得意味深長,你不知道他是引用了別人的話,還是自己的話,但總之,和撤檔風波一勾連,成為一條絕好的註釋。這種奇特的“一語成鑑”感,使觀眾們紛紛表示欠婁燁一張電影票。
導演婁燁
上映並未推遲,很快形成了兩極化的口碑。影片展現出一貫的婁燁風格,情慾流蕩。但不同的是,這次婁燁特地強調了和時代的關聯,在採訪中他表示一直想拍一個反映改革開放背景的電影。於是《風中有朵雨做的雲》成為一次揭開時代膿瘡,反映改革開放時期的另一面——地方腐敗、官商勾結、地產黑幕、權錢交易的嘗試。電影海報上也仿照報紙頭條的形式,寫着:“電影會幫我們記住我們和我們的時代”,來呼應他“拍吧,不然就忘了”的初衷。
但是,這種嘗試並不成功。除了開場用紀實手法拍攝廣州城中村拆遷的畫面外,影片只是靠不斷切換的年份、舊照片、舊服飾、偽新聞來凸顯時代印記,故作一種城市邊緣和權力中心的二元對立。我們什麼也沒被喚醒,什麼也沒記住。
影片就像是一場對“改革開放”的碰瓷。這樣的碰瓷,也出現在文學作品裏。
我們的作家開始變得對時代有強烈的訴説慾望。這折射出一種沒能參與到時代進程的焦慮。進入21世紀後,文學在時代觀的塑造中,發揮着越來越少的作用。我們日新月異的生活是被科技改變的,而不是文學。連對現實的呈現,靠的也是新媒體,有人把短視頻視作絕佳的人類學樣本,觸角覆蓋廣袤大地,在日復一日的生活裏,展示着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它們有着粗糙且堅硬的現實質感,把作家、小資青年用文字塗抹的粉飾,一層層擦掉。千萬種真實撲面而來,讓人恨不得長出複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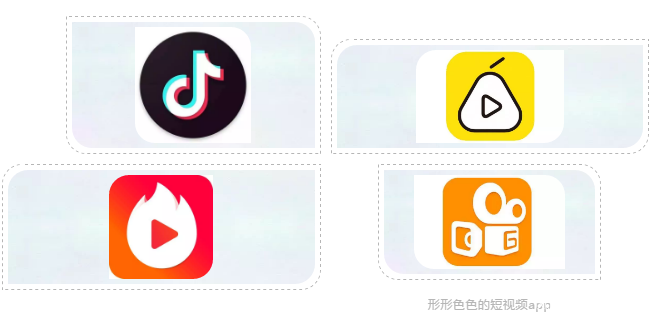
頑強的作家想通過文學介入時代,來證明自己對時代的表達依然有效,由此穩固住自己的存在感。作家總是認為自己對時代有絕對的闡釋權。所以會造成這種錯覺,是由於各種侷限和自大,使他們把自己關心的問題等同於世界的問題,把自己交往的人羣等同於“人民”,不知不覺遮蔽掉一些東西,建立了一種“文人史觀”,凸顯歷史書寫的“文學性”。但隨着科技的發展,文學的記錄效用被削弱。與此同時,文人地位也開始陷落。
我們想通過文學回顧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想從文學中瞭解中國發展如何一步步至此的希望也隨之落空。文學與時代分裂的危機從80年代文學最後的輝煌開始顯現。時代是由一個個真實的現實組成,80年代文學以“純”為標準,剝離絕對真實,製造不確定性,“將‘現實’視為偶然性、不確定和充滿變數的存在”。1 文學獲得了最後的榮光,也走向了封閉和自戀。
很快,文學的步伐跟不上90年代不斷變化的外部經驗。劉大先深刻闡釋了這種危機:“(小説)像一駕農業時代就開始挎着軛奔波在路上的馬車,被生活疾馳而過的高鐵列車拋在身後,為了保持尊嚴,開始自我安慰地吟唱着‘從前慢’。小説要同當下生活保持一定的審美距離,進而虛構要從雜亂的現象中轉入內心,這種辯護逐漸變得站不住腳,因為它讓內心承擔其難以承受之重,終至不可避免地崩潰”。2 “沿襲自八十年代中期以來形態探索與觀念更新所形成的範式日益窄化,把審美自足性生生縮減為文本內部體系的增生,這造成了創造性上的孤立和僵化,而使得文學與生活之間發生脱節,淪為一種自我循環而又自命不凡的嬉戲。”3
劉大先《文學的共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在這種自我陶醉中,在文學現代性對歷史現代性的反抗中,文學和時代漸漸脱節,時代的話語權被政治、經濟、科技所奪走。一些作家懷抱着的精英意識,實際上是為對時代的無所適從和對現實的遲鈍打掩護。所謂的文本實驗和突破,只是一枚枚精緻的碎片,割斷了文學與時代的關聯。或許,有些作家內心深處就不認可時代的變化,把失去話語權歸因於時代變化太快,人心浮躁。他們缺乏對時代真正的思考,時間都用來雕琢技藝,和加工奇異的經驗上。
文學逐漸失去關注,於是有些作家想通過進入歷史重新建立和時代的關係。中國人大多喜歡歷史,也喜歡在歷史問題上表達自己的見解,每個人都想知道自己從何處來,到何處去,想從前人的生命經驗中,尋找人生困惑的答案。但真正能潛心研究歷史的人並不多,歷史學越來越成為一個專門化的學問。當作家發現“文學化”表述歷史可以吸引回讀者,還沒形成完整且正確的歷史觀,就把歷史當作展現人的慾望、日常生活的瑣碎、特異經驗的背景,把對封閉內心的描摹重又挪移在歷史敍述中,使歷史也充滿了非理性和荒誕。
此時的歷史,已經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些作家並未想過正確表現歷史,而是塑造出一種觀念的歷史,越靠近當下,這種觀念性越強,尤其是對重要歷史節點符號化,把在歷史中沉浮的人物概念化,未曾認識到歷史事件發展邏輯的複雜性。他們缺乏處理重大歷史問題的能力,也缺乏抽絲剝繭的耐心。他們追求的只是歷史背景下的一種戲劇情境和參差對照,只有把歷史情境塑造得越極端,才越能掩飾他們筆下人物行為的諸多不合理和思想上的孱弱,歷史僅僅是人物幽深內心的外部裝飾。他們並非追隨歷史事件的發展邏輯,而是以某種價值立場預設邏輯,以一種直觀性、二元對立的歷史認知,形成流行的歷史論調。一些極端歷史書寫甚至變成“審醜”和釋放惡能。這樣的作品談不上歷史還原,更缺乏歷史反思。
學者賀照田曾説,直觀性的歷史認知方式其實是將歷史中的對象和事件作了簡化處理,卻沒有注意到任何一個歷史社會中的“我”都是被封閉在各種意識、認知方式之中的,要想突破或解放自己的眼光,有效達成自己對人世的關切,必須對自己的意識存在狀態非常警惕,才有可能與歷史、現實形成互動關聯。4 但一些作家過於相信自己的意識,把自我與歷史都封閉起來。歷史的魅力在於它是開闊的,有邏輯線索的,滿足我們從何處來,到何處去的好奇。可一些文學創作又把歷史置換成了封閉、虛無的“現實”,沒有來龍去脈,人物雖然充滿個性,卻在風雲變化中不曾獲得真正的成長,這樣的歷史主體難以代表時代的前進方向。
有人藉着歷史創作不斷彰顯自己的勇敢,尤其偏愛那些所謂“禁區”題材,“敢於觸碰歷史真相,揭露沉重現實”成為對這些作家最好的褒獎。成名作家大膽將歷史扭曲、變形,在海外戴上光環。年輕作家假意從沉迷內心的敍事掙脱出來,觸碰特定題材,收穫轉型成功的稱讚。但鮮有人去追究這份勇氣背後,所揭露、觸碰的真實與程度。一些作家曾經引以為豪地反叛了國家意識形態,又陷入了另一種意識形態的牢籠。他們的“文人史觀”缺乏對於歷史中人物和情境切身的體會,迅速把歷史的轉折歸結在某一兩個點上,誇大或刪減某些歷史情境,缺乏歷史遠見。他們的作品呈現了一種虛假的歷史感,並將這種虛假關聯起我們現實的處境,又將對現實的種種不滿,投射到歷史中,用當下的視角構建歷史,循環往復。如果説過去歷史寫作,是為了指明前進的方向,那現在的一些歷史寫作,並非有什麼獨特的見解或驚人的發現,而是想通過歷史為當下的混亂尋找誘因。
儘管小説是虛構,但史跟實之間微妙的關係,以及一些作家“勇敢”、“誠懇”的姿態,仍讓人信以為真,把文學中的歷史當作進入當下問題的路徑,造成了歷史、時代與現實、自我之間錯誤的聯繫。歷史感影響着現實感,現實感也作用於歷史感,錯誤的歷史書寫容易讓人形成扭曲的歷史認知。
有些作家以為僅憑着這份“勇氣”和激情,就可以在時代中重尋自己的位置。可遠遠不夠,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時代書寫者,需要投入時間,進行大量的調查工作,實地走訪和資料研讀。需要準確把握歷史-現實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一些作家往往是被網絡上某個社會新聞所吸引,以為這就是現實本身,然後進行藝術加工、素材堆砌。他們樂於撿拾一種現成的經驗,或迷信個人經驗,殊不知看似獨特的個人經驗也存在很多複雜社會、歷史面相。尤其是個人歷史經驗在當下的回溯中顯得不夠可靠,加入了後設的立場,抽離了當時的歷史情境,融入了當代的感覺和氛圍,不能被直接還原為事實本身。一些作家缺乏對時代敏鋭的感知,這種敏鋭不光需要天賦,也需要在大量準備工作基礎上磨練對細節的敏感。這樣才能真正進入創造性的歷史時刻,把被歷史記錄遮蔽掉的東西打撈起來,形成對世界與他人的切實理解。
新媒體的發展已經使生活實感壓迫了歷史記憶,缺乏歷史記憶就無法把握時代。但我們是否還能把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和把握,把對人民精神生活的全面呈現寄希望於文學?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實踐方式,如果依然以一種碰瓷的手段處理歷史,展現時代,必然會陷入虛無。
就好像《風中有朵雨做的雲》上映的過程中,有一篇微信公號文章,標題叫做“恕我直言,這個時代配不上婁燁”。這粗暴的碰瓷,讓人不免替時代感到可憐,它如提線木偶般被利用,被諷刺被塗抹,卻配不上任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