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中的政治:Alejandro Zaera Polo談《外殼的政治》_風聞
全球知识雷锋-以雷锋的名义,全世界无知者联合起来!2019-09-19 07:07
作者:俞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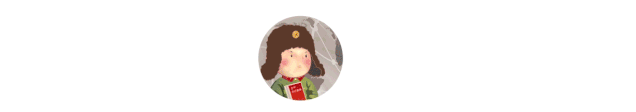
“我非常喜歡弗蘭普頓的這本書《建構文化研究》,我甚至去找他希望他來寫這本書的前言,但當我告訴他我這本書就是為了要殺死他所討論的“建構”而寫的之後,他拒絕了我。”
導語
講座由Randall Korman開篇介紹
Randall Korman,雪城大學建院前院長
非常榮幸地向大家介紹Alejandro Zaera Polo,雖然這是我們的第一次見面,但我早就知道他的作品了——橫濱國際客運碼頭,格羅寧根的藍月酒店,Carabanchel社會住房等等。這些項目最吸引我的就是它們每一個都以自己的方式挑戰了傳統的立面(facade)觀念,因此我總是在我關於立面的課中引用它們。
幾年前我讀到Alejandro出色的論文《外殼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Envelope)》的時候非常高興,因為我發現有一位當代的建築師/作者能如此頻繁地去討論關於立面的內容,這是很少見的。因此當我組織這次的系列講座時,我馬上想到的人就是Alejandro。我非常高興他接受了我們的邀請。
Alejandro出生於馬德里,以優異成績畢業於馬德里理工大學建築學院(Escuela Técnica Superior de Arquitectura de Madrid),後在哈佛大學同樣以優異成績獲得碩士學位。1991到1993年他在鹿特丹的OMA工作,後創立了自己的公司FOA(Foreign Office Architects),並在2011年組建了AZPML。他的作品長期以來融合了建築實踐與理論研究,並結合了建築,都市設計和景觀設計。他遍佈世界各地,橫跨公共和私人領域的設計作品享譽學界並屢屢獲獎。此外,自1993年來他還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地參與教育工作:93年到99年間執教了AA的學位課程,00年至05年他位居代爾夫特大學(TUD)的Berlage教席,10年到11年他還是耶魯大學諾曼·福斯特教席的首位獲得者。從12年到14年,他任職普林斯頓大學建築學院的院長,同時他還擔任哥倫比亞大學和UCLA的客座評委。如今,他已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終身教授。在建築師和教師之外,他還善於辨別社會和政治的動向,並將它們帶入到建築的討論中來。讓我們歡迎Alejandro Zaera Polo!
講座正文
Alejandro Zaera Polo,普林建院前院長
非常高興回到雪城大學來,我這次分享的內容與上次不同,主要是基於我早已完成的一本書的內容。
我為這本書工作十年了,它早應該出版了,但是因為各種原因一直被推遲。今天因為內容很多,所以我接下來會講得很快。不過能不能講完並不是那麼重要,我只是想將這個議題提出來以引發更多討論。作為一個理論家,我一直喜歡做的就是用辯論的方式去接近理論——我不喜作出單方面的評論或評價,我覺得讓我的提案去引發討論才是對理論真正的實踐。
我想先交代一下我個人對於外殼的興趣是怎麼來的。這張幻燈片是我二十五年前拿來做開場的,討論的是一個 “無邊界的世界”。那個時候,我對於時間和空間中的位置移動很感興趣,因為我覺得有了它們才會有世界,而我們正在走向一個越來越無邊界的世界。在這張幻燈片裏,交通、交流、科技的圖像在一邊,代表了我們為了移動我們自己和物品,為了交流而不斷增長的“空間移動”能力。另一邊是信用的機制;這些機制讓我們能夠獲得時間上的自由,在時間中置換轉移,這是“時間移動”的能力。將無邊界和移動作為背景,那時的我非常痴迷以這兩者為基礎來產生一種全新的建築形式。
可是隨着時間飛逝,實際上我們看到的卻是這種機制如何成為了摧毀城市的元兇,我們看到了在911事件之後,信用系統的崩塌。我之前所相信的那些機制不僅沒有實現我們讓邊界消失、讓物品可以自由的移動的願景,邊界反而變得比任何時候都更惡劣和強大了。
從這時候我就開始想也許我們不應該再玩“消解,融化,沒有邊界”這種概念了。思考侷限,思考邊界,而不是忽視邊界去構想一個沒有邊界的世界,也許是一個更加要緊的事情。
很多事情的發生讓我們突然開始注意到我們在走向災難,比如氣候變化。這更讓我堅信我們應該要去思考邊界——比如那些分割環境的邊界,阻隔熱量和氣流的邊界。
1
A MATERIAL HISTORY AND THEORY OF ARCHITECTURAL SURFACES
材料的歷史與建築外殼的理論
我的理論就由此開始:平面和截面圖一直都是建築師用來創造空間的主要機制,但它們在面對建築外殼的設計時就沒有那麼重要了。由此我有了“外殼的政治”這個概念,利用它我試圖用建築的形狀和比例去進行建築分類。由此我們就有了一種新的與城市產生關係的形式。這時是2007年。
時間繼續往前到了2014年,因為一直在做立面相關的東西,我受邀去參加fundamentals建築雙年展去做一個立面,也就是在這期間我完成了我的這個計劃的主體部分。庫哈斯想讓這個雙年展有市集的感覺,讓人能夠透過建築的部件去觀察一棟建築。根據這個概念,我從審視材料開始我的工作。
我拿到了這些資料,這裏左邊是一個立面的原樣大小的實物樣品,右邊是那棟樓的照片。讓我震驚的是當你看到它們時候你會覺得那個立面的實物模型比那棟樓要精密得多。那棟樓看上去可能就是普普通通的,但當你走近了看那個實物模型又會覺得很有意思。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可以成為雙年展中一個有趣的提案,來引起“微觀視角下的建築”的討論。
我們關於建築的思維被訓練的如此抽象的。 西格拉姆大廈的立面繪成立面圖其實就是一堆線,但是裏面的每一條線其實都充滿了細節,是自己的一個小世界,當你靠近細看的時候,會有種想搞懂的慾望。大家自己設計和討論的時候都看過這些節點圖吧?但我還是沒法完全搞懂它們。我們用這些非常細緻,複雜的東西去構建我們的立面,卻對它們的工作方式不甚瞭解。但這些微小的結構正是我們處理空氣、能量、水這類要素的場所,而這些要素正是我們在關於所謂的“人類世”的政治討論中成天討論的東西。所以最終我的研究從一個大的尺度,從思考外殼比例、幾何關係的方式中進化出來,變成了去試圖找到一種能將我們建築學和那些浮現的政治議題相連接的思想方式;而不是像我們這個學科一直以來所做的那樣,將這些微結構視作互相獨立的物件。
我們就好像是在做古生物研究一樣,研究這些立面,外殼中的微結構、微截面。它們的地位日漸重要,但卻是在建築學當中長期缺乏理論。為了去研究分類它們的方法,去理解它們,我想到了生態學,把它們看作是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的過程中不斷成長的物種。就像居維葉、聖伊萊爾和達爾文那樣地去觀察它們。我發現了丹尼爾・丹奈特(Daniel Dennett)説過這樣的話:“宣稱‘真相不存在,有的只是解釋’的後現代主義思想學派雖然已經在荒謬中窮途末路了,但它卻在身後留下了整整一代的被不相信真相、不尊重證據給剝奪了能力的人文學者。在他們所進行的對話中,沒有人是錯的,也沒有什麼是能被確認的,所有的事情都只是被他們斷言着,以一種他們所拼湊出的風格。”
所以從一開始,甚至是該用何種方法都還不明確的時候,我就想將建築外殼研究和“表現(representation)”——這個着實膚淺的領域——分開,轉用我剛剛所説的那種技術去研究。我們用以揭示這個真相的主要工具之一就是歷史,去看這些“物種”是如何形成的。
這是我們為雙年展所做的一張圖表,在裏面我們找了12個“物種”——這段歷史其實不是很長,因為外殼的問題到了十九世紀才變得重要起來——在這張圖裏我們標註出了它們的發展,衰落和滅亡。有些時候它們會“滅絕“,但是有些又會復興。其中你可以看到它們遭遇各種事件,比如1973年的石油危機和二戰的結束,這些事件又會改變它們。我們特別展現的是這些”物種“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是如何進化的。我們把這些“物種”稱為立面組合(façade assemblage)來描述這些材料,比如磚、鋼、玻璃,經過結構的設計和組裝之後已經超出了原本屬性的材料。我們將這種組合作為單位集合來看它們是如何在20世紀的時間中進化的。不過這是張老圖,現在已經不是12種組合了。
所以整本書就是去嘗試分析外殼的“物種”和“生態”,試圖通過四個基本的視角去描述它們。
第一個是功能(Functional: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s),“這些外殼有什麼用”,比如控制透明度,控制人的進出、防水、採光、通風,最終還有經濟性。
第二個視角是看它們的組成元素(Elemental: Components)。就像聖伊萊爾和居維葉通過觀察鳥的腳給鳥分門別類,我們提取出了外殼的三個基本的組成元素:幕牆框架*,接縫和膜(mullions,joints,membranes ),然後試圖去追溯這些元素,或者説是説法(narratives)的歷史——這個研究計劃從某個角度來説其實是很文字性的,而且我也並不是想把它做成一個非常嚴謹的歷史研究,我只是在拋出議題。與其説去發掘事情的本質,我想做的只是為這三個元素分別提出一些説法,或者是微説法而已(micronarratives),我想去講述這些元素的進化故事。
* Mullion的意思是窗户的豎框,在幕牆中則指的是玻璃幕牆中支撐玻璃的豎向構件。這裏Alejandro泛指幕牆中包括豎向橫向的所有框架,所以翻譯成“幕牆框架”。
第三個視角是組織(Organizational: Assembly Types):外殼是如何被組織起來的。關於現代的外殼我們總結出兩點:分板和分層(Panelization and layering)。這兩種組織的方式給予這些外殼“生物”我們能看到的一致性。最後一種視角——其實我們最初是從最後的這種視角出發的——是類型學(Typological: Assemblages)的視角。這與前面三種視角都不一樣,它們都是橫向跨越所有“物種”的,而在最後的一個視角中,我們基於前面的特性將物種分為九個門類。
所以為了向你們介紹我們所做的工作——又因為這本書裏的圖像佔了很重要的位置——我會挑一些過一下,我希望你們能看到我們是怎樣嘗試着去將這些“物種”、元素、系統、或者是性能納入一個生態系統中並找到它們相對應的位置。最終,這個生態系統將它們和建築領域之外的東西聯繫起來:將他們與政治現實,政治事件,技術發現等等——在其中還能看到來自其他領域的技術轉化——聯繫起來。 把其中一種立面的做法單獨拎出來是沒有意義的,只有把它們放入這個生態圈中我們才能去解釋,去概念化它們。你無法説出哪種“物種”在生態圈裏占主導地位,因為每一個被我們放在書裏的例子所代表的都只是一種暫時的平衡狀態,而這種狀態往往意味着巨大的博弈與實驗。但這種博弈與實踐放在今天都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現在的文化越來越強調在設計中減小風險。
2
FUNCTIONAL:THE TELEOLOGY OF THE ENVELOPE
功能:外殼的目的論
Transparency:The Material Tempering of a Modern Ideology
所以就讓我從功能分析開始。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樣,我們會在這裏考察透明性,保温性,氣密性,防水性和經濟性;這是功能的五要素。就像動物的物種一樣,這些外殼的“物種”也是與它們的環境和生態圈緊密相關的。所以引入自然光的需求才會最先出現在北歐,比如荷蘭,的大城市裏,因為那裏的人們想要儘可能多地引入自然光。在英格蘭,人們對於技術的興趣集中在了玻璃製造業上。
玻璃作為一種材料明顯與建築的透明性相關:瞭解生產大塊的平直玻璃的技術不斷進化的過程,對於瞭解建築外殼的透明性的進化是非常重要的。這張圖試圖説明你在什麼時期可以得到多大尺寸的玻璃。你可以從這裏看到,我們現在可以製造十八米長三米寬的玻璃了。這在我剛剛幻燈片裏展示的那些建築的時期可是不可能的。
雖然無法得到那麼大的玻璃,但是那時候的人們還是渴望透明性,比如你可以看到城市中的商業建築追求更透明的立面來展示更多的商品。還有非常密集的工業建築,第二張圖是聖路易斯的工廠,它們代表了在十九世紀末期出現並且在往後世紀中持續進化的建築技術。
上:十九世紀末的芝加哥建築,下:二十世紀初的芝加哥建築
這些立面其實都在講故事。從十九世紀末期開始,芝加哥城市中出現了立面上有着大量玻璃的建築。但是這股潮流卻在20世紀初突然被反轉了。這是為什麼呢?
吉迪恩*會説這是因為1893年芝加哥舉辦的哥倫比亞博覽會上提出了迴歸古典主義風格的倡議,所以新建築會有這種新古典的、更加封閉的造型。
*希格弗萊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二十世紀著名建築理論家,著有名作《空間•時間•建築(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但如果你看霍拉伯德*——也就是芝加哥這些建築物的設計師——的説法,會看到完全不同的看法:變化的發生是由於電力價格的下降和玻璃價格的上升;而芝加哥哥倫比亞博覽會作為第一個完全由電力照明的世界博覽會,正好是這一變化的體現。這是因為之前所有的玻璃製造商都集中在匹茲堡的產油區,便捷的資源給了玻璃低廉的價格。但之後油田逐漸枯竭導致玻璃價格上漲,而且低廉的電力價格使得日光照明不再重要。正因如此,信託大樓(Reliance Building)*之後,建築就變得越來越不透明瞭。
*威廉姆斯・霍拉伯德(William Holabird)1854-1923,芝加哥學派重要的建築師,早期摩天大樓的重要設計者
*前圖,上排中間。第一棟大面積採用玻璃的高層建築。
所以對我來説,這種對於建築的“生態”的解讀遠比吉迪恩做的那些傳統的歷史分析有意思。吉迪恩的分析侷限在建築學內部,他將建築當作一個在內部自我循環的系統,繼而排除了所有外部的那些“生態”。有了這個視角之後你就能察覺這些不斷髮生的事件。
這是20世紀能源價格的曲線,曲線上的每一個峯值或者低谷都會立刻對建築的設計,和建築師探索的方向產生可見的影響。這種視角才是我們所感興趣的。
60年代浮法玻璃*生產工藝的發明對於我們能夠達到的透明性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這張幻燈片中,不同的玻璃技術造就了建築不同的設計和建造的方式。從左邊,利華大廈(Lever House)使用的是單層平板玻璃;可口可樂大廈的出現緊接着浮法玻璃的發明,更加的透明,但是它沒法染色;在接下來鏡面玻璃出現了,因為石油危機導致能源價格大漲,空調變得昂貴,我們必須要隔絕日光暴曬帶來的熱度,所以出現了鏡面玻璃,給了建築這種反射表面;然後到了現在,菲利普・約翰遜的PPG廣場使用了濺射鍍膜玻璃(sputter coating),這種新技術能讓玻璃能像鏡面玻璃一樣過濾光線,又能更透明。因為有了這個技術我們才能看到現在的很多嘗試。
*浮法玻璃的方法是將玻璃熔液倒進一缸熔解的錫內,玻璃浮上錫面後自然形成兩邊平滑的表面,慢慢冷卻及成長帶狀離開錫缸。之後經過火打磨便成為接近完全平的玻璃。
Watertightness:From the Roof to the Wall
防水性是另外一種性能,不過我這裏就快速的過一下:防水性是建築首要面對的問題。在這一章所講的故事裏,在傳統的建築裏,所有的那些防水的技術都是用在屋頂上的,而立面則是從來都不是那麼防水的,它們是會“呼吸”的。但是在20世紀裏,所有的這些技術都從屋頂往下走了,將我們的立面牆壁也裹得嚴嚴實實的——這一章主要就是在講這個。
氣密性是另一個很有趣的性能,同樣出現於19世紀的末期。它的出現來源於工業化和城市增長所帶來的一系列環境問題。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疫情爆發代表着由人口聚集帶來的傳染病也成為了一個問題。還有,20世紀初誕生了化學武器成為了人們心頭憂患,並且將在此後的整個世紀當中都將持續地影響建築設計。當然,同一時間,空調誕生了。這一切的結果就是你不再想要呼吸外面的空氣了,你想要處理過的空氣。而為了處理空氣,你就必須把自己嚴嚴實實的密封起來,關進一個密閉的泡泡裏。對於氣密性的追求也成為了20世紀初期外殼進化過程中的一個特點。
一個例子就是拉金大樓*(Larkin Building),在這裏建築突然就變得完全不能呼吸了,它有了這一整套的人工通風系統來幫助它呼吸。通風系統甚至還被塗上了特別的塗料以保證完全密封,所有的窗户也都被鎖上了。
*拉金肥皂公司管理大樓,弗蘭克•勞埃德•萊特設計,位於紐約州布法羅。1906年建成,1950年拆除
太空競賽同時也通過一系列圖像,將這種“泡泡生活”渲染得很吸引人。(70年代很具有代表性的泡泡孩子)同時霧霾不斷的出現,催生了人們不惜一切代價通過各種技術——比如硅——來達到氣密性的嘗試。還有HomeWrap(房屋隔離材料的一個品牌),最終成為了我們現在解決氣密性的方法。
於是建築物變得非常的密閉,導致在70年代能源危機來臨的時候,人們不得不關閉原先的空調系統,結果裏面的人都得病了。這就是著名的“病態建築綜合症”。從某些角度,這已經是把建築變成一個封閉泡泡的這種建築科技的徹底失敗,但與空氣相關的問題在接下來的時間中還是層出不窮:沙林毒氣事件、傳染病、還有空氣污染。
這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狀況,而這可能又會催生新的外殼。一個例子就是我們現在的被動式節能屋技術(passive house):將整個建築密封起來,在牆壁裏填上保温材料,然後把整個換氣的過程都交給機械來節約資源。這可以看作這整個世紀基於氣密性發展的技術路線的最新體現。
Insulation:The Rise of the Cellular
接下來的一個性能就是保温性。有趣的一點是在十九世紀,很少的房子是添加了保温材料的。它們的“空調”就是在室內支一個壁爐生火。直到十九世紀末礦物棉的偶然發現才讓人們發現還有這樣能夠阻擋熱量穿牆且能持久的材料。
這之後保温材料的生意才逐漸出現,特別是29年大蕭條的時候,能源變得異常昂貴。岩棉行業乘勢大為發展,根本供不應求。此後保温材料順勢發展,甚至產生了主要圍繞着保温材料的外殼和建築。
這張幻燈片來自1950年的《建築論壇(Architecture Forum)》雜誌,這一期主要講的是幕牆結構——其實也就是波浪鋼板包裹保温材料。在這裏立面的主要作用就變成了將內與外隔離開來,阻隔內外間能量的流動。對更多的保温材料的需求催生了合成保温材料的誕生,大大降低了保温材料的價格。而很多材料我們持續使用至今——我們現在房屋保温材料的一大部分甚至是50年代發明的。
石棉值得單獨一説。在5、60年代石棉可是一種魔法材料,因為它能夠保温、適應性強、持久還便宜。但突然地,人們發現它其實是很危險的一種材料。作為一個外殼“物種” 它必須要能與人類共生,如果它不能做到,那這個“物種”就只能滅亡了。
所以你看到73年的石油危機和29年的大蕭條一樣都是推力,有些“物種”就因為它們的保温能力突然一躍到了生態圈的上層。這種變化往往能產生非常戲劇性和獨特的故事。比如幻燈片裏的這個外牆一體保温系統(EIFS, exterior insulation finishing system)是用特殊的砂漿將泡沫固定在那裏的做法。這種材料50年代就在德國被髮明出來了,但是一直沒獲得成功。
直到出口到美國,並在這裏申請了專利,突然有一天它能在美國的所有商業建築市場中佔到15%。真是很有意思一點,因為這些用了這種EIFS技術的建築看上去就像是彩色卡紙做的。這種材料非常還非常適合塑性來製造這種東西——這是在拉斯維加斯。
也有建築將這種便宜、商業化的材料用出高級感。波特蘭大廈*(Portland Building)就是一個例子。
*波特蘭大廈,邁克.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設計,1982年建成,後現代主義的代表作品之一。
我們在做這個研究的過程中逐漸發現了一系列的人物,從而發現了我們不曾注意的英雄和惡人們。雖然在建築領域裏默默無聞,我卻認為他/她們比密斯・凡・德羅還要重要;比如對於邁克爾·格雷夫斯*那覆蓋着EIFS的波特蘭大廈嗤之以鼻的彼得羅.貝魯奇*(幻燈片中右側的那位),他是第一個設計了幕牆的人。
*邁克.格雷夫斯,1934-2015,美國建築師,紐約五人組之一。
*彼得羅.貝魯奇(Pietro Belluschi),1899-1994,意大利建築師,長期工作和生活在美國,國際主義風格的重要設計師。
不過無論如何,EIFS還是使得這種建築成為了可能,而這些建築也最終在建築史中得到一席之地。是的,也許這些建築師的理論和著作才造就了後現代主義,但是沒有這些廉價的外形保温一體化的材料他們也無法以合適的成本造出這樣的建築。
這是個材料失敗了的例子,在這裏彼得·埃森曼在他辛辛那提的建築上用了EIFS材料。但是這不能怪埃森曼,這是EIFS固有的問題:只要你把保温層放在外面,你就沒辦法避免內部結露的問題*,而水會從內部腐蝕材料。對於使用EIFS的建築有大量的法律訴訟,而且立面很多的立面都必須被重建。
*因為温差會導致冷凝水,夏天時因為保温層在牆體外側,保温層兩側會有温差,冷凝水會出現温度較低的牆內側,原理和汽車玻璃起霧相同。
説到這個,現在如何去重新更新保温材料也成為了一個我們要面對的問題。我很有信心對這個問題的探索會成為誕生一種新風格的契機。打個比方,傳統的結構會有這種非常厚重的保温層和大量的塑料型材。這種因為保温要求所造成的“肥胖”是我們必須深思熟慮的。我不相信建築師只應該就學學歷史,然後就去做後現代的設計了,我們應該反思我們審美超向了儘可能薄的立面和構件。我們的教育來自於那羣50年代的、不用考慮能源和環境問題的老人們,但現在這些問題明顯是不可能忽略的,所以我們也需要修改我們對於這些外殼 “肥胖”的評價了。
還有一個性能表現是經濟性,我在這裏就不多説了:比如建築物的進深,重量,材料的運輸等等。我們就直接進入下一個部分。
3
ELEMENTAL:MICROEVOLUTIONS OF THE ENVOLOPE
要素:外殼的微進化
Mullions:The Rarefaction of the Envelope
幕牆框架(mullions)是個很有意思的東西。我們今天對於幕牆框架已經很瞭解了,但是它完全可能走上另外一條發展道路。
這張圖來自於我們的研究。我們標註出幕牆框架中各部分的功用和位置,並像生物學家通過鳥腳的特徵給鳥分類一樣,我們通過這些功用和位置——比如玻璃是在幕牆框架的內側還是外側——給不同的幕牆框架分類。這樣我們獲得了很多有趣的信息,比如以前幕牆框架常常是在玻璃的外側的,比如像密斯設計的房子,但現在這卻很少見了。這是為什麼呢?這不是因為建築師突然覺得突出在外的幕牆框架醜了,而是和環境與能源狀況與建築建造中的觀念的變化導致的。幕牆框架作為一種建築的部分是反構造的。
如果説高端的建築學(Architecture with the capital A; 開頭大寫的建築學)是關於砌築的、非常清晰理性,那麼幕牆框架的存在使得牆面彷彿變成了一種帶圖案的織物——不過是一系列隨意交織的元素,其中一些元素提供支撐,另一些填補牆面上的空洞。所以框架結構的使用開始就並非正道,而是從那些用以娛樂的、展示殖民地搜刮來的奇珍異植的温室開始的。
這種結構利用擠壓成型的鐵構件通過摩擦力來固定玻璃,雖然其中現代幕牆框架中的各種部件都已經誕生,但它們的形態都還是非常粗糙。這一時期的許多新生事物——車站,市場,工廠——對於大空間的需求推動了這一技術的發展。因為並非傳統建築類型,所以很多這一技術背後的人物,比如設計了水晶宮的帕克斯頓*並不是傳統的建築師,而是園藝師。而當時都市中心的商店的發展也使得幕牆框架的形態越來越精緻和漂亮。
*約瑟夫•帕克斯頓(Joseph Paxton),1803-1865,英國園藝師。
幕牆技術發源於建築之外的領域,並且逐漸進入到建築的實踐當中,而在此之後,建築師才姍姍來遲並想要試圖將幕牆理論化——格羅皮烏斯和吉迪恩湊到一起並告訴每個人他們是幕牆的發明者,他們才是帶有大玻璃的房子的創始人。直到此時建築師才意識到有這麼一系列的技術,然後才有了包豪斯。
但是此時的幕牆框架還是一種比較粗糙的工業產品,直到二戰結束下一次的幕牆框架革新才會發生。在二戰結束的時候,大量原本生產鋁製飛機座艙的軍工廠產能過剩了,大量的鋁沒有地方去。最終他們把注意力從武器的生產轉到了建築上。因為這些鋁原本是生產飛機的,技術的精度非常高,這次轉向也使得建築物的精度急速上升,誤差的範圍縮小了十倍。
比如這張照片裏的公正大廈(Equitable Building)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彼得羅.貝魯奇設計的。它是第一棟真正的現代玻璃幕牆大樓,第一次採用了鋁作為幕牆材料。它非常超前,你可以看到它有雙層玻璃,它還有地熱和熱泵,是那個時代的工程奇蹟。我認為貝魯奇比密斯更重要就是因為正是他,看到了鋁廠低價拋售高精度的鋁材料,想到了可以把鋁用在玻璃幕牆上。
不過有趣的是貝魯奇去當了MIT的院長,就把自己的公司賣給了SOM。SOM拿到玻璃幕牆這個點子之後做了利華大廈,但利華大廈卻是一個倒退,放棄了鋁而用了鋼,而且用回了單層玻璃。
這一系列的建築——公正大廈、利華大廈還有聯合國大廈為建築打開了一個新的範式,卻也帶來了新的問題。這些玻璃幕牆的玻璃都是用油灰固定的,但油灰會隨着時間脆化需要被替換,不然就會漏水。事實上建成不久之後利華大廈和聯合國大廈的立面都需要被完全的更換,因為他們到處都在漏水——高層建築和温室不一樣,高處的風壓會把水壓進任何小的縫隙裏。所以人們不得不借用別的領域裏已經出現的橡膠墊圈技術——直到這個時候,幕牆中才出現了密封墊圈。
但馬上下一個問題出現了:鋁是一種導熱性非常好的材料,比鋼還容易導熱。如果你看公平大廈的節點你就會發現,即使貝魯奇試圖用雙層玻璃保温,但是內外聯通的鋁構件很快就讓熱量從這裏逃出去了,造成了一個冷橋。
所以如何將這冷橋斷開成為了下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如果你在去看我們剛剛看過的幕牆框架節點,你會發現所有的這些非金屬的構件都是在為了不讓熱量通過金屬構件直接傳到到另外一邊,而這些構件無疑又增加了幕牆框架的複雜程度。
而最後一個為幕牆框架增添複雜程度的部件可能就是那些用以平衡壓力的部件了,也就是雨幕(rain screen)。這些部件內部設計有空腔來平衡壓力,防止高空的風壓將水滴擠壓進裂縫從而保護建築立面。
因為充滿了這樣空腔,所以現代立面的截面才會如此複雜和怪異。
Joints:Subject to Movement
幕牆框架之後是接縫(joints),接縫是為了讓建築的各個部分能夠移動,在變形、沉降等情況下不至於損壞。
Membrances:Performance without Form
然後還有膜,比如Tyvek*——Tyvek 70年代還不存在,但現在每一個住宅建築都會使用這種能透氣的外牆保護膜,所以這後面一定有一段特別的發展史,但我在這裏就不贅述了。
*Tyvek,中譯名為“特衞強”,是美國杜邦公司於1955年開始研發的一種烯烴材料,質輕、強韌,常作為防水透汽材料用於建築外牆。
4
ORGANIZATIONAL:THE ENVOLOPE’S COMPOSITION PLANS
組織:外殼的成分
Panelized:Embodied Labor
我在這裏進入“組織”的部分。之前説過的,從組織去看外殼的構造模式有兩條線索,其中第一條就是將立面分塊使之適應預製裝配的趨勢。一個例子就是當時最輕薄的幕牆結構,沙裏寧設計的IBM研究中心。
Layered:A Vertical Geology of Hidden Tectonics
另一條線索就是現代建築立面有了越來越多的層次:有保温層、防水層、防水汽層,這個層那個層的來保護內部的結構不受腐蝕,此外還有雨幕來平衡氣壓防止雨水滲透。所以傳統建築的砌築的系統到了今天已經被隱藏在表面下的一層又一層疊加的帶有不同功能的材料取代了。
幻燈片裏是模弗西斯*事務所的作品。它與弗蘭克·蓋裏設計的畢爾巴鄂古根海姆美術館不一樣。在畢爾巴鄂那裏,蓋裏的想法還是把雨幕假裝成一個整體,隱藏那些用來讓空氣流過從而平衡氣壓的孔隙。但是這裏模弗西斯所做的是利用雨幕的洞隙,把建築立面這種一層一層的結構表現出來,去發掘其中視覺和美學的可能性。
*Morphosis建築事務所,由建築師湯姆·梅恩主持。
5
TYPOLOGICAL:THE SPECIATION OF THE ENVOLOPE
類型學:外殼的物種進化
The Modern Facade Currency. Curtain Walls
到了四個視角中的最後一個:將前面所有的要素囊括進來對外殼做類型學的分類。我這裏不打算展開了,就簡單地過一遍。第一個類型是玻璃幕牆。玻璃幕牆不單是讓一座建築透明那麼簡單,作為工業化的產品讓整個城市都能輕易變得透明,這與工業化一道賦予了玻璃幕牆某種“民主”的含義。所以玻璃幕牆不光是一個建築的功能部件,在某種程度上還成為了現代民主和工業、政治透明的的象徵。
很有意思的是查爾斯·拉克曼(Charles Luckman)——造就了利華大廈的這位利華公司CEO他自己就是一名建築師。他抱着對於未來的願景,決定在戰後一片頹勢的紐約建一棟現代化的公司總部。抱着這種樂觀願景,在利華大廈之後出現了一批之後不斷被重複的現代主義玻璃幕牆建築的原型,例如百事可樂總部,西格拉姆大廈。
不過在這裏你可以看見西格拉姆大廈的薄薄的保温措施,還有直接連接的金屬件造成的冷橋。這對於那個時代的人們不是問題,比如拉克曼就信誓旦旦地向所有人保證,隨着核能的發展,未來會有無限量的能源,能源幾乎會是免費的——所以密斯才會在西格拉姆的立面豎框上設計突出來的鋼結構,且花盡心思去表現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考慮如何為立面做保温。
但能源危機來了,這種類型的建築出現了。幕牆框架從玻璃的外側撤退到了內側;這一種工業技術、標準精確和透明性的象徵最終在七十年代從建築的立面上消失了,在反光玻璃的後面默默承擔着儘可能隔熱的職責。
貝聿銘的漢考克大廈是這一時期的標誌,但它也是幕牆進化史中重要的一個節點。出於節能需求,漢考克大廈引入了雙層玻璃,但出乎意料的是它卻帶來了大問題。
整片的玻璃碎落,整個外立面全部需要替換,以至它獲得了一個外號——膠合板大廈(Plywood Palace)。如此嚴重的失誤讓人們有足足十年都不敢使用雙層玻璃,幕牆又倒退到了單層玻璃的時代。
Precast Concrete. Sin and Redemption
接下來是預製混凝土。如果説預製混凝土要有個標題的話,我一定會選擇《罪與救贖》,因為在它的歷史中,預製混凝土就是不斷在兩個極端之間來回移動:一端是藝術的表現力,比如艾莉諾·寇迪*(Eleanor Coade)的作品——她是第一個有目的地利用預製混凝土的人;而另一端則是大規模的工業生產。
*艾莉諾·寇迪,1733-1821,英國女企業家,發明了名為寇迪石的人造石,並經營使用寇迪石生產新古典主義雕像和裝飾的生產廠。
Screens. The Making of the Mask
接下來的一個分類是圍屏(screens),之前提過的雨幕就是這類,用於平衡立面上的壓力。從挪威的農場小屋上的一種技術逐漸進化成了我們如今看到幕牆豎框中的雨幕結構,建築師也開始將其作為一種當代建築立面分層化的表現給強調出來——有時候甚至不只是強調。蓋裏的這個建築就是,雨幕就好像突然得了失心風開始羣魔亂舞,演變出了整個建築。
The All-glass Envelope. Total Vision
第四個全玻璃外殼——如何儘可能減少玻璃的框甚至讓它完全消失。這一開始可能是為了更大的商店櫥窗,但逐漸這個潮流被浮法玻璃和工業硅膠技術的發展越推越大。
Double Glazing. Climate Incorporated
下一個是雙層玻璃立面。雙層立面能將氣候有效的利用起來——這並不是一個很新的技術,譜系上可以追溯到kastenfenster(箱式窗)。比如第二張圖裏是17世紀西班牙北部的建築,那個時候人們就已經理解了温室效應,並利用兩層立面之間的空間接受和儲存太陽能了。
玻璃在蘇聯被當作一種革命的象徵,但是俄羅斯的冬天非常冷,所以他們也都採用了雙層玻璃。
柯布西耶對於雙層玻璃也很感興趣,他甚至設計了一種雙層的牆體,將熱空氣泵進立面的空隙建築就不需要額外的供暖了。當然他失敗的非常徹底——他在蘇聯的嘗試失敗了,他又試圖在巴黎救世軍大樓安裝這種系統,卻因為工程縮水只建設了一層,導致整個建築熱得就像一個大火爐。諷刺的是,好在幾年後建築物因為轟炸受到了損傷,他得以有機會重新設計立面——當然這個時候他就徹底的放棄了他雙層幕牆的想法了。
到了60年代,嬉皮士運動又興起了利用陽光的潮流。
這裏我就不展開講了,但8、90年代雙層幕牆這種技術在歐洲的興盛與當時的政治情況是分不開的:當時的進步政府關注環境問題,同時又希望人們能夠有機會去推開窗户,但單層玻璃幕牆要通過內外隔絕保温節能的,所以它是封死的。因此想要同時滿足兩者的想法就帶火了雙層幕牆技術。比如在德國就有一段時期,因為出台了公司的僱員對於所在的建築也有決定權的法律,一夜之間所有的公司都開始建造這種非常昂貴的,帶可調節百葉的雙層幕牆系統。
Tensile Envelopes. From Precarious to Spectacular
Media Facades. From Message to Atmosphere
彈性外殼,這個我只能先跳過了。媒體外殼,在這一節中你可以看到它是怎麼從傳達一種信息的工具,隨着LED技術的發展變成一種氛圍的——比如《銀翼殺手》裏面的那些建築的立面。有趣的是第一部《銀翼殺手》和最初的LED產品正好是同一年誕生的,所以你看到那裏面的那些立面都還不是用LED,而是用電視顯示屏拼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