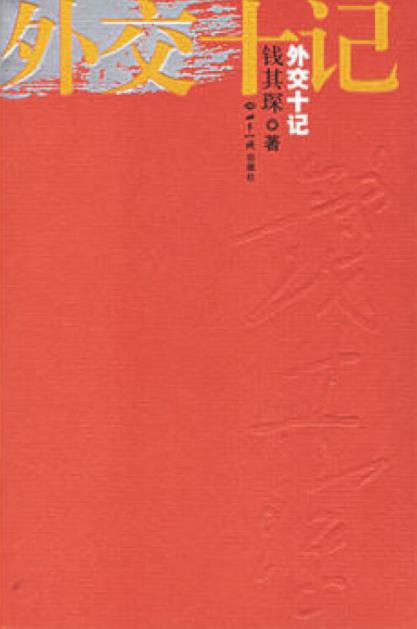一個資深外交家的蘇聯生活片段_風聞
瘟疫公司搬砖部-最近在看《宋案重审》2019-10-14 21:36
文:錢其琛
我第一次出國就是到蘇聯。那幾乎是50年前的事情了。1954年8月,我被派到蘇聯團校學習。那年我26歲,初為人父,女兒出生只有20多天。
從1951年起,共青團中央每年選派一些團幹部到蘇共中央團校學習,為期一年。我參加的是第四期,領隊是當時在東北做青年工作的徐淨武同志,副隊長是北京大學的張學書。
我們19名學員,加上兩名翻譯,共21個人,於1954年8月底離京飛往莫斯科。記得我們乘坐的是一架小型的蘇聯飛機,從北京起飛,途中降落兩次,並在伊爾庫茨克過夜,第二天換乘大型飛機,中間又停了好幾站,最終才到達目的地。到莫斯科的那天,印象中,那裏好像剛剛下過雨,走出機場時,腳下還不時踩到雨後一片片的積水。
蘇聯中央團校坐落在莫斯科郊外的小鎮威什尼亞基,離莫斯科市區有市郊列車6站地的路程。學校周圍有一片白樺林和一個不小的湖泊,附近還有一座彼得大帝時期一位大臣的莊園,那時已改做博物館。
團校的課程有聯共(布)黨史、哲學、政治經濟學3門主課,還有俄語、青年團工作等幾門副課,另外就是體育課了,冬季還要學習滑雪。團校授課採取課堂宣講和課下自學相結合的方式,每天,教授在課堂上先講授3到4個小時。那些蘇聯教授的理論功底都很深,講起課來真是引經據典,照本宣科,馬列主義的某個觀點、某句話,在哪一本著作中的第幾頁上,都能一一説出,分毫不差。課下,我們則要用大量時間來閲讀指定的理論書籍,也就是馬列主義經典原著。此外,就是由教師圍繞教學內容組織的課堂討論,俄語叫“席明納爾”。在這種討論中,教師和學生是一種互動的關係,可以互相提問,內容當然只是從書本到書本,從理論到理論,很少有與實際相結合的討論。
赴蘇之前,所有學員只受過為時半個月的俄語訓練。開始時,老師授課和師生之間交流都要通過翻譯,從俄語翻譯成中文,再將中文翻譯成俄語。學習俄語,成了首要任務。
根據學員的水平,俄文課分成了4個小班開設,每個班約有四五個人。分班前有個水平測試,讓從地圖上指出某個城市,還問一些諸如“你是怎樣到這裏來的?”之類的問題。我和幾位曾在國內自學過俄語的同學分在一個班,被其他同學戲稱為“高級班”。
開學後,大家每天清早一起牀,就都忙着背俄語單詞或朗誦課文。到了學習結束時,我和有的學員已經可以用俄語回答問題了。
除了課堂學習外,蘇聯團校還組織我們參觀革命遺址、紀念館、工廠、集體農莊,以及參加一些文化娛樂活動。我們參觀過托爾斯泰故居、高爾基紀念館,觀賞過特列季亞科夫畫廊,還在莫斯科大劇院觀看過經典的芭蕾舞《天鵝湖》,以及聽一些著名的歌劇。
1955年寒假,我們去列寧格勒旅行。時值隆冬,天寒地凍。在一片皚皚白雪中,我們參觀了冬宮、斯莫爾尼宮和因 “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而聞名的“阿芙樂爾”號軍艦。全班同學還在蘇聯和芬蘭邊界附近的拉茲裏夫湖畔的一個小茅屋前合了影。當年,列寧就是住在那間小茅屋裏,寫下了著名的《國家與革命》。暑假期間,我們又被安排去烏克蘭旅行,並乘船遊覽了黑海和克里米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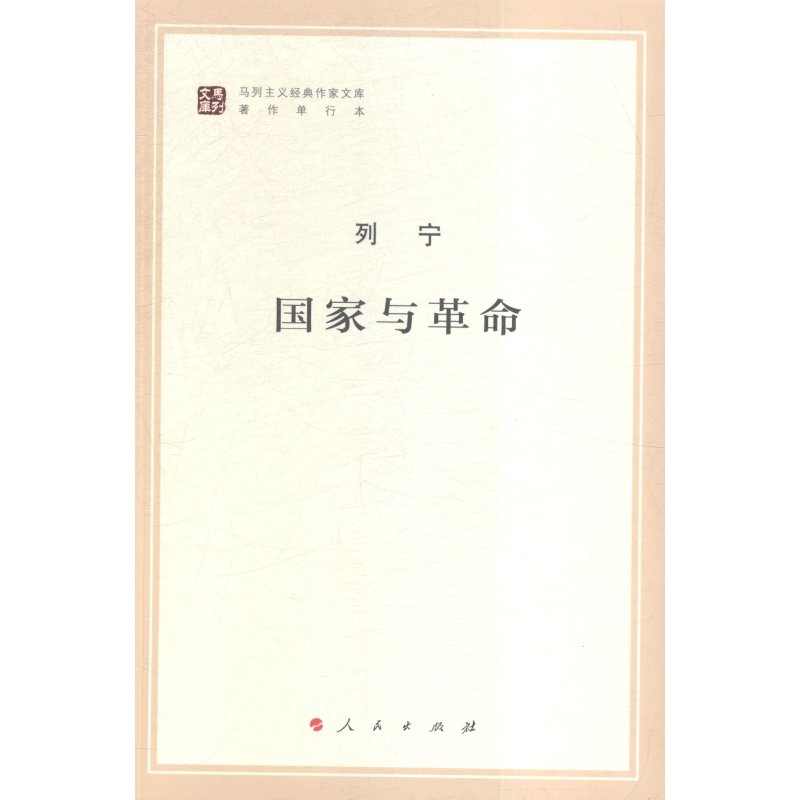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蘇關係正處於最好的時期。蘇聯團校的教員、同學、翻譯,乃至後勤工作人員,對中國學員都非常熱情,在學習和生活等方面,也照顧得很周到。我們的俄語老師聽説中國人喜歡吃花生米,就在課堂上説,她一定會給大家找一些來。過了很久,大家差不多把這件事忘記了,那位老師卻真的為大家帶來了許多花生米。那是她從莫斯科市裏千方百計找到的。當她把花生米一一分給她的中國學員時,臉上帶着滿足的笑容。班上的翻譯瓦里婭,還受校方委託,負責安排學員的各種活動,假期帶領大家到外地參觀訪問。她不辭辛苦地幫助中國學員解決校園生活中遇到的種種問題,那份耐心、熱情和周到,給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時,在我們中國學員的心目中,蘇聯是革命聖地、列寧的故鄉,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樣板。蘇聯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又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而社會發展的光明前景,更是令人嚮往。新中國剛成立不久,百廢待興,在經濟建設等很多方面,都在學習蘇聯的經驗。我們到了蘇聯,都很興奮,生活又很愉快,一心要以蘇聯為榜樣,好好學習。
但是,在蘇聯學習的時間長了,和老師、同學的交往多了,慢慢發現蘇聯也存在着一些難以理解、不如人意的社會現象。不少蘇聯人在談吐中,不時會流露一些不滿情緒。大家最初深感詫異,想不明白,為什麼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幾十年的蘇聯,會有這麼多的問題呢?社會主義社會難道也會不完美嗎?
10年後,也就是1972年初,我正在安徽幹校勞動之時,又一次奉命赴蘇,到駐蘇使館擔任政務參贊。
當時,中國仍在經受十年“文革”的磨難,人們的思想在經歷了社會動亂之後,正孕育着對社會主義的新認識。在赴莫斯科的火車上,我也在想,不知10年後的蘇聯會是什麼樣子,社會有什麼變化。
從北京到莫斯科,火車要行駛整整一個星期,一路上,倒是可以好好觀察一下。從車窗望出去,仍是一望無際的森林和原野,挺拔的白樺樹,廣袤的草原……風光依舊。只是沿途看不到什麼大的建築、新的工廠或新的城市。列車一站站停靠時,從行色匆匆的旅客們的衣着和行李上,以及車站小賣部搶購食品、到處有人拎着麪包的情況來看,蘇聯沒有什麼變化,發展好像停滯了。當年赫魯曉夫吹噓的“20年內建成共產主義”的“宏偉規劃”顯然已成泡影。
要説有什麼變化的話,那就是北京至莫斯科的國際列車上乘客已經寥寥無幾了,和10年前的境況真有天壤之別。我們幾乎可以獨享整節車廂,旅途煩悶時,只能和乘務員聊聊天。當時,中蘇之間的交往已經很少,但兩國間的國際列車仍照舊運行。
中國駐蘇使館在列寧山上,佔地12公頃,主樓是一座宏偉建築。這時,使館的工作人員已大大縮減。由於雙方關係緊張,蘇聯方面設了好幾個警察崗哨,對中國使館進行嚴密“保護”,也就是嚴格監控。
從使館的樓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莫斯科大學建築的尖頂上閃亮着碩大的紅星。1957年11月,毛主席正是在這所大學的大禮堂裏向留蘇的中國學生説,你們青年人好像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當時,留學生們高喊着“為祖國建設奮鬥50年”的口號來回應,場面激動人心。
時過境遷,當年熱情澎湃的場景已經不再。駐蘇使館裏相當冷清,與對方已經沒有多少外交業務了,只能在使團中開展工作。對蘇方,除了一些禮節性拜會外,就是我方提出抗議或是駁回對方的“抗議”。
20世紀70年代初期,駐蘇大使是劉新權同志。使館有3位政務參贊,除了我,還有馬列和王藎卿同志。
由於莫斯科地處交通要道,過往的中國代表團仍然不少。使館的一項工作就是向他們介紹蘇聯的情況,以及逗留期間應注意的事項。
我們也利用一切機會到蘇聯各地旅行,去了解情況。我先後訪問了外高加索地區和波羅的海沿岸。蘇聯方面對我們的出行格外注意,採取嚴密的監控措施。被“盯梢”真是家常便飯。只是這種“盯梢”太容易被發現了,有時把他們甩掉,有時也開開他們的玩笑。有一次,在旅途中,我乾脆就直接跟“盯梢”的人説,你跟在後面太辛苦了,我們正好不認識路,還是請你到前面來,給我們帶路吧。“盯梢”的人被弄得哭笑不得。
1974年夏,我調離蘇聯,去非洲的幾內亞當大使。
從1954年算起,斷斷續續,我在蘇聯度過了整整10年,經歷了中蘇關係最好的時期,也見證了兩國關係的逐漸惡化,而最後這兩年,則是中蘇關係最為緊張和困難的時期。
蘇聯的解體,可以説是20世紀最令人驚歎、也最令人深思的事件之一。
蘇聯的解體,幾乎像是一朝一夕發生的事情,但導致其瓦解的許多因素,卻是長期積累下來的。在這裏,不能不提到在上個世紀初,兩個著名的法國作家當年對蘇聯的觀察。
在20世紀30年代,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和安德烈·紀德都曾懷着對這個當時蒸蒸日上的國家的極大興趣,來到莫斯科旅行。他們都將自己在蘇聯的所見所聞、所疑所思,以日記的形式記載了下來。
紀德把自己的日記命名為《從蘇聯歸來》,並在1937年公開發表,坦率地把他對蘇聯的現實考察和長遠思考説了出來。而以小説《約翰·克利斯朵夫》聞名於世的羅曼·羅蘭卻宣佈:“未經我特別允許,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滿期之前,不能發表這本日記。”他的這一舉動,曾引起不少猜測,從而使他的訪蘇日記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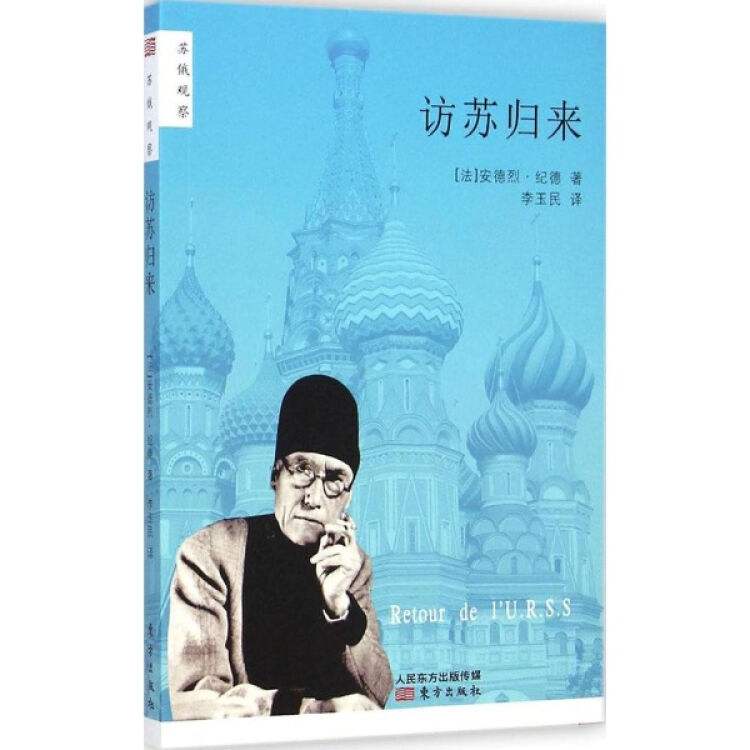
現在,我們可以看看他們當時的觀察和思考。羅曼·羅蘭一方面表示,“我從這次旅行中得出的主要印象與感覺”是“無比高漲的生命力和青春活力的強大浪潮”,“他們正在為全人類更美的、最好的、燦爛的未來而工作”;一方面又認為,那裏“正在不人道地形成賤民階級,必須承認這一切,只能對此感到可惜,只能糾正和根除”。紀德則寫道:“對絕大多數勞動者來説,每日工資為5盧布或更少;而對某些享有特權的人來説則享受更多的優惠。”他得出的結論是,蘇聯出現了貴族。
無論是羅曼·羅蘭還是紀德,在自己的日記裏,都不斷地將高大的紀念性建築、寬敞的別墅和窄小、簡陋、擁擠的普通老百姓住房作為對比。
紀德在日記中對當時的蘇聯市場有着深入的觀察。他是這樣描繪的:百貨公司還不到營業時間,門前已開始有兩三百人在排隊。那天是賣牀墊,或許只有四五百件,卻來了800到1000多顧客。不到天黑,所有的東西都賣光了。需求量那麼大,顧客那麼多,就是在很久以後,一切東西仍會供不應求。
羅曼·羅蘭則對蘇聯人的精神狀況表示了擔憂:“我確信,他們有時甚至過分低估其他民族的生命力。即使資本主義的政府和制度是他們的敵人,也不能低估其生存力。蘇聯勞動者堅信他們擁有並且親自創造了一切最美好的東西,而其餘的世界喪失了這些美好的東西(學校、衞生設施等)。青年不可能自由地將自己的智力成就和思想與他們的西方朋友的成就相比較。真擔心有朝一日突然發生這樣的事,就會產生動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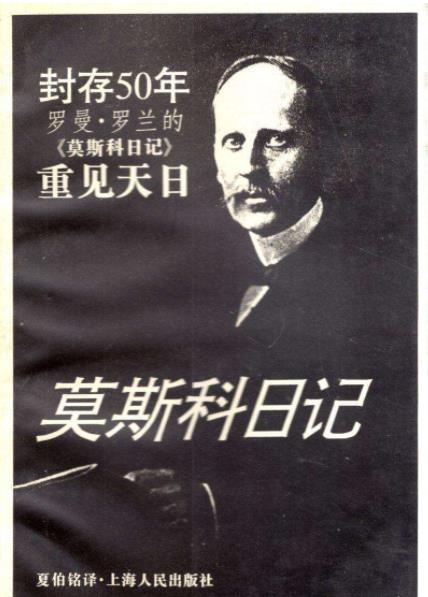
對此,紀德顯然也有同感。他寫道:“蘇聯人對於國外的局勢和狀況處於驚人的無知之中。不僅如此,他們還被弄得深信:外國的一切都遠不及蘇聯好。”他説,有一個青年人曾這樣對他説:“幾年前,德國和美國還能在某些方面讓我們獲益。而現在,我們沒有什麼必要去向外國人學習了……”
俄羅斯學者阿爾巴托夫是這樣論述20世紀70年代的蘇聯的:經濟學者已經意識到蘇聯的經濟發展一直是在走外延發展道路,而現在外延增長的因素已經枯竭。因此,必須把轉向集約化發展道路提上日程,必須從依靠行政命令轉為用經濟槓桿調控經濟。必須重視已經開始的新科學技術革命等。當這些問題被提到蘇共代表大會上時,只是議論了一番。實際上,一切依然如故,毫無結果。
到了20世紀80年代後期,用曾任蘇聯總統助理的切爾尼亞耶夫的話説,對蘇聯社會的質疑開始出現了。當戈爾巴喬夫説“忠於社會主義價值”、“純淨的十月革命思想”等等時,“我們自己也弄不明白,我們究竟是處在什麼樣的社會中”。
曾任蘇共中央領導人的利加喬夫説,我們當時感到特別驚訝的是,蘇聯在科技方面與西方的差距非常大,我們對社會民主化進程的停滯也感到擔憂,這一切都影響到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社會思想。他認為蘇聯進行改革的前幾年,解決了一些住房之類的社會問題,隨後便困難重重,在經濟方面出現了無組織現象。由於急於扭轉經濟上的不利局面,而又不懂經濟規律,就匆忙決定快速轉向市場經濟,結果遇到很多困難,尤其是消費品嚴重短缺,從而引起社會的強烈不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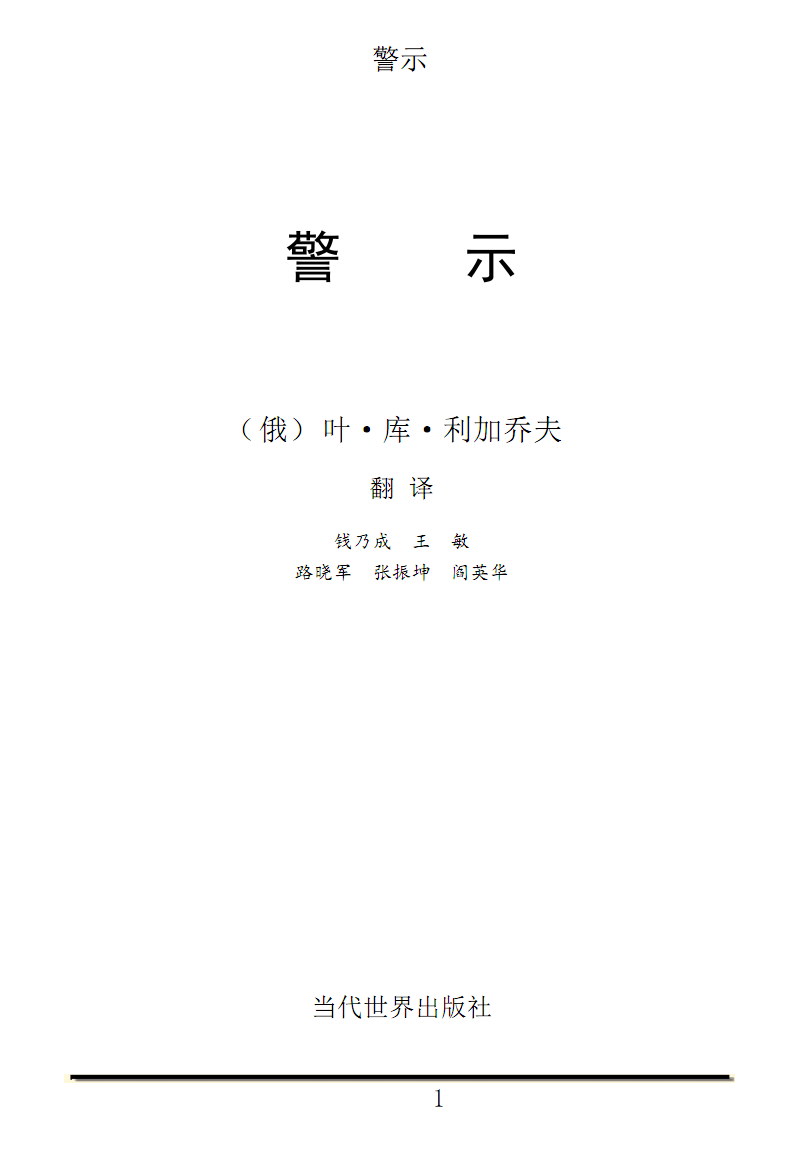
利加喬夫在分析蘇聯瓦解的原因時,特別強調以下因素:首先是大批黨的領導人在國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下變了質;其次,是蘇聯為增強國家的防禦能力而過度消耗了大量資金,把最優秀的幹部、專家學者,最好的設備、材料和大量的工業企業,都投入到這一領域。
切爾尼亞耶夫進一步分析道,西方用超級武器進行的威脅,原來都是虛張聲勢的嚇人手段,而莫斯科卻特別容易受到這些嚇人手段的支配,並捲入了致命的螺旋式的軍備競賽,為之犧牲了一切,最終,也包括犧牲了自己國家的未來。
曾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雷日科夫認為,俄羅斯議會1990年6月發表主權宣言,是蘇聯瓦解的決定性事件,此後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阻止蘇聯走向崩潰。一旦俄羅斯明確宣佈自己是小於蘇聯整體的主權國家,聯盟的瓦解就成為不可避免。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認為,有兩件事對蘇聯解體產生了巨大作用,一是1990年俄羅斯的主權宣言,因為當時全蘇聯境內除了波羅的海三國外,沒有一個加盟共和國搞獨立,俄羅斯向誰要主權?答案只能是:向其他加盟共和國,向蘇聯;再就是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宣佈退出蘇聯共產黨。這兩件事一發生,蘇聯解體的命運就定了,因為支撐它作為一個統一國家的主要支柱已經坍塌,維護和保證國家統一的紀律和意識形態也不復存在了。
如今看來,可以這樣説,就蘇聯而言,成也俄羅斯,敗也俄羅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