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譯啊張譯,你可算是紅了!_風聞
最人物-最人物官方账号-记录最真实的人物,品味最温暖的人间2019-10-15 14:19
作者| 東北童星
來源| 最人物
張譯説,在別人對自己的眾多評價中,他最喜歡賈樟柯導演的那句:“張譯,能行的。”
四兩撥千斤,只表示“還可以”,但卻是他聽過最舒心與準確的“表揚”。
1985年8月18日,松花江上發生了一起特大沉船事故,船上238名乘客,最終僅67人生還。
當天下午,距離這條江十幾公里之外的某單元樓門口聚滿了人,街坊們左顧右盼,神色緊張,因為他們聽説,今天老張一家都去坐船了。
好在,虛驚一場。
當晚死裏逃生的老張夫妻説,他們之所以沒有上船,是因為小兒子——張譯,非要去動物園看大馬猴,他們才臨時改變了過江遊玩的計劃。
一不小心做了全家人的“救命恩人”,這讓當時年僅7歲的張譯驕傲到躺在牀上一宿沒睡着覺,他想: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自己一定是“天選之子”,以後必定大有作為。
抱着這樣的想法,張譯沒羞沒臊地活到了18歲,而也是直到那一年他才發覺,自己的確是“被神選中的孩子”,但很不幸,這一次選中他的是“衰神”。
張譯的人生是從16歲那年開始走“背”字兒的。
那時他是整片小區裏最特別的孩子,性格內向,不愛學習,但對調皮搗蛋卻始終熱情。
身為教師的父母看着着急,天天拿着戒尺跟在他屁股後面,可無論挨多少揍,男孩都死性不改,他説,“寫作業”是一種“生理上的疼痛”,一想起來就覺得肝顫。
不念書、不交友,不知道拿什麼解悶的張譯,只好將眼光投向了小動物。用大葱喂兔子惹它們發瘋、在母雞腦袋上撒尿逗它們撒野、用斧子掘螞蟻窩看它們落荒而逃……
“不着調。”這是彼時張譯收穫的“一致好評”。
可無論平日裏有多麼混不吝,對於每天早上6:30開播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他的心中總是充滿了敬畏。聽着主持人字正腔圓念出的新聞,“雄壯而令人振奮”的聲音迴盪在老街之上,他想“播音員”一定是這個世界上最神聖的職業了,沒有之一!
張譯(右二)童年照
1994年春天,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開始在全國招生。彼時張譯高二,雖然還不夠高考的歲數,但還是報名參加了院校專業課的考試。
幾個月之後,成績公佈了,專業課全國第一。但因為沒有文化課的成績,張譯最終還是隻能與“廣院”擦肩而過。得知消息後他挺沮喪,但同桌卻顯得格外興奮:
“彆氣餒!以你的實力一定能考上廣院!中央台有個羅京你知道吧?到時候你就是羅譯!”
抱着一定要成為“哈爾濱羅譯”的想法,張譯在第二年再次報考了北京廣播學院。為了表明自己的決心,他在最終志願表上只寫了這一所學校的名字。
在高考這條路上,他沒給自己留後路。而巧合的是,高考也沒給他留後路。
那一年北京廣播學院只在東北招收兩名學生,他因沒得到特殊加分,最終成績從並列第二“咣噹”成了全國第三——
張譯,又落榜了。
張譯童年照
兩次追夢無果,讓這位18歲鐵骨錚錚的東北爺們兒第一次感受到了夢想破滅的滋味。在家裏連着躺了小半個月,拒絕復讀的張譯從居委會大媽手中雙手接過了“待業青年證”。
看着面前翠綠翠綠的小本子,張譯大腦一片空白,這怎麼待業還發證書?成榮譽了?!
眼看着成為“東北羅譯”是沒戲了,張家父母又幫兒子盤算起別的出路。得知哈爾濱話劇團招學員,張爸爸連打帶罵地將兒子薅到了招生辦門口。
隔着一道門,老師只抬頭看了張譯一眼便搖了搖頭,站沒站相,坐沒坐相的,這一看就不是做演員的料啊!
老師説得挺直接,但張父卻不想放棄。好話説盡,笑臉賠盡,前前後後跑了幾趟,才拿着借來的3萬塊,自費把張譯硬塞進了話劇團的大門。
忙活了半天,張譯終於擺脱掉了“待業青年”的標籤,但他的心裏卻沒有半點高興的意思。
因為當時的他始終認為,相比於端坐在廣播廳裏的央視主播,做演員簡直是一份沒落到不能再沒落的工作了,太掉價了!
又糾結了十來天,張譯才心不甘情不願地走進了表演的課堂。他心疼錢,更心疼父所以儘管百般彆扭,入校之後他還是會每日按時出現在教室裏。
看着在地上模仿動物,連滾帶爬“解放天性”的同學,張譯兩眼一黑:
什麼玩意兒!花裏胡哨!
在哈爾濱話劇團灰頭土臉地混了小半年,張譯迎來了生命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當時全國正在舉行文藝調演活動,團裏演話劇,張譯閒得無聊便去看了兩場。坐在觀眾席中,張譯將自己完全置身於舞台之外,開始第一次如此認真的,以旁觀者的角度去正視演員這個身份。
起初他只是看,然後看看看着,便開始痛哭流涕。
也許是被台上老師的演技所折服,也許是被強大的舞美燈光所吸引,總之那一天的張譯,近乎是以光速,在眼淚與感動中頓悟了表演這一職業的偉大與不易。
“演員,應該比播音員厲害一點吧。”
從初二第一次知曉播音這個職業,到後來兩度名落孫山,那是張譯第一次承認,有一件事會比“考上廣院”更讓自己驕傲。
當發現自己已經一發不可收拾地愛上了表演之後,張譯幾度想過要帶着鋪蓋睡在劇院的排練廳裏。
白天可以看人排練,晚上能自己練習,既節省了來回宿舍的時間,又幫團裏省了牀鋪,這簡直一舉兩得。
那時話劇團裏有一間類似“藏寶閣”的圖書室,裏面放着團裏多年來的經典劇目,明裏借不來,他便每天裹着軍大衣窩在角落裏偷着看,什麼時候讀完,什麼時候心裏才算舒坦。
急赤白臉地學了一年,張譯可算在劇本和話劇中摸出了點門路。老師看出來他對錶演上心,旁敲側擊地暗示他,要真想在這條路上混出點名堂,那還是要去北京。
那時候“北漂”尚屬新興詞彙,而對於北京,張譯也只知道那幾所知名錶演院校,別人勸他再想想,結果他大手一揮頭也沒回地就坐上了進京的火車。
“想啥想?北京,高二那年我就想去了!”
1997年,19歲的張譯正式做起了北漂一族。當時他住在一間招待所的頂樓,條件艱苦,但他覺得這樣“一步登天”的寓意還不錯。但俗話也説,爬得越高,摔得越狠。
到了北京以後,張譯開始頻繁出現在各大表演院校的考場上。
報考解放軍藝術學院,體檢結果顯示營養不良,他連主考官的面都沒見上;
參加中央戲劇學院複試,他對着老師大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的利與弊,言語中滿是自己前後讀過超過2000個劇本的驕傲與自豪,結果老師只是看着他沉默,然後問道:
“你考不考慮去讀中文系或者導演系?”
在眾多報考表演系外貌極其周正的考生中,張譯小眼睛單眼皮,一看就一臉憨厚樣的長相顯然不吃香。
院校看不上他,他也不強求,考不上拉倒,老子還不伺候了呢!
收拾好鋪蓋,張譯轉身和室友道別,這時他聽見對方説:“要不你去你再去軍區戰友文工團試試?”
幾乎是抱着“必死”的決心,張譯又向人打聽到了戰友文工團的地址。
坐着老式公交車,走在只修了半截的破公路上,張譯一邊吃着揚在空中的黃土,一邊對着窗外大聲朗讀着等下要背誦的詩歌散文,一開始還有腔有調,後來乾脆就變成了鬼哭狼嚎,那時他想:
“這北京城這麼大?怎麼就容不下我呢?!”
結束了在北京的所有考試,張譯回到了老家哈爾濱。左右等不來消息,他便硬着頭皮主動給戰友文工團打了電話,對方有些猶豫,最後極其不情願地説了一句:
“還有三個自費名額,你來嗎!”
“來啊!”
前後不到3個月,張譯二度進京。穿上軍裝,背上行囊,折騰了兩年,他終於得到了一個落腳的地方。
和其他表演院校不同,文工團的表演課程繁雜且量大。
從週一到週六,從早上7點到晚上10點,除了要正常上課,戰士們還要擔起慰問演出、日常作戰訓練等一系列活動,雖然每天忙到腳不沾地,但張譯依舊樂此不疲,他説,自己是高高興興去吃苦。
在文工團做學員期間,張譯偷偷摸摸地談了個女朋友,交往了兩年,最終戀情還是在公開的當日,被女方家長當場掐斷了氣。
問理由,對方答:
“這男孩看着像大隊會計,臉好像被屁股不小心坐過的,以後肯定當不了演員。”
被屁股坐過,還是不想小心的!張譯苦笑:“不就是嫌我長得醜嗎?這事兒不用你説,我自己知道!“
想當初班裏評選“醜男top榜”,張譯排第三,獲獎理由是“有一張驢臉”,而排第一的是睡在他上鋪的的好兄弟,外號“對眼醜矮子”的“燕小六”肖劍。
睡在張譯上鋪的好兄弟:“燕小六”肖劍
夜深人靜時,哥倆時常坐在一起看雪看星星,情到濃時還談談詩詞歌賦和人生理想,也是在這個過程中,張譯知道自己只能玩命走實力派這一條路了。
決心發奮之後,張譯成了班裏典型的“努力派”。
配廣播劇、寫小劇本、研究小品包袱、自制搞笑段子,那幾年他自學各種才藝,做過場記、當過道具、打過燈光、學過剪輯,用本山大叔的一句話來説那就是,“這知識啊,都學雜了”。
然而,他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而且單照溝渠還夠,還連帶着把張譯也帶進了溝裏。
文工團時期的張譯
當學員時,每日上交的小品作業,是老師考核的最重要標準。在這過程中,從劇本創作到舞台設計,再到最後的正式演出全部都要學生自己完成。
當時張譯是他們小組的主力,點子多、想法好、甩出的包袱也比別人好笑。
但不知道為什麼,無論前期準備工作做得多充分,到正式演出時他們一定會狀況百出。

《追兇者也》張譯
記得有一次,張譯吭哧吭哧寫了小半個月,終於寫出了自己認為“最滿意”的劇本,預備憋個大招亮瞎眾人。
為確保演出萬無一失,他找來了最信任的搭檔,就連道具都是自己親手做的,結果萬萬沒想到,演員剛一上場,就被道具絆了個四仰八叉。
台上張譯慌忙起身,抬眼便看見台下主考官莞爾一笑,然後説道:“別演了,滾出去。”
諸如此類的事情,在當兵的那些年裏他經常遇到:
説雙簧碰到觀眾冷場,演小品遇到道具失靈,就連日常交個作業,都能碰到因為吃撐了彎不下去腰,而被老師趕出教室的情況……
文工團十年,論倒黴,誰也比不過張譯。
後來他想,已經這麼衰了,老天爺還會讓我更倒黴嗎?!
命運答:完全沒問題啊!!
《我的團長我的團》張譯
從學員班順利畢業之後,張譯正式“轉正”成了一名光榮的文藝兵。告別了曾經苦哈哈做學徒的日子,團內所有人的演藝生涯都開始逐漸步入正軌,除了他。
作為老師口中“全班唯一一個不會演戲”的學生,彼時的張譯只能在舞台之上扮演一些龍套角色。一晃而過的賣雞蛋大爺、上場就犧牲的英勇戰士,以及各種從觀眾全世界路過的甲乙丙丁,這些都是他在那十年裏演繹的主要人物。
某天老師找張譯談話,雜七雜八説了一堆,最終總結成一句話便是,只有小演員沒有小角色,還是得找機會發揮長處。
聽了這話他苦笑一聲,心中百感交集:台詞兒都沒有,上台就卧倒,這上哪兒發揮去?!
有一次團裏破天荒選張譯當了個男三號,他高興得“如夢如幻,欲仙欲死”。開機前他一通準備,最後被告知拍不了,因為導演被‘擼“了,劇組得重新選角。
張譯不甘心,接着問:“那我咋辦?”領導輕笑説:“我推薦你去劇組做場記了。”
人倒黴了,還真是喝水都塞牙縫。
2003年前後,張譯恩師退伍,分別前大夥湊在一起吃了頓飯,席間師徒二人抱頭痛哭,老師語重心長地對他説:
“孩子啊,你演戲那就是個死啊!”老師酒後吐真言,張譯瞬間心如死灰,別人演戲出體力,他演戲倒鬧出人命了。
這之後張譯消沉了一段時間,別人都以為他可能從此便放棄了,結果沒成想,他根本就是一個認死理的愣頭青。
演不行,寫總可以了吧!
後來張譯得了一個寫劇本的工作,他洋洋灑灑一路寫,期間還把自己寫哭過好幾回。按照要求他要寫20集,眼瞅着差2集就收尾了,對方打來電話説,不好意思啊,沒錢拍了,劇本不要了。
你説,八百年都碰不上一回的事兒,怎麼全讓他趕上了呢?

前些年,張譯曾在某訪談中説過自己一個“怪病”,不能躺着,因為只要一平躺,他就馬上會進入半昏迷狀態。於是為了不耽誤大家的時間,他極少以卧姿演出,能站着便絕對不坐着。
而這也似乎也在冥冥中寓意着,他這一生便是勞碌命。
團裏沒機會,劇本寫不成,認死理的張譯又拿着自己的照片開始了“跑組”工作。手握自拍照,他見過各色各路的導演,但得到的最終回覆卻出奇一致:
“我們不需要你,因為你長得沒特點。“
聽了這話,張譯又笑了,摸出手機他給“對眼醜矮子”肖劍發了條短信:
“長得醜不叫特點嗎?怎麼你醜得就那麼有特點呢?!”
“跑組”的日子張譯捱了四五年,不僅一個角色沒“跑”來,還把自己自信心打壓得夠嗆。
彼時的張譯已經26歲了,要啥啥沒有,那段時間連他自己都覺得自己這輩子也就這樣了,可老天卻告訴他:
別急,你再等等,快了,就快了。
2004年張譯出演《農工》,殺青時前輩問他多大了,他答快27了。對方點點頭,開口道:
“這男演員啊,28歲要還出不來,那可就夠嗆了。”
這話雖然聽着有點嚇人,可張譯倒沒放在心上。“夠嗆”算個啥,這麼些年在表演這條路上,他都被判了多少回“死刑”了?
轉眼到了年下,張譯從朋友那裏得知《士兵突擊》劇組正在選角,他想試試,於是提筆便給導演寫了一封3000多字的自薦信,裏面詳細列舉了自己適合飾演許三多的16點理由。
第二天,他把這封信鄭重其事地交給了導演康洪雷,當天晚上便接到了劇組副導演打來問檔期的電話。
張譯高興,張口就説:“我沒檔期”,想想覺得不對趕緊又補了一句:“我沒有任何可以稱之為檔期的工作!”
《士兵突擊》劇照 張譯扮演史今
正式進組前,張譯向部隊申請假期,因為時間不定,領導顯得很是為難。他怕給部隊添麻煩,乾脆把心一橫,直接遞交了轉業申請。
穿了十年的軍裝要還回去了,他捨不得,但拍戲這事兒他也盼了小半輩子了,他不想放棄。
後來張譯沒能演成“許三多”,變成了把許三多招入部隊的史今。“班長”的戲份不多,一共9集,張譯沒拍太久,便迎來了自己的重頭戲,也是殺青戲——史今退伍。
拍攝當天,張譯恰好接到了部隊的通知——轉業申請通過了。他沒説話,轉過頭和扮演高城的演員張國強坐進了車裏。
路過天安門時張譯癱坐於後座嚎啕大哭,嘴裏含着的半顆大白兔奶糖沒了甜味,只剩下了眼淚的咸和十年來的苦澀與無奈。
他知道,從那一天起,自己再也不是一個兵了。
2006年平安夜,《士兵突擊》開播,帶火了整整一個排的人。雖然只是出演了一個配角,但張譯依舊滿足,好賴自己真的是個演員了不是?
這部《士兵突擊》,給人們留下了無盡回憶。劇中的張譯,也給人們留下了無盡的淚水。在劇中情到深處的張譯,已經無需演技。
而那一年,張譯剛好28歲。
《士兵突擊》張譯:“你選擇了這種生活,到該走的時候就得走……”
連滾帶爬地走了十年,張譯終於如願當上了演員。因為深知每一個機會都來之不易,所以面對角色他永遠心懷敬意。
出身部隊,張譯不懂投機取巧,永遠只會拼盡全力。
《雞毛飛上天》張譯演繹八年後“重逢愛人”
看一次哭一次
拍《兵團歲月》,為了力求真實他在零下三十幾度的大雪天裏洗澡,最後被人扛着回帳篷取暖;
拍《生死線》,他一開機便被通知內臟有問題,但他覺得沒事兒,結果差點當場淹死在片場;
拍《我的團長我的團》,張譯扮“瘸”5個月,因為長時間用力不均,兩小腿的直徑發生了變化,他硬生生將自己好腿走成了“瘸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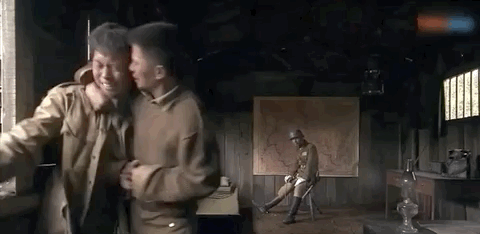
《我的團長我的團》張譯
拍《紅海行動》,為了不耽誤全劇組的拍攝進度,他愣是拖着骨折的腿完成了自己所有的戲份;
拍《八佰》,別人演哭觀眾,他演哭導演;
拍《攀登者》,他又裝瘸,演技之逼真,惹得人特意去網上開貼詢問“張譯是不是真的瘸了?”

《攀登者》拍攝現場
張譯零下十幾度赤腳登雪山
演員20載,張譯要戲不要命。
“我的老師是規矩人,我也是規矩人,所以演得戲也要規規矩矩。”
一直點背、倒黴、默默無聞的張譯,終於看到紅起來的曙光了。
有的人,一夜成名、一站走紅,而張譯的紅,慢熱,充滿坎坷、血淚、傷痛,這樣的人不紅,實在有點説不過去。
3年前,憑藉着在電影《親愛的》中的出色演出,張譯拿下了金雞獎最佳男配角獎,這是他出道以來,獲得的第一個專業性大獎。
領獎台上,張譯一口氣説了17個“感謝”,謝天謝地,唯獨忘了謝謝這麼多年,無論怎樣都沒放棄的自己。
迎難而上容易,但迎了這麼多難還在往上爬的,張譯算是為數不多的人。

《親愛的》張譯哭戲演哭片場所有人
這些年,張譯前前後後拍了很多戲,拿過影帝,走過戛納,沒事兒還去柏林電影節裏溜溜彎,他的演技一直在被肯定,但人氣卻始終不温不火,問他難受嗎,他搖搖頭説:
“其實找我上綜藝的不少,我都推掉了。我沒有本事去娛樂大眾,我就只會演戲。”
踏踏實實做人,認認真真演戲,軍隊紅磚綠瓦下長大的男人,永遠樸實與炙熱。
《紅海行動》拍攝現場張譯受傷
記得張譯剛剛憑藉《士兵突擊》讓觀眾臉熟時,某主持人問他“對於過去各種倒黴的經歷,你覺得是苦難嗎?”
他回:“從前覺得是,現在想想,也挺好的。”
不抱怨,不糾結,從千難萬險中走出的演員,始終勇敢與樂觀。
張譯,挺好的。
很多年後,張譯仍記得自己當初在北京備考的日子。
那天陽光明媚,但是大風不停。他花100塊錢買了輛二手自行車,頂風騎了兩個小時跑到了北京廣播學院。因為沒有學生證,他只能從側門進去。走在夢寐以求但兩次錯過的大學校園裏,張譯滿心惆悵。
那一天,他將學校內所有帶“廣播”二字的地方都逛了一遍,然後在主教學樓裏上了趟廁所,最後騎上車又逆風騎着回到了宿舍。
因為吹了一天的風,張譯第二天就發了燒,室友笑他,問他這是何必呢,他迷迷糊糊地答:
“喜歡,嚮往,沒辦法。”

部分參考資料:
1、張譯:《不靠譜的演員都愛説如果》
2、《最佳現場》張譯專訪(2006年~2011年)
3、《魯豫有約》張譯專訪
4、《可凡傾聽》張譯專訪
5、《易時間》張譯專訪
6、《金星秀》張譯專訪
7、《非常靜距離》張譯專訪
8、《超級訪問》張譯專訪
9、電影《攀登者》、《紅海行動》、《追兇者也》、《親愛的》等幕後花絮及主創採訪
圖片來源:網絡、影視截圖、視覺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