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崎駿與庵野秀明的「父子局」:拍同一個故事有什麼區別?_風聞
动画学术趴-动画学术趴官方账号-2019-10-18 09:58
“動畫作品的好壞並不取決於某一種技術是否被用到或某一種理念是否被伸張,真正關鍵的問題始終是它們的使用是否符合作品的整體意圖和作者表達。”
前段時間,我們以兩篇文章的形式,向大家介紹了一部世界級的動畫學術名著——由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東亞研究系教授托馬斯·拉瑪爾(Thomas LaMarre)教授撰寫的**《動畫機器:動畫的媒介理論》**。
在第一篇推送中,我們向大家簡單介紹了動畫機器的基礎理論以及這一理論涉及到的一些基礎概念。而在另一篇推送當中,我們專門討論了宮崎駿的影像技巧,並重點談及了他的作品**《天空之城》**。(可點擊相關文字,前往相應的推送查看)
今天,我們就來繼續與之相關的討論。
托馬斯·拉馬爾認為,《天空之城》在宮崎駿的系譜裏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它承前啓後,堪稱宮崎駿創作生涯的轉折點。
《天空之城》是吉卜力工作室成立後製作的第一部影片,其內容與宮崎駿此前參與的作品有很多關聯——巴魯和席達在末日後的世界裏的冒險很容易讓人想到**《未來少年柯南》的故事,而席達胸前的神秘項墜又似乎與《太陽王子霍爾斯的大冒險》**中希爾達的項墜有着某種呼應。
但《天空之城》與之前的作品相比又有着明顯的區別,而且在它之後,宮崎駿就背離了他原本所擅長的少年冒險類故事,轉而把少女作為了他之後多數作品的主角。
《未來少年柯南》
《太陽王子霍爾斯的大冒險》中的希爾達
因此,《天空之城》就像是宮崎駿對自己過往作品的一次總結,他把以往作品中的各種元素集中起來,彙總成了《天空之城》中的故事和背景。而這次總結其實也是一次告別,之後他就開啓了一個以飛翔的少女為核心的動畫新紀元。
有趣的是,在幾年之後,一部名叫**《藍寶石之謎》**的電視系列動畫播出了。這部動畫無論在世界觀、角色還是劇情上都與《天空之城》有着大量相似之處。但由於製作背景、播放體裁的不同,兩部作品也有着明顯區別。
《天空之城》作為以劇場公映為目標的電影作品有着更為精美的畫面和更為流暢的動畫,整體給人的感覺也更具品質和藝術性。而《藍寶石之謎》作為電視動畫,在預算和時間雙雙受限的條件下還要為了長期播出而擴充內容,難免在品質上有所欠缺。由於這樣的差別,《藍寶石之謎》很容易被人們看成是對於《天空之城》的東施效顰。
《藍寶石之謎》(又名《海底兩萬裏》)
那麼《藍寶石之謎》真的就沒有價值了嗎?面對《天空之城》的珠玉在前,它的創作意義又何在?
關於這一點,拉馬爾也有話要説。在這篇推送當中,我們就從他的理論出發,簡單聊聊這兩部作品之間的關係吧。
《天空之城》和《藍寶石之謎》
《藍寶石之謎》是Gainax工作室早期由庵野秀明執導的作品,90年代引進過中國,是不少人的兒時回憶。簡單來講,它就是一個改編自凡爾納小説**《海底兩萬裏》**的故事,與《天空之城》的文本比較,也有相似之處。
二者的故事都圍繞一個戴着神秘項墜的少女展開(席達和娜迪婭),熱愛科學的少年(巴魯和讓)偶然與少女相遇,隨之遭遇到的還有追蹤少女而來的盜匪(朵拉一族和格蘭蒂斯一夥),以及更為危險的秘密組織(黑眼鏡和新亞特蘭蒂斯人);少年一邊幫助少女躲避追捕一邊同其一道展開冒險,原本作為反派登場的盜匪在這個過程中轉變為少男少女的同伴;最終,少女的身世會被揭曉為某失落文明的後人,這一文明曾掌握着足以毀滅世界的先進技術,而項墜上的寶石(飛行石和Blue Water)則是重啓毀滅技術的關鍵。
席達和娜迪婭,她們的胸前分別佩戴着飛行石和Blue Water
巴魯和讓
朵拉一族和格蘭蒂斯一夥
黑眼鏡和新亞特蘭蒂斯人
事實上,兩部作品在文本構成上的相似並非偶然,《藍寶石之謎》原本就是宮崎駿在70年代為東寶動畫所寫的一個企劃案,原標題為**《海上環遊地球八十天》**。
儘管這個企劃未能在當時推進下去,但宮崎駿卻將其中的許多構想用在了《天空之城》裏。而《天空之城》的成功又讓NHK和東寶動畫反過來想起了這個被遺忘的企劃案,決定將其製作成電視動畫,並由此找到Gainax工作室。所以,《天空之城》和《藍寶石之謎》其實從文本的源頭上就有着密切的關聯。
可儘管《天空之城》和《藍寶石之謎》有着諸多重合之處,它們所呈現出的面貌和帶給人的感受還是非常不同的。**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去尋找它們不同的原因,但討論的結果往往會是一種簡單粗暴的厚此薄彼:**認為《天空之城》作為影院級別的動畫長片,更追求全動畫的美學理念,因而更深得動畫藝術的精髓;而《藍寶石之謎》作為成本有限的電視動畫,高度依賴具有日本特色的有限技法,追求高效,而在藝術性上大打折扣。換句話説,《藍寶石之謎》就像是一部廉價版的《天空之城》,它自身似乎並沒有創造出任何新的價值。
關於促使人們做出這種評價的動畫觀念,可以參考我們之前寫過的文章:宮崎駿VS手塚治蟲,站在命運十字路口的日本動畫,我們在這裏就不再贅述了。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對於宮崎駿和手塚治蟲所代表的兩種動畫類型的區分有其存在的意義,但當這種區分被簡單地用來做高下之分時就有問題了。換言之,在討論《天空之城》和《藍寶石之謎》的異同時,我們不能對這種結論輕易買賬,應該用更加客觀科學的方法來進行比較。
開放合成和扁平合成
説到客觀科學的方法,自然就輪到**“動畫機器”**的理論出場。
在之前關於宮崎駿的分析中,我們已經領略到了他對開放合成的靈活應用。他一方面通過背景和角色之間的反差來強化影像內的間隙感,一方面又利用流暢寫實的角色動畫來抑制這種間隙感,兩者配合,相得益彰,形成了獨具一格的畫面張力,並藉由飛翔的主題,同他對現代技術的反思結合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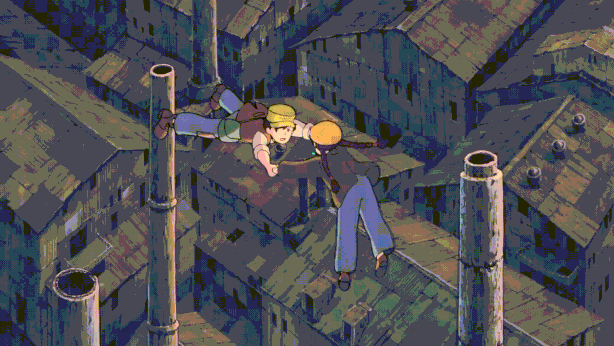
而在《藍寶石之謎》中,我們看到的則是另一種合成方式。與《天空之城》不同,自然寫實的角色運動在這裏成為次要的運動來源,圖層間的相對運動和攝影機的視點運動則更為突顯。
比如該系列第一集中這個展現馬戲團後台的鏡頭(見下圖),其中的角色基本靜止,完全依靠前後圖層的相對運動和攝影機的移動來產生動態。又如後面那個娜迪婭走路的鏡頭(見下圖),角色走路的動作用到了循環動畫,而前進的動態則主要來源於背景圖層的滑動和攝影機的推動。這種形成動態的方式是該系列的主流,構成了該作整體上不同於《天空之城》的合成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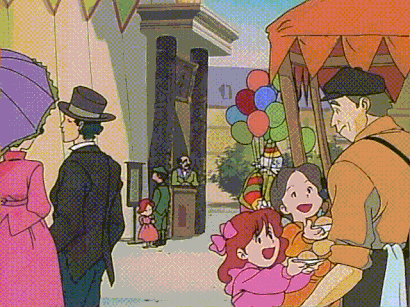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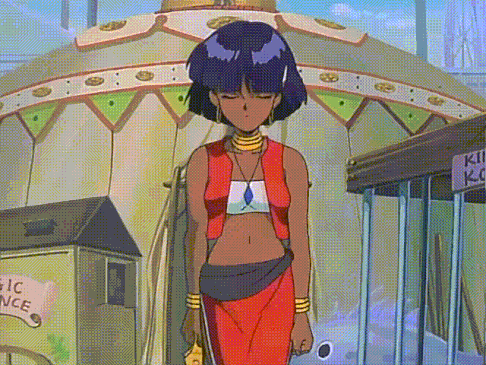
此外,二者在處理背景和角色的關係時也採取了不太一樣的態度。在《天空之城》中,背景細節飽滿,明暗豐富,充滿深度,看起來十分貼近自然現實;與之相對,角色則造型簡約,色彩平面,帶有一定的圖形性。這就使背景和人物的反差十分明顯。
而在《藍寶石之謎》中,背景的繪製相對粗率,線條和色彩分佈都更為圖式化,有時還會採用和角色相近的風格。與此同時,角色的造型則更為複雜,細節更豐富。兩相對照,雖然還是能夠看出明顯的分別,但信息密度和深度效果上的差異有所減小。比如在下面的截圖中,兩部作品在處理天空和花草時的手法就有着一目瞭然的差別。
歸納起來,《藍寶石之謎》的合成方式與《天空之城》中的開放合成是有着明顯差別。儘管兩種合成方式都可以讓我們察覺到影像內部圖層間的間隙(這種間隙在封閉合成中是看不到的),但《天空之城》中的間隙感****一方面會被深度背景和平面人物之間的反差給強化,一方面又會被角色運動所彌合;而《藍寶石之謎》則一邊通過等量的細節和相近的風格來弱化前後景的差異,一邊通過圖層間的運動來強調間隙的無處不在。鑑於後者所產生的效果,拉馬爾將其稱為扁平合成。
又是這張圖
在拉馬爾看來,扁平合成和封閉合成、開放合成一樣,都是活動影像的合成方式。採用不同的合成方式,我們就可以按照不同的思維來引導活動影像的潛力。也就是説,**不同的合成方式反映的是不同的影像思維,而不同的影像思維之間是沒有高低之分的。**要評判合成方式的好壞,主要還是看它所體現的影像思維與作品的表達意圖之間是否契合。
儘管《藍寶石之謎》與《天空之城》的文本有着許多重合,但動畫所採用的合成方式卻並不一樣。換句話説,《藍寶石之謎》其實是在用一種不同於《天空之城》的影像思維處理與之相同的文本命題,就好像用不同的思路來解同一道題,最終的卷面呈現也會因此而出現差異。
那麼,《藍寶石之謎》究竟為什麼要使用扁平合成的方式呢?這種合成方式與它想要表達的東西之間又有什麼關聯?
單一參照系和多重參照系
拉馬爾認為,《天空之城》裏的風景極為寫實、充滿深度,這種背景風格其實暗示着一個外在於那裏的絕對自然,併為角色提供了一個秩序井然的世界框架。角色在這個世界中的運動方式也是符合自然法則的,即使有魔法和技術的幫襯也不能完全隨心所欲。與之相較,《藍寶石之謎》中的背景在繪製方面往往沒有那麼講究,缺乏穩定統一的深度,對角色的約束也並不十分牢固。
他由此指出,宮崎駿的背景裏始終有着一種**“預先存在的深度”**(preexisting depth),這在一定程度上規定了角色的活動空間,就像一個固定的參照系。儘管角色會在飛翔的過程中不斷調整角度來探索和這個參照系之間的關係,但其實並不能真正動搖它的內部秩序。圖層間的相對運動也是以此參照系為依據而顧慮重重的。不僅如此,宮崎駿在《天空之城》以後的作品裏還在不斷地強化背景的細節和深度效果,這其實就是在鞏固這個參照系的權威。
不過,這種權威在扁平合成的動畫裏卻不是必須或一以貫之的。由於圖層間的差異時常會被抹平,背景就未必比其他畫面元素顯得更有深度,也無法提供作為絕對參照系的權威。預先存在的深度雖然也會偶爾出現,但不會成為一個始終在場又無懈可擊的框架。它同角色的關係也相當任意和鬆散,角色可以遵從它也可以無視它,總之不會較真兒地把它當成唯一的標準。
換句話説,影像的扁平風格帶來了一種去等級化的效果,孰上孰下、孰內孰外、孰遠孰近的關係都變得不明確了。原本由深度背景所擔保的不容置疑的外部世界變得可懷疑和可取代,單一固定的參照系也因此失效了。

《藍寶石之謎》中的多平面互動
如上圖所示,在一個由多平面所組成的世界裏,當所有平面都相對扁平的時候,沒有哪個平面比其他平面更為絕對或更具權威,它們同樣散佈在一個相對運動着的關係網中,就像電腦屏幕上不斷交換位置的多重窗口,新的窗口會不斷產生,而每個活動中的窗口也都有可能在下一秒被隱藏或來到頂層。
單一參照系的坍塌也預示着多重參照系的出現。事實上,《藍寶石之謎》的很多方面都印證了多重參照系的存在。這一點同樣可以通過與《天空之城》的比較看出來。
在《天空之城》裏,儘管宮崎駿沒有明確故事的發生時代,但整體的服裝、環境、技術條件都在有意識地營造一種19世紀再臨的感覺,這讓劇中的角色可以面對現代化來臨的時刻重新做一次選擇。**而****在《藍寶石之謎》中,儘管時間被明確設定在了19世紀末,我們卻可以同時在這個故事裏找到來自於不同時代的技術。**這種時空錯亂的旁徵博引幾乎將故事裏的19世紀變成了整個技術文明史的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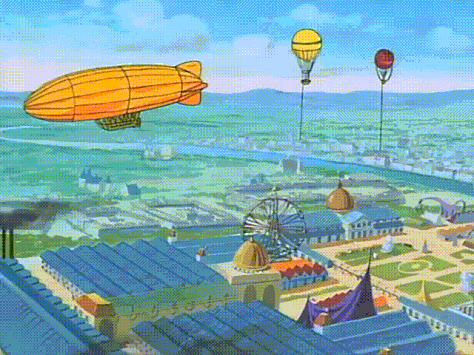
《藍寶石之謎》第一集中的巴黎萬國博覽會
造型具有不同年代感的各種設備
**其次,我們在《藍寶石之謎》主人公的設定上也能發現不可思議的身份雜糅。**娜迪婭的裝扮、膚色和在馬戲團的工作都暗示着她在奴隸貿易背景下的被殖民者身份,但她真實的身份卻是殖民地球的外星人後裔。同時,她對於科學技術的態度也總是搖擺不定,她一方面對技術深惡痛絕,一方面又無法離開技術帶給她的種種好處。這種混雜着矛盾的設定使娜迪婭的表徵意義曖昧不清,同時與不同的文化和意識形態背景相聯繫。與之相較,《天空之城》中的席達在設定上就沒有那麼多指涉,比較單純和統一。
娜迪婭在馬戲團充滿異域風情的海報
**最後,《藍寶石之謎》所關涉到的主題似乎也較之《天空之城》更為龐雜。**當鸚鵡螺號船員們的多種膚色將我們引向多種族文化的主題時,亞特蘭蒂斯人的人類製造計劃又在挑戰宗教和進化論的主題,而娜迪婭、讓和尼莫船長等幾位重要角色面對科學技術時的不同立場又促使我們不得不思考人與科技、自然與文明之間的關係……相較而言,《天空之城》所關注的問題就比較集中,整體都聚焦在對於現代技術的反思上。
《藍寶石之謎》中提到的諾亞方舟
總之,從方方面面來看,《藍寶石之謎》都在打破單一固定的參照系,以雜糅的方式與各種各樣的參照系產生溝通。拉馬爾將此稱為**“參照系的增殖”**。
由於參照系的增殖,我們沒有辦法像在宮崎駿的動畫中那樣獲得一個超然而又統一的視角去反思人與世界的關係。因為要對某樣事物進行宏觀把握,就必須和它拉開一定的距離,在其外部找到一個位置。可是在《藍寶石之謎》所創造的世界裏,焦點被多種多樣的參照系給分散了,無法凝聚為一個超然於世界之外的統一視點,因而只能陷在這個嘈雜的世界裏,捕捉各種局部的、臨時的、個體化的關注。
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藍寶石之謎》壓根就不打算像宮崎駿那樣從一個宏觀的維度去思考什麼人與世界的宏大主題,而只想從各種微觀的角度去呈現我們在這個世界裏的無比瑣碎的生存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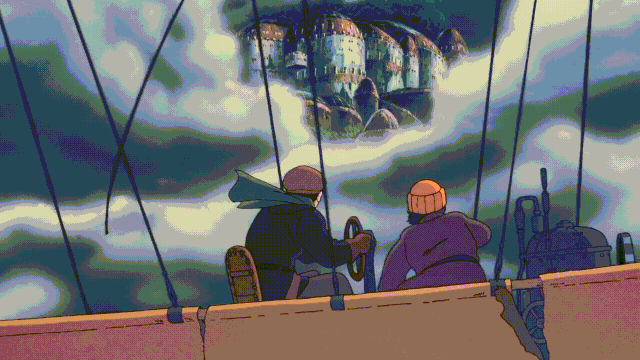
《天空之城》中在世界之外的觀看
《藍寶石之謎》由此可以被看成是一種以動畫形式對後現代社會所做的診斷。它一方面通過扁平合成的方式,在平面化的、去等級化的、相對化的影像流中瓦解獨一無二的“大”世界的根基。
另一方面又通過混淆的時空元素、曖昧的人物設定、散漫的敍事和廣泛的主題涉獵召喚人們去做出自己的選擇,發展自己的個體化“小”世界。這種由大到小的轉變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許多後現代理論家所指出的宏大敍事的崩塌,以及御宅族在消費模式上的轉變。
綜上所述,在拉馬爾看來,儘管《天空之城》和《藍寶石之謎》建立在相同的故事大綱上,但是卻通過多平面的動畫機器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
**開放合成幫助宮崎駿在《天空之城》裏構建了一個超然於世界之外的宏觀視角,啓發我們從外部去尋找擺脱現狀的替代選項;扁平合成則夥同《藍寶石之謎》那令人分心的多重參照系將人們困在世界內部,通過放大瑣碎的沉迷來表明現代技術的難以擺脱和不可逃離。**這就好像,當《天空之城》帶着我們飛到世界之外的時候,《藍寶石之謎》卻在用玩笑般的語氣反問:“你確定你真的飛出世界了嗎?”
結語
通過對《天空之城》和《藍寶石之謎》中的合成方式的比較,我們發現後者絕不僅僅是對前者的粗糙複製,它也有着自己的觀點和表達。**而且,這種表達並不完全依靠對人物和劇情的改動來實現,**它也反映在該系列對於影像的處理上。
當《天空之城》利用影像中的間隙來清晰劃分充滿深度的世界和相對扁平的角色,拉開二者的距離,讓角色在世界之外獲得一個觀看世界的位置時,《藍寶石之謎》則讓前後景都顯得相對扁平,讓角色彷彿生活在“平面國”中的圖形一樣,無法超越自身的維度去觀看世界。
動畫《平面國》(改編自埃德温·A·艾伯特同名小説)
總之,“動畫機器”的方法讓我們得以不受各種固有觀念的干擾,正本清源地去考察藴藏在動畫中的活動影像潛力。它讓我們明白,動畫作品的好壞並不取決於某一種技術是否被用到或某一種理念是否被伸張,真正關鍵的問題始終是它們的使用是否符合作品的整體意圖和作者表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