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雙子殺手》:遇見更年輕的自己,你會愛他還是殺了他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70212-2019-10-22 17:04
本文轉自:騷客文藝
作者:韓松落
音樂人周雲蓬今年開始彈電吉他了。很多人問他原因,他説:“老那麼如魚得水,老那麼庖丁解牛,其實並不好。所以,想給自己設點兒門檻兒,給自己找點兒難題”,何況“電吉他一方面看起來更有娛樂性,另一方面電吉他因為使用效果器,會讓人的思路更開闊,更容易刺激人的創作。”但事實上,他在練習過程中發現,“木吉他和電吉他差異性很大,幾乎是兩種樂器”,他於是用了很多時間,來練習電吉他。
接連看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和《雙子殺手》之後,我想,李安大概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才開始變成技術派的。

他是想給自己找點難題,想用技術來刺激創作,更重要的是,用新技術拍電影,看有沒有可能拍出一種新電影。
我也很想知道答案。

不過,看了《雙子殺手》之後,還是有點遺憾的。因為全世界只有很少的影院可以按照這部電影的技術要求進行放映,絕大多數人看到的,依然是一個較低配置的版本。所以,我們既無法感受電影中幾個經典場景的美妙,也無法判斷120幀版本和別的版本的差異,就還是,更多關注故事吧。

畢竟,《雙子殺手》還是有一個故事,還是要靠故事來驅動人們更敏鋭的感官體驗。
可是,電影看到一半的時候,我腦子裏開始跑馬,想起一些華語武俠片。這些武俠片有個共同的故事——刺殺魏忠賢。故事往往發生在明朝,皇帝昏庸,任由奸臣當道,忠臣和忠臣的後代遭到誣陷、迫害,並被追殺,經過一番江湖動員之後,仁人志士團結起來,和養好傷練好武的忠臣後代一起反殺奸臣。皇帝始終隱形,像一種又不確定又可怖的存在,由着芸芸眾生在前台打打殺殺,只在最後,當仁人志士騎馬遠去,重新隱入江湖的時候,有一點清曠和寂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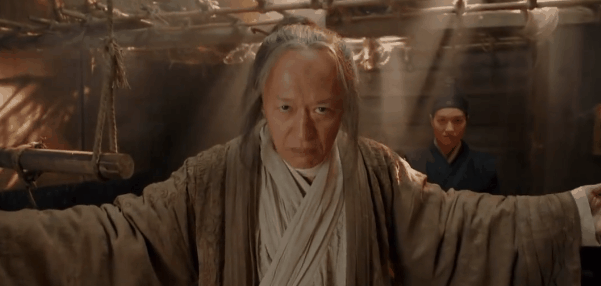
電影《繡春刀》,金世傑飾大太監魏忠賢
差不多有四十年時間,香港和台灣拍了很多刺殺魏忠賢或者其他奸臣的故事,魏忠賢已經在銀幕上死去很多次。這些故事已經有了非常成熟的模式,偶然會有一些變體,比如奸臣收養了忠臣的後代,悉心培養成殺手,帶隊去追殺忠臣一家,用血親相殘的方式加深對忠臣的懲罰,在關鍵時刻給他們以最沉重的擊打,當然,最後通常還是父子相認反殺奸臣。血緣的力量大於後天的教化。
《雙子殺手》就是這樣一個故事。只要把克里夫·歐文扮演的那個反派大BOSS換成魏忠賢,它的故事源頭就非常明顯了:年輕人如何認識自己,如何找到真相,如何找到自己的生命源流,並且在最後關頭做出選擇。

最有寓意的一場戲,就是年輕的威爾·史密斯和老年版的自己一起,在古老的墓穴裏獲得重生,並且一起墜入墓穴中的水池,像又一次經過羊水浸泡,才能讓彼此的生命基因融匯溝通。

也就是説,《雙子殺手》的第一層故事,和身份認同有關。
這種身份認同,是典型的中國特色。因為,幾千年以來,中國人始終是披着迷彩生活的,“隱真”是中國人生活裏最重要的技能,也是中國文化裏最隱蔽又最重要的深層意識。每個人必須隱藏愛,隱藏恨,隱藏自己的政治觀點,甚至道德底線,才能在殘酷的生存資源爭搶中,順利地存活下去。

所以,華語電影人非常熱衷於身份認同這個議題,中國觀眾也對這類故事心領神會,聶小倩陳永仁(《無間道》裏梁朝偉扮演的角色)的故事,在中國語境下完全成立,一旦翻拍就荒腔走板。
只有這麼一層意思是不夠的,所以《雙子殺手》裏又套了一個父子故事,這是李安熱衷講述的故事類型,孽子孽女,在父親佈下的天羅地網裏掙扎求生,尋找現實的和精神上的出路。弒父,成為父親,也重新認識父親。

不過,《雙子殺手》裏,給出了兩個父親,一個是克里夫·歐文扮演的邪惡的、無情無人性的父親,把“兒子”當做工具,甚至越來越無情,越來越工具化,他就是那個數據化的、機器化的未來的代言人。另一個父親,是威爾·史密斯扮演的,人性的、善良的、睿智的、憂患重重的父親,他曾經非常強大,現在依然強大,依然謹慎,而且不服老,不停地向“自己”發出召喚;他有許多技藝需要傳遞下去,更有許多關於世界的、人性的憂思,需要傳遞下去,他是那個人性的、有血有肉的過去的代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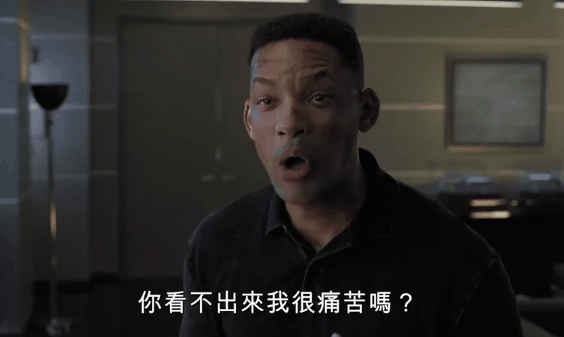
兩個父親,面對的是同一個“兒子”,這個兒子強悍、莽撞,正在有情和無情之間做出選擇,他曾經非常兇殘,對邪惡的父親非常忠誠,但邪惡父親的謊言,讓他的信念出現了裂縫,他聽從了善良父親的召喚,進入墓穴,跌入羊水,得到重生。最重要的是,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源流。

故事在春花怒放的時節結束,一切都在復甦,一切都重新絢爛。
但兩個威爾·史密斯之間,又不是尋常的父子關係,而是母本和副本的關係。從基因的角度講,他們是同一個人,是一個人和年輕二十歲的自己的相遇。這種身份,讓這兩個人之間有了一種情色感,他們兩個人打鬥、糾纏、制服的場面,都有了情色意味。各自和別人打鬥時,都乾淨利落,一槍致命,毫不含糊,甚至連敵人的臉都不用看。而他們之間的打鬥,總是有所顧忌,有所保留,會留一手,以制服為目的,而不是以擊殺為目的。在每次打鬥中,揭開面具、互相凝視,更是必經的流程。

他們的打鬥,和李慕白與玉嬌龍在竹林間的打鬥一樣,是制服、馴服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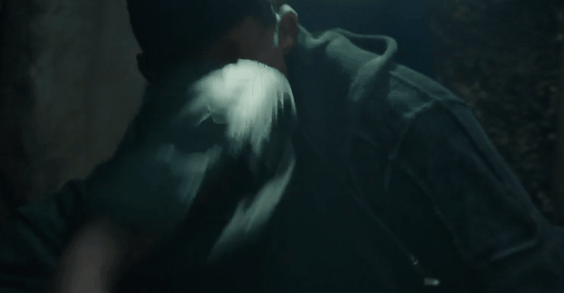
在年輕的威爾·史密斯猶豫着要不要以弒父來做出抉擇的時候,中年的威爾·史密斯替他做出了決定,承擔了罪責、罪惡感,因為做完這件事,“你的內心就不再完整了,你很難修復它”。
其實,這是一個人對年輕時的自己的愛情。就像李安在接受採訪時説的,面對新技術,他希望自己年輕二十歲。他在電影裏做到了,但在現實中,他依然是那個要清醒地面對自己的老去,並且以不斷的重新開始,來反對自己。

不過,《雙子殺手》裏,不管是身份認同,還是父子情結,兩層意思都很淺,都沒有多麼幽深,可能是為了讓出更多的心力給技術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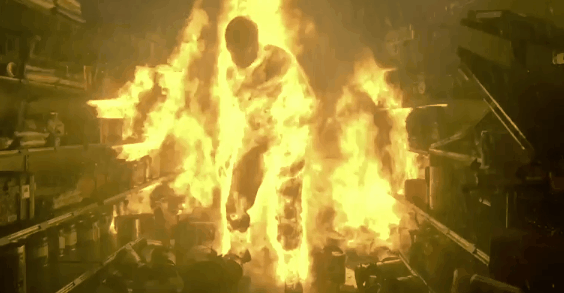
人的能量畢竟還是有限的,不可能面面俱到。想到這裏,我又一次覺得李安的存在,覺出他人性的部分,即便是缺陷,也依然是充滿人性光輝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