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民窟的百萬建築師:GSD系主任的20年實踐_風聞
全球知识雷锋-以雷锋的名义,全世界无知者联合起来!2019-10-24 00:32
作者:孫志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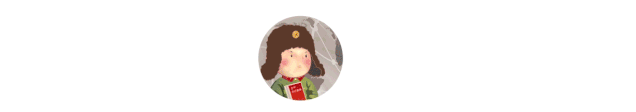
歡慶只是城市景觀的“隱喻”,當黏土塑像緩緩溶解於海灣,景觀便終結了,成為城市記憶的瞬間,這與建築相反——建築是囊括公眾記憶的靜態永恆。
孟買甚至都能從Bombay更名為Mumbai,所以這裏的空間和圖景一直在被消費、重新解讀和循環利用。
這些遊行隊列、婚喪禮儀、節日慶典、販夫走卒、引車賣漿之輩、街頭地攤和貧民窟居民全都是一日千變的街道景觀的締造者。
講座正文
Rahul Mehrotra,GSD建築與城市設計系主任
非常感謝喬治.貝爾德*的邀請,感謝理查德·索梅爾*,今天也很高興看到了GSD的Robert和其他同事,我感到無比榮幸。我要給大家分享在孟買做建築的經歷——主要體現在我撰寫的一些文獻書籍和過去20年間我們所參與的項目。
注:George Baird,多倫多大學建築景觀學院院長,曾任GSD建築系主任。Richard Sommer,多倫多大學約翰·丹尼爾斯建築風景與設計學院院長。
印度是一個充滿意趣的實踐場所,那裏的建築師正盡力解決社會、文化和經濟變革產生的新問題——空前的城市發展迫使他們重新思考職業的社會角色。這些變革正以難以想象的洶湧之勢塑造(mold)着我們的建成環境,我認為在這種進程中,職業建築師的地位在印度不可避免地被愈加緣化(marginalized)。
所以今天這場演講就是對行業內部變革的批判和反思,因為在傳統的建築實踐中,職業建築師們通常不會思考更廣義的地形環境,而是更關注處理場地本身的獨特性,或許這就是喬治所説的我們要識別(discern)出地形環境和文獻資料中的微妙差異(nuanced)並加以聯繫。我覺得如果你不這麼做就會立刻與場地文脈失去聯繫,更不用説是像印度這樣正經歷日新月異變化的環境,而你的建築實踐也會被認為是“鼠目寸光”(myopic)的。
這是孟買都市區的圖片,我們在孟買的工作方法就是將城市和區域本身作為實踐的發生器*(generator)——方法自身也在隨城市變化而不斷進化,同時通過一些建築語彙從我們這個整合多學科知識的行業的靈活定義中汲取養分,並介入到印度城市的動態(kinetic)都市景觀之中。
注:“generator”一詞見於《時代建築》2006/06期論文《在孟買做建築——城市作為實踐的發生器》(Working in Bombay——The City As Generator of Practice),指孟買作為實踐的“發生器”。
我認為研究“建築如何作為抵抗兩極分化(polarization)的手段”是極有價值的,這種兩極分化現象正發生在我們的城市和社會之中,而如果你去過印度就會發現“不平等”尤為明顯,它深刻影響着建築環境,孟買的複雜城市現象是多元的,它的城市特徵表現為某種尖鋭的二元性:貧窮與富裕共生,西方圖景與傳統符號並置,臨時材料與鋼筋混凝土同在……這種不斷加劇的複雜性不僅在孟買,在印度乃至亞洲城市都是非常典型的,所以如何才能傳神地表達出塑造城市環境的多元性(pluralism)和二元性(dualities)呢?
所以我把今天的講座分為兩部分——首先給大家分享我過去20年在孟買做建築所觀察到的現象和作出的選擇,第二部分是我選取了個人認為最棘手的六個項目來展示——因此儘量避免選到週末住宅或美麗的藝術博物館,因為設計那些建築是我們都夢寐以求的享受(indulgence),當然它們也是能給予我們養分和磨練(crucible)的建築實驗,但我想講六個最困難的項目,因為它們是最能反映設計師處理建築與社會關係的技巧的。
研究倡導,實踐模型,建築生態,弱化界限,精製傳統,本土化與全球化
ETH的Mark Anjali告訴我他曾和學生們去埃塞俄比亞(Ethiopia)考察研究臨時居住區(informal settlement),他們在寒冷的冬季乘坐公交車發現了一處臨時棚屋區,大家興奮地跳下車花了足足三天進行踏勘繪製mapping,第四天他們終於在和當地人聊天中意識到這裏根本不是臨時居住區,而是政府居住區——所有人都擁有自己的土地,所以他們定義“非正規”的標準完全囿於審美,這就很成問題——因為如果我們用審美和價值觀來形成這些非黑即白的二元論,那就很難察覺事物的本質,但審美問題絕不是唯一的問題。
研究倡導
對我們而言,研究倡導(research advocacy)也是重大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開始挑戰你們所謂的純粹的平等或二元論,例如住在所謂非正規城市的人們其實往往在正規城市工作,而住在正規城市的人們通常忍受着各種非正規的嘈雜喧囂(rackets),此時你就明白“平等”是不可思議的事,所以根本問題就是:調研分析公共環境得到的設計智慧可以給我們何種指引?設計師在本土地區如何發揮作用?建築師該如何切入差異化的世界?如何滿足它的訴求又尊重文脈?如何同時回應過去、現在和未來?
我深信所有調研項目以及它的方法都會對設計結果產生影響(bearing),所以在實踐初期我們會組織大量關於城市的文獻資料,但我回顧它們時便發現沒有一本書是能被引用的——因為這些出版物並非學術作品,更多的只是宣傳工具,有時記錄一座建築僅為了案例研究以便日後進行保護——這些都是城市空間創造的自發(self-initiated)意識,並不需要出版商(當然其中有些出版了)。
但它確實幫助我們專注發掘(excavate)城市條件,這是很嚴肅的——因為當你需要寫文章並將它們歸納成一本書時,就不得不條分縷析地挖掘內容,最終一些文獻作品也以法律的形式呈現——我們確實影響了法律,有時我們研究小組甚至參與建築保護法的編制,學習土地循環政策和城市相關課題。數年之後人們會意識到這些記錄城市瞬間的檔案的價值,但它最重要的作用是使我理解了曾百思不得其解的“意義”和“本體”(identity)的問題——我們在場地發現“意義”然後就竭盡所能地用設計去強化它,大談“本體的形成”……但其實這些都存在於建造過程之中。
本體與意義以及其它未知事物歸根結底都是被建造的物體和現象,我想這個説法一定改變了你對建成環境的既有認知,但它確實重要——因為在這種場地上“意義”並非固若金湯,它是瞬息萬變的——你會發現孟買甚至都能從“Bombay”更名為“Mumbai”,所以這裏的空間和圖景一直在被消費、重新解釋(reinterpreted)和循環利用。孟買更名以後就像印度乃至全球許多城市一樣在後工業化語境(post-industrial scenario)下出現了服務與生產區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新體系,短短十年間產生了三百萬人口的驚人增長,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長率導致了一種奇異的(bizarre)城市主義,滲透到城市景觀的方方面面——這是由外部因素產生的城市主義,而精英們主導着國家正統的現代性——這就是Ravi Sundaram*所説的“盜版者現代性”(pirate modernity)——它悄悄潛藏在城市法律的灰色地帶,有意無意地滋長着一種反文化思潮(counterculture)。
注:Ravi Sundaram,城市學者,著有《Pirate Modernity: Delhi’s Media Urbanism》。
這種現象對城市接軌全球經濟至關重要,然而它所創造的空間被極大地排斥在主流文化話語(cultural discourse)和全球化之外——這些話語體系下往往是精英主導城市生產,所以孟買不能簡單地用“貧困城市”和通俗意義上的正規與非正規模式或其它諸如此類的二元論來解讀,儘管這些語彙常用來描述發展中國家例如南美、亞洲、非洲的城市條件。但這就是我所説的“動態空間”——這些模式分解成單一實體所形成的空間,其中所有的意義都是變幻莫測且曖昧不明的,也就是我今晚想重點講的“動態城市”空間——所有建築師、保護主義者、城市設計師和規劃師都能各自為陣,求同存異地參與它的空間設計。
你能在動態城市中看到如此奇異怪誕的並置——全世界最大的住宅和最小的居住區,就住宅(dwelling)而言這些環境都是多網格分支的(intermeshed),即便在拉丁美洲的非正規城市裏空間也不會支離破碎(segregated),而孟買的這些多網格分支的破碎空間或許與民主有關,所以動態城市不能通過建築與城市設計手法感知,居住模式決定了它的形式和概念。孟買是一種有特定本土邏輯的內生的(endogenous)城市主義,並不全是網絡圖片所顯示的貧困城市,而是一種充滿暫時性的流動和居住空間,它不僅創造了更豐富的空間使用,而且揭示了空間邊界開始蔓延到了從前難以想象的地步。
而真正影響它的城市設計術語就是“彈性(elasticity指空間靈活性)”、“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指空間增長方式)”和“佔用(appropriation指空間使用策略)”,我會通過幾點觀察來向你們闡釋。
例如孟買的公共綠地空間,這個數據也包含了交通安全島的綠地面積,孟買即使與德里(Delhi)相比也是令人驚愕的,所以這種綠地密度決定了我們需要富有彈性的設計。
紐約、德里、孟買、東京、巴黎、倫敦公共綠地空間對比
與紐約曼哈頓相比,孟買的綠地空間顯得更支離破碎(disaggregated),而圖中標示的還是孟買最大的綠地,所以很多全新的空間想象可以在此展開——從這種意義上説孟買不是貧困的城市,而是城市空間最富餘的地方。
左:曼哈頓,美國;右:孟買,印度
板球(cricket)是我們根據英國板球發明的印度運動,板球場是充滿神聖性的空間,而到了結婚時節這片板球場就被用作婚禮場地,而這個功能僅持續10小時,因為次日清晨這些婚禮設備和桌椅涼棚都會消失,場地又恢復成了板球場。
講完了彈性現在來説漸進主義,這張圖解就是五種佔用(squat)城市空間的漸進階段——是60年代一位英國建築師發表在《建築評論》上的圖紙,圖中的人物在第三階段坐在桌前,而等到酷暑來臨他便支起了涼棚——所有人都贊同他的行為,他也獲得了甲方的支持,然後雨季到來後他又通過建造使自己與外部隔離(barricade)——這就是他用大家司空見慣的隨身用具(paraphernalia)度過一年的方式,也構成了城市景觀的一部分。
整個孟買都是被這些漸進的行為塑造的,當然它有自身的缺陷,因為會造成粗暴的破壞(demolition),而住宅是幾乎不留痕跡的了——例如這兩張改造前後的圖片,你們會發現它留下極其微小的破壞痕跡,但它仍是破壞——當然這就是關於住房的更復雜的問題了。
而街道會在節慶時期被這些紙模製成的建造物佔據10天——整條街道會呈現全新的意義,空間會被如此佔用,人們於此歡慶歌頌,此時它就不止是貧困的城市,而動態城市的景觀也會在其它層面發生作用。
例如建築保護——這是英國人建造的孟買市政廳(Town Hall),它是少有的幾座入口前34級台階的古典建築,而我們的傳統是英國殖民長官會站在這裏對市民進行每年一度的演講,而此後我們沿襲了這項英國傳統——印度地方長官每年也會於8月15日的印度獨立日在此演説,此時恰逢雨季中期,所以總是會降雨。因此工務局負責確保長官在34級台階內不會被雨淋濕——當然可以用一些美麗的雨傘進行遮擋,但他們想出了截然不同的方法:將整座建築包裹起來。這個舉動激怒(berserk)了城市中的保護主義者,他們給社論撰寫人瘋狂寫投訴信——這在英國傳統中被認為是最強烈的抗議形式——他們確實是義憤填膺,但這種“包裹”是可拆除的(reversible),到第二天清晨它就消失了——它非常“輕柔”地與建築進行接觸,這也是佔用和彈性的概念——殖民地的烙印在獨立日被“佔用”了。
某種意義上説這個策略很有價值,但在建築保護的語境下它顯然在不少市民的看法裏是事與願違的(counterproductive),而那些在紐約或倫敦留學的人們總是用英文研究建築遺產保護,但我認為“動態城市”的想法可以從經濟層面理解——例如城市中的創業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自發自治的過程,它表現了一種將正規與非正規事物融入共生關係中的能力。而“達巴瓦拉”*是孟買風靡一時的服務,他們會在早晨從你郊區的住宅領取你的午飯盒送到你的工作地點然後再將空飯盒送回,僅收取每月3美金的費用——人們選擇這種複雜的服務出於很多原因,有些是為了衞生,還有的是出於宗教信仰和食物禁忌或因地鐵非常擁擠不方便攜帶午餐,當然印度人往往喜歡熱氣騰騰的午飯,所以有三千多人從事這種非正規服務。
注:dabbawal又名“飯盒人”,指印度孟買從事將剛做好的午飯盒從上班族住處運往工作地點再將空飯盒帶回的行業的人。
他們利用正規的基礎設施——鐵路系統來運送午餐,從郊區取出午飯盒後他們會使用一套分程傳遞(relay)的系統——當送到市區的中央商務區時將這些午飯盒進行合計,然後進行拆解分配,他們甚至還有一套編碼系統——哈佛商學院曾針對他們做過一項案例分析,調查顯示他們配送的失誤率是百萬分之一。它真是一項動人的服務,因為這些依賴於相互配合的網絡創造出無與倫比的協同效應(synergy),完全無需精心組織的複雜架構,所以它將正規與非正規引入到了第三空間層面,模糊了二元論的概念。
讓我們看看其它形式的經濟活動——商販發明這些小袋洗髮水是由於普通勞動者不能支付相當於一個月工資的整瓶洗髮水,而將它們按每日所需量分裝到小袋中,既符合工薪階層的購物力,又創造了靚麗的城市視覺文化風景線。
這是孟買有外賣服務的麥當勞店的統計圖,這顯然完全背離了麥當勞的初衷——他們面向大眾市場就是因為快餐店無需人們遠途就餐,所以企業會理解如何制定策略、如何靈活運用“彈性”、“漸進主義”和“佔用”這些技巧,運用正規的基礎設施拓展自身邊界(margin),然而城市設計師、建築師和規劃師還未涉入我們對這種城市主義的探討。
對我而言,研究如何模糊二元論的邊界、如何創造第三空間、如何化用設計智慧並將其作為規劃設計的基礎就是迫在眉睫的議題,所以具有奇異形式的“動態城市”可以被視為典型的新興印度城市的景象——這些遊行隊列、婚喪禮儀、節日慶典、販夫走卒、引車賣漿之輩、街頭地攤(hawker)和貧民窟居民全都是一日千變的街道景觀的締造者。一座處於永恆運動狀態下的城市的實體結構(physical fabric)是充滿動態的,反之靜態的(static)城市則需依靠建築來表現自身。
動態城市:模糊二元論
如今在動態城市中,建築早已不再是人們解讀城市的單一意象,甚至都不算是城市的“景觀”(spectacle)*,相對而言城市中也不包含某個鶴立雞羣的地標了——大量的節日歡慶應運而生,成為動態城市中的景觀。它們的出現構成了遍佈印度城市日常性的景觀,成為主導潮流視覺文化的重要因素,例如偉大的象頭神(Ganesh),這個每年一度的節日會聚集三五百萬人,人們會對着約1200個巨大塑像和成千上萬更小的雕像頂禮膜拜,整整十天大家都會沉浸在穿行城市的浩大遊行隊列中。
注:spectacle一作“景觀”,見於居伊·德波《景觀社會》中“在現代生產條件無所不在的社會,生活本身展現為**景觀(spectacles)**的龐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轉化為一個表象”。
這種空間佔據當然形成了城市景觀,這是相同的街道的另一幅圖景——你會看到整個寶萊塢劇院(Bollywood Theater)都被人們建造出來以供十日歡慶期間觀影,而十天之後這些都會消失得無影無蹤——這些空間都是通過不同裝置移居(colonized)於此,而最後一天會被清除。
人們歡慶的情緒只是一種對城市景觀的“隱喻(metaphor)”,當黏土塑像緩緩溶解在海灣的水中,城市景觀便宣告終結,沒有任何靜態或永久的方式來記錄這場奇觀,此時城市的記憶只是一個暫時上演的瞬間過程,它和建築恰好相反——建築是囊括公眾記憶的靜態永恆的實體存在。
城市與它的建築有時甚至會包含不同的涵義,而在動態城市中,意義與不穩定的空間往往被使用、重新解讀和循環利用——動態城市常常循環利用或佔用靜態城市的空間並巧妙利用它達成自身目的。另一種極端環境就是建築作為城市的核心工具,我稱之為短期投機資本的城市(cities of impatient capital)——它們隨時做好用土地迎接資本的準備,急切地表達並實現價值。這張拼貼就是此類城市的典型案例,而從這些短期投機資本的城市例如上海和迪拜演化出特定的建築類型,它們有強大的權力(autocracies)使這些資本可以毫無阻力地落地——但我認為這是有問題的,因為它缺乏在地性(rooted),尤其是迪拜爆發的經濟危機將這些問題暴露無遺,而在印度這種民主體制與不平等錯綜交織的環境下,我們如何應對全球資本?如何與地域產生聯繫?如何從長遠角度提高生產?否則你就只能創造一種脆弱的(brittle)城市形式。所以我認為像孟買這樣的城市就面臨短期投機資本居高臨下地侵入(bully)城市引發的財政實力和權力問題,我們都遭遇過這些問題——它會導致對城市的另一種解讀——關於脱離(detachment)場地而非在地性。
另一個關鍵問題是我不希望將動態城市描述成僅關於以人為本的暢想,我想將這個觀點作為一種城市主義敍事的灌輸(infusion)——我們思考印度的城市只是為了解讀一些細微差別(nuance),從兩個極端之間找到平衡的中間地帶——這也是我提出兩個極端的原因,真正的問題是當動態城市作為城市主義語境的一部分時你能從中學到什麼。美國人類學家克里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寫過一本名為《農業的內卷化》*的書,其中他探討了印度尼西亞的稻農們種植多種作物使田地非常高產——這就是高產的機制(mechanism),但它的內在複雜性也使其極易受事故的影響而失靈(malfunction),這種情形同樣發生在印尼的稻農身上——當一種作物與其它不同步(out of sync)時,有時他們花費四年時間才能收穫一種普通莊稼,因為它使整個生態系統紊亂失常(out of whack)了。我認為這種情況在孟買同樣存在,我們也正經歷城市的內卷化——不斷使城市局部空間變得愈趨複雜和高產,陷入沾沾自喜而得意忘形,缺失了構建更復雜和多樣化(plural)城市模式的發展的眼光。
注:《農業內卷化——印尼的生態變化進程》(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Clifford Geertz,1969
當你審視住房問題時會發現它更切中肯綮(pertinent),會發現這些城市景觀中貽害無窮的破壞(disruption)——當然某些人會倒退回對城市的想象中,那就完全偏離了我們探討孟買的主旨。因此你會看到越來越多的社會學家、科學家、人類學家和其它專家對有限的城市空間作出許多大同小異的解讀,反而明明有能力思考更多的建築師和規劃師並沒有參與到討論中來。
這是我們在哈佛GSD研究的議題,今天不會詳細展開,我將它們羅列出來是因為我覺得創造平衡是很要緊的——當我們在70年代探討自然景觀(emergent landscape)時主要是“否定(denial)”,到了80年代我們討論“根除(eradication)”,民主時代來臨時我們講“寬容(tolerance)”,貧民窟提升改造進行得如火如荼時我們倡導“改進(improvement)”,但最終都回歸到“預期(anticipation)”——你會通過推斷來預測它在微觀尺度和城市尺度上對基礎設施的影響。
否定,根除,寬容,改進,預測
微觀尺度對建築師而言意味着什麼?這是查爾斯·柯里亞*做的位於政府住區之間的住宅項目,它被稱作集羣住宅(mass housing)——會有政府製作的箭頭標誌告訴你這是集羣住宅。查爾斯·柯里亞所做的是遞增的有機住宅(incremental organic housing),隨着收入增長人們可以在集羣周邊進行擴建,而政府不知道如何處理這片區域,只好把它稱作“藝術村(artist village)”,因為他們覺得這有些烏托邦(utopian)和放蕩不羈(bohemian)。我認為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利用基礎設施,例如交通是對住宅最好的間接補貼(indirect subsidy),所以如果這片地區有便利的交通,那麼住宅很容易實現遞增,否則就會淪為我所説的非正規城市或貧民窟。
注:Charles Correa,印度著名建築大師、規劃師和理論家,第三世界發展低收入者住宅的先驅之一。曾於MIT研究建築,其作品注重流行資源、文化和氣候條件,注重建築與城市規劃緊密結合,致力於解決第三世界國家因發展而帶來的人民生活問題。
實踐模型
這就是我們在研究倡導中探討的議題,而關於實踐模型的問題也使我們憂心忡忡,調研過程中我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實——印度有7座人口八百萬以上的大城市(megacities)和28座二線城市(Tier Ⅱ)——在座的印度朋友們應該能説出至少一半的此類城市名,還有393座僅存十萬至一百萬人口的一級城市(Class Ⅰ Cities),二十年後它們也都會達到百萬人口——所以共有約四億印度人生活在這些我們平時鮮有提及的城市,它們沒有規劃師和生產力,堪稱印度的城市“定時炸彈”,即使我們常去孟買、德里、加爾各答(Calcutta)、金奈(Chennai)、班加羅爾(Bangalore)、海得拉巴(Hyderabad)和艾哈邁達巴德(Ahmedabad)並對這些市名如數家珍,也會無比驚愕地發現印度正潛藏着城市的“定時炸彈”。
這對建築師意味着什麼?70年代的情境下,昌迪加爾(Chandigarh)是過去的政治和經濟中心,而如今新德里、艾哈邁達巴德、孟買和本地治裏(Pondicherry)就像是建築實驗的飛地,著名建築大師多西在離開恩師柯布西耶與路易斯·康後在此進行實踐,城市軸線上的所有教育、學校、政治、資本中心都與建築有關。加爾各答、海得拉巴和班加羅爾成為新興的中心城市,信息技術大爆炸產生了很多新的形式和資本中心,如今這片空間揹負着現代主義的包袱,現代性儼然成為一種風格,審美現代性在社會現代性之前進入印度,新一代充滿天賦和超凡魅力的建築師創造出影響我們所有人的景觀,而在這些全新景觀中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現象——人們專注於傳統,雖然並未揹負着現代主義的包袱,但還是不斷使古老的意象復甦(resurrected)。
這是我最近寫完的一本書,它探討了四種典型的(emblematic)出現在印度的實踐模型,而我們作為實踐建築師面臨着巨大的教學(pedagogy)問題,教學模式不再受到重視——它們完全演變成截然不同的參與、引導和建造的模式,比我們經歷過的任何全球項目都要龐大得多。
建築生態
我們有幸能在這種新興城市中做建築,接觸到新穎的實踐模型,而建築生態的問題在我們參與的建築保護項目中同樣突出。我們意識到一個事實——建築生態和工藝會反映社會現實,當你看到這些保護項目就會發覺它們不以建築為中心(building centric)——誠然我們不可避免地對那些人口高度稠密地區進行測繪,這是尼扎姆*佔有的位於海得拉巴的宮殿建築羣,所有標紅的部分都被侵佔(encroached)了,所以我們的任務就是在海得拉巴如此高密度的城市環境下保留一片穩定的公共空間。
注:Nizam,18世紀至1950年海得拉巴的君主稱號。
在這個保護項目中,我們運用石灰(lime)和真實材料對建築進行修復,通過研究有許多層石灰的花崗岩構造(granite structure)來製作模具,找到精通石灰技藝的工匠們來操作——每根柱子都需花三個月時間建造,所以這是為期九年的項目。它將我們引導向另一種時間的維度,因為你無法想象只用兩年就完工,因為每根柱子都要三個月,所以長期的合作帶來豐富的人際關係——它使我們既參與到建築保護中,又體驗到更復雜的建築生態。
這是用模具製作的嶄新的天花板,然後我們利用尼扎姆的遺產將它改造成一座低成本的博物館,雖然沒有經費安裝空調和加濕器,但它使大量來自高密度地區的普通人得以欣賞到價值連城的手工藝品。
它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引導我們與這座位於阿格拉(Agra)的聞名遐邇的歷史遺蹟發生關係——我們接受塔塔集團*的委託制定一項印度考古調研的管理計劃,這又花了六七年時間。當我來到泰姬陵(Taj)時就發現了它的單行格局(one-liner),讓我們回到探討意義與本體的問題,它極度複雜——只是我們通過制定建築保護的標準(canons)將它過度簡化了。
注:Tata,印度最大的私營製造業公司。
如果你來到泰姬陵,穿過大門就會瞥見建築主體,此時保安會將手伸入你的錢包進行安檢,然後你進行觀覽直到口乾舌燥,最後回家(笑聲),這對阿格拉的經濟極為不利,因為旅客們甚至沒有酒店留宿,而導遊只會帶着他們白天參觀五個遺蹟後回到德里。
而泰姬陵起初的設計並非如此圖所示,它的平面會一直延伸到河對岸,研究莫卧兒建築*的人們都會聯想到池塘和天堂花園(Garden of Paradise),歷史建築總是居於正中心,但其實並非如此。這是八邊形的倒影池,我們從小到大都相信國王想要建造一座黑色的泰姬陵,但不幸早逝,而他理想中的倒影池叫做“月光花園的池塘(bog of the moonlit garden)”——國王坐在平台對稱的(symmetrical)位置看到泰姬陵倒映在倒影池中陰鬱朦朧的(murky)光影——我相信關於黑色泰姬陵的詩歌也多半源於這種想象。
注:Mughal,伊朗伊斯蘭建築影響下融合印度傳統建築元素形成的簡潔明快而裝飾富麗的風格。
有趣的是調研過程中我看見這些印度教朝聖者(Hindu pilgrims)正徒步去往馬圖拉(Mathura)——一座距此不遠的朝聖中心(pilgrimage center),而儘管他們是印度教徒,當他們走進泰姬陵時卻對着一個穆斯林墳塋做出了敬禮(reverence)的手勢,所以在印度這樣的國家人們與泰姬陵的關係比我們想象中複雜得多。
它也是帶有居住功能的歷史建築——大家或許都不知道,因為每週五泰姬陵會關閉,而這片地區所有的穆斯林都會來此祈禱,所以它也被用作清真寺(mosque)的功能。而你們也知道泰姬陵不僅滿足遊客的審美需求,它也和建造者發生了許多故事,所以我們與來自Getty的專家學者們聯合發起了一個綜合項目,並與一些印度機構合作了兩三年,不僅為了研究哪些建築構件需要修復——例如剝落的(stripped off)柱基(plinth),還希望引發關於保護的思考。
我們將這兩座建築改造成遊客中心的過程中涉及到許多複雜的技術上的細節,但很遺憾政府並未使用它們——他們決定全部進行保護。我們思考並嵌入(embed)了安全系統和坡道交通,這裏便成了人們等待、休憩和舉辦展覽的極佳場所,大家都知道泰姬陵所有的石材包括鋪路石上都有製作它們的工匠的簽名,而大塊石頭上甚至有工匠的全名。工匠們的技巧薪火相傳,所以當我們對建築進行保護時可以用相同的材料替換整根柱子——工匠們從相同的採石場(quarries)獲取材料,他們的祖先正是泰姬陵的建造者,而根據保護條例這是不被允許的,但當局感受到這種傳統的傳承還是批准(ratify)了——他們認為這是合情合理的(justified)。
再次回到關於意義的問題——標準開始受到挑戰,阿格拉作為最壯麗的濱水城市發生過許多故事,曾經沿河一線有40座御花園(pleasure garden)而泰姬陵只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因為根據莫卧兒王朝的法律你不能繼承祖輩的土地,而一户家庭想要永遠持有土地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它變成墳墓,那麼國王就允許他們繼續耕作這片土地,所以才會有那麼多御花園,而泰姬陵就是國王建造的墳墓——所以他並沒有違反法律,只是做了一點調整。
最後是一張我們大家都習以為常的關於泰姬陵的真實照片,但其實它恰恰是最不真實的表現,英國的長官——勳爵的表妹創造了這座花園,而阿格拉的政體下他們的權力很大,所以他們跟地方長官提出每晚要在柱子下表演節目,長官便下令砍伐果園(orchard)騰出空間。你可以走進這片花園,它是建築與景觀的完美結合,女士們可以在此鋪開毯子與孩子進行野餐,一邊享受樂隊的演奏,如今這就是泰姬陵的真實圖景。
這是泰姬陵被用作辦公室時的歷史照片,果園雖然不再保留,但仍有繁茂的果樹,而國王在小徑上漫步時很容易嗅到新鮮蔬果的香氣,而難養活的樹木往往會栽在臨水地帶——因為它們更需要水。
這是在濃霧天氣下泰姬陵的景象,你會發現它漂浮在半空中宛如仙境一般,這就是花園完全被改造後的場景。
這些女大學生看到了歷史建築上關於天堂花園(paradise garden)的紋樣,我們使用“永恆之花(eternal bloom)”的花朵來表達“天堂”的感覺,所以花園對於營造這種氛圍是十分關鍵的。
我們為了重建花園也研究了古植物學(paleobotany)和其中的植物品種,但當地政府一個字也聽不進去,所以當我們剛提議重新恢復果園時,這個項目就已宣告破產了。
但你走到像孟買這樣的城市,它的環境在後殖民時期(post-colonial)變得愈加複雜——因為它是由兩種不同文化交織構成的,你如何構建這些敍事?如果你從倫敦和英國的文化遺存中獲取靈感,那就能在特定領域產生歷史感和懷舊之情(nostalgia),但如今後殖民情況下文化發生了根本轉變,城市更復雜了。
這匹黑馬名叫卡拉,孟買的公共空間現在有18座這樣美麗的雕塑,當孟買的市名從Bombay改成Mumbai時,右翼政治家將它們挪到孟買動物園的牆邊一字排開。1995年我們開始為這片歷史區撰寫立法草案,而最終這項法律獲得通過了,這是我們在印度制定的首次被批准的法律,它也衍生出以後的其它法規,所以當我作為一位城市設計者回到印度時,就參與到這些研究中,城市設計在美國有時就是大型建築的設計。
我們開始為這片地區創造使用功能,其中之一就是藝術季——如何用現代藝術激活社區?如何創造意義?我們做了一些小嚐試例如粉刷建築的牆壁使人們興奮,發明一些節慶活動使人們繪畫的同時喚回歷史記憶,以此募集資金用來修復公共空間,如今這些空間都用來表演節目了,而政府認為最重要的事就是衞生設施(sanitation)、住房、路牌、街道和傢俱,這些資金如今都可以從節慶活動中獲得——包括建築修復都是由當地人中的行動主義者們資助的。
我們項目的首要任務就是修復公共空間,而最後就要對建築進行設計——建築師的任務無比複雜,因為要創造意義,而且它存在固有的風險,所以你有額外的責任要保證建築完好無損,因為它就像打開潘多拉魔盒。因此當你進行重新使用和裝修時就將自己置於更大的壓力之下,因為偶然事件(contingencies)會接二連三地發生,但你在改變意義,這種意義的改變會成為推動建築保護進程的現代引擎。
我們找到一箇舊倉庫並在其中添加了交通空間改造成美術館,這是舊的印度撒拉遜(Indo-Saracenic)建築的平面圖,我們開放了一塊五萬平方英尺的藝術展示空間——易於改造的鋼結構為片區增加了新的意義,從歷史區脱穎而出——最近我們還加建了一座遊客中心。
後殖民時期的環境為建築帶來了新可能性,我們選用不鏽鋼板是經歷了一番思想鬥爭的,因為大家都認為甲級建築應該用石材,而這種美妙的反射給歷史區增添了不少現代感。
弱化界限
接下來的問題是弱化界限,我相信建築是創造和強化不平等的重要工具——它在社會各成分間創造了牢不可破的門檻,你如何通過建築去改變它?孟買周邊的農莊和週末住宅是非常流行的,而這種內向庭院(introverted courtyard)的建築類型是從帕拉弟奧別墅(Palladian villa)生髮的靈感,我記得坐船經過港口時遇到了這座頗有代表性的住宅的承包商,我問他:“房子的設計者是誰”,他説:“沒有,這是我自己設計的”,而如今我的甲方給了我一大疊美國白宮的照片然後説:“照着它做(replicate)”,於是我就遂了他的心願。
這有點賣弄誇耀(ostentation)的意思——其實就是市區的富人們在郊區施展自己的幻想(fantasy),但這種農村環境充滿貧困,設計過程中也會產生尖鋭的兩極分化——這就是情形不斷惡化(compound)的原因,你能看到帶刺的鐵絲網圍欄(barbed wire)和安全警報器。大量年輕建築師在實踐初期都在做這類項目,我們對合作的甲方説:“您看您一年使用這座住宅的時間都不超過20天,所以為什麼不對場地作出一定的回應呢?”
終於住宅對村莊擺出了自己的姿態(gesture)——村民們都能共用這裏的水源,看門人和他的家人在附近閒逛,場地獲得了重新開發(recolonized),這就是我所説的“弱化界限”,因為它使建築更具滲透性(permeable)——不僅是對使用者,而且預想到了社會中業已存在的顯著的(pronounced)不平等和兩極分化。這並不是讓建築妥協,而是改變姿態——屋頂完全由鍍鋅(galvanized)金屬而非不鏽鋼製成,它的排水最終都會聚集在巨大的排水井(gutter)中,而光線也以極富趣味的方式被調節(modulated)——因為甲方是一位對光線極其敏感的年輕紀錄片導演,所以我們想到了這個方案。
另一個類似的項目我們還是通過創造一系列的基座——它會吸引勞作的農民和村民來到這塊土地,佔據這座房子,滲透這片空間,廚房就在住宅後方,所以人們圍坐於此——大片茶園正是住宅的一部分,我們使它滲透進居住空間而非創造強烈的分隔,但這更無需犧牲住户的私密性,想要重建鄉村的人都會贊同這樣做。
原本業主想要砍伐兩英畝的茶田來建造假山和花園,但我們成功勸説了他——他們同意“輕柔”地處理場地環境,所以我們小心翼翼地在大屋頂下設計了三間房——屋脊使用花崗岩,而公共空間運用當地建造工藝,精心打磨的木材用以框景,下沉的座椅保證了私密性,當人們工作或在茶園勞作時就能與當地居民發生交流。
在許多類似項目中我們都有意識地顛覆(subvert)本體,例如這座本該是別墅(villa)的建築,當地人卻稱它為茶廠,而另一些人稱它學校——因為看起來像有大屋頂的校園建築,因此對我而言顛覆建築本體就是一種消解(dissipating)兩極分化的手法。
精製傳統
傳統和工藝是我們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還是要在超越我們所迷戀的木材石材的基礎上進行延伸。而氣候是與生俱來的條件,我們總會忘記雨季的威脅直到它來到孟買,但它給了我們回應氣候條件的契機,我們創造了與氣候有關的建築。
接下來再談天氣,遮風避雨是短期投機資本的建築最基本的需求,這就涉及到材料的選用了。我們在建築保護項目中觀察了很多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