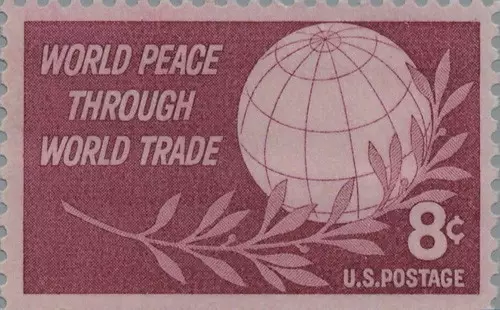一戰的爆發,首要原因是英德兩國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嗎?_風聞
瘟疫公司搬砖部-最近在看《宋案重审》2019-10-28 21:30
作者:梅然
一
一戰發生時的英國外交大臣叫愛德華·格雷,他從1905年起就擔任此職,但也許是英國曆史上最具爭議的外交大臣,很多英國人認為,是他未及時警告德國不要動武導致一戰的發生和英國的捲入,從而令數百萬英國子弟血染沙場。格雷有一個在今天看來很不適合擔任外交首長的個性:他很不喜歡出國,在任期間僅有一次正式出國訪問,還是陪同國王出訪。但在1914夏天,他打算前往德國治療眼疾。這雖然只是私人出訪,但他在德國必會接觸德方政要,英德關係和歐洲和平也可能因此而得到促進。可是,就在他動身前,薩拉熱窩事件發生,一戰在一個月後接踵而至,英國和德國旋即成為戰場上的死敵。
但無論格雷是否去了德國,都難言英德開戰本就是無法擺脱的歷史宿命。英德為何兵戎相見?一個常見解釋是:當時英國是世界上的頭號老牌強國,德國則是一個崛起中的新興強國,德國人隨着自身國力的上升要求獲得與之相配的利益和影響,相對實力下降的英國人則要力求保持自己的既有地位,於是雙方間的矛盾不可調和並推動戰爭來臨。在國際關係學界,英德戰爭或一戰的發生常被説成“修昔底德陷阱”即新老強國之間難以避免的對抗的再現: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就將這場戰爭的發生首先歸因於雅典權力的增長以及斯巴達對此的恐懼。相應地,今天的一個重要話題是,中美是否可能落入或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而當年的英德關係也常常成為當今中美關係的參照物。

二
在一戰前的英國和德國之間,隨實力地位的變化而凸顯的矛盾確實存在。但是,如果多考察一下當時英德關係的細節,應該説雙方在一戰前夕遠未勢同水火,也有不少因素趨於限制風險的失控。比如,兩國可以説是同文同種,英國人因其祖先主要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因而也多是日爾曼人的後代,有不少英國人將德國人稱為“我們的日爾曼兄弟”,而且兩國都是新教國家。如果這聽起來還比較虛,兩國宮廷和貴族之間的親緣關係則要實在得多。隨着德意志的漢諾威家族在1714年入主英國,英國王室其實就是德國裔,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阿爾伯特也本是德意志貴族,其九個兒女也大多以德意志的王子和公主為婚嫁對象,德皇威廉二世的母親就是維多利亞女王的大女兒,而威廉二世對外祖母維多利亞女王也頗有感情,他從小就多次去外婆家,也是女王臨終時守在榻前的唯一“外賓”。
可以理解,到了20世紀初,在民族-國家觀念和大眾政治已呈強勢的背景下,英德之間的政治互動已愈發不受宮廷之間的“私情”左右。但另一方面,英德在一戰前已經互為歐洲世界中的最大貿易伙伴,在金融和投資領域也有着十分深厚的紐帶。用常説的一句話,兩國間業已形成高度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經濟相互依賴。我們通常會認為,經貿關係的深厚有利於維持國家間和平,因為戰火會燒掉太多的來自和平經濟交往的紅利。正是由於這個首要的道理,無論在當時的英國還是德國,尤其在經濟界中,都可找到很多主張維持雙邊和平的言論。若説兩國的資本家由於對利潤的貪慾而想對對方動武或發動世界大戰,這是很牽強的。比如,德國的鋼鐵大王斯廷尼斯在一戰來臨前夕正在考慮擴大對英投資,戰爭的發生令他猝不及防;德國的航運大王巴林和英國金融家卡塞爾則熱心地在兩國間奔走斡旋,以求促成英德諒解。
軍火商是有可能從戰爭中發財,但也無證據證明他們控制了兩國政府,他們在兩國經濟界中也絕非一言九鼎的大拿;何況對他們來説,國家間保持適度的政治緊張並進行和平的軍備競賽就已能讓自己大賺一把,大打出手反而可能帶來難以控制的重大風險;而且,當時的大軍火公司(比如大名鼎鼎的德國克虜伯)多是軍品和民品兼營。誇張一點講,説軍火商就是戰爭販子,等於説病菌都是棺材店老闆傳播的。
不僅是資本家階層總體上不想打仗尤其是打大仗,工人階級也是如此。工人們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與僱主們一體的。他們也擔心,如果戰爭打起來,進出口中斷,產品賣不出去,自己的生計也是大問題。在德國,體現工人階級聲音的最大政黨是社會民主黨,而它也是德國最重要的反戰力量。在英國,自由黨主持的政府正推行英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福利計劃,這首先也是對工人階級訴求的回應。自由黨也正是由於提出了多福利承諾的競選綱領才在1905年議會大選中獲勝,但如果大戰來臨,政府也就既無時間也無金錢去關注福利問題了。
維多利亞女王、阿爾伯特親王及其子女(右側第二人是女王的長女,同時也是德皇威廉二世的母親)

三
當然,當時英德兩國在意識形態上是有明顯差異甚至對立的。英國早已是一個議會民主國家,德國還保留着君主專制色彩,或者説是威權主義國家。但不能説,當時的英國人普遍對德國有着政治制度上的優越感,或者説對於“非民主”的德國多有偏見甚至敵視,進而要去遏制或搞垮德國。在一戰前的世界上,真不能説議會民主制已被廣泛視為最佳,即便是在傳統的議會民主制國家中。統一後的德國不僅在軍事上是歐洲各國中最強大的,還擁有最有效率和廉潔的公務員隊伍,並在世界上率先推出了大規模的社會福利制度,在教育和科技上也迅速發展為翹楚,這些都讓當時的很多英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羨慕,進而令其稱讚德國式的威權並懷疑本國政體的優越性。1878年5月,正在德國遊歷的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温寫信告訴朋友:“這塊土地是怎樣的一個樂園!怎樣的乾淨穿着,怎樣的美好面孔,怎樣的安詳滿足,怎樣的繁榮,怎樣的的真正自由,怎樣的優越政府!”
而且,即便是英國政府自己,其對外指導思想也沒有那麼強的意識形態色彩,而更多體現了實用主義,尤其強調為本國工商業營造穩定的國際環境。19世紀中前期以推行“炮艦外交”聞名(並在鴉片戰爭中用大炮轟開中國大門)的英國著名外交家和政治家帕麥斯頓曾説:其他大國是自由還是專制無關緊要,因為英國的政治利益是由將國內福利最大化的商業利益決定的。今天的歐美政客應是沒幾個人敢這樣説。
四
一戰前的英國常被説成“小店主的國度”,拿破崙和威廉二世都這樣講過。這個比喻至少在兩點上是對的:一是,英國的對外政策很看重為工商業利益服務;二是,英國的對外政策頗有務實之風,很明白國家間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如同做生意。在一戰前,英國人也廣泛認為,既然自己的相對實力已不如前,讓包括德國、美國甚至日本在內的新興強國能多分些蛋糕,從而願意維持現狀和合作,這總比開啓大戰要務實得多。
還有很多英國人認為,一個統一、強大和繁榮的德國在國際政治上對英國也不無益處。英國對歐陸的一個傳統政治原則是謀求均勢,因為如果某個國家控制了歐陸,它就既更有能力進攻英國,也更有能力在海外與英國競爭。在很長時間中,法國是英國的主要擔憂對象,兩國從17世紀末到拿破崙時代斷斷續續打了一百多年仗。從19世紀中期起,英國主要擔心的是俄國,俄國對英國的威脅是雙重的:一方面,俄國如果不斷向中東歐擴張,也有染指歐洲霸權之嫌;另一方面,俄國對近東、中亞和遠東的擴張直接威脅到英國在這些地區的利益。而且,英國外交中的意識形態色彩雖然不強,但在面對俄國時還是暴露最多的,英國人普遍將俄國視作最專制國家,同時也很反感俄國對國內被壓迫民族比如波蘭人的嚴酷統治。這樣,俄國其實是最被英國人排斥的一個大國,甚至被認為不配屬於歐洲文明圈。
這樣,對英國人來説,一個統一、強大和繁榮的德國既可向西牽制法國,也可向東牽制俄國。因此,英國人對德意志的統一曾經是廣泛地樂見其成。到了20世紀初,英國與法國和俄國的關係都有緩和,標誌就是分別訂立於1904年和1907年的英法協約和英俄協約,它們解決或緩和了兩國間的一些重要爭端。但是,英國人對法俄的擔心仍一直存在,尤其對俄國。俄國與英國訂立協約首先是由於日俄戰爭的失敗,是為了獲得喘息之機,因此英國人一直不安地擔心着俄國是否會重新變得咄咄逼人,而該擔心在一戰前夕正呈上升之勢。
1900年的一幅描繪英俄對抗的漫畫

但話説回來,英國人雖然不反對德國“適度”擴張其影響,甚至不反對德國主導中東歐,但反對德國採取危險的武力方式。因此,當德國大規模擴充海軍時,英國人明顯感到了來自德國的入侵危險,一時還冒出了多篇以德軍在英國登陸為題材的政治幻想小説,英德關係也有了明顯的緊張感。不過,英德海軍競賽在一戰前其實已經緩和,兩國關係在其他領域也不乏進展,包括在波斯灣地區大致劃分了利益範圍(其中還約定將聯合開發該地的石油)。這樣,在一戰前夕,雙方政要對兩國關係反而表達出前所未見的樂觀。1914年1月,時任英國財政大臣的勞合·喬治告訴記者:英德關係已改善到可能不再需要擴充英國海軍的地步。
五
但是,德國並未放棄用武力消除來自法俄的挑戰。如果德國與俄國開戰,英國人至少暫時可以坐視不管,他們既不喜歡俄國人,也不關心東歐;但如果德國進攻法國,他們就難以不顧了,因為德國在控制西歐後就更有能力威脅英國。
然而,卻有一種壓力越來越強地推動德國走向與法俄的戰爭:面對這兩個強大並結盟的鄰居,尤其是本來就具有人力和資源優勢而且在快速工業化的俄國,德國的主要決策者覺得力量對比將愈發對德國不利,覺得時間將愈發不站在德國一邊;他們於是有意先下手為強,在法俄變得過強之前就擊敗或削弱它。但他們又認為,如果要避免陷入與法俄的拖沓的兩線作戰,必須先迅速擊潰較弱的法國。而且,英德關係近來的改善多少增加了他們的如下幻想:在德國動武時,英國至少可能會暫時地保持中立。
英王喬治五世在1913年5月訪德,威廉二世(左)與其騎馬並行。

在薩拉熱窩事件發生後,德國最終邁向了戰爭之路。當德國大軍經由比利時向法國突進時,英國人雖然多少也沉浸在英德關係近年來令人愉悦的氛圍中,但還是坐不住了,他們拒絕如德國人希望的那樣保持中立,接受不了聽任德國佔領海峽對岸的危險。於是,英德轉眼間從把酒言歡變成了摔杯廝打。
六
綜上所述,英德開戰雖與英德矛盾有關,但與其説首先源自於它,不如説首先源自德國與法俄尤其俄國的矛盾。換言之,一戰的發生的首要原因很難説是由於英德兩國在“修昔底德陷阱”中難以自拔,而德俄矛盾也更像是兩個崛起中大國之間的矛盾(鑑於俄國國力在工業化背景下的提升)。問題是,雖然俄國也是英國人不喜歡而且不放心的,但德國人首先進攻的是西歐,這等於他們打出的第一棍也是落在英國人身上,於是後者被拖入了戰爭。諷刺的是,俄國既是德國也是英國的擔憂對象,但德國人重在削弱俄國的作戰計劃卻讓英德扭打在一起。
很多英國人批評格雷,是認為他應提前並有力地告訴德國人:英國不會在你們進軍西歐時袖手旁觀。但不少史料表明,即便格雷這樣做,大概也不足以對德國當政者尤其軍方產生足夠的威懾。格雷還擔心,對德的嚴厲警告可能既加大法國在防務上對英國的依賴感,也讓法俄在德國面前更有恃無恐,甚至會推動德國鋌而走險:德國人可能覺得,既然英法俄反德聯合的壓力在加大,自己更應先下手為強。當代學術名家尼爾·弗格森在其大作《戰爭的悲憫》(the Pity of War)中甚至斷言,英國如果不捲入大戰,對英國和世界反而可能更好,德國贏得歐陸戰爭的勝利可能更有利於歐洲的穩定和繁榮。
一張宣揚貿易促進和平的美國郵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