磯崎新王者歸來_風聞
全球知识雷锋-以雷锋的名义,全世界无知者联合起来!2019-11-01 00:19
本文為中央美術學院建築學院授權全球知識雷鋒特別報道。
PPT圖片版權歸磯崎新事務所所有,禁止擅自轉載。
特別感謝胡倩女士、辛美沙女士提供的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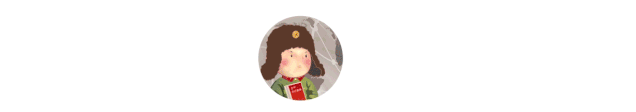
“日本還有磯崎新這樣的設計師嗎?”
“沒有”
“我覺得日本建築肯定是完了”
“我覺得磯崎新也基本認同”
本文整理自於2019年10月29號下午2:30在磯崎新設計的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舉辦的講座及研討會。張昕萌記錄翻譯講座,婷玉專訪,徐紫儀記錄研討會,騰雲攝影(下方標註️©的照片由央美提供)。
文章全長29112字,閲讀完需要20分鐘
第一環節
磯崎新主題講座
講座主題:磯崎新之謎 “息”+“島”篇
時間:2019年10月29日星期二下午2:30 – 4:00pm
地點: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報告廳
主持:朱錇
朱錇老師開場
尊敬的各位來賓:
大家下午好! 歡迎大家來到中央美院建築學院學術現場。今天是我們“央美建築系列講座”(CAFAa Lecture Series)的第四場,主講人是我非常敬重的世界知名建築家,也是我們央美的老朋友磯崎新先生。
磯崎新先生出生於日本大分,1963年成立磯崎新工作室,代表作包括羣馬縣立近代美術館、洛杉磯當代美術館、迪斯尼總部辦公大樓、西班牙巴塞羅那體育館、都靈冰球館、深圳文化中心、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現代美術館、卡塔爾國立會議中心、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等等諸多偉大作品。磯崎新的建築生涯獲重要獎項無數,包括日本建築學會年鑑獎、英國RIBA金獎、美國藝術學院學院紀念獎、日本文化設計獎、威尼斯建築雙年展金獅子獎、西班牙公民勞動勳章大十字獎、日本藝術院會員、2019普利茲克獎等。
此外磯崎新先生也擔任了眾多建築競賽評委,比如威尼斯雙年展國際建築展日本館評審、 建築思想的國際會議策劃、「仙台媒體中心」、「橫濱港國際郵輪碼頭」、「北京CCTV新大樓」、中國國家美術館等國際競賽的評審。
相信很多在座的來賓都已經熟悉“央美建築系列講座”的特點,即一個是主題講座,緊接着是一個與主講人緊密關聯的專題研討會。我們以這樣的形式力求聆聽到主講人最深刻的思想,同時也讓許多重量級嘉賓圍繞主講人特定的專題呈現最精彩的辯論。我們今天的活動也是這樣的結構:
首先是磯崎新帶來的主題講座,題為《磯崎新之謎/“息”+“島”篇》。這個講座是和磯崎新今年9月的大分展同名,應磯崎新之邀,我有幸參加了此次展覽的開幕式,傾聽了他對展覽深刻的闡述,令人深受啓發、回味無窮。
下面我們用掌聲歡迎磯崎新先生為我們帶來他精彩的演講——
©中央美術學院建築學院
磯崎新主題講座
今天我帶來的演講主題,可以從“間ma”的概念的產生簡單説起。比較漢字、日語和英語就能發現,不同的語言文化對時間和空間的關係有着的不同理解,它們的互動孕育出了“間”這一概念。我想先從這個話題切入,再展開接下來具體的討論。我是如何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的呢?一開始,我們都是從歐洲文明、尤其是英語中學習關於時間、空間的科學或哲學的定義。而日本作為深受漢字圈影響的國家,試圖用日語去理解這些概念的時候,自然引入了翻譯這一行為。
用英文來説,時間本來的意思是chronos,而空間則對應着void。這些概念通過印度、中國大陸傳入日本,以文字的形式被我們認知。然而實際到了日語中,我們只用了“間”這同一個漢字來表述時間與空間兩個概念——“間”讀作“ma”的時候往往對應時間,讀作“kan”的時候時常對應空間。翻譯的過程使得時間與空間的概念在漢字文化圈中融合為同一個詞,這正體現了日本一直以來從歐洲與亞洲兩種文明的交融關係中去學習的思維模式。
除此之外,我想舉出另一個我們常常使用的與時間相關的詞:時代精神——在德語中是Zeitgeist,在日語裏則被翻譯為時の霊(時間之靈);相似地,與空間相關的詞是土地の霊(土地之靈),相當於拉丁語中的Genius Loci。像這樣,從漢字出發的思考方式,和英語、德語、拉丁語等各種各樣歐洲文明語境下的知識概念,分別從兩個側面塑造了日本人的思維,我稱之為雙重的思考(ダブル思考)。正因如此,一些很難向歐洲人表達清楚的概念反而能在日本和中國被充分理解,“間”正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我還想就建築多談一點時間與空間的關係。Architecture被翻譯為建築,那建築是什麼呢?在古代中國被稱為“營造”,在日本則被稱為“規矩”“墨縄”,當然這也是從中國傳過來的説法。像武術、茶道一樣,這當中的技藝被精煉提純至一種“道”,其理論化的同時Architecture就誕生了。今天,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建築都常常被視作單純的構築物(building),但它其實既是社會系統的構築物,亦是建造體系的構築物,這種層次上的理解才更加接近architecture的真實含義。現在我們一般使用的“建築”的含義和歐洲所廣泛使用的“architecture”的含義之間仍然存在着細微的差別,我想這差異中恰恰藴藏着我們思維模式的獨特之處,並且我一直相信,當我們關注到這些差異的時候,不同於往常的新理論就會誕生。
説起來,“建築師”或是“建築”這樣的用語在過去其實對應的是一批藝術家,例如弗蘭克·勞埃德·賴特這樣的建築家。與之相對的一種描述是建築師也是工程師,如諾曼·福斯特——即使成為了建築家,也積極地從工程師的角度去思考設計。此外,如果多去關注英文的報刊新聞就會發現,最近常用的一個説法是建築師也是策略家——他的職責不僅僅是像一般人所以為的那樣去設計房屋,而涉及到策略的提出,例如提出一個全新的規劃方案。這張照片是暗殺本拉登的時候白宮內部的情形,他們在一邊對着幻燈片給出指示,一邊不斷核對暗殺行動的各個環節——我想這也是廣義的建築師的任務之一。
從理論發展的角度再來回顧一遍我剛剛所講的建築師角色的變遷,就會發現我們關於建築的理論如何被語言文字所左右。比方説差不多130年前的奧托瓦格納筆下的《近代建築》(Moderne Architektur, 1895),關注建築背後理性與合理性等要素所扮演的角色;而到了後來哈佛大學出版的《空間·時間·建築》(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1941)、這本對我們來説相當於建築啓蒙的教科書,它把建築和時間空間並置在一起進行考慮,教我們把所感受到的時間和從中所理解的建築聯繫起來。最後是我偶然得到的這本叫《建築藝術論》的書,它由朝鮮第二任主席金正日於90年代所著,內容既包含了一直以來社會主義建築的構造方法等議論,也在篇末具體涉及到了整個都市的規劃概念與政策,這從某種意義上説正是我剛剛所談到的作為策略家的建築師。儘管這種説法有些過時,但仔細想來,在世界上任何一個有着與我們完全不同的建築理解的地方,我們也總是能找到一些彼此思維上的共通之處。
如果硬要説建築是什麼,我認為它對我們每個人來説意味着各自不同的設計建造體系、不同的社會體系,不過其中有一點是共通的:那就是城市設計(urban design)背後的整體性思維。
具體來説,我們往往先有都市全體的規劃平面(masterplan),佈置好整體的基礎設施,隨後界定出特定的功能區域(zoning),建設環狀的道路與鐵路,等等。通常在這些工作都完成之後,才有建築師的登場的機會,而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又從前面環環相扣的整體佈局中脱離出來,反過來侷限了他們看待問題的視野。唯有同時關注到建築和城市兩個方面,建築師才能把各個層面上建築的意義貫穿起來——我稱這樣的建築為城市建築的合體裝置。我自己是這樣理解建築的。
今天演講的後半部分我將圍繞建築運動的發展展開。我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建築實踐,那個時候都市的建設也剛剛起步。接着進入60年代,我因為感興趣而從事了一些與媒體相關的工作。到了70年代,我開始通過對包括文字在內的語言的構成的研究來思考我們的文化。在50年代到70年代期間,我所接觸的一系列跨行業、跨學科的工作所帶來的經驗,都融會貫通到了我對城市設計(urban design)的思考當中。
比如説這本柯布西耶的著述《PROPOS D’URBANISME》,它是我學生時代擁有的第一本關於城市設計的書籍。在法語版出版的下一年,它被翻譯成了英文版,標題譯成了《Concerning Town Planning》。就如“architecture”被翻譯成“建築”時產生的語義變化一樣,urbanism和city planning這兩種表述即使是在相鄰的國家其意思也有着很大的差別。無獨有偶,與城市相關的新學科在美國創立時也延續同樣概念“混亂”的局面:哈佛大學設計研究院下的Urban Design學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城市研究學院下則對應着Civic Design,而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那裏,它又被稱為Environmental Design。這些學科都在50年代設立,對今天的我們來説似乎已經是半世紀以前的事了,但正是這些當初確立下來的具有微妙差異的概念被傳承了下來,各自發展出了其特有的思想。
今天我所講的內容主要是介紹從50年代到70年代的建築運動是如何進行的,而對於中國來説,直到80年代,各個圖書館之間的信息交流都處於相當閉塞的狀態,當時國外的建築運動的發展其實很少滲透到中國國內。中國倒也按照自己的節奏,在全國層面上產生了一些獨自的發展動向。而到了與世界接通聯繫的80年代,那些從50年代我還是學生的時候就接觸到的信息開始湧入中國;這些信息的湧入往往是零散的、隨機的,並不依照它們本來的登場順序。
簡而言之,urban design這一特定的用語每傳播到一處就產生一個變種,在日本的土壤上也孵化出了“都市環境”這樣的專有名詞。80年代前城市設計的概念以各種各樣形式的理論展開,我在這裏把它的發展分A、B、C三個階段。A階段是過去town design的時期;B階段是功能主義的時期;C階段則以TEAM 10為肇始、對應着現代主義後期,建築師們的思考方式傾向於從結構性的角度切入;隨後迎來的60年代初手法主義的抬頭,這使我開始關注逐漸擴大的媒體的影響。在每個階段裏,信息的承載方式都隨着其中的那一代人發生着改變。
接着剛才提到的不斷髮生改變的中國現代都市往下説,我們所設想的hyper village/超·都市的圖景不正是今天的中國不斷締造的現實嗎?要説大都會(metropolis)是屬於最近兩個世紀的風景的話,那麼都市(city)則是在18、19世紀就已經確立下來的概念。下面我就以不同的世紀劃分為依據,稍微展開來追溯都市的變遷過程中城市設計思路的演變。
針對各個階段的基本介紹,大部分關於城市史的書籍都講得相當詳盡了。我想專門一提的是在某次思考日本城市空間的時候偶然想到的一點——在演變至今天的城市肌理中,我們其實能夠挖掘出取之不盡的空間素材,在其基礎上演變就能進一步創造豐富的表現方式,如下面這張幻燈片中右上圖所示。擁有的特殊性的傳統日本城市空間,和用城市理論、建築理論、空間理論等文字的方式構建起來的現代都市,在人們的理解上有怎樣的關聯和區別?不同的時代的城市理論引導着我們去了解當時都市的真實面貌以及人們對應的思考方式。
50年代的CIAM從某種意義上説領導了一場對我們那些年形成的常識的重構,同時在更大的尺度上為今天城市所處理的問題對象、設計手法以及概念提供了思考的範式。
從CIAM中分離出來的TEAM 10,從世代來講的話在日本就是丹下健三,在歐洲的話則是以喬治·坎迪利斯(Georges Candilis)、彼得·史密森(Peter Smithson)、阿爾多·凡·艾克(Aldo Van Eyck)為代表的一羣人,他們的思想的核心在於把都市作為結構來整體考慮。
從一個具體的實例來講,1957年舉辦了一場題為柏林首都(Hauptstadt)規劃方案的國際競標,包括柯布西耶在內,幾個當時著名的建築師都參與了評選,尤其對於柯布西耶來説這是他晚年做的最後一個方案(儘管最終落選)。
儘管Hauptstadt這一名稱是基於希特勒的對二戰勝利後柏林作為世界首都的設想(Welthauptstadt Germania,“World Capital”),戰敗後的德國力圖用不同的策略來處理同一個場地。
最終脱穎而出並且建成的彼得·史密森的提案中,我們可以看到貫穿東西的交通幹線與行人的道路相分離;雖然今天這已經是隨處可見的基本規劃常識了,但今天的常識的形成卻集中在這過去的短短10年間。這也是歷史上第一次有方案提出用電動扶梯來聯繫空中行人的走廊和地面的街道。
當時還是學生的我,受到了這個方案很大的影響和啓發,也立即在隨後跟隨丹下健三先生開展的東京灣項目中試圖去應用這些手法和策略。
我們希望創造與東京舊城相對的一個新的東京城,這在中國古代其實是很常見的一種策略——放棄舊都城而重建新城。在海上建設城市的想法,源於丹下先生1959年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時所開展的海上A形巨構建築的研究。
在東京灣項目後,我將同樣的想法應用到了一個名為Skopye City的地震災後重建的競賽項目中,這也是我第一次作為東洋的/日本的建築師在國際競賽的都市景觀部門取得成績。從方案的來説,實際做了半年左右,通過這樣的形式,一定程度上初步呈現了我所設想的建築和城市作為合體裝置的想法,儘管未能實現,但也承接了我之後的思考。
幾年後,懷着為未來理想城市提供一種值得參考的模式的希望,我參加了大阪世博的規劃設計。圖中黑色的向四面延伸的區域,表示着我所設想的一個獨特的整體結構,它既能作為道路聯繫園區各個部分,又能自身作為建築被使用。這是最處的基本概念,而在實際推進方案的過程中,儘管不斷被修改,我也儘可能在概念上去堅持。右下角的圖是最終實施的方案。
1970年的世界在我看來,要説文化和技術最繁榮的地方,不是美國、歐洲,也不是日本,而是伊朗。當時的伊朗王后法拉赫·巴列維曾是學建築的學生,成為王后後她希望能親自引入新的文化和理論來建設國家。大概是在1972年左右,她召集了幾位著名的建築師,這張照片中她身後站的正是路易斯康。
我們並非作為CIAM集結,而是各自為工作恰好碰頭在了一起,在這一程中路易斯康的設計思維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我無比傾佩。他的方案一開始只呈現為一些簡單的分析圖和草圖,但在他不斷的推敲中,他想表達的建築圖景就漸漸浮出了水面。
其中有一個項目,王后邀請了丹下先生和路易斯康分別提出不同的方案。從具體的方案來看,路易斯康將中心部分全部空了出來,與之相對,丹下先生像東京灣時的提案一樣設置了巨大的軸線,將各個部分都聯繫起來。路易斯康在設計這個方案時所繪製的一張草圖成為了他去世之前留下的最後一張圖紙。一年後,我將丹下先生的方案和他的方案綜合起來提出了一個折衷案,稍微表達了一些我的追憶與敬意吧。
在接下來的部分裏我想針對象徵性(symbolic)的城市設計思路展開一些討論。
我一直在探索藉助電腦來進行城市設計的過程背後所藴藏的思考方式,在這個過程中提出了“看不見的城市(Invisible City)”的概念。
具體來説,前期階段先大致地考慮周邊環境的要求與限制條件,提供與之相匹配的容器(shelter);緊接着,將都市所需要的各種各樣的功能全部嵌入、佈置到其中。最終生成的方案尺度接近1.5km,這個大小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説當然如同家常便飯,但在當時聽上去卻與天方夜譚無異,根本不可能實現。當初我為這個方案設想的地段還是一片海灣,而在今天那裏已經成為了東京迪士尼樂園所在之處。只能説,作為建築師的我還是沒有能夠博得足夠的信任,而如此大規模的項目對於我的建築生涯來説,哪怕只實現了其中一小部分,也成為了非常重要的一幕。無論如何,城市尺度項目的設計經驗使我得以更加嫺熟地在大型的活動為背景的項目中去應用建築城市合體裝置的想法。
另一個我探索過的方面是機器人式的建築。儘管拿不準自己是否真正把握到了機器人的精髓,總之我以“機器人”這個概念為線索,最終找到了“表演(performance)”這個關鍵詞。起初我設想的機器人建築的高度是30m左右,最終實現的只有15m,它伸伸手倒是可以到20m附近。這個項目從時間跨度來看也是我設計過程中的小小的變奏之一。最後這個裝置偶然充當了夜間的照明,並且也如預期的那樣為一系列的表演提供了依託。
結合幾個已經建成的城市設計項目來看,每當我們具體地思考城市建築合體裝置所呈現的恰當的樣貌時,總是繞不開近代烏托邦的思想,能否產生獨特的想法取決於我們怎樣去理解並繼承從早期的現代主義建築家們到後來路易斯康、丹下健三先生留下來思想。這些烏托邦式的想像雖然不能立刻實現,但是它們展示出了大家所向往的未來理想的樣子。
60年代以來,近代建築的對烏托邦的想像從上一個世代中脱離出來,交接到了下一代的建築師手中。比如塞德里克·普萊斯(Cedric Price)、彼得·庫克(Peter Cook),他們所作的各種嘗試都在試圖重新定義未來城市的構成方式;還有將這些不同的設想融合起來進行比較的克里斯托芬·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以及在實際的規劃體系去實踐烏托邦想法、在社會體系中去挑戰權威的Archizoom,等等。我們可以發現諸多建築師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持續着烏托邦式的對未來的探索與追問,而進入21世紀之後,這些想法或許真的能夠成為現實。當然,在中國它們一直都在不斷地成為現實。
今天最後要提及的這個項目還在備案階段,是位於埃及亞歷山大港的一個大學校園規劃方案。儘管不大能想像方案全體都能最終得以實現,但用一小部分來實現基本的思路還是可以期待的。這個方案的基本概念是對抗一直以來功能主義所塑造的大學校園的樣貌,比如重構研究室與教室、演講廳、以及宿舍之間的關係,在乾燥炎熱的沙漠中營造一個適宜居住的環境。這些圖片展現的只是我們設想的一部分光景,但這些光景包含了我們從都市角度出發對建築城市關係展開的新的思考。
尾聲
這次講座的內容太多,我一直注意着時間,很多地方都沒有展開討論。今天我在這裏演講所想到的一點是,從現今中國各種各樣的情況來看,以及從我90年代以來和中國各界的人士交流的感受來看,我發現世界的信息正在一點點地進入並且影響着中國。從80年代開放到2010年左右的三十年間已經完成了如此大量的信息交換,我相信再過三十年,世界所有最前端的信息也已經完全被中國所吸收了。
在此基礎上,中國開始用中文這樣的媒介探索並創作獨自的東西是從最近10年開始。如果我們參照過去日本的發展,會發現日本在80年代之前尚未對世界產生大的影響,而到了80年代,無論是從經濟上、還是從藝術、文學等文化方面,日本突然就搖身一變成為了“特殊的日本”,甚至成為了“奇怪的日本”,被很多人認為是世界上文化最豐富而繁榮的國家。在我看來,中國今天同樣迎來了這樣一個時代的分水嶺。從2008年之後各個城市所展示出來的問題就可以看出,世界上各種各樣的信息都已經進入並紮根到了中國國內,是時候必須要開始創作自己獨特的東西了。像日本從70年代跨入80年代所經歷的考驗一樣,中國必須在完全消化現代主義的基礎上提出新的時代主題,必須要回答在世界的信息洪流裏中國的東西到底是什麼這一問題。
我自己一直把日本式的東西形容成“Japanist”,因此中國所需要提出的主題也應當具有足以被稱為“Chinanist”的分量——無論是文化論、藝術論,還是創作的方法論。從50年代到90年代,再到21世紀以來,中國始終都在吸收着來自世界的信息,這個過程的結束應當伴隨着下一個階段的開始。什麼東西會成為代表中國的東西,現在也還存在很多爭議;就我自己而言,也始終在探索日本的 80年代以來能夠稱得上“Japanist”的藝術、思想與建築形式。我想對於此後的中國來説,類似的爭論只會越來越多。我所帶來的日本的經驗興許能夠提供一些參考,但是一定不會是直接的參考,這其中總會存在分歧和差異。不過我相信把握住這些寶貴的差異可能就是新的思想誕生的契機。
注:
PPT圖片 (C)磯崎新事務所 禁止擅自轉載
PPT圖片 (C)Arata Isozaki 無斷転載禁止
提問環節
朱錇:
剛才磯崎新先生因為時間的原因未能充分展開,但是我們也從中可以看出他講座的脈絡。磯崎新先生很難得有這樣的機會能從他創作背後的思想進行闡釋,特別是他的這次講座,起源於剛才我們看到的第三空間的展覽。實際上這跟霍米·巴巴提出的所謂第三空間類似,以各種跨領域的合作為起點。緊接着講座進入了他早期60年代的空中城市、70年代的電腦城市、80年代的須體城市,以及到90年代的海市城市的內容,當然他沒有展開。最後一部分他也談到了中國。
接下來我們會跟在座的各位,特別是參與今天研討會的各位有5分鐘左右的提問環節,不知道在座大家有沒有問題問我們的演講者?
Q1
很高興和老先生又一次見面。磯崎新先生提到60年代的問題,我想60年代人類文明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美國記者卡遜寫的《寂靜的春天》;73年聯合國再在斯德哥爾摩提出宣言:“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人類在工業文明之後發生的整個西方文明向大自然的懺悔,從那個時候開始了全世界文化對自然的關注,在這個歷史上,人類的文明各個角度都要回到自然的懷抱。因此我認為60年代以來整個人類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和自然發生關係?如何和老天爺發生關係?這是我提的一個問題。
磯崎新:
在60年代,對我來説影響最大的是當時的嬉皮文化。所謂嬉皮,在當時的表現就是拒絕一切的科技,作為赤身裸體的人類重歸自然的懷抱,在這個過程中孕育新的交流與新的人類社會。我自己其實私下跟披頭士這樣的團體有很多交往,從與他們的交往中我發現,他們所推崇的搖滾樂不是用傳統古典樂的樂器進行演奏,而是加入了電子吉他等新的元素,製造了更加新穎的旋律。這種自然而然的音樂繼承方式,以及人們自然聚在一塊兒享受新的音樂的方式,是我最為感慨的地方。我們一邊使用的新技術手段,一邊將我們過去的自然、傳統與新的文化現實重合起來,這不正是我們在時間的長河中前進時所追求的目標嗎?
然而,在大的人類進程中,文化的發展是受限制的。技術的發展是為了技術的成果,人們對技術本身的關注佔據了非常中心的地位。所以説在某種意義上,剛才講的這種自然地與過去、與現實和諧共處並且創造新文化的活動,其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幾乎全部遭受了挫折。因此,就如我之前講座中提到的,我想我們唯一的出路只有回到更古老的時代去追溯我們文化的本源,重新構建我們的思維方式。
由於社會對新的設計總是抱有巨大的期待和需求,在一定的時間點上,比起科技技術,新的設計與提案往往會有所滯後,難以迅速地找到它清晰的表達。只有我們給予時間一些耐心,新的文化才可能有更多自由表達的空間。
Q2
老師好,我今天對磯崎新老師最後的講幾句話特別感興趣,也是我今天思考的一個問題。他説過去在日本發生的不一定100%在中國發生,但是我認為100%會在中國發生。30年前東京市政府搬到了新宿,30年後的今天北京市政府從王府井搬到了通州;30年前爆發了美日貿易戰爭,30年後爆發了中美貿易戰爭;30年前有個東京愛情故事,30年後的今天有個北京愛情故事;30年前日本由於政府對於經濟不能干預,造成了這種危機,在今天我們國家一直在拖着中國的經濟,這也是我今天在想的問題。在這樣的一個轉折的背景之下,作為城市的規劃師,或者建築師來講,我們職業者的命運是什麼樣的一個變化?因為磯崎新老師也是一個跨越時代的建築師,我希望聽一些在這樣大的歷史背景之下建築師如何自處?謝謝。
磯崎新:
日本已經沉沒了呀(諧音沉默)。(有一本書叫做《日本的沉沒》)
三十年後,中國甩下的不僅僅是日本,而是整個世界。
現在日本政府千方百計想要做的事正是讓已經沉沒(沉默)的日本再一次在世界上捲起一些波瀾,因此他們發起了Cool Japan這樣愚蠢的運動,試圖通過動畫、漫畫、卡拉OK這些形式重新樹立起一個特殊的日本形象。我常常在想他們要失敗多少次才會醒悟。這樣的對手根本不值得中國在意。
從長遠的歷史潮流中來看,中國不管從體量也好,從歷史也好,永遠是日本學習的對象。但是現在大家都在面臨剛才所説的同樣的問題——在時代裏面,技術都是最顯眼的,因而被認為很容易被政府、被社會接受或者推崇的,在它背後真正的文化力量則會相對來説延緩一點才呈現。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我認為在這個年代都還沒有真正的能夠把對應這個文化,或者對應這個社會最本質的東西以更新的狀態呈現出來。但是我相信中國之後的爆發力。現在面臨的情況整個社會是一樣的,但中國爆發的力量遠遠大於日本。
Q3
剛才您的演講裏面提到了建築和城市的合體,關於城市和建築的討論在中國當下也是一個熱點話題。比如是不是還應該有城市規劃,或者應該以城市規劃為主體,還是應該以建築為主體。我想問一下,在您的創作和思考中,建築思維是佔主要的位置,還是城市思維占主導地位?謝謝。
磯崎新:
如我剛才講座裏指出的,“建築”這一詞彙的含義與“architecture”在西方語境中的含義之間其實是存在一些錯位的。建築一般被我們理解為建築物(building),都市其實也是建築物的一種;與此相對,Architecture則並不指稱具體的某種東西,而指涉更加廣義的結構(structure),它是把結構建立起來的一個系統(system),這是從羅馬時代就流傳下來的理解,本身就是一個包含了社會性、政治性、藝術性的概念。因此,您剛剛提問中的建築與城市的區別其實是肉眼看得見的建築與肉眼看不見的建築(architecture)的區別,看不見的部分甚至可以擴展到社會的制度、政治等領域的構成。
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來説,只有將這兩個方面聯繫起來,我們才能洞察一種文化內部它所賴以形成這種文化的骨架,或者説它的建構方式。實際的城市當中,文化的架構往往還處於一種初步的階段,但我們以前所提到的關於烏托邦社會的種種暢想正展現了我們想要清晰建立的目標。現在的中國亦是這樣利用現有制度的同時不斷地進行新的社會重構,讓實際的城市演變為我們親眼所目睹。所以説並不是在都市,或者建築各自之間,而是要把這兩者有機的聯合起來進行一個梳理,才是更好的。
朱錇:
由於時間的原因,我們的提問就這樣。當然磯崎新先生在他的講座裏,包括回答問題當中,都映射出一種東方的智慧。為了感謝磯崎新先生給我們帶來深刻的講座,我們建築學院特地為磯崎新先生準備了一個小禮物。這個作品的創作者是建築學院課程教授王長春老師,非常感謝王長春老師,一會兒我們跟磯崎新聊。
贈送禮物
場內外座無虛席 ©中央美術學院建築學院
以再一次的掌聲感謝磯崎新深刻的講座,我們休息10分鐘,10分鐘以後我們開啓系列講座的第二部分,是我們的嘉賓和磯崎新先生展開一個深刻的學術討論,一會兒見。
第二環節
專題研討會
研討會主題:六十年代以來的建築運動
時間:2019年10月29日星期二下午2:30 – 4:00pm
地點: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報告廳
特邀建築家:張永和、王明賢、劉家琨、周榕、史建、張路峯、李興鋼、王輝、童明、華黎等
**特邀藝術家:**劉小東、朱樂耕、方振寧、陳文令、吳達新、丘挺、包泡
朱錇老師開場
©中央美術學院建築學院
下面開始我們的研討會環節。首先請允許我介紹一下今天參與討論的各位來賓。首先是磯崎新先生,國際著名建築師,2019普利茲克獎得主,剛剛給我們帶來了精彩的講座。
另外還有著名建築師、建築教育家,同濟大學建築學院教授,非常建築事務所創始人、主持建築師張永和,
中國藝術研究院建築與藝術史學者、中央美院視覺藝術高精尖創新中心專家王明賢,
著名建築師,家琨建築設計事務所創始人、主持建築師、中央美院視覺藝術高精尖創新中心專家劉家琨,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副教授、中央美院視覺藝術高精尖創新中心專家周榕,
著名建築評論家、策展人,有方合夥人史建,
中國科學院大學建築研究與設計中心教授張路峯,
中國建築設計院有限公司總建築師,李興鋼建築工作室主持人李興鋼,
著名建築師,都市實踐設計事務所創始人、主持建築師王輝,
著名建築師,同濟大學城市規劃系教授,TM STUDIO建築事務所創始人,主持建築師童明,
著名建築師,跡.建築事務所創始人、主持建築師華黎。
此外,這次我們請到著名藝術家,
中央美術學院造型學院教授劉小東,
著名藝術家,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學藝術創作院院長,教授,全國政協委員朱樂耕,
著名獨立策展人和學者、藝術家、建築師、藝術批評家方振寧,
著名藝術家陳文令,
著名藝術家吳達新,
著名藝術家,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學院山水系系主任、教授丘挺。
剛才磯崎新先生在長達一個半小時的講座中,深刻地揭示出其建築創作背後的思想,在磯崎新先生60餘年的職業生涯中,數百座建築物包括建成、未建成已在多數的著作中發表,是全世界範圍內最重要的建築家之一。然而,策展、合作的藝術品、裝置的試驗性作品未必被人們所熟知。加上城市規劃和建築,這些活動可以被稱為磯崎新的“第三空間”。常年以來,佔據藝術、設計、音樂、戲劇等其它領域活動的磯崎新並不是安於單純僅做建築家,就像“第三空間”的概念,今天,這個位於中間的、交雜的、曖昧的、含有與自身相關意義的概念被更廣闊地使用。以這個概念為原點,從這些廣闊的業績文脈中可以追尋到文化現象的創造性實踐、時空裝置的滲透、迷一般魅力藝術家新思想的光芒。
接下來這個研討會希望在磯崎新的思想基礎上,聚焦三個具體的主題展開。這三個主題分別是:“六十年代以來的建築運動”、“磯崎新與中國”、“磯崎新與當代藝術”。我們將從建築、跨文化實踐和藝術批評的角度分別切入,並且以中國語境為基底,立足當代,放眼全球,希望每位來賓從多元的自身視角出發,為我們的這場學術盛會帶來精彩的思維碰撞。
張永和
著名建築師、建築教育家,同濟大學建築學院教授,非常建築事務所創始人、主持建築師
大家好,雖然我只講幾分鐘,但我還有個題目——《廢墟的理想主義》
1985年,我在舊金山一家建築事務所工作。因為金融區停不起車,我每天只能在漁人碼頭那邊停車,到事務所要走40分鐘。路上有一家叫US cafe的美國小館,大玻璃窗上印着絲網印刷版畫,畫的是建築的廢墟。每天上下班,我都把鼻子貼在玻璃上,沒完沒了地看。莫名地,我被這版畫深深吸引。
這幅版畫就是磯崎新畫的他設計的房子——筑波中心。
1996年,在東京召開來一次有關亞洲建築的會議,我就有機會認識磯崎新先生了。之後也很感謝他邀請我參與了很多事情,有展覽,有會議,我們還一起做過競賽。這些事情對我來説都是特別好的學習機會,其中一個特別好的學習機會,就是跟他一起吃飯。在離他事務所很近有一個意大利餐館,餐館裏也沒什麼人,我們一點完餐,餐館老闆也一個多小時不出現了。這就給我們創造了長談的機會。
在這個過程中,我開始對他的思想有所瞭解,對這些畫開始有一個認識。首先,在磯崎新之前也有建築師把設計的房子畫成廢墟——這張是一位英國建築師畫的他設計的英國銀行——他好像表現的是疾風暴雨把建築摧毀的場景,你不會覺得這組建築再有任何的未來。可是磯崎新先生的畫,是在黃昏裏面,好像是更有一種廢墟的詩意,也可以説廢墟里麪包含着一種劫後餘生的希望:天是藍的,很晴,還有深深的陰影。
所以我開始似乎明白了一個道理,這個廢墟有消極的,也有積極的。這積極的,實際上是把建築的生命呈現出來。建築也有生,也有死————在生命的呈現過程中,如果人有人性,其實把一個建築性再在裏面表達了——也就是説,建築可以毀掉,但是建築性還可以延續,甚至還可以發揚光大。所以我當時看了這些畫,並沒有因此覺得做建築這個事不靠譜,而是覺得這個事太有意思了,所以我更下了決心做一個建築師,那個便是我在畫裏感受到的。
所以回到這個話題:如果建築性可以和人性相比,過去這些年,實際上我自己對人性是很失望的。當然這個事很不可笑。當然除了磯崎新先生的版畫,他的思想,我也在其他的一些場合遇到了另一些一直保持着對人性信念的啓發,所以我現在也在努力恢復我對人性的信心。有一點我明白了,如果咱們每個人都對人性有信心,人性其實有可能是重新放出光芒,而不是像電視上整天看到的都是一些最悲慘的消息。
對人性的信心,我也發現就是理想主義的定義。所以從這些版畫裏,我也看到磯崎新先生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建築師。
在今天磯崎新先生講的建築與城市的合體,講的烏托邦,我是覺得再一次體現了人性還是充滿了一個希望,而且對人類的發展有一個很堅定的信心。我不知道我講的對不對。我這段同時也是我的問題,他是否認為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對人性有多少信心?
謝謝。
王明賢
中國藝術研究院建築與藝術史學者、中央美院視覺藝術高精尖創新中心專家
我簡短的發言就是《磯崎新與中國》。
先從60年代談起,60年代日本建築師羣星璀璨,對整個世界建築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像庫哈斯用7年的時間研究日本建築,以及新陳代謝派。我之所以對新陳代謝派如此感興趣,也因為它第一次體現了非西方的先鋒派如何在美學和意識形態上壓倒西方,控制了話語權。1968年整個激進的學生運動席捲了歐美,特別法國的五月風暴更是對世界影響很大,建築思想領域真正的革命正在醖釀。像磯崎新和庫哈斯都對法國的五月風暴很感興趣。還有一個是對毛澤東的推崇,當時毛是他們重要的符號,磯崎新先生也是非常認真的讀了毛澤東的著作。這個對於他們未來的建築思想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80年代開始國內有對磯崎新先生的解讀,1981年在《世界建築》出版的日本專號,開始介紹了磯崎新,介紹了1984年的筑波中心大廈,還介紹了洛杉磯現代藝術博物館。1988年《時代建築》也推出了磯崎新的專號,以及磯崎新建築談話錄,還有羅瑞陽的文章,像《新建築學報》、《新建築》、《華東建築》等等有一系列的介紹。
汪坦在《戰後的日本建築》文章中提到,近十年來,日本建築已經在世界上獲得了卓越的聲譽。這篇文章是1981年發表的,他對西方建築理論有很深的研究。再下來是1988年,鄭時齡的文章,這是中國建築史第一篇評論磯崎新的文章。這裏面寫到,無論是在東西方文化的交融和滲透中,或者在西方文化開拓新道路的探索中,今天的日本建築都起了領先作用,在眾多傑出的日本建築師中,磯崎新富有個性的創作經過三十年的努力,走出了堅實的路,得到國際建築界的矚目,享有世界性的聲譽。
我再談一個問題——磯崎新與中國實驗建築。中國青年建築師都得到了磯崎新先生很大的支持和幫助,像張永和、王澍、劉家琨、朱錇等等這些中國的建築師都得到了磯崎新先生很大的幫助。我就記得在上海雙年展上,磯崎新先生談到中國的青年建築師,都非常重視,而且他覺得中國青年建築師未來肯定在世界的發展上佔有一席之地。
這就是中國建築師在威尼斯雙年展上的作品:這是張永和的“竹化城市”;這是王澍的“瓦園”;這是劉家琨在“民間未來”上的作品;這是朱錇的“意園”。當然中國建築師和磯崎新的聯繫,下面可以聽到更多的解釋。
張永和“竹化城市”
王澍“瓦園”
劉家琨在“民間未來”上的作品
朱錇的“意園”
我還想談一個問題——磯崎新與中國當代藝術。除了建築師以外,磯崎新跟中國很多當代藝術家也是好朋友。比如磯崎新跟蔡國強先生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就記得比如像90年代當時美術館的展覽,磯崎新就邀請了蔡國強參與,也做了很有意思的工作。中國當代藝術家們在空間環境上、東方美學的認知上,跟磯崎新的思想有很多相通之處,蔡國強的藝術充滿着活力,震撼人心,書寫了大地藝術的奇蹟。還有當代藝術家徐冰,有一個挑花源的作品,他認為桃花源的故事是一則隱喻,在這則隱喻中,我們所渴望的理想世界看起來那麼的遙遠,這是一個面向全球觀眾的全球性問題。磯崎新探索的也是關於烏托邦的問題。
還有當代藝術家汪建偉,他持續探索知識走合與跨學科對當代藝術的影響,他的作品跨越了影像錄像、戲劇、多媒體、裝置、繪畫和文本等領域,磯崎新先生也是一個跨越多領域的這麼一個建築師和藝術家。
還有像當代藝術家邱志傑,比如他的記錄世界地圖計劃,也是非常有意思;還有劉小東,2005年他在三峽創作了油畫《温牀》,後來做了很多寫生;還有當代藝術家朱樂耕先生創立了自己的陶瓷語言系統,並把這種陶瓷語言跟建築空間結合,創作了具有歷史文化內涵的公共藝術作品;當代藝術家陳文令,陳文令的作品在當代的文化情境中反思新的風景形態,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當代藝術家吳達新以獨特的全球化視角創作了大鱷,既有西方工業化的粗獷,又不失東方的禪意;當代藝術家邱挺,在他的山水畫作品中並不僅僅有傳統的功力;還有當代藝術家沈勤,以空靈的水墨語言創造了一種神秘的水墨空間,他的繪畫是當代藝術的實驗,傳遞了一種東方的文化精神……
我覺得磯崎新先生對中國建築師跟中國當代藝術家影響都是很大的,至少我們的藝術家每次走到中央美院美術館門前就能受到建築的薰陶。
磯崎新先生在90年代,在珠海附近的南海橫琴島上設計了“海市計劃”。那是一個人工島計劃,是一個將現行政治、社會公認的各項制度完全隔絕的世界,也是接近磯崎新烏托邦理念的作品。我個人覺得那是一個古往今來建築師關於人類未來空間最重要的設計。我覺得現在中國設計師設計的任務非常多,設計技術非常好,但是好像關於城市的未來、建築未來的思考少了,寫作也少了,我覺得像磯崎新先生這種建築思想家富有遠見的思考應該給我們中國建築師非常多的啓示。謝謝。
劉家琨
著名建築師,家琨建築設計事務所創始人、主持建築師、中央美院視覺藝術高精尖創新中心專家
大家好,朱院長讓我臨時説,我來不及準備PPT,就拿手機做了一下草稿。
讀大學的時候磯崎新先生是我們大家的偶像,剛才張永和説的那些廢墟也是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當時有點震撼,做建築還可以這樣想,把房子給蓋廢了(笑)。
我沒有主題,只好回憶一些交往的細節。
2003年,我和磯崎新先生共同策劃了南京的中國建築藝術實踐展,是在佛手湖(四方當代藝術湖區)。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我也是初次和磯崎新先生合作,由磯崎新先生邀請國際建築師,我邀請國內建築師,對於我來説也是一個全新的活動。有一個事情:項目地形都劃定了,突然用地出現問題,後來又在旁邊收了一塊地。但是建築師都在來中國的路上了,最後還是找磯崎新先生商量,就決定不告訴這些建築師換了地,所以他們過來的時候看見的還是有些湖,有些半島,還有些水。可能直到現在,很多人都未必知道他們其實是到了另外一塊地上開始了設計工作(笑)。
2004年,我們和張永和一塊兒策劃了建川博物館,邀請磯崎新先生設計日本侵華罪行館。磯崎新先生去了以後,建川就很激動,但是其實又不太知道怎麼樣接待磯崎新先生。後來我們發現磯崎新先生喜歡美食,喜歡美食的人到了成都就有救了。磯崎新先生好奇心很強,什麼樣的菜都想試一試,而且興致勃勃的那種吃法尤其有感染力(笑)。所以這讓我們重新反思我們已經吃的不厭其煩的那些菜,其實對我們有所觸動。
有一個細節我覺得特別有意思,建川發現竟然真把磯崎新先生給請來了。他就很激動的給磯崎新先生講話,他開始用四川話講,突然發現聽不懂,改成川普感覺磯崎新先生好像懂了。我就在那兒納悶,講了一大堆,動作又大,還手舞足蹈的。之後,磯崎新先生起來跟他握手,我們很奇怪,我後來就問,您聽懂了嗎?磯崎新先生説了一句話,我到現在印象都很深,他説:“我一句都沒聽懂,但是我很激動啊”。(笑)
本來我寫的他是充滿熱誠和批判精神的建築大師,這個他自己都講了。一個視野廣闊的國際知識分子,這個好像自己也講了,張永和也講了。另外一個,他的確是熱愛生活親切隨和的一個大哥。
我講最後幾句,大概十來年前,我不記得什麼事情,我也曾經像這樣致了一個辭,具體什麼原因、説的什麼我都忘了,但是真心話不會忘。我記得當時説建築學應該給他更高的榮譽,才能當得起他對建築學的貢獻。今天我還可以説這句話,但是有點困難了,他什麼獎都得完了。
我覺得磯崎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