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珀聯盟的天才院長正在幹什麼?_風聞
全球知识雷锋-以雷锋的名义,全世界无知者联合起来!2019-11-06 00:11
作者:孫天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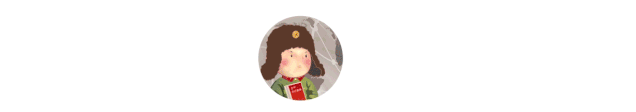
我時常想起格雷戈·林恩描述一個建築師能力的方式:他能從一條線開始演進成一個樣條函數,從而解放一種新的建築造型的可能性。
我先後在三代人的影響下學習——先是傳統手繪時代,接着是數字建模時期,然後是編碼和程序——幾乎從沒能趕上時代。
在建築學中,繪圖絕非只是圖像的平面操作,它已經是一種建造行為。
推薦語
本篇講座由都市實踐合夥人、主持建築師劉曉都推薦
內達爾·特拉尼(Nader Tehrani)教授的這個講座是兩年前做的。在此一年前因為邀請他在深雙UABB做建築裝置有過幾面之交。原來知道Nader和Greg Lynn等被稱為建築設計行業探討數字建造方法的幾個先鋒人物之一,而聽過其人作品才有了多一些的認識。Tehrani教授是我認識的最欣賞的當代建築師和學者之一。尤其讚賞他是理論實踐俱佳的人才。這樣的人並不多,像艾森曼那樣艱澀更加理論的大師,也是理論更加突出,而Nader則是處於十分平衡的狀態。很高興知識雷鋒能夠介紹他的建築理論和實踐。
Nader Tehrani為深雙UABB設計的裝置
如其本人所説,Tehrani教授在個人電腦普遍應用之前就學了建築,是舊的設計體系訓練出來的,之後一直在跟進和求變。同時在那個時代學院建築學思潮正經歷從後現代主義向後結構主義向解構主義的劇烈變化,這些理論卻沒有提供實踐的解決方案,而很快電腦數字新方法也出現了。他們這代人便是在如此複雜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Tehrani教授作為不多見的建築學者中重視建築實踐而且頗有建樹的人物,他把建築學的內涵不僅呈現在時間、空間上,更重要的是在材料上。他甚至於提出繪圖的意義不只是對建築的再現表達,更多的是建造的一個部分。當然 90 年代的歐美建築學校的教育已經形成對材料認知的敏感度,在一年級的設計初步課程訓練中就讓學生做抽象構成模型,把材料應用作為空間和造形之外的重要手段。從而為數字建造初始的“表皮” (Surface)設計風潮做了準備。Tehrani教授儘管是玩表皮的大師,但他的嘴裏基本不提表皮,而是把實踐和建造掛在嘴邊。我建議年輕的建築學子認真關注他的這個特點,如果能夠就此改變對國內仍然侷限在空間和造型至上的蒼白建築手段和思維模式,則會是最大的收穫。
Tehrani教授自述在電影製作和建築學之間曾經有過選擇。所以他在羅德島設計學院學習建築學及後來的哈佛GSD的學習仍然受到電影製作的影響。空間敍事,意義表達,視覺高潮都在他的作品裏有所表現。講座中講到的墨爾本大學設計學院是他的得意之作,也是我最欣賞的作品。中庭裏做了個一氣呵成的從變形的巨大頂棚懸掛下來的木構體量,真是神來之筆。看得出建築師對形體和材料的控制力非常出色。
墨爾本大學設計學院中庭
Tehrani教授所領導的建築事務所NADAAA,包括前身Office DA的建成作品並不很多,但每個作品都嚴肅的回答了他所思考和着力的問題。他所涉獵的設計類型範圍非常廣闊,從不同類型的建築到建築裝置直至傢俱設計都有涉及。他早期的作品,北京通州Gatehouse就實驗了磚的砌法與構造所能引發的新形式機會。他在探索數字建造的方法的同時也沒有拋棄傳統建築學的基本原則和品味。
北京通縣藝術中心
Tehrani教授接替張永和老師做了幾年MIT建築系主任,事務所也在波士頓。近年做了紐約Cooper Union的建築學院院長,每週乘火車在兩個城市間來回奔波。在火車上也勤勉地讀寫思考。相信Tehrani教授還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高質量作品。
講座正文
Nader Tehrani,庫伯聯盟艾文·錢尼建築學院院長
感謝如此友好的介紹和邀請,也十分高興能參與大家的評圖,其實評圖過程中我提的許多問題和我們工作室多年來嘗試解決的一些問題緊密相關。表達(Representation)這個問題當然有諸多隱含意義:從圖像的角度上來説它和“如何通過模擬的方式來表現現實”有關,例如畫法幾何,或是其它能夠暗示某種特定工具性的描繪現實的方式。
我時常想起Greg Lynn這樣描述一個建築師的能力:他能從一條線演進成一個樣條函數,從而解放一種新的建築造型的可能性。我們始料未及的當然是編碼和程序的到來,因為這就是為數不多的例子之一:此時,一個非視覺語言有着重要但又具有擾亂性的潛力,能發起一場與視覺圖像領域的對話。這種語言實際上已經不再和視覺聯繫,所以也不再是一種構圖語言。因此我們這一代很多人經歷了艱難的轉型,對此我也難有發言權。
這是我們極大的劣勢,因為諸位可以想象我畢業時,計算機還沒有進入這個學科,一年後它才出現。於是我先後在三代人的影響下學習,先是傳統手繪的一代,接着是數字建模的一代,再然後是編碼和程序的一代——我幾乎從來沒能趕上時代。因為我在美國早年對這樣的轉變並不熟悉,也少有這類客户或接觸這類委託的特殊渠道,我們便選擇自發地做一些項目。這些項目都是裝置,換句話説,是嘗試學習和開發將那些通常分配給承包商的建造方法的作品。我之後會更深入地講一下,但是重要的是這類研究為我們設計建築鋪平了道路。
那些年裏我們做完項目便提交給“進步建築獎(Progressive Architecture Award)”進行評選,兩次都拿到了獎項,這也就有了後來的Terry Riley,屆時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的策展人給我們打電話的事情:他想讓我們為MoMA一個名為“Fabrications(建造)”的展做一個裝置作品。我們自然覺得這是一個虛無縹緲的目標,於是掛了他的電話。直到他十分惱火地回撥,質問我們究竟怎麼回事(我們才接受)。(觀眾笑)在那個時代背景下——那時是1996年——這其實是非常創新的,因為建築師只繪圖,不建造。他(Riley)説我不想要任何圖紙或模型,只想要一個表現建造的建築片段:它一定要直面觀眾,一定要橫平豎直,同時一定要將材料誤差控制在半英寸之內,(指向幻燈片)而我們的作品的確都滿足這些要求。
我們要做的似乎是在MoMA的花園中創造出一個扁平的、絕對抽象的畫布。我記不清這裏有多少個單元了,這有大約45個扁平且具有漫反射表面的板塊,和抽象的現代繪畫頗有聯繫——可是大家都知道這(種沒有空間感的裝置)是我們最不想做的效果。實際上,我們苦心鑽研的是當時行業並不關注的一種鋼鐵建造技術——不用工字鋼和直角尺,而是運用摺疊鐵片來支撐結構。我們運用了當時比較先進的激光切割技術,通過刻痕互相偏移以製成類似“縫合”的節點,最終達到一種摺疊結構的清晰度和連續性。
我們真正想做的是一個類似看台的漂浮階梯,一個不由標準構件組成的樓梯。這些構件中顯然沒有任何兩個是相似的,因為此項目的概念正是一個透視變形的詭計(anamorphic ruse):只有你從特定視角觀看時它才橫平豎直——其視覺正交性也是我們衡量建造誤差是否在半英寸之內的標尺(gauge)。整個項目的摺疊是為了賦予結構足夠的剛度,但也證明了這是有效的建造手段。
建造痕跡
促成這個項目的前兩個項目分別是Weston House 和Casa La Roca,也是我下面會講的。在Weston House中,我們為一幢平房住宅加建二層,同時也想設計能夠掩藏兩層之間縫隙的表皮。但這還不夠,我們希望這個覆蓋物能營造雨棚的空間感,它需要容納空間,能成為一個入口(threshold)。我們瞭解到,瓦楞銅板能在豎直軸線上有結構剛度,而在水平軸線上有完全自由的延展性。
這意味着我們能夠通過將其捲起而留出空間以便插入連接地面和二樓客廳的樓梯,瓦楞銅板的上寬一定與下寬完全相等,而這個對於簡單幾何原理的詮釋與建造行為有着直接聯繫,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關於繪圖的一個結論:在建築學中,繪圖絕非只是圖像的平面操作,它已經是一種建造行為。所以你並不需要真正地將一個東西建造出來以檢驗它的可行性,只需知道這銅板的兩條邊應當完全相等(並以此繪圖)。
可展開曲面或者説直紋曲面的原理早已隱藏在於瓦楞表面的邏輯中,我們都知道,瓦楞形式能產生組成直紋曲面的矢量,其邏輯並非複合弧線,而是由諸多單獨的直線構成的。
隱含在我們想法的背後其實是形體(figuration)和構造(configuration)之間的張力,如同一個硬幣的兩面。我們可以這樣想,瓷碗其實和鳥巢相似——瓷碗在燒製時也是由集成體組成的,可能是泥土,只是在打磨和上釉時將建造的痕跡抹去罷了,實際上它仍是由小型模塊形成的場構成的。但是鳥巢並不掩飾這個場的痕跡,鳥一次次銜來稻草才創造了一個集成鳥巢的可能性。當然有趣的是,在產生鳥巢之時,稻草還可能形成多種其它形態,而不只是碗狀結構。我們大多數的研究都和這圖解的右半部分(鳥巢)有關,我們不認為構造細部是建築的最終產物,而是一個能夠成長為建築的種子。
當我們研究萊韋倫茲(Sigurd Lewerentz)的作品時感到好奇的並不是磚,而是磚之間的縫隙,也就是砂漿填充的位置。如今諸位完成的研究(關於的磚的非傳統建造課題)會是一份影響後世的工作,而我早年也在相似的情形下遇到過這類難題。我意識到在萊韋倫茲的作品中,砂漿的體積甚至可能比磚本身還大,這(靈活性)也就意味着當我們到達位於Caracas的場地時,Casa La Roca中的砌築系統可以(與傳統方式)完全不同。
這是我在場地上畫的一張草圖,在後院有一塊巨大的岩石,和這個演講廳差不多高——約二三十英尺,因此其周圍無法容納一座房子。於是我們採用了L形體量和迫近體量的鄰居宅牆一起圍合出一箇中庭,與岩石一同形成軸向的視角。(圖的右邊)就是那塊岩石的剖面,草圖的這部分是是一個摺疊的牆面,正像Weston House一樣能夠賦予側向的結構穩定性。諸位對此並不陌生,只不過諸位將牆體捲成弧狀,而我們則將其摺疊。於是我們回去便直奔細節,研究出了建造方法。
我們特別注意的是,右邊的磚砌手法是一種物質的實體構成,而左邊的賦形則是某種設計衝動被強加於磚的結果。如同萊韋倫茲一樣,我們堅持用物質本身來建造,即運用磚固有的屬性作為形式操作的基礎。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我們便對比了全順梅花丁的磚做法——看待梅花丁時,我們並不將序列中的磚的短面(即丁)看作是一塊磚,而是一個可以被泥漿填充或者完全留出的空當。
我現在為大家展示的圖紙也正體現了我所經歷的教育過渡階段,所以請原諒我用鉛筆製圖——我們當時就是這麼繪圖的。
如果這個空當尺寸可變,那我們便能發明一種可變的磚砌系統,既不是全順也不是梅花丁。空當的間隙尺寸是一個未知數,一個指標,而只要它能夠比磚的長面短,保證其穩定性,便可自由伸縮。
沒有哪塊磚止於斜線——因為牆的摺疊恰好發生在斜線上,不管組成摺疊的牆面的尺寸如何,磚只有在突出的邊緣才戛然而止。當諸位看到這個細節的時候,不妨回想伍重(Jørn Utzon)在悉尼(歌劇院)的手法,當瓷磚鋪設到一個表面的邊緣的時候需要重新校準其尺寸以收邊。
我們那時知道伍重,但不知道他的瓷磚細節,我大概二十年後才發現這個,當時不由歎為觀止——因為我們總習慣將悉尼歌劇院看作一組形體或一座雕塑,而在實地考察之前卻對其構造一無所知。Casa La Roca的根本邏輯便是將承重牆解放出來,在產生摺疊結構的同時,營造半通透表面以允許光與空氣流通。我講這些不免有點班門弄斧,因為你們(ETH的數字建造研究團隊)早已做過這些事並且做得更好。我們是在沒有機器人的時代(pre-robotic)做的,於是(在數字時代到來之後)又採用了新一代的數字表達來回顧這個項目,這是一種反向的教育。五六年之後,我們根據手繪圖紙上的牆體摺疊的矢量,學會用計算機將這個項目繪製出來——項目的木製模型當然也是手工製作的,有趣的是我們那時使用了固定木頭的夾具,但我們在原計劃將模件固定的前一天離開了工作室,回來之後我們發現潮濕的空氣使模件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膨脹,原本模件上膠水量的差異更加劇了這一點,最終我們不得不將模件單獨打磨使其恢復原來的尺寸。
現在展示的是我最近一次向Matthew Waxman學習編碼——利用程序識別每一個磚塊的端點,生成這種可變磚砌系統,考慮它如何生成一個斜向摺疊的場,討論磚牆能站立的最大疊澀[1]角度……這些圖中你能看到面、正軸測、側面軸測、剖面軸測這些表達方式。
注[1]:疊澀(corbelling)指砌磚時上層磚與下層磚有位移,多次重複形成出挑——Tehrani的動畫中,磚牆先挑出再收回。
這個圖紙數字化、編碼化的過程其實就是一種概念性的過渡:從基於圖像模擬的指紋到基於索引標記的條形碼。條形碼不再是一種表達,而是一種標記和索引。我們在思想上需要經歷這樣的過渡,在此之前設計教育還從沒有被這樣思考過。
Casa La Roca的客户離婚了,因此項目無法落成。但同時我們收到一份委託——在波士頓設計一家餐廳,預算是23萬美金。項目要求很多:需要一個吧枱區、就餐區還有地下室等等,我們感興趣的則是這個小型的籠狀包間。
問題在於我們將繪圖交給承包商時,他們給這個結構的報價約18萬美金,而餐廳其它部分的預算只剩下5萬。那是二十多年前,我們還很年輕,並不知道這個結構為何會如此昂貴——於是我們決定先將它從總設計中撤出,讓承包商來做剩餘部分,而我們自己來建造這個結構。我們用長2英尺,厚1英寸的木條作為原料,直接將施工圖貼在天花板上,然後從上面吊下鉛錘作為木條位置的參照,將誤差控制在了1/16英寸之內。
一天後我們已經完成了11層,這説明可以在一個月之內並且花費不超過3萬美金的情況下完成這個結構並仍能獲利。相比之前的預算,這可是15萬美金的差距——這就是美國建造業的一個縮影——如果你不明白建造意味着什麼,你將無法控制結果。這裏的木條就像Casa La Roca中的磚塊一樣,通過摺疊賦予這個表面結構的穩定性,在頂部生成一個星形開口。
那個項目為我們與建造業的對話提供了新的契機,也在通州門房這個項目上有所體現。可變的磚砌系統使建築可以呼吸,暖通空調(HVAC)可以持續使用,同時磚牆是結構表皮,而混凝土的模板並不是結構本身。大家想象一下,每兩英尺的標高重複一次磚砌-鋼筋-混凝土的操作,直至完成。只有北立面上的混凝土結構和磚砌模板才能被完整地展示出來,這個系統的“純粹性”恰恰體現在了磚砌表皮不僅作為結構,還過濾了光線且使暖通空調能與外界換氣,[2]講到這裏算是我們早期實踐的一個小結。
注[2]:正如Tehrani在問答環節會講到的,他崇尚的並不是真正純淨的系統,而是多個系統同時擔當多個角色,互相依靠使其綁定在一起。
地板和天花
下一個階段始於我們對地板和天花的“對立關係”的研究,縱觀古今所有建築,我們終究必須站在地板上,但是天花卻有另一層潛力——聖彼得大教堂就揭示了這些潛力:拱頂能產生跨度,保證光照和通風。聖彼得並不只有一個拱頂,而是兩個——外拱頂所代表的城市公民意識和內拱頂所代表的天堂意象是不同的,這與懸吊天花系統並不完全相似,但是也不盡然相異。
聖彼得大教堂,梵蒂岡
我們現在所知的建築很少將地板和天花合併成一個面,庫哈斯的朱西厄圖書館(Jussieu Library)或許是為數不多的一個案例。
朱西厄大學圖書館,OMA
實際上這兩個系統本質上就不同,不幸的是,因為照明設備、水電暖管道和消防設施的存在,懸吊的天花和抬升的地面就是我們現在亟待解決的難題。
一個研究題為“非物質,超物質”的裝置作品啓發了我們,使我們把目光轉向建築之外、有關幾何的問題:在這個穿戴裝置中仔細觀察衣服從胸部到臀部的變化,你會發現我們身着的無非是褶皺和裁剪的產物。
順着這個邏輯,我們將材料的一部分切掉然後再縫合起來,本質上是形成了一個錐形曲面——平面上微小的起伏使非標準的鋪設系統可能實現。如果不順着木紋裁切,材料就會受損,因此我們也極其注意紋理(grain)[3]的方向性——這成了一次設計任務的勇敢嘗試。
注[3]:Tehrani此處提到的grain原意指材料(尤其是木材)的紋理,但是英文中grain已經不止於一種物質現象,而是成為了一種形式特徵,指形式上可以讀出的主導的方向。Tehrani多次演講過題為“Tectonic Grain”,即建構的紋理的演講,就是為了詮釋這個廣義的概念如何從物質和形式上影響他的實踐。
我們嘗試在這個餐廳的室內設計中將地板完全解放出來,利用天花懸吊所有的水暖系統。從一個方向上,它製造了流暢表面的假象;從另一個方向上,它將討厭的水暖等技術設備都遮擋起來。當時這個項目沒有任何結構功能,於是我們總在尋找機會使它和建築的其它系統發生交叉。
在喬治亞理工學院(Geogia Tech)[4],我有幸得到一年的客座講席職位並有機會開始下一項研究。我問自己:為什麼我們總是默認分別由矢量、體積、表面主導的結構系統根本上都是不同的類型,而從來沒有拷問過它們能否拓撲合併?
注[4]:vector/form/surface-active structural system,這三個概念在Heinrich Engels的Structure System中有所分類,美國建築高等教育常用此書做參考。
就像我們默認水能自由凝固成冰雪、汽化成蒸汽,但是我們從來不對一塊磚思考類似的問題。
我們在這個裝置項目裏生髮一種筒形結構,通過三維的變換生成了一個箱型梁、一個摺疊梁和一個矢量主導的梁(涉及之前提到的三種形式)。
懸吊結構
基本上這些建造零件——或者説是磚——就構成了從右到左的堆垛結構、編織牆結構、梁結構和最終的懸挑結構——成果看似混亂,但其實有着嚴密邏輯,我們對懸挑處的高度誤差進行了測量,發現竟然只有一英寸,我的預估是至少六英寸,所以這實屬意料之外。可以肯定的是,這種對於懸吊結構的痴迷多年來一直伴隨着我們。
這是西扎的一個非常美妙的結構,特別是當光從結構邊緣傾瀉下來的時候,給人以織物的想象,當你發現它是混凝土、其實有重量時,它的存在就昇華了。
當然,這個路易斯·康在威尼斯的未建成項目體現了懸吊結構其實可以被人棲居或置入空間功能,我一直都很喜歡長軸上的那個講演廳。
和這個有緊密聯繫的是高迪用懸鏈原理優化拱形結構的研究。
Axel Kilian[5]的研究使得我們可以在不做任何懸鏈實驗的情況下計算複雜多變的結構,這些都影響了我們在某企業大廳做的一個裝置——完全由回形針組成的懸鏈結構。
注[5]:Axel Kilian,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曾在普林斯頓大學,荷蘭代爾夫特大學教學。碩士和博士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研究方向為計算機設計與建模。https://architecture.mit.edu/instructors-and-research-staff/axel-kilian
這些知識又在最近被我們轉譯成了一個研究項目:如何發展既由體塊材料組成、零件之間只受壓力,又是懸鏈結構的裝置。中心思想就是嘗試將懸掛的繩索換成有重量的實體——這是高強度泡沫塊——並將其變成一個可棲居的空間。就像把拱頂倒過來,但是這時拱心石(keystone)就會滑出整體,所以我們要將零件互相鎖釦起來。
我參考的正是埃斯科里亞爾修道院(El Escorial)[6],因為拱頂之上還有一層,所以這是一個平頂天花演變成拱頂的例子,拱心石不只有一塊——它的作用被散佈在所有組成平頂的石頭身上。
注[6]:16世紀西班牙皇室所建造的包括修道院和其他宮廷設施的巨型建築羣。
於是我們將這個原型倒置,並使其能互相水平鎖住,就像拼圖一樣,試驗證明每一個零件都能承受300磅的重力,而所有零件加起來也只有300磅重,我們便知道這個結構行得通。
從遠處看它的時候第一印象是一塊光滑的手帕,一個輕質的懸掛結構,只有靠近才發現這其實是由不同零件組成的、有重量的物體,同時拱心石完全移位使原來的位置變成了一個洞口(oculus)。想要將零件用數控雕刻機(CNC router)製造出來,我們必須將粗糙的內部面平放在機牀上,這使被切割的外部面成了光滑輕盈的表面——兩者形成了一種對立。
三個建築學院:天頂的實驗
顯然,這些細節在我們腦中都和關於建構的問題——重力、感官和懸掛現象——有關,兩張圖片中左邊是在喬治亞理工學院,右邊是墨爾本大學建築學院。我不打算將這些項目的來龍去脈都細講,而是需要快速地梳理一遍。
總之,我們從業主手中拿到的是比現在的演講廳高兩層的有着隔間的空間——曾經是工程學的研究空間,裏面停過直升機和其它機械設備。
它的品質足以作為一個建築學院,是人們將這個空間想象成公共空間的組成部分,甚至是一個令人心生敬意的地方,可能沒有英國泰特美術館大,但是它充滿想象。
問題在於那是經濟繁榮的2007年,業主給的任務書太過繁複,以至於功能空間的擁擠幾乎使項目窒息,但是2008年經濟危機的到來使業主損失慘重,整個建築的預算從1600萬美金降到了1100萬,足足低了三分之一。
但是我覺得這恰恰拯救了項目,因為這給建築的核心部分留出更多空間,我們也需要在其中懸掛一些重要空間。
圖解大概是這樣:如果地基在你上方,那麼你就可以懸掛任何元素,將地面解放出來,使其變成極其靈活的空間,對於一個設計學院來説,這個空間需要容納畢業典禮、電影放映、大尺度裝置……
想象一下,把你們的建造實驗室(fab Lab)從地下一層移到地面層,同時地面層還需要保證其他功能不變。這個龍門起重機一樣的、被懸吊的骨架就成為了工作室新的地基,將二層和三層連接起來。因為第二緊急逃生通道、工作室空間、和照明都由天花提供,而地面則可以自由地和碩士項目的空間、博士項目的空間、建造實驗室產生對話——基本上這就是一個倒立的建築。
我們在墨爾本遇到的挑戰則是打造面向未來的工作室空間——墨爾本大學為了和RMIT(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競爭,希望新建工作室空間,但他們負擔不起費用,癥結就在這裏。當我們提出一個內院類型的方案時,發現如果把原本五又四分之一英尺寬的走廊拓寬成九英尺,並將每一層的走廊空間利用起來,這樣你可能在室內隱秘地拼湊出一塊垂直工作空間。同時我們也思考更多的工作室空間和天窗光源,這就生成一個圖騰式的物體(totem/totemic object)——我們想和先例產生對話,但又和它們都不一樣。
其中一個先例是坦比哀多禮拜堂(tempietto),它的矛盾在於它是一個建築,但它是聖彼得大教堂內院裏面的一個微型建築,它並不滑稽的原因是你從一定距離看這個建築是無法理解它的尺度的[7]。
注[7]:坦比艾多類似的古典建築中柱、門等建築元素之間的相對尺度、即比例並當保持恆定,而絕對大小則比較靈活。
在路易斯·康的耶魯大學英國藝術中心裏,這個圖騰柱式的物體也和建築其它部分包括天花都沒有聯繫[8],而是掩藏了一個逃生樓梯。第三個例子我認為他是蓋裏最好的作品之一——強調了抽象的框架和內部有機形體的衝突,我們想要的結構需要兼顧天窗光源、結構和材料系統以懸吊一個工作室空間。
注[8]:英國藝術博物館中,康使用了正方形網格作為牆體和天花在平面構成中的基本單位,但是這個圓柱體完全沒有遵守這個網格。
我們打算在中庭上方做一個頂梁系統,自上而下懸掛一個工作室空間,梁的橫軸排列便於南面陽光進入——南半球的南方就像我們的北方——由巨大的木材組成,大概八九英尺高。從頂梁系統延伸出來的仍然是巨大的木材沿重力方向伸出,但不接觸地面,隨着承受張力的減少而越來越輕薄——這和建造高塔頗為相似,只是方向相反[9]。
注[9]:Tehrani的原話是”reverse tectonics”,譯者理解為是在闡述自地而起的壓力結構和懸吊的張力結構對於形式影響的相似之處。
在澳大利亞,有趣的是人們都喜歡預製建材,這個項目的80%都是在工地之外預製的,包括頂梁系統。他們凌晨四五點把準備好的材料運到工地上,兩週之內完成了工程。這種在工地之內組裝預製建材的速度創造了一種戲劇感,我只能用歎為觀止[10]來形容,我不站在評論家的角度,只是站在觀眾的角度這麼説。
注[10]:Tehrani原話為sublime。
在少有的幾個瞬間,我們會驚喜地發現建築並不是畫出來的那樣,而是一種現象學的體驗——這就是其中之一。在我眼裏,這和從頂部的木樑龐大和底部的木板輕薄之間反差有關。屋頂的材料重量和梁的彎曲相呼應——就像柱式的卷殺(entasis)[11]一樣——到了底部則變成一片片隔音板,形成地面的會議空間。
注[11]:Entasis, 建築構造中,對柱等構件從底端起的某一比例起始砍削出緩和的曲線至頂端,使構件外形顯得豐滿柔和的處理手法,是用形式表現結構的一個例子。
交錯層壓木材(cross-laminated timber,簡稱CLT)和鋼筋組成模板,澆築混凝土之後不拆卸,一起形成建築的結構——垂直堆砌的陽台廊道則嵌入結構中。一層是展覽空間,被懸掛的展覽板可以在評圖時自旋轉;二層配備工作室之外的會議桌,也可以用來做模型,三層有着連續的工作桌用來繪圖;四層則是非正式的評圖空間;再上一層則是本科、研究生和博士項目的專用空間,整個學校在豎直軸線上形成了對話。有趣的是,因為他們的工作空間不夠,所以中庭總是很熱鬧。
接下來我想講和懸吊有關的裝置,雖然風格迥異。我們經常與其它工作室和藝術家合作,這是我和一位普瑞特設計學院的服裝設計師合作的項目,她來自約旦,現居紐約。我們的想法和敍利亞難民營有關——將這些難民使用的毛毯捲起來形成柱形結構,然後通過懸掛賦予其結構剛度。我想説的是,很多小項目產生的興趣都會在之後的大項目中悄然出現,提醒我們利用大項目繼續做感興趣的事情。
屋頂系統
我們想在丹尼爾做的事情[12]和懸吊無關,但是依然和利用結構來催化整個建築的蜕變有關。丹尼爾學院教學樓是一個翻新項目,我們只是插入了一個笨重的方盒子而已。但如果你瞭解場地的話就會發現項目和景觀、地形有更大的聯繫——如何將室外地形嵌入地下的建造實驗室?如何將街道延伸到建築內部?如何調節本科、研究生項目空間和光的關係?屋頂採用層壓木材(laminated timber),在結構、照明和雨水收集方面都很有意義,我們的想法是屋頂不再繼續使用普通的柱網系統,而採用大跨度結構。兩個塔架(pylons[13])相隔100英尺,在樓兩端撐起屋頂,繼而在中央形成懸挑。如果我們用了剪刀桁架,對懸挑塔架產生的轉動慣量會過大,以至我們不得不加深地基,所以我們在其中兩個橋板——第一個和第四個——加入了一塊“拱心石(keystone)[14]”以保證其穩定性。
注[12]:Tehrani指的是他第三個建築學院的項目,多倫多大學約翰·H·丹尼爾建築景觀設計學院的教學樓。
注[13]:Pylon,建築史中常指古埃及建築中神廟的入口兩的巨大門房;現代英語中多指撐起和連接電纜的塔架,Tehrani使用此詞的時候融合了這兩個特定含義,指大跨度結構兩端的塔柱。
注[14]:Tehrani加入的中央結構受壓力,同時抵消了了剪刀桁架的轉動慣量,受力和傳統的拱心石相似,雖然並不是拱。
Nader Tehrani手繪草圖——加入一塊“拱心石”
下面的動畫可能有些長,但我們基本的想法是不只滿足LEED綠色建築評分的標準,還想和學生教員們關於生態建築的研究相結合,一起在這個建築上探討環境和景觀設計的問題。這不僅和整幢樓的總耗能有關,還和人們抵達建築需要消耗的交通能耗有關——是步行、乘電車還是騎行呢?我們也考慮了木和混凝土結構的剖面細節——1)如何實現自然對流、如何使其更高效、如何除去污染物;2)在允許自然照明的同時,人工照明如何在需要的時候起作用,而不需要的時候則關閉節能;3)如何用屋頂的形態收集雨水以澆灌周圍的綠地。
我們把圖交給學院,他們的結論是我們做不了這個結構,這並不出乎意料,因為北美地區的承包商覺得任何(稍微複雜一些的)東西都造不出來。我之前説過,這其實就是一個直紋曲面,利用混凝土澆築表面完全可行,就像這個費利克斯 · 坎德拉[15]的先例一樣。
注[15]:Felix Candela,西班牙-墨西哥雙國籍建築師,以其水泥結構的創新為世人所知。
我們知道這樣澆築有難度,所以把施工圖和模型都寄給了承包商,但是他們就是不願意嘗試,一口咬定説造不出來。一次我在去墨爾本出差途中在機場給工作室打電話,説既然他們這麼肯定,那我們就自己造一個大樣給他們看看。於是我們將曲面分成輕量型鋼結構骨架,每一塊模板都是線性的,它們每一端的排列關係也是線性的,其實紙板作材料都是可行的。但我們找到了一種輻射板(radiant panel),這樣可以和天花之上的製冷系統結合起來,可以和地面中安裝的供暖系統相呼應。
這樣的整合系統預計可以為建築省下70萬美金的開銷,最終也的確是這樣。這樣一來承包商就找不到藉口了,把整套系統轉譯成了鋼結構。這讓我們再次思考:製作一個表面有何意義?什麼時候應該捨去表面,展示背後的結構?我們曾出過一套方案——只在大廳的天花鋪上表面,而其它角落都讓鋼結構紋理裸露出來,形成一種表達。但是這方案沒被接受,因為施工已經開始了。已有樓板的利用效率也是系統的一部分,為了讓天花的底部呈水平,我們在底部和頂部之間加入了用回收皮艇加工成的塑料,埋在混凝土中以減輕重量,最終我們在這個直紋曲面上塗了石膏,使它視覺上光滑起來。總之,屋頂系統就是結構的層層疊加,形成建築的輪廓,也表達了建築性能。
無序建構
講座接近尾聲了,感謝各位的耐心。我們所有的作品都是關於建構模件的積累,幾年前的韓國光州雙年展也不例外。我們設計了一個複雜的張拉整體式結構(tensegrity),畫了很厚的施工圖,提前一週上交給了組委會。
他們非常喜歡,説:“很想做這個,但如果你不介意的話,能不能把所有的張力結構替換成壓力結構”,我們在韓國有過類似經驗,能夠理解他們的訴求,所以回答:“給我們多一週時間重新設計”。我們和門把手供應商合作——使用回收過的大件把手作為模件,不能再像其他項目一樣用標準的方式懸吊結構了,而是使用密集的模件堆成柱子。
柱頭將頂端的重量重新分佈向下傳遞,就像蘑菇一樣,而亭子頂部正好相反,只要有足夠的桁架保證其側向穩定性,模件的密度應當越低越好。我們跑了一些算法,得出了正確的密度和框架,在此框架之內可以靈活組合,這樣一來,我們畫出的位置不一定是這些門把手最終的位置。
地下有地鐵系統,地上有樹木,這個以密度為中心的結構系統靈活地繞過這些路面上下的基礎設施。我們根據樹木的位置在頂部開了兩個洞,為了視覺效果又開了一個。我們沒有去過現場,但是結果證明建造效果比想象的好很多,這樣無序的建構和之前所有的項目都大相徑庭。
混凝土的嘗試
我以這個建築結尾,因為它意義重大。混凝土建築對於你們來説習以為常,但在美國我們很少用混凝土。我們接到委託要在法國南部做一個房子時,第一次體驗這種“液態”的建構,之前關於木製、金屬建材的知識體系在這裏已經不管用了,因為混凝土要麼遵從模板的形態、要麼和後期雕刻有關——就像保羅·魯道夫(Paul Rudolph)和柯布的作品一樣。
我們想讓房子成為已有景觀的一部分,借用不規律的地形將房子和中庭在平面中進行扭曲,使得朝向地中海景色的視野最大化,並形成向山上樹林眺望的極佳視野。
我們借傾斜的地勢將生活空間和就寢空間放在不同的兩層,而泳池和中庭則在兩者中間。通過屋頂的形變將向西的視野也敞開來,體量在東南角以鋭角相交,解放了地面空間,流線從這個角下方穿過到達泳池,穿過客廳來到房子北面的山坡。
現在展示的立面其實並非立面,而是一根結構梁。泳池旁邊的牆壁經過延伸和懸挑迴廊裏的梁相交,同時被一個東西方向的、同樣是懸挑的樓梯支撐着,所以其實這就是兩個體量在空中呈T形相交形成懸浮。
這個房子其實和案例研究之家[16]沒什麼不同,邊緣都是玻璃幕牆,但是我們沒有在長廊的短軸截面上做文章,而是在長軸上向西面開窗。
注[16]:案例研究之家,美國《藝術與建築》雜誌在二戰後贊助的美國住宅建築實驗,邀請知名建築師設計住宅模型以應對大批老兵回國的住房需求。
同時我們也在考慮使用混凝土究竟意味着什麼,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混凝土成形的模式有兩種——第一種模式是藉助數字時代的技術優勢,將複雜的模板用數控工具雕刻出來,甚至使用布料作為模板實現表面的起伏,這樣我們可以實現房子內表面平滑到外表面粗糙的過渡,和周圍的山石形成對話。我們很清楚這種像素化的表面只是一個視覺系統,沒有其它任何性能。
另一個模式是通過調整混凝土中砂石的大小,使每一塊水泥板中的石塊運來越多,而水泥越來越少,最終完全和地表融為一體。這的確遵從了視覺規則,但結構上它也是一面從房子延伸出來的擋土牆。
最後我以一個小發現結尾,多年前我去羅馬不理解為什麼地面上的鵝卵石按照拱形排列,直到最近我才明白這其實表達了人體運動在地面留下的印記。兩千多年後,當我們在鐵路設施上塗鴉時,這仍是人體運動的表達——人們將身體向建築物的一面傾斜,留下自己的印記。有趣的是數字革命正在消除這些印記,首先它可以消除模塊之間的縫隙——磚和板材交接處;其次它甚至有可能打印更微觀的結構——防水、保温層也許可以成為打印的目標。
這是令人激動的時刻,因為這可能會徹底推翻我今天所説的一切。謝謝大家!
問答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