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國正在優雅衰落?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40545-2019-11-28 09: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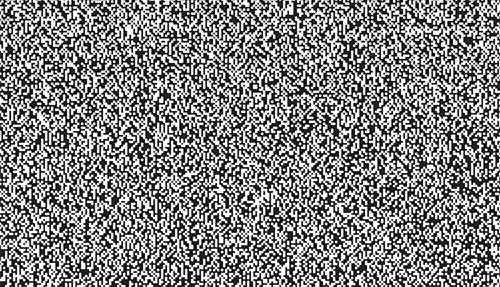
英國大選在即,英國首相鮑里斯再度宣稱,英國將在聖誕前完成脱歐。從 2016 年開始的“脱歐”一直拖延到了今天。今天的英國在經歷着什麼?脱歐為為什麼如此艱難?在今天推薦的這本書中,我們也許能找到答案,而且,它很可能會是你下次英國之行的參考書。
大英帝國正在優雅衰落?
撰文:沈律君
就在一個月前,我和我的同事們因為工作,去了一趟英國。抵達的當晚,我們走過議會大廈,它的一多半,包括大本鐘在內都被腳手架包圍着,面貌並不真切,遠不及一街之隔,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旁空地上的那一排旗幟。那幾乎是一片旗幟牆,英國國旗和歐盟盟旗或纏或掛,是如此密集,以至於旗幟後面的旗杆幾乎看不到了。
米字旗和星環旗比着要迎風飄揚,兩種旗幟下面站着彼此的支持者,他們像衞兵一樣守在那兒,兩方沒有交談,也並不急於宣發傳單,只是守着,站在各自的旗幟旁。在旗幟牆後面,空地上有十幾頂帳篷,看來他們打的是持久戰。
當我走遠了一點再回頭看,米字旗顯然佔了上風。當然也可能只是它飄起來顏色比較鮮豔。無論如何,在抵達的第一天,我意識到了脱歐問題在這個國家佔據着的位置。英國人為脱歐專門發明了一個詞,Brexit,是不列顛(Britian)和退出(exit)的合體。在此後的幾天,它反覆出現在電視中和街邊的海報上,儼然頭等大事。
看到《英國:優雅衰落》這本書之後,我有些後悔,沒有在出發前就讀到它。作者桂濤是新華社倫敦分社的時政記者,這一身份讓他得以遍行不列顛,和各行各業的人交談。他們的故事像是今天英國的一個切片,在桂濤乾淨簡練的行文下顯微出來。
從名校校長到議會議員,老記者到大學生,從軍情五處負責人到恐怖襲擊受害者,還有二手書鎮上的國王,這些故事都圍繞着一個共同的主題:衰落與脱歐。
衰落。就在我們到達的時候,倫敦有 15 萬無家可歸的人,特拉法加廣場東側每天都排着領救濟餐的長隊,旁邊就是流浪漢們的帳篷。18 年的民調中,只有六分之一英國人相信明天會更好。
▲特拉法加廣場東側,黑壓壓的人羣都在等待救濟餐。
然而,正如桂濤在書中所説:今天,“世界仍然享受着‘衰落的英國’不斷留下的遺產:郵票、火車、青黴素、互聯網、標準時間、英語、議會民主制、莎士比亞、沖水馬桶、007、唐頓莊園、哈利波特……”這是大英帝國在百年衰退中的餘暉和新光。對於這種“衰而不滅”,桂濤在自由民主黨原黨魁克萊格那裏得到了回答:英國正在優雅衰落,但脱歐會讓英國遭受“二戰”以來最大的危機。
關於脱歐,桂濤在大不列顛的各處找到了完全不同的答案。這再次印證了這個看似孤懸大西洋的的英倫三島內部的複雜。我們知道今天的聯合王國是由四個部分組成的: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而這其中,唯有北愛爾蘭不是以國家身份加入的聯合王國,它的存在感也是聯合王國裏最低的一個。
在來英國的旅行者眼中,“北愛”是偏遠的,同時也是危險的存在。它和英格蘭不處於同一個島,需要再穿過一次海峽才能到達。一百年來不斷的衝突讓這裏和巴格達、波斯尼亞一起成為旅行危險區。1969 年以來,英國一共發生過 3000 次政治謀殺,其中大半在這裏。“衝突最嚴重的 1972 年,平均每天就有超過30起槍擊與爆炸事件。”
幾乎無法想象這一切發生在被我們定義為理性、秩序和民主的英國。在北愛的首府貝爾法斯特,甚至依然矗立着當代的“柏林牆”——貝爾法斯特和平牆。它隔離着城市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今天世俗化的世界裏,他們依然“被迫”懷着深仇大恨。
新教徒忠於聯合王國,天主教徒則致力於北愛和愛爾蘭共和國合併,統一整個愛爾蘭。唯一“愛爾蘭共和軍”和“統一派”的暴力對抗與流血持續了幾十年的時間。90 年代至今,政黨政治已經幾乎取代曾經的恐怖和暴力,成為今天北愛人抗爭的主要形式。但脱歐讓這一得來不易的温和抗爭有加劇的危險。
北愛和愛爾蘭的邊界是開放的,今天人們在兩地自由穿行。而一旦脱歐成功,這裏很可能會重新樹立起圍牆,而那將會是英國和歐盟國家的第一條實體邊界線。
這樣一來,偏遠的北愛就變成了脱歐的關鍵點以及最容易觸發的痛點。宗教衝突和今天的族裔與政治變遷相互聯繫,新的抗爭會以什麼樣的形勢出現?而這個抗爭的敵人又會是誰?
“從來沒有一個海島像大不列顛島這樣攪動了人類近代史”,這是這本書的第一句。而在今天的時間節點上,它正在攪動我們的當下。
《英國:優雅衰落》
桂濤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
貝爾法斯特、德里:牆與界的詛咒
在北愛爾蘭出生、長大的人,一定不會太過於樂觀。
—— 愛爾蘭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謝默斯·希尼
除了教派衝突導致的恐怖襲擊外,北愛爾蘭在歷史上似乎從來就沒有進入過世界輿論的中心。這片面積比北京略小的土地總是處於一種矛盾而尷尬的境地。
困惑
北愛(北愛爾蘭簡稱)離倫敦飛行距離只有一小時,但距離英國的政治中心卻太遙遠。沒人知道英倫三島最大的淡水湖、最好的高爾夫球場和最棒的油炸食物都藏在這裏,英航的乘務員甚至也會偶爾記錯,以為這裏與倫敦有一小時時差。它有自己的首府、議會和政府,但其他國家卻無法在此設立使館;它有自己獨立的法律體系,可以發行自己的郵票,卻沒有自己的貨幣;它在政治概念上屬於英國,在地理位置和名稱上則更接近於同處一島的愛爾蘭共和國。對北愛的定義本身就足以讓人困惑。各種旅遊指南或是政治學詞典在談到北愛時總會給它不同的稱呼,而這些稱呼背後隱藏的是書籍編纂者們對它的不同定性以及迥異的政治立場。
有人稱北愛為“國家”,理由之一是它有自己的國家足球隊,隊員們還曾在 2016 年歐洲盃足球賽中淘汰世界冠軍德國隊後,興奮地揮舞北愛“國旗”——一面白底紅十字旗,十字中心有白色的六角星和一個紅手掌。六角星代表北愛的六個郡,紅手掌則源於古老傳説,説的是一個勇士在賽跑中自斷手掌並扔向終點愛爾蘭島,好讓自己身體的一部分率先到達。從帶有強烈民族自豪感的傳説提煉出的紅手掌符號,被視為最能代表北愛、最能凝聚這裏各政治派別的符號。
▲北愛爾蘭旗幟
有人稱北愛為“省”,因為它的地理範圍確實大致曾是愛爾蘭歷史上的四個省份之一,名為阿爾斯特。如今,以阿爾斯特命名的地方包括北愛的國家博物館、歷史最悠久的銀行、一座知名大學、一支目前已不復存在的武裝力量,以及難以計數的小旅館、啤酒館、政治團體和橄欖球隊。北愛政府還曾一度考慮用阿爾斯特作為自己的官方名稱。
有人更願意用方位來指稱北愛,把它叫作“愛爾蘭之北”,或者乾脆就叫“北部”。他們更願意強調愛爾蘭島南北兩部分之間的聯繫,畢竟這兩者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時間比北愛和不列顛島在一起的時間要長得多。
更極端些的人稱北愛為“殖民地”,因為它直到 400 年前才完全被英格蘭控制,在 200 年前才作為整個愛爾蘭島的一部分正式併入英國,在 100 年前才正式確定下和南部的邊界——今天的愛爾蘭共和國與英國的邊界。在此後絕大多數時間裏,愛爾蘭島上都有要求脱離英國獨立的呼聲。特別是在近 100 年,衝鋒槍與汽車炸彈讓這種呼聲響徹世界。你可能都想象不到,在離我們如此之近的 2005 年至 2015 年這 10 年裏,北愛還發生了 1243 起槍擊和爆炸事件以及超過 1.5 萬起教派衝突事件,26 人死亡、851 人受傷、436 人被以與恐怖主義相關的罪名起訴。在衝突最嚴重的 1972 年,平均每天就有超過 30 起槍擊與爆炸事件。衝突雙方在回答同一個政治問題——北愛是否要結束英國人的殖民,成為獨立國家或併入愛爾蘭共和國?
對北愛最保險的稱呼是“地區”。它被國際社會認可的正式身份是“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的一部分,但和聯合王國其他三個部分——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不同,北愛以地區而非國家的身份加入。因為愛爾蘭南方信奉天主教為主的 26 個郡組成了新的獨立國家——愛爾蘭自由邦(即現在的愛爾蘭共和國),北方信奉新教為主的 6 個郡則作為聯合王國的一部分留了下來。那之後,北愛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是效忠於愛爾蘭共和國還是效忠於英國王室”的問題上衝突不斷。20 世紀 60 年代起頻發的暴力事件更是讓愛爾蘭問題成為對英國政治體制最突出的挑戰。
北愛在歷史上和中國偶有交集。1843 年成為首任香港總督的璞鼎查是北愛人,晚清擔任中國海關總税務司半個世紀之久的羅伯特·赫德也出生在這裏。中國街頭的郵筒刷成綠色而非倫敦街頭的紅色就和作為中國現代郵政推動人的赫德有關,他選擇了給中國的郵筒塗上代表愛爾蘭凱爾特文化的綠色而非代表英國的紅色。今天在貝爾法斯特的一些天主教徒居住區,還能看到紅色的郵筒被人用油漆塗成綠色。
外人很難理解,為什麼北愛的天主教徒與新教徒視彼此為仇敵?這種仇恨對北愛及英國的未來意味着什麼?我正是帶着這些問題來到北愛的。
北愛有一種魔力:它總能讓你的旅程無法輕鬆愉快。在我印象裏,這裏總在下雨,總是即將天黑。其實這麼説並不公平。温帶海洋性氣候讓這裏只在冬天多雨,高緯度也讓這裏夏天到 8 點多才天黑,但也許是每年漫長冬季裏低温、冷雨、長夜的組合更讓人難忘吧。
▲貝爾法斯特
厚重悲慘的歷史也重新定義了北愛的各個景點:貝爾法斯特曾與貝魯特、巴格達、波斯尼亞一同被認為是旅行者們應該避免的危險“B 地區”(它們的英文名同以該字母開頭);貝爾法斯特市中心的歐羅巴大酒店曾經常出現在《新聞聯播》的國際報道中,尋求實現愛爾蘭統一的愛爾蘭共和軍總是在這裏設置炸彈,讓它成為全歐洲挨炸次數最多的酒店;貝爾法斯特港口的泰坦尼克博物館是這艘被詛咒的巨輪誕生的地方,博物館裏的電腦復原出巨輪當年的奢華舞池,玻璃展櫃陳列着當年船上乘客的家書,它們都讓泰坦尼克號撞上冰山的那一刻看起來更具悲劇性;熱播劇《權力的遊戲》在北愛取景最多,臨冬城靜謐灰暗,北境森林幽暗邪魅;大西洋邊的“巨人之路”(由火山熔岩冷卻凝固形成的四萬多根玄武石柱排列組成、綿延數公里的北愛知名自然景點)也在灰色海水的襯托下顯得恢宏悲壯。
和解
我找到了曾經在和平牆兩側為各自的政治理想作戰的老戰士皮達爾·韋蘭和努爾·拉格爾。
韋蘭是愛爾蘭人、天主教徒,年輕時是愛爾蘭統一運動狂熱的支持者。在 1977 年的一次天主教徒武裝力量組織的遊行中被捕,他記得在警察把自己按倒前,他剛剛砸碎了一間房子的窗户。拉格爾是新教徒,年輕時隨叔叔參加各種“政治活動”——打砸搶、拿着一把馬格南左輪手槍追殺“北愛獨立分子”,目的是捍衞英國在北愛的領土。拉格爾年輕時的夢想是成為職業足球運動員,還曾有機會進入阿森納隊,但狂熱的政治理想讓他在1982 年被捕。不久,妻子和牢房裏的他離了婚。
韋蘭和拉格爾生下來就被貼上兩個敵對陣營的標籤,但他們很像。他們都是 60 歲,都曾以謀殺未遂等罪名被關押了 16 年,如今又都在一個關愛北愛刑滿釋放人員的公益項目幫助下,受僱於旅遊公司,為遊客介紹和平牆。他們都不願多談自己在獄中的生活,只説在那裏認識了不同宗教信仰的犯人,但出獄後就沒再聯繫。他們對自己年輕時的所作所為都曾認真反思。他們先後登上同一輛大巴,車從牆的一邊轉到另一邊時,也是他們的交接之時。
他們會彼此打個招呼,然後拿着麥克風開始講述當年的歷史,將各種教派名稱、歷史事件一股腦兒地拋給前來獵奇的遊客,並將責任推給“牆那頭”。
▲貝爾法斯特和平牆
在北愛,每段關於歷史的敍述都有至少兩個版本,它們來自不同派別。我的採訪本上記下了韋蘭和拉格爾的話。
韋蘭:“英國人總愛用給你‘定罪’的方法來解決衝突。”“在道德上,我後悔當年的行為,但在政治理想上我並沒有錯。”“拆牆?可能至少還需要 15 年吧,等對(動盪)那些年的記憶消失了吧。”
拉格爾:“我不認為這是什麼‘和平牆’,它是安全隔離牆。”“這牆是為了阻止牆那頭愛爾蘭共和軍對新教徒的襲擊而建。”“(對愛爾蘭人)憤怒?我沒有憤怒,我為我的政治理想獻身,這是我的選擇。”“最好別拆牆,至少現在不行,大家都習慣了有牆的生活。”我還記錄下一段與拉格爾的問答,我的問題似乎讓他有些不高興。
“你現在有幾個天主教徒朋友呢?”我問他。
“你有幾個朋友?”他問。
“我?朋友?幾百個吧。”我沒想到他會反問我。
“他們之中有幾個天主教徒?幾個新教徒?幾個佛教徒?幾個穆斯林?你會這麼給他們分類嗎?”“但是,你剛才提到在你小時候只有過一個天主教徒朋友,所以我才這麼問。”我試圖説明提這個問題的前因後果。
“聽着,現在在北愛,沒人這樣區分朋友。”拉格爾説,“但我可以回答你的問題——兩個。”
我沒有繼續追問,至今也不知道拉格爾是不是在開玩笑。在北愛,像韋蘭和拉格爾這樣在“動盪時期”被關押過的人今天還有 2.5 萬。雖然仇恨短期內仍難以消失,但北愛也不會輕易再回到此前教派武裝衝突的混亂局面。30 年內亂導致超過 3600 人喪生、3 萬人受傷,這對人口不到 200 萬的北愛來説刻骨銘心。自從 1998 年《貝爾法斯特協議》簽訂後,北愛自治政府、愛爾蘭政府和英國政府在美國的壓力下實現和解,和平成為絕大多數人的共識。
德里
從貝爾法斯特到北愛第二大城市德里,車程兩小時。如果這世界上有什麼地方最能讓人覺得“人間的一切爭執都是名詞之爭”這句話有多麼正確,那一定就是這裏了。德里這名字就是分裂的產物。英格蘭在 17 世紀完全佔領愛爾蘭後,德里曾被改名為倫敦德里,以顯示它與“新東家”的密切關係。但此後,反感威斯敏斯特統治的北愛天主教徒仍稱呼它為德里。2015 年,倫敦德里市議會投票,將這座城市的名字重新改回德里,而親倫敦的北愛新教徒則堅持稱呼它為倫敦德里。“名詞之爭”讓德里的商家有些左右為難,他們不得不在自己的廣告招牌上畫蛇添足地寫上“德里/倫敦德里一日遊”或是“德里/倫敦德里最好吃的烤肉”之類的話,這也讓德里乾脆被一些人稱為“斜槓城市”。400 年前,英格蘭的新教徒向愛爾蘭遷徙,並建立種植園,德里就是因種植園興起的城市之一。
▲倫敦德里當地的指示牌,“倫敦”二字被塗抹
在這座被城牆環繞的小城,“牆內”和“牆外”是當地人言談中經常使用的地理座標。我們從七個城門之一的“屠夫門”入城,因在北愛的“動盪時期”,德里就曾是愛爾蘭共和軍襲擊的重點目標。它就在英國與愛爾蘭共和國的邊境旁,7.5 萬居民中四分之三是天主教徒,要求結束英國“殖民”、與愛爾蘭共和國統一的呼聲也最強。1972 年的“血腥星期日”事件就發生在德里,當時駐守在這裏的英國傘兵向正在遊行的市民開槍,殺死 14 人。“血腥星期日”被約翰·列儂和 U2 樂隊都寫進歌裏,成了德里最不堪回首的一天。
小城街頭建築物上的大幅政治塗鴉畫迅速把我帶回 30 年前戰火紛飛的德里。塗鴉畫上有德里最年輕的議員在號召大家為爭取民權奮鬥,有“歡迎來到自由德里”的政治口號,還有德里第一個在教派衝突中遇難的孩子。幾十年後,當《貝爾法斯特協議》簽訂時,人們在那個孩子的畫像旁添上了一隻代表新生的藍蝴蝶。
德里市中心的公園和標誌性的大橋均以“和平”為名。那大橋罕見地建成蛇形,從新教徒聚居的一岸彎彎曲曲地通向天主教徒聚居的對岸。德里人開玩笑説,橋面不建造成直線是為了防止兩派面對面過橋時朝對方扔石頭。
我來德里是為了去看看那條邊界。英國與愛爾蘭共和國之間的邊境線從德里城外穿過,北愛衝突雙方曾因這條割裂愛爾蘭島的邊境線而戰,今天英國的“脱歐”也再次讓這條邊境成為全世界最受人關注的界線之一。
自從 1921 年愛爾蘭南部地區選擇獨立後,愛爾蘭全島設置“共同旅遊區”,英國公民與愛爾蘭公民可自由往來。自那以後,邊境線上沒有檢查證件的崗哨,只在一些地方保留了幾個攝像頭。
但在“動盪時期”,邊境成為教派衝突的前沿,邊境線上一度出現崗哨與鐵絲網,並隨即成為襲擊對象。正是在貝爾法斯特和平牆開始修建的 1969 年,德里邊界線上的二層關税辦公樓不得不在日益頻發的暴力衝突中被迫關閉。邊界地區成為無人區,兩側分別是英國與愛爾蘭共和國的駐軍。《貝爾法斯特協議》簽訂後,英愛邊界再度開放,這常常被視為北愛和平進程取得成功的重要象徵。
在非洲,我曾步行穿越多哥和加納的邊境線,被掛着槍的加納軍人勒令刪去相機裏一切關於邊境線的照片。那個中尉在檢查完我的相機後又坐回露天的木桌前,繼續在我遞過去的護照上蓋章、簽字。木桌上的小收音機大聲地放着流行音樂,上面盤旋的蒼蠅似乎都在和着節奏跳舞,那景象幾乎就是好萊塢電影裏的畫面。我期待在德里的邊界再有奇遇。
司機倒數着“三、二、一”,車已經從英國一側進入愛爾蘭共和國一側,周圍的車輛都沒有減速。在司機的提示下,我才發現,地面上的交通標線從英國境內的白色變為愛爾蘭共和國境內的黃色,路旁的限速提示牌也從“限速 60 英里”變成使用歐盟計量單位的“限速 100 公里”。手機短信倒是忠實地提示:“您已進入愛爾蘭共和國。”再仔細看,一個“歡迎進入北愛爾蘭”的路標上的“北”被人用顏料塗掉,意在表達“北愛爾蘭是愛爾蘭共和國的一部分”的政治訴求。
僅此而已,這就是英愛之間的“軟邊界”。許多德里人每天都要幾次往返於邊境兩側的居住地和工作地。唯一麻煩的是要在口袋裏裝上英鎊與歐元兩種貨幣,便於在邊界兩側消費,但信用卡早已讓這不再是問題。目前每月有 17.7 萬輛貨運卡車、185 萬輛小客車和 90 萬人次要跨越這條隱形的邊境線。
▲英愛邊境
“脱歐”帶來了新問題。愛爾蘭共和國是歐盟成員國,因此在 2019 年 3 月英國正式退出歐盟後,這條邊境線也將從目前的國境線變成“歐盟區與非歐盟區”的界限。在“脱歐”後如何處理這條邊界是英國與歐盟談判的重點與難點之一。英國政府曾多次表示,英國將在“脱歐”後退出歐洲共同市場和歐盟關税同盟。
這意味着如果英歐之間未能達成新的自由貿易協議,那麼英國與愛爾蘭共和國的邊界註定將從目前貨物與人員自由流動的“軟邊界”,變成需要對進出歐盟人員和貨物進行核查與徵税的“硬邊界”。一旦這樣的情況出現,這將是英國曆史上第一條與其他歐洲國家的陸上硬邊界。
但德里人都知道,一旦這樣的邊界出現,邊界上任何代表英國的符號——崗哨、身着制服的邊檢官、關税辦公室——都有可能激起德里天主教徒的不滿,並引來針對它們的襲擊,就像在“動盪時期”那樣。但沒有實體設施又將如何核查往來穿越歐盟邊境的人員、如何向進出歐洲共同市場的貨物徵税?這是個兩難的選擇。
邊界“軟”的時候,居住在邊境線兩側的愛爾蘭人根本不會注意到它的存在。一旦“硬邊界”出現,它將帶來令人尷尬的問題:一家農場就建在這條邊境線上,農場上的牛羊和它們的放牧者都將面臨出入境問題;汽車在愛爾蘭島上主要的交通動脈 N54/A3 公路上行駛,要在這條曲折的高速公路上四次穿越邊境線,在英國與愛爾蘭共和國兩國間來回。
支持北愛與愛爾蘭共和國最終統一的新芬黨成員、德里的英國議會下院議員伊麗莎·麥克卡利昂告訴我,大約五分之四的德里人在前年的“脱歐”公投中都選擇“留歐”,就是因為擔心退出歐盟可能帶來這樣的邊境問題。“脱歐”將讓北愛爾蘭的最終歸屬問題再次被提上政治議程,並將導致“愛爾蘭統一”公投出現得可能比人們預想的更早。但她也承認,北愛再次出現 1998 年以前的大規模衝突已不太可能。要求北愛脱離英國的“民族派”已經作為與“統一派”平等的政治力量出現在北愛政壇上,公開表示希望“愛爾蘭統一”已經不再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了,不再需要用生命來爭取。
35 歲的麥克卡利昂年輕靚麗,她的姓是典型的愛爾蘭人姓氏。
她從十幾歲起就為了“愛爾蘭統一”的政治理想奮鬥,曾當選德里市長。麥克卡利昂像每個德里的母親一樣,每天要幾次穿越英國與愛爾蘭共和國的邊境,接送三個孩子上學,為的是讓他們去南邊的愛爾蘭語學校讀書。
我問麥克卡利昂:“如果‘脱歐’真的製造出一條‘硬邊界’呢?”“我會像愛爾蘭民族的每個人一樣,去為反對它而戰鬥。”她回答。
“不惜代價?”“不惜代價。”“你真的覺得這值得嗎?”我有點懷疑。
“值得,那是為了我的孩子們不再需要像我一樣為愛爾蘭的邊界而戰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