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巴黎警察全城搜捕的他,卻拯救了上萬人的命_風聞
未读-未读出版社官方账号-未读出版社官方账号2019-12-07 15: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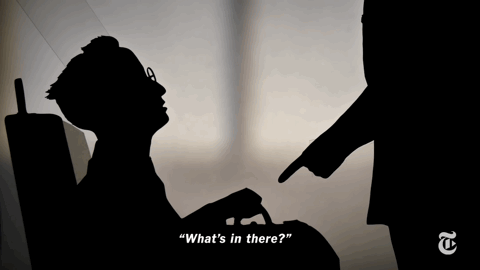
如果有人對你説他靠“造假證”救人,你會作何反應?
是不是會微微一笑,暗自思忖這八成是個江湖騙子無疑?不瞞你説,我也是這麼認為的——直到我認識了阿道夫 · 卡明斯基。
以畫家的身份作為掩護,和隊友們“隱身”在巴黎街道上的一間狹窄小閣樓裏的他,用舊貨店裏找來的廢棄材料,造出高度精密的儀器,以紙張、墨水、煙斗……為救人武器,他造出的每一個假證件,都讓一個又一個猶太人生命得以延續。
他是當時所有警察都在竭力搜尋的偽造者,更是所有猶太人生命的守護者。
深讀第83期,為你帶來的就是這位“隱身大師”的故事,一起見證這位曾經的小毛孩,如今的慈祥老爺子,是如何在三天之內救出300個孩子的。
我當然知道,一直以來所有警察都在竭力搜尋巴黎的偽造者。我還知道這是因為我找到了大規模偽造證件的方式,這些證件早就遍佈整個北方地區,甚至遠及比利時和荷蘭。我最大的優勢在於,警察們可能一直都在找一個擁有機器的“專業人士”,有印刷機和木漿廠。他們肯定不會猜到,原來他們一直在找的那個偽造者,不過是一個小毛孩而已。
很明顯且幸運的是,我不是一個人。我們實驗室的頭兒叫薩姆 · 庫傑爾,二十四歲,大家都叫他“水獺”。上一個負責人是勒妮 · 格盧克,同樣二十四歲,代號“睡蓮”,是一名藥劑師,後來離開這裏去護送孩子們和處理邊境前線事宜了。實驗室的成員還有在藝術學院就讀的蘇西 · 席德洛夫和赫塔 · 席德洛夫姐妹倆,她們一個二十歲,一個二十一歲,憑藉着辛勤的工作和永不消減的幽默感為實驗室做出了巨大貢獻。以上就是傳説中法國猶太人總工會的神秘分支“第六部”偽造證件實驗室的人員配置。
我們假裝成畫家作為掩護。偽造證件的實驗室在聖佩雷斯街十七號的一間狹窄的頂層小閣樓裏,這裏已經被改造成了一間藝術工作室。我們會在旁邊放上幾支畫筆,好讓人以為這些瓶瓶罐罐都是繪畫用的顏料和溶劑。
為了升高工作台,我在兩張桌子底下胡亂拼湊了數十個抽屜架。這樣,我們就能在沒人察覺的情況下一次性晾乾大量證件了。還有幾面牆上掛滿了我們匆忙完成的畫作,在這些畫的背面藏着我們偽造好的證件,直到能把它們交給聯絡人。
我們每個人都遵循着一個固定的日程表和辦公時間,以免引起看門人的懷疑,而且時不時地,我們還會帶着畫家專用的調色板過來。所以,沒有一個鄰居過來問我們屋裏為什麼會有化學品的氣味。查電錶的人也是如此,每次他進來都會恭喜我們完成了新的畫作。當他的腳步聲消失在樓梯盡頭時,我們總會爆發出一陣大笑。要知道那些都是亂畫的,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我們為所有人服務。訂單源源不斷地湧進來,數量越來越大。
其中有來自巴黎的、來自法國猶太人總工會的、來自南部地區的,還有來自倫敦的。我們不得不保持一定的工作節奏來應對這幾近無法控制的工作量,有時甚至一個星期要做五百個證件。
一般情況下,由水獺和我負責聯絡那些下訂單的人。我記得水獺看上去也很天真無邪,和我一樣。這是我們最好的偽裝。通常,我們會把見面地點安排在巴黎一些繁華的地段,最好是和一個女人接頭,這樣見面時就可以假裝是正在約會的情侶。一旦感覺被監視了,兩人就會深情地對視。當我們分開時,彼此都知道接下來的任務是什麼。
但有一次和我見面的不是我虛擬戀人中的任何一個,而是馬克 · 哈蒙,綽號“企鵝”,他也是法國猶太童子軍的一員,當初就是他把我招進了抵抗組織。
我明白,如果是企鵝親自來的話,那就説明問題非常緊急,他已經等不及讓組織裏有空的女成員來了。
“昨天倫敦電台給我們傳來了一些好消息。德國軍隊正在全線撤退,而且從現在起,所有北非軍隊都站在我們這邊。不過問題是,納粹決定加速清除猶太人,正準備在整個佔領區內實行一次大型圍捕。三天之後,巴黎的十個兒童福利站將會同時遭到突襲。我給你準備了一個清單。我需要上面的一切材料:定量供應卡、出生證明、洗禮證明,還有協助孩子穿越前線的大人的身份證、命令單,以及所有人的通行證。”
“有多少?”
“你是説多少個孩子?……超過三百個。”
**三百個孩子。****這意味着要準備超過九百個不同類型的證件,而且是在三天之內!**這根本不可能。一般來講,每天收到的訂單數量有三十到五十個,有時候會多點。此前我也面臨過巨大的挑戰,但這一次數量實在太過巨大,我震驚了。
和企鵝的會面結束之後,我第一次害怕起失敗來。在這之前,我總能通過積累的各種知識,想出一些神奇的辦法來解決技術問題。但這一次我們要的並不是解決方案,而是巨大的數量,而我清楚當時自己已經是滿負荷運轉了。一天的時間不會縮短,但不幸的是,它也不會延長。沒時間多想,我得先去雅克布路造紙:緊緻的、好用的、密實的或精細的,有紋理或沒紋理的——根據證件原本的質地來準備。我必須得抓緊,倒計時已經開始,比賽的槍聲已經打響。這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與死亡的抗爭。
我抱着裝滿空白證件的公文包氣喘吁吁地趕到實驗室時,水獺、蘇西和赫塔已經在那兒等着了。令我驚訝的是睡蓮也在——因為有別的任務,最近很少能在實驗室看到她。他們都看向我,表情無比震驚。他們告訴我説已經接到了通知,畢竟事關三百個孩子——這也是睡蓮會出現在這兒的原因,她是特地來幫我們的。除此之外,水獺還剛剛收到了一份來自移民工人組織的訂單:他們需要給匈牙利小組的成員準備證件。所有人都以詢問的目光看着我。他們想知道:我們真的能滿足所有需求嗎?為配合當前這種緊急的情況,我把一個裝滿空白證件的紙箱子放在桌子上,用行動給出了一個信號。
“孩子優先!****”睡蓮補充道。
實驗室裏馬上變得一片忙碌:睡蓮負責用切紙機把紙板裁成卡片,蘇西填色,赫塔用筆和打字機填寫文字。只有水獺,一般情況下,他從不參與制作,只負責管理所有行政瑣事,像遊魂一樣轉來轉去,茫然無措。
“如果你想幫忙,那就從蓋章和簽字開始吧。”
於是他立刻投入工作。而我正用一台自己造的機器把紙張做舊:塞進去一些灰塵和鉛筆芯,然後轉動把手,讓紙張看起來又髒又舊,以免看上去太新,或者像是剛從打印機裏拿出來的一樣。屋子裏慢慢開始瀰漫起一種化學用品混合着汗水的氣味。在不同的角落裏,我們切紙、裁邊、蓋章、上色、打字,在這個簡易文書工廠裏埋頭苦幹。
我們把做好的假證件放到鏡子背面和底部可拆卸的抽屜裏,塞得滿滿當當。雖然在內心深處我們都知道這個目標很難完成,但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不把它説出來。一切都取決於我們的意志力。畢竟,除了樂觀,我們一無所有,這也是我們繼續前進的唯一動力。
天黑以後,所有人都回家了,我朝位於雅克布路的實驗室走去。即便有睡蓮和水獺的幫助,我們一整天也才完成了不到四分之一的數量——在這種情況下,我怎麼能睡覺?按照這個節奏,我們或許能完成孩子們的證件,卻要以犧牲那些匈牙利人為代價。這讓我無法接受。
保持清醒,時間越長越好,和睡眠做鬥爭。算法其實很簡單:一個小時我能做三十張空白證件;如果這一個小時我用來睡覺,就會有三十個人因此而死去……
經過兩個晚上無止境的痛苦工作,我的眼睛幾乎快要貼到顯微鏡上——疲勞成了我最大的敵人。我得一直屏住呼吸,偽造證件是一項只有一絲不苟才能完成的任務——你的手甚至不能有一點抖動,是非常精細的工作。哪怕一瞬間的注意力不集中都會是致命的,因為每一張證件都生死攸關。每一頁我都會一遍又一遍地檢查,哪怕它們已經很完美了,我還是會擔憂。那就再檢查一遍。
壓力雖然消失,但更糟的是,我已經在打盹兒了。我站起來想讓自己精神一下,在屋裏走了幾步,甚至扇了自己幾巴掌,然後重新坐下。一個小時等於三十條人命!我沒資格放棄。我眨了眨眼,然後眯起眼睛讓自己看得更清楚。到底是我把這些東西印模糊了,還是我的眼睛在這暗室的微弱燈光下已經什麼都看不見了?
第三天,聖佩雷斯街的實驗室裏充盈着一股激動的情緒。
我們就要完成任務了。下午五點,水獺和睡蓮就會帶着我們做好的所有證件出發,這是我們三天來不眠不休勞作的成果。**當我們這天早上已經完成八百多份證件的時候,我終於開始有信心了。**所有人都像機器人一樣,瘋狂重複着同樣的動作,我們以熟練的手法不停歇地工作,速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快。我們的衣服早已變得油膩,散發着化學品的刺鼻味道,身上全是汗,不過這一天空氣中卻散發着一種新的氣息,有什麼無形的東西飄在空中。那是狂喜!**我們大聲地喊出一個個數字來為自己鼓勁:****八百一十、八百一十一、八百一十二……**伴隨着打字機不間斷且有節奏的嗒嗒聲、切紙機的撞擊聲、蓋章的砰砰聲、訂書機的咔嗒聲,還有紙張做舊機器低沉的隆隆聲。
正當我沉醉於各種操作的旋渦中時,我突然感到眼前一黑,緊接着,就在那一瞬間徹底暈了過去。我眨了眨眼,又眯了眯眼睛,但無濟於事。感覺眼皮很沉,沒有知覺,眼前一片漆黑。我的聽覺被一陣持續的嗡嗡聲所取代,雙手麻木。感覺身體一下子不再受自己的控制。
我再也無法支撐自己,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再次醒來時,我發現自己躺在地板上,蒙着眼罩。睡蓮把我帶到了住在附近的一個聯絡員的家裏,以便有人照顧我。我很擔心會因為自己不在而導致證件無法及時完工,堅持要他們別讓我睡超過一個小時。我還記得睡蓮當時説的話,這句話把一種對他人生命的責任感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裏:“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證件偽造者阿道夫,而不是另一具屍體。****”
△ 如今阿道夫 · 卡明斯基對世界的期待:“眾生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