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醫藥產業的黑歷史:用收容所兒童進行殘酷實驗_風聞
德不孤-新闻搬运工2019-12-15 10:33
來源:文匯書摘 2019-12-02
【導讀】在如今風光的美國醫藥產業背後,曾有着不堪的黑歷史,早年的美國醫學精英們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用社會地位、種族、身體與智力上的缺陷的兒童作為醫學實驗的樣品,而當時美國的貴族、社會名流以及各行各界精英們對此覺得理所當然。一位用遲鈍兒童、囚犯和窮困的老年人長期進行臨牀實驗的美國醫學工作者後來懷念道:“從沒有人過問我在做什麼,真是一段美妙的時光。”這種現象直到1960年代中期,美國國內才開始有人提出質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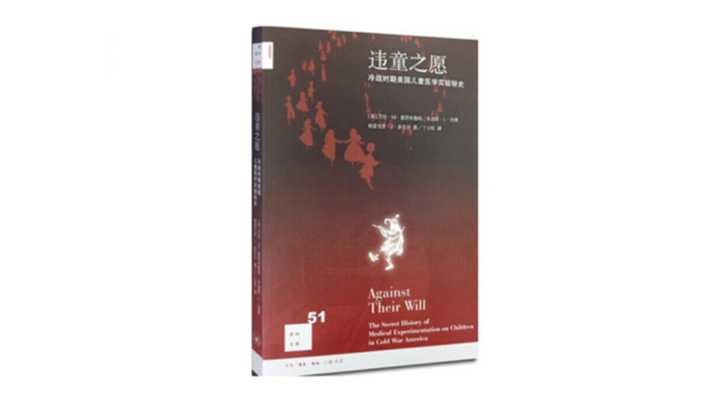
1929年春夏,全美國最為傑出的三名科學家打算為紐約市郊某州立“低能兒”收容所的一個十三歲的“先天愚型侏儒”實施預謀已久的閹割手術。
這場非治療性的手術由美國頂尖優生學家與優育倡導者查爾斯·本尼迪克特·達文波特主刀,他的不懈努力將“純粹的偏見帶入到嚴格的社會等級中”。達文波特的行為得到了畢業於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的知名醫生、外科手術技藝精湛的喬治·華盛頓·科納,以及出身耶魯的科學家、細胞學專家西奧菲勒斯·H·佩因特的協助,後者還在隨後進行了組織培養分析。
1920年代時,將收容機構裏的孩子用於探索性方法、調查性治療以及實驗性預防法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在美國,像達文波特這樣的重要優生學家給這些囚禁於經營不善、人員不足的國立或州立收容所、醫院和孤兒院的孩子們貼上了無價值羣體、人類棄子的標籤,因此有顯著必要了解他們這羣人的特性。在優生學領域,有些人認為這些孩子同樣可以作為科學研究的“素材”——用於與他們自身的狀況不相關的方面。
隨着時間的流逝,收容所兒童越發成為了犧牲品,研究者們紛紛尋找他們作為實驗素材。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後來的冷戰進一步加大了對實驗素材的需求。牢牢把持着身心缺陷兒童的研究“志願者”和收容機構因其自身的便利條件、與世隔絕乃至低廉要價而成了香餑餑。許多研究者都把這些機構看成老天的恩賜,而且要多少有多少。
在醫學研究領域,功利主義、家長主義和精英主義的觀念一直普遍存在着,但是美國對優生運動的狂熱,以及身陷兩大國際衝突之中的事實,也使開發型研究實驗變得更為必要。有了這樣強有力的理由作為支持,部分曾經宣誓絕不傷害的醫生開始屢屢違背從前的誓言。幾乎沒有人站出來反對這種狀況。
一直以來,查爾斯·B·達文波特就醉心於與遺傳障礙相關的任何知識,“先天愚型侏儒”更是他關注的重點。他曾對萊奇沃思低能兒收治所的主管説,這種病症來源不明,且一直被認為是無藥可醫的,通過對“矮生植物與昆蟲”的研究,他發現了一種可能的方法,這讓他越發相信“先天愚型侏儒也許是染色體複合異常造成的”。
他需要用人做實驗來驗證自己的假設,而且他完全清楚去哪兒能搞到實驗體:有一家專門收容缺陷人羣的機構,他已經在這一領域鑽研多年。他在書面申請中對機構主管説,是時候“對先天愚型人的分裂細胞相關染色體檢查一番了。唯一確定能夠觀察到細胞分裂的器官就是睾丸。而在適宜條件下獲得該固定染色體的組織,從而對其進行觀察的唯一途徑,就是閹割”。
達文波特堅信,對這一科學難題的探索完全合情合理,而對先天愚型兒童進行閹割則“對解決這一難題大有裨益”。申請很快就獲得了許可,包括這個孩子的單親父母、收容機構主管和研究者在內,沒有任何人對這種以獲取知識的名義來閹割兒童的行徑提出異議。
直到19世紀末期,在布魯克林藝術科學學院任教期間,達文波特創辦了一間生物實驗室,專門對長島某片叫做冷泉港的繁茂沼澤區當中的原始海洋哺乳生物進行研究。一邊翻暗礁、挖牡蠣,觀察各種生物羣落,他又一邊開始認真鑽研優生學創始人弗朗西斯·高爾頓的理論。他被高爾頓的觀點深深地吸引了,而這對大洋兩岸的科學與觀念都不是個好兆頭。
高爾頓出身于傑出的達爾文家族,一直就被人寄予厚望,但他平庸的學術生涯讓人們對他不再抱有任何幻想。然而,他的漫遊癖和永不止息的好奇心卻讓他成為了一名環球旅行家、自學成才的地理學家,還因卓越貢獻獲得了皇家地理學會金質獎章。
但是,他對人類差異性的與生俱來的好奇心以及對數學的熱愛促成了他在遺傳方面最具爭議的科學發現。高爾頓猜測,敏鋭的觀察者能夠由人類多樣性中的累計差異推導出的數學形式與趨勢,預見在時間推移中,一個給定人口數某特定變量的變化,比如身高、體重或智力等。不僅如此,當龐大人羣中存在多方面的巨大差異時,人羣的代際差異就會變小。對高爾頓來説,遺傳不僅體現在人的眼球顏色、身高等自然特徵上,也體現在人的心理和情感素質上。一個人具有創造性或總是慢吞吞,都是遺傳的結果。對遺傳,尤其是1860年代英國顯赫家族的天賦遺傳思考得越多,高爾頓就越發堅信,科學與數學才是發現生殖秘密的鑰匙,一旦瞭解了其中的奧妙並得其要領,人類將會獲得永久的飛躍。簡而言之,“不受歡迎的就拋棄,受歡迎的就多多益善,這樣難道不好?”
和19世紀最後二十幾年的許多人一樣,高爾頓的腦中盤旋着無數關於種族淨化和完善人類的疑問。1883年,他出版了《探求人的能力及其拓展》;又經過數年對其遺傳理論如何命名的權衡,他最終選擇了將兩個希臘語詞彙“eu”(良好,優秀)與“genes”(出生)合而為一,造出了“eugenics”(優生學)這個詞。這一詞彙將會迅速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並最終在五花八門的形式、政策與事務中變得面目全非。
在高爾頓看來,無論是被叫做種質、原生質或隨便什麼名字,這種使生理和心理特徵產生代際遺傳的關鍵所在,就是遺傳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他跟同時代其他人並未真正理解遺傳性狀是如何傳遞的,但他們知道一個人的種質合格與否與其環境和生活質量幾乎沒有任何關聯。
高爾頓表示,他對那些不合格家族的悲慘境遇並非冷酷無情,但他同時也認為,想要社會進步,就必須對這類不合格因素加以遏制和淘汰。雖然他沒有説看不起那些疾病纏身和生活不幸的人們,但他確實主張把這些人羣隔離開來,從而讓這些可能產生“墮落者”的家庭終止繁育。
19世紀最後二十年裏,對特定人羣的妖魔化和污衊不僅獲得了廣泛支持,其合法性也日漸完善。高爾頓強調應該將從社會最佳代表那裏的收穫最大化,他還主張對那些最沒有社會地位的人加以限制,比如通過嚴格控制婚姻許可,來避免基因缺陷人羣形成等。20世紀早期,這項運動不僅在社會中生根發芽,更使社會籠罩上一層更加黑暗沉重的光暈。高爾頓的強調通過生物學上有益的婚姻來拯救社會的“積極優生學”,很快就被“消極優生學”所取代,後者強調通過激烈手段與政策,對基因不合格者,如果不能消滅,就要加以控制——凡是被判定為心理衰弱、種族墮落或非原生北歐日耳曼血統的人都在此列。而那些基因低劣的人則受到了更加粗暴的對待。
自1883年高爾頓造出了“優生學”這個單詞才過了十年,美國醫生兼瘋人院主管霍伊特·皮爾徹博士,閹割了堪薩斯州温菲爾德低能與弱智兒童收容所的近七十名男孩。皮爾徹的前任主管曾經連續多年對該機構中“確診手淫患者”的病人們無償施以行之有效的救助。就任瘋人院主管伊始,在“對這一課題進行一番理性審視”後,皮爾徹着手鑽研能夠終結此種連綿不絕的惱人問題的“臨牀療法”或解決方案。他相信自己已經通過外科手術發現了答案,那就是閹割。
皮爾徹的行為讓許多堪薩斯人感到恐懼,但醫學團體卻呈現出支持的態度,甚至表現得非常積極。某州立醫學期刊稱,對皮爾徹的“猛烈”攻擊完全是盲目的誇大其詞和“政治恐嚇”,還説“醫學領域對閹割的熱情日益高漲”,將其當成遏制疾病與犯罪的雙重利器。該文章中還表示,向公眾“傳授”這一觀念迫在眉睫。
其他醫生們迅速聲稱,閹割對各種疾病和社會問題都有奇效。1897年在費城舉行的美國醫學會會議上,埃弗雷特·弗洛德教授對同行們説,馬薩諸塞州鮑爾德温鎮一家收容所的二十六名兒童才被實施了閹割。弗洛德説:“最初施行閹割只是抱着減少手淫這種頑疾的想法。”這位醫生寫道,一個男孩“不知廉恥,確診為癲癇,而且多少有點弱智”。弗洛德説在獲得了兒童父母的許可後,一位外科同僚實施了手術。這些實驗性手術的效果出乎意料地好,弗洛德説道,因為“每一例手術後,手淫症狀都停止了”。與此同時,閹割後的兒童都變得“面色更加平靜”,多長了“不少肉”,變得“更可控”,表現得更好、更誠實了。弗洛德指出,最後同樣值得關注的是“他們把缺陷遺傳給後代的可能性被徹底消除了”。
19世紀的最後十年,科學領域催生出了大量為了優生進行閹割和絕育手術的能手,哈里·C·夏普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印第安納州教養所的一名外科醫生,並在這場絕育運動中成為了一名直言不諱的領導者。夏普就普遍存在於美國社會的日益加劇的缺陷種質問題進行了大量的寫作與演講。他所謂擺脱缺陷種質的“直截了當的方法”就是絕育手術。緊接着他又講到,他給四十二名青年男子做了絕育手術,當中有些人只有十七歲。他還説,為了確保這些人不會成為罪犯和社會的蛀蟲,他一定會為更多成百上千的人進行絕育。夏普對自己的結論十分滿意,他堅稱“激進的方法是必要的”,並鼓勵醫生同行們向當職官員施壓,讓瘋人院、監獄和智障收容機構的主管將每一個收治其中的男性病患都執行絕育。
同行們對夏普的文章基本上都給予讚許,從庫班麻風病人聚居所到俄亥俄監獄的主管們都對他表示支持。事實上,夏普還曾打算競選美國國家監獄協會的醫師協會主席,通過這一職位他就能擁有更大的權威宣傳其理論。醫學領域有越來越多的人宣揚絕育手術的可行性與實用性,而夏普也不過是其中之一。在1880年到1900年間,醫生們撰寫了大量推崇“通過絕育實現社會約制”的文章,大多都持同一種論調,即譴責犯罪率增長、關押犯人成本提高以及對病人術後表現出的勤奮、雄心勃勃與快樂進行滿懷自豪的高度讚揚。
越來越多的醫生參與表態,有些也因此聲名鵲起。一位聲望頗高的外科醫生威廉·T·貝爾菲爾德博士在1907年12月的芝加哥醫生與律師俱樂部會議上籤署通過了優生學與大規模絕育手術政策。他的發言很快在新墨西哥州醫學會期刊上發表,強調説美國兇殺案發生率急劇上升,已經“比倫敦高出三十三倍”。貝爾菲爾德敦促伊利諾伊州的立法者儘快通過與其時剛通過不久的印第安納州法律類似的絕育法案;其他人也紛紛進行類似的遊説活動。
新澤西州癲癇病人之家主任醫師大衞·威克斯博士、弗吉尼亞州立感化院首席外科醫生查爾斯·卡林頓,以及加利福尼亞州立精神病院委員會秘書長F·W·哈奇博士,都積極撰文、遊説,或用萬能的優生理論試圖治癒美國的“社會痼疾”。有些優生學擁護者,如萊維利斯·F·巴克爾和G·弗蘭克·林德斯頓等,他們不單是各種機構的主管,更是醫學界的首要人物。巴克爾是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的首席醫師;林德斯頓則是伊利諾伊大學泌尿生殖外科專業的教授,極力主張通過醫學抵制非優生羣體——南歐移民——而且恬不知恥地對這些觀點大加鼓吹。他不僅提倡對強姦犯進行閹割、對不良羣體(癲癇、酗酒和肺癆患者)施行絕育,還建議用毒氣室“把殺人犯和愚蠢的低能兒都殺掉”。巴克爾和林德斯頓的文章,尤其是被《美國醫學會期刊》和《紐約醫學雜誌》發表過的那些,讓當時許多美國人意識到,優生學手術已經獲得了專業領域的認可。……
直到1940年,拿收容人口當小白鼠的情勢終於發生了改變,卻是由相對小規模的行業內部行為,轉化成了政府出資、高校資助的成熟的現代醫學支柱。(摘自三聯書店《違童之願》)